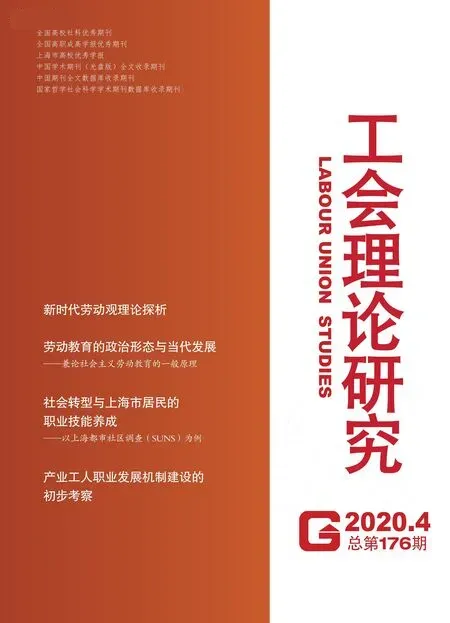冲突与安全:民国时期上海徽州墨业罢工事件研究
2020-03-11张剑
张 剑
(安徽师范大学 历史与社会学院, 安徽芜湖 241002)
对于“历史”而言,它或可理解为“三个面相”,①笔者按:对于“历史三个面向”的论述,是笔者对于历史研究之感悟,不当之处,请大方之家多多指正。其一为“历史的本身”,即浑然一体的历史全部;其二是“现存的历史”,即现存已知的或者将来能知的文献、遗迹等被留存下来的历史(历史资料);其三是“研究的历史”,即研究历史的人员依靠掌握的研究方法、研究手段对上述两个面相进行研究而形成的历史(历史研究成果)。在历史的建构中既有徽商之类的“大历史”,也有上海徽州墨业罢工之类的“小事件”。微小如苔花的“小事件”总是缺乏足够的关注,对此,刘石吉教授(以下简称“刘文”)和罗士洄博士(以下简称“罗文”)有所论述。“刘文”是以“近代中国城市手工艺工人集体行为”为研究视角,概述了徽州墨业罢工事件的经过,分析了当时社会对以徽州墨业工人为代表的近代手艺工人的抗议形态及其历史意义。“刘文”的论述重点揭示出“近代城市手艺工人与传统农村社会的共生关系”,②刘石吉:《一九二四年上海徽帮墨匠罢工风潮——近代中国城市手艺工人集体行动之分析》,载《江淮论坛》,1989年第1期,第65页。同时也展示了传统行会制度的没落和现代工会组织的萌芽。“罗文”则是以社会史的视角,展示“徽墨”作为器物的社会生命,将徽州墨业罢工事件放入“墨业纠纷”的视域,极为简单地阐释了墨业罢工之情况,认为“来自墨工的罢工,实则是墨业在整个社会变迁过程中必然出现的一个社会现象,无论墨工还是墨店主,都在承受这一传统产业走向衰落的阵痛”。①罗士洄:《物的社会生命:徽墨的社会史研究——基于个案的历史分析》,载《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2018年第4期,第71页。就专著而言,有唐力行先生对于徽州墨业罢工事件进行研究,唐先生将徽州墨业罢工事件置身于“同乡会”学术研究背景下,以“徽州墨业罢工事件”来展示徽州“同乡会”在“调解劳资纠纷”中的作用,认为“同乡会从同乡的角度出发,秉持致力于劳资调节的立场,最终使双方达成妥协”。②唐力行:《延续与断裂:徽州乡村的超稳定结构与社会变迁》,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202页。由此可知上海徽州墨业罢工事件有深度挖掘之潜力与必要。正如吉霞所认为的那样,“在人们追求大历史时,我选择了‘小历史’”。③吉霞:《中国小史丛书·中国古代堪舆小史·主编絮语》,北京:中国长安出版社2015年版,第208页。“小历史”在某种程度上而言就是一个个“小事件”的组合串联。因是“小事件”,故可穷尽史料。在史料相对富集的基础上对“小事件”进行客观而细致的分析,对找出历史的真相,还原历史面貌具有标的作用。这是开展上海徽州墨业罢工事件研究的根本原因。
本文将以民国时期主要报刊中的史料为重点,对上海徽州墨业罢工事件进行深入探索,并对刘文中提及的相关内容进行补充,同时对上海徽州墨业罢工事件形成原因及其影响进行解析,期以上海徽州墨业罢工事件此类的“小事件”来折射徽商之“大历史”。
一、对刘石吉教授关于上海徽州墨业罢工事件相关问题的补充与商榷
依现有史料,中国近代史上关于上海徽州墨业罢工事件总计有三次,分别在1913年、1924年、1936年。其中以1924年之罢工事件持续时间最长,过程亦最为曲折。
“刘文”对1913年上海墨业罢工事件略有提及:“1913年3月间,墨工第一次集体罢工要求加资的奋斗中,取得了几乎全体墨店的同意……”④刘石吉:《一九二四年上海徽帮墨匠罢工风潮——近代中国城市手艺工人集体行动之分析》,载《江淮论坛》1989年第1期,第61页。“刘文”的“一笔带过”不经意间留下了可深入思考之契机。关于1913年上海徽州墨业罢工在《上海公报》和《申报》上均有记载。
如据《上海公报》的“(吴知事)批具呈人墨业查贵生、查旺丁等呈请酌加工资给发示谕”条中说:
“据呈向章墨业做手,每工银四分,敏捷者每日二三工亦有,现共墨店十余家每工允加一分,唯詹有大成记不允。今已停工五日,请为传谕遵照,并给示等,请察核案有所云……而察查贵生、查旺丁均系二妙堂墨店做手,何以干涉詹大有成记之事?詹大有亦有做手,何以并不列名?可见所陈各节显有不实不尽。……一面饬吏传知各工人,即日照常工作,必须一律开工方可,劝导各店主酌量体恤,否则同罢工干犯刑律……”⑤《批具呈人墨业查贵生查旺丁等呈请酌加工资给发示谕》,载《上海公报》,1913年2月25日。
由此则材料可知,1913年上海确有徽州墨业罢工之事件,且墨业罢工事件已经在政府层面进行处理。作为墨工一方,其“加薪”的要求被大部分墨店主所接纳,并允已执行,但是詹大有成记不予执行。正是詹大有成记之不配合才有了“吴知事”的批示。作为政府代表的“吴知事”对于墨业罢工事件的态度甚为“恶意”,他怀疑墨工的诉求有“不尽不实”之处,并且“痛恨墨工之要挟”,但“吴知事”的处置方式又以“居中调和”为主,望“墨业罢工”此事能尽快处理,并对墨工和墨店主都施以压力。但在六天之后,“吴知事”对墨业罢工事宜的态度有所变化,反而对墨店主施加重压,要求他们“酌加工资”,以安墨工。
如据《又批墨业查贵生等呈遵谕开工请饬传》条中说:
“……本知事只有劝导之责,无代为允许之权。应俟定期传集各店主,察酌商情,饬令议复,再行饬遵,尔等务各安营生,静候核示……”①《又批墨业查贵生等呈遵谕开工请饬传酌加工资以安生业》,载《上海公报》,1913年2月25日。
此则材料清晰展示在1913年徽州墨业罢工事件中政府之态度。政府代表“吴知事”虽然口称“无代为允许之权”,但要求“各店东”静候核示,静候如何之核示呢?静候“酌加工资以安生业”之核示也。刘文中对于1913年之上海墨业罢工之描述仅从墨工、墨店主之视角,此则材料则增添了政府之角色,使此次上海徽州墨工罢工之情况更为全面与立体。
关于1936年上海徽州墨业罢工事件,刘文中并未提及,特补充如下:
如据《婺源帮制墨工人罢工 反对资方减低工资》条陈说:
“……最近又议将原有每工工资,减为每工法币八分,全体工人表示不愿,纷请制墨工会函请笔墨同业公会,要求资方维持原约,发给工资,但迄无结果。致引起全体工人不满,于昨日起自动罢工……”②《婺源帮制墨工人罢工(反对资方减低工资)》,载《申报》,1936年3月6日,第11版。
又据《婺帮制墨业工潮(昨有一部份复工 未解决者静候党政调处)》条陈说:
“……该会奉令后,即进行调处,兹悉郎桂山、时永有等墨店资方,体恤工艰,已允仍照原有工资发给。故该两店工人昨已复工,照常工作,其他未解决各店正听候上级依法调解云……”③《婺帮制墨业工潮(昨有一部份复工 未解决者静候党政调处)》,载《申报》,1936年3月9日,第9版。
由此两则材料而知:1936年上海徽州墨业罢工事件虽在细节上有所缺失,但大体可知其情况。此次上海徽州墨业罢工的时间为1936年3月5日,罢工原因是“原有每工工资,减为每工法币八分”,墨店主如此做法既违背1927年签订的墨业工资协议(此协议是1924年墨业罢工的重要成果之一,在后文将有论述,此处不提),更是置墨工权益不顾,引起工人愤慨。从最终结果看,有部分墨店如“郎桂山”“时永有”按照原来的工资标准发给墨工,但仍有部分墨工因工资问题并未复工。限于史料,此次上海徽州墨工罢工事件的最终结果未能确切展示,故用“婺帮制墨业工潮 昨有一部份复工 未解决者静候党政调处”此标题作为指示性结果。
在刘文开端之处便提及:“1924年5月31日之7月28日,旅居上海的安徽婺源帮制墨工人发动了一次规模不大……过程又极为复杂曲折的罢工运动”。④刘石吉:《一九二四年上海徽帮墨匠罢工风潮--近代中国城市手艺工人集体行动之分析》,载《江淮论坛》1989年第1期,第60页。同时在“罗文”中也提及“1924年5月31日……婺源墨工朱润斌……余包杰⑤笔者按:“余包杰”应是“余宝杰”,在1924年6月15日的《时报》上有明确记载。等为首的徽帮墨工……向店主二妙堂等数十家要求增加工资……拉开了此次罢工风潮的序幕”。①罗士洄:《物的社会生命:徽墨的社会史研究——基于个案的历史分析》,载《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2018年第4期,第67页。在“刘文”和“罗文”的论述中都以1924年5月31日作为上海徽州墨业罢工事件的起点。另外唐力行教授认为,墨业罢工的开始时间是“6月9日”,②唐力行:《延续与断裂:徽州乡村的超稳定结构与社会变迁》,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197页。唐教授并未对此时间做出说明,不知何证?刘教授和罗博士以此上海徽州墨业罢工实践之日作为开端,诚然不错。但是此次绵延两月的上海徽州墨业罢工事件并不是偶然猝发,它是工人经过酝酿、具有高度组织性的事件。早在1924年5月6日《申报》上就登载了《旅沪婺源墨业工人之呼吁》一文,原文摘抄如下:
致皖同乡会函
“……安徽同乡会诸位执事先生台鉴:……夫吾墨店皆手业行,所盈余之□(钱),虽东家□(鸿)运,亦吾工帮同做起来,当患难相共,与狼狈一般。东家无我工人,亦不能余钱。论□□(其工)俸,每有不过八九元之数,早六点□(钟)就要起来,晚一点余钟歇手。论其吃食,每人每日只有二十文菜,监(盐)油在内,上海手业工人,□(算)墨作最苦……吾等三百余工人,皆抱不平,候同乡会开会之日,伏惟执事先生公直正断处置店东,改良待遇,以雪吾等之恨也。”③《旅沪婺源墨业工人之呼吁》,载《申报》,1924年5月6日,第14版。
在这不足六百字的会函中,满纸皆是上海徽州墨工对墨店主的控诉。墨工每天几乎要连续工作近18个小时,而其工资仅有八九元钱,且伙食仅是“二十几文的菜”,医疗等待遇更是无从说起。墨工竟用“雪吾等之恨”的字眼来进行呼吁,可见墨工之苦大仇深。上海徽州墨工的呼吁或可认为是1924年徽州墨业罢工事件的前奏。
前文提及此次上海徽州墨业罢工有组织性,那是否有进步人士④笔者按:“进步人士”是指“热衷于进步和改革的人,特别是指进步团体的成员”,如热衷于推翻清政府,改变旧中国的人。下同。在鼓舞推动呢?当时“护军使属”⑤笔者按:“护军使属”的意思是“护军使”属员。“护军使”是官名。北洋军阀政府于1913年设置护军使,并颁布《护军使暂行条例》。北洋政府任命的护军使分为两种,一种是没有军政长官的省区,而一种则是有军政长官的省区。没有军政长官省区的护军使最为简单,他们能够节制全省的军队,与督军、都督或将军无异,都是一省的最高军政长官。例如,曾担任吉林护军使的孟恩远,在张作霖崛起之前,他就是吉林省的最高统治者;至于有军政长官的省区护军使,则一般只能享有本省的部分地盘。例如在上海地区设置的淞沪护军使,一般管辖的区域就是上海滩一地。不过,虽然名义上护军使职位在本省军政长官之下,但实际上,护军使是否听从本省的军政长官,完全根据护军使的实力。实力强劲的护军使完全可以自行其是,将本省军政长官撇在一边。因此就本文中而言,“护军使属”就是上海淞沪军护军使属员,他一定是当时上海军方之代表,但未必是当时政府之代表。但若从“大政府”视角看此,或可被广义地理解为“政府代表”,特此说明。下同。曾怀疑“该工人方面犹复拒绝上工,显系有人从中鼓煽,冀图扰乱治安,情殊可恶,究系何人鼓动?□即密拿讯办,以维地方”。⑥《墨业罢工潮又成僵局(店主不受调处、工人相率出厂、韩国钧之压力)》,载《时报》,1924年6月28日。然“上海警察厅陆厅长”①笔者按:此“上海警察厅陆厅长”,从时间上来推理,可发现陆厅长可能是被王亚樵刺杀的徐国梁厅长的继任者。(徐国梁厅长于1923年11月10日遇害,陆厅长之言论是发生于1924年6月28日,由此而推断,然证据不足,难以确认,以待来者。)则肯定“该工人尤复坚执如故,虽保无人从中鼓励,久不解决,隐患堪虞,仰仍设法双方劝导,以期和平了结”。②《墨业罢工潮又成僵局》,载《民国日报》,1924年6月28日。“陆厅长之肯定”与“护军使属之怀疑”给笔者留下了思索之空间。鉴于此,翻检现有史料,寻根问底。从1924年墨工罢工事件之经过来看,更倾向于“陆厅长之肯定”。在此事件中有所牵连的进步人士是徐锡麟和詹效伯,③笔者按:关于徐锡麟,并非是近代史上我们所熟知的人,乃是新出现的徐锡麟,其事略不详。对于“詹效伯”我们所知道的信息也较少,只知他是民国第一杀手王亚樵的手下,也是上海斧头帮的骨干成员,与朱善元等为兄弟。曾经接到任务刺杀上海警察厅厅长徐国梁。其相关之记载在王亚樵的传记中被提及。且徐锡麟曾“报告墨业工友组织工会”④《工团联合会委员会纪》,载《申报》,1924年5月30日,第12版。之事宜,且徐锡麟之报告之时间为1924年5月30日,正是此次上海徽州墨业罢工前一天,似乎契合进步人士鼓动之时间条件,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徐锡麟和詹效伯之所以与徽州墨业罢工牵连甚深,主因是他们乃工团联合会推举调停徽州墨业罢工之代表,“即派代表詹效伯、徐锡麟至该店(老胡开文墨店)调查,面见该店店主胡君,他允明日调解”,⑤《绩溪帮墨工之影响》,载《民国日报》,1924年6月10日。可知徐、詹之代表身份。但在三天以后,徐、詹两人因罢工代表之身份陷入麻烦,“前日工潮代表徐锡麟、詹效伯至小东门詹大有成记墨做接洽该店主不受□□(调解),双方□□(僵持)。店主诳报警署,谓此次工潮系徐、詹所主□(谋),警署将徐、詹二代表□(备)文送□(警)察□(局)”,⑥《墨业店主太忍心、诳报警署、拘留工团代表》,载《民国日报》,1924年6月13日。詹、徐两人因被詹大有成记墨店老板诬陷而身陷警局。对于詹、徐之被诬陷,工团联合会对此甚为愤怒,致函警厅陆厅长:
“一区二分所杨贵署员竟听一面之词,将敝会代表送押贵厅两日之久。方始释放。损失敝会名誉可尔蔑以复加……近管贵厅属员之行动,出乎寻常情理之外,深为不解。为此而请贵厅对于无辜拘押敝会代表损失名誉之处,贵厅如何辨理……”⑦《工联会致警厅函》,载《民国日报》,1924年6月14日。
由此而知,詹、徐作为工团联合会墨业罢工之调停代表,在工作不到三日之情况下就被詹大有成记墨店主诬告而身陷囹圄,于情于理都不会是上海徽州墨业罢工之幕后推手。再者有一旁证也可说明此点:
据《时报》中“墨工上工后续闻(函谢工团联合会)”条陈说:
“……贵会徐、詹诸公侠肠毅力,拯救无告。凡在工人感德难忘。兹推代表朱润斌趋前叩谢,乞赐接洽为荷……”⑧《墨工上工后续闻(函谢工团联合会)》,载《时报》,1924年7月30日。
这是墨业罢工首领朱润斌的感谢函。此时已是1924年7月30日,上海徽州墨业罢工已然结束。从感谢函之内容来看,詹、徐二人也仅有“调停之功勋”,实无其他之效力。因而1924年徽州墨业罢工事件并无进步人士涉入其中。
根据红外热成像数据可知,电池爆炸燃烧温度在550~600℃范围内,且电池发生爆炸后随着喷射物的耗尽,电池周边温度迅速降低,但是电池壳体温度仍然较高。
但可肯定的是此次墨业罢工具有组织性。从5月6日“徽州墨业工人之呼吁”,到徽州墨业工人“组织工会,推出各店代表三十二人筹备一切”,①《制墨工人加薪潮(昨日提出条件)》,载《时报》,1924年6月1日。并“召集代表会议,讨论第二步手续办法”②《墨工要求加薪之昨讯》,载《时报》,1924年6月5日。中可见此特点。
由此可知,1924年徽州墨业工人罢工事件是由墨工自行组织,酝酿策划,且坚持不懈,运用多种斗争形式(如致函寻求帮助、积极配合调停、改业别图、暂借徽宁会馆住宿等),最终取得胜利的罢工事件。正因墨业工人的组织性才有此次徽州墨业罢工能够持续两个月且取得成功。
“刘文”认为1924年上海徽州墨业罢工事件,其开始时间为5月31日,诚然不错,但忽略了墨业工人组织性的特点。1924年上海徽州墨业罢工事件至少可以从5月6日算起。
另1924年徽州墨业罢工事件的结束时间,“刘文”认为是“7月28日”,此可能是刘石吉教授之疏忽,因为在7月27日上海徽州墨业罢工事宜已完全解决,这一点唐力行教授也是甚为认可,他认为上海徽州墨业罢工“至7月27日结束”。③唐力行:《延续与断裂:徽州乡村的超稳定结构与社会变迁》,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197页。
再如《申报》的“墨业工潮完全解决”条陈中:
“店主已允即日加资,婺帮墨工自迁出全皖会馆,全体回店。上工相持二月之工潮,业已告一段落……”④《墨业工潮完全解决》,载《申报》,1924年7月27日,第15版。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7月27日上海徽州墨工罢工情形虽全部结束,但墨工要求并未全部实现,特别是7月27日至8月15日之间的工资待遇问题未能达成一致。“多数店主对于八月十五始行加资一层可予通融”,⑤《墨工业工人昨已上工(工人致谢全皖会馆)》,载《申报》,1924年7月26日,第14版。徽州墨业工人为回应墨店主之善意,“于昨晨七时商议,结果遂全体迁出会馆,计上工者七十三人,其余十一人均因他故暂缓上工,并移住他处,日用仍由同乡筹给……”⑥《墨工业工人昨已上工(工人致谢全皖会馆)》,载《申报》,1924年7月26日,第14版。且因“墨作出货本甚稀少,故各工人除在清晨工作三四小时,下行(午)多停工歇息”,⑦《墨业工潮完全解决》,载《申报》,1924年7月27日,第14版。可见墨业工人已在履行其责。且墨工于7月27日虽“有十余人因故不能上工”,⑧《墨业工潮完全解决》,载《申报》,1924年7月27日,第14版。但确实是因“自身以深受痛苦,不愿再行上工”,⑨《墨业工潮完全解决》,载《申报》,1924年7月27日,第14版。其余墨业工人都履行约定按时上工。7月27日至8月15日之间所得工资也是罢工之后的“新工资待遇”。事实上墨业工人之复工却给墨店主带来再次剥削之借口,墨店主认为“工人此次系自动上工,对于加资实行期间仍声明照□(旧)论规定”,⑩《墨工上工后闻(加资期间之波折、函谢祁门同乡会)》,载《时报》,1924年7月29日。即使“加资时间问题,尚未妥洽。但各工人为息事宁人起见,不愿有所表示,静候各调人之公判”。⑪《墨工上工后续闻(函谢工团联合会)》,载《时报》,1924年7月30日。限于史料,无法得知最后上海徽州墨业工人在7月27日至8月15日之间的工资待遇是如何“公判”,但至少推知当年上海徽州墨业工人想要解决工资待遇问题之艰难,墨业工人罢工成功之不易。这虽是历史进程中的“小事件”,在浩如烟海的历史事件中可谓微尘,但微尘虽轻如鸿毛,其所承载历史要素确是重如泰山。
关于1924年上海徽州墨业罢工事件,笔者认为1924年徽州墨业罢工事件的起讫时间为5月6日至7月27日,总计约有婺帮墨工四百余人、①《工人代表向军署请愿》,载《时报》,1924年6月15日。绩溪帮墨工十余人,②《绩溪墨工之影响》,载《民国日报》,1924年6月10日。两者相加至少410余人参加此次罢工,如若再加苏杭地区的婺帮墨工五十余人,③《苏杭墨业罢工》,载《时报》,1924年6月23日。在1924年苏浙沪地区至少有460余人的墨业工人进行罢工。另外此次上海徽州墨工罢工事件虽是由工人自行组织发动,但其具有严密的组织性和计划性。不管是罢工事件的酝酿阶段呼吁全体墨工罢工,还是墨业工人罢工“五项条件”④《制墨工人加薪潮(昨日提出条件)》,载《时报》,1924年6月1日。其五项条件具体内容为:“一是春节每月工作不得超过百工之外(每工即每墨一件);二是增加工资,每工照原有工资改为纹银一钱二分;三是菜钱改为大洋五分,月规酒资每月三角;四是工人遇有疾病时须有相当补助,备工人调养、医治;五是店主不得虐待工人,以及开除工人。”的提出;不管是有组织要求“墨工全体一致罢工”,⑤《墨工有今日罢工说》,载《时报》,1924年6月8日。还是到“警厅请愿”;⑥《工人代表向军署请愿》,载《时报》,1924年6月15日。不管是墨业工人的“全体迁出(徽宁)会馆”,⑦《墨业工潮昨日解决(上工者工七十三人 工人致谢全皖会馆)》,载《民国日报》,1924年7月26日。还是墨业工人的全体回籍;⑧《墨工潮又有变化(全体工人决议回籍、苏杭墨工停工援助)》,载《时报》,1924年6月23日。不管是墨业工人的“暂住徽宁会馆”,⑨《墨业工潮之昨讯》,载《申报》,1924年7月6日,第13版。还是“墨业工人的纷纷改行”;⑩《墨业工人纷纷改业》,载《民国日报》,1924年7月1日。不管是“两次致董事领袖函胡靖畇”,⑪笔者按:墨业工人对于胡靖畇的致函,分别在1924年7月8日和7月10日。即《墨业工人之呼吁(函请胡靖畇允住徽宁会馆)》,载《时报》,1924年7月8日;《墨业工潮稍和缓(詹方寰预备开工、工人再致胡靖畇函、警厅饬谕加资)》,载《民国日报》,1924年7月10日。还是积极“参与警厅和同乡会的调解”;不管是“致谢函祁门同乡会”,⑫《墨工上工后所闻(加资期间之波折、函谢祁门同乡会)》,载《时报》,1924年7月29日。还是“致谢函工团联合会”⑬《墨工上工后续闻(函谢工团联合会)》,载《时报》,1924年7月30日。都能说明此点。
综合上述,上海徽州墨业的三次罢工在中国近代罢工史上只是“小事件”,但它也是“大历史”,是研究徽州墨业商人的重要对比点,此对比点使上海徽州墨业徽商研究更立体化和形象化。
二、1924年上海徽州墨业工人罢工事件之原因及影响分析
在历史事件发展的过程中总是潜藏着历史事件之成因,1924年上海徽州墨业罢工事件也是如此。“刘文”对1924年上海徽州墨业罢工事件之原因未做详细分析,只是稍有提及墨工要求加薪而墨店主未允准而有罢工事件,且对此罢工事件之影响也未作正面之阐述。故将1924年徽州墨业罢工之原因及影响分析如下:
(一)1924年徽州墨业工人罢工事件之原因分析
制墨业是我国古老的手工技艺,距今至少有三千年之历史,①王俪阎、苏强:《明清徽墨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2页。而徽州墨业因奚氏家族之努力,唐末已有发端。正是在奚氏家族的带动下,“徽州地区以制墨为职业者纷纷涌现,皖南歙州为中心的南唐制墨业蓬勃发展,从而奠定了宋代以至元明清徽州地区制墨的雄厚基础”,②王俪阎、苏强:《明清徽墨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20页。近代的徽州墨业依其强大历史惯性迁延发展,“上海的‘胡开文’……‘二妙堂’等墨店都是由徽人开设的,上海的徽墨贸易几乎成了他们的专利”。③张海鹏、王廷元:《徽商研究》,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3页。墨商因其历史因素而享受优厚“专利”。然上海徽州墨工又是怎样的待遇呢?墨工待遇乃是“订于光绪年间”,④刘石吉:《一九二四年上海徽帮墨匠罢工风潮--近代中国城市手艺工人集体行动之分析》,载《江淮论坛》1989年第1期,第61页。即“工人工僧(资)原为每工五分五厘,系以制墨担数为计工编着,每担自三十二至五十二不等。每月工作约自一百工至一百五十工之数”。⑤《墨工有今日罢工说(要求增加工资)》,载《时报》,1924年6月8日。略微合计,如按照墨工最大的工作量来计算,墨工仅可得8.25元工资,老弱病残之墨工实得工资应是更为微薄。如若工资水平低,且物价水平也低的话,这也无妨。但1924年上海“每个成年人每月伙食费4.6元,衣服费每月约3元,居住费每月2.3元,燃料水费每月2元,杂项每月费用7.7元”,⑥陈明远:《鲁迅时代何以为生》,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62页。初步计算可知,1924年上海成年人生活的基本消费为19.6元,是墨工的工资水平的两倍多,且墨工为获得此工资需要“早六点□(钟)就要起来,晚一点余钟歇手”。⑦《旅沪婺源墨业工人之呼吁》,载《申报》,1924年5月6日,第14版。故要求加资、改善待遇成为徽州墨业工人罢工首位的现实原因。
如若将徽州墨业工人罢工事件置于经济社会史背景之下,从其经济社会的“肌理”来分析,徽州墨业工人罢工是由“劳资冲突”造成。以徽州墨工为代表的“劳方”和墨店主为代表的“资方”同处于经济中,他们“因经济利益等诉求之不同互相冲突,又因互利而合作”。⑧田彤:《民国时期劳资关系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载《历史研究》,2011年第1期,第185页。这一点从徽州墨业罢工的起因、经过和结果等方面都有较为明显的体现。于徽州墨业工人而言,他们的罢工是“主动性抗议”,⑨(美)裴宜理,阎小骏:《底层社会与抗争性政治》,载《东南学术》,2008年第3期,第6页。这一行为“并非以纯生产关系作基础的‘阶级观念’为主导,反而常以生产服务的职业或行业整体利益作出发点,同时也渗杂着极为浓厚的‘乡土意识’和‘宗族血缘’感情因素”;⑩陈明銶:《晚清广东劳工“集体行动”理念初探》,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1期,第71页。于徽州墨店主而言,他们以“集体行动”⑪巫仁恕:《明末清初城市手工业工人的集体抗议行动:以苏州城为探讨中心》,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97年第28期,第53页。为主要应对方式,在罢工之初采用类似“无情鸡”⑫霍新宾:《“无情鸡”事件:国民革命后期劳资纠纷的实证考察》,载《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1期,第41页。之手段,收效甚微。当墨店主意识到墨工行为之坚决和组织之严密后,在此 “劳资合行”①霍新宾:《阶级意识与行会理念--广州正式政府成立前后的劳资关系变动》,载《学术研究》,2011年第11期,第108页。传统行会理念的影响和支配下,主动改变策略,实现与墨工之妥协,进而使墨工罢工事件得以平息。
其次,墨工之所以罢工是因为其感受到社会之不公平,特别是社会稀缺资源,即金钱分配之不公平。当墨店主获得大量的社会稀缺资源后,却对自己假仁假义。虽然墨店主将有病墨工送往徽宁医院就医,且死后可领堂材,但这是墨店主之“虚情假意”。因徽宁医院“是救济贫民无投处之人,而墨作东家竟当作惠自己出,且沾沾以每年出少数捐款自矜。此□(真)欺世之谈”。②《旅沪婺源墨业工人之呼吁》,载《申报》1924年5月6日,第14版。墨店主如此做派,墨工必会认为“现存不平等系统是不合法的”。③宋林飞:《西方社会学理论》,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30页。取消这样“不平等的系统”成了墨工首要的行动要素,进而引起冲突。而墨工和墨店主冲突的重要表现便是罢工,这是墨业罢工的观念原因。需重点指出的是,徽州墨业罢工事件应置于当时“大历史”背景下。当时上海不仅出现墨业罢工事件,还有“成衣工人罢工事件”④《成衣工人罢工》,载《时报》,1924年5月31日。“皮匠罢工事件”⑤《杨帮皮匠大罢工三志》,载《时报》,1924年7月29日。“丝工罢工事件”⑥《丝厂罢工风潮之续闻》,载《时报》,1924年6月21日。等诸多罢工事件。这绝不是巧合,就观念来说与西方思潮息息相关。面对不公,反抗的意念便会产生,罢工事件便会频发。墨工必不能也不会摆脱时代之窠臼,才有此次上海徽州墨业罢工事件,这是上海徽州墨业罢工事件的观念原因。
在此次墨业罢工原因分析中,除前文论述之现实原因与观念原因外,尚有徽州墨业工人所独有的心理原因,即墨工与墨店主之间“亲密关系”被破坏。传统意义上来说“亲密关系是对我们有情感意义的重要他人……包括亲人、朋友、恋人等”⑦刘伟志:《心理调适》,上海: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91-92页。,而在深植“远亲不如近邻”价值理念之中国,乡谊必然是被中国人所认可的“亲密关系”。上海的墨工与墨店主都是来自同一地方——徽州,即墨店主和墨工不仅是同乡,更有可能是同宗同族。但是随着时间的变化,这种以地域为纽带,以情感为基础的“乡里乡亲”的亲密关系遭受破坏,其破坏的原因之一是墨店主对墨工人格的“奴视”。⑧《墨业工形势严重》,载《民国日报》,1924年6月22日。这种“奴视”与徽州宗族社会中“仆佃制”⑨笔者按:赞同叶显恩先生关于徽州农村社会中“仆佃制”研究的相关论述,可参看叶显恩先生之著作《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仆佃制》,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下同。息息相关,可以视作“仆佃制”在近代社会之残余。墨店主之不尊重,导致墨工之不忠诚。再加之墨工与墨店主之间由于对财富的需求不同,又因各自价值体系的不同而形成冲突。“不忠诚”和“价值体系相异”无形中割裂了两者的“亲密关系”,这也是导致俞郎溪等徽州商人多次想用“乡谊”劝说和解不得成功之原因。且此次墨工与墨店主“亲密关系”被割裂之后,很长时间内都难以彻底恢复,才有1927年“墨店东主被辱”①《笔墨店主被辱》,载《申报》,1927年5月11日,第9版。事件。
由此而知,1924年上海徽州墨业罢工之原因有三:其一为墨工之要求加资,改善待遇之现实原因;其二为墨工观念之变化;其三为墨工与墨店主亲密关系之破坏。概而言之,此次墨业罢工事件因为不平等的社会系统,作为下层代表的墨工受到思想观念之变化、亲密关系之割裂而造成此次罢工事件。
(二)1924年徽州墨业工人罢工事件之影响分析
从社会学角度来说,罢工事件的实质是冲突,是敌对情绪的表达。敌对情绪表达有三种方式:“(1)将敌对情绪发泄到该发泄的对象上。(2)替代,即把敌对行为指向替代目标。替代又可以分为手段的替代与目标的替代。(3)没有对象的直接表现”。②宋林飞:《西方社会学理论》,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35页。徽州墨业罢工事件即是将自己的敌对情绪发泄到真正的对立面--墨店主身上。我们在看到其破坏性功效的同时,也要看到其安全阀的功能。在物理学中安全阀的作用是将原本猛烈的蒸汽不断缓慢释放,在释放蒸汽的过程中可以保护整个结构的安全。对社会而言,墨业罢工事件就是冲突,就如同蒸汽结构中多余的蒸汽,它也需要释放,其释放过程虽有一定的伤害,但难以撼动整个社会结构。这种冲突调整了整个社会关系,进而在较小损失下保护了整个群体。这是社会冲突对于社会安全的积极意义。而上海徽州墨业罢工事件便是以墨店主和墨工冲突之形式,对上海徽州墨业之发展起到保护之影响。
就1924年徽州墨业罢工事件的客观影响来说,其影响有二:
第一,此次上海徽州墨业罢工事件促使墨商调整规则,给予墨业发展新的机遇。对于墨商规则调整之事,在徽州墨业罢工期间已有端倪。如俞郎溪就曾建议修改墨业旧规,“向例端节进退工人,今可改为正月财神日行之,并增加每工工银五厘以补现在生活”。③《墨业工潮不易解决》,载《民国时报》,1924年7月2日。这是俞之建议,最终被否。上海徽州墨业行业规则之改变则是发生在1927年,即“十二条规则”之新订。现将部分规则引用如下:
(一)各店东承认制墨工会有代表墨业工人之权。……(三)做填工友学生每人每月由店东结与菜钱二元,月福在内。(四)做填工友每月由店东给与月规大洋五角,学生减半。(五)各店东津贴工会开办费二十元,以一次为限。(六)各工友如患疾病,中医送广益医院普通病室,西医送红十字会,一月以内医药费由店东担任,倘因公死亡者由店东量力抚恤。……(八)做填工友工资每工照原价加银二分,学生月规照月价加三成,学生外工照师减半。(九)工友学生逢参加大会停工时,各店应表示认可每人每日包工两工(以有上海工会组织统一委员会命令为限)。(十)内外执者作薪资由店东酌加。……④《婺源帮制墨工会暨笔墨业商民协会新订之条件》,载《申报》,1927年5月22日,第15版。
较之之前所提出“墨业罢工五条”,此十二条新规对上海徽州墨业发展的积极影响更大。此新规不仅在工资标准上有所提高,保障了墨工工作的权益,更给予墨工更多福利待遇和人文关怀。其中的“医疗补助费”“探亲交通费”“停工带薪”于今而言仍具有参考价值。如前所述,通过对敌对情绪的释放——墨业罢工潮的形成——对维护墨业发展的积极影响,此“十二条新规”对上海徽州墨业发展的正面作用不言而明。1924年上海徽州墨业工人罢工之影响便是在此。
第二,此次上海徽州墨业工人罢工影响到“造茶工人罢工事件”。在此次上海徽州墨业罢工行动中形成了以朱润斌为首的罢工领导小组。何以认为朱润斌为此次墨业罢工之领袖?最好的证明便是“旅沪婺源墨业工人之呼吁”和墨业罢工胜利之后的两封致谢函(《函谢祁门同乡会》《函谢工团联合会》)均是出自朱润斌之手。如非墨业罢工之领袖,无以写此檄文与信函也。而朱润斌因墨业罢工之成功经验,成了其再次参与两年之后造茶工人罢工事件的“经验资本”。
如《申报》的“警厅保护星江茶业公所”条陈中指出:
“……最近之茶业工潮亦因此发生,如自称代表之朱润斌、吴伯超、洪万才、程灶海、俞乃庚等受觊觎者之指使,于本年四月间,藉加工资为由,煽诱制茶工人到处胡闹,逞强挟制笔难缕述……”①《警厅保护星江茶业公所》,载《申报》,1926年8月23日,第9版。
由此而知,朱润斌鼓动造茶工人罢工之事实显而易见,他以星江茶业公所委员会的名义发放传单并开展茶工罢工宣传工作,他之所以能成为茶工罢工之参与者,主因乃是其墨业罢工取得成功之“资历”,这也是此次上海徽州墨业罢工之影响。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此次上海徽州墨业罢工事件造就了一批以朱润斌为代表的罢工群体,在更大范围来说,对中国的民主革命都产生了影响。
总而言之,上海徽州墨业罢工事件对徽州墨业发展起到“社会安全阀”之影响。上海徽州墨业罢工事件看似是社会冲突,对社会发展有不利影响,但因为其胜利果实之取得在无形中对上海徽州墨业之发展起到“减压”之影响,并使墨业工人之权益得到保障,进而促进了1927年徽州墨商对墨工待遇的调整,再因此次事件之成功逐步形成了以朱润斌为代表的罢工群体,进而影响到1926年“造茶工人罢工事件”。由此而知,1924年上海徽州墨业罢工事件在某种程度上保障了上海徽州墨业之延续,推动了社会发展,维护了社会安全。
三、余论
马克思有一基本观点,即“压迫越深,反抗愈烈”。上海徽州墨业罢工事件便是在压迫下的反抗,但是这种反抗对社会发展并未起到如火山喷发式的革命性打击,而是一种如释放压力式的促进社会稳定的力量。上海徽州墨业罢工事件其本质是“压力释放模式下的社会改良事件”。这再次印证了陈旭麓先生之论断:“改良是以渐进的斗争形式推动旧事物向新事物转化……或缓或急地促进社会的新陈代谢”。②陈旭麓:《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与改良》,载《历史研究》,1980年第6期。又见《〈历史研究〉五十年论文选:近代中国·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330页。还需要注意的是,正如前文所述,在近代“改良”的主体除了知识精英外,最为多数的是绅士和商人群体。“特别是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的绅士和商人,广泛地参与了由各种社会团体组织的活动”,③(美)周锡瑞:《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5页。他们几乎都是改良的坚定支持者和践行者,但从客观效果上来看,“改良非但没有……避免革命,反而在某些方面推动了革命进程的发展”,①(美)周锡瑞:《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页。这就是历史的吊诡之处,也是值得深思和反省之处。
上海徽州墨工罢工事件通过三次墨业罢工使不利于墨业发展的“敌对情绪”得到逐级释放,而墨店主在这种“负能量”的冲刷下,逐渐看清社会现实,不断地调整经营方式,由“老古董”转变为与时俱进的“创新人”,在“改良润滑剂”的推动下促使墨业的新陈代谢。在上海墨业罢工的“改良实践”中,我们特别需要注意当时政府的角色扮演。政府对罢工事件有天然的恶意,因为罢工破坏了原有“动态平衡”的社会秩序。在罢工之初,政府对工人进行打压,甚至还出现了“警察和工人冲突事件”。②《墨业工潮仍在相持中(工人向警厅请愿、致与警察冲突)》,载《申报》,1924年6月20日,第13版。但是当罢工处于低潮,工人纷纷离店时,政府就着力敦促墨店主满足墨工之要求。这两者看似矛盾,实则统一。即政府在面对问题时,其所采用之政策乃是处于居中调停之位置,处于“维稳”的状态。政府之角色、墨工之角色、墨店主之角色三者从不同层面对社会进步起到了促进作用。墨工通过罢工释放社会压力,政府通过行政手段缓解社会压力,墨店主通过调整经营方式缓和社会压力,共同实现社会之稳定结构。上海徽州墨业罢工事件虽是“小事件”,却对徽商墨商研究的“大历史”有映射之功效,研究上海徽州墨业罢工事件其实质是研究徽商墨商能够存续之缘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