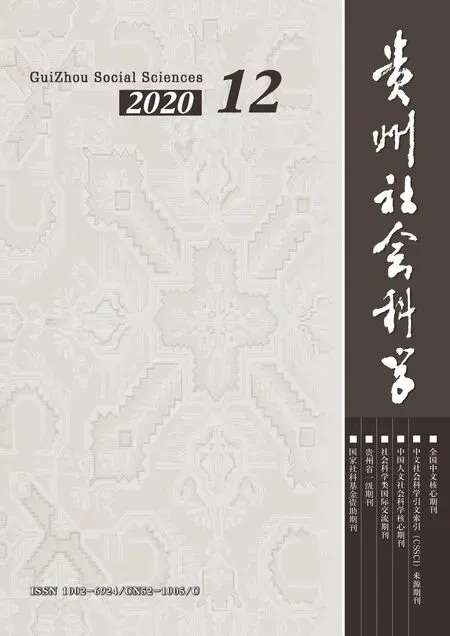欲望书写与灵魂救赎
——论王彪的长篇小说创作
2020-03-11张晓英
张晓英
(上海师范大学,上海 200234)
王彪(1)王彪(1961—),男,浙江黄岩人,作家、编辑、国家一级编剧,现任《收获》杂志副主编。1992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1997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长篇小说《身体的声音》《越跑越远》《复眼》《你里头的光》,小说集《致命的模仿》《隐秘冲动》,中篇小说《干净》《错误》《病孩》《欲望》《庄园》《在屋顶飞翔》《死是容易的》,短篇小说《青丝》《手相》等。2000年之后,创作方向从小说转向编剧,主要代表作有《红日》《东方红1949》《大明王朝1449》《明末风云》《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旗袍》《胭脂》等。自20世纪90年代起开始小说创作,创作伊始便以怪异的先锋色彩和鲜明的个性特征引起人们的注意。“他以一种异常敏感而又相当独特的审美心理直接叩问人类精神存在的巨大困惑,感受着种种生命欲望在社会视域中所遭受的煎熬。”[1]王彪的小说多着眼于男女两性间的泛滥情欲,通过对性欲的书写,表现出当代人内心的伤痛与面对命运的无力,他的创作也渐渐呈现出现实主义的色彩,从先锋走向现实,在带有象征色彩的意象中,表现人生的困境,在内心灵魂的追问下,探讨救赎的可能。
一、欲望泛滥下的情欲书写
王彪的四部长篇小说都涉及对情欲的描写,在对这一原始欲望的书写中,表现出身陷欲海的迷途者们的苦苦挣扎,他们都已千疮百孔、伤痕累累,像迷路羔羊般受困于命运之网中。王彪曾坦言:“生、死、病、性,在一段时间里,它们是我作品里游荡不去的幽灵。”[2]在他的长篇小说中,情欲的冲动往往与死亡联系在一起,它们就像是一对孪生姐妹,情欲推动着故事的发展,使人们从欲望走向毁灭。
王彪对情欲的描写,多将其直接表现为性冲动、性本能,大多缺少风花雪月的浪漫情怀,赤裸裸地展现人物间的肉体关系,神圣的爱情只不过是在“力比多”的作用下产生的性欲。《身体里的声音》以带有先锋色彩的叙事手法,描写了复杂混乱的人物关系,父亲与母亲、母亲与木匠、父亲与豆腐香香、铁匠弟弟与豆腐香香、琴姐与牙医、琴姐与伞匠、刻章师傅与新婚妻子、卖蛇人与妻子、何小军与甘草,这些人物都陷入情欲的漩涡中,处在一个畸形的、失范的生活状态下,在末日的狂欢中奏响着欲望的悲歌。
《复眼》以马绎为中心,牵连出他与邢曼娜、妻子小蜂与女孩“小蝶”三个女人之间的故事。小说充满着情欲、背叛、性交易以及犯罪等内容,在欲望的煽动下,马绎越过了道德的底线,一步步走向了堕落。王彪的长篇小说将人的内心深处最隐秘的欲望毫不留情地揭露出来,他所描写的性不再具有活力与生机,只不过是人的一种原生状态,这些没有精神深度的人,需要的也只有欲望而已。
王彪也描写了那些发自内心的、真挚的情爱,但他的目的并不是为了颂扬爱情,而是表现出在缺少理性的制约下,泛滥的欲望会一步一步地腐蚀掉最初的美好。正如米兰·昆德拉所言:“在现代世界,丑陋无所不在,它被习惯仁慈地遮掩,但却在所有不幸的时刻突然出现。”[3]131王彪的长篇小说,往往描写出在情欲的外衣下,潜藏着欲望泛滥下人的丑陋面貌,非常态的性欲刺激,导致了人性的扭曲。泛滥的情欲挣脱了理性的制约与意志的束缚,如同黑洞般吞噬着人们,暴露了人性的空虚与灵魂的脆弱。《你里头的光》中的陈米海、高红梅与齐国耀,本拥有着自然美好的少年情愫,却在时代背景的影响下,蒙上了诡计和背叛的阴影。陈米海喜欢高红梅,但高红梅却迷恋着齐国耀,当陈米海在25年后终于如愿以偿时,他发现自己得到的却是松弛的身体、虚幻的爱的假象,年少时的美丽绮梦在漫长的时间里早已消耗殆尽,“就像被虫子蛀空了的果子”[4],只剩下肉欲的满足和对性的索取。高红梅的情意一直被齐国耀忽略,得不到回应,因爱生恨的她竟然写信告发了齐国耀与他的“兄弟帮”,对齐国耀造成了沉重打击。齐国耀一直追求阮霏,在他失意下得到了高红梅的安慰,两人便成为了夫妻。当齐国耀得知检举他的人竟是高红梅后,原本是“公子落难小姐送情”而顺理成章的婚姻,演变得水火不容。在爱与欲的纠葛中,他们丧失了善良,也都为此付出了代价。《越跑越远》中的老张头渴望拥有红云,他迷恋着红云,执着地跟随在红云身边,更强行与红云发生性关系。他本以为把红云的嗓子毒哑后,便能独享她,没想到这却成了红云自缢的导火索,嫉妒与自私最终酿成了一场悲剧。从潘多拉魔盒中溢出的仇恨、嫉妒与贪婪附着在王彪笔下的人物身上,无论是告密的高红梅,还是偷偷下药的老张头,他们在欲望的教唆下,陷入了罪恶的渊薮中,内心的贪念、嫉恨毁灭了原本美好的情爱。
在王彪的长篇小说中,男欢女爱总没有好的结局,小说中的人物被欲望所控制,情欲就像野草一样在他们心中疯长,性作为一种本能,几乎不再需要爱与情感为基础,失去了理性与规范,失去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本性,从人性变为兽性。但他并没有将这种欲望描写得过于烂俗,他所描写的情欲并不迎合商业化的猎奇心态与恶俗趣味,而是着力塑造这些千疮百孔的人物内心的无力与宿命感,他们以抵抗内心的痛苦而走上欲望之路,但这条路却没有给他们以解脱。
《越跑越远》所描写的高中生与女戏子之间的畸恋故事,表现了灵与肉之间的挣扎、较量、纠缠与角逐。梓青与红云之间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暧昧,两人看似离得很近,但始终有一道隔膜。在梓青的潜意识里,总有一种逃离固有生活的渴望,他并不清楚目的地在哪里,他只想要“越跑越远”。红云的出现则是一个契机,这是一个能带他逃离的女人,在一定程度上为他沉闷的生活增加了刺激感。梓青对红云的迷恋,更多的是出于青春期性意识的萌动,是对生活的反叛,他既对性的诱惑感到渴望,同时又总被一种恐惧感所缠绕,一方面,他沉迷于红云成熟的胴体,另一方面,他又对陷入情欲中的自己感到怀疑和自责。在红云死后,梓青并没有选择去上大学,而是成了草台班子里的名角,过着吉普赛人式的流浪生活,虽然梓青脱离了原有的生活轨道,但他依然不清楚自己想要的究竟是什么,只是沿着命运的既定轨道自在地走动。红云作为情场老手,一个阅历丰富的戏子,游走于各个男人之间,尽力施展着自己的魅力,如同女王般享受着被爱慕的感觉。她在梓青身上找到了寻求已久的、不同于成人世界的单纯与真情,她把梓青看作是拯救她的希望,渴望在梓青那里得到真正的爱情。但同时,她也害怕伤害到梓青,在她看来,让梓青沾染上情欲是不对的,这样会害了梓青,可是她却无法说服自己拒绝梓青的接近,甚至于自己主动引诱梓青,沉醉于这场感情游戏中。在她对男性失望后,梓青就是她的寄托,可是梓青的力量太弱小了,无法真正改变她的境况,希望的错位和现实的阻碍最终使她走向了灭亡。
王彪小说中的欲望背后往往隐藏着痛苦,他以泛滥的情欲书写来表现当代人生存的尴尬困境。在王彪看来,“没有畏惧感的时代是非常可怕的,它消灭了精神,至少是消灭了精神的深度,人需要的只是欲”[5]。王彪以性来观照当下人的生存状态,他否定这种缺少理性的动物本能,人一旦成为情欲的奴隶,在欲望的圆舞曲中肆意狂欢,便会脱离正轨,陷入痛苦的深渊。
二、象征隐喻下的人生伤痛
王彪的长篇小说向来不会给读者一种舒适感,相反,总能让人感到痛苦。正如他所言,“小说要有伤痛感”,要表现出精神的深度,要有“灵魂的伤痛”和“生死的悲悯”[5]。读者总能被他的小说所呈现的黑暗及苦难感染,与小说中的人物共同直面人生的困苦。王彪以带有隐喻色彩的意象来展现人们内心的痛苦,表现出小人物在庸常人生中所面临的困境。
王彪将美与恶展现在人们面前,在光明与黑暗、理性与非理性的对比中,将恶的一面肆意放大,表现出美好破灭的人生伤痛。在《身体里的声音》中,王彪以一个“傻子”的视角来叙述小镇上各个人物的卑琐生活。如同韩少功《爸爸爸》里的丙崽一样,“我”也常被欺负,不被认可,既被同龄孩子所排斥,也游离于成人世界之外。傻子象征着与他人的格格不入,不被归为同一群体,由一道无形的鸿沟将“我”与镇上的其他人隔离开,尽管“我”知晓镇上发生的一切,却没有倾听者,也没有人在意,“我”存在这个镇上却不属于他们中的一员。“我”虽是一个傻子,但内心却始终保持着孩童般的纯净,没有同镇上的人一样充满着色情与暴力。可是,尽管“我”存有心灵上的美好,却无法在现实世界中得到幸福,父亲去世,母亲改嫁,就连唯一的朋友最后也抛弃了“我”。小说以“傻子”这一具有象征意味的形象来表现在无理性的生活中,人所感受到的痛苦与生存权利的剥夺,真善美在恶的世界里毫无抵抗力。
王彪也大量采用带有象征色彩的词语作为小说标题,如小说《身体里的声音》第二章“地板和酒瓮”,以“地板”表示父亲生存空间的被剥夺,在县城械斗交火中失去双腿的父亲,也失去了发号施令的权利,为了不被仇敌找到,藏身于地板之下,与老鼠虫蚁为伍。身份的巨大落差使父亲的性格变得古怪,权力的旁落与地位的丧失,使父亲失去了存在价值。“酒瓮”象征着酱酒店女老板琴姐的胸脯,铁匠弟弟唱了一首带有性暗示色彩的歌曲:“大酒瓮,小酒瓮,酱酒店的女人香喷喷;开开封,没开封,开了封的老酒酸死人。”[6]以开了封的酒瓮暗指琴姐已并非清白之身,“酸死人”不单单是对酒的口感的评述,更是代表了传统的男性思维对所谓不守贞洁的女人的批判,在固有观念下,女性被随意地贴上标签,她们不仅会受到男性的骚扰,更无法实现自己的合理诉求。第六章“老公猫成仙了”,以何小军家里那只被妖魔化的老公猫,象征着原始的生命力,而它却遭到了阉割,表现了镇上人们的愚昧和无知。
除了表现人生美好的破灭外,王彪还关注到现代人生存意义的焦虑与失去自我的伤痛。市场经济的畸形发展,道德伦理的失范,生活节奏的加快,社会普遍呈现出浮躁的状态,现代人很难再以一种平和的心态看待自己与他人。社会变化引发的不安全感以及人们心理上的失落感、压迫感,诸多因素让人感到迷惘,奔走于一地鸡毛式的琐碎生活中,失去了对人生意义的思考和追问。王彪抓住了这一时代痛点,他的小说描写出现代人在追寻自我途中的挣扎与痛苦以及失去自我的伤痛。《越跑越远》中那条传说中的大鱼象征着人对自我价值的追求,海根下定决心一定要找到那条大鱼,并将其捕杀,不仅是向小汶证明自己的勇猛,更重要的是表明自己与外来人、所谓的城市人之间的区别,在孤注一掷的勇夫行动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这种“最后一个渔佬”的形象,将城乡两种身份进行了区别,海根代表着原始的、古朴的渔民形象,他不像小汶那样羡慕城市的生活,也瞧不上梓青这样的城里人,固执地坚守着传统的生活方式。即使偏居一隅,这座海岛也无法避免地沾染城市的气息,鱼越捕越少,娱乐设施渐渐变多,岛民也对城市有了渴望之心。在城市文明的蔓延下,乡村也渐渐走向城市化,二者之间的差别也逐渐消失,这也意味着,古老和传统的乡村文明受到了冲击,已很难再保持它原有的质朴。海根凭自己之力,很难与大鱼抗争,最终他没能打败那条大鱼,反而丢掉了性命,就像他无法挽留异变中的渔村一样,他用行动捍卫着自己的尊严,谱写了一曲属于自己的悲壮的、命运的挽歌。《复眼》这一书名本身就带有象征意味,以昆虫数以万计的小眼组成的复眼表明人时刻处于紧张的、被窥探的生活状态中,从不同的眼睛折射出来的个体也便拥有了不同的身份。无论是镶满镜子的咖啡馆,还是马绎收藏的蝴蝶标本,它们都有无数的小眼在观察着周围的一切,每个人都处于窥视与被偷窥之中。在复眼的世界里,人们看到的会是上万种不同的面庞,在这变幻莫测的视觉里,每个人都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也渐渐失去了自我。
在王彪的长篇小说中,常常表现出时代带给人们的伤痛,小说中的人物好似被一双无形的手推着,如同上帝的棋子一般被随意摆弄,他们被命运的枷锁束缚着,渴望冲破牢笼,却苦于找不到出路,只剩下满目的荒凉与无奈,这更加剧了命运带给人的伤痛感。虽然已有官方话语对那场特殊的政治运动进行定论,但其中隐含的无理性、暴虐、人性的丧失等丑陋的一面通过血液在代际中得到传递。《你里头的光》以果子象征受父辈影响的后代,上代人之间的爱恨情仇,加诸于三个无辜的年轻人身上,严杰、齐梦飞与陈小安不曾参与到那段历史,但他们以自己的方式续写父辈的故事,背负着本不应该属于他们的沉重负担。齐梦飞与严杰虽然没有亲历那种种人间惨剧,但仇恨的种子已在他们体内生根发芽,小说以父辈的被“谋害”、母亲的被侮辱来表现复仇的必要性,他们化身为复仇者,但其复仇行为却充满了反讽。齐梦飞的复仇之路,并不是一条自我拯救之路,而是一条毁灭之路,暴虐思想的种子在齐梦飞身上得到了生发,他就像25年前的齐国耀一样,热衷于批斗,眼神里透露着冷峻的目光。他无法直接向陈米海讨债,便将仇恨转移到陈小安身上,并向她施加种种严酷的审讯手段,以对她的侮辱完成为父亲的复仇,失去理性的复仇行为令人毛骨悚然。在齐梦飞身上表现出青年人所具有的狂热,对生活的破坏性是极其强烈的。这也说明了青年人“在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的变动过程中并不只是被动的受教育者”[7],他们以自己的方式理解既定的意识形态,对其进行挑战甚至是颠覆。严杰在丁校长的步步引诱下得知了严英才自杀的真相,多年来一直隐忍不发潜伏在刘建东身边,当他以为完成复仇时,却陷入了俄狄浦斯式的结局,他设计害死的仇人竟然是他的亲生父亲。齐梦飞和严杰都自认为以“正义”的方式为父亲报仇,但他们的复仇对象都发生了偏移,他们报复的都不是自己真正的仇人,在特殊历史的影响下,他们既是迫害者,同时也是受害者。王彪的长篇小说以带有象征色彩的意象来表现被命运掌控的人生伤痛,命运“就像一口残酷的井,落到里面,怎样呼号也难以逃脱这黑暗的坑”[8],他们看似是自己命运的主宰者,但在时代潮流中,每个人都难逃命运的牢笼。
王彪在小说中以独具特色的私设象征,表现了人们面对生活的无力与内心的痛苦。私设象征是具有作者“强烈个人意味的象征物,是作者神思飞动时一个偶发的灵感”[9],因而能够很好地表达作者的意图。王彪以地板、酒瓮、公猫、复眼等这些带有个人印记的私设象征隐喻出时代及命运对人的操控,表现了当代人的生存困境及人生伤痛。
三、魔幻现实与叙事流变
王彪的写作时间跨度很大,从1998年在《收获》上刊载第一部长篇小说《身体里的声音》,到2017年出版《你里头的光》,创作间隔长达20年。王彪的写作技巧在不断成熟,叙事方式也有了很大的变化,从最开始的魔幻色彩越来越倾向写实的风格。
王彪早期的小说创作带有后先锋小说的色彩,既有着奇特、怪异的想象,又有着现实历史的影子。小说的叙事者往往以一个“病孩”的视角呈现,通过孩童的眼光反映这个光怪陆离的魔幻世界。小说《身体里的声音》以奇异的想象,呈现出一幅末日神话图景,小说没有比较明显的故事情节,通过诸多人物的轮番上场,展现小镇上奇异的生存状态。小说以一个傻孩子的视角来进行叙述,虽然是第一人称视角的口吻,但又不局限于此,“我”承担着全知全能的叙述角色,镇上发生的一切都逃不过“我”的眼睛。小说人物众多,由不同人物的“声音”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多声部的组织形式拼接在一起构成了小说主体。在“我”的叙述中,往往夹杂着人物之间的对话,将不同时间、不同空间发生的事情糅合在一起,模糊了时空的界限。这些对话以短对话为主,大多含混不清、意义不明,缺少完整的逻辑线索,陷入了集体独白的局面中。小说充满了超现实的色彩,在这座封闭的小镇上发生了许多匪夷所思的事情,死去的铁匠的骨架竟然重新出现在人们面前,就像被悬挂起来的标本一样立在门板上。这件令人毛骨悚然的事情背后暗含着对非正常化社会的隐射,王彪将政治事件进行了意象化的处理,以象征的手法表现出社会运动给人造成的创伤。铁匠弟弟家那只被妖魔化的老公猫也带有魔幻色彩,在它身上有许多成仙的事例,甚至有传言称何小军是老公猫的孩子,老公猫可以像人一样做爱。这些带有魔幻色彩的描写展现了一个奇异的小镇图景,而在这些奇幻色彩的背后反映了小镇人的愚昧与残忍。“魔幻现实主义的主要特点并不是去虚构一系列的人物或者虚幻的世界,而是要发现存在于人与人、人与周围环境之间的神秘关系。”[10]王彪借鉴魔幻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给现实披上了一层荒诞怪异的外衣,以虚构的小说世界来映射现实中人与人之间紧张压迫的生存关系以及自身生存空间的逼仄。
王彪在其后的长篇小说中,采用了多样的叙事手法,也越来越贴近现实生活。《越跑越远》以场景的变换来推进小说的发展,小镇、海岛、城市、乡村,以不同空间的转移来表现梓青的心理变化。《复眼》以零度写作的方式来表现诱惑与背叛,疑案与犯罪,带有侦探小说的色彩。马绎陷入对“复眼”般的世界的想象与探索,着迷于寻找隐藏的真相,而在现实中,一个个谜团相继呈现,神秘的少女、逃亡的抢劫犯、被杀的教授,真相逐渐显露出来,过去的历史被一页页揭开,在眼花缭乱的外表下,掩盖的是失去自我的人生伤痛。
王彪在2000年左右暂停了小说写作,转入编剧创作,而在他的最新作品《你里头的光》中,王彪越发地关注到当下生活,更多地涉及到对现实问题的描写和表现。小说以现实主义的叙述手法展开描写,无论是发生在25年前的历史往事,还是当下的热点问题,王彪都力图真实呈现,具有强烈的社会批判性。小说揭露了很多现实问题:学校围墙因豆腐渣工程,质量不过关,倒塌压伤了几位学生;医院领导贪污受贿拿回扣,甚至卖假药、假疫苗;齐国耀成立“宝塔会”,在巨额利润的背后却是精心的骗局与非法的交易;闵师父表面上一副世外高人的样子,内心却极度渴望能当选政协委员。小说所描写的对金钱的崇拜、官商的利益勾结,都真实发生在现实生活中,揭露了社会的不堪与黑暗,令人深思。
王彪长篇小说的叙事风格,从最开始的魔幻色彩,逐渐向现实主义靠拢,小说描写的涵盖面更广,架构更宏大,涉及到的内容也较为多面,不再局限于男欢女爱的情欲书写,由欲望描写转向对人性黑暗的揭露,表现出文学的社会功能和现实意义。
四、内在追问与灵魂救赎
王彪的四部长篇小说描写了陷入欲望泥沼里的人物,在这些情欲的背后则隐藏着痛苦与绝望,他们饱受着人生及命运带来的苦难,时刻感受到灵魂的不安。王彪曾谈到自己对人的生命与本性问题感到着迷,也期待能回答这些人类必须直面的问题。[2]因此,王彪从没有放弃寻找解脱的出路,为他小说中的人物找到求生之路,探讨救赎的可能。
王彪小说中的人物往往都没有好的结局,他们被沉重的枷锁束缚在痛苦中,苦于寻找自我拯救的方式。《复眼》里的马绎受过去的影响,在他的生活中总有刘斌的影子,刘斌死亡的景象时刻出现在他的脑海中,像幽灵般一直围绕在他身边,而与邢曼娜发生的那一段暧昧之情,也令他始终难以摆脱旧日的阴影。他沉迷于研究“复眼”,对“复眼”所呈现的世界感到好奇,总感觉有人在偷窥他,生活在幻觉与疑惧中。他希望能得到解脱,从过去中走出来,而在现实生活中,他却一直被迷雾所环绕,一步步走向犯罪,不仅受困于记忆陷阱,更受到法律的制裁。王彪还常以一种冷漠的笔调叙写人物的死亡,以生命的结束借以摆脱苦难的人生。《身体里的声音》中的父亲,在与铁匠弟弟的械斗中失去了双腿,藏匿于地板之下,不仅被剥夺了政治权利,失去了领导权,在家庭中也失去了控制权,对母亲的占有受到了木匠的挑战,只能在对母亲的暴力中显示自己的权威。王彪没有具体描写父亲的心理活动,但能从父亲的言行中,感受到他精神的失常,身体的受创,使父亲变得暴力与猜忌,最终父亲死在了水缸里,在他所去的世界中所有人都是没有腿的,父亲终于能够获得一个公平的结局。《越跑越远》中痴迷于戏台生活的红云,最后却不是为戏而死,而是在羞辱与愤恨中死去,死亡便是她对自己过去生活的忏悔与弃绝。红云看似对什么都不在乎,其实内心却极度渴望真情与关爱,充满着对新生活的渴望以及对情与欲结合的爱的企求。在她看来,“戏就是人,人就是戏”,她本来可以在戏曲中逃离现实的一切,从中得到慰藉,但当她“倒嗓”后,失去了最后这一立身之处,无法再继续扮演她的角色,失去了生存的意义,从而也失去了她的救赎之路。
死亡并不能真正解决那些悬而未决的难题,反而使其增添了无法逃脱的宿命感,更让人感到绝望。于是在《你里头的光》中,王彪便将目光转向宗教,以爱与宽容作为救赎的方式。在小说中,王彪以陈小安作为化解仇恨、挣脱时代阴影的希望,渴望借助她来点亮人们的内心,驱赶黑暗。这不仅是陈小安的自我救赎、自我解脱,也是作者本人所寻找的出路,更是当代人所需要的。陈小安在遭受到齐梦飞等人的侮辱与侵害后,没有像过去时代的人们那样,互相告发,颠倒黑白,她从赞美诗中获得力量,选择正视现实,用爱来化解两代人之间的仇恨,在法庭上说出事实的真相。福克纳曾提到:“人之所以不朽,不仅仅因为在所有生物中只有他才能发出难以忍受的声音,而是因为他有灵魂,富有同情心,自我牺牲和忍耐精神。”[11]在陈小安身上,便具有基督徒式的宽容与博爱,表现出人所应有的特质。尽管陈小安并不确定自己是否会彻底原谅齐梦飞,但她心中充满爱,她相信爱能解决问题,在爱里没有惧怕,陈小安便是王彪内心的那束光,也是他想要人们相信的希望所在。对于政治运动的重新审视,许多作家以回看的姿态呈现、控诉、反思当时人们的种种做法,如反思小说、伤痕文学等,重拾对理性的呼唤。王彪将目光转向现在,过去的因结成了现在的果,思考对于历史遗留问题,又该如何处理。“小说家既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是预言学家,他是存在的勘探者。”[3]43小说家的任务并不是为种种社会现象提供良方妙药,而是指出存在的问题,以期唤醒大众的关注。王彪选择从基督教中获得解决方式,以爱与宽恕来跨越鸿沟,与历史和解。宗教是否具有如此强大的力量能够摆脱历史的枷锁,尚不得而知,但正如王彪在小说后记中所言:只要不遗忘,也许我们还有希望。王彪笔下的救赎并没有被现实摧毁,生存信念也没有完全消失,没有放弃在黑暗与痛苦的罅隙中对理性之光的追寻,留给人们希望与痛定思痛的思考。在愈发膨胀的社会,现代人缺少敬畏感,缺少“美的、宗教的纯情感”[12],缺少向内在的心灵探寻,缺少对人类的终极关怀。越来越多的作家关注到这一现象,他们选择转向宗教,如当代作家北村、史铁生,以及海外华人作家施玮、张翎等人,他们或者皈依宗教,成为教徒,或者受到教义的影响,在宗教中寻找依托与救赎,探讨人类的新出路。诚然,宗教并不一定是唯一的救赎方式,但无论如何选择,都应以积极的方式寻求心灵的安慰,获得灵魂的救赎。
王彪的长篇小说在情欲书写中表现出人生不可避免的伤痛,更探讨了灵魂救赎的可能,他的这种努力需要得到大众的呼应与关注,但同时不能忽略这一尝试的不足,陈小安的原谅显得稍微有些突兀,人物形象并不充实饱满,从而让人产生疑惑的是,一个16岁的中学生,在她受到如此大的屈辱后,是否真能如小说所言挣脱时代的阴影,原谅齐梦飞对她的伤害,信服力稍显不足,小说所呈现的黑暗何等之大,这一人性之光则显得既珍贵又微弱。王彪的小说也存在一些模式化的缺陷,《你里头的光》中严英才与叶美丽的故事与《复眼》中刘斌和邢曼娜的遭遇如出一辙,同是妻子在丈夫被隔离检查时被校长强暴,丈夫都因得知妻子怀孕的消息而自杀;《越跑越远》与中篇小说《欲望》的情节模式也很相似,都是高中生对女戏子的迷恋,女戏子也因遭到羞辱而自杀。因此,王彪的小说创作还应更精细化,摆脱自我框架的限制,在人物描写上更饱满些,做到既有思想的深度,又有小说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