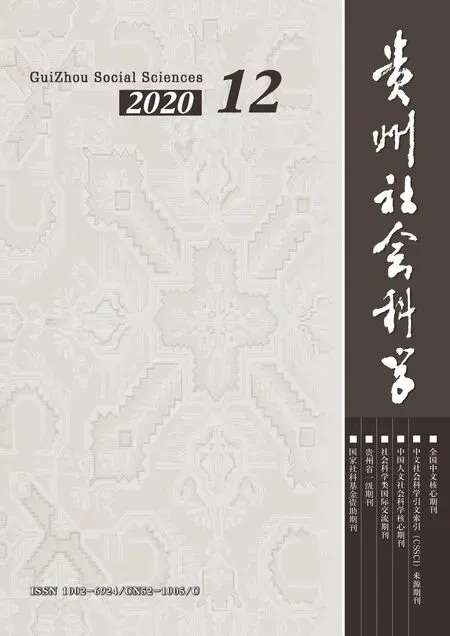当代作家的“冷硬”派批评
——以《小说稗类》为中心
2020-03-11叶立文
叶立文
(武汉大学,湖北 武汉 430072)
一、当代作家批评与小说的本体论意识
当代作家介入批评领域,以“批评体式的解放”和“重写他者的自由”解读小说经典,业已成为了近三十年来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1]在马原、余华、格非、残雪和毕飞宇等人的批评实践中,大量颠覆旧说、另立新规的经典重读和原作“重写”,不仅实现了创作与批评这两种异质文体的跨界融合,而且也提炼了不少与小说叙述有关的技术经验。虽然这些技术经验常被人诟病成壮夫不为的雕虫小技,但考虑到自新时期以来当代作家形式意识的觉醒,则不得不说只有具备了奇技淫巧的形式标识,小说才能在哲学或历史的知识谱系外另立门户。个中缘由,当然与“文以载道”的观念有关。由于在很长的时间内,小说家都念念不忘于对“道”所指代的各类知识的宣传,故而质胜于文的写作现实也就遮蔽了小说的形式自律这一文学本体。直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先锋作家对小说应当“怎么写”的高度重视,当代文学方才开始了脱离知识束缚、继而回到自身的写作实践。
不过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小说其实很难传达作家的文学本体论观念。这是因为隐藏在人物塑造、情节设置和场景安排之下的当代作家的形式诉求,往往会受制于小说意义的自我增殖。更为致命的是,每当作品问世以后,总有一些并不具备创作经验的批评家积极介入,他们对小说的意义指认和形式分析,基本上都来自于域外的文学理论,而这些理论话语的先验性和适用性问题,也导致了批评家无法完全揭示小说的形式价值。有鉴于此,与其听任学院派批评家去误解小说的形式试验,当代作家倒不如以文学批评的跨界写作,在“借他人酒杯浇自己胸中块垒”的过程中,间接发布关于小说艺术的个人看法。因此,通过研读小说经典去谈论小说的技术问题,就成为了作家批评里的一个重要环节。
我们注意到,在提炼小说的叙述方法这一技术手段时,很多当代作家都默契地遵循了以下原则,即不以直陈的方式去说明小说应当怎么写,而是通过分析技术手段的功能与效果问题,来印证和完善自身的形式诉求。这一做法,不仅可以规避小说主题对于形式试验的思想赋魅,而且也因对形式问题的关注,为批评本身带来了一种修辞学意义上的“冷硬”派风格。在这当中,“冷”描绘的是一种排除了作家情感温度的中立的价值立场。在讨论技术问题时,当代作家并不抱持人文主义或启蒙主义的价值预设,也不会扩大化形式问题所隐含的价值取向,而是以小说匠人的态度专注于技术手段本身;至于“硬”,则指的是结构方式、心理描写、叙述速度和小说腔调等技术手段本身。较之主题分析这类想象式的虚拟性意义阐释,技术手段自然是属于小说的硬通货。因为它的存在,实际上给写小说这件事设定了准入门槛——技术成为了区分故事与小说的标尺。就像叙事学家所说的那样,“国王死了,王后也死了”是故事,而“国王死了,王后也因悲伤而死去”则是小说的情节,[2]后者不光是给前者两个并列的事实加入了因果关系,同时也在叙述上为读者预留了想象国王与王后故事的创造空间。这个例子说明,对那些只有主题和故事构想而无技术手段的写作者来说,写小说也因此变得复杂了起来。小说门槛的提高,自然会缓解当代作家对于写作事业的某种合法性焦虑——因为在技术经验被单列以后,小说终于在部分程度上摆脱了附庸于其它知识的尴尬境地,进而成为了一种专门的知识。这既是当代作家多年来开展形式试验的结果,也是他们在文学批评中秉持技术理性原则的产物。换言之,当代作家的“冷硬派”批评实际上是以文学批评的方式,延续了他们早年在创作实践中对于小说艺术的知识合法性证明。这当然是一种小说的本体论意识:小说存在的理由,不再是为了反映或者表现其它知识,而是以技术为王的姿态,证明了小说的本体根本上就是各种形式话语的建构、拆解与博弈。
二、传统小说技术手段与现代小说艺术经验的互通
从文学版图上看,近年来致力于文学批评的当代作家主要集中在中国大陆,其中又以早年的先锋作家为代表,像马原、余华、残雪、格非和毕飞宇等人,不仅推出了《阅读大师》《内心之死》《灵魂的城堡》《雪隐鹭鸶》和《小说课》这样的批评名作,而且还在技术经验的提炼上用力甚勤。蕴藉其中的,自然是这一代作家对于早年破而不立的先锋写作的反思。有关他们的批评实践与文学史价值,以及和晚近兴起的作家驻校制之间的关系问题,笔者都曾以系列文章做过爬梳洗剔与概述整合。(1)参见叶立文:《作家驻校制与作家批评的兴起》,《小说评论》2018年第5期;《写“不写之写”,书“书中之书”》 ,《天津社会科学》2019年第1期;《游移的叙述与可疑的作者》,《中国文学研究》2019年第1期;《从灵魂之旅到技术理性》,《贵州社会科学》2017年第9期;《批评如何“小说”》,《天津社会科学》2014年第2期;《“复述”的艺术》,《文学评论》2012年第4期;《延伸与转化》,《文学评论》2006年第1期。不过在大陆以外的台港澳等中国地区,实际上仍有为数不少的当代作家活跃于批评领域。由于和大陆作家相比,他们的成长经历、思想背景和艺术旨趣多有不同,故而在谈论小说的技术经验时,也就呈现出了另一种写作风貌。如果说大陆作家基于历史经验和创伤记忆,即便是在分析小说的技术手段时,也经常与启蒙主义、自由主义等思想话语发生价值纠葛的话,那么台港澳作家就更注意纯文学传统内部的技术流变。虽说两者在写作立场上都偏于冷硬的价值中立,但仅以超越启蒙思想范式、聚焦于技术经验的专注度而言,台港澳作家较之大陆作家显然更为纯粹——他们对于小说技术经验的形式研究,事实上已经为大陆当代文学的形式建构提供了有益参照。从这个角度说,讨论台港澳作家的文学批评,不仅可在中国当代文学的整体视域内去发现作家批评的历史价值,而且也有助于廓清当代文学的本体论和工具论之争。
作为很多人心目中最有天分的台湾作家,张大春的写作历来就以跨界见长。他的小说、杂文、文学批评,甚至是流行音乐的歌词创作,都在华语文坛名重一时。虽然他的声誉主要得益于《城邦暴力团》和《大唐李白》这些作品,但如果只论影响力的话,则《小说稗类》这本文论集也不遑多让。由于他所坚持的小说观,正是大陆先锋作家念兹在兹的文学本体论。因此将这本书引入作家批评的研究视域内,当可用比较的方式得见另一种批评理路。与先锋作家近乎宣言式的本体论诉求相比,张大春往往能在抽象的理论概念之外,以细致的文字表达将小说本体论分解为一些具体的技术问题。这些技术问题看似微观琐碎,但作家的推敲思辨却极尽知识考古之能事,尤其是在讨论现代小说对于中国叙事传统的技术传承时,更能见出张大春欲与西方叙事学一较长短的批评雄心。因此若是能够阐明《小说稗类》一书所提炼的技术经验,那么就能在深受西方文学影响下的大陆作家之外,得见另一类主要以传统文学为师承的技术资源。而两者之间的互补关系,庶几可证“冷硬派”批评在建构当代小说本体论方面的重要价值。那么,《小说稗类》是一本怎样的书?张大春的炫技式批评,又提炼了什么样的技术经验?
从目录安排上看,《小说稗类》并无一条明显的逻辑线索结构全书。除了序言和附录,正文中的二十七则短评多以平行方式排列,如此也就意味着读者可以自由选读而无滞涩之感。但这并不意味着全书的体例,就是传统批评里常见的“例话”形式。如果仔细考究的话,那么每一则笔力纵横、才情洋溢的短评,都暗含着一些散落于细节丛林中的点睛笔致:它要么涉及小说的起源论,要么关乎小说的本体论,抑或是指向小说的功能论等等。而这些草蛇灰线、千里伏脉的叙述方式,无不体现了作家不预设价值立场,只讨论“体系解”“因果律”“速度感”等技术问题的“冷硬派”批评风格。与此同时,张大春还会以隐藏整体逻辑、召唤读者参与的文本游戏,不断开掘着中国传统小说里独具的技术资源。这一由西返中的批评路径,自然和大陆作家的文学批评多有不同。
由于受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大陆作家在提炼小说的技术经验时,往往会表现出一种结构主义的小说现代性意识。在他们看来,小说家的形式自觉主要指的是那些基于整体艺术考量之上的叙述匠心。所谓“一笔不肯苟且,一句不肯放松”[3],说的正是经典作家不会在叙述中使用任何闲笔,即使是艺术留白,亦有“不写之写”的叙述功能。循此理路,很多大陆作家都相信伟大的小说不仅思想深刻,甚至就连所有的技术手段都经过了周密设计。而批评家的任务,就是阐释每一处技术细节的叙述功能问题。在这方面,不论是格非的《雪隐鹭鸶》,还是毕飞宇的《小说课》都堪称极致。他们对于文学经典的解读,尤其注意那些游移于故事整体之外的闲笔与留白,以为其中必有深意存焉,由是这两位作家的作品阐释也就多以“闲笔不闲”的思路展开。耐人寻味的是,尽管他们的作品分析精彩纷呈,但对闲笔与留白的过度阐释,却有罔顾作者意图、借机表达自我形式诉求的写作倾向。换言之,在一些大陆作家的文学批评里,批评对象有时仅仅是通达自己艺术主张的途径与通道,至于批评本身是否能够揭示对象的技术经验似已不再重要。
不过这种状况在《小说稗类》里却构成了一个反转。较之大陆作家的创作式批评,张大春不仅追求技术手段的客观,而且也将当代小说可资借鉴的艺术经验指向了传统小说。为阐明这一问题,就有必要打乱《小说稗类》由目录所示的平行结构,通过重理章节、调整阅读顺序,提炼张大春写作此书的整体思路。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理解这本书对于传统小说技术手段的创造性转化如何展开。
三、 立足传统、反思小说现代性
如果按照目录顺序来读《小说稗类》,读者必定会迷惑不解。虽然起首的“说稗”能够破题,但随后的章节安排却颇有随意散乱之感——比如开篇为什么是小说的体系解,而本体论、起源点、修辞学、因果律、指涉论等各节又依据什么样的原则分列前后?至于学术论著常见的整体结论又在哪里?凡此种种,皆能制造一种陌生化的阅读效果,即读者不论对张大春的修辞美文怎样击节赞赏,对其中的奇思妙想又如何拍案惊奇,都有一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迷惘。以至于会不由追问,难道这种舍弃了整体视野和宏观认识的碎片化写作,莫非也要将文学批评降格为不入流的稗类,以至于“不当成个东西”?[4]2-3
然而《小说稗类》还有另一种读法。当我们重理章节目录、打乱原有顺序之后,就会发现此书和常见的学术著作相比,依旧称得上是体系完备、自成一格。全书的逻辑起点是正文第二则“一个词在时间中的奇遇——一则小说的本体论”,张大春在此开宗明义,以为小说不过是词语的时间奇遇。他反对文学的工具论,批判小说“十足异化的附庸旅程”[4]34,指明小说的“角色”和“故事”其实是从词语开始,随时间“预演”了“一整个世界”[4]36。接下来是正文第一则“有序不乱乎——一则小说的体系解”。这一则纵论庄子与司马迁等人对于小说的贡献,以为对另类知识的叙写实际上成为了小说的起源点。尽管后来“小说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减法’”[4]28,但这并无碍于司马迁将虚构手法带入官修正史,刘歆将散碎记录制为笔记小说……。而对小说史的梳理,实际上是为了埋下一个全书最为重要的伏笔,即小说应无序而乱,因为当“小说有序而不乱的时候”,“小说也就死了”[4]31。小说一旦变得中规中矩,承载起反映生活、阐扬人性世情、吻合理论规范、以及用另类知识冒犯公设禁忌时,当然会有序而不乱,但也会因此失掉原来粗粝如稗的生命力。事实上,在“两只小雨蛙,干卿底事——一则小说的离心力”“叙述的闲情与野性——一则小说的走马灯”“为弥彰而欲盖——一则小说的修正痕”等节中,张大春都暗斥了有序而不乱实际上是人为追求小说现代性的结果。与之相比,无序而乱才是小说的起始和本源。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何他会认为闲笔和留白一类的游移叙述,其实既不具备反映主题的叙事功能,也不会成为结构作品的有效拼图。
毫无疑问,当张大春批评小说的有序而不乱,反对过度阐释闲笔与留白之时,他就已经站在了格非和毕飞宇的对立面。因为他坚持认为,若不是受到了西方小说现代性经验的桎梏,中国小说原本是可以保持稗类一般的旺盛活力的。这也是张大春为什么会在附录部分写下“离奇与松散——从武侠衍出的中国小说叙事传统”一文的原因。作为一篇对小说起源点、体系解和本体论的回应之文,附录其实是张大春为正文里的短评所寻找的一个技术依据,即传统小说里的离奇与松散这一叙事传统,最终引发了他对离心力、走马灯和修正痕的讨论。因为这几种叙述方法都是导致小说结构趋于松散和无序的手段。从这个角度看,如果遵循“说稗”“本体论”“体系解”和附录的阅读顺序,我们才能理解正文内许多短评的批评意图与行文逻辑,因为前者是总纲,后者是论据。若不如此,则纲不能举、目亦不可张。
需要说明的是,既然这一阅读顺序已重列在此,那么我们就无需过多追索张大春的批评观念——因为不论是倡扬小说本体论,还是指认小说未成附庸之前的初始形态,张大春都能以提纲挈领之方式,表达自己立足传统、反思小说现代性的文学观念。由于这一观念作为一种由西返中的学术潮流并不鲜见,因此真正应该引起注意的,其实是张大春对于这一观念的论证过程。我们知道,文学批评最讲究纲举目张,然而举纲并非难事——但凡有创作经验的小说家,谁不会就文学观念说出个子丑寅卯?困难的反而是张目,因为很多作家在文学批评里的论证方式,要么是借他人酒杯浇自己胸中块垒,要么是借他山之石以攻玉,总之利用研究对象去表达自己的文学主张,免不了会陷入到过度阐释的陷阱里去。相较之下,张大春的“冷硬”派批评则客观了许多,这是因为他将反思小说现代性的批评纲要,从抽象的观念具化成了一个纯粹的技术问题,即以结构的松散、叙述的离心和美学的闲情等话题,在对闲笔和留白的叙述功能进行去魅的前提下,批评有序而不乱的小说观念。由此也就形成了一个对比,同样的游移叙述,在格非和毕飞宇笔下会被赋予特定的叙述功能,似乎不如此就不能证明经典作品的有序而不乱——这当然是两位大陆作家秉承小说现代性意识的结果;但在张大春那里,小说中游移于主线故事之外的闲笔和留白,却根本不会去承担表现主题的叙事功能,反倒是以讲述另类知识的方式,在拆解小说有序性的同时抵抗着文学的现代性神话。
四、闲笔:离心与向心之辨
如前所述,倘若我们无需过度追索“本体论”和“体系解”等则所表达的批评观念的话,那么理解张大春论证过程的起点就是附录部分。这是因为在“离奇与松散——从武侠衍出的中国小说叙事传统”一文中,张大春实际上以金庸小说为切入点,梳理出了“闲笔”这一技术经验在中西文学谱系里的不同地位。按有些学者的说法,金庸作品如《天龙八部》情节离奇、结构松散,两者相得益彰,从而实现了形式与内容的统一。但问题就在于,形式与内容的统一为何会成为美学的最高典范?事实上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时代起,西方文学便有将这一典范奉若圭皋的传统。其影响之深远,几乎成为了一个排斥其它任何典范的美学黑洞。以至于五四时期渴慕西学的胡适等人,也在推崇此一传统的前提下对结构松散的中国文学大加挞伐。可是小说还有另一个传统,即从庄子、《史记》、唐传奇、宋元话本到明清笔记小说的中国文学传统。在这个传统里,被西方文学观念视为“废话”的闲笔,以及松散的结构等等,都是小说未被遭遇异化之前的初始形态。若是将西方文学及其影响下的大多数中国现当代小说视为谷类的话,那么这一传统和它的当代传人,如金庸等武侠小说家,就是“小一号,次一等,差一截”的稗类。[4]2这一比附当然反映了小说现代性谱系的等级秩序,但在张大春看来,小说如稗却令人“满心景慕”,因为“它很野,很自由”,人若是不欣赏它,“那是人自己的局限”。[4]3由此可见,从梳理武侠小说的叙事传统入题,在提炼出了闲笔和松散的结构等技术资源之后,张大春也就将批评锋芒指向了当今已成霸权的文学现代性神话。而附录部分也因此成为了“离心力”、“闲情与野性”这些关乎闲笔之短评的叙述先声。
在“两只小雨蛙,干卿底事——一则小说的离心力”中,张大春小试牛刀,以日本作家志贺直哉的短篇小说《雨蛙》为讨论对象,深入分析了作为闲笔之一种的“离题”问题。仿佛是为了配合小说如稗的无序而乱,张大春并不直陈其事,而是漫谈牛顿力学,用“向心力”和“离心力”之说,区分了小说叙事的两类传统:“向心力”是小说现代性神话的基本表征,它暗示着一部作品里所有的叙述话语,皆具有反映小说主题的叙述功能;反之“离心力”则意味着闲笔。一部作品里若是出现了和主题无关的描写,那么它就会以闲笔的形式造成叙述的游移和结构的松散,此即为小说的离题。以小说现代性观念来看,离题当然不是什么好事。因为它无关宏旨也就罢了,最糟糕的是离题还会以松散的叙述淡化、模糊甚至消解掉小说的主题。基于此,很多人才会将离题视为“文章的盅毒鸩祸”[4]199。
但这样的价值判断又有何意义?站在小说现代性的立场,批评家自然会指责离题对于作品统一性的破坏。事实上,除了强化现代性霸权以外,单纯的指责并不能解释如下问题,即志贺直哉这样的小说家难道不知离题的祸害?
在这部短篇小说里,志贺直哉讲述了一个外遇的故事。小关是主人公赞次郎的妻子,某晚因独居A市而与G小说家共寝一室。次日,当赞次郎接小关回家时,竟隐约从妻子“如梦似幻的眼神”里觉察到了什么。[4]200虽然志贺直哉并未实写主人公的心理活动,但返家后赞次郎烧书的细节,却颇可泄露他内心难以言说的痛楚。单从叙述功能上看,烧书当然是一种叙述的向心力,因为它以动作描写直入人心,不管是无法启齿的责难,还是悔不当初的懊丧,都将叙述的进程与外遇这一核心情节紧密相连。但就在夫妻二人归家的途中,志贺直哉却插入了一段再明显不过的闲笔,内容说的是赞次郎在路边撒野尿,无意间看到了“两只雨蛙重叠着蹲在那里”,“这幅情景使得赞次郎感动,他以亲切的感觉注视着那对雨蛙”。[4]201如此横生枝节的突兀一笔,无疑成为了小说的离心力——毕竟舍弃外遇主线而去写两只小雨蛙,绝对算得上是离题万里。
但张大春对此却另有新解。他认为按读者的阅读习惯,如果一味思考闲笔的寓意,试图在揭晓其叙述功能的基础上将闲笔变成小说的向心力,则“美学的角度便庶几没有容身的空间”。“事实上,离题是一个美学手段,也是一个叙述功能。强行为美学手段和叙述功能寻绎出它们和小说寓意之间的联系,反而是在诬陷小说作者刻意经营意义结构手段之低劣,同时炫示了评者冗赘的巧辩和机智而已”。[4]202那么,志贺直哉为什么要离题?张大春说:“此语一出,小说起飞了。因为读者和主人翁同时(无论它多么短暂)被一令人措手不及、不明就里的物事吸引了。”[4]203确实如此,当读者和赞次郎乍见两只小雨蛙时,必会因错愕不已而遗忘了小关出轨的核心事件——离心力带读者“起飞到窗外”。[4]202这便是离题的作用,它将读者和赞次郎从一个故事的困境中甩了出去,在转移注意力的同时,悠然得赏另一种奇异的美学。换言之,两只小雨蛙解放了读者和赞次郎因外遇事件而倍感焦灼的内心,它抚慰着读者和人物,同时也将叙述引向了一个犹如稗子般粗粝、同时又生机盎然的世界——离题也因此制造了主线故事以外的闲情与野性。分析到这里,张大春实际上用闲情与野性这一美学传奇,呼应了“体系解”一则中对小说应当“有序而不乱”的质疑。因为闲情与野性既是小说原初腔调的回响,也是小说在文学现代性谱系之外依然葆有活力的明证。
五、重解小说如稗的美学价值
在“叙述的闲情与野性——一则小说的走马灯”里,张大春继续深化了上述论题。只不过与“小说的离心力”一节相比,他的分析对象也从日本小说转移到了中国书场的章回小说上。这则短评虽然关注的仍是闲笔问题,但张大春的视野已然更为阔大。他不再拘泥于一部作品的细读,而是投身于历史悠久的中国说书传统,试图在此文学场域内重解小说如稗之时的美学价值。
本则短评起步于一个说书人的轶事。话说杭州有说书人某,擅讲《水浒》里的“武十回”,每每说到关键处,必一拍惊堂木,道一声“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有书迷因事外出,又怕错过了精彩段落,所以付重金央求说书人且拖它几日。收人钱财、替人办事,说书人当然会“即兴跑马、闲说扯淡”[4]205,于是由他敷衍编排的各种插叙闲话,就硬生生地以离题的方式中止了故事。直至书迷归来,情节方才得以接续前回。由于章回说部的定本大多从说书人的“凭空即兴、敷衍铺陈”里搜罗而来[4]206,因此张大春会说,定本里面的那些经典段落,极有可能来自“无名说书人的随机应变、信口开河”[4]206。而书场为章回说部所赋予的诸多插叙,又带来了一种叙述的闲情与野性。所谓“闲中着色,精神百倍”[4]206,说的正是这些离题的闲笔插叙,最终为小说制造了一种令人目不暇接的美学传奇。由此可见,若是没有这些天南海北、无所不包的即兴因素,或者说要是少了如此纷繁杂沓的走马灯式的描写,那么小说也就会少了一份美学的韵味。这说明作为一种小说的离心力,闲笔虽无助于强化主题,但它却能以讲述另类知识和制造奇异美学的方式,让小说重新回到了那个粗粝如稗却又生机盎然的文学传统。
除此之外,张大春还以《儒林外史》和《水浒》中的一些闲笔段落为对象,通过分析人物吃饭喝酒等叙事场景,一再彰显了闲情与野性所制造的奇异美学。耐人寻味的是,在这则短评的结尾处,张大春又借力打力地慨叹了一番现代读者“对小说叙述的容忍力”问题。他说这一类小说写法因其趣味太闲,而“一部毫无布局、毫无结构、渐行渐远无穷的走马灯又太‘野’”,所以读者已“无法承受这样的闲情和野性”。[4]213问题就在于,现代读者为何无法容忍无序而乱的小说?
由于中国古代小说里存在着“述史”和“演义”两大传统,因此也就导致了《金瓶梅》和《水浒传》一类的小说,不论是作为本事的历史叙述,还是作为衍生于本事之内、继而又无限延展的主题演义都变得歧义丛生——唯一可以确定的是,这些古典名著的很多故事情节,其本事都非名义上的“作者”所创。那些书场说书人在临场发挥时所添加的桥段包袱和闲言碎语,虽在定本中被名义上的作者加以了修改,但松散的结构和叙述的闲情,多少仍会被保留下来。不过对深受文学现代性神话规训的读者来说,他们已难以欣赏此类小说。这是因为世界整体性的破碎和恒定意义的丧失,使得现代读者急需文学提供一种心灵的慰藉。于是他们渴望文本的统一性,唯有这种统一性才会“以文本存在具体意义的观念来取悦我们”[5]。从这个角度看,现代读者之所以忍受不了无序而乱的小说,对那些另类的知识和奇异的美学无从欣赏,盖因我们已经失掉了这个与书场有关的文学传统。在这个传统里,说书人与听众之间无疑具有一种张大春所说的“语境契约”[4]211:听众会期待说书人的临场发挥,沉迷于口技之类的旁门左道而不能自拔,同时也会借着茶楼酒肆的人声鼎沸,共情于那些趣味十足的段子和炫人耳目的表演……倘若以此类比小说,则不得不说传统语境的失落,于今已让小说如稗的美学奇观无处容身。
综上所述,较之大陆作家的文学批评,张大春同样是一个“冷硬”派的技术主义者。他立足于中国传统小说的技术经验,既不抱持启蒙主义或自由主义的价值预设,也不认同文以载道的小说功能,而是从庄子出发,炫技似地杂论诸家,在揶揄嘲弄了一番小说的“有序而不乱”后,终以文学批评的方式揭示了小说的另一面相。尽管他的小说观与当下的文学主潮颇显隔膜,但对于大陆文坛而言,却有着反思小说现代性神话的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