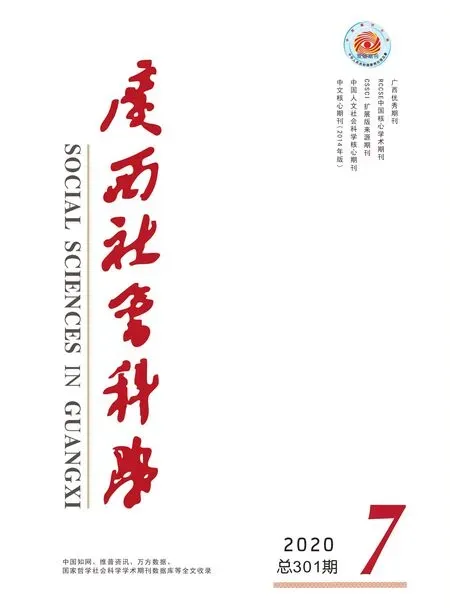民间文学到文人文学再到民间文学
——以“文学桂军研究资料丛书”之一《韦其麟研究》为中心说开去
2020-03-11
(中共广西区委党校,广西 南宁 530022)
民间文学与文人文学之间有着紧密的关联,这种关联不仅仅停留在民间文学是作家创作的原料和土壤这一传统说法上,而且作家创作的作品可以回到民间,成为新的民间文学的组成部分。这同时意味着,“民间文学—文人文学—民间文学”不是简单的循环,而是一种螺旋式的上升,民间文学与文人文学相结合,能够不断推动当代文学的新发展。韦其麟正是这样的典型,他的文学创作一方面汲取了民间文学的丰富营养,另一方面还表现出文人文学的艺术特质,也因此具备了重要的研究价值。钟世华先生编著的《韦其麟研究》一书,作为“文学桂军研究资料丛书”的第一部,近日由云南大学出版社推出并引起学术界创作界的热烈反响,尤其弥补了学术界当前有关韦其麟研究的薄弱环节。
一、《韦其麟研究》成书经过和基本内容及其当代价值
韦其麟不仅在中国当代文学史和少数民族文学史上,是一位具有代表性符号性的作家;而且在当代广西文学史和壮族文学史上,是一位壮族文学先驱和诗坛一座高峰。由于在文学界的崇高地位和诗歌创作的巨大成就,他成为广西和壮族第一位连续两届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的作家。韦其麟持续创作半个多世纪,始终受到文学界、学术界的关注,其影响远及海外。《韦其麟研究》中钟世华撰写的《韦其麟小传》,言简意赅地概述了韦其麟的民族身份、学习经历、曲折道路、创作历程和作品成就。韦其麟1935年3月4日(农历正月二十九日)出生于广西横县校椅镇壮族聚居的文村,从小学到高中一直在家乡生活读书。韦其麟从小酷爱民间文学,高中毕业之际文学创作已经崭露头角。他受到民间文学熏陶而创作的叙事诗《玫瑰花的故事》,在《新观察》杂志1953年第15期发表,接着被英文版的《中国文学》和日文版的《人民中国》转载。1953年他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二年级时在《长江文艺》1955年6月号发表叙事长诗《百鸟衣》,产生轰动效应。他与创作《不能走那条路》的青年作家李准一道在1956年春全国青年创作会议上引人注目,同年他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他经过政治运动和下放劳动的坎坷,1959年夏调到广西文联,做过《壮族文学史》编写和下乡搜集各族民间文学资料的工作,1964年元月在《长江文艺》发表以民歌形式创作的叙事长诗《凤凰歌》。1978年3月到《广西文艺》编辑部诗歌散文组当编辑。这一期间,重新修改1964年发表的《凤凰歌》,并于1979年9月出版这部长诗(二稿)的单行本。1980年3月,调至当时的南宁师范学院(现南宁师范大学),在中文系任教,并兼任该院民族民间文学研究所所长,直至1991年5月。这一时期主要作品有:1984年发表叙事长诗《寻找太阳的母亲》,并以此为书名出版共收入24首叙事诗的诗集,1987年出版诗集《含羞草》和散文诗集《童心集》,1988年出版论著《壮族民间文学概观》,1990年出版散文诗集《梦的森林》。1991年4月,在广西第五届文代会上当选为广西文联主席,后调到文联就职,并担任党组书记。1996年、2001年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五、六届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第五、六届副主席,之后被聘为第七、八、九届名誉副主席。这一期间主要作品有:1994年出版诗集《苦果》;2002年出版《广西当代作家丛书·韦其麟卷》,内收入未发表的新作《普洛陀,昂起你的头!》,这是一部20世纪90年代创作的叙事长诗;2008年出版以散文诗为主的短文集《依然梦在人间》;2012年出版散文集《纪念与回忆》。
著名文学评论家容本镇教授在《韦其麟研究》的序言中对成书的经过作了披露。韦其麟先生取得了丰厚的创作成果与卓越的文学成就,为人处世却极为谦逊与低调,晚年更是深居简出,极少参加文学界及各种社会活动,几乎不接受媒体及业界人士的任何采访。青年学者钟世华编著《韦其麟研究》,需要大量资料,迫切地希望得到韦其麟先生的同意与支持,但他心里一直没底,因为多年前他曾吃过一次“闭门羹”。2011年,钟世华开始做“当代广西本土诗人访谈”项目,第一个列为访谈对象的就是韦其麟先生。但当他打电话联系这位德高望重的老诗人时,却被婉言谢绝了。韦其麟后来在致友人的信中谈到了婉拒的理由:“多年前,他曾打电话给我,说希望对我作一次关于诗歌的访谈。由于年纪的老去,思维的迟钝和保守,对报刊上有些关于诗歌的说法和诗歌作品,也看不懂。自觉得实在谈不出什么名堂,如硬着头皮装懂乱说一通,恐怕只有出丑的份。我感谢他的好意,对他坦率说了我的心思。他也爽快,免了那次访谈。这是我和他没有见面的最初的交往。”(韦其麟《致友人》)2015年《穿越诗的喀斯特——当代广西本土诗人访谈录》一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后,钟世华向韦其麟赠送了一本。书中虽然没有韦其麟的访谈资料,但他对这部访谈录却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由于受到感动而产生信任,当钟世华再次拜访韦其麟先生时,他没有拒绝。其后随着接触和交往的增多,两人逐渐成了“忘年交”。韦其麟经历过许多风雨,其工作单位、工作地点曾多次变动,很多原始资料自己并未保留下来。加上时间久远,有的资料非常难找,在广西区内图书馆和网上都查找不到。钟世华便委托朋友到京、津、沪等地的图书馆查找,甚至委托国外的朋友帮忙查找或购买相关资料。他从一条线索发现另一条线索,并一直追踪下去,直到查找到相关资料为止。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并不是简单的归拢与分类,实质上是需要学者本人具备相当高的学养、识见和判断力的,而资料的搜集整理又往往与学术研究本身密不可分。钟世华一边搜集整理《韦其麟研究》资料,一边对韦其麟及其作品进行持续而深入的研究。他连续撰写了《壮族身份认同中的民族寻根与文化守护——韦其麟诗歌研究系列之一》《壮族诗人韦其麟的诗语意象探究》《〈百鸟衣〉的经典建构与影响焦虑》等多篇学术论文,还主持完成了一项广西哲学社会科学课题“韦其麟年谱长编”[1]。这些研究及成果,为《韦其麟研究》的编著奠定了基础。
《韦其麟研究》一书,对著名诗人韦其麟自新中国成立至21世纪初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研究成果和研究资料进行了收集与整理,主要内容包括韦其麟小传、研究综述、自述、访谈和印象、评论文章选辑、附录,全书长达58.5万字;书中收入韦其麟图片34张,自述文章29篇,访谈和印象文章10篇,评论文章31篇;附录收入韦其麟书目11部,列举的文学史有关韦其麟的章节目录45处,其著作年表涉及时间年限56年,存入诗文目录共610多篇;该书立足前人研究成果,对韦其麟研究资料再次进行了整理和充实,不少内容为独家首次披露,以翔实的文献资料,为深入研究诗人韦其麟提供了大量的佐证材料[2]。
《韦其麟研究》的当代价值是多方面的。一是前所未有地全面梳理了韦其麟的创作脉络,展示了其作品概貌,完整地提供了韦其麟著作系年(1956—2012年)、韦其麟作品索引(1953—2015年),为评价中国当代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提供了一个鲜活的范本。二是选辑了文学史有关韦其麟的章节,精选了对韦其麟的评论论文、访谈记忆、个人自述的比较完整的资料,改变了韦其麟研究的碎片化现象。三是不辞劳苦、不怕麻烦,深入调查研究,面对面采访不愿意张扬的当事人,首次披露独家获取的不为人知的第一手材料,这在作家年事已高的情况下带有抢救史料的性质。四是有利于当代青年作家学习韦其麟胸怀人民群众、扎根壮乡沃土、从民间文学做起的草根精神,传承韦其麟创造的以民族文学和地域文学为特征的文脉,守正创新,创作更多更好的文学精品,推动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五是《韦其麟研究》作为“文学桂军研究资料丛书”一个为文学桂军建档立传的开创性成果,对丛书研究人员以聪慧的眼光、敏锐的识见和严谨的学术精神,恰切地处理好丛书编撰遇到的难点和问题,切实编著好一套有质量、有分量的“文学桂军研究资料丛书”,有一定的示范借鉴作用,是拓展桂学研究领域、提升桂学学科高度的一部创新之作。
二、从《百鸟衣》看民间文学与文人创作
以《韦其麟研究》为中心,综观韦其麟作品全貌和中国当代文学有关史料,长篇叙事诗《百鸟衣》无疑是韦其麟的成名作、代表作和最具影响力的杰作。正是这首诗确立了韦其麟在当代诗坛的地位。韦其麟在武汉大学中文系读书时,年仅20岁,就在《长江文艺》1955年6月号上发表了叙事长诗《百鸟衣》。接着《人民文学》1955年7月号和《新华月报》1955年7月号相继转载。1956年4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百鸟衣》单行本,并附有韦其麟的《写〈百鸟衣〉的一些感受和体会》。《百鸟衣》的发表,在广大读者中引起热烈反响,受到文艺界同人和高层的关注。周扬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学的任务》的报告中,曾把它和《阿诗玛》放在一起,同誉为这一时期的文学珍品。而且《百鸟衣》很快传播到了国外。1956年3月31日苏联的《文学报》发表了奇施柯夫的文章,文中说:“人民革命胜利以前,中国各少数民族身受国民党国家层层机构和地方封建地主的双重压迫。那时,根本谈不上发展民族文学和文化。只有解放以后,他们才能在中国兄弟民族的大家庭里创立新的生活。过去六年来,国内少数民族作家和诗人的创作大大地丰富了中国文学。内蒙古青年作家玛拉沁夫享受到崇高的声誉,撒尼人民创作的优美的长诗《阿诗玛》,维吾尔族人,藏族人和其他民族的童话和传说已获得广大读者的热爱。韦其麟的长诗《百鸟衣》在这些作品中占有自己一定的地位。”[3]
据《韦其麟研究》“文学史有关韦其麟的章节目录”所载,从1961年7月至2016年12月,共有35家国内外出版社出版的45部关于中国当代文学史的著作教材,对《百鸟衣》和韦其麟文学创作作出了正面评价,有的列出专章专节评论。包括广西壮族文学史编辑室、广西师范学院中文系的《广西壮族文学·初稿》,华中师范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稿》,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十年来的新中国文学》,林曼叔、海枫、程海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稿·1949—1965·大陆部分》,张钟、洪子诚等的《当代文学概观》,郭志刚等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胡仲实的《壮族文学概论》,华中师范学院编写组的《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中国当代文学》,杨亮才等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汪华藻、陈远征、曹毓生等的《1949—1982中国当代文学简史》,公仲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编》,二十二院校编写组的《中国当代文学史·3》,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教育学院系统分会的《中国当代文学十讲》,邱岚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中南民族学院的《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稿》,吴重阳的《中国当代民族文学概观》,中南五省(区)师专的《中国现代文学·下编》,高文升、单占生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稿·上册》,湖南师范大学的《新中国文学史(试用本)》,雷敢、齐振平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刘文田等主编的《当代中国文学史》,梁庭望、农学冠的《壮族文学概要》,姚代亮主编的《当代中国文学》,黄绍清的《壮族当代文学引论》,洪子诚、刘登翰的《中国当代新诗史》,曹廷华、胡国强主编的《中华当代文学新编》,黄子建、佘德银、周晓风的《中国当代新诗发展史》,张炯等主编的《中华文学通史·第八卷·当代文学编》,叶志刚、智川的《中国少年民族作家文学》,特·赛音巴雅尔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特·赛音巴雅尔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当代文学史》,马学良、梁庭望、张公瑾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修订本·下册),王庆生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唐金海、周斌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通史》,程光炜的《中国当代诗歌史》(上篇),黄修己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李建平、王敏之、王绍辉等的《广西文学50年》,李云忠的《中国少数民族现代当代文学概论》,周作秋、黄绍清、欧阳若修、覃德清的《壮族文学发展史》,雷锐主编的《壮族文学现代化的历程》,张健主编的《新中国文学史》(上卷),谭伟平、龙长吟主编的《现代中国文学教程》,钟进文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基础教程》,张炯主编的《中国文学通史·第十卷·当代文学》(上),梁庭望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诗歌卷》等。关于韦其麟和《百鸟衣》的论文、访谈、新闻更是达数百篇之多。
韦其麟《百鸟衣》取得如此闪光的成就,与壮族丰富的民间文学有着很大的关系。民间文学是指民众在生活文化和生活世界里传承、传播、共享的口头传统和语词艺术。从文类上来说,包括神话、史诗、民间传说、民间故事、民间歌谣、民间叙事、民间小戏、说唱文学、谚语、谜语、曲艺等。民间文学和文人文学都来自人民广阔的社会生活,源头在文字产生以前的原始社会。民间文学常常被称为口头文学,归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其显著特征是众人创作,口口相传。博大精深的民间文学,作为人类的文化宝藏,是孕育文人文学的母体。《百鸟衣》文本作品的出现绝不是偶然的。韦其麟生活在壮族山乡,在学习劳动中长期受到壮族民间文学耳濡目染,加上他特有文学敏感和创造能力,才能够创作出带着壮乡神韵、饱含乡土气息的《百鸟衣》这样的作品。
民间文学与文人文学相结合,有三种方式。第一种,文化人对流传于民间的故事、传说、神话、史诗、歌谣、谚语、民俗等进行收集整理,在保留故事雏形、人物典型和语言要素的前提下,将口头文学变成书面文字,如刘三姐故事,桂林山水传说等;第二种,文化人收集已经成型、世代流传的民间文学史诗一类作品,保持原汁原味,将多种版本整合,语言疏通,改正错误,弥补漏洞,使之成为书面作品,如云南彝族撒尼人使用口传诗体语言讲述或演唱的《阿诗玛》,藏族民众集体创作的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等;第三种,作者生活在某种民间文学浓郁的环境中,或者经常深入民间采风,汲取民间文学的养料,受到故事主题和情节细节及语言技巧的启发,重新构思,进行再创作。第一种方式由传承人口述,文化人记录整理,产生的是纯粹的集体创作的民间文学作品;第二种方式是文化人通过传承人发现民间文学宝库,将已经成型的口头书稿挖掘出来,加以鉴别梳理,产生的是价值巨大的集体创作的民间文作品;第三种方式是文化人依据民间文学的素材,发挥创作的主观能动性,开展有个人思维方式和审美特点的创作劳动,作品属于作者独立创作,由个人署名,作者享有著作权。
《韦其麟研究》中多篇文献证明:韦其麟《百鸟衣》无疑可归于第三种创作方式。《百鸟衣》是韦其麟受到壮族家乡民间文学感染,汲取民众传说的百鸟衣故事元素,而重新构思,独具慧眼地选择体裁,首次运用长篇叙事诗表达的个人独创的作品。在民间传说的基础上,韦其麟对故事情节、人文塑造、活动细节、民俗语言等进行了大胆的创造,赋予作品具有社会进步意义的新思想、新主题,甚至于连男女主人公古卡和依娌的名字都是韦其麟取的。关于《百鸟衣》与民间文学的关系,韦其麟在《〈百鸟衣〉前记》中作了回答:
许多年来,我看到或听到一些介绍壮族文学的文字或发言,有“‘《百鸟衣》’是壮族民间长诗”“壮族有民间长诗《百鸟衣》”等说法。我认为这是不确切的。百鸟衣的故事并没有以诗歌的形式在壮族民间流传。壮族民间文学经过几十年的发掘搜集,至今也未发现诗歌体裁的这个故事。这部作品是根据民间故事而创作的长诗,而不是经过壮族民间原有的长诗整理出来的产物。整理和创作并不存在谁高谁低的问题,但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和范畴,两种性质不同的工作,应该加以区分。民间文学作品和作家创作的作品也不应混同,特别是对民间文学的研究,必须严格地科学地区别[4]。
这个观点得到评论家和文学史的普遍认可。郭辉在《从韦其麟等作家的创作实践谈神话传说与作家文学的关系》一文中,肯定韦其麟把古老的、丰富多彩的民间神话传说或借鉴,或改编,熔炼成为具有自己风格、具有时代气息的作品,《百鸟衣》正是作者成功地借鉴运用了壮族神话传说这一题材,并给它注入新鲜血液,使得古老的文学形式在今天又焕发出奇异的光彩[5]。张炯主编的《中国文学通史第10卷·当代文学·上》说得更清楚,韦其麟的“《百鸟衣》取材于壮族民间故事《百鸟衣的故事》(又名《张亚源和龙王女》),汲取了民间故事的基本情节,同时从现实生活出发,加以合理的改造和大胆创作,使本来具有不同程度神异色彩和‘皇权’思想的简单故事,成为更加合乎生活情理,歌颂劳动,赞美真挚爱情,颂扬人民反封建斗争精神的优秀长诗”,“长诗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既定时代的局限性而获得了民间艺术永恒的审美价值”,并在注释中指出,“由于《百鸟衣》脱胎于民间故事,并与民间文学资源间保持了较直接的关系,以至于连文学理论家周扬都误认为《百鸟衣》是‘经过整理和改编的民间创作’,并把它与撒尼人的《阿诗玛》同视为‘经过整理和改编的民间创作的珍品’。周扬的这个错误恰好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当代少数民族诗歌与民间资源间的直接的血缘关系”[6]。
三、民间文学与文人创作的双向流动
源远流长的民间文学不仅给文人创作提供素材,而且是文人生活的文化环境和创作生成的土壤。从这个意义上说,扎根于广阔社会生活的民间文学及其民众作者是作家的母亲。在中国文学史上,有许多作家利用民间神话传说素材进行创作的事例。战国时代的大诗人屈原,所著的《离骚》《天问》《九歌》等不朽名篇都广泛汲取了神话传说,成为古代积极浪漫主义的典范。汉代的司马相如、扬雄、张衡等著名辞赋家,晋代的陶渊明,唐代的李白、杜甫、白居易、李贺、李商隐等诗人,无不具有深厚的民间文学功底。
韦其麟当然也不例外,《百鸟衣》就是一个从取材、立意到表达都受益于民间文学的典型。《百鸟衣》在《长江文艺》发表不久,韦其麟即明确告诉读者:他之所以能自觉地以本民族的神话为题材进行再创作,与他从小生活的环境和文化陶染有关。壮族文化将韦其麟哺育成人。他小时候,每到晚上,就喜欢坐在大榕树下,听老人讲着那古远的、永远也讲不完的故事,百鸟衣的故事就是其中最打动人的一个。这许许多多故事,滋养了韦其麟的童年时代,造就了韦其麟“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艺术风格。
从民间文学到文人创作的正向流动,印证了社会生活是文学的源泉的原理。从韦其麟创作《百鸟衣》的体验我们看到,正是有了对本民族文化生活的熟悉和理解,有了对这些文化的挚爱和敬重,才使得作家产生为人民代言、为民族而歌的冲动,作品才蕴含着浓郁的民族情愫。民间文学是作家创作的活水源头,是作品成功之本。作家敬畏民间文学,拜民间文学传承人为师,从民间文学中获得养料,激发出灵感,才可能创造出紧接地气、具有草根精神、为人民大众喜爱的优秀作品。
不能否认,文人创作对提高民间文学思想性艺术性影响力有重要的作用。韦其麟创作《百鸟衣》,不是直截了当地将听到的百鸟衣故事还原,而是进行了艰苦的创造性劳动,用诗意的语言改造了原来比较粗俗的口语叙述,对一些重要情节和关键细节作了重新安排,对人物形象从姓名到行为重新塑造,使之更符合生活逻辑、民族环境和民族性格。特别是对民间传说的主题进行了升华。从作品的篇幅上来看,非遗传承人韦世族口述的百鸟衣传说,经过整理,不到400个字,故事比较简单。1961年7月出版的《广西壮族文学·初稿》最早记述这个故事,字数和《广西民间故事辞典》收录的相差不大[7]。而韦其麟创作的《百鸟衣》不仅主题深邃、结构紧凑、情节曲折,篇幅也大得多,1956年4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百鸟衣》单行本,60多个页码,共4章1000多行。
作家依据民间文学创作的优秀作品,一方面可以比原作更真实、更集中、更典型,也就更有审美价值;另一方面还更适宜通过现代印刷和商业途径,以及现代网络传媒,产生更大的覆盖面和影响力。《百鸟衣》单行本,仅1956年至1964年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就印刷5次,达30多万册。加上国内其他出版社出版和多国翻译出版,韦其麟创作的叙事长诗《百鸟衣》在中国当代文学诗歌创作和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毋庸置疑,在民间文学向文人创作正向流动的同时,文人创作也向民间文学逆向流动。民间文学向文人创作正向流动,夯实了作家的民族文化根基,丰富了作家创作的内容;而文人创作向民间文学流动,激活了古老的民间文学,使之在新的作品母体中适应现代社会而重生。在双向流动中,我们一方面必须对民间文学有敬畏心理,仰慕劳动人民的伟大创造,吸取原始口头作品的艺术和智慧,绝不能歪曲糟蹋人民喜爱的、世代相传的故事传说和神话歌谣,丑化抹杀民间相传的英雄人物。另一方面,应当尊重作家的创作,承认作家的劳动果实,保护作家的署名自由和著作权,褒扬作家对民族民间文学发展的贡献,鼓励作家艺术家通过创造性的工作,传承弘扬民间文艺经典。
就此而言,民间百鸟衣故事与韦其麟叙事诗《百鸟衣》双向流动,民间百鸟衣故事流向韦其麟《百鸟衣》长诗,哺育了韦其麟的民族情怀,激起了作者的创作欲望和灵感;韦其麟《百鸟衣》流向民间,为广大读者所接受,在民间广泛流传,反哺了原有的百鸟衣神话传说,在民间出现了百鸟衣故事的现代版。2009年笔者与甘安顺、凌海金、谢平祥等学者到韦其麟的故乡广西横县调研,在听取编创人员介绍戏剧《百鸟衣》的剧本后,笔者当即表示这些“民间故事”的内容语言,基本来自韦其麟的《百鸟衣》,可见韦其麟《百鸟衣》在他的家乡已经深入人心,成为家喻户晓的“民间故事”。
1955年韦其麟创作的《百鸟衣》发表,随后几年至“文革”前,《百鸟衣》成为多种艺术形式改编的题材,广西各地出现创作编演邕剧、粤剧、壮剧、歌舞剧等的热潮。1996年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发行动画片《百鸟衣》,2013年南宁市艺术剧院推出大型壮族歌舞剧《百鸟衣》,均取得成功。南宁版的舞剧《百鸟衣》在广西区内外演出时收到了令人瞩目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这些改编自《百鸟衣》的动漫、歌舞、戏剧作品虽然在剧情简介和演出字幕中均标榜依据民间文学百鸟衣创作,但实际上它们在不同的程度上采纳了韦其麟《百鸟衣》的成果,演绎了韦其麟很大部分虚构的壮族贫苦农民古卡和他的妻子依娌的故事,而不仅仅是青年张亚原与小龙女的神话传说。实际上,韦其麟根据小时候在村头大榕树下听老人讲的一个故事所创作的同名叙事长诗《百鸟衣》,在国内迅速传扬,还被译为英、法、意、日等13种文字远传海外。这对于后来者改编的各种艺术形式的作品的传播具有扩大效应。借助著名作家韦其麟和长诗《百鸟衣》的名声,可以提高新作品的知名度和票房价值,讲好广西故事,传承民族精神。
民间文学与文人创作的双向流动,不是简单地对流,而是相互影响、相得益彰,在双重转化中螺旋式上升。民间文学与文人创作,从来就不是绝对的,特别是在这个文化文字普及、互联网迅猛发展、几乎人人有手机的新时代,口头文学可以迅即变成书面文学,这种双向流动可以说是瞬息万变。我们应该积极主动地应对双向流动,促进文学艺术向更高层次、更好质量发展。
《韦其麟研究》给我们的启示是多方面的。传承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国家实现伟大复兴的必要条件和重要任务。传承弘扬首先是传承,没有传承,弘扬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青年学者虔诚地向老一辈文艺家学习,不辞劳苦搜集挖掘民族民间文化宝藏,系统地加以研究,大有可为;守正创新,对优秀传统民族文化创造创新转化发展,必须不厌其烦地从一个个案例做起;应坚持“双向流动”与“双重转化”,实现民间文学活化永世长存,根植于民间文学的文人文学,才能以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民族特色更好地走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