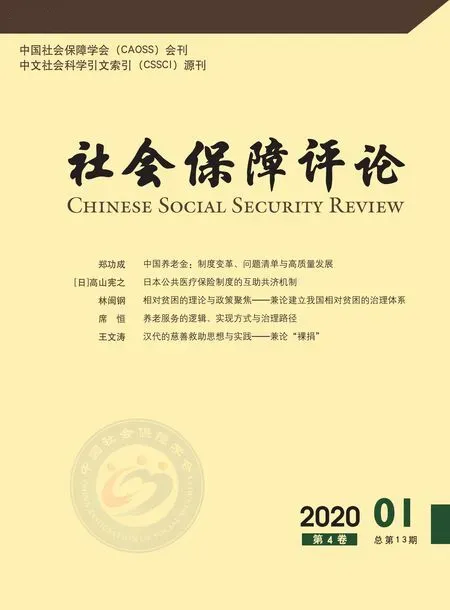可持续生计视角下“参与式”反贫困路径探索
2020-03-11王一
王 一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走出了一条有特色的扶贫道路,从“开发式扶贫”到“精准扶贫”,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扶贫成效,农村贫困发生率①按照2011年中国农村贫困线标准计算。从1978年的97.7%下降到2018年的1.7%②参见陆娅楠:《2018年中国农村减贫1386万人》,《人民日报(海外版)》2019年2月15日。,并且正在致力于到2020年历史性地解决绝对贫困问题。2020年后,面对新的贫困现象和贫困结构,需要重新审视贫困问题,把握贫困现象和贫困结构,形成科学合理的反贫困策略。后2020贫困问题所面临的变化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从广泛的“社会动员”到常态化的反贫困制度。脱贫攻坚是新时期的民生底线和头号民生工程③李志明:《习近平关于精准扶贫重要论述及其实践路径研究》,《社会保障评论》2019年第2期。,绝对贫困问题被视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的突出短板,扶贫开发工作作为重大政治任务,采取了广泛社会动员和资源投入的策略,这有助于迅速解决绝对贫困问题,但当绝对贫困逐渐成为历史,脱贫攻坚应当过渡为常态化的反贫困制度,使反贫困成为国家治理体系中重要、稳定的组成部分,形成既能够真实反映、满足社会成员基本需求,又能够符合经济社会发展环境的贫困治理体系。
二是从以“绝对贫困”为主体,到以“相对贫困”为主体。贫困标准的确定通常有基本需求法和相对收入法两种方法。基本需求法源于“生物学”意义上对贫困问题的界定,认为贫困是“总收入不足以获得维持体能所需要的最低数量的生活必需品”①阿马蒂亚·森著,王宇等译:《贫困与饥荒》,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9页。,与绝对贫困相对应。相对收入法则将全部人口中收入较低的一定比例的人口认定为贫困人口,与相对贫困相对应,例如欧盟将家庭可支配收入低于平均水平的60%确定为贫困人口②汪三贵等:《从区域扶贫开发到精准扶贫——改革开放40年中国扶贫政策的演进及脱贫攻坚的难点和对策》,《农业经济问题》2018年第8期。。也就是说,以基本需求为基础的绝对贫困现象是可以解决的,但基于人际比较的相对贫困则是永恒存在的,如何认定相对贫困取决于对贫困的认识和贫困标准的确定。中国政府于1985年首次制定了中国的农村贫困线,国家统计局将人均营养标准确定为每人每天2100大卡,然后根据20%的低收入人群的消费结构测算出满足这一标准所需要的食物量,再按照食物的价格计算出相应的货币价格,标准为每人每年206元③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中国发展报告2007:在发展中消除贫困》,中国发展出版社,2007年,第32页。。2011年,中国政府以2010年不变价2300元为基数制定了新的农村贫困标准,新标准在满足2100大卡的食物摄取基础上,同时满足了每人每天60克的蛋白质需求④李小云等:《中国减贫四十年:基于历史与社会学的尝试性解释》,《社会学研究》2018年第6期。。目前的扶贫对象就是低于农村贫困标准的贫困群体。可以看出,中国现行的农村贫困标准是以基本生存需要为依据的绝对贫困线,而当绝对贫困问题基本解决后,就需要科学合理确定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相对贫困标准。
三是从以农村地区为主体,到农村与城市并重。改革开放初期,在以农村、农业、农民为主体的社会形态下,中国的扶贫工作主要针对农村居民。但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环境的变化,城市贫困问题日益突出,支出型贫困家庭、临时性贫困家庭、下岗失业群体、长期失业(无业)群体、贫困流动人口群体、长期失业群体、贫困老龄群体、贫困残疾人群体、困境儿童群体等困难群体的贫困问题凸显,以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核心的社会救助体系正在发挥重要作用,但仍然需要更加系统、综合的解决方案。与此同时,在农村地区,当绝对贫困问题解决后,既要防止贫困人口返贫,又要预防产生新的绝对贫困人口,更要形成符合现实的“相对贫困”治理体系。而数以亿计的进城务工人员又将城市和农村的贫困问题链接起来,随着我国城镇化发展和农民工的代际更替,一大批20世纪80、90年代出生的农民工到城市“寻梦”,但在就业、看病、住房、子女入学、权益保护等方面,仍面临一系列难题⑤李培林:《中国改革开放40年农民工流动的治理经验》,《社会》2018年第6期。。因此,在新的社会环境下,贫困是城市和农村共同面对的问题,需要形成“城乡并举”的贫困治理体系。
综上,本文致力于针对2020年绝对贫困基本解决后的新贫困问题,采用多元贫困视角,把握贫困现象和贫困结构,形成科学合理的反贫困策略,制定更具包容性和可持续性的常态化反贫困制度,解决农村和城市的相对贫困问题。
二、转向“可持续生计”的贫困治理逻辑:“多维贫困”视角与“权利-义务”平衡的整合
贫困问题研究是当前的学术热点,但当面对“什么是贫困”“怎样看待贫困”等根本性问题时,却仍处于模糊状态。从历史角度看待贫困,我们会发现人类社会经历了漫长曲折的发展历程才最终摆脱了“穷人应该受穷”的观念,18世纪末,在让-雅克·卢梭、亚当·斯密、伊曼努尔·康德等伟大思想家的共同努力下,在法国大革命的洗礼下,救济穷人开始从“恩惠”逐渐成为“国家义务”。到了20世纪中期,在公民权利理论、现代分配正义原则不断成熟的背景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凯恩斯-贝弗里奇”为指导,建构了以“福利权”为基础的福利国家体制。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经济增速放缓与福利国家危机相伴而生,资本主义福利国家普遍开始寻求以削减福利开支、促进就业为核心的转型之路,此间出现的各种理论思潮是距离我们最近的、鲜活的思考与争论,对于我们理解贫困问题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这段时期的贫困治理逻辑从整体上来看有两条线索,即对“福利权”的反思,以及多维贫困观的形成。
从第一条线索出发,这一阶段的贫困治理思潮可以被看作是对理查德·蒂特马斯及准蒂特马斯学派的批判和反思。在20世纪中期至70年代期间,蒂特马斯关于贫困和福利的学术思想在西方社会占据主导地位,在蒂特马斯看来,“贫困问题不是个体特征和任性的问题,而是经济和工业组织的问题”①参见 Richard Titmuss, "Social Administration in a Changing Society," Essays on the Welfare State, London, Unwin University Books, 1970.,因此福利必须是普及性和非判断性的,而且蒂特马斯认为通过这种再分配过程能够促进社会整合并鼓励伙伴关系。利己主义福利学派的代表人物默里在20世纪80年代率先对蒂特马斯的观点提出反对意见,默里认为非判断性的福利制度导致“隐形贫困”的出现,很多处于工作年龄的年轻人选择退出劳动力市场、非婚生育、依靠福利生活,“这种社会政策正在引导人们相信他们无需为其生活负责。这样的政策是抑制人们追求幸福,是相当不道德的”。②参见Charles Murray, In Pursuit of Happiness and Good Government, New York, Touchstone Books, 1988.政府的努力方向应当是形成“个体为自己负责”的环境和政策。查尔斯·默里的观点引起前所未有的争论和批判,也正式拉开了贫困治理争论的帷幕。家长式福利制度的代表人物劳伦斯·米德认为当时福利政策的主要问题在于过分强调对穷人的收入或物质救济,而忽略了帮助穷人履行公民义务的重要性。“我认为部分原因是联邦政府支持弱势群体和失业人群的措施是宽容的,而不是强制的。也就是说,联邦政府把救助给予受助者,但是很少规定条件,以鼓励他们在社会中承担责任和义务作为回报。”③参见Lawrence Mead, Beyond Entitlement, New York, Free Press, 1986.在米德看来,长期处于贫困状态的人群有强烈的“失败感”,缺乏与其他群体一样的协调能力,以至于不会对经济激励政策做出任何反应。因此,家长制福利视角要求政府转变角色,要求个人获得福利的权利受制于其个人的行为条件,那些依赖救济的人将失去福利、机会和政策激励,也就是说,如果穷人享受同样的公民权利,那么他们必须和其他人一样,履行同样的责任和义务。米德的观点基于两个假设,一是失去工作是长期贫困和福利依赖的主要原因,二是穷人没有工作是因为其缺乏能力和品质。这两个假设引起了巨大争议,但也引起了各种福利视角对福利依赖的警觉和反思,而且对工作和公民义务的强调逐渐鲜明。社群主义思潮对责任和公共利益的强调,也在客观上推动了社会政策在权利与责任、惩罚与归谬之间建立一种更为清晰的联系,试图“跳出左翼和右翼思潮之间的原有争论,建立第三种社会哲学”①阿米泰·埃齐奥尼著,吴继淦等译:《通向和平的艰苦道路:一种新的幸存战略》,世界知识出版社,1964年,第78页。。这一点在安东尼·吉登斯的第三条道路思想中得到了更突出的体现,强调权利和义务的平衡、拓宽有偿就业机会、重建公众对福利的支持。一种新的“普遍观点”出现,平等、社会融合、社会保障和机会均等等古典美德让步于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社会政策是一种应加强经济增长和国家在世界市场中竞争力的公共投资。②克劳斯·彼得森:《为福利而增长还是为增长而福利?北欧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之间的动态关系》,《社会保障评论》2019年第3期。
从第二条线索出发,传统的贫困问题研究通常将收入作为判断贫困的重要标准,直到可行能力理论的出现,才根本改变了人们仅关注贫困者收入这一重点,转向了贫困者自身能力这一核心问题。③林闽钢:《激活贫困者内生动力:理论视角和政策选择》,《社会保障评论》2019年第1期。20世纪末,阿马蒂亚·森提出“可行能力”视角,认为“可行能力”是个体有可能实现的、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组合的实质自由,贫困必须被视为基本可行能力的被剥夺,而不仅仅是收入低下④阿马蒂亚·森著,王宇等译:《贫困与饥荒》,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9页。。在阿马蒂亚·森的主张和参与下,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发布的《1990年人类发展报告》在能力方法理论框架下颁布了“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简称HDI),提出了预期寿命、受教育年限、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等3个层次的概念体系;《1997年人类发展报告》中进一步提出了“多维贫困指数”(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Index,简称MPI),其中的指标包括寿命、读写能力、生活水平等3个维度,致力于反映不同个体或家庭在不同维度上的贫困程度,为贫困问题研究提供了更为丰富的研究视角。
综合两条线索,20世纪末,联合国计划开发署(UNDP)、世界银行(WB)、英国国际发展部(DFID)等国际组织推动形成了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并成为研究贫困问题的重要工具。生计作为一种谋生方式,是以能力(Capabilities)、资产(Assets)、活动(Activities)为基础的综合性概念体系⑤参见苏芳等:《可持续生计分析研究综述》,《地球科学进展》2009年第1期。,可持续生计通常被认为是“某一个生计由生活所需要的能力、有形和无形资产以及活动组成。如果能应付压力和冲击进而恢复,并且在不过度消耗其自然资源基础的同时维持或改善其能力和资产,那么该生计具有可持续性⑥参见杨云彦等:《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下农户生计资本的调查与分析——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库区为例》,《农业经济问题》2009年第3期。”。而“消除贫困的大目标在于发展个体、家庭和社会改善生计系统的能力”。⑦纳列什·辛格、乔纳森·吉尔曼:《让生计可持续》,《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2000年第4期。目前学界广泛采用的可持续生计框架通常将生计资本划分为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自然资本(Natural Capital)、物质资本(Physical Capital)、金融资本(Financial Capital)和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国内很多学者借助这一框架对我国贫困问题进行了多维度的分析和研究。⑧郝龙:《“行动者导向”反贫困——基于生计实践过程的贫困问题治理》,《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8年第6期。可以说,“多维贫困”视角与“权利-义务平衡”反思共同构成了当前贫困治理的理论与价值基础,而可持续生计框架提供了一种可行的整合思路。
三、可持续生计框架下的贫困治理效果实证分析:基于形成型指标结构方程模型
可持续生计框架已经成为贫困治理的重要实践策略,在我国的贫困治理当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事实上是“多维贫困”视角与“作为义务的权利”理念的一种融合,倡导一种以行动者导向为基础的“可持续生计”解决方案,将“脱贫”理解为贫困者在生计要素、生计偏好和生计环境等条件下,通过生计策略的选择与实践来应对潜在风险和追求可持续生计的自主行动过程。运用可持续生计框架来分析我国的扶贫战略,可以看出我国的扶贫工作是从改善外部条件和提升内生能力两个层面展开的。一方面,“精准扶贫”政策致力于突破长期沉淀于社会结构中的各种制约因素,大力推动农田水利、村级道路、危房改造等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充分发挥产业扶贫、金融扶贫作用,重视“扶贫扶志”,将提升生计的可持续性作为实现稳定脱贫的依据和路径。这两个层次的综合体现了在改善生计环境和生计要素的基础上提升贫困者的可持续生计层次,“两不愁、三保障”等标准也表现出多维贫困理念。也就是说,我国的贫困治理实践既体现了“权利-义务平衡”的理念,又倾向于“多维贫困”的衡量标准,很好地体现了可持续生计理论的核心思想。接下来,本文将在可持续生计框架下分析我国贫困治理的效果和影响因素。
(一)模型建构与结果分析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课题组于2018年12月—2019年2月期间在吉林省开展的问卷调查。吉林省属于经济欠发达省份,但不属于“三州三区”,完全没有接受“现代性”的“孤岛”地区几乎不存在,农村居民的致贫因素大都是更具普遍性的病、残、孤、寡、灾,能够比较客观观察可持续生计框架的有效性。此次问卷调查采取多层次分层抽样的方法,以经济发展水平和地理位置为依据选择5个国家级贫困县(含已退出)进行调查,分别是:吉林省延边州和龙市、吉林省白城市镇赉县、吉林省白山市长白县、吉林省延边州图们市、吉林省白城市通榆县,每个县(市)根据经济发展水平抽取3个乡镇(在所选县域范围内经济发达、经济中等发达、经济欠发达各选择1个乡镇),共抽取15个乡镇,每个乡镇抽取100户左右,累计发放1500份问卷,累计回收有效问卷1341份,回收率89.4%。
本文通过建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生计资本对多维贫困的影响,结构方程模型通常有形成型指标模型和反映型指标模型两种,多维贫困和生计资本都属于难以直接、准确测量的“潜变量”,而形成型指标模型基于变量的协方差矩阵分析变量间关系,能够较好地解释潜变量、测量变量之间的显著性,同时并不要求测量变量的正态分布,允许较高的自由度。潜变量之间因果关系及潜变量与测量变量之间关系的方程表达式分别为:
η=α+г ξ+ζ①η为内生潜变量向量,即农户多维贫困;ξ为外生潜变量向量,即生计资本;α为常数项,г为路径系数,ζ为残差。
η=Пyy+δy②y是η的测量变量,П是多元回归系数矩阵,δ为残差项。
ξ=Пxx+δx③x是ξ的测量变量,П是多元回归系数矩阵,δ为残差项。
在变量选择上,目前多维贫困的维度、指标、权重都没有统一的标准,本文参考国际通用的多维贫困指数(MPI)④MPI指数选取了健康、教育、生活水平等3个维度测量贫困,总共包括10个维度指标:营养状况、儿童死亡率、儿童入学率、受教育程度、饮用水、电、日常生活用燃料、室内空间面积、环境卫生和耐用消费品。,结合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贫困现状、数据可获得性,选择了健康与医疗、教育与就业、生活质量、收入等4个维度,健康状况、子女营养、医疗保险等15项指标。在多维贫困测量中需要确定剥夺临界值,达到临界值则说明受访者在某一维度陷入贫困,详见表1。生计资本一般分为人力资本、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本文结合基本国情和数据可获得性形成了相应的维度和指标,采用等权重法,详见表2。

表1 多维贫困指标

表2 生计资本变量及描述性统计
本文运用SmartPLS3.0软件分析3个结构方程式,模型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变量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拟合优度较好(详见表3、表4)。

表3 变量的信度系数① 通常α信度系数在0.7以上为好,0.4—0.7之间为中等,低于0.4为较差。

表4 变量多重共线性检验结果(VIF值)② VIF值小于10即说明变量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
从生计资本对多维贫困的直接效应来看,金融资本改善多维贫困的效应最大(系数为-0.465,路径调节系数为0.221),其次是物质资本(系数为-0.172,路径调节系数为0.032),其后是社会资本(系数为-0.104,路径调节系数为0.012)和自然资本(系数为-0.048,路径调节系数为0.004),而人力资本改善多维贫困的效应(系数为-0.042,路径调节系数为0.003)最小(详见表5)。

表5 生计资本对多维贫困的效应
可以看出,收入、存款、住房、生产(生活)资料对多维贫困的影响要远远超过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本。从当地扶贫政策来看,2018年,吉林省产业扶贫、就业扶贫、医疗扶贫、教育扶贫、金融扶贫等多种举措共同发力,安排财政专项扶贫资金24.6亿元,整合涉农资金49.9亿元,当年累计发放金融精准扶贫贷款196.7亿元、扶贫再贷款42.4亿元,实现农村贫困劳动力转移就业1.9万人。①参见薛宝生:《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是决战决胜更是一张答卷》,《吉林日报》,2019年10月25日。但从实施效果来看,仍然是直接补助、住房改造等政策对贫困的影响更大,为提升贫困农户的金融资本和物质资本奠定了基础;而与能力建设相关的政策对贫困的影响相对较小,特色种养、庭院经济、乡村旅游、农村电商、光伏等扶贫产业政策的效果并不尽如人意,也直接制约了社会资本、人力资本作用的发挥,而且农户依靠自然资本摆脱贫困的可能性非常小。当前,绝对贫困问题被视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的突出短板”,扶贫开发工作被视为重大政治任务,广泛的社会动员和资源投入有助于迅速解决绝对贫困问题,政府通过组合性的扶贫资源为农户摆脱贫困提供了支持,但在此过程中,通常没有把农户的参与考虑进来,农户往往处于“政府要我脱贫”的状态,而不是“我要脱贫”的状态。而当超常规的扶贫举措过渡为常态化的反贫困机制时,农户能够依靠自身力量持续稳定脱贫,成为值得思考的问题。
因此,我国的扶贫政策虽然将提升生计的可持续性作为实现稳定脱贫的依据和路径,但从具体实践来看,仍然是直接补助、住房改造等政策发挥了更好的作用,体现的是“社会权利”的实现,对于发展改善贫困户生计系统的能力表现并不显著,在此背景下,贫困户的生计策略选择很难与“权利-义务平衡”相契合,很可能产生福利依赖,影响生计能力的有效提升和可持续性。
(二)可持续生计视角下的贫困治理反思:社会权利与公民义务的冲突与平衡
可持续生计框架虽然有利于实践层次的整合,但在我国的实践当中,表现出重权利、轻义务的倾向,直接影响了扶贫政策效果和农户可持续生计的提升。究其根源在于可持续生计框架与现代分配正义原则所确立的现代贫困观念之间的价值冲突。
现代贫困观念的价值基础是:国家救济穷人是社会权利的实现。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动力来源于以生物学为基础的个体利益最大化,生存性伦理催生出竞争,进而产生差异,这种差异又不断地社会化、结构化,使得某些群体或个体被排斥在经济社会发展之外,难以分享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贫困作为竞争性差异的后果不可避免产生。这就需要一种与竞争性差异相制衡的力量,为了使全体社会成员都能获得基本的物质保障,现代分配正义原则要求国家对财产进行重新分配。因此,贫困问题研究应当建立在“我们彼此负有义务”这一规范基础上,主要不是从社会或者作为整体的人类,而仅仅由于其是一个人的自然事实或每个人都具有先天的平等尊严(平等对待要求)这一规范性事实,国家运用强制性权力保障每个人获得平等的必需品的必要份额,即从自由而平等的个体之间所负有权利和义务的角度,要求国家无条件保障所有个体的基本需要满足①塞缪尔·弗莱施哈克尔著,吴万伟译:《分配正义简史》,译林出版社,2010年,第8页。。可以看出,可持续生计框架与现代分配正义原则所确立的现代贫困观念是存在冲突的,这种冲突集中体现在“不虞匮乏的社会权利”与“权利、义务相平衡的贫困治理路径”上。
要解决这种冲突,还需要从贫困的基本理念出发,寻找与可持续生计框架结合点。从现代分配正义理念出发,贫困与社会结构中产生的各种不平等相对应,政府消除贫困的行动是为了实现每个人都有的诉诸于平等的“绝对价值”,而且“不试图判断人们对导致不幸结果的选择如何负责”,但需要“公民根据他们相对他人的平等而不是低劣,对彼此提出要求”,要求“通过限制以集体方式所提供的善的范围,并且期待个人对他们占有的其他善承担个人责任”,同时,“就算公民并不具有平等的能力,他们也具有——至少是在根本性的最低程度上——使他们能够终身成为充分参与合作的社会成员所需要的道德能力、智力能力和体力能力”②Jalan Jyotsna, Martin Ravallion, "Are There Dynamic Gains from a Poor-area Development Program?"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1998, 67(2).。可以看出,现代分配正义原则放弃对贫困者进行价值判断,而是对其提出共同体意义上的基本要求,即国家有义务无条件保障所有社会成员的基本需要满足,但社会成员需要在根本性的最低程度上具备充分社会参与的能力。这就使得“社会参与”成为理解贫困的关键性概念。在贫困问题中,“社会参与”不仅作为必要条件,而且作为衡量标准。也就是说,所谓“不匮乏的生活”所追求的实质是让社会成员能够“充分参与合作”。对于贫困问题而言,国家与社会成员间的互动基础在于国家有责任为社会成员提供必要的必需品份额,而社会成员需要具备基本能力进行社会参与。
因此,“社会参与”可以为解决可持续生计框架与现代贫困观念的冲突提供一种方案,贫困的根源与社会参与的失败相关联,贫困者没能有效参与到经济社会生活当中,无法从经济社会发展所带来的社会分配中获得有效收益,③王一:《后2020参与式反贫困路径探索》,《社会科学战线》2019年第5期。而反贫困则需要通过可持续生计框架提高贫困者社会参与的能力(详见图1)。也就是说,国家有义务使全体社会成员过上不虞匮乏的生活,但要通过可持续生计框架下的社会参与来实现。

图1 现代贫困观念、可持续生计框架与社会参与关系图
四、可持续生计视角下的“参与式”反贫困
可持续生计框架与现代分配正义原则所确立的现代贫困观念之间存在着“不虞匮乏的社会权利”与“权利、义务相平衡的贫困治理路径”的冲突,导致实践中出现重权利、轻义务的倾向,直接影响了扶贫政策效果和农户可持续生计的提升,而“社会参与”则为解决冲突提供了一种可能。
(一)可持续生计视角下“参与式”反贫困的基本论域
虽然“社会参与”是一种常态性的群体行为,但学界对“社会参与”的论域和概念并未形成相对统一的看法。广义的社会参与通常面向全部社会生活,而且能够体现参与者价值,主要有两种研究视角,一是介入视角,认为社会参与是指社会成员以某种方式参与、干预、介入国家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社会生活、文化生活以及社区的共同事务,从而影响社会发展的过程①王兵:《当代中国人的社会参与研究述评》,《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1期。。二是资源视角,认为社会参与是一种社会导向下的与他人分享资源的行为②Chanda Srei, Mishra Raman, "Impact of Transition in Work Status and Social Participation on Cognitive Performance among Elderly in India," BMC Geriatrics, 2019, 251(9).。而狭义的“社会参与”面向的是单一的政治生活或社会生活,主要包括两种研究视角,一是将社会参与等同于政治参与,或者从政治参与开始逐步扩展到对公共事务参与的分析,认为社会参与是公众通过直接参与政府或与其他公共权力机构互动的方式决定公共事务和参与公共治理的过程③蔡定剑:《公众参与及其在中国的发展》,《团结》2009年第4期。。二是仅仅面向社会层面,认为社会参与表述了个体是如何积极地参加正式与非正式群组,以及其他社会性的活动④Hughes Clarissa, et al., "Increasing the Social Participation of Older Rural Residents: Opportunities Off ered by 'OPTEACH',"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Rural Health, 2019, 318(8).。
在贫困问题研究领域,社会参与往往被视为以“参与式社区”综合发展为表现形式的一种扶贫模式。20世纪50年代,城乡社区发展开始成为各国社会发展的重要形式,“参与”的理念在反贫困实践过程中逐渐彰显。20世纪80年代末,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开始大力推动这种将“参与式发展”①“参与式发展”最早由美国康奈尔大学诺曼·厄普霍夫(Norman Unhoff )教授于1990年提出,强调对发展对象的关注,认为发展对象要参与到执行、检测、评价的全过程。思想引入反贫困实践的“参与式社区”扶贫模式,认为援助对象的参与有利于改善社区援助的有效性。在阿马蒂亚·森之后,发展的中心含义在于增加人们“选择的机会”,而达到此目的之关键,是赋权(Empowerment),参与式扶贫模式则是达到赋权目的的有效途径。因此,参与式发展计划应该打破传统的规范和策略,比之前更加包容和民主,重新赋权于社会弱势群体(Disadvantaged Group)、边缘群体(Marginalized Group)以促进机会均等。世界银行在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中,发现参与式的发展干预有助于穷人参与到贫困的界定、分析中,并在学者和专业人士的帮助下,参与制定减贫措施,对干预项目和政策效果进行评估,提高了发展干预的效率和效果。
自20世纪90年代,参与式发展模式开始被引入中国,联合国计划开发署等国际机构开始在中国的扶贫领域试验、示范和推广参与式发展的方法,中国的学术界和政府部门也积极回应,推动了“京郊及宁夏治沙”项目、“云南省永胜县扶贫”等项目,在实践当中逐渐形成了贫困领域“参与式发展”的基本共识,认为这种扶贫模式改变了政府主导思考,出发点是为了建构一种贫困群众参与扶贫工作过程的机制,提高扶贫行为的可持续性和目标瞄准精确度,以及减少扶贫资金的中间渗漏。②郭君平等:《贫困脆弱性视角下参与式社区综合发展的精准“防贫”效应分析》,《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参与式发展”的核心是赋权,而赋权的核心则是参与发展援助活动的全过程的权力再分配。简言之,即增加社区的穷人与妇女在发展活动中的发言权和决策权。传统的发展方法将重点定位于经济领域,而参与式的发展方法则将重点定位于“人”的发展上:对人的尊重,尤其是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尊重,对基本人权的保障和全面发展。③李小云:《参与式发展概论》,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42-43页。
可以看出,在目前的理论和实践当中,“社会参与”与“贫困”之间的关联通常被局限在“参与式发展”的实践中,而且这种实践往往限定在某个“社区”当中。因此,“参与式发展”的论域远远不能涵盖“社会参与”与“贫困”的关联性。贫困意味着贫困者没能有效参与到经济社会生活当中,社会参与对贫困而言是本质和目的,而非手段。在贫困问题当中,社会参与并不仅仅局限于某一层面而是一个广义的概念,是指社会成员以生产性、社交性、团体性等方式参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活,并体现“自身价值获得”或“收益能力提升”④王一:《后2020“参与式”反贫困路径探索》,《社会科学战线》2019年第5期。,包括经济性参与、政治性参与、社会性参与和文化性参与。经济性参与一般是指“参与有报酬的商品生产及服务供给的活动”。政治性参与通常是指通过与政府(或其他权力机构)互动公共治理过程参与公共治理过程、决定公共事务。⑤蔡定剑:《公众参与:风险社会的制度建设》,法律出版社,2009年,第5-7页。社会性参与包括参与到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社会救助、扶贫等社会福利项目当中,也包括参与到社会组织当中。文化性参与主要包括教育、培训,以及文体娱乐等社交活动。
从前文的分析当中可以看出,“社会参与”可以为解决可持续生计框架与现代贫困观念的冲突提供一种方案,因此,我们可以在可持续生计框架下探讨贫困、社会参与、生计之间的关系。在发展干预领域应用比较广泛的是英国国际发展部(DFID)在1997年开发的可持续生计框架指南,整个分析框架由脆弱性背景、生计资本、结构和程序的转变、生计战略和生计输出等5个部分组成,如果将社会参与置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之下,社会参与可以被定义为:社会成员以经济性参与、政治性参与、社会性参与、文化性参与等方式参与到生计资本、结构和程序的转变过程,最终提升生计输出能力,进而推动其可持续地摆脱困境。社会参与成为链接生计资本和生计输出的关键,也就是说,通过社会参与的方式提升个体或家庭改善生计系统的能力,使全体社会成员实现不虞匮乏的生活(详见图2)。

图2 可持续生计视角下“参与式”反贫困框架示意图
(二)可持续生计视角下“参与式”反贫困问题路径探索
社会参与作为链接可持续生计框架和现代分配正义原则的关键,在贫困治理过程中要充分体现贫困者的参与性,并在此过程中实现参与者价值。因此,农村反贫困治理,要根本改变贫困群体被动参与、象征参与或无参与的现状。①林闽钢:《激活贫困者内生动力:理论视角和政策选择》,《社会保障评论》2019年第1期。具体地说,就是通过经济性参与、政治性参与、社会性参与、文化性参与等方式,推动贫困者有效地参与到经济社会生活当中,从经济社会发展所带来的社会分配中获得有效收益,提升个体或家庭改善生计系统的能力,摆脱困境、规避陷入贫困的风险。
1.提升贫困者经济性参与能力
经济性参与是社会参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实质是要提升贫困者参与劳动力市场的能力。在现代社会,参与劳动力市场不仅是维持基本生活的基础,而且具有满足社会交往、维护自尊、自我价值实现等内在价值。“以工作为中心重构福利制度”是当代西方福利改革的核心,也是“权利-义务”平衡的重要体现。对于符合工作年龄且具备劳动能力的贫困者而言,就业是最快捷且可持续摆脱贫困的方式。通过前文的分析可以看出,自然资本改善多维贫困的效应很低,贫困者依靠土地等自然资源实现脱贫的可能性较小。因此,贫困农户需要通过非农就业来摆脱贫困,这就需要贫困农户掌握市场所需要的技能和能力。
一是要积极建设就业服务平台,通过与各类工业园区企业,以及农民合作社、产业化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接,及时了解用工动态,加大岗位信息采集力度,实现就业供给与需求的信息对称。结合当地经济发展特点和社会需求,开发一些适合贫困劳动力就业的岗位。开展就业专项活动,以“春风行动”“农村贫困残疾人就业帮扶”“就业扶贫行动日”等活动为契机,为贫困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二是要提升贫困者适应新变化的能力,把承受最大贫困风险的社会成员整合进来,对有意愿在乡屯创业就业的贫困劳动力,积极协调农业农村、商务、财政、扶贫等部门和农业科学院等科研院所,采取专家巡回指导等方式开展中短期实用技术培训,集中优势职业教育资源,重点培养生产经营的熟练劳动力,有条件的可进一步培养初中级技术人才,确保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掌握一技之长。对有意愿外出务工贫困劳动力,聚焦吸纳就业能力较强的家政服务、物流配送、养老服务等产业,开展就业技能培训和劳务品牌培训。对在企业务工的贫困劳动者,开展企业新型学徒制培训、岗前培训、岗位技能提升培训,在效果上力争实现“培训-就业-脱贫”的可执行性,提升困难群体的就业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进而实现稳定脱贫。
当然,经济性参与并不是狭义的工作,因为许多残障人士可能终生都不适合工作,而且很多人都会面临摩擦性失业或选择性失业。因此,包容性社会需要的是为不能工作的人提供基本的生活所需和多样性的生活目标。一方面,必须有充足的财政预算,在规范的救助程序下让所有符合条件的困难者获得真正有效的援助,同时还应当维护受助者的人格尊严,因为这是公民最基本的社会权益与最低的人权保障。①郑功成:《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现状评估与政策思路》,《社会保障评论》2019年第1期。另一方面,要使贫困群体不仅获得收入,而且成为对社会有贡献的、有尊严的公民。同时,通过社会参与培养公民的社会责任担当,致力于培育有竞争力且负责任的公民。②王一:《后2020“参与式”反贫困路径探索》,《社会科学战线》2019年第5期。
2.提升贫困者政治性参与能力
政治性参与主要是使贫困者参与到贫困治理当中,进而提升贫困治理效果的过程。畅通的参与渠道是政治性参与的首要问题,在扶贫工作中,要设计合理的参与渠道,形成农户全过程参与规划、决策、实施、监测评估、后续管理的常态化制度体系,体现贫困者的主体地位。例如,在贫困村治理过程中,各级扶贫主体要使农户客观认识到所处的自然资源和条件,与农户们共同探讨生产、生活、医疗、教育等各个方面的问题,讨论不同贫困类型村民形成的原因,以及需要解决问题的迫切性、问题之间的关系等。在贫困农户充分参与的前提下确定发展策略,形成项目规划,并在落实、评价过程中体现农户参与性。总之,要通过深入的参与性使贫困者逐步形成主体意识和责任意识。
在此基础上,更重要的是培育贫困的利益表达能力。目前,我国贫困群体参与意识的发育程度较低,权利意识和利益意识相对匮乏,导致利益表达能力较弱。要通过充分发挥各种利益表达渠道和途径,进行有效的政策引导,在扶贫标准确定、扶贫对象选择、扶贫政策制定过程中,广泛采取民意调查、座谈、对话与协商、评议等方式提高贫困者的参与性,体现贫困者的发言权和决策权,逐步提升贫困者的利益表达能力。
3.提升贫困者社会性参与能力
社会性参与的核心在于通过社会化手段防范和化解重大疾病、灾害等事件所带来的贫困压力,完善教育、医疗、社会保险等基本公共服务,推动贫困者形成稳定的社会支持网络,积累社会资本,提升改善生计系统的能力。
一是要通过提高贫困者子女的受教育水平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要积极做好贫困地区的基础教育工作,使贫困学生有学上、上得好,提升其文化、技能水平,预防贫困的代际传递。充分发挥义务教育薄弱学校改造计划、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作用,着力改善贫困地区薄弱学校的办学条件和师资力量,培养造就素质较高且扎根乡村的教师队伍,完善并落实贫困学生全程资助计划,实现信息化教育资源的城乡共享,提升贫困地区基础教育的管理和服务水平。二是要探索从治疗到健康的医疗服务体系,以恢复贫困患者生产生活能力为核心有针对性地开展健康体检、分类救治;加强防治结合,提高贫困人口整体健康水平,使贫困家庭从能治病向少生病过渡,从根源上解决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问题,提升贫困家庭的可持续生计能力。三是要充分发挥现行社会保险政策作用,完善落实社会保险扶贫政策,支持帮助贫困人员参加社会保险。在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政策方面,落实地方人民政府为贫困群体代缴部分或全部最低标准养老保险费,将上述人员纳入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覆盖范围,实现有效扶贫和防贫;建立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调整机制,增加贫困者现金收入,更好保障其基本生活;同时要强化多缴多得、长缴多得的激励约束机制,完善缴费补贴政策,引导城乡居民主动参保缴费。在医疗保险方面,要充分发挥基本医保的基础性作用,同时有效利用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在医疗扶贫当中的重要作用,全面提高农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医疗保障水平。积极开展建筑业、交通、铁路、水利等行业工伤预防工作,减少工伤事故,防止因伤致贫,积极发挥社会保险防贫、减贫功能。
4.提升贫困者文化性参与能力
文化性参与是社会参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使贫困者真正融入社会,有活力、有信心、有归属感、有幸福感的重要体现,不仅有助于提高贫困农户的思想文化素质,更有利于形成积极向上的脱贫氛围。
“扶志”和“扶智”是文化在脱贫攻坚工作中的意义所在。一是要满足贫困者的基本文化权益,落实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农村电影放映工程、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农村文化大院建设、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送戏下乡、农家书屋等公共文化服务项目,实现贫困农户看电影、看电视、听广播、读书看报、进行公共文化鉴赏、参与公共文化活动等权益。二是要加强载体建设,加快健全完善县、乡、村三级农村公共文化设施网络,做到县有公共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文化广场、电影院,乡有文化站,村有文化大院,并保证设施完善、规模合理。将农村公共文化资源整合到农村文化大院,满足贫困农户的基本文化需求;拓展乡镇文化站统筹管理和服务供给的双重功能;完善县级文化设施网络,将县域公共文化服务的触角延伸到农村。形成适应贫困农户精神文化需求的公共文化生产方式,提高生产能力和服务水平,丰富公共文化供给内容;全力推进文化精品创作工程建设,努力形成农村公共文化品牌;鼓励创新公共服务供给方式,实现供给主体和供给方式多元化;丰富活动内容,激发贫困农户文化兴趣,推动贫困农户广泛参与公共文化服务项目,提升贫困农户文明素质。三是建立健全沟通协调机制,坚持以贫困农户需求为导向,建立科学合理的贫困农户参与制度,在公共文化产品的生产、配送、供给等阶段都要注重征求贫困农户意见,提供贫困农户需要和喜闻乐见的文化产品,切实满足贫困农户的精神文化需求,提升群众满意度。推动建立农村公共文化发展和文化人才扶持专项资金,通过对各类文艺人才的补贴,充分激发热爱文化、参与文化的主动性,提升文化人才和社团的艺术创作力,形成有产业发展、有民生保障、有文化内涵、有和谐环境的可持续脱贫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