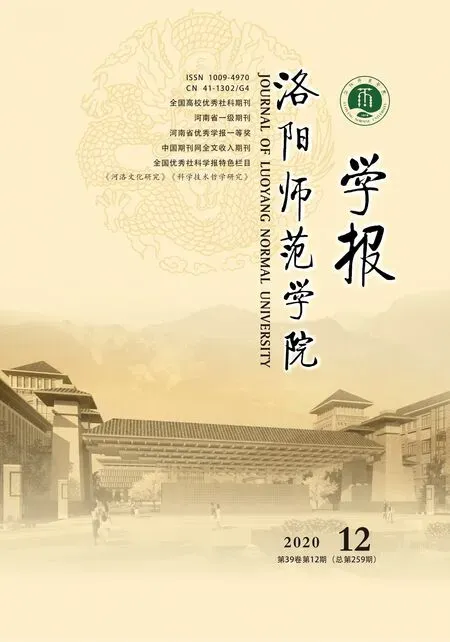日本文化视域中的洛阳
2020-03-03黄婕
黄 婕
(河南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河南 洛阳 471003)
古都洛阳在日本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在社会文化中体现为日本国民对洛阳这个名称产生的向往和亲近感,在学术界则体现为“日本洛阳学”的形成。文化史学家内藤湖南1894年提出的“文化中心移动说”将洛阳定位为中国最早的文化中心,影响深远。伴随着日本近代学术体系的建立,以洛阳为研究对象的学术文化具有自发性、全面性的特征,在一些领域甚至显现出局部系统性。作为系统考察日本洛阳学现象的第一步,有必要梳理和明确日本文化视域中的洛阳形象。
一、日本社会文化中的洛阳印记
(一)京都的别名
洛阳是京都的古名与雅称,其渊源可追溯到9世纪末。日本的宫室、都城的源流都出自中国,模仿唐代的长安城和洛阳城的意识非常强,其中以平安宫和平安京最为著名。[1]日本学者认为《帝王编年纪》中桓武天皇时开始有东京左京、唐名洛阳,西京右京、唐名长安的记载,10世纪后期“左京=洛阳、右京=长安”的说法开始固定下来。[2]虽然平安京的都城布局、内部形制等主要模仿长安,命名却多来自洛阳。据王仲殊考察,左、右京中大约有13个中国式坊名,其中铜驼、教业、宣风、淳风、安众、陶化、丰财、毓财8个坊名仿自洛阳,除了应天门以外,宫城的上东门、上西门之名也仿自汉魏时代的洛阳城。[3]
受环境地形、形制布局等因素影响,右京部分荒废不用,“洛阳”成为京都的别名一直保留下来。江户初期画家狩野永德留下著名的屏风画作品《洛中洛外图》。建筑学家认为“为特定空间制作的洛中洛外屏风不只是现代人眼中的一幅装饰‘画’,也是在室内营造出的一种‘以小观大’的幻境,足以透视出时人对于理想城市风景的一般印象”[4]。日本之所以用洛阳命名京都,连宫城建筑命名也完全照搬汉魏时代的洛阳建筑,显然是源于对大陆文明的向往,试图将古都洛阳作为理想的都城进行全方位的复制。
(二)龙门样式
一般认为佛教最早正式进入日本是崇佛派苏我氏在自宅中供奉佛像,这成为日本佛寺营造的滥觞(1)佛教经百济王朝传入日本的具体时间,主要有两种说法:据《日本书纪》记载,大约在钦明十三年(552);据《上宫圣德法王帝说》在538年。。日本最早期的佛寺飞鸟寺、法隆寺、四天王寺等,伽蓝配置都与洛阳永宁寺的伽蓝配置一致,体现了北魏风格。飞鸟寺中金堂供奉的本尊释迦铜质坐像建造于606年,1400多年来虽然多次损毁,除头部和双手之外都曾经过修复,但从雕塑整体来看,与龙门宾阳中洞本尊的密切关系清晰可见,龙门佛像被称为飞鸟佛像的母胎[5]27。据此可以推断北魏文化是日本飞鸟文化的源头之一。
制造飞鸟大佛的鞍部止利,其祖父是从百济移居日本的司马达一族,这个家族后来专门从事佛像制作,留下大量造像和建筑,形成止利派风格。著名的法隆寺金堂本尊释迦三尊像也是止利派的作品。这种风格较之肥体、薄衣的云冈样式,更接近长脸、瘦身、厚衣的龙门样式,特点是眼睛呈杏仁形状,唇边隐约露出古朴的微笑,长长的耳垂上没有开孔等,与洛阳龙门北魏时期佛像的亲缘关系清晰可辨。佛衣采用的是中国式的“通肩”设计,用圆润弯曲的线条来刻画衣纹,上衣襟张开,襟边沿上斜穿,掩盖住左肩和右腋的内衣,且可以看见衣裙带子的结头,这是印度佛像所没有的,是中国的独创。[6]止利派造像的另一大特色是结跏趺坐的下面拖出长长的衣裙。衣裾垂于座前的“悬裳座”最早出现于云冈石窟,在龙门石窟时发展成熟。厚重的衣裙上强化了装饰性刻画,属于中国北魏“褒衣博带”类型,形成类似云纹的浮雕,这种佛像造型显然是学自中国北魏后半期的“龙门样式”。[7]此外,佛像手足指间有缦网相连、犹如水禽的脚蹼这一北魏造像的典型风格也体现在止利派造像中。龙门样式通过止利派造像,成为日本古典佛像的典范。
武则天在洛阳造大佛铜像通天浮屠、在龙门奉先寺雕刻卢舍那大佛石像的崇佛行为,被日本圣武天皇(701—756)效仿,752年他举全国之力在奈良以东(现东大寺的位置)也筑造起巨大佛像。东大寺大佛以洛阳龙门奉先寺石窟卢舍那大佛坐像为原型,高达14.9米,是世界上现存最大的镀金铜像。洛阳与日本的佛缘不止于此,因请鉴真东渡而著名的日本僧人荣睿、普照是随第九次遣唐使来到中国的。他们在洛阳福先寺受戒并修行三年,736年请福先寺僧人道璿赴日弘法传戒。当时住在福先寺内的印度僧人普提仙那也一同来到日本,在奈良大安寺宣讲戒律。先于鉴真赴日的道璿是首位获日本天皇敕请的唐僧,为华严宗、禅宗、律宗各佛教宗派东传日本做出巨大贡献。东大寺大佛的开眼仪式由普提仙那主持,道璿担任咒愿师,这两位历经万难从洛阳来到奈良的高僧,从东大寺大佛身上看到了龙门卢舍那大佛的影子。从北魏到隋唐,洛阳佛教对日本佛教影响深远,特别是龙门石窟造像,不仅是日本古代佛像的源流,也是飞鸟时代日本吸收大陆文明的有力实证。
(三)名园文化
遣唐使中断之后,尽管中日之间的直接交流大幅减少,宋元时期日本仍然通过僧侣和贸易往来继续吸收大陆文化。北宋司马光等一大批官僚和文化名人聚居西京洛阳,形成“西京千古帝王宫,无限名园水竹中”(穆修《过西京》)的景象。山川形胜和亭台楼阁、奇花异草交相辉映的洛阳名园,构成了北宋一道独特的景观。后来中原板荡,名园尽毁,这种名园文化却在日本以另一种形式被传承下来。
日本的名园大多建于江户时代,因体现了日本文化独特的美学而闻名于世。被称为“庭园中的国宝”的兼六园始建于1676年,是日本园林文化的最高代表之一,名字取自中国宋代的《洛阳名园记》。李清照之父李格非(1068—1100)从“天下名园尽相望”的洛阳园林中,精心挑选出十九处特别出色的园子记录下来,并且提出当时园林建筑的互为对立的三组审美元素:“洛人云,园圃之胜不能相兼者六,务宏大者,少幽邃;人力胜者,少苍古;多水泉者,难眺望。” 并特别指出:“兼此六者,惟‘湖园’而已。予尝游之,信然。”[8]湖园曾是唐代名相裴度在洛阳集贤里的宅居园林,“筑山穿池,竹木丛翠,有风亭水榭,梯桥架隔,岛屿回环,极都城之盛概。度视事之隙,与白居易、刘禹锡酣宴终日,高歌放言,以诗酒琴书自乐,当时名士皆从之”[9]。
江户时代日本兴起筑园之风,既是对唐宋名士聚居洛阳的风雅生活的向往,也含有对《洛阳名园记》中筑造园林的审美思想的继承。江户幕府第8代将军德川吉宗之孙、陆奥国白河藩第3代藩主松平定信为此园取名“兼六”,意为洛人所提出的六个要素兼而有之。针对《洛阳名园记》中的宏大、幽邃、水泉、眺望、人力、苍古六个条件分别设置了景物一一对应,有欲与唐代洛阳的湖园相媲美之意。事实上,作为日本三大名园之一的兼六园是一座林泉回游式园林,的确符合白居易《裴侍中晋公以集贤林亭即事诗三十六韵见赠》诗中对湖园“竹森翠琅玕,水深洞琉璃……幽泉镜泓澄,怪石山欹危”的描述。
日本社会文化中与洛阳的关联很多,深入考察,总能发现丝丝缕缕的洛阳印记。比如京都的鸭川时常被称为洛水,“洛阳牡丹吐新蕊”用来表达禅意等。日本男女老少都耳熟能详的国民歌曲《箱根八里》,开篇第一句就是“箱根之山为天下险,险过函谷关”,用洛阳城西的函谷关强调箱根的险峻,足见日本人对于洛阳风物的熟悉程度。
二、历史的交汇——中日交流史上的洛阳
日本自古就与深处内陆的洛阳关联匪浅,是有记载的中日交流正式展开的起点。关于日本列岛的最早的记录,几乎都与洛阳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使这个中国古都成为解读日本古代史的关键切入点。
(一)光武帝金印
由于中国与日本列岛只有一海之隔,沿海一带自古就存在人员往来,因此《汉书·地理志》才会有“海上有倭人”的记载,中国和朝鲜半岛到日本的人被称为“渡来人”。成书于5世纪的范晔编纂的《后汉书》中开始有进一步涉及日本的内容,《光武帝纪》《安帝纪》《东夷传》等篇章,多处明确提到日本对东汉王朝的朝贡。
刘秀建立东汉以后定都洛阳,“建武中,东夷诸国皆来献见”。特别是《后汉书·东夷传》有“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国奉贡使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赐以印绶”,正式记载了中日间的官方往来,是关于中日间正式外交关系的最早记录。这些文字显示,古代日本岛与中国的交流在东汉时期发生了突破性进展,岛中倭奴国(2)王仲殊等学者认为其意为“倭之奴国”,表示奴国只是日本列岛上众多国家之一。使节向在洛阳的光武帝朝贡,并得到封赐。朝贺是诸侯百官向天子参拜的礼仪,倭奴国的来朝是对东汉显示臣服的举动,光武帝的赏赐则意味着对他们国家的认可和赐福。这是中国和日本历史上第一次实现最高层次的正式往来,开创了两国关系的新篇章。此后,倭王在安帝时代再次派遣使节来到洛阳进贡。日本通过朝贡,被纳入到中原王朝的册封体制之内。
值得一提的是,金印于1784年春在日本九州地区被发现,后来的驻日本公使黄遵宪“尝于博览会中亲见之”,特意在《日本杂事诗》中留下“博物千间广厦开,纵观如到宝山回。摩挲铜狄惊奇事,亲见委奴汉印来”的诗句,并注释说“有金印一,蛇纽方寸,文曰汉委奴国王。云筑前人掘土得之。考《后汉书》,建武中元,委奴国奉贡朝贺,光武赐以印绶。盖即此物也”。日本主流学说认定此印为当年汉光武帝所赐,并写入历史教科书,但金印的真伪之辩是日本历史学界的著名课题,争论200多年仍未有定论。
(二)邪马台国之谜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这期间日本列岛也战乱不断,没有中日间发生交往的记录。直到三国纷争的尘埃落定,天下大势基本上归魏时,日本岛上列国才再次开始正式朝贡。这距永初元年(107)对东汉的最后一次进献已达百余年。再次开启的中日间的正式交往,仍然是以洛阳为中心进行的。
《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对魏晋时期的中日交往有更为详细的记录。这段大约两千多字的记叙简称《魏书·倭人传》,较为具体地涉及了日本岛上邪马台国的位置路线、风土习俗以及与曹魏六次使者交往及礼品、赏赐等,可见这期间日本列岛与中国发生了相当频繁的往来和交流。特别是邪马台国的首领卑弥呼女王于239年派遣使者来到魏都洛阳献上奴隶进行朝贡。卑弥呼政权得到魏明帝肯定,不仅被封为亲魏倭王,还获得金印紫绶及锦缎绢织、包括百枚铜镜在内的大量财物。邪马台国在随后的正始年间也数次来朝,与魏国保持了良好的关系。这个时期,日本列岛仍处于弥生时代的中晚期。曹魏与日本列岛交往甚密,甚至还派遣官员前往岛上协助处理邪马台国与狗奴国的争端以及卑弥呼死后事宜,说明这种外交对当时的国际秩序和日本岛上的国家格局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作为日本的史前记录,《魏书·倭人传》中的“南至投马国,水行二十日……女王之所都,水行十日,陆行一月”等记叙,第一次用具体数字记录了日本列岛上的众多原始国家的位置和风貌,文字的细枝末节中包含有日本原始国家时期的线索,为了解古代日本列岛以及日本国家的起源提供了可能性。日本学者以这些文字为根据,经过考证、辨别发现了大量信息。有人试图通过使节沿途的记录探究他们从中国到岛上列国所走的路线和路程,进而确定邪马台等国的具体位置;由于早期表现外国人名和地名时是比较随意地采用汉字注音,有人通过当时洛阳通行的语言发音分析各个名称的汉字标记,从读音上分析日本古国名中可能存在的日语发音,与日本古史对照,考察当时的国名;由于后来出土的古坟时代的部分铜镜上刻有“师出洛阳,铜出徐州”的字样,还有人专门研究铜镜是否为当时魏明帝所赐的魏镜,或者是由中国洛阳的技师来到日本以后在日本本土制造的。上述诸多课题都涉及日本国家起源,需要与考古、历史、语言学等众多学科结合考证,而“洛阳”是解读邪马台国谜团的重要依据和参照物。
(三)“日出处天子”的国书
魏晋之后中原大乱,洛阳成为纷争的漩涡中心。虽然有学者认为从1世纪中叶到3世纪后期的200多年间,日本遣使访问中国,以“入洛”始,以“入洛”终。如日本学术界通常所称,就中日两国的使节往来而言, 4世纪是“空白的世纪”。[10]但也有人认为西晋泰始二年(266)以后到义熙九年(413)的约150年间, 倭人与中原王朝一直保持着朝贡关系,只不过是由于当时倭国国内、中国和朝鲜半岛局势的变化,古倭国朝贡次数与以前相比不太频繁,但这种朝贡关系还一直维系。[11]随后日本列岛基本上完成了统一,建立起全国性政权大和政权,与南朝有交流,留下倭国五王遣使朝贡的记录。隋朝统一中国后,中日之间的交往再次出现突破性进展,标志是圣德太子致隋炀帝的国书。
大业三年,其王多利思北孤遣使朝贡,使者曰:“闻海西菩萨天子重兴佛法,故遣朝拜,兼沙门数十人来学佛法”。其国书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云云。帝览之不悦,谓鸿胪卿曰:“蛮夷书有无礼者,勿复以闻”。
——《隋书·倭国传》
虽然还有一些争议,但学界基本认定圣德太子607年派出以小野妹子为首的使节,在东都洛阳谒见隋炀帝,并呈上写着“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的国书,引起隋炀帝的震怒。刚刚在极短时间里动用200万人力完成了营造东都洛阳新城奇迹的隋炀帝,正处在意气风发之际,蕞尔小邦试图和天朝大国的皇帝以平等的姿态对话,必然引起其不快。也许是为了彰显天朝大国的风范,隋王朝并没有计较日本的自大,降罪于来使,反而启用洛阳的鸿胪寺四方馆接待日本使团,并敕命高僧负责教育留学生及沙门,甚至派出文林郎裴世清为圣德太子之遣隋使的回礼使。裴世清一行跟随小野妹子进入飞鸟京、后从难波津回国等具体日期和行程,在《日本书纪》皆有明确记载。
中日之间的这次交往,受到日本学者气贺泽保规的关注,并被评价为“瞬间的交错,引起火花飞溅”,认为圣德太子(574—622)与隋炀帝(569—618)生长在同一时代,都极富个性和才能,推动各自国家的政治进程并留名青史,有必要放在一起进行对比研究。[12]如《明史·占城传》所述,“大都海外诸蕃,无事则废朝贡而自立,有事则假朝贡而请封”,不少学者认为周边小国对中国中原王朝的态度以各自的“国家理性”为内在固有机能,“作为‘岛夷’的倭(日本),可以说就是这些机能特性所表示出来的典型的‘戎狄’”[13]。
日本与中国自此建立起稳定的外交往来,此后也有日本的遣隋史多次来往于中日之间,有留学生(僧)长期滞留中国,学习中国的政治文化。关于日本派出的遣隋使的次数,由于《日本书纪》与《隋书》中的《倭国传》《炀帝纪》有不一致之处,至今未能完全明确。早期以本居宣长为代表的日本史学界的传统主流观点认为共有3次遣隋使,后由宫崎市定等修正为4次,也有学者提出5次、6次之说。虽然具体次数还有待探讨,但日本向仅持续了短短37年的隋王朝频繁派出大量遣隋使,是无可置疑的。
圣德太子极力效仿中国,推动佛教传入日本,并颁布著名的冠位十二阶及宪法十七条等制度,明显模仿中国中原王朝的宗教态度和政治体系。这些政策让日本从比较初级的大和政权过渡到中央集权,逐渐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日本佛教从仅与朝鲜半岛的交流转变为与中国交流, 也是始于日本向中国(隋)派遣使节。[14]通过亲身到过洛阳的遣隋使等媒介,这个时期中国对日本的影响带有鲜明的洛阳痕迹。例如,随着佛教传入,日本也掀起了造寺造像的热潮。今天的日本关西一带,仍可以看出《洛阳伽蓝记》中记载的“招提栉比,宝塔骈罗”的景象,龙门样式极有可能是在这个时期传入日本的。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古代史书上对日本的称呼由“倭”到“日本”的转变始自武则天在神都洛阳执政的时代。最明确的记载是唐朝《史记正义》上“武后改倭国为日本国”的记录。此后的十几批遣唐使虽然主要居留在长安,但大多“游学于两京”,与洛阳交集甚密,从最近引起热议的洛阳出土的吉备真备书丹的墓志可见一斑。
综上所述,古代日本发展史上的每一个重要节点,几乎都能找到与洛阳的关联性。古都洛阳的历史隐藏着研究日本古代历史的重要线索,文字资料极度欠缺的日本古代史需要借助洛阳丰富的古代史料来解读,因此“古都”是日本文化视域中最基本、最原始的洛阳形象。
明治维新实行文明开化,使日本步入现代化之路,建立起现代学术研究体系。经过一段沉寂之后,内藤湖南让洛阳再次引起世人的注意。内藤湖南1894年提出的“文化中心移动说”影响深远,成为东洋史学理论的重要支柱。内藤湖南借用了清人赵翼的“长安地气”说,认为文化中心随历史的推移而变化,但明确指出“在长安之前有洛”,认为“武力之强在于冀州,唐虞夏商,在南面以钳制天下;食货之利在豫州此间人文酝酿;洛恰于此二州文化风物聚合之处”[15]。正因为内藤湖南将洛阳一带定位于中国最早的文化中心,此后日本文化视域中的洛阳研究大多兼具对文化起源和历史传承的思索。由于日本古代历史与洛阳的重叠,相比中国其他都市,日本人对洛阳有天然的亲近感。2016年朝日新闻社出版丝绸之路特集《洛阳——乡愁之都》,标题即体现出这种文化的依恋。
三、文学想象——日本文学中的洛阳书写
日本学者为研究日本历史而关注洛阳,普通日本人对洛阳印象的形成则多源自日本文学中洛阳书写所营造的想象空间。事实上,日本人将“洛阳”作为平安京(京都)这一特定空间的称谓,就是通过命名表达对理想都城的向往。基于对洛阳作为历代古都历史地位的长期憧憬,同时再加上大量与洛阳相关诗文名作的文字构建起的想象,日本文化视域中的洛阳形象逐渐具体和清晰起来。
(一)古典汉诗中的场景嫁接
日本人从大约1300年前开始创作汉诗,这得益于训读法。用在汉文字上加注标记调整语序的方法对中国的古籍文章稍加标示,就能让日本人像阅读日语文章一样看得懂汉语古文。日本汉诗来源于中国诗歌,同时又体现日本社会文化传统,在东亚汉文化圈中独树一帜。
白居易的诗歌在日本被奉为圭臬,是古代日本人感受到汉诗之美而痴迷热爱汉诗的源头。白诗不仅极大地渗透到整个平安时代的日本文学,对日本文化和审美都影响深远。日本诗歌和书法爱好者自发地在洛阳城东的白居易墓地立起纪念石碑,用中日双语刻下的“伟大的诗人白居易先生是日本文化的恩人”绝不是夸大其词。一生挚爱洛阳的白居易,写下无数关于洛阳四季风景和风土人情的诗篇,他晚年定居洛城17年,并且坚持要求死后也埋在香山琵琶峰上与龙门对望。这样的情结无疑也让日本人对这个城市产生一种特殊的情愫。
火舶铁车租税通,鲁西以外一家同。
东京自此洛阳似,道里均平天地中。
——大沼枕山(1818—1891)《东京词》
洛阳知己皆为鬼,南屿俘囚独窃生。
生死何疑天付与,愿留块魄护皇城。
——西乡隆盛(1828—1877)《狱中有感》
日本汉诗中常有“洛阳”出现,但需要区分其所指,可能指中国古都洛阳,也可能指日本京都。以上两首同是风起云涌的明治时代的汉诗,前者借吟咏江户成为东京的沧桑巨变,讽谏了幕府末年日本迁都等时政。洛阳作为天下之中的古都印象在日本已经根深蒂固,作者借《史记》等古文献中周朝营造洛邑时“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的典故,有意识地将东京和洛阳作比较,认为从此以后东京就像洛阳一样成为天下的中心了。后者为“维新三杰”之一的西乡隆盛“尊王攘夷”失败后,被流放于孤岛时所作。这首诗中的洛阳指代京都,抒发了他愿意为推翻幕府、王政复古而鞠躬尽瘁之意,被胜海舟刻在石碑上作成“留魂碑”,立于东京上野公园。
日本汉诗中的洛阳,除了以上两类可以明确判断指向的以外,还有不少从意义上来说是模棱两可、任凭读者意会的。淫浸于汉文诗风中成长起来的日本文人,尽管很多人终生未到过中国,却借助文字在心中构筑起一个典雅精致的想象世界,常常创作以中国风物为主题的汉诗。由于京都也可雅称洛阳,字面上和洛阳相关的日本汉诗,很可能是日本诗人看似不经意、实际上却是有意识地把中国汉诗典故中原有的洛阳,悄然与他们所处现实时空中的“洛阳”(京都)嫁接起来的结果。例如:
洛阳一别指天涯,东望浮云不见家。
合浦飞来千里叶,阆风归去五更花。
关山月满途难越,驿使春来信尚赊。
应恨和羹调鼎手,空捋标实惜年华。
——新井白石(1657—1725)《千里飞梅》
新井白石虽生于江户时代破落的武士家庭,却积极向学,专习朱子学数年,成为江户时代的学者型政治家。《千里飞梅》的词句明显与“浮云一别后,流水十年间”(韦应物《淮上喜会梁川故人》)、“人言落日是天涯,望极天涯不见家”(李觏《乡思》)等唐宋诗句的语意相似,可见作者的古典文学素养深厚,对中国诗文可以信手拈来。新井白石因著有《古史通论》和《外国之事调书》等研究邪马台国与曹魏王国的交往历史而闻名,对古代洛阳的人文地理非常熟悉,所以诗中使用了“合浦杉”的典故。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合浦叶或者杉叶都常常作为思归洛阳的形象出现,表达乡愁。明朝的杨慎在《升庵文集》中专门设立了“合浦杉”一条,列出“传闻合浦叶,远向洛阳飞”“杉叶朝飞向京洛,文鱼夜过历吴州”等诗句。新井白石作这首诗的具体创造情况已不可考,通常被看作含着青春少年的豪放与自许,又包含着壮志未酬、空白了少年头的悲慨。[16]其中“合浦飞来千里叶”与“洛阳一别指天涯”既有逻辑上的照应,也有意象的连接,无论是实指还是虚指都很和谐。
这类诗歌数量不少,其中“洛阳城里飞如雪,不送行人空送春”[室直清(1658—1734)《杨花》]、“春雁似吾吾似雁,洛阳城里背花归”[直江兼统(1560—1620)《春雁》]等都是日本脍炙人口的名句。这些诗句明显因袭了“洛阳城里花如雪,陆浑山中今始发”(宋之问《寒食还陆浑别业》)、“洛阳城东西,长作经时别。昔去雪如花,今来花似雪”(范云《别诗二首》)、“洛阳愁绝,杨柳花飘雪”(温庭筠《清平乐·洛阳愁绝》、“乡书何处达,归雁洛阳边”(王湾《次北固山下》)等,让“洛阳”一词在中国古典文学中的风花雪月的浪漫形象在日本文学中也得到继承。
日本汉诗中的洛阳书写,无论是实际语义、借用典故还是使用氛围,都与传统文学形象中的洛阳一脉相承。既可以理解成日本诗人的隔空致敬,也可以理解为以“洛阳”指代京都。日本诗人有意识地继承和使用独具洛阳特色的相关典故意象,又将京都的实际意义和“和习”描绘入诗,诗中两种所指皆符合逻辑,创造出一种崭新的诗歌意境,达到“一弦二歌”的效果。这种写作手法显得异常精妙,使“洛阳”一词体现出的中日在文学、文化、审美方面的共识得到继承,成为理解中日两种文化的一种特殊路径。
(二)近代文学创作
除古典文学外,当代日本人对于洛阳这个城市的印象受到通俗文学作品的影响更多。以《三国志》及这段历史为蓝本的众多系列衍生作品,让洛阳以更为生动的形象展现给世人。特别是发生在洛阳城的曹操刺杀不成献刀的机智、貂蝉美人计中的权谋、董卓火烧洛阳城的惨烈、关云长首级的诡异等画面,都作为三国故事中的经典深入人心。日本人对三国群雄争霸情节的熟悉程度超出中国人的想象,洛阳作为三国故事的重要舞台,一直为日本的三国迷所神往。
近代天才小说家芥川龙之介是日本最受欢迎的作家之一,他改编自中国古典小说的《杜子春》完成于1920年,是进入日本中小学国语课本的必修内容。故事原型来自中国神仙小说中唐代郑还古所著的《杜子春传》。芥川龙之介将原本发生在长安的故事挪到洛阳,以“某个春日沉沉的黄昏,唐朝京城洛阳的西城门下”作为开篇之辞,使之成为日本家喻户晓的经典名句。小说中多次出现对洛阳城繁华风貌的描写,故事跌宕起伏,情景充满神仙玄幻色彩,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现代日本文学中洛阳形象的塑造。
当时的洛阳极为昌盛,是个天下无与伦比的京畿。大道上车水马龙,人潮熙来攘往,夕阳的光辉如同一抹金黄浓稠的亮油,映照在西城门上。可以看到老人的罗沙帽、土耳其女人的金耳环、装饰在白马上的彩丝羁绳,交替流动、变幻不止,那景象美得像一幅画。
——芥川龙之介《杜子春》(3)芥川龙之介《杜子春》1920年刊登于《赤鸟》杂志,在中国有多种译本,此处为笔者翻译。
长期以来,日本有不少以洛阳为舞台的历史小说,21世纪以来出版的就有以西晋皇后贾南风为主人公的《洛阳的姐妹》(安田笃子著,讲谈社2002年版)、以貂蝉为主人公的《洛阳炎上》、反映武则天时代的《则天武后》(气贺泽保规著,讲谈社2016年版)、以薛怀义为主人公的《洛阳的怪僧》(佐佐泉太郎著,东洋出版2017年版)等。除了有历史原型的小说,还有很多几乎完全虚构的文学作品也把洛阳设定成舞台,如《双子幻绮行——洛阳城推理谭》(森福都著,详传社2001年版),通过一系列同名推理小说,刻画了一对双胞胎在风云诡谲的洛阳城中屡屡侦破奇案的故事。新型历史文学作家相木钟三连续出版了《洛阳的纸价》(文艺社2005年版)、《洛阳春》(大众幸福出版社2018年版)。因被翻拍成《妖猫传》而引起话题的《沙门空海之大唐鬼宴》(梦枕貘著,德间书店2007年版)中,也有相当多的场景被设定在洛阳。
日本学者早就注意到洛阳都市形象的特色,橘英范曾考察中国志怪、传奇小说中的洛阳形象,认为“隋唐时期洛阳特有的都市环境,即洛水将城市一分为二、架于其上的天津桥等具有‘桥’与‘市’的双重性质,起到与异界分界的作用,使洛阳带上神异色彩,成为造就丰富多彩的小说的世界”[17]。日本当代作家对这一传统进行了继承和发扬,部分借用历史对洛阳的记载,又大量加入文学的想象,通过扑朔迷离的故事情节,让洛阳城“笼罩上绮幻与怪异的面纱”,营造出“诡异之都”的形象呈现给民众。
日本的洛阳书写,“非理性浪漫主义文学的需求使幻想文学迅速崛起,而异国的千年古都无疑能够吸引读者目光”,“日本作家擅长描绘历史舞台上欲望与野心碰撞,爱与绝望交织的画面。比起客观的历史,他们更关注人性在欲望与杀戮前所展示的黑暗。作为故事发生的场所,洛阳处于这一切黑暗的漩涡中心,展现了冷酷鬼魅的一面”。[18]如果说汉诗等日本古典文学赋予洛阳形象以典雅的内涵,历史志怪小说、当代创作的悬疑作品则赋予洛阳形象以神秘的外延。
四、结语
日本社会对洛阳的特殊关注源于其在中日交流史上的原点性地位。古代日本使用汉字作为书面语言,曾经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里以学习、吸收中国文化为荣,其思想体系、审美意识、宗教精神等都与中国一脉相承,古都洛阳作为中日交流的起点都市,在中国文明传入日本的过程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中日早期的每一次正式交往,汉、魏、隋、唐时期使节接触几乎都和当时的洛阳有直接关联。这种历史的重合使得日本的历史、文化、考古、宗教等各个领域,都会或多或少涉及洛阳,这个城市与日本的交集如同一条隐秘的纽带,可以窥见日本民族的历史渊源,探索日本文化的内部结构。中国古典文学中大量和洛阳相关的古典诗词、小说演义等文学作品也被日本人熟知和喜爱。诗人们常常借助洛阳相关事物或典故与京都的场景进行嫁接创作诗词,营造出被风花雪月所浸染的古典浪漫主义形象,而小说家则喜欢创作以洛阳为舞台的小说,有历史基础但不拘泥于史实,通过扑朔迷离的故事情节和推理,营造洛阳神秘诡谲的城市形象。这些文学作品广为流传,成为日本大众认识和想象洛阳的依据。
总而言之,洛阳对日本社会的影响余韵悠长,至今仍能在日本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发现洛阳文化的印记。通过历史的重合与文学的想象,洛阳在日本文化视域中形成典雅与神秘并存的古都形象,并固定下来。日本文化视域中形成的长期稳定的洛阳形象,为日本洛阳学现象的形成积累了广泛的社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