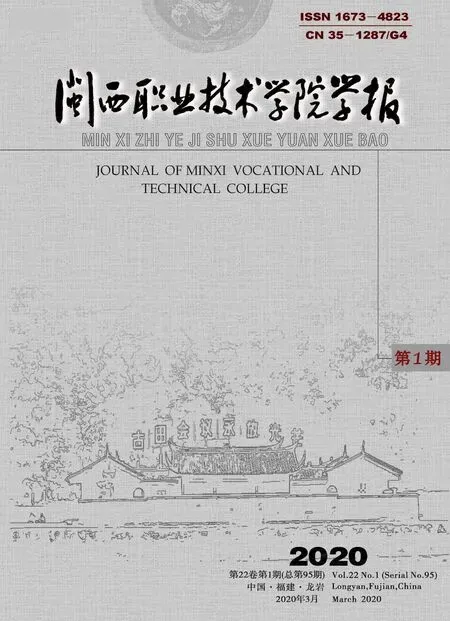论《野草》中儿童形象的书写
2020-02-28毕莉莉
毕莉莉
(安徽大学 文学院,合肥 230000)
《野草》收录鲁迅1924—1926 年创作的23 篇散文诗与题词,在《求乞者》《颓败线的颤动》《过客》《风筝》《立论》5 篇散文诗中,儿童这一特殊形象均处于较为突出的位置。在创作《野草》之前,麻木愚昧的国民、黑暗的社会现实以及兄弟失和的不如意状态,使鲁迅在追求希望中产生强烈的无力感与悲痛感。在《野草》中,鲁迅通过塑造儿童这一特殊形象,将自我体验以象征手法融入其中,以儿童的形象与视角传递启蒙者的呼喊。这些儿童形象带有鲁迅式的沉郁与思考,可以使我们更加全面深刻地理解鲁迅的思想。
一、《野草》儿童形象的寓意
《求乞者》中向“我”乞讨的小孩,《颓败线的颤动》中怨恨、瞧不起母亲的小女孩,《过客》中对过客施以善意的小女孩,《风筝》中喜欢风筝的多病小兄弟,《立论》中请教立论方法的小学生,这些鲜明的儿童形象都具有深刻的寓意,交织着鲁迅思想斗争中的绝望与希望。
(一)希望的哀叹
在《求乞者》中,作为希望代名词的孩子,却成为求乞队伍中的主体,这使“我”感到羞愧与痛苦。“一个孩子向我求乞,也穿着夹衣,也看不见悲戚,而拦着磕头,追着唉呼。我厌恶他的声调,态度。我憎恶他并不悲哀,近于儿戏;我厌烦他这追着唉呼。我走路。另外有几个人各自走路。微风起来,四面是灰土。一个孩子向我求乞,也穿着夹衣,也不见得悲戚,但是哑的,摊着手,装着手势。我就憎恶他这手势。而且,他或者并不哑,这不过是一种求乞的法子。”[1]
孩子沦为求乞的主体,不论是对于孩子自身来说还是对于作为成人的我们来说,都是一件难过的事:因为作为孩子,他们失去了成为希望的资格;而作为成人,我们没有为他们提供一个美好、光明的世界。但是,“我”在求乞的孩子眼神中“看不见悲戚”,他们“装着手势”,磕头乞讨,没有任何的尊严、骨气和傲气,这使“我”更加痛苦。因此“我”憎恶的是孩童本该有的天真烂漫被生活麻痹成如灰土的墙体一般,毫无生机与希望。
如果说《求乞者》中的孩子麻木到不见悲戚,那么《颓败线的颤动》中的小孩则凶狠地让人胆战心惊。年轻的母亲为抚养幼女而出卖身体,忍受屈辱与痛苦,但成年后的女儿却因此怨恨、瞧不起母亲,视其为自己的拖累,“‘我们没有脸见人,就是因为你,’男人忿气地说。‘你还以为养大了她,其实正是害苦了她,倒不如小时候饿死的好!’‘使我委屈一世的就是你!’女的说。”[1]长大成人的孩子给了母亲第一刀,而孩子的孩子则给了母亲致命的一刀,“最小的一个正玩着一片干芦叶,这时便向空中一挥,仿佛一柄钢刀,大声说道:‘杀!’”[1]一声来自孩子的孩子,而且还是最小孩子的一声“杀”,使母亲感受到了最强烈、最凶猛、最寒冷的恶意。
《野草》中的这一类孩子成为希望最大的反叛者,他们是“缩小的成人”,社会将他们过早地硬塞进成人的模子中,禁闭扼杀了他们的天性。他们照着成人的模式行事,行乞的孩子深谙成人的心理,磕头,摊手,装着行乞的姿势以便博得更多的同情。牙牙学语时期的孩子,脱口而出带有最大恶意的字眼——“杀”。这些孩子如提线木偶任人摆布,又如利刃一般使人感到寒冷恐怖,这不禁使人哀叹希望是否会在暗无天日的角落里慢慢消亡。
(二)希望的彷徨
在《求乞者》与《颓败线的颤动》中,鲁迅感受到的是希望处于绝望境地的痛苦。与“缩小的成人”的儿童形象相比,《过客》与《风筝》则展现鲁迅心中另一类儿童的形象,体现儿童的本质特征。
《过客》中有一个约十岁,紫发、乌眼珠、穿白底黑方格长衫的女孩,紫色是所有人物与背景中唯一的亮色,正如小女孩之于老者与过客。她充满好奇,在过客还未走近她与老者时,她便急切地向东望着;她天真烂漫,当过客问起前面是什么时,女孩回答是野百合与野蔷薇,与老者回答的坟场截然不同;她善良友好,当看到过客脚流血时,主动递上一块布,让他包扎伤口。代表革命者的过客,因不知如何报答这份好意而拒绝了女孩,“倘使我得到了谁的布施,我就要像秃鹰看见死尸一样,在四近徘徊,祝愿她的灭亡,给我亲自看见;或者诅咒她以外的一切全部灭亡,连我自己”[1]。黑暗社会不是儿童生活的乐土,与其让他们被污染不如将其毁灭;或者只留下孩子,杜绝一切污染他们的可能[2]。大概因为这两者都不是孩子所希望看见的,所以革命者拒绝了这份好意。小女孩正如希望之于绝望社会现实中所开出的美丽花朵。
《风筝》与《过客》相比,增加了更多的现实因素。作品中的“我”向来不爱放风筝,并且不准自己的小兄弟放,还粗暴地毁掉了小兄弟苦心孤诣做好的风筝。作品中“我”的小兄弟,多病,瘦得不堪,但只要能看他人放风筝,他天真活泼的儿童天性就显露出来,“远处的蟹风筝突然落下来了,他惊呼;两个瓦片风筝缠绕解开了,他高兴得跳跃”[1]。但这些在“我”看来是笑柄,是可鄙的,“我”为破获小兄弟的秘密感到满足,以摧毁他的心血为胜利[3],“我”的存在让小兄弟纯真的儿童本性更显珍贵。
不论是《过客》中的小女孩,还是《风筝》中的小兄弟,他们在成人的世界中是弱小者,但他们的世界正如鲁迅所希望的那样与成人的世界截然不同,他们承载着在世界新潮流中不被淹没的希望。这样一类儿童形象是灰暗社会中的一缕微光,他们的儿童天性得到一定程度的“解放”,儿童纯真的本性感染灰暗现实社会中的他者,进一步实现“引起疗救的注意”。
(三)希望的追求
在暗淡无光的旧社会中,虽然现实给予鲁迅更多的是冰透骨髓的巨大黑暗与绝望,但他仍执着地追求着希望,《立论》正是这一精神的体现,其中塑造的儿童形象成为他寄托希望的所在。
《立论》中的“我”带着一个小学生的面具出现,“我”在小学的讲堂上向老师请教立论的方法,初学如何表达观点,但却不得要领。“我”对“这孩子将来要发财的”与“这孩子将来要做官的”恭维奉承行为感到深深的不屑,大声说出“我愿意既不谎人,也不遭打”的主张,即使面对老师“那么,你得说:‘啊呀!这孩子呵!您瞧!那么……阿唷!哈哈!Hehe!he,he he he he!’”打哈哈式的圆滑立世原则,“我”也没有予以苟同[1]。作为小学生的“我”,在这种失语的状态下,依然具有独立思考问题、明辨是非的能力,拥有独身自好的品格,是坚定的希望追寻者。这样的儿童形象在《野草》中是独特的,在充斥着绝望气息的《野草》中,这个儿童形象寄托着鲁迅对儿童、对社会无限的希望。
从《求乞者》《颓败线的颤动》到《过客》《风筝》再到《立论》,鲁讯塑造的5 个儿童形象,有绝望、有惊恐、有欣喜、有悲叹、有希望,他们虽不光彩夺目,但承载着鲁迅对自我、对国民性的残酷犀利解剖,以及作为一个先觉者强烈的责任感与无力感[4]。鲁迅超前而敏锐地关注儿童这一群体的成长与教育,闪烁着先驱者的智慧,同时带有深刻的警醒意义。
二、《野草》儿童形象的承载
《野草》是鲁迅对自我内心深处最深刻、最严酷解剖的成果,其中的儿童形象是其冷眼观察与冷静思索的产物,他们是鲁迅式的,带有鲁迅式的沉郁与思考。这些儿童形象在象征性地展示儿童真实生存境遇的同时,也贯穿着鲁迅的自我体验,承载着鲁迅的人生哲学。
(一)受难的意识
对鲁迅而言,受难意识是其从小就形成的责任感的体现。鲁迅14 岁那年,父亲身患重病,祖父深陷牢狱之中,往日看似和睦的家族顷刻瓦解,还未成年的鲁迅承担起家庭的重任,而亲友间的冷漠彻底击碎了鲁迅对诸多美好的向往。《野草》中一次次展现的受难意识,正是萌芽于这一时期的情感体验。从外部环境看,鲁迅写作《野草》适值“五四”退潮,中国陷入“五四”运动之后最黑暗的时期,政治时局动荡不安,军阀混战,军阀政府滥杀无辜摧残争取自由权利的学生与工人。女师大风潮、“三一八”惨案均对鲁迅思想产生极大的震荡。与弟弟周作人的兄弟失和以致决裂,使鲁迅极力维持的完整家庭概念不复存在,他最后的精神家园至此四分五裂。但是,鲁迅坚定地选择独自不断战斗,在《野草》中深刻地表现受难意识。
在《求乞者》中,受难意识表现为对民众惰性、“少耻”社会环境的反思。面对孩子的行乞行为,“我”坚定地反对布施,因为无用的同情与施舍无法改变一个人或国家的命运。这样的遭遇引发“我”深深的内疚,因为惰性已经遍布于整个中国社会,人们麻木地屈从于寄生虫式的、奴隶式的命运,而且从儿童开始,社会整体风气流露出畸形的宽容,无形中加剧了民众命运的悲剧性,民众无法看透自身挣扎与痛苦的根源,因为他们从未从自身去寻找根源。
而在《颓败线的颤动》中,受难意识表现为母爱受到反噬产生的巨大悲苦。母亲为了孩子的生存出卖肉体,长大成人的孩子却站在母亲的对立面怨恨、鄙夷、痛斥母亲,这样的对立非但没有改变现实境遇,反而使双方陷入更加痛苦的境地。母亲的付出与牺牲变成自取其辱,作为受难者的母亲,思想从震惊到无言以对再到最终一切归于沉寂,展示从怀有希望到无所希望的过程。
写作《野草》前后,正值鲁迅的多事之秋,“五四”新文化运动出现逆转与挫折,《新青年》团体解散,鲁迅似在沙漠中孤军奋战的勇士。而与弟弟的失和决裂,使其失去家的精神依托。即使身处这样的时期,他也没有放任自己随波逐流,而是宁愿独自受难也要保持自身思想的独立性,他用心去观察与体味,将受难意识融入文学创作当中,展现他对时代使命的担当。
(二)自省的品格
《风筝》一文,主要体现鲁迅的自省品格。这种自省意识不仅表现为对群体的共性深度思考,而且表现为以自我为剖析对象,对个体进行自我考量与自我批判,从人学视角不断阐释自我的觉悟。
《风筝》是异地思乡之作,是对童年生活的回忆。夏志清曾指出“鲁迅的故乡是他创作灵感的源泉”[5]。当年的“我”扼杀了小兄弟放风筝的梦想,长大成人的“我”反思发现当年自己的行为属于对他人的精神扼杀,内疚心理渴望得到小兄弟的原谅。但在多年后“我”向小兄弟表明心迹时,小兄弟已全然忘却这件事“‘有过这样的事么?’他惊异地笑着说,就像旁人听着别人的故事一样”[1]。这样的回答使“我”心情更加沉重。忘却对受害者来说是最大的恩惠,而对于耿耿于怀的犯错者来说是最大的惩罚,于此鲁迅再次强调乞求得到他人宽恕或是惩罚,并不能得到真正的心灵救赎。《风筝》体现人们更加注重自己的社会属性,希望在复杂交错的社会关系网中,自己的行为能够得到他人的认可。
《风筝》中的自省是社会学角度下的灵魂自省,以个人心理需求为分析对象,探讨在社会集体中,个人行为是得到他人认同更重要,还是满足自我心理需求更重要。鲁迅认为,当人们强烈寻求个体在社会集体中的认同感以及独立性价值时,潜伏着丧失斗志与盲目从众等巨大隐患,因此需要反思自身行为能否满足心理需求,清晰定位自身的行为能否得到他人的认可。这种自省的品格是社会觉醒的基础,也是鲁迅自省哲学不可或缺的部分。
(三)反抗的精神
坚韧的抗争一直是鲁迅所推崇的精神,这种精神能够关照行动,具有内敛性的同时又展现出一种外拓的精神。在遭受军阀混战、女师大风潮、兄弟失和等之后,鲁迅的心灵受到极大的震荡,因此鲁迅将这种坚韧的抗争精神摆在更加显要的位置,在《过客》与《立论》中体现这一精神。
《过客》中的坚韧抗争精神集中体现在“过客”身上。“过客”不知道来路,无路可退,永不停息地“走”,在突出坚韧性的同时强调其中的耐久性[6]。“过客”在前行的道路中遇到饥饿寒冷等障碍,但最大的阻碍来自于情感。纯真的小女孩担任了这样的角色,她的布施与挽留是孩子内心善意的表现,但安逸却会损耗人的斗志。在那个时代,为美好理想抗争的人是孤独的,所有的人都臣服于现状,被黑暗的社会磨去反抗的勇气,麻木地苟活于世上,但“过客”最终选择了继续前行,传达出坚韧之外的恒心与信念。
《立论》中赞扬了询问立论方法的小学生“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坚韧抗争精神。鲁迅用一个“梦”的形式,采用近乎寓言的笔法揭露了当时社会真理被扭曲、黑白不分的丑恶现象。说真话坚持真理的必然遭打,鼓吹逢迎的得到好报,而作为小学生的“我”却愿意既不谎人,也不遭打,文章最后虽用一张“好好先生”圆滑老练的嘴脸以及一连串的象声词结束,表明“我”不愿苟同如此做法。《立论》突出的是在缺乏求真勇气的社会大环境下,意志稍微不坚定就容易被侵蚀同化,个人要突破这样的畸形社会风气,不仅需要坚韧和信念,还要有对事物冷静的思考和辨识能力。用象征的手法表达对现实的坚韧抗争,体现出鲁迅对世情清醒的认识与果敢的态度。
三、结语
鲁迅作为“五四”文学革命的先驱,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和犀利的眼光,挖掘近代中国社会人们病态的生存状态。《野草》展现鲁迅在最苦闷时对自我内心的剖析,在彷徨中探索前进,而塑造的儿童形象,则表现鲁迅以一个先觉者强烈的责任感对自我与国民性进行残酷犀利解剖,揭示人与人之间的不理解、不同情和心理上的隔绝,并通过对故乡的眷恋、审视与批判,贯穿他深刻的人生哲学。从儿童形象塑造走进《野草》、读懂《野草》,不浮于表面、流于形式,才能感受到最大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