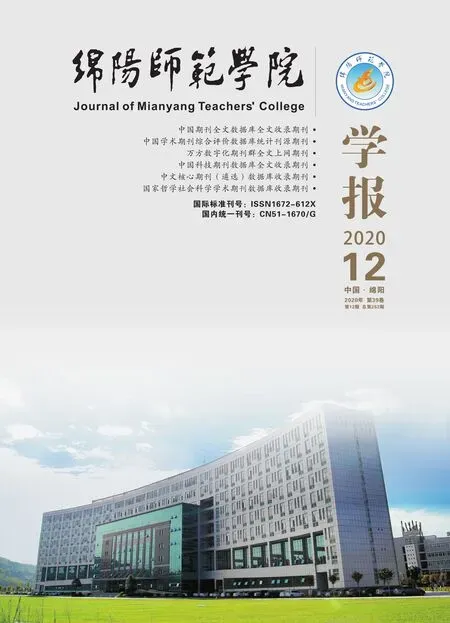第三代诗歌事件中的人、物关系探
——以韩东和于坚为例
2020-02-27徐冰月
徐冰月
(山东大学文化传播学院,山东威海 264209)
引言
“事件”本是一个哲学范畴的术语,随着后来的不断阐释逐渐进入到文学领域,进而再发展到叙述学这一专门的学术领域中[1]。叙述学中的事件理论深受英国哲学家怀特海和法国哲学家巴迪欧的事件理论影响,他们都强调事件作为思考存在的先导性意义。在怀特海看来事件的流变和事件的相互扩延产生了抽象的时间和空间,因此“事件成了衍生时间和空间的本体”。巴迪欧更是强调存在本身即为事件,事件的“关键属性”在于“它的突发性显现,甚至就是它突然显现的一瞬间”,事件以其变动本身显现存在[2]。伴随着哲学领域事件在本源性意义上对传统哲学的颠覆,事件成为世界存在的基本单位,并具备动态和过程两个基本属性,在诗歌叙事学方面也出现了意象化抒情到事件化抒情的转向。“事件化抒情是指通过描述事件或场景来抒发情感的抒情方式”,它“肯定日常体验的本真性,并使日常体验和艺术体验重合”[3]。具体到第三代诗歌,他们将哲学范畴的事件存在意义吸纳进诗歌,把握事件的动态和过程特性,在拉近日常体验和艺术体验距离的同时,表现出对人的存在、物的存在、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物关系的独特思考。正如巴迪欧所说“事件乃是变动本身”,变动意味着诗歌中人与物时刻处于一种运动状态,人以其游走性彰显生命的绵延而存在,物连一瞬间的光影中也不能静止,人与人之间关系在剥离了外在的社会规约之后显示出短暂的时效性,人与物之间也并非既定的我高你低、我尊你卑的地位。重新打量于坚和韩东诗歌事件中的人、物关系,有助于我们返回事物本身作出一些本源意义的思索。
一、人的存在——游走性
第三代诗歌从发生之时起就表现出对当下人生活状态的极大兴趣,而诗歌中出现的人,在客观的日常体验叙述中常常表现为一种游走状态。他们不为什么而行动,仅仅是因为生活或者生命本身就是一场体验式的存在,在剥离了一切社会价值之后,他们的存在姿态表现为在地理空间上赤裸裸地游移和行走。最典型如韩东的《大雁塔》,诗中韩东重复了三遍“爬上去”“然后下来”的过程,无论是来自“远方”的人,还是“不得意的人们”“发福的人们”,还是“我们”,大家重复着同样的动作并有着同样模糊爬上大雁塔的冲动——“做一次英雄”。当所有人的行动具备了同质性时,“做一做英雄”不过是自我内心的一种虚荣和自我抚慰的幻影,“当代英雄”是跳下大雁塔在台阶上开出的一朵红花,这种嘲笑的口吻进一步解构了人的行为意义,只剩下垂直空间上的上去下来,以及横向空间上到来和返回。同样的,韩东在《像真的似的》中说“为了来这里坐坐、走走/漫无目的,无所事事/悠然自得,像真的似的”,去丽江古镇的旅行也是一场纯粹的地理空间上的“游走”事件,短短的一小节诗中,“像真的似的”重复出现了四次,这种重复的叙述在经过多次强调之后就变成一种无法确定的疑问。事实上“河水”“蓝天”“白云”“雪峰”都是真的,诗人所深深怀疑的恰恰是自我存在的虚无和无法捉摸,“打飞机过来/一路跑马”,一场漫长的颠簸之行之后,诗人体会到作为自我的人不过是“坐坐、走走”这样“漫无目的、无所事事”的游走。行走,不带任何目的,不负担任何文化价值意义,这是对生命本真无始无终的绵延状态的纯粹展示。
对于旅行,旅行中的游走,第三代诗人体现出一种无法掌控生命的运动,也不想停下运动的追逐状态。于坚的诗《在车上》中写道:“我不喜欢车停 这当儿我总是出汗/直到汽笛响起 世界又一次向后退去/我才一阵凉快 像远处的云/被阳光缓缓地松开。”车不能停,人也不能停,也许车一停、人一静,片刻的静止就会让诗人产生存在的虚无和恐惧,“我害怕我会在那儿消失”。诗中于坚还表现出人从青年到中年思想状态的变化,年轻时人关注的是外在的体验,“奇异的事物”“一闪即逝的景色”就会令人“动心”,但是“一过中年,日子就快了”,“时间和死亡再也不是敌人”(韩东《海啊,海》),诗人更加关注这些体验背后人本身的存在,所以会注意到天空和大地的安静。人的存在即是一种游走的姿态,人被“游走”所驱使,同时又无可阻挡地迷恋着、向往着“游走”,这其中有一种无法掌控命运、无法安宁于任何一种静止状态的慌张。于坚在《送行》中进一步表现了“游走”尽头之死亡的不可预约性,“你可以浪迹四海/远离故乡/但你不能在一个最喜欢的所在死去/你不能在想象的钟点撒手而去”。前路莫测而行走不止,死亡是生命游走中一个偶然遇见的驿站,你不能预见它出现的空间,也不能指定它到来的时间,“从一个站到另一个站”,生活永远是“陌生”的。我们能感受到死亡的存在,但永远无法真正看清它的面目,唯有当下的体验最真实,也是一步步追问人的终极存在的必然路径。韩东在《飞着去,游着回来……》中流露出同样的无可奈何的游走使命感和宿命感——“哦,这前途莫测但命中注定的旅程。”一场生命的体验,不管“开始或结束”,不问性别是男是女,也不管是“一个或是一双”,人想要定位自己在世界的位置是困难的,因为本质上人就像鸟儿和鱼儿一样不过是“飞着”“游着”,在此地和彼地之间有一定空间距离的“游走”。只有在剥离社会价值的规约之后,人才有能力变得聪明和通透,于人的存在游走性中寻求一种自我和世界之间的平衡方式。游走使得形而下的肉身得到一种解放从而释放部分焦虑,“像远处的云被阳光缓缓地松开”,达到自身一种舒适自在的状态。正是在这种后现代的生命体验中,我们看到人“是一群漂泊的符号,游荡在无确定的当下,孤独、迷惘而又真实”[4]。
二、物的存在——过程性
第三代诗歌中的事物除了具有回归日常生活的特点以外,诗人更注重在诗歌中表现事物自身的流动状态。他们善于捕捉日常生活中的细微之物,以及一些稍纵即逝的瞬间,通过事物的运动过程呈现平淡的诗意。虽然怀特海认为事件的流变和扩延产生了时间和空间,但也同时强调事件以及其中的事物必须放在具体的时间和空间中才能称为事件。
对于表现事物在时空流动中的存在或者说事物本身的存在过程性,于坚很擅长借用“阳光”这个物象,一方面阳光的流动蕴含着时间的流动,化抽象时间为具象阳光,化无形为有形。另一方面阳光的流动过程十分细腻和微弱,非细心之人无以察觉,非宁静心态无以感受,可以说阳光天然具备了诗性的特点。于坚的“阳光”流动的世界同时具备了电影中的慢镜头和特写两种效果,时间被放慢,事物的局部被放大。于坚在《一只充满伤心之液的水果》中写道:“一只充满伤心之液的水果/搁置在清晨的桌面上/塞尚的白桌布/野兽们梦想中的钻石/阳光旋转/搬动着影子/让它青涩的一面向着光源/红色的一面在黑暗深处/绿色的一面在镜子中。”桌面上的水果加上“塞尚的白桌布”,本来是一副典型的静态油画,但是诗人一旦发现了“阳光”就有了动态。于坚的诗中阳光不是片刻映照下对水果产生黑白两面的色调差异,而是在“旋转”,在“搬动影子”,我们仿佛能看见光影围绕着水果的不同角度在做着轨道运行一般地流转。在《一枚穿过天空的钉子》中,一枚普通的钉子本是静态的,但于坚笔下这枚钉子因为“穿过阳光”“穿过房间和它的天空”,从而具备了一次动态的生命过程。这个生命过程从穿过阳光那一刻就延长了,并产生了一段故事:从前它被人敲进墙里,然后挂了帽子一直遮蔽,帽子烂了,它从墙壁上露出来,重见天日。即使像铁钉这样没有思维的事物,它也有跌宕起伏的生命存在过程。《阳光破坏了我对一群树叶的观看》中一整片无差别的树木因为晴朗时刻阳光的到来,将它们分割成了至少三种象征,“暗示光明或者黑暗/告密者和叛徒/在二者之间/摇摆”,“摇摆”一词使得树木一下子活过来了,有了思想,他们一会儿站队光明,一会儿站队黑暗,更多的时候是摇摆不定的告密者和叛徒,因为阳光的加入使树木处于一种喧哗骚动的过程中。《苍山之光一秒钟前在群峰之上退去》中,苍山之光退去的过程,像“叛乱的马群”被赶进马厩,像“日光伪造的金币铺/一间间倒闭”。一秒钟光影的时空运动,被诗人连用的两个动态比喻表现得壮观而欢腾。这几首诗中所涉及到的物象是阳光——水果、阳光——钉子、阳光——树木、阳光——群山,于坚在表现事物在时空的变化过程时,自己往往并不参与其中,而是退居其后隐藏自己的态度,呈现客观事物之间本身的相互映照、动态关联,表现物“是其所是”的自然流变状态。“存在,就是在途中。诗就是在途中,途中就是能指或命名呈现的过程。”[5]144于坚正是通过事件书写这个载体,表达“万物皆流”的哲学思考。
同样是对瞬间变化的把握,对光影的书写,韩东的诗歌中有着对时空不一样的运用。韩东《黄昏的羽毛》中捕捉到黄昏降临过程中的某一时刻,“窗外一片静谧”,黄昏瞬息间展开巨大的翅膀将万物悄然无息地淹没,这种宏大而安静的场面突然间触动了诗人的心灵,但诗人惊讶地发现黄昏以及黄昏之下的一切和自己“就像隔着一层玻璃”,安静而清晰,“它们并不和我接触”。这种矛盾来源于两条时间线和两种时空的对照。“我坐在家里”的私人空间或社会化了的空间和“窗外”的自然空间或物理空间相对,“点灯”的心理时间和黄昏降临的物理时间相对。“点灯”是人们经验世界的事件,当一些动作已经习以为常,我们习惯性地屈从身体的反射在某一时刻点灯,时间更像在人们的心里流动。而黄昏自有其自身的运行时间,它不以“我”的行动为参照,更不照顾“我”内心时间流动的感受。当黄昏降临这种当下的体验超出了“我”的心理预期或者说“我”的经验范畴,两种时间擦身而过便产生生命的断裂感和慌张感,也许这就是古人“时不我待”感受的最初来源,诗意也就产生于这瞬息的变化中。
对于事物的瞬间变化过程,于坚倾向于表现客体自身的存在姿态,探究事物在时空中的本源意义;韩东则在观照客体时多了一份主体与世界互动时的古朴情愫,这种看似“粗野”浅白的当下呈现,其实是当下经验在形而上层面的真实状态。尽管二人有着不一样的哲学思索,他们对于物的过程性的呈现却表现了第三代诗歌在回到当下、回到生活本身的诗学理念主导下的多维可能。
三、人与人——时效性
于坚和韩东的诗歌中常常会出现一些公共空间如“广场”“公园”“火车车厢”等,人们因此而发生了部分交集,也可能会因为一些社会公共事件如“结婚”“旅行”等产生联系。对公共领域事件的书写,诗人一般采用外聚焦叙事,在冷静地塑造芜杂的群像之时,更十分清醒地表达着对人与人之间本质的深刻思考。
以于坚的《广场》为例,都市广场是一个较具开放性的公共化场所,某种程度上人们对于广场的接受度仅次于自己的居所,进入一个广场谁都不会产生闯入陌生的或者私密领域的隔阂感、拘束感。世界各地的人都来这里“看天”“看地”“看热闹”,大大小小的鞋子停泊在这里,很多人要穿新衣服,打扮得花枝招展,“拥挤/碰撞/五光十色/摩肩接踵/流吁喘息”,一派热闹欢腾的景象。而当傍晚降临,“鞋子一双一双驶远/门一道一道关上”,广场又陷入“空阔而巨大的黑暗中”,白天的一切声音、热闹的人流都像没有发生过一样,只有广场上石膏砌成的假人像一个“永生的戏子”在孤独中沉睡。
广场每天都上演着“一个男人碰上一个女人或者一个女人碰上一个男人”这样短暂的社会生态,大家似乎因为广场的存在而具有了某种联系,但转眼间“世界在这里聚集/又在这里走散”,又似乎没有任何关系。诗人认为“每个人的脸上都有两颗害怕孤独的星星”,人们因为孤独而冲到人流之中用集体的喧闹掩盖内心孤独的本质,但其实用这种行为在广场上所构建的人际交流是暂时的、虚妄的、无效的,这种群体间的相处对于从本质上缓解人存在的孤独没有帮助,只是在骗自己而已。广场上的那个石膏砌成的假人,可以分三个层次来理解。首先,他确实是物理空间上存在的石像,是广场生活的一部分;其次,他有时是诗人自己,不带任何情感地观看着人潮的来来往往,诗人采用外聚焦的视角,客观地陈述广场上的一切,就像石膏一样做个假人,隐藏自己的态度,尽力还原广场的原生面貌;最后,这个雕像其实也是作为个体的人的一种象征。每个人就像广场上的石像一样,曾经来到广场凑热闹,随时和各个时段、世界各地的人发生着偶然的联系,世界相聚时带着“两颗孤独的星星”,世界离去时又在“孤独中沉睡”,人们拒绝着孤独但又摆脱不了孤独,白天发生的一切就像一场舞台上的一出戏,个体的人不过像石像一样都是一个“戏子”,做着骗自己的动作,谁又能真正关心另外一个人想什么呢?于坚在这首诗中对人与人之间这种“过客”般的体验给予了无情地揭露,也从本质上表达了人生在世是一场孤独的个人之旅的哲学思索。
韩东的《街头小景》描述了“我们”在街头站牌遇到两个哑巴,然后他们上车离开这样一个事件。诗中涉及到三种语言系统,“树和风”“两个哑巴”以及“我们”。尽管大家处于“街头”这同一个空间中,相互谈论着一些东西,但是谁都听不懂对方说什么。我们和哑巴之间并不是没有联系,“我们议论着两个哑巴”,也许两个哑巴也曾议论“我们”,这些都表明人与人之间也许只是遇见过然后走开的关系,仅此而已。这种关系也出现在于坚的《事件·谈话》中,因为下雨家中进来两个“素昧相识”避雨的人,我们都认识“李”而成了“熟人”,一场谈话经历一些“沉默”和“小幽默”,十一点整“分手时间”,所有的声音“消失在万物的根里”。
以上种种“相聚-离开”的人际交往模式在生活中十分常见,但在诗人呈现出来之前却被很多人忽略。长久以来,人们总是下意识地寻找熟人打交道,寻找所谓的心灵伴侣、红颜或蓝颜知己,但人们没有意识到的是生活中的陌生人总比熟人多。我们的生活本质上也许并不是和熟人越聊越热,而是每天和许多陌生人进行着烟火般一闪即逝的摩擦,人与人之间这种破碎的、片段的体验才构成了过往和当下。这也正是人与人之间关系时效性在无形中发挥着它的规则力量时所呈现出来的世界的另一种面貌,看起来陌生又可怕。
除了公共空间中对陌生人之间人际建构的思索,对于人世间的爱情、婚姻关系的理解,韩东和于坚都曾选择剥去了它们神圣的外衣,在事件书写中更进一步揭露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本质。于坚的《事件·结婚》表现了集体喧嚣之后复归宁静的巨大落差,极具讽刺性。新人结婚因为“在中国社会上/孤独是可耻的”,新郎只有通向婚姻的小人国,“紧紧牵着他的新娘子”才具备“堂堂正正做人”的资格。新郎牵着新娘像牵着一只“光宗耀祖的孔雀”接受着“真真假假的祝福”。除此之外,诗中涉及的群像更具讽刺意义:“小舅子扛着摄像机 露出邪迷着的左眼”,“当母亲的/把循规蹈矩的老脸/凑近”,“沉默是喜宴的大敌”,说话是人人应有的礼貌,“抓住机会/过去喝一杯/胁肩谄笑/嘘寒问暖/把有些开裂的关系网/补补”,经过一系列“应酬/尴尬/狼狈/临了/杯盘狼藉/席终人散”。这首诗于坚将很多词语、短句进行并列、混合、交叉,时而节奏明快时而细细打量,展现了结婚这个热闹的事件里复杂而分裂的关系网。人们因为一些社会既定的规约维持着闪闪烁烁的关系,说着似是而非的话,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维系微妙而孱弱,纤若游丝。结婚像一场闹剧,人们进来这个舞台表演着自己的角色和应有的风度,然后离去。于坚对人社会性一面的揭露一方面是慨叹人本真性的缺失,同时也是对人与人之间关系在社会中存在的时效性表示怀疑。
韩东《爱的旅行》拿神圣的爱情开刀,对爱情做出理智冷静的考量。《爱的旅行》中的男女“在车厢里认识/在车站分手/分别从两边的车窗/完成了平原的图画”。人世间的爱情就像一场旅行,两个人在一起不过是恰巧遇见有着同一个“爱的目的地”,所以渡过一段共同旅程。也许每个人还有自己想要完成的“平原图画”,当车到终点自然分开,仅此而已,经历即是存在。“也有人永远孤独”,一生带着“梦的蝴蝶”在旅行,你经过了“开花的原野”,但也仅此而已。爱情不是必然会到来,到来的爱情并不必然会长久,爱情并不神秘和美丽,没有开花结果的义务。爱情不过是生命旅程中一个平凡的事件,“是一段无目的的、合目的性的遭遇和见闻[4]。其实,不仅仅是爱情,包括亲情、友情,人世间没有哪一种关系是永恒不变的,父母、爱人、朋友、孩子都不过是人生某个阶段的旅人,最长的路一定是一个人走到底的。韩东自己的现实生活体验最能体现他诗歌中流露出的这种人生观,幼年他的父亲自杀离去,这成为需要诗人用一辈子去化开的结;青年时创办《他们》诗刊,又在时代浪潮中经历过了曾经志同道合好友们的聚合与离散。人生的分分合合,走走停停,每一段路程都有一个时效性。在诗歌《进行曲》中,韩东表示“不想再做人/不想再忙碌/不想再思想/不想理解需要理解的东西”,“我丢下一切/让他们自由”,诗人放下了固执的思索,回到生活本身的自然状态,对于“那些爱我和不爱我的事物/和另一些爱我和不爱我的事物”,选择“让时光匆匆流过……”。诗人在洞明世间人与人、人与物的牵连之后,就多了一份坦然面对的勇气。
四、人与物——相对性
第三代诗歌对日常事件的书写,诗人选择了一种平视乃至仰视的叙述视角,主动放低自己的姿态,以一种平等甚至谦卑的姿态去呈现事物。退出人全知全能的角色,选择从“他者”的眼光来反观自身,这其中呈现出的哲学意义是人而不是世界的中心,世界的构成不是靠单方面人的观察决定的,人与物之间的地位并不是仰望与俯视的位置,而是处于一种像镜子一般的双向映照中。这也使得诗中的人与物之间具有了相对性,借助“他者”的眼光,人在完成自我重新认知时,也部分地完成了对世界存在的解构与重构。
于坚在《作品100号》中称“你明白你现在活着/身体健康/你的生命得到一只苍蝇的证实/当它降落的时候/你搔了搔鼻尖”,在这里人的生命状态被一只苍蝇所证实,而不是人去感知苍蝇的存在,人要依靠外物去感受自身活着的状态。在《灰鼠》里,“我”与一只在房间的老鼠斗智斗勇,灰鼠似乎完全具备了高水平的智识和自由行动的能力,“我”只会“乱敲乱捅”“心烦意乱/茫然失措”“担惊受怕”,但是灰鼠在一边从容地啃咬蛋糕、衣物,酣然睡去。透过老鼠的眼睛,作为万物之灵的人是下面这幅窘态:“你在暗处/转动着两颗黑豆似的眼珠/看见我又大又笨/一丝不挂/毫无风度/你发现我在夜里的样子……使我深觉难堪。”人的优越感和尊严一扫而尽,反而显得“灰”溜溜地。“一丝不挂”的样子在某种程度使读者联想到人作为动物赤身裸体的本来面目,“我”之所以感到“毫无风度”,“深觉难堪”,一方面是现代文明的道德规约所致,另一方面是“我”对突然间失去了文明遮蔽的动物身份感到陌生和紧张,借助动物的眼睛人们得以重新观照自己。《一只蚂蚁躺在一颗棕榈树下》中,“我”蹲下来看一只蚂蚁,对于它“千奇百怪的念头”,“我也无法知晓/对于这个大思想家/我只不过是一头猩猩”,诗人在一只蚂蚁的眼睛里明确了自己是“一头大猩猩”一样庞然大物的身份。除了在身份上降低自己的姿态以外,在思想上也表现出对生物的敬畏,“我”并不明白这些动物头脑中丰富的世界,我们对动物的认识区域远不如未知的空白多。在诗歌《三乘客》里面,三个乘客在车厢中兴致勃勃地谈论着关于狼的故事,在漫长人物对话叙述之后,诗人将空间描写由车厢内转到了车厢外,当放到更大的时空中去看世界时,事件就变成了这个样子:“这是一个平静的夜晚/任何地方都没有发生车祸/有几头狼在黑暗里/经过这条铁路附近/停下来/默默望着这列火车。”随着时空转换所呈现的情节转折,给读者造成强大的心理冲击。在乘客和狼的相对关系中,三个乘客似乎处于一种茫然无知的状态,而狼在黑暗中默默地望着列车经过的动作,更像是清醒地、静静地蓄谋猎物,造成一种“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惊悚感,人的主体地位完全被消解掉,处于一种被看被俯视的状态。
相对关系的变化呈现出世界的另一种真相,那是人不能以自己的感知来自知自明的。拉康的“镜像”理论认为:“自我的构建离不开自我的对应物,即来自于镜中自我的影像,自我通过与这个影像的认同而实现……人们苦苦找寻自我,而当找到它时,它却往往外在于我们,总是作为一个他者存在,被自身无法掌控的外部力量所决定,因而永久地被限定在与自己异化的境地。”[6]这似乎是一个存在悖论,个体的存在有其自在的意义,但自我的构建和认同又必须借助于他者来证实,这其实是人自我认知局限性的体现。当第三代诗歌走出个体全知全能的角色,关注他者,被知觉者反过来审视知觉者,诗中的事件所呈现的生活面貌,不仅打破了对人之存在的固有印象,也重构了日常生活尊严,丰富了我们对世界存在中人、物位置关系的认知,引导人们去发掘海德格尔口中那大片被“遮蔽的黑暗”。
五、结语
从人的游走性、物的过程性、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时效性、人与物之间的相对性出发,把握第三代诗歌紧紧围绕事件所具备的动态性和过程性特征的叙述原则。事件尽管在哲学上具有构成思考世界存在逻辑起点的重要位置,但在叙事学中位置并不是那么显著,热奈特就将“事件”看作是“故事”的从属部分。“只有面对诗歌这种独特的叙述文本时,事件作为独立性的核心价值才能被充分彰显出来,因为在诗歌叙述文本中,事件并不总能构成哪怕是最小意义上的故事。”[2]对诗歌事件诗学的分析需要借助叙述时间和空间、叙述视角、叙述人称等这些经典叙事学的其他方面综合分析,未来还有很广阔的空间可以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