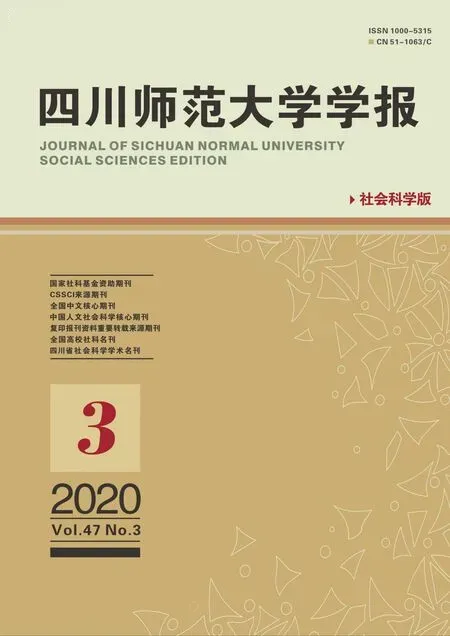文化的表演与再生产:基诺族人神婚恋文化的人类学解读
2020-02-25何点点罗绍林
何点点,罗绍林
(1.清华大学 社会学系,北京 100084;2.四川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成都 610066)
婚姻制度在不同人群中普遍存在,通过乱伦禁忌、包办婚姻、固定婚姻圈等多种形式在特定社会中建立对内对外的稳定秩序。当整体环境或个体经验与严格的婚姻制度失调时,容易引发社会冲突,甚至导致殉情悲剧。在西南地区,纳西族、拉祜族的殉情现象曾较为突出。丽江地区“改土归流”后日益强化的包办婚姻制度和与其相应的封建伦常观等是促成纳西族殉情悲剧的重要原因。而纳西族在强制性的移风易俗政策冲击下所形成的二元婚恋形态——“婚前恋爱自由,婚姻不自由”,则是这一原因中的核心部分。(1)杨福泉《政治制度变迁与纳西族的殉情》,《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第7页。拉祜族高发的殉情案例则与其早婚现象容易导致婚姻不和,离婚代价极高且被施压于道德伦理下有关。(2)陈艳萍《多元文化背景下的拉祜族殉情现象研究》,《云南艺术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第52页。基诺族阿细支系中也曾频发父系氏族内婚禁忌与巴什情的矛盾(巴什是对来自同一父系氏族的恋人的称呼)。杜玉亭在1950年代调查到基诺山巴亚寨青年中有一大半都有巴什情人,除了一对因坚持巴什婚被逐出村寨的男女外,都最终选择了在世时分离的法俗。(3)杜玉亭《基诺族传统爱情文化》,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92页。相较于纳西族、拉祜族,基诺族巴什们往往妥协于婚姻制度,以符合社会规范的方式度过一生。究其原因,有学者指出,巴什们对正常死亡的人才可以到祖先生活之地“司杰卓密”成婚的期望,相信非正常死亡的人不能回到此地的观念,以及巴什情可公开表达的特懋克节所提供的短暂幸福时光都合力消解了巴什们殉情自杀的冲动。(4)陈艳萍《守望生命守望爱——基诺族巴什悲情与巴什情歌》,《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第37-39页。笔者在基诺山调查时了解到,流布于基诺山阿细支系的《巴什》古歌、《箐神传说》和相关仪式构建了“神女”与成年男性的宗教性爱情联结,并以此象征巴什情人终成眷属。(5)本文所用资料,除注明出处的文献外,均来自笔者2015年三次田野调查的资料。这类不断被演述的人神婚恋情节和被展演的人神婚恋仪式,为巴什们建构了“反禁忌”的场域,进而消解了社会冲突。杜玉亭、刘怡、白忠明、沈洽等都对这类口头传统和仪式进行了记录和分析(6)杜玉亭《基诺族传统爱情文化》,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刘怡、白忠明主编《基诺族文化大观》,云南民族出版社1999年版;沈洽主编《贝壳歌——基诺族血缘婚恋古歌实录及相关人文叙事》,上海音乐出版社2004年版。,但并未把口头传统与仪式作为人神婚恋文化整体来探究其在修复社会失序与延续文化再生产时的深层意义。
一 基诺族人神婚恋文化的社会背景
1950年代末以前,西双版纳基诺山的基诺族居住在原始森林中,实行刀耕火种、狩猎采集的生计方式,并用棉花和茶叶同傣族、汉族换取盐、猎枪等物品。这样的自然环境与生计方式保证了基诺族万物有灵的原生宗教信仰的延续。基诺族把所有的灵统称为“乃”(7)“乃”是对基诺语发音的汉译,1950年代以来,受国家话语、市场行为以及学界习惯的影响,“乃”被先后译为“鬼”和“神”,这样的翻译存在着概念上的名实不符或似是而非,关于这个问题参见:何点点、高志英《从祭灵、撵鬼到造神:20世纪以来基诺族宗教文化变迁研究》,《西南边疆民族研究》2018年第4期。本文采用当地人当下的汉语表述方式,把文中与人神婚恋有关的女性“乃”称为神女,把人、物的“乃”称为魂。,并围绕自然之灵与祖先之灵践行一系列生产、生活祭祀和个体相关仪式。这些用以社会治理的仪式以及村落的日常管理主要由村寨长老和宗教师负责。1950年代以前处于父系公社制的基诺族以氏族为单位构成象征权力组织和宗教、社会团体。基诺族村寨按照规模分为大中小三种类型,分别由七个、五个、三个长老主持日常事务。首先,长老均由男性担任,在氏族内世袭,一般为该氏族的最年长者。其次,作为人灵媒介的宗教师包括白腊泡(巫师)、莫丕(祭司)和铁匠三类,司职不同,也由成年男性担任。
男性在社会中作为权威象征,进一步影响了社会中个体归属的血缘纽带——父系亲属制度的形成和巩固。虽然母系制构成基诺族亲属关系的另一个系统,且曾在基诺族社会中发挥支配作用(8)杜玉亭《基诺族简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1页。,但父系制早已是其首要的认同基础并以此形成了相应的社会网络。特别是在1950年代末以前,通过父子连名制追溯为同一父系祖先的氏族作为村落生产、生活的基本单位,共居于一座长房(大房子)里,有些长房居住人数多达百人。居住在长房中的堂亲(9)基诺族认为同一个父系家族的成员之间都是堂亲关系,这个关系网中包含的人数较多。,基诺语称为“巴什”。每一长房有家长一人,领导长房成员的生产、生活。(10)汪宁生《基诺族的“长房”》,《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3期,第234-250页。长房内又以一夫一妻及其子女为家庭单元使用一个火塘。长房内部成员之间禁止通婚。基诺人禁止“同氏族婚配”的自然法规,实质上就是严禁“大房子”内部的通婚。(11)沈洽主编《贝壳歌——基诺族血缘婚恋古歌实录及相关人文叙事》,第378页。父系氏族内婚禁忌是父系氏族制的一个普遍特点,然而,多以家族为主建寨(12)刘怡《基诺族古婚制的化石——基诺古歌〈巴什〉的产生和意义》,《民族艺术研究》1997年第4期,第49页。,大家族共居的家庭结构,以及交通不便、居住分散等原因导致传统社会单位具有封闭性,造成同一氏族的青年男女的恋爱频频发生。因源于同一父系氏族,这些情侣也被称为“巴什”,他们试图结婚的愿望与族内婚禁忌矛盾不断。
二 反禁忌的表演:人神婚恋传说与仪式实践
特纳强调“社会戏剧”(social drama)产生于冲突的背景之下,属于积极的结构性概念。(13)特纳《戏剧、场景及隐喻:人类社会的象征性行为》,刘衍等译,民族出版社2007年版,第29、39页。换言之,通过社会戏剧把在社会结构中产生的压力和紧张表达并展示出来,而这些社会戏剧常常是以仪式的形式来表达的。(14)刘涛《社会戏剧中的符号:人类学仪式与象征阐释研究》,《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第52页。基诺族阿细支系流布的《巴什》《箐神传说》等口头传说以及相关仪式展示了神女与成年男性的爱情关系,并把神女视为巴什女死后所变,以象征巴什关系。具体表现在两类仪式中。第一类是宗教师的诞生仪式。成为铁匠、莫丕(祭司)或白腊泡(巫师)必须经过以下途径:该男子要意外地得到被视为铁匠神女、莫丕神女或白腊泡神女向其“示爱”的礼物(前两种多为鼠、鸟,后一种主要为贝壳)。经父寨(15)父母寨是某支系在基诺山建立的第一、二个寨子,阿西支系的父寨是司土寨。的老白腊泡(16)老白腊泡是指经验丰富的白腊泡,一个寨子可能会有多个白腊泡,也可能没有。确认后,举行隆重的宗教性结婚仪式。这位男性根据“结婚”的对象获得相应的宗教师身份。第二类仪式是“猎祭仪式”。猎手打到的马鹿、野猪等猎物被视为兽神(17)兽神也被称为箐神,基诺族认为女兽神住在箐的上游,男兽神住在箐的下游,本文提到的兽神为女性,是巴什女的化身。赠与的爱情信物,当晚猎手要独自在家屋中的兽神柱(18)兽神柱是基诺族房屋中五个被赋予神圣意义的柱子之一,下文提到的神女柱也是五柱之一。旁睡一晚或三晚,以象征与兽神“同寝”。
恋人相互赠送定情信物是基诺族情侣之间的习惯,恋爱时,男方会送给女方竹筒、耳环、口弦、烟盒,女方送给男方槟榔、鲜花等。相比之下,神女的礼物更为贵重,鼠、鸟可以满足大家庭的日常食物需求,野猪、马鹿等大型猎物足以提供整个氏族乃至村寨一次盛宴;贝壳则是基诺族地位最高的宗教师白腊泡的法器,象征极高的巫术能力。猎物与宗教师在高度依赖自然环境、信仰万物有灵的社会中极为重要,人神婚恋文化一方面解释了其获得与产生的偶然性,一方面通过隐喻让口头传统与现实生活成为相互表达的文化系统。
(一)人神婚古歌及仪式
古歌《巴什》是对巴什爱情悲剧的描述和情感抒发,在基诺山的阿哈支系和阿细支系中流传着不同的版本。阿哈支系流传的《巴什》以最终实现族内婚为结局,以巴亚寨为代表的阿细支系则流行严禁血缘通婚型的《巴什》。阿细支系的《巴什》有三种较为普遍的结尾方式,用基诺人的话来说,就是有三条“歌路子”。(19)刘怡《基诺族古婚制的化石——基诺古歌〈巴什〉的产生和意义》,《民族艺术研究》1997年第4期,第47页。本文研究的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种‘歌路子’”(20)刘怡《基诺族古婚制的化石——基诺古歌〈巴什〉的产生和意义》,《民族艺术研究》1997年第4期,第46页。,也被称为《贝壳歌》。该古歌讲诉道:巴什郎与巴什女被迫分离后,巴什女想要自杀,可是巴什郎劝道:“‘不病去死,魂就到不了司杰卓密’。祖先住的地方,我俩活着成不了双,死后总得同回祖先住的地方。”(21)沈洽主编《贝壳歌——基诺族血缘婚恋古歌实录及相关人文叙事》,第139-140页。在基诺族对死亡的分类中,病死属于正常死亡,死后的魂可以回到司杰卓密。在这里,巴什可以成婚,而自杀等非正常死亡的人则无法抵达这里。这一信仰从根源上阻断了巴什殉情的冲动,巴什女最终因思恋郁积成疾而去世。死后久未等到巴什郎的巴什女,先后化身为铁匠神女、莫丕神女往来灵界和人间,通过赠送鼠、鸟等爱情信物向巴什郎表明爱意。巴什郎求助白腊泡后,确认了示爱的神女实则为巴什女,便和巴什女的化身举行结婚仪式。但是巴什女认为“这种成双,只不过是挂在那口头上”(22)沈洽主编《贝壳歌——基诺族血缘婚恋古歌实录及相关人文叙事》,第209页。,便再次化身为白腊泡神女,把自己变为贝壳,作为赠与巴什郎的爱情信物亲自去到巴什郎身边,最后通过结婚仪式与巴什郎建立了真正的婚姻关系。(23)沈洽主编《贝壳歌——基诺族血缘婚恋古歌实录及相关人文叙事》,第209页。
这首古歌依次用铁匠神女、莫丕神女、白腊泡神女象征巴什女。巴什女借用神女身份与人间巴什郎建立宗教性的婚姻关系不仅在这类口头传统中演述,还在1950年代末以前的基诺社会中通过仪式进行模拟和再现。笔者在田野调查中对白腊泡神女与成年男性的仪式进行了口述史调查。白腊泡作为宗教师中地位最高、职能最多的一类,其诞生仪式也最为隆重。该仪式需要三位白腊泡共同主持,即父寨会蒙贝的老白腊泡(24)父寨会蒙贝的老白腊泡是仪式最核心的主持者,因为不是所有的老白腊泡都会蒙贝,其在基诺族中的地位极高。、本寨的老白腊泡和即将成为白腊泡的仪式对象。白腊泡会蒙贝与否取决于是否成功举行了婚礼中最关键的蒙贝仪式(25)关于蒙贝仪式的仪轨,详见下文的婚礼仪轨。。举行过三次蒙贝仪式的白腊泡地位最高,三次仪式全部完成往往要经过数十年,因为每一次仪式都花销不菲。
该仪式对象在仪式前会意外获得被视为白腊泡神女示爱的预兆,如:该男子拉弯弓打野猪时,原本没打着,却看到野猪站在那里一动不动,走近一看野猪已经死了,耳朵里有一颗贝壳;盖房子时,帮工的男子轮流到引水的竹筒边洗手,只有该男子洗手时会获得顺水流出的一颗贝壳。经历了这类事件后,该男子往往卧病不起,由家人拿着鸡蛋、米和他的衣服到白腊泡处占卜,白腊泡确认病因为神女所致后便由该男子所属的整个氏族开始共同筹备结婚仪式。仪式在该男子家中举行,共六项。第一项为祭雷神,当日早上八点后,由莫丕到该男子家屋外的空地上念祭词举行,仪式需要制作一个三角形竹桌,其中一足高出桌面,且带有坠下的竹尖,高、矮桌脚部分别放一头白猪和一头黑猪,猪嘴巴含着柱子,一白一黑两只公鸡分别摆在其后。第二项为花架迎白腊泡,花架需前一天制作好,为竹制,长度约15至20厘米,绑上各色树叶和鲜花,顶部插入一束鲜花,其中两个花架装饰得鲜艳饱满,另一个稀松单调。当父寨白腊泡到村寨门口时,几个成年小伙子依次抬起三个花架,装饰鲜艳的在前,敲着铓、镲和锣,迎着白腊泡从寨外穿过寨心走到仪式场地。三个花架分别在路上、仪式对象家屋院坝和登上入户楼梯后由全寨人抢夺,但后两个花架中间插着的那束花不能抢,要由白腊泡的助手拿下。第三项为祭“乃”,由父寨白腊泡主持祭祀荞魂、钱魂、男性的九魂、女性的七魂和鼠、鸟、兽魂等,以排难祈福。第四项为剽牛,所剽的水牛拴在吊脚楼下层的水牛柱上,这棵柱也叫神女柱。牛旁依次摆上鸡、鸭、狗。父寨白腊泡在助手的辅助下,一边念祭词一边用火钳夹着葫芦瓢(26)基诺族崇拜葫芦,是生殖崇拜的表现之一。里的槟榔和槟榔叶喂给这些动物,并把葫芦瓢里的水泼在动物身上,寓意献给神女的牲畜内外都已去除污垢,达到宗教意义上的洁净。洁净后,开始剽牛,先由父寨白腊泡剽三次,剽牛时呼唤神女三种名字之一(27)三种名字是指白腊泡神女具有的三种魂,即荞魂、钱魂和鼠、鸟、兽魂。呼唤哪一个名字与父寨白腊泡自身情况有关。地位最高的白腊泡是举行过三次蒙贝仪式的人,第一次是和白腊泡神女的荞魂结合,第二次是和神女的钱魂结合,第三次是和神女的鼠、鸟、兽魂结合。如果父寨白腊泡自身只举行过一次蒙贝仪式,那么他在剽牛时呼唤的就是荞魂,如果他举行过两次了,就要呼唤钱魂。,另外两位白腊泡再剽牛致其死。第五项为放神房和供牛头。父寨白腊泡把神女的神房送到家屋内神女柱旁的神台上,此时已快到半夜,他的助手把牛头抬起来,白腊泡念祭词以示供牛头给神女,接着,三个白腊泡绕遮科(28)“遮科”是在竹板两端竖起两根竹子,竹子顶端削一个V形的口,固定上一根竹子的物品。转三圈。神女房由椿树板围成,登台木做顶,约长80厘米,宽、高各60厘米,神女房象征神女的居所,需终生供奉。第六项为蒙贝,父寨白腊泡同仪式对象站在祭桌前,桌上摆有牛头、一个装水的铓,水里飘着三片生姜(29)基诺族认为生姜可以辟邪。,他手拿扇子呼唤神女时,先后有两颗贝壳从远处飞来落到铓里,父寨白腊泡拿扇子盖住铓口,再把贝壳拿出来让仪式对象在嘴里沾一下,接着用一个粘有蜜蜡的竹片把贝壳粘住放进一个竹筒里,竹筒放到竹篮里,竹篮放到仪式对象的枕头边,仪式至此结束。
(二)人神恋传说及仪式
与此类似的用人与神女隐喻同氏族恋人的口头传统还有“箐神”传说:
有一对基诺族的堂兄妹,从小就居住在一幢大竹楼里,他们终日生活、游戏在一起,一个香蕉掰成两截,每人吃一节,一个鸡蛋分成两半,各人吃一半。小时青梅竹马,成年时相爱更深。但氏族内禁止婚配,两人约着逃到深山密林里,仍不敢公开露面,阿妹住在箐的上游,阿哥住在下游。后来阿妹死了,成为神,阿哥很伤心,每当他在箐中拉弓狩猎时,都要在他们两人同居过的山箐里做纪念阿妹的仪式,阿妹也常常送些野兽在箐中,让阿哥随意猎取。后来,猎人若到深箐里拉弯弓狩猎,都要在箐中做纪念仪式,祈求箐神多多赐给野物。(30)姚宝瑄主编《中国各民族神话·水族 布朗族 独龙族 基诺族 傈僳族)》,书海出版社2014年版,第173页。
箐神也被当地人称为兽神,是掌管森林、动物的神女,巴什在这则传说里被象征为猎手和兽神。狩猎是基诺族最为重要的传统生计方式之一,是获得肉食的来源。1950年代前受制于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打猎和采集的可变性和随机性太大,一户人家不能依靠独立打猎或采集来长期维持生计,人们之间高度依赖,无论是刀耕火种还是狩猎分肉都多以氏族或村寨为单位进行。食物共享保证了一个社区食物来源的长久性和稳定性,因此基诺族在下压木、置弯弓前都要举行祭祀仪式,射中猎物的那名猎手更被认为是兽神示爱的对象,作为对兽神的回应,当晚必须举行娱神和谢兽神的猎祭仪式,包括象征与兽神“同寝”的仪式。完整的猎祭仪式较为复杂。首先,应根据具体猎物当场制作名为“布姑”或“奇科”的竹筒乐器,然后一边抬着猎物,一边敲打竹筒返回寨子。敲击竹筒一是为了报信,村里人根据调子判断打到猎物的种类和大小,以便提前烧水准备;二是为了娱神庆贺。煮猎物时最先煮出的泡沫要打进竹筒里并由猎手放到家屋中兽神柱旁的兽神房一角,基诺族认为这是最好吃的,也寓意第一口要献给兽神。献后人们才可以吃饭,饭前先由长老祭兽神,长老们拿着一小团和着肉、汤的饭念道:“今天我吃了小麂子肉,希望过两天能吃到大野猪、大马鹿的肉,愿每次穿山都能得到猎物。”念后把饭团放在桌子上便可开始吃饭。晚饭后,大家继续敲竹筒乐器、唱《奇科调》(《捕猎歌》),直至凌晨才散。此外,要根据长老、氏族、青年组织等社会成员与猎手的亲疏尊卑关系进行分肉。
晚上客人走后,猎手把猎物的肋巴骨在火塘熏后,在火塘边的架子上挂一晚,待第二天早上煮吃。并把猎物的一块头骨、空壳鸡蛋、一小包肉和饭放在篮子里,篮子放在兽神柱的大梁上祭祀寨神、祖先和兽神,祈求下次的收获。这些仪式后猎手在兽神柱旁独自睡一晚,象征和兽神“同寝”,睡时取下头巾和耳环,以示敬意。第二天赶在村民出工前,猎手带着弓箭独自一人送兽神出村口,这是因为兽神害羞不能碰见人。猎手走到村口,折一支树叶,坐到上面,拿弓箭瞄向打猎的山,寓意下次还能打到好猎物。
(三)巴什情在日常生活中的表达
《巴什》古歌最主要的两个演述场合是“特懋克”和“上新房”。“特懋克”意为盛大的打铁节,是基诺族的年节。“上新房”是氏族内家族的父系家长继任仪式,即在父系家长去世后,新的继任者必须要盖新房杀黄牛,以祭祀“乃”和祖先。这两项全村参与的重大喜庆场合包容了悲剧性的巴什情,在仪式空间里,被迫分离的巴什男女无论年龄都可以执手相依,以歌诉情。一位老人曾向笔者回忆了他年轻时看到老人们泪流满面地对唱《巴什》古歌的情景。除了大型活动,日常生活中也时常可见人们对巴什情的表达,往往包含在当事人与过去的情人(31)基诺族允许婚前恋爱自由,可发展为同居关系,许多人都曾有一个或多个恋爱对象。这一关系的范畴里。婚礼上,曾经与新娘恋爱或同居过的小伙子会用淘米水向新娘泼洒,表示对女伴忘记旧情的“报复”。(32)于希谦《基诺族文化史》,云南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第202页。《奇科调》中也有打猎后,把肉分给过去的情人的情节。这些允许表达巴什情的情境是文化提供的释放压抑之情的空间,抚慰了巴什恋人。
人神婚恋的戏剧表演基于人神与巴什这组隐喻关系,是一种反禁忌的宗教想象。人类世界不断上演的戏剧表演——在年节特懋克、上新房等重大时刻演唱《巴什》、在传统家庭与社会教育中通过代际传承《箐神传说》,举行人神婚恋的仪式实践,以及日常生活的释压情境——模拟了与社会结构“相反”的剧情。巴什们通过声情并茂地演述和身临其境的仪式,进入有别于世俗生活的婚姻秩序与道德的场阈,把铁匠神女、莫丕神女、白腊泡神女、兽神与人间男性想象为自己的一个象征身份,延续恋爱关系,完成象征性的结婚仪式,建立宗教性的夫妻关系。在超越结构关系的“共睦态”(communitas)(33)对communitas有多种翻译,本文采用台湾“中研院”余光弘教授的观点。参见:赵红梅《也谈“communitas”人类学视野下的一种旅游体验》,《思想战线》2008年第4期,第44页。中,巴什们通过理想体验,弥补现实遗憾,获得情感上的满足。在反结构中,尽管个体可能通过仪式受到了剧烈影响,但他们最终返回的社会系统作为一个整体并没有改变;个体可能因为创造性的仪式过程发生一系列的改变,但社会系统的结构在整体上却是恒定的。(34)拉波特等《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关键概念》,鲍雯妍、张亚辉译,华夏出版社2013年第2版,第220页。在基诺族社会中,社会结构通过社会戏剧的不断上演在“禁忌-反禁忌”的循环往复中继续稳固地存续下去。
三 文化再生产:人神婚恋文化的意义探讨
拉德克利夫-布朗认为宗教仪式是社会团结的表现,它的功能表现在,通过对情感的强调来“重塑”社会或社会秩序,而这些情感是一个社会中团结和秩序的依靠。(35)A.R.拉德克利夫-布朗《原始社会结构与功能》,丁国勇译,江西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150页。宗教强调的情感是文化塑造的共同的心理基础,产生于社会生活,也重塑社会生活。与婚姻禁忌相关的、具有反禁忌意义的人神婚恋文化将一种婚姻制度、精神情感与巫术/超自然力联系起来,由婚姻禁忌引发了反禁忌的宗教性仪式,进一步再生产出巫术诞生的地方性逻辑。
(一)嫉妒、死亡与巫术:人神婚恋的产生逻辑
基诺族实行一夫一妻制,但跨越人类世界与灵界的人神婚恋构建了与之相悖的象征意义上的“一夫多妻”形态,由此,普遍存在于人类世界的情绪——嫉妒被用以形容男子的两位“妻子”之间的情感对立。《贝壳歌》里描述了巴什郎惧怕妻子的嫉妒,只得隐瞒巴什女的身份,与她的三种神女化身成婚的情况:
我情不自禁喊出你的名字,把睡在我身旁的咪勒惊扰。她气愤地问我梦中见到了谁?我哪能直说梦见的就是你——我十心爱着的巴什妹!我只能告诉她:“是哞莱(哞莱浦麽指灵界的铁匠神女寨——引者注)的女神来找,看来是德莱咨首(德莱咨首指铁匠神女——引者注)要我把铁匠来当。”(36)沈洽主编《贝壳歌——基诺族血缘婚恋古歌实录及相关人文叙事》,第174页。
神女也同样表现了她的嫉妒。女性不能进入兽神房,不能触碰娱神乐器奇科、布姑,在人神婚恋仪式期间,仪式对象不能与妻子同寝,猎祭仪式时妇女不能上桌吃饭,这也是基诺族社会活动中妇女少有的不能上桌吃饭的情况。“兽神会嫉妒”,这是老人们普遍的解释。
嫉妒是婚恋关系中常见的情感表达。巴什郎在人间获得社会认可的婚姻关系受到死后化身为神女的巴什女的嫉妒和埋怨。嫉妒的目标是在存在或出现一种分离的危险时,保持或者创造一种连接的状态。(37)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嫉妒的制陶女》,刘汉全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68页。神女正是通过“婚恋仪式”创造与巴什郎的连接状态,通过对“情人”的占有和对“情敌”施以禁忌宣泄嫉妒可能引起的消极情感。在很多社会形态中,嫉妒是以巫术(witchcraft)、邪恶之眼(evil eye)或妖术(black magic)等形式表现出来的(38)张慧《羡慕嫉妒恨:一个关于财富观的人类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9页。,如阿赞德人说巫术就是嫉妒,如果某人处于弱势或者有仇恨、嫉妒的情绪就会导致别人指控他使用了巫术(39)埃文斯-普理查德《阿赞德人的巫术、神喻和魔法》,覃俐俐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129-130页。。这里的巫术是一般被我们认为的消极巫术的部分,即出于破坏性目的的巫术行为。但在基诺族的宗教观里,嫉妒引发的巫术并不是破坏性的,而是一种“积极”巫术。神女借以表达嫉妒和占有的象征物——巫术能力和大型猎物——是基诺族社会维系中必不可少的对象。可见,基诺族对嫉妒与巫术关系的理解有其独特性。
巴什婚姻能够成立以及巫术行为能够发生,都基于巴什女死后成为灵这一前提。“人间-死亡/巫师-灵界”模式可以用以理解基诺族人神婚恋文化的深层机理。在基诺族宗教文化中,死亡与巫师都是勾连人间与灵界的介质。死亡是自然发生的,巫师则需要文化主体创造。死亡与巫师通过巴什女产生关联,即死亡这一经历赋予了巴什女巫术能力,巴什女又通过婚恋仪式把巫术能力(猎获大型猎物和成为宗教师)赋予巴什郎。特纳认为巫术体现了特定的社会结构和一套道德价值和规范(40)特纳《作为社会过程之一阶段的占卜》,史宗主编《20世纪西方宗教人类学文选》,金泽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807-809页。,正如在基诺族的宗教世界里,巫术的产生一方面源于社会的需要,另一方面反映了人们突破社会结构,特别是社会禁忌的想象。
(二)修复、稳固与延续:禁忌文化的再生产探讨
不同于其他族群,基诺族对禁忌与巫术关系的解释有其独特性。一方面,基诺族把积极巫术作为禁忌的结果,禁忌不仅不会产生社会恐慌,反而被赋予诗意和新的社会功能。这也是基诺族和谐、乐观的文化特质的体现。另一方面,禁忌与巫术的关系不能简单用因果关系加以解释,而是一种文化再生产的过程。布迪厄(又译作布尔迪约)的文化再生产理论指出,文化通过“再生产”维护社会结构,稳定社会秩序。(41)布尔迪约、帕斯隆《再生产:一种教育系统理论的要点》,邢克超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
文化再生产是一个连续性过程,基诺族禁忌文化的再生产首先表现为族内婚禁忌容易导致抗争、逃走、自杀等不利于人口较少且相对封闭的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在此情境下,人神婚恋的口头传说与仪式构建了虚拟关系,修补了社会失序。现实中的巴什郎通过置身于真实上演的人神婚恋仪式获得反禁忌体验,而现实中的巴什女则亦可通过不断置身于古歌、仪式构筑的圆满情节,允许重叙巴什情的节日、仪式空间排解苦闷。
其次,人神婚恋文化完成了人间到灵界的文化再生产。基诺族认为灵界运行着与人类世界相仿的社会秩序,两个世界通过神话思维产生关联,并借助神话的隐喻相互转换。在灵界,婚姻生活依旧存在,宗教师死后也要去到相应的神女寨与举行过结婚仪式的神女一起生活,正常死亡的人也可到司杰卓密重建婚姻。灵界是现世生活的延续,又是现世生活的突破,现世的婚姻禁忌可以到灵界打破。延后到灵界的婚姻生活作为宗教想象满足了巴什们的夙愿。
第三,人神婚恋文化成为解释信仰万物有灵的狩猎采集社会中宗教师的诞生和猎人捕获大型猎物的原因,由最初的嫉妒而衍生出的一系列文化表征最终被再生产为这类事件的产生机制。可见,文化再生产赋予原本具有消极影响的文化禁忌以积极意义,修复了原本可能被禁忌破坏的社会秩序,稳固了社会结构,进而保障了社会的延续。此外,化为神的巴什女施与人间巴什郎的积极巫术可以被视为对禁忌造成的缺憾的补偿,猎获大型猎物和成为宗教师的巴什郎能够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宗教师通过为他人占卜治病、主持仪式还可以获得一定的收益(肉、米等)。
四 结论
综上所述,1950年代末以前,在基诺族结构性社会中具有强有力的规范性力量的婚姻禁忌与反婚姻禁忌的巴什情的冲突构成了一种社会文化“场景”(socialcultural “field”)(42)特纳《戏剧、场景及隐喻:人类社会的象征性行为》,第4页。,这个场景促使文化主体探寻解决冲突的方法,社会戏剧便是途径之一。社会戏剧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形成打破社会结构的“阈限”(liminality)(43)维克多·特纳《仪式过程:结构与反结构》,黄剑波、柳博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807-809页。阶段,为巴什们提供了申诉、抗议的反结构空间。当阈限结束,婚姻禁忌存在的文脉(context)得以固化,社会结构也得以延续。这一过程蕴涵了基诺族文化的深层逻辑。首先,人神婚恋的主体象征现实世界中受制于婚姻禁忌的“巴什”,人神婚恋文化,特别是仪式的举行恰恰为巴什提供了弥补遗憾的象征场景。其次,人神婚恋文化为社会生活中至关重要又偶然发生的事件作出了地方性解释,即猎物的获取、宗教师的产生是一种人神互惠,互惠得以存在的逻辑基础是人神之间的爱情关系,也即是巴什情。第三,人神婚恋文化实际上成为了男性通过与神女建立亲密关系获得超自然力量,以巩固与维护父系权威的手段。这样独特的文化事项得以存续与基诺族的自然环境、生计方式、宗教信仰直接相关,体现了文化主体从地方性经验出发进行生态适应、文化调试,构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关系的努力。
人神婚恋文化一方面借助宗教力量成为受制于禁忌的弱势一方对抗强势的社会结构的手段;另一方面,通过仪式赋予弱势一方巫术能力以及新的象征身份——宗教师,使禁忌的消极结果转为嵌入社会结构的地方性知识。这套解释机理与行为策略是文化主体化解社会结构中潜在危机的主动性策略。从禁忌这一文化事项再生产出的人神婚恋仪式以及相关的文化事实反而坐实了禁忌的合理性,重塑了潜在的失序状态,同时巧妙地阻止了禁忌可能导致的消极结果的发生。这一切都体现了文化再生产在维系社会结构时的重要作用,也昭示社会文化中的内生动力在调试文化、修复失序时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