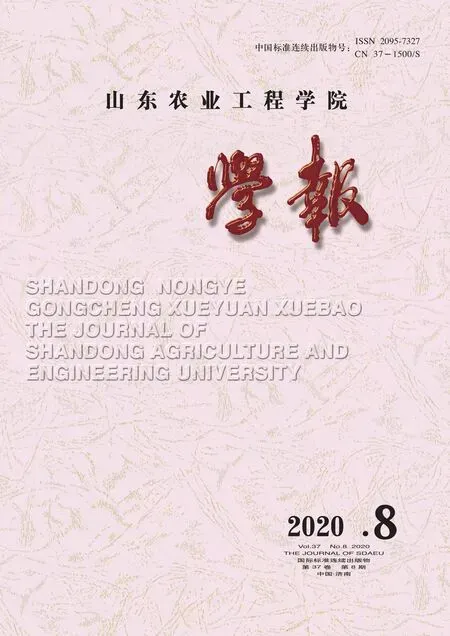论《金瓶梅》的“戏谑”艺术
2020-02-25
(淮南师范学院文学与传播学院,安徽 淮南 232038)
明代“四大奇书”中,《金瓶梅》完全颠覆了《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的累积型创作模式,开启了中国小说史上的第一场“真人秀”表演,它以核磁共振的方式全方位扫描现实生活,再现了明代后期的社会现实,至今虽然毁誉参半,甚至不能完整出版,但在当下的阅读视野中行情看涨。潘知常认为,《金瓶梅》描写的是“裸体的中国”,“裸体的民族”,“是中国文学史的第一次回归生活的本来面目”[1]。
戏谑,“作为现代美学的一个范畴”,原指用诙谐有趣的话开玩笑,与嘲讽、调侃、搞笑亲近,本来与古代小说批评无涉,倒是十分疑似戏曲表演中的“插科打诨”,但“如果戏谑有可能允许被进入美学殿堂的话,那么,我就请它到丑学的祭台上去供奉遥远迷茫的阿芙洛狄武女神。”[2]若以戏谑作为审美范畴,考察《金瓶梅》的文本描写倒也十分妥贴。本文无意于对小说的思想艺术作全方位评判,仅就戏谑艺术的的作用和手法做些琐碎的探讨,求教于各位同人。
一、戏谑的对象
《金瓶梅》洋洋百回,人物800余,根据人物性格刻画的完整和丰富程度以及出场次数的多寡,为下文论述之便,我们暂且把《金瓶梅》的人物分为三类,即主要人物、次要人物和过场人物。
1.对主要人物的嘲讽
《金瓶梅》命名直接关联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几个主要人物,但一号人物还是西门庆。以79回为界,西门庆的人生可以分为两个时段。
生前的西门庆,是王婆眼中的 “钻石王老五”,一个“潘驴邓小闲”的五全人物;而熟悉西门庆的蒋竹山,看法恰恰相反,但更接近实际,说“此人专在县中包揽说事,广放私债,贩卖人口,家中丫头不算,大小五六个老婆,着紧打倘棍儿,稍不中意,就令媒人领出卖了。就是打老婆的班头,坑妇女的领袖。”作者眼中的西门庆:“专一飘风戏月,调占良人妇女,娶到家中,稍不中意,就令媒人卖了。一个月倒在媒人家去二十余遍,人多不敢惹他。”(词话本第2回,人民文学出版社,)今人孟超概括为“包括了地主、官僚、商人、恶霸、市侩、流氓,额外再加上少不了的色鬼欲魔”,[3]
死后的西门庆,水秀才的祭文故意恶搞。有意为男性阳具画像,倒也与活着的西门庆十分般配。
“维灵生前梗直,秉性坚刚;软的不怕,硬的不降。常济人以点水,恒助人以精光。囊箧颇厚,气概轩昂。逢乐而举,遇阴伏降。锦裆队中居住,齐腰库里收藏。有八角而不用挠掴,逢虱虮而骚痒难当。受恩小子,常在胯下随帮。也曾在章台而宿柳,也曾在谢馆而猖狂。正宜撑头活脑,久战熬场,胡为罹一疾不起之殃?见今你便长伸着脚子去了,丢下小子辈,如班鸠跌脚,倚靠何方?难上他烟花之寨,难靠他八字红墙。再不得同席而儇软玉,再不得并马而傍温香。撇的人垂头落脚,闪的人牢温郎当。今特奠兹白浊,次献寸觞。灵其不昧,来格来歆。尚享。”
2.对次要人物的戏弄
西门庆的交际网中,妓女和帮闲是最基本的两类人群,前者有李家妓院丽春院的李桂姐、郑家妓院的郑爱月,后者有西门九友。
《金瓶梅》洋洋洒洒八十万字,主要人物西门庆、潘金莲之外,应伯爵的戏份最多。仅小说回目中,就有八处立题直接涉及应伯爵。西门庆的日常生活中几乎天天可以见到应伯爵的身影,他是西门庆的座上客和开心果,两人关系十分 “融洽”,“熟得狗也不咬”。应伯爵如影随行跟着主子帮嫖、吃酒、解闷。
拥有了金钱和权势的西门庆,女人和帮闲是必不可少的交往对象,前者供其调情纵欲,后者助其消磨业余时光。前者属于西门庆的私有财产,基于家庭地位的不对称,她们在西门庆面前为衣食之欲和钱物之利,只能俯首帖耳,是完全的性奴隶。她们与以应伯爵为代表的那些狼狈为奸、低眉趋利的帮闲人物一起成为作家戏弄调侃的对象。
第六十八回写应伯爵在郑爱月儿家置酒宴饮,席间,他要粉头们吃酒。“爱月儿道:‘你跪着月姨儿,教我打个嘴巴儿,我才吃。”黄四也道:“二爷,你不跪,显的不是趣人。”伯爵“于是奈何不过,真个直撅儿跪在地下……这爱月儿一连打了两个嘴巴,方才吃那杯酒。”他善于装疯卖傻、嬉皮笑脸,打情骂俏,丑态百出,可谓无耻之极。对他来说,这些常人难以忍受的屈辱竟然成了他生活中的不可缺少的部分,只要这种“闲情逸趣”不触及自己的切身利益,能博得西门庆一笑,即使丧失人格,他也会心甘情愿。目的就是满足衣食之欲,钱物之利。帮闲需要智慧,需要口才,更要有牺牲精神,那就是面子、脸皮,说得文乎一点:尊严!
他给被西门庆赶走的乐工李铭传授秘诀说:“他有钱的性儿,随他说几句罢了。常言:嗔拳不打笑面。如今时年,尚个奉承的。拿着大本钱做买卖,还带三分和气。你若撑硬船儿,谁理你!全要随机应变,似水儿活,才得转出钱来。你若撞东墙,别人吃饭饱了,你还忍饿。”[4]这是他自己的经验总结和生存之道,甘做帮闲的应伯爵早已做好了心理准备。
《金瓶梅》是市井小说,其中的人物以清和县城为中心。决定其人物从厅局级的州府官员,下至各色人等。在小说的人物图谱中,以西门庆为中心主要刻画了两类不同的形象,一是位高权重的大吏,如亲家杨提督、太师蔡京、状元、御史、巡按、提刑,他们贪污受贿,巧卖禄奉,为西门庆带来滚滚财源,成为西门庆的政治靠山和经济后盾,作品用了很小的篇目写他们,不是作者主要的关注对象。而在西门庆的日常生活中,接触更多的是普通的饮食男女和市井百姓。
好色的西门庆“一个月倒在媒人家去二十余遍”,媒婆自然成了西门庆“飘风戏月”的交接对象。职业媒婆薛嫂子就是带着七言八句的出场诗登台亮相的。
“我做媒人实自能,全凭两腿走殷勤。唇枪惯把鳏男配,舌剑能调烈女心。利市花常头上带,喜筵饼锭袖中撑。只有一件不堪处,半是成人半败人。”(第7回)
媒婆和庸医自古以来就是民间文学和宋元话本取消调侃的对象,《金瓶梅》的作者继承了传统的题材,在小说中依然作为插科打诨的最佳选择。作者借鉴戏曲上场亮相自我介绍的方式,让那些边缘搞笑人物现身说法。
小说第六十一回,写赵太医给李瓶儿看病。赵太医居然这样介绍自己:
“我做太医姓赵,门前常有人叫。只会卖杖摇铃,那有真材实料。行医不按良方,看脉全凭嘴调。撮药治病无能,下手取积儿妙。头疼须用绳箍,害眼全凭艾醮。心疼定敢刀剜,耳聋宜将针套,得钱一味胡医,图利不图见效。寻我的少吉多凶,到人家有哭无笑。”(第61回)
医生不比媒婆,那是一种救死扶伤的职业,需要的是技术和经验,人命关天,丝毫马虎不得。即使岐黄不济,医术有限,通常也不至于自毁声誉,砸了生计的饭碗。而赵太医竟然说找他看病就“少吉多凶”、“有哭无笑”。这不是自己炒自己的鱿鱼吗?他开了一味药,连八十一岁的何老人都不以为然,倒是与其 “赵捣鬼”的外号相得益彰了。读到此处,人们自然想起《窦娥冤》的赛卢医,他那“行医有斟酌,下药依《本草》,死的医不活,活的医死了。”的自我表白就有了异曲同工之妙了。赵太医的确很像《窦娥冤》中赛卢医的复制、重生。
3.过场人物的插科打诨
插科打诨,是中国戏曲普遍使用,制造滑稽效果的一种表现手法。“科”指滑稽动作;“诨”是指滑稽语言。插科打诨在戏曲中的作用是制造滑稽,逗乐观众,成为喜剧性的穿插;插科打诨也发挥着一些戏剧功能,是戏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具有独特的艺术特色和美学旨趣。从参军戏到元杂剧皆有插科打诨的诙谐调侃和笑料打趣。李渔《闲情偶寄·词曲部》专列“科诨第五”章予以讨论,认为插科打诨“乃看戏之人参汤也,养精益神,使人不倦”[5]。
作为一种古老的艺术样式,比起小说来,戏曲是地地道道的民间娱乐方式。要求在限定的时间和空间演绎人物的悲欢离合,出于对观众和读者的关切,减少听戏的瞌睡和阅读的疲劳,剧作家们送上一碗碗插科打诨的“人参汤”。《金瓶梅》的作者精心借鉴俗文学的表现手法和宋元杂剧插科打诨的养料,在小说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插科打诨风格。
所谓“过场人物”,可以有姓但无名,其出场多昙花一现,一次露脸便完成使命,自行告退。这些人物出场时,作家甚至连完整的姓名和字号都吝于施舍,只省略为一个代号。接生婆蔡老娘、牛皮街陶扒灰、丫环玉簪儿即属此类。
西门庆家庭成员中女性众多,虽然主人开着药铺,但似乎不通医术,并不能保障家庭成员的健康,卓二姐、吴月娥、李瓶儿一向身体不好,平时需要经常看医生,临清有名的医生在李瓶儿病危期间仿佛都集中到了西门大宅。与经常路面的医生这类次要人物相比,接生婆的出现倒是屈指可数,原因在于西门庆的女人们肚子不争气。西门庆生前唯一的一次接生过程中,就出现搞笑的接生婆蔡老娘形象。
小说第三十回,李瓶儿生孩子,家里请来接生的蔡老娘。这位蔡老娘居然如此介绍自己的接生技术:
“横生就用刀割,难产须将拳揣。不管脐带包衣,着忙用手撕坏。活时来洗三朝,死了走的偏快。”
这是接生吗?与其说是接生,简直是催命!
作品第三十三回写西门庆的伙计韩道国妻王氏与小叔韩二偷情,被好事者游街示众的描写:须臾,围了一门首人,跟到牛皮街厢铺里,就哄动了那一条街巷。这一个来问,那一个来瞧,内中一老者见男妇二人拴做一处,便问左右看的人:“此是为什么事的?”旁边有多口的道:“你老人家不知,此是小叔奸嫂子的。”那老都点了点头儿说道:“可伤,原来小叔儿要嫂子的,到官,叔嫂通奸,两个都是绞罪。”那旁边多口的,认的他有名叫做陶扒灰,一连娶三个媳妇,都吃他扒了,因此插口说道:“你老人家深通条律,相这小叔养嫂子的便是绞罪,若是公公养媳妇的却论什么罪?”那老者见不是话,低着头一声儿没言语走了。看到这段描写,令人油然想起《红楼梦》第七回借贾府老门人焦大醉后詈骂的情景。比起陶扒灰的赧然知耻,宁国府贾珍之流更觉道貌岸然。
小说第九十一回,在李衙内、孟玉楼之间安排一个吃醋使性的丫环玉簪儿。这个丫环用这样的口气对她的主子说话!
先是命令男主人:“老花子,你黑夜做夜作,使乏了也怎的?大白日打睡瞌睡,起来吃茶! ”
再是抱怨女主人:“你未来时,我和俺爹同床共枕,那一日不睡到斋时才起来。和我两个如糖拌蜜,如蜜搅酥油一般打热。房中事,那些儿不打我手里过。自从你来了,把我蜜罐儿也打碎了。”
这是低眉顺眼的丫环做派吗,即使李衙内、孟玉楼再如何高风亮节,这样的丫环也很难置身李府。
二、戏谑的手段
1.讲笑话
李家妓院李桂姐答应西门庆包月后又私自接客王三官,西门庆大闹丽春院,关系紧张。应伯爵牵线搭桥,从中斡旋。为疏解尴尬气氛,应伯爵开始表演其拿手绝活。
伯爵道:“你过来,我说个笑话儿你听:一个螃蟹与田鸡结为兄弟,赌跳过水沟儿去便是大哥。田鸡几跳,跳过去了。螃蟹方欲跳,撞遇两个女子来汲水,用草绳儿把他拴住,打了水带回家去。临行忘记了,不将去。田鸡见他不来,过来看他,说道:‘你怎的就不过去了?’螃蟹说:‘我过的去,倒不吃两个小淫妇捩的恁样了!’”桂姐两个听了,一齐赶着打,把西门庆笑的要不的。(第21回)
小说第五十四回,应伯爵、常峙节在郊外的内相花园宴请西门庆,作家一连让应伯爵说了四个笑话,“江心贼”、“生矾”、“铜钱牛”和“品屁”,是应伯爵说笑话最多的一次。“江心贼”与“生矾”暗示西门庆的富贵有劫色劫财的强盗贼人之嫌;“生矾”旨在调笑妓女金钏儿。经常峙节提醒,西门庆领悟后,应伯爵自觉,马上罚酒两杯,为弥补过失,照顾主子的尊严,赶紧说了第四个笑话“品屁”。这个笑话显然是为帮闲画像,所以常峙节奉承道,“你自得罪哥哥,怎的把我的本色页说出来。”
2.漫画式扫描
圣人不讳言“饮食男女”,何况芸芸众生。一百回的《金瓶梅》中,写到应伯爵的有六十多回,而其中写到应伯爵跟随西门庆混吃溜喝的就达五十回之多。可以说,在应伯爵与西门庆的交往中,能够贯穿始终的就是一个“吃”字。
小说第一回应伯爵第二次出场就写到了吃早饭的问题。西门庆热结十兄弟不久,应伯爵借口传播武松打虎事大清早便来西门庆家蹭饭了。
西门庆故意问道:“你吃了饭不曾?”伯爵不好说不曾吃,因说道:“哥,你试猜。”西门庆道:“你敢是吃了?”伯爵掩口道:“这等猜不着。”西门庆笑道:“怪狗才,不吃便说不曾吃,有这等张致的!”一面叫小厮:“看饭来,咱与二叔吃。”伯爵笑道:“不然咱也吃了来了,咱听得一件稀罕的事儿,来与哥说,要同哥去瞧瞧。”(第一回)
两人早餐,饮食的内容和过程一般比较简单,何况又不是蔡状元那样的贵客,小说就此省略。至于集体宴饮,则需多费笔墨了。小说第十二回写西门十友在丽春院聚餐,那吃相真如饕餮盛宴,作家一夸张性的漫画手法为读者精彩奉献:
“人人动嘴,个个低头。遮天映日,犹如蝗蚋一齐来;挤眼掇肩,好似饿牢才打出。这个抢风膀臂,如经年未见酒和肴;那个连三筷子,成岁不筵与席。一个汗流满面,却似与鸡骨秃有冤仇;一个油抹唇边,把猪毛皮连唾咽。吃片时,杯盘狼藉;啖顷刻,箸子纵横。这个称为食王元帅,那个号作净盘将军。酒壶番晒又重斟,盘馔已无还去探。
当下众人吃得个净光王佛。西门庆与桂姐吃不上两锺酒,拣了些菜蔬,又被这伙人吃去了。那日把席上椅子坐折了两张,前边跟马的小厮,不得上来掉嘴吃,把门前供养的土地翻倒来,便剌了一泡屯谷都的热屎。临出门来,孙寡嘴把李家明间内供养的镀金铜佛,塞在裤腰里;应伯爵推斗桂姐亲嘴,把头上金琢针儿戏了;谢希大把西门庆川扇儿藏了;祝实念走到桂卿房里照面,溜了他一面水银镜子。常峙节借的西门庆一钱银子,竞是写在嫖账上了。”(第12回)
3.谐音提示
崇祯本第一回《西门庆热结十弟兄 武二郎冷遇亲哥嫂》就描写一群人格卑微并非大奸大恶的市井人物。小说仿照《三国演义》的桃园结义写到了西门庆的九个结义兄弟,他们的姓名,结合张竹波的评注[6],使人自然而生谐音联想:
应伯爵:硬白嚼,字光侯,光喉也;不吃白不吃,吃了也白吃。
云理守:云里守;字非去,飞去也。
常峙节:常时借,有借无还。
祝实念:逐日粘,抑或住十年。
孙天化:天话;字伯修,不羞也。
吴典恩:无点恩。
卜志道:不知道。
白赉光:白借光,
谢希大:携带也。
……
古代中国人格外看重名、字、号,姓氏属先天血缘决定,除偶尔皇帝赏赐,无法更改。起名一般由父亲或祖父完成,字由德高望重的前辈赏赐,号则多为主人自己完成。名和字多在出生后不久形成,号多在中年后自我进行,而绰号更多地带有社会的色彩。中国小说创作中人物绰号的命名与《三国演义》同步完成,多以人物的容貌关联,如美髯公关羽。《水浒传》一百单八将都有一个绰号,这些绰号的意义正如伊恩·P·瓦特所说,“它所应象征的是,人物被看成了一个特殊的人,而不是一个类型。”[7]赋予人物一个绰号,使之成为这个人的象征,凸显其主要的性格特点,成为小说作者塑造陪衬人物的重要手段,金陵笑笑生借鉴施耐庵、罗贯中的做法,对西门庆的十兄弟逐个贴上标签,所不同的是,《水浒传》的人物绰号多以武功的专擅、器械的使用为考察标准,《金瓶梅》的人物绰号则与人物性格的刻画直接关联。
4.直接戏谑
古代小说大多运用全知视角描写人物,并经常从道德层面对人物进行评判,以表明作家的情感态度。《金瓶梅》的评语,又多从戏谑的角度入手,以调侃语言出之。
小说伊始,王婆第一次出场时作者就直接出面进行调侃:
“开言欺陆贾,出口胜隋何。只凭说六国唇枪,全仗话三齐舌剑。只鸾孤凤,霎时间交仗成双;寡妇鳏男,一席话搬说摆对。解使三里门内女,遮莫九皈殿中仙。玉皇殿上侍香金童,把臂拖来;王母宫中传言玉女,拦腰抱住。略施奸计,使阿罗汉抱住比丘尼;才用机关,交李天王搂定鬼子母。甜言说诱,男如封涉也生心;软语调合,女似麻姑须乱性。藏头露尾,撺掇淑女害相思;送暖偷寒,调弄嫦娥偷汉子。”(第2回)
西门庆死后不久,李娇儿先是浑水摸鱼,盗取几百两元宝,然后迫不及待的归来丽春院,其薄义寡情连作家都看不下去了,直接出面嘲讽:
“看官听说,院中唱的,以卖俏为活计,将脂粉作生涯;早辰张风流,晚夕李浪子;前门进老子,后门接儿子;弃旧怜新,见钱眼开,自然之理。饶君千般贴恋,万种牢笼,还锁不住他心猿意马。不是活时偷食抹嘴,就是死后嚷闹离门。不拘几时,还吃旧锅粥去了。(第80回)
妓院出身的李娇儿无情,一向蒙主子惠顾的帮闲更是无义。西门庆尸骨未寒,应伯爵立马改换门庭投到张二官麾下,继续他的帮闲生涯,作者给予无情嘲讽。
“看官听说,但凡世上帮闲子弟,极是势利小人。”当初西门庆待应伯爵如胶似漆,赛过同胞弟兄,那一日不吃他的,穿他的,受用他的。身死未几,骨肉尚热,便做出许多不义之事。正是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第80回)
5.恶搞
俗话说“谑而不虐”,意即开玩笑不宜过分,不令人难堪。如同“怨而不怒”抒情传统一样,强调节制,含蓄。戏谑也应该 “戒淫亵”“忌俗恶”“贵自然”,做到“雅俗同欢,智愚共赏”[8]。可惜的是,《金瓶梅》的戏谑运用,偶尔流于油滑和恶搞。小说第五十二回和第五十四回里就有两处对妓女的恶谑性描写。
应伯爵发现西门庆与李桂姐离席很久,就悄悄跟踪寻找,终于发现二人在藏春坞里苟合。常人唯恐避之不及,这个下流无耻的家伙不仅没有回避,先是在门缝外“只顾听觑”,然后“猛然大叫一声,推开门进来”,要“抽个头儿”,硬是按着李桂姐“亲个嘴”,在妓女身上揩完油方才罢手。(第52回)
“伯爵一面叫摆上添换来,转眼却不见了韩金钏儿。伯爵四下看时,只见他走到山子那边蔷薇架儿底下,正打沙窝儿溺尿。伯爵看见了,连忙折了一枝花枝儿,轻轻走去,蹲在他后面,伸手去挑弄他的花心。韩金钏儿吃了一惊,尿也不曾溺完就立起身来,连裤腰都湿了。不防常峙节从背后又影来,猛力把伯爵一推,扑的向前倒了一交,险些儿不曾溅了一脸子的尿。伯爵爬起来,笑骂着赶了打,西门庆立在那边松阴下看了,笑的要不的。”(第54回)
三、戏谑是小说艺术的审美需求
苏涵说,“在中国小说美学中,趣味追求是一种普遍的现象,一种同样富于文化意味和审美意味的现象,我们甚至可以把它视作中国小说审美理想的先导。今天的古代小说批评,很少涉及小说趣味问题,实在是学术上的一个疏漏;今天的小说创作,回避小说趣味,也实在是文学与小说的遗憾。”[9]
“趣味”是小说与生俱来的审美诉求,宋元以降,伴随城市的繁荣和市民阶层的扩大,审美趣味的易变成为历史的必然。诚如潘知常所言,“伴随着明中叶审美理想、审美趣味的变化,对于艺术美的要求,也就从‘意境’转向了‘趣味’。”“明中叶,最先以趣味作为审美范畴的,是李贽。”[10]
李贽在《水浒传》第五十三回的评语中发出了“天下文章当以趣为第一”的审美呼唤,在《西游记评》中更有47处 论“趣”之语,深刻影响小说的创作和批评。比起《西游记》作者对佛道人世的调侃,兰陵笑笑生小说对社会、人性的批判力度更深,手法更丰富。
明代中叶以后,整个社会物欲、人欲横流,道德滑坡。“既然现实是如此荒唐滑稽,那么作为艺术形式的戏谑就不可避免地要在文艺作品表现出来,这既是艺术家的必然选择,也是现实的必然选择。”[11]这或许就是《金瓶梅》的主要创作动因和审美追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