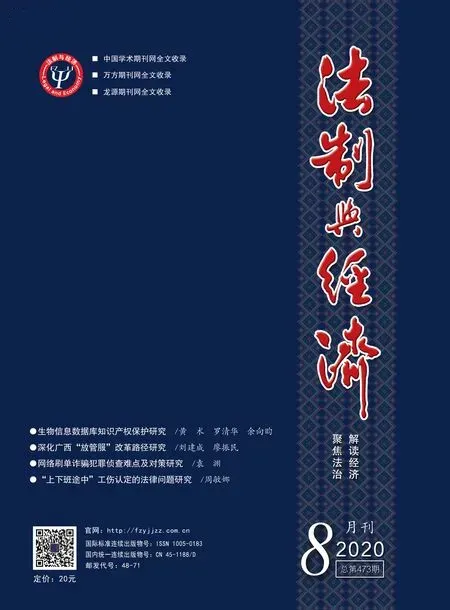普通背信罪构成要件研究
2020-02-25林文怡
林文怡
(华东理工大学法学院,上海200237)
一、背信罪概述
(一)背信罪的概念
普通背信罪(以下简称“背信罪”),是指为他人处理事务的人,为谋求自己或者第三者的利益或以损害委托人的利益为目的,而违背其任务,致使委托人的财产受到损失的行为。[1]德日的刑法中早已规定了背信罪,我国刑法虽尚未将其作为一个罪名进行规制,但已经存在了数个背信罪的“影子”,我们称之为特殊背信罪。特殊背信罪是背信罪构成要件的特殊化,一些常见的特殊背信罪如《刑法》第185条的金融机构工作人员挪用资金罪、第186条的金融机构工作人员违法发放贷款罪、第270条的职务侵占罪、《刑法修正案(六)》增加的第169条之一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刑法修正案(七)》增加的第180条第4款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等。
(二)设立背信罪的定义
不管是“老鼠仓事件”之后颁布的《刑法修正案(六)》还是《刑法修正案(七)》所增加的金融机构从业人员利用内幕信息以外的其他未公开的信息交易行为,所作的都是在填补我国普通背信罪缺位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而新增的这些罪行是否能够真正解决已经存在的问题还有待商榷,例如有些学者认为,《刑法修正案(七)》第2条第2款设立于内幕交易条款之下的条文中只是解决了狭义的“老鼠仓”,而广义的“老鼠仓”(如相关从业人员违背受托人义务,用自己管理的基金将自己在先买入的股票价格拉高,从而自己利用股票的股价差获利)依旧无法得到规制。[2]另外,相比较于国有公司、企业而言,刑法对于民营企业的保护力度还有待加强,针对后者工作人员的失职和背信损害公司利益的规制,在刑法中还不能找出相应的解决方法,而且依照罪行法定的原则,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2018年11月,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民营经济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被充分肯定,随后最高法和最高检提出“多举措保护民企合法权益”“凡属于违法侵害民营企业和企业家的合法权益的,法院应当坚决依法予以制裁”,背信罪能够将民营公司、企业纳入其保护的主体,有力地给予其与国有公司、企业同等力度的保护。
二、背信罪的基本构造
(一)主体
背信罪的主体为为他人处理事务的人。按照“为他人处理事务”权利的来源不同,可以将主体分为以下两种情况:其一,委托关系或者可以视为委托关系而产生的“为他人处理事务”,委托人可以是国家、法人、非法人组织以及自然人,受托人可以是单位或者个人。将这类的民事纠纷纳入刑法规制的范畴是因为平等主体之间的委托所涉及的财产利益越来越大、社会金融服务也呈现多样化和复杂化,因此,很多行为委托人无法亲力亲为,“委托”成为现代社会非常普遍的一种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委托人如果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是能够亲力亲为,而不需要委托他人的,[3]这也是信任关系产生的非法律因素——自身能力的限制和对他人的信任。所以“委托”是将自身手臂的延长,是他人头脑的借用,因此其中的委托人具有了一定的独立性。通过委托关系,受托人获得一定程度的决定权或者仅仅是执行权,而受托人背离与委托人的约定致使委托人遭受财产上的损失的,为背信罪的主体。其二,是基于劳动关系而产生的“为他人处理事务”,这类关系的双方为用人单位和劳动者。而不将雇佣关系和劳务关系一并列举在这一类中是因为这两类关系属于民法调整,双方属于平等主体,因此可以将其之间的“事务”视为由委托关系而产生,即上面所说的“可以视为委托关系”。在用人单位这个可大可小的组织体中,不少人的职责就是处理涉及用人单位较大经济利益的事务,若该劳动者违背用人单位对其的信任,致使用人单位遭受重大的财产上的损失,该劳动者可成为背信罪的主体。
“为他人处理事务”中的“事务”既包括合法的财产性事务,也包括合法的非财产性事务。前者如受托拍卖委托人的珠宝,受托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卖给自己的好友,致使受托人遭受财产利益的损害;后者如律师受托处理委托人的非财产性事务时,出于为自己或者第三人牟利的方式,致使委托人财产的损失。“事务”的性质不是区分是否构成背信罪的事由之一,只要行为人故意使委托人的财产利益遭受损害即可。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医生为患者开具不必要的、昂贵的药和检查是否属于背信罪?常常被学者用来讨论,认为“事务”只能是财产性事务的学者自然认为其不是背信罪,[4]而认为“事务”既可以包括财产性和非财产性事务的学者认为其属于背信罪。[5]笔者认为,上述行为不能被视为背信罪,原因并不是对于“事务”的认定,虽然在民法原理上,医患关系被认为是一种特殊的委托合同关系,但这种“特殊”使得其不适合刑法进行规制。处方药的获得和身体检查往往需要医生的处方,从这方面看,患者寻求医生的帮助是出于资格问题,而不是自己能力的问题;并且,医生并没有帮助患者处理一定的事务,并且其开具的药物和检查时有义务告知患者相应的目的,最后接受检查和药物服用与否的决定权在患者,实施主体为患者,因此不可视为严格的委托关系,不能被视为背信罪处理。
(二)客体
背信罪的客体是财产权。在我国对于背信罪客体的分歧是到底是单一主体,即财产权,还是复杂客体,即财产权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或者财产权和市场经济的信用制度。产生这一分歧的原因之一是现有的特殊背信罪分散在刑法的不同章节中,如《刑法》第169条之一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规定在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第270条侵占罪规定在第五章侵犯财产罪。明确犯罪客体不但是确定背信罪处于刑法体系的哪个位置,还能以一定程度上回应背信罪有违刑法的谦抑性质疑。
财产权是背信罪的客体是不存在争议的。背信罪以致使委托人的财产遭受损失作为其既遂的条件,因此侵犯他人财产权是背信罪的本质特征。德日两国虽然没有客体一说,但从对背信罪在刑法体系中的安排可以看出,背信罪被归为财产犯罪:《德国刑法》将其归在第二十二章“诈骗与背信罪”,《日本刑法》把其归在第三十九章“侵占与背信罪”。
笔者以为市场经济的信用制度不是背信罪的客体,原因有以下两点:首先,所谓的信用制度在我国本身就是十分抽象的,而刑法需要有具体的表现形式。[6]即便信用制度已经渐渐地从一个抽象的概念走向具体的表现形式,但该制度在我国依旧是不完备的,因此将其作为客体,会增加背信罪规制的社会行为的广度以及不确定性;其次,信用制度也不是刑法真正需要去独立保护的客体,并且如今对于“信任关系”依旧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也正是因为信任关系本身就具有较强的主观性、广泛性和民事性,如果刑法在行为侵犯信用制度的程度就进行规制的话,未免过早地介入到市场经济活动的背信行为之中,有违刑法的谦抑性。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也不适合视为背信罪的客体。其原因是违背扰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并不是所有背信罪侵犯的客体。但在市场经济中的重要性前文已经进行论述,其对社会市场经济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因此民营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背信行为不但会给企业本身造成较大的经济损失,还会对市场经济秩序造成破坏。因此在接下来设计法条的时候不但需要参考财产类犯罪的条文设计、量刑幅度等,还需要从侵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类犯罪出发思考。
(三)主观方面
背信罪的主观方面应当是故意,即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他人财产权益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危害结果发生。过失不构成犯罪。
在这一方面还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是否只有行为人具备特定的目的才能成立本罪?德国刑法规定,行为人出于主观故意和损害结果即可;日本刑法除了故意导致的损害结果外,还严格规定了行为人的犯罪目的,即具有加害于被害人和图利的目的。
在我国,有些学者认为,犯罪目的是一种主观的心理状态,在实践中难以去判断,行为人故意的背信行为不会是无缘无故的,必然存在一定非法目的,所以规定目的没有意义,反而会增加举证难度,不利于对委托人的保护。[7]我们确实也能发现只有较少的财产类犯罪规定了犯罪目的,绝大部分的财产犯罪关注的是犯罪行为,在这种情况下笔者依旧坚持背信罪应当基于特定目的的原因是,背信罪中的委托行为通常具有一定的专业性,受托人的特定行为不能简单地认为是背信行为,可能存在更长期的营利目的。因此对于认为行为人的背信犯罪一定是出于特定非法目的的观点,过于绝对。日本作为一个规定背信罪为目的犯的国家,正如其国内的有力说认为,即便是出于故意给他人造成了损害,也有可能是出于后续为委托人牟利的目的。因此不能绝对地认为行为本身就带有非法目的。
背信罪应当规定为目的犯除了有上述的一部分原因外,还出于设立背信罪所要保护的法益有向民法调整的社会关系干预的情况,并且增设新的罪名带来的缺乏实践经验,因此为了体现刑法的谦抑性和背信行为需要刑法规制的必要性,将背信罪的目的严格、明确地规定为加害和图利,更有利于司法实践的开展,和对于犯罪嫌疑人的保障。
(四)客观方面
背信罪的客观方面是为他人处理事务的人背信损害了委托人的财产利益的行为,并且造成委托人财产损失的结果。
我国刑法通过“违背忠实义务”和“违背受托义务”作为对“背信”的解释采取严格限制,因此一些典型的背信行为并没有被包含进去,例如自己与公司进行交易行为等。笔者认为,违背信任应当是背信罪的本质,但落实到刑法的规制,需要有具体的表现形式,权限的滥用就是该罪表现形式,因为“权限”是一个可以通过举证证明,除了权限滥用之外还存在其他的表现形式,只要能够证明双方形成的具体的法律关系反映了信任关系即可。
三、结语
普通背信罪的设立是时代发展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因此为了使普通背信罪能够真正地入罪,明确背信罪的四要件构造十分必要,也是划定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