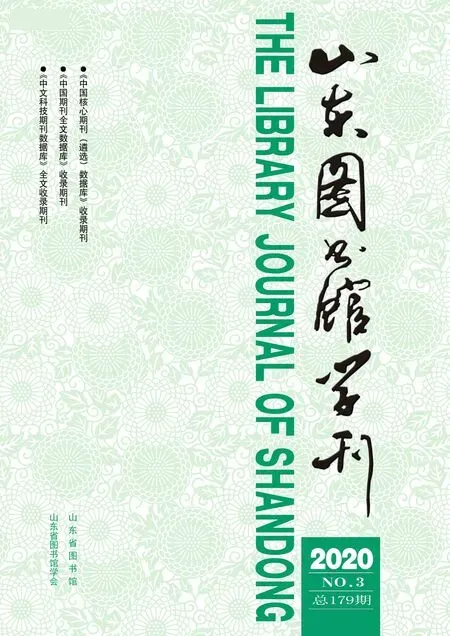清初同朋作品集编辑与出版初探*
——以《檀几丛书》《昭代丛书》等为例
2020-02-24凤轶群
刘 瑞 凤轶群
(陆军工程大学基础部,江苏南京 210023)
各类当代作品选本大量涌现是清初顺康时期文坛的一个显著特点。这些选本在许多方面都体现出极大的相似性:从编创人员的关系来看,编纂人与创作者之间、创作者与创作者之间都存在着密切的交游,共处于一个友朋网络当中,随着编纂活动的展开,这个网络也不断趋于扩大;从成书过程来看,采用独特的开放式征稿方式,随到随刻,随刻随传,过程漫长。此外,征稿、采风之际的请托周转,编纂过程中的磋商共事和刻书费用的共同筹措等,都让这些选本体现出鲜明的“同朋”性质。《檀几丛书》《昭代丛书》是清代康熙年间江南知名文士、刻书家张潮、王晫编纂的两部专门汇辑时人小品杂著的丛书,也是清初同朋作品集的典型代表。这两部丛书,集中体现了清初当代作品集在地域、创作群体、编纂及流行方式等各个方面的特点,特别是以扬州为中心、与各类文士息息相关的交游网络。联络友声匡赞风雅的选文方式,使得这些选本具有了凸显一代人经历与价值观念的代表意义,也提供了一条从社会史特别是书籍史的角度考察清初文士社会生活状况和精神状态的有效线索。
1 非商业化的编刻旨趣
关于清初选本的编撰动机,谢正光先生有过相关论述:“有的标明为示人以作诗的方法;有的为保存平生交游的作品;有的想‘以诗传人’,或‘以人存诗’;有的欲藉选诗来标榜某种诗歌理论;有的则想藉以标榜个人;有的甚至是仅为谋利而已。”[1]和商业出版的唯利是图不同,以《檀几丛书》《昭代丛书》等为代表的同朋作品集,其编刻者常常是在明知无利可图的情况下,为着友情、道义或者对著书立说的热爱而投身其中。细分之,刻书者的意图或动机大致不外乎以下几种。
其一是求不朽。张潮友人吴思祖曾致信张潮:“弟以衰老迂夫,漫涉骚坛艰境……且思此举本欲图不朽之名,倘贪一时微饵,杂不类之人,收不经之句,遗臭将来,何苦以数十年风窗辛力,一旦置之锱铢尺寸之间。”[2]其选书初衷、择稿标准,无不为求令名于世。这种心态在文人刻书中有着极其广泛的代表性。
其二是求友声。明亡清兴,山河易主,丧家辱国颠簸流离的悲愤、骨肉分离故人星散的凄凉,不管是在矢志守节的遗老还是随波浮沉的新民身上,都纠结成复杂的时代情绪,怀旧,遂成为清初许多作品和选本的鲜明主题。冯舒《怀旧集》、陈衍《箧衍集》、王士祯《感旧集》等一批选本虽然在情感基调上有所不同,但都意在缅怀故友[3]、永志不忘。而对于那些辗转各地采风的选家来说,在人文俱胜之通都大衢的长期游历,正是联络友声、匡赞风雅的社交,得到沿途众多新交故知的襄助、参与是其编刻活动得以顺利进行的重要保障。这种鲜明的友声特征,也是许多清初选本被四库馆臣斥为明末标榜声气之积习的重要原因。
其三是阐幽微。张潮在《昭代丛书》丙集例言中说:“穷愁著书,乃其人一生精神学问所存,原欲流传于世,然未及梓行,势必终归淹没,故仆前后诸选,于友人未刻抄本尤所萦怀。”这是为道义而刻书。实际上,作为一名仕途失意、又无鸿篇大文足以立德立言的下层文士来说,张潮之所以在扬州和江南宇内具有一定声望,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得益于他对文人窘境的深刻同情和阐幽发微的古道热肠。
除此以外,揄扬一地人文的本土意识也促成了清初大批地域文学选本或其他地域性作品的编纂、刻行。安徽同乡程元愈曾致信张潮:“夏秋间,留金陵数月……因约有今文之选,拟为安徽诸属稍张一军。征启奉览,望先生勿吝珠玉,并祈传布吾乡诸同人。”[4]张潮资助和参与的众多选本中,就有不少是出于这种浓烈的本土意识和同乡之谊。
正是出于彰显友朋间“相好之雅”之目的,编纂者往往会放宽选文标准,对于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友朋之作,也予以保留,勉力梓行,这也导致一部分选本良莠不齐,失之芜杂。
2 “朋友圈”式征选组稿
清初同朋作品集的选文主要有两个来源:一为平日获赠,一为广泛征求。
其一,平日获赠。朋友交际圈是清初士人作品流通的重要渠道,也是以文会友、以书传人的重要途径。张潮曾多次随书札将自己和父祖的作品寄给友人:
承索先君各种,今补寄上……承索拙著种种,内所云《聊复集》半皆少年游戏之作,久不刷印,今补奉《昭代丛书》《下酒物》并《三字经》《闺训》,其余如《花影词》则尚未授梓,如《逸民四史》《弈乘》《禽史》《禅世说》《仙世说》尚未成书,惟《李杜牌》已刻,容后续寄……[5]
康熙三十三年(1694)初夏,张潮与王晫初会于西湖,两人都热心于编书刻书,揄扬风雅。王晫返家后将平日所辑时人小品三十七种寄给张潮。关于这些作品的来历,王晫在《檀几丛书》初集序言中交代:“予简弃人事,屏居北郭,独四方贤士大夫不相遐遗,率以文稿持赠,累书若城……曩既汇其文之隽永者刊《文津》一书问世,并取经世鸿篇辑成目录,已又择其一卷之中可以自为一书者,随手抄写,阅有年所,凡得若干种,以其丛积无所附丽,命曰《檀几丛书》。”可知丛书所收作品,大多来自平时友朋相赠。张潮在收到王晫的丛书远赐后,复将先祖张正茂、先君张习孔、家兄张沄和己作数种增入,又加上此间自友人处征得数种,遂有《檀几丛书》初集五十种之数。
其二,广泛征求。这是丛书和清初其他选本最具特色同时也是最行之有效的一种组稿方式。《四库全书总目》在评价丛书作者陈鼎《留溪外传》时说:“……其事迹由于征送,观卷首《征事启》末附载二行云:‘凡有事实,可寄至江宁承恩寺前刻匠蔡丹敬家,或扬州新盛街岱宝楼书坊转付’云云,则仍然征选诗文标榜声气之风,未可据为实录”[6]这种颇令四库馆臣反感的征选之风,正是清初最为盛行的编辑方式。李渔在其《尺牍新征》卷首《征尺牍启》中写道:“今天下之为诗赋古文辞者,既已家灵蛇而户鸣凤矣,故自京都以至远所溪谷,无不有集,无不有汇征之集”[7]李渔所说“无不有汇征之集”,正是注意到这些选集所采用的编辑方式不再是单一的“汇”,而是要求编创双方尤其是创作者们主动、自觉参与的“征”。其实不止传统的“诗赋古文辞”,这种高调、广泛的征求方式在小说、传记、尺牍、小品等各类文体的地域和全国性选本中无不效验。在具体操作上,往往是发布征稿启事、遍告同人、以书征书等多种方法兼举并用。
正式的征稿启事一般是发布在选本的卷首,如陈鼎《留溪外传》、钱肃润《文瀫初编》、李渔《尺牍新声》《四六新声》、周亮工《尺牍新钞三选结邻集》、陶煊张灿《国朝诗的》等清初时文选集卷首均有征启发布,这类征启是和选本本身的宣传效应结合,为嗣后诸集大开稿源。选本未出的征启,则往往需要借助其他文本行世,如张潮《征选外史启》就收在他的《心斋聊复集》中[8],也有单独刻印的,如张潮征求悼念亡姬诗之《征诗启》[9]、杨自牧《潜籁轩征诗行卷》[10]、汪士鈜《新都风雅》征诗启[11]、程元愈、戴名世选刻今文《征启》[12]便随书信附寄友人或托人周转。
除了发布征启,选家还会在同人中广而告之直接约稿。张潮在康熙三十三年(1694)仲夏收到王晫的三十七种书目后,即着手在交游圈中为《檀几丛书》征稿。第一个收到稿约的是名士冒襄之子冒丹书(青若):“湖上王丹麓欲选刻时人小品杂著如眉公秘笈之类,名曰《檀几丛书》,属弟广为征购。忆尊公先生有《岕茶汇钞》《兰言》诸刻,最为精妙,向年曾蒙惠读迄,今日久,亦不记为何人爱而携去,年台读礼之余仍乞检出寄下。此外有与此种相类者,贤桥梓昆玉及知交中不妨代为搜罗,大抵如淮阴将兵多多益善耳”[13]。此后,余怀、江之兰、殷日戒、吴肃公、狄亿、黄云、王弘撰等老友新知皆收到张潮的稿约和“代为搜罗”之请。同人们的积极投稿和宣传是相当有效的,因为时至翌年(1695)仲夏,即《檀几》初集告竣前夕,“丛书二集……所辑已将五十种矣”[14]。
“以初征为媒”也是征稿方式之一。康熙三十四年(1695)夏末,《檀几丛书》初集刻峻,张潮开始遍寄同人:“近刻丛书特呈台政,尊著有类此者不妨邮示,以为二集三集之地也”[15]。这样以书征书的功效正如王晫在《檀几丛书》二集序中所说:“予曩有《檀几丛书》之辑,岁在乙亥,张子山来刻而传之。其明年,张子仿其意,又自为《昭代丛书》,流布宇内,皆为大雅君子所赏识,四方著作家以鳞鸿相托者,弆箧恒满,于是予与张子复谋《檀几》二集”。《檀几丛书》初集和《昭代丛书》甲集的流通,为嗣后诸集的充足稿源与顺利推出打下了良好基础。
同人好友的积极投稿、广为宣传,使编者得以突破个人交游所及的局限,极大扩展了丛书的创作群体。清初名士、《桃花扇》作者孔尚任在扬期间与张潮颇为交契,《檀几丛书》初集刻成后,张潮以书伴函寄赠孔尚任,此后,孔多次将友人王士祯等人的作品、书信转致张潮,并将侄子孔衍栻、友人金德纯、程石麟等人作品推介给张潮。而王士祯后来又把自己的小品13种寄给张潮,还先后将先兄王士禄、岳丈张万钟、门人东荫商、张弨、林佶、老友张英及己作数十种荐入丛书。
对于孔尚任、王士祯这样极富声望者的参与宣传,张潮是颇为自豪和重视的,曾经在《昭代丛书》乙集编额已满的情况下不惜“裁去数种,以便增入”[16]。事实上,也的确是王士祯等兼具政治地位和文坛声望的名公钜卿的加入,使张潮及其丛书在地域、阶层和时间跨度上具有了更深远的影响。
3 同人“联欢”式的编辑体例
和组稿方式一样,编辑进程中的同人作序、参阅参评等也是清初选本同朋性质的典型体现。康熙元年(1662)五月,王士祯《渔洋山人诗集》刻成,作序者多达26人,目录后列名参校者多达28人,包括尊长、兄弟、友朋、门生、子弟等。邓汉仪《诗观》除在各卷卷首列出校阅人爵里、姓名外,还往往于卷末以寥寥数笔记录好友间一同选诗、评诗、编诗的生动细节,激扬文字,甲乙时贤,使读者如临其境。交际圈频繁互动的编辑方式和体例,仿佛一场以书为媒的同人“联欢”。
《檀几丛书》《昭代丛书》同样如此。在《檀几丛书》初集中,除了实际承担编校工作的张潮、王晫外,友人黄奂、殷曙、顾彩、黄云、朱慎等都名列校阅者,《昭代丛书》甲乙两集更甚,两集凡一百卷,每卷皆署“新安张潮山来辑,某地某某校”,校阅者多达数十人之多。
从丛书诸集例言和张潮与友人的往来书信看,作为选家的张潮和王晫自然主要承担校阅工作,在审稿过程中若发现舛误,两人一般会寄返本人进行修改,或先行校订后将刻样寄给对方复审。如《友声集》新集卷一吴陈琰《与张山来》:“王丹老持尊刻拙作一篇及小图见示,不胜狂喜,谨遵谕校正璧上……”。王晫《与张山来》:“拙作《看花述异记》又校出数伪字,特将原刻样缴还,以便凿补改正”。也有一些作者、荐稿人和其他时常过往、深有同好的友人实际参与了校阅工作,但更多名列校阅者却往往是“有名无实”。最先是由张潮主动约请友人列名参校(1)如《尺牍偶存》卷八《寄黄涵斋户部》《寄赵天羽前辈》《寄裴赓年编修》诸札,附寄《昭代丛书》乙集,并告知对方丛书内某卷“藉重台衔校阅”(对方则在回札中表示荣幸和感谢),可知对方此前并不知情。,随着编选工作的开展,又转变成很多友人主动要求列名其中,以满足自己以书传人、和丛书共“不朽”的愿望。这给张潮带来了不少麻烦,为免是非,张潮在编选《檀几丛书》丙集时干脆不再胪列校阅之人。
丙集例言第一:“前选各卷俱借光诸名家先生校定,然亦必素所往还,非敢漫然从事也。不谓诸知交纷纷见属,设有遗漏,获罪良多,是以兹集概不复用。”
这种有名无实、一味借书求名的浮华风气也遭到后人的批评,如谢正光先生曾举清初倪匡世《振雅堂汇编诗最》为例:“入选的作者不过二四八人,但书前胪列曾‘就正’的‘参校诸先生姓名’(或许是今人所说‘审订者’的意思),竟达四二六人之多,便不免贻人口实了。”[17]
4 “随录随刊”的出版方式
和编选前人或古人作品的“同行”相比,清初选家对于自己的当代选本并没有绝对的主动权,和对选本规模、时间跨度等诸多因素的预知能力。其原因在于,他们所借用的“征文”形式对编创者之间的互动有着强烈的要求,想要用一种精心策划的方式将来自不同时段、不同地域的稿件进行统一编排,确乎其难。因此,这些选本不约而同地呈现出随到随编、随刻随传的状态,这也是清初当代选本的又一特征。
李渔《尺牍新征》凡例第三:“是编征到名稿,随录随刊,不分次第,有布衣韦带翻居绅笏之前,宿士先贤偶刻时髦之后者,总以所得之先后为序,初无殿最与期间也”[18],魏裔介《观始集》凡例第三:“公卿名宿,偶尔诠次,多有参差。帙既告成,投赠后至,如李贰公、胡宛委诸公,遂续卷后,止存琬琰,非有低昂也。”[19]和那些以作者身份、年齿为次的选集相比,不分爵里、不论尊卑的编次方式显示出更多的随意性。
另一方面,随到随编的编刻出版方式使选本内部呈现出较为清晰的时间序列,从而为研究者梳理脉络、考稽史实提供了极大方便。以张潮所编书信集《尺牍偶存》《友声集》为例,康熙三十九年(1700),张潮致信张渭宾,随信寄书十数种,并告知“《友声》补奉全部,其《尺牍》今已得八卷,嗣当续寄”,又《友声集》辛集李淦《与张山来》:“恶札中有一二言可采,尚希宗工节取入友声之内,以附不朽”。可以明见这两部书信集同样采取了征稿和随到随编、随刻随传的方式,这和前后诸札内容上的连贯性、持续性是相互印证的。正是这种随意、轻松的编纂方式,为我们较为清晰地梳理张潮其人其事、再现以扬州为圆点的士人活动,尤其是发掘有关《檀几丛书》《昭代丛书》等同人选本的丰富材料提供了重要可能。
《檀几丛书》《昭代丛书》同样采取了这样公平、简单而不失灵活的方法(2)其不同之处在于,张潮是将先后收到的丛书陆续付梓,俟五十种俱已刻完后大致按经史子集之序编定(《尺牍》卷四页七《寄王丹麓》),这样,各集之间次序井然,每集之内又错落有致.,较先收到的数种、数十种刻成以后即辗转流传于同人圈中。“新城王阮亭先生邮到种种小品,美不胜收。因篇目已定,不获全登为憾,嗣当采入《昭代丛书》乙集,以成巨观”[20]。《尺牍偶存》卷四《寄王丹麓》:“(檀几)丛书五十种已刻就其半,今以全篇者特寄奉览,幸照入”,王晫收到丛书后即在钱塘诸友间传阅。时在康熙三十四年(1695)晚春,《檀几丛书》初集全部于时年秋间方告竣。
对于编纂者来说,随到随编、随刻随传的灵活方式,缩短了丛书由开选到传播的流程周期,使许多因财力不济而无缘以全编行世的选本有机会得以流传。这种呈现出鲜明时间序列的编刻方式,也为今人了解某个作家、群体在特定时段内的创作、交游、思想提供了较为生动的细节,从而使这类文学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书籍史、社会史层面的意义。
但是,这种随录随刊的编刻方式也导致了一些问题,首先是版本的错乱。以《昭代丛书》为例,今存诸版本中,各集内容、种数皆有出入,尤其是出现较晚、流传较少的丙集,在恢复原貌的过程中,更是耗费了整理者大量精力(3)(清)沈懋惪《昭代丛书合刻略例》第三:“丙集系山来晚年所刊,流传尤罕。余始假长洲顾君沅旧藏初印残本,仅二十余种,幸卷首总目具存,……今按原目重加排比,以复旧观”,第六“慧楼先生纂辑五编时,遍求丙集总目,迄未之得,故所采《荆园小语》《荆园进语》《绝域纪略》丙集易名《宁古塔志》《醉乡约法》皆已收入丙集,未免重复为嫌,爰从先生文孙肇初取素藏郭钦华《渔谈》、张英《恒产琐言》、郁永河《稗海纪游》、沈清瑞《七娱》四种易之,仍各附跋语于后,用识鄙见”。《昭代丛书》道光世楷堂刊本卷首。。其次是一些选本字体、版式芜杂,体例不一。如朱观《国朝诗正》凡例:“予侨寓广陵最久,镂板亦多。若汉水漳江等处,俱偶一游历。还新安,亦养疴逾载,所镌板皆随地命工,而告成则于淮阴。故剞劂略有不等”[21]。
以《檀几丛书》《昭代丛书》为代表的清初同朋作品集,以其独特的编辑旨趣、征选方式、编辑体例和流传路径,生动地反映了文士创作与书籍出版、流通的互动作用以及清初江南出版业的文化内涵。同时,作为清初士人社交活动的一种典型方式,同朋作品集的编刻过程集中体现了士人群体的思想倾向、审美趣味、创作追求以及相互之间的声气相求,从而具有了折射清初士人风貌和文化场景的独特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