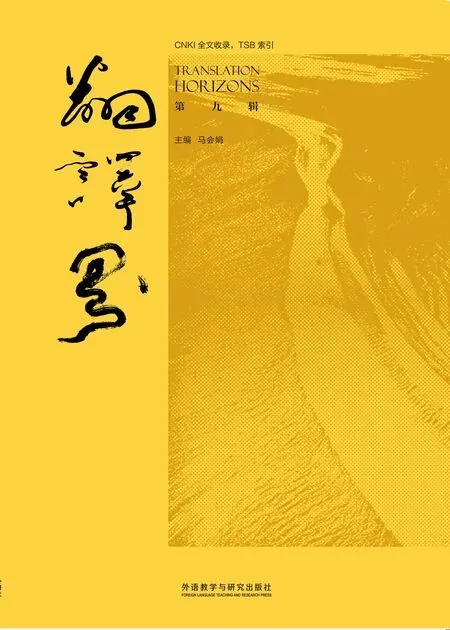创译、语境化阅读与世界文学:重读庞译《长干行》①
2020-02-24曹培会
曹培会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1.引言
《神州集》(Cathay),(Pound 1915)是由美国诗人庞德(Ezra Pound)翻译的一本诗集,其中共收录中国古典诗歌14 首。在该诗集中,庞德使用“翻译+创作”的“创译”模式对中国古典诗歌进行了意象诗歌改造,使中国古典诗歌成了长期滋养英美现代主义诗歌的东方养料。不仅如此,中国古典诗歌也通过《神州集》成功融入英语主流文学空间,进而成为世界文学。尤其是诗集中收录的中国诗人李白的《长干行》,曾多次以庞德代表作的身份被收录到各大英美诗歌选集中,成为一篇经典的英语诗歌。本文借助“创译”这一概念探究翻译的本质,并从翻译的生产和阅读两个方面重塑《长干行》翻译的历史语境,论证其成为经典化世界文学的合理性。
2.创译:世界文学的一种生产方式
奥地利哲学家维特根斯坦(Ludwig Josef Johann Wittgenstein)曾不无遗憾地说:“我的语言的界限意味着我的世界的界限”(维特根斯坦,1985:79)。作为语言的一种表现体,文学也因语言的异质性演变成为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民族文学。但是,翻译的出现延展了人们的认知空间,沟通了民族文学,使世界文学成为一种文学事实。因而,世界文学本质上是一个跨文化概念,而翻译在世界文学的建构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达姆罗什(David Damrosch)从翻译的生产、流通和阅读三个方面定义世界文学:“世界文学是民族文学间的椭圆折射;是从翻译中获益的书写;是一种超然阅读方式”(Damrosch,2003:283)。首先,世界文学天然涉及了两种语言符号和文化体系,文学作品经过源文化和东道文化的双重文化过滤,其产物必然是杂合的。其次,世界文学的杂合性也决定了世界文学与民族文学不同,民族文学是由一个中心点组成的完美的圆形空间,而世界文学是有离心率的椭圆形空间,因而折射性也是世界文学的本质属性。最后,世界文学空间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空间,它在时间和空间的维度上会随源文化焦点、东道文化焦点和焦距等因素的变化而变化。因而,世界文学是一个流动的概念。
世界文学的杂合性、折射性和动态性决定了翻译是一种有离心率的创造性活动,即创译。创译是“在目的语系统中,对源语文本进行编辑、重组、创作性重写、创意性重构等的转述方式,实现目标话语的表达性与目的性的文本”(陈琳、曹培会,2016:126)。但是,世界文学也是一个流通的概念,翻译文学在目的语文化中被阅读是其成为世界文学的必要因素。目的语读者的语境化阅读与创译产生共振,强化了其文学地位,使得翻译作品在阅读中得到流通,成就其历久不衰的世界文学地位。
3.创译:庞德与《长干行》
3.1 创译的文化和诗学背景
19 世纪末,在美国本土,以惠特曼(Walt Whitman)为代表的新诗人要求摆脱欧洲母体的传统影响,发展独立的美国诗歌的呼声愈来愈高。在这种诗学背景下,英美现代主义诗歌运动应运而生。现代主义诗歌并不特指某一流派,而是一个统领的概念,指一切反传统的诗歌流派。“这种现代性的核心内涵就是彻底反叛传统、十足的标新立异的精神”(刘象愚等,2002:2)。这种创新体现在形式上是格律体向自由体的转变。“创造新的节奏,表达新的情态。……我们坚信,相比传统形式,自由体能够使诗人更好地表达自己。诗歌中,新的韵律意味着新的思想”(Lowell,1915:vi)。现代主义诗人认为传统的格律诗虽然整齐统一,但过于严谨和刻板的诗歌模式会因韵害义、因律损诗,影响诗情的抒发。因而他们主张对旧的格律诗进行革新,抛弃韵脚、音步等的束缚,以无固定模式的自由体作诗。但自由体并不意味着绝对的自由,而是指以自然语流的划分来替代韵律,使诗歌依然富有音乐性。
除了诗歌形式的创新,诗歌语言也是英美现代主义诗人进行诗学实验的领域。被公认为“美国诗歌之父”的惠特曼于1855 年发表诗集《草叶集》(Leaves of Grass),开启了用新形式和新语言创造属于美国人民的新诗歌的传统。“英语有助于表现美国的宏伟,它足够刚健、灵活、完整。……它是一种强大的反抗性语言,是常识的方言”(Whitman,2002:635)。在诗歌语言的使用上,现代主义诗人摈弃了维多利亚诗歌传统中繁复修饰的特点,追求诗歌的简洁和语言的本土化及口语化。继承惠特曼的诗学传统,英美现代主义诗人反对晦涩难懂的语言修饰,致力于用大众化语言书写现代主义诗歌传统。“使用大众化语言,但必须是精确的词语,不要近乎精确,也不要修饰词”(Lowell,1915:vi)。现代主义诗人认为,繁复的语言修饰不利于直接表现事物和情感,而大众化语言是体现诗歌个性化和表现力的强有力的工具。“从某种层面上讲,日常英语(plain English)的发展史同时也是后浪漫主义诗歌(尤其是现代主义诗歌)的历史。至少,低语域(low register)可以比喻为现代主义迷宫中的一根引线,用以判定现代主义的动机和理由,探寻现代诗歌的发展路径以及诗人们选择背后的动机”(Rosen,2006:3)。
3.2 创译的文本表现
《长干行》是《神州集》中收录的诗歌之一,庞德将其译为《河商之妻》(“The River-Merchant’s Wife: A Letter”)。译文响应英美现代主义诗歌的要求,采用无韵自由诗体,以叙事书信体细腻刻画了一名女子对经商在外的夫君的思念之情。译诗语言口语化,浅显易懂。
While my hair was still cut straight across my forehead
I played about the front gate, pulling flowers.
You came by on bamboo stilts, playing horse,
You walked about my seat, playing with blue plums.
And we went on living in the village of Chōkan:
Two small people, without dislike or suspicion.
At fourteen I married My Lord you.
I never laughed, being bashful.
Lowering my head, I looked at the wall.
Called to, a thousand times, I never looked back.
At fifteen I stopped scowling,
I desired my dust to be mingled with yours
Forever and forever, and forever.
Why should I climb the lookout?
At sixteen you departed,
You went into far Ku-to-Yen, by the river of swirling eddies,
And you have been gone five months.
The monkeys make sorrowful noise overhead.
You dragged your feet when you went out.
By the gate now, the moss is grown, the different mosses,
Too deep to clear them away!
The leaves fall early this autumn, in wind.
The paired butterflies are already yellow with August
Over the grass in the West garden,
They hurt me,
I grow older,
If you are coming down through the narrows of the river Kiang,
Please let me know beforehand,
And I will come out to meet you,
As far as Chō-fu-Sa.
(Pound,1915:11-12)
3.2.1 中国故事与西方叙事
庞德译诗采用书信叙事体,体现了统一的叙事结构,这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上。
第一,是词语层面上的叙事统一。原诗以一名妇人的口吻,以时间顺序向在远方经商的夫君追述他们两人两小无猜的童年生活,喜结连理的甜蜜,愿同尘与灰、心心相印的誓言,最后表达了对远行夫君的牵挂和思念。庞德在译诗中通过用still、went on living、at fourteen、at fifteen 等词/词组,同样遵循了原诗的叙事结构,尤其是第一句中的still 一词仿佛带着读者回到了男女主人公初识的时候:我,一个额发未满的小女孩在门前折花玩耍,而你踩着高跷,扮作一匹马向我跑来,于是两个纯真可爱的小孩子成了两小无猜的玩伴。此后两人同在长干里生活,长大。went on living表现了两人共同度过的青梅竹马的童年。
第二,则是篇章结构层面上的统一。“五月不可触”本意为:瞿塘地势险峻,暗礁多,水流湍急,尤其是到了五月,水势上涨,暗礁不可见,易翻船。庞德则译为And you have been gone five months。研究者多认为此处为庞德误译,且译得突兀,打乱了原文的叙事结构,让人不知所云。“最后一句里,把五月份译成五个月。这样使得长江三峡特有的猿声哀鸣景象显得非常唐突”(党明虎,2003:63)。但是笔者发现,该处“误译”实则是庞德的有意创译。庞德对汉语以及汉诗都知之甚少,《神州集》是以汉学家费诺罗萨(Ernest Francisco Fenollosa)的手稿为基础翻译而成,所以费氏手稿基本决定了庞德对汉诗的理解。但经过对比费氏手稿,笔者发现费氏对此句的解读是正确的:“The ship must be careful of them in May”(Pound,2015:78)。如此一来,庞德的翻译就成了有意识的误读,即创译。庞德此处创译不但没有打乱原文的叙事结构,反而是遵循了原文的叙事结构:你去了险峻的瞿塘,一走就是五个月,我仿佛听到了头顶上有哀怨的猿啼声。“五个月”体现了“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思念,“仿佛听见头顶上哀怨的猿啼”体现了对身处险境的夫君深深的牵挂。译诗把一个新婚不久、独在家中思夫的妇女形象刻画得淋漓尽致。
“(西方)叙事诗重在事件的线性发展的外在呈现,在语言上显然以动态性词语为主导,中国诗重在情感的碎片化和非连续性的内在抒发,在语言上,静态描写性的词语占主导地位”(魏家海,2017:221)。李白的《长干行》是一首爱情叙事诗,在诗歌的前半部分,“我”通过“两小” “十四” “十五” “十六”这一条清晰的时间线,回忆了自己与夫君从两小无猜到缔结姻缘,从相知相守到忍痛分离的过程。而诗歌的后半部分则回归到了中国诗歌“一切景语皆情语”的创作模式,描写了五月的水流、猿啼、绿苔、秋风和落叶,还有八月西园里双宿双飞的蝴蝶,由情及景,触景生情,叙事的时间线在此隐入文本。而庞德将“五月不可触”译为“你已离去五月之久(And you have been gone five months)”,以叙事口吻述说“你”离开之后的春去秋来之变化,令后面的景物描写合理化,也使译诗的叙事结构更加外显化和完整。通过这一创译,庞德将李白笔下的中国故事以英语诗歌的叙事方式呈现给了西方读者,实现了中国古典诗歌在英语世界的初步接受。通过这种创译处理,“庞德将诗歌叙述者对丈夫的激情和爱意做了前景化处理,同时,也有意或无意中消匿了原诗中的矛盾因子”(Yu,1998:187)。
3.2.2 去典和普罗化
庞德译诗遵循了现代主义诗歌走向通俗化和大众化的诗学要求,这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第一,译诗放弃了原诗中的典故,照顾到了英语读者的阅读体验。原诗中“常存抱柱信,岂上望夫台”意思是:时常心存至死不渝的信念,却不想一日登上望夫台。这一联既为下面“十六君远行”作铺垫,也表现了“我”对远去夫君的嗔怨。此处一共使用了两个典故。一是“抱柱信”,出自《庄子·盗跖》中的一个成语“尾生抱柱”。相传一位名叫尾生的男子与心爱的女子约定在桥上相会,久候女子不到,水位上涨,尾生却不愿违背承诺离开,后乃抱桥柱而死,一般用以比喻坚守信约。诗中借该典故比喻“我”要与夫君生死同尘、不离不弃的信念。“望夫台”则来源于一则民间故事。传说夫君久出不归,妻子登台眺望,天长日久变成了一块石头矗立在台子上,故将台子称为“望夫台”,一般借此表达妻子对夫君的思念盼归之情。
典故深植于文化背景之中,所负载的文化意蕴对于母语读者尚需琢磨查究,对不谙中国文化的普通英语读者则更加难以理解。在翻译中,如要忠实传达,要么在文中加以解释,要么在文外加以注释。但是前者容易造成行文啰唆,后者则容易打断读者的阅读。两种方法都非读者友好型翻译策略。惠特曼认为“伟大的诗歌没有阶层、肤色和人群之分,诗歌的创作也要适时使用一些常见习语或短语——美国俚语和粗鄙俗语——行话等”(Howard,1930:449)。英美现代主义诗歌运动主张诗歌普罗化,即让诗歌走向大众。作为这一运动的领军人物,庞德在译诗中采取的处理方法是略去典故不译,用三个forever 承接上文,表达了“我”对夫君延绵深厚的爱意,接着用一个反问句Why should I climb the look out?一方面表达了“我”沉浸在新婚生活的幸福和对婚姻所怀的坚定信念中,另一方面也为下文夫君远去的转折作了铺垫。采用这种去典的翻译策略,译诗既表达出了原诗中“我”对远行夫君至死不渝的承诺,又使译文通俗易懂,体现了充分性和可读性的结合,也为《长干行》变身为《河商之妻》,进入英语普通读者的阅读视野奠定了文本基础,开拓了《长干行》作为世界文学的阅读维度。
第二,庞德对中国古典诗歌中带有丰富文化内涵的专有名词,如地名等也进行了去典化处理。在翻译“西出阳关无故人”(《送元二使安西》)时,庞德将“阳关”译为“the gates of Go(离门)”(Pound,1915:28),巧妙地体现了原诗浓浓的离别之意。同样,庞德在翻译《登金陵凤凰台》中“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一联时,再次将“吴宫”译为“house of the Go”(逝去家族的遗址)(Pound,1915:30),虽未将原诗中“吴宫”与“晋代”的历史文化信息译出,却将诗中蕴含的怀古之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庞德以“Go”一词奠定了两首诗的情感基调,通过巧妙地变换“Go”的词性构建了两个鲜明的意象,这种意象既是“接近骨头”般对事物坚实和直接的呈现,又是对情感有力的阐释。同时,也体现了庞德对“意象”的阐释:“意象是一瞬间理智和情感的复合体的呈现”(Pound,1913:200)。但是,同样收录在《神州集》中的《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庞德将其中“相随迢迢访仙城,三十六曲水洄潆”中的“仙城”译作“Sen-Go”(Pound,1915:19),即“仙城”在日语中的发音“RA(ix)ご”。同时,其对同一首诗歌中的另一地名“洛北”的翻译,也是以相对应的日语“Raku-hoku”(Pound,1915:18)翻译而成。由此说明,当时对汉语及汉诗知之不多的庞德,对《神州集》中地名的翻译实则是依赖费氏手稿中的日语注释而成。但是,无巧不成书,“阳关”变成了“离门”,“吴宫”变成了“旧屋”,看似荒谬的“误译”却变成了一首经典创译案例中妙手天成的点睛之笔,成就了中国古典诗歌在英语世界的世界文学地位。
4.创译之后:语境化阅读
当一个文本被译为另外一种文字之后,它便不再是源文化或源文本的独特产物,而变成了“仅仅始自母语的作品”(Damrosch,2003:22),具备了文学独立性,有了全新的文学生命和生长空间,其样貌如何、寿命长短都由其宿主的社会文学环境和读者来决定。谢天振(2013)曾经从译介学角度,将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分为媒介者的创造性叛逆和接受者以及接受环境的创造性叛逆两种类型。前者指翻译过程中译者主体在文本层面的创译,后者则是翻译之后宿主文化读者对译文的语境化阅读。译文最终在世界文学空间的接受和流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宿主文化对译文的定位和认知。此外,语言学家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Kaspar Malinowski)、弗斯(John Rupert Firth)以及韩礼德(M.A.K.Halliday)等人都认为语境对于文本意义的理解和传达至关重要。其中,弗斯(Firth,1957)将语境细分为语言语境和情景语境,前者指语言内部各要素的上下文环境,后者则指社会、文化等语言外部环境各因素。不管是译介学的接受环境的创造性叛逆,还是功能语言学派中关乎意义认知的情景语境,都决定了语境化阅读是译文意义再生及译文世界文学经典地位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一环,也是翻译研究的应有之义。
《神州集》出版于1915 年,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第二年。庞德从数十本费诺洛萨手稿近150 首诗歌中“精挑细选”出14 首组成《神州集》①“1913 年末,费诺洛萨遗孀通过在伦敦面交或邮件形式一共给了庞德八本笔记、几卷能剧注释稿、几本中国诗学讲演稿以及几沓活页纸。所以才有了为我们时代发明中国诗歌的机会……初版《神州集》中收录的14 首诗歌是从笔记中近150 首诗歌中挑选出来的,它们成了第一批基于对中国诗歌文本的详细注释完成的自由体译诗。”(Kenner,1971:198),其中有描述战争之苦的《诗经·采薇》《古风十四·胡关》《古风六·代马》,也有体现妇人盼归之怨的《长干行》《玉阶怨》《古诗十九首·青青河畔草》,还有诉说离别亲友之不舍的《送元二使安西》《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送友人》《送友人入蜀》。“征战” “思念”和“离别”等诗歌主题集中出现在一本薄薄的诗集中,使得《神州集》成为一本反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应景之作”。“第一次世界大战赋予了《神州集》以新的维度……庞德把古代中国诗歌中的惆怅之殇:送别、思乡、流离、孤独、怀古、破败等调和成了《神州集》中的战时之音”(Froula,2013:212)。身处战时的人们,包括普通士兵,均饱受战争的流离和远离亲友的苦楚,在这些诗歌中他们找到了情感的共鸣。曾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并在战争中牺牲的法国年轻艺术家亨利·戈蒂耶-布尔泽斯卡(Henri Gaudier-Brzeska)在战壕中从这些诗歌里汲取勇气:“这本书一直在我的口袋里…… 这些诗歌以一种绝佳的方式描述了我们身处的环境”(Kenner,1971:202)。伟大的诗歌之所以历久不衰,就在于它们时隔千年万里的时空仍能给人带来当下的共振。“读者是文学的接受主体,在文学完成的整体过程中,它不是消极被动地接受文学作品,而是以积极的创造性的参与,对文学发展进行反制的”(陈思和,2011:5)。庞德为读者构建了一个战争语境,契合了战时人们的心理阅读期待,士兵在这些中国诗歌中找到了“归乡”,士兵家属找到了“思念”,形成了《神州集》以战争为背景的语境化阅读。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神州集》中所收录的译诗不完全是译自中国古典诗歌,还有一首庞德译自古英语诗歌的《水手》(“The Seafarer”),此诗通常被国内学者忽略。《水手》讲述了水手历经海上航行的各种磨难,渴望回归岸上,过安稳生活的心情,诗歌中写道:“哀怨/是我心头的欲魔/出发,继续寻找他乡的锚”。这又何尝不是为战争所迫,在外颠沛流离的士兵的心声呢?《水手》本就来自于读者熟悉的英语文化背景,其诗歌主题为英语读者阅读一同收录在《神州集》中的其他中国古典诗歌提供了指向性阅读导向,并与这些中国古典诗歌一起形成了一个文本空间,为读者的阅读作了语境化架构和诗学铺垫。因此,《水手》与《长干行》《诗经·采薇》等诗歌中西映照,作为构建阅读语境的一部分,共同满足了读者在战时对安稳的渴望、对亲人的思念等心理和情感期待。中国古典诗歌也因此在读者的阅读中获得了新的诗学阐释。
庞德在译诗中的创译,使中国古典诗歌在形式上披上了现代主义英语诗歌的外衣,并在西方沃土种下了中国古典诗歌的种子;而战时语境下,西方读者在阅读中感受到的共情则给予了中国古典诗歌在英语世界文学中源源不断的生命力。“《神州集》演绎了一首首哀婉的战争诗歌。这些诗歌是反映一战诗歌作品中最持久的一批,即使是在之后的50 年间仍具有蓬勃的生命力”(Kenner,1971:202)。
5.创译之“实”:世界文学
“世界文学在翻译中受益,在译入语文化中获得一种新的生命,其意义也在译文和新的文化语境中得以重构”(丹穆若什,2014:III-IV)。中国诗人李白的《长干行》经过庞德的创译,以及宿主环境和读者创造性的语境化阅读,其文本意义和阅读语境均得到重建,成为英语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河商之妻》。自《神州集》问世至今一百多年的时间里,《河商之妻》频频入选各大英语文学选集,这些选集包括:《新诗选集》(The New Poetry:An Anthology,1917)、《牛津现代诗选:1892-1935》(The Oxford Book of Modern Verse:1892-1935,1936)、《袖珍本现代诗选》(A Pocket Book of Modern Verse,1954)、《诺顿美国文学选集》(Norton 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1979)、《英语诗歌评论:1900-1950》(English Poetry, 1900-1950: An Assessment,1981)、《文学:150 篇小说、诗歌、戏剧名作》(Literature 150 Masterpieces of Fiction Poetry and Drama,1991)、《现代美国诗歌选集》(Anthology of Modern American Poetry,2000)、《最佳儿童诗百首》(100 Best Poems for Children,2002)、《诺顿诗歌选集》(The Norton Anthology of Poetry,2005)、《企鹅丛书:二十世纪美国诗歌选集》(The Penguin Anthology of 20th Century American Poetry,2011)等等。《长干行》的世界文学生命在一次次的入选和阅读中得到更新,使得这朵中国文学奇葩在异域他乡绽放至今,经久不凋。2015 年是《神州集》出版100 周年,美国纽约新方向出版社推出《神州集》一百周年纪念版。该书不仅再现了1915 年《神州集》的原貌,还在书内增加了费诺洛萨的注释手稿。“庞德用英语创译了中国诗歌。他似乎早已预测到:在无尽的、永远无法逃脱的当下,日日新就意味着要不断回归过去。”①参见https://www.wwnorton.co.uk/books/9780811223522-cathay(2020 年3 月23 日读取)。
不仅如此,一些英语诗人还对《河商之妻》进行诗学仿拟,如“Letter to Ru Yi, the River-Merchant’s Wife”和“The Expat’s Partner: An Email”②对这两首诗歌的详细分析可参见https://www.worldliteraturetoday.org/blog/translation-tuesday/contemporary-faces-river-merchants-wife-tammy-lai-ming-ho(2020 年3 月23 日读取)。等。这些诗歌仿照《河商之妻》的诗学形式,在现代语境下寄以当代人的情感,既是当下诗歌对过去的回归,也是《河商之妻》受到广泛阅读和影响深远的明证,同时更是《长干行》成为世界文学,具有文化、文学通约性的有力体现。
世界文学是创译的产物,同时也是一种语境化阅读的结果。从创译和阅读两个方面对庞德所译《长干行》的重新审视使我们能够植根于中国文学,放眼世界文学,在中外文学的互动关系中考查如何在西方语境下讲述中国故事。李白为中国文学创作了《长干行》,庞德则为世界文学创译了《河商之妻》。在庞德的创译和宿主语境下读者对译文的意义重构等多重作用下,《长干行》成功走进了世界文学的流转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