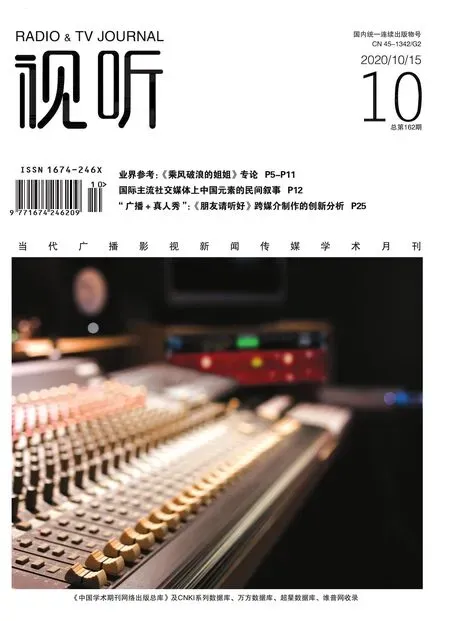基于传播社会学视角浅析网络时代的“缺场交往”现象
2020-02-24张金娟
□ 张金娟
在传统观念中,交往主要是指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场域也被认为是重要的条件。然而在网络时代,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革,身份的隐匿性、跨时空互动等特征使身体不在场的交往方式成为可能。这种缺场交往改变了我们的交往方式,使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得以重构。
一、“缺场交往”形成原因
(一)网络社会的到来
加拿大传播理论家麦克卢汉提出,“媒介即信息”。其核心意义在于媒介决定了信息的存在和传播方式,也改变了我们接受信息的方式,从而深刻地影响了我们的交往方式。网络时代的到来有力地佐证了这个观点。随着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的出现,人们的交往方式发生了极大的改变,使得交往突破了场域的限制,这种缺场交往有力地冲击了传统的面对面的交往方式。但是尽管缺场交往看似是一个虚拟的交往方式,但是它必须有不虚的载体,需要有网络技术的支持,因此,网络社会的到来为这种交往方式提供了可能性。
(二)交流欲的催生
人是社会性动物,因此人类对于交流的欲望也从未停止。随着技术的发展,形成了“处处是中心,无处是边缘”的社会,人们的交流欲望已经不满足于面对面的交流互动,而是希望能够借助网络媒介实现跨越时空的交流。这种以离开身体接触为特征的缺场交往满足了人们新时代交流的欲望,缺场交往使得人际交往突破了距离和时间的限制,重构了人们的交往方式,因此受到了人们的推崇。
(三)从原子化个体到共同体想象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曾经农业社会所特有的家园温情、睦邻友好式的熟人社会开始瓦解,人际关系的淡漠变成这个时代的特征。网络时代的来临,使得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开始缩小,熟悉的人之间、陌生人之间都可以实现实时的互动,并且可以发表自己的声音,从而找寻到志同道合之人,人们对于这种温情的共同体的想象使得缺场交往被赋予了很大的期望。很多学者认为这种交往方式使哈贝马斯提出的“公共领域”成为可能,个体公民聚集在一起,共同讨论他们所关注的公共事务,形成接近于公众舆论的一致意见,进而影响国家活动。
二、“缺场交往”可能带来的问题
(一)社会规范的缺失
缺场交往时,双方的身份都有一定程度的隐秘性。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在个体身上的不充分在场使得很多人披着自由的外衣随意地发表言论。其中最明显的就是谣言的肆虐,因为其在缺场交往时没有身份的束缚,很多网友开始编造一些不真实的言论以引得关注,而很多不知情的人由于缺少相应的媒介素养,有意或者无意地成为了谣言的助推器,使社会规范失序。另一方面,随着人肉等技术的发展,隐私权的保护也成为迫在眉睫的事情。
(二)负向社会认同
尽管社会认同对于社会凝聚力具有重要的作用,但在很多情况下,有的社会认同却是包含着很多负向的甚至是不实的内容。比如在“表哥”“郭美美事件”中很多人对政府表现出了极大的不信任,尽管政府处理了相关人员,网上还是一致质疑政府的“作秀”嫌疑。这种不信任的蔓延使得社会的信任危机更甚,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另一方面,在建构社会认同的同时,社会成员也对相反的观点保持着排斥的态度,甚至引发网络暴力事件。这种一边倒的、无理性的社会认同对于社会建构有害无益。
(三)真实自我与虚拟自我
我们在缺场交往中可能会扮演各种各样的角色,有的角色是真实的自我,有的可能是扮演的自我或者想象的自我。这种虚拟环境中的“我”可能会带来很多不同的现实体验,以至于常常会使人迷失自我,导致很多人沉迷网上的社交,厌恶现实中的自我。同时在自我的重新塑造过程中,我们也在塑造着想象中的对方,把虚拟环境的对方当作真正的“他”。这种交往方式本身就是一种想象的交往,以至于当这种交往演变为现实中的交往时,会让人产生迷茫和失落。这也是缺场交往带给我们的惊喜和失落。
(四)彼此沟壑更深
我们都说缺场交往有力地克服了时空的局限,扩大了人们的交际面,然而现实的情况却是我们面临的沟壑更深。在很多场合,我们面对面的交流被手机的交流所取代,即使双方都在场,彼此之间沟通也甚少,“低头族”变成了普遍的社会现象。我们为了更好地交流,所以不断地改进交流的渠道,可是这些新兴的媒介在便利我们生活的同时,是否也相应地加深了我们彼此之间心灵的隔阂呢?这也是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
三、如何完善“缺场交往”
(一)建构规则秩序
无规则不成方圆,在网络空间中,也应该有一定的规则和秩序,因为参与的双方都是现实中的人,负有一定的社会责任。尽管网络空间自身的特性赋予了人们一定程度的自由,但自由并不是绝对的,在网络空间也是如此。缺场交往的规则和秩序有赖于政府的引导和规范,但更重要的是参与其中的人自觉的地维护,在表达自身诉求的同时不损害其他人的利益,不发布和散播不实的消息和言论,尊重别人的隐私权,合理合法地表达自己的观点,这些都需要每一个参与者自觉遵守和守护,只有有规则、有秩序地交往,才能有更为良性的互动。
(二)重视“智识者”的作用
知识分子在西方语境中即“intellectual”,有学者将其译为“智识者”,认为其原意基本上指的是一种类型的群体,这些人具有真知灼见、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以理性给人启迪。中国的知识分子在网络中普遍处于“失语”的状态,在微博使用占比上份额较小,而且很多网络意见领袖是为娱乐消遣的“网红”。因此难免会在很多公共事件和人际交往中处于一种非理性的状态。积极正面的社会认同需要充分发挥这些“智识者”的作用。一方面知识分子应该对时事保持关注,并发表自己的意见,起到良好的舆论引导作用;另一方面,制度也需要为这些知识分子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这样可以避免网络负向的社会认同,也能够更好地规避许多不合理的网络现象。
(三)不可忽略“在场交往”
彼得斯在《交流的无奈》中认为“亲临现场恐怕是最接近跨越人与人鸿沟的保证”,尽管缺场交往大大便利了我们的交流,但是它不能代替在场交往。在场的情况下,我们除了符号语言,还能感受到对方的姿态语言和情绪变化,这样才能够更好地消除误会、关爱对方。正确有效的做法是将缺场交往当作在场交往的补充,重视每一次相遇,当时间和空间不允许的时候,充分借助缺场交往,联络彼此之间的感情。
四、结语
网络时代的来临,消弭了时间和空间的距离,在这种情况下,催生了人们交流的欲望,使得城市化进程中形成的原子个体重新结成新的共同体,并因此使“公共领域”成为可能,使“缺场交往”变成一种新的交往方式。但是随之而来的问题也有很多,由于其隐匿性,导致社会规范的缺失和更多的负向认同,并带来了真实自我与虚拟自我的割裂。为此,我们要完善这种“缺场交往”的方式,重建规则秩序,重视“智识者”的作用,同时重视在场的作用,只有这样,“缺场交往”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