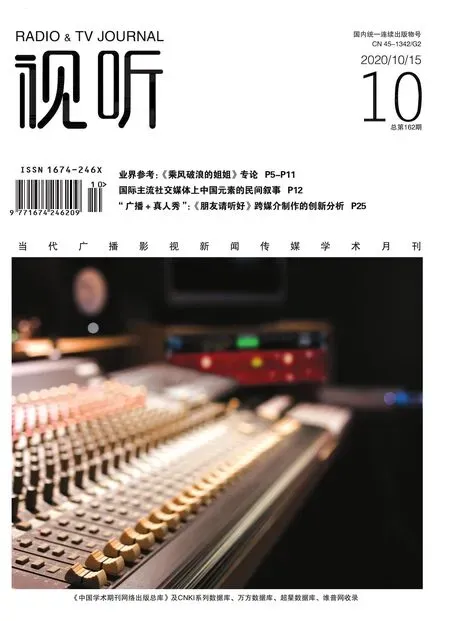故事的叙述与“被叙述的”故事
——谈《大红灯笼高高挂》的文学改编
2020-02-24史秀秀
□ 史秀秀
各文明体系的造字过程都必经的初级阶段就是创造可以代表语言概念的象形符号。中华文明的文字也有古象形字阶段,这种描摹事物外形特征以表达语言功能的造字过程似乎彰显了文字与现实形象之间久远的渊源。饶有趣味的是,古代象形文字从模仿形象到创造文字符号,如今百年新生的科技产物——电影,仿佛东趋西步,用“形象”去重现文字。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无数经典的文学作品被搬上银幕,进行了从书面到银幕、从文字到影像的尝试。众所周知,张艺谋是一位钟情于文学改编的电影导演,其对中国当代文学的高度倚重体现在迄今为止他所导演的二十二部影片中有十五部改编自文学作品。更让人讶异的是,多数脱胎于文学作品的影片往往一鸣惊人,创造了备受瞩目的影坛神话,而摆脱了“文学拐杖”的电影作品却屡屡遭人诟病、受人訾议。不容置喙的是,张艺谋成功的改编实践已成为研究电影与文学改编的绝佳范例之一,而他又分明地体现着“张氏改编”的痕迹,这种独特性与前述的令人讶异之处启示着研究者去探寻文学对张艺谋电影不容小觑的滋养与形塑的效力。本文以张艺谋的《大红灯笼高高挂》为个案,探讨其对苏童小说《妻妾成群》的改编。
一、文学创作的“语言革命”
20世纪80年代以启蒙精神、精英话语为主导的时代语境,蕲求解释伤痕与反思重负的集体无意识,历史反思向纵深发展的逻辑必然,渴望对电影进行从内容到形式的颠覆性变革的强烈愿望等,成为推动张艺谋电影横空出世的外部合力,而真正对张艺谋的电影观念、电影形式起到决定性影响的内在力量则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的莫言、苏童、余华等人深受现代主义思潮影响的文学作品。
“人们对现代主义文学的接受是从表现技巧和手法开始的,文体形式和新的表现技法的认知和接受是新时期文学观念嬗变的最初形态。”①传统的文学观念强调形式为内容服务,忽略了文学作品的本体与叙述技巧的功能和价值。20世纪80年代中期,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与文学理论深深影响了马原、莫言、苏童、余华、格非等人的创作观念,“说什么”已经变得不重要了,“怎么说”才是目的。符号论美学家苏珊·朗格的论述或许可以提供一些对叙述形式和技巧的重视所彰显出的独特意义,“艺术品是将情感呈现出来供人观赏的,是由情感转化成可见的或可听的形式,它是运用符号的方式把情感转变成诉诸人的知觉的东西。”②这些具有现代性特性的文学作品的叙述形式和技巧成功地赋予了艺术品“意味”,这种“意味”是一种具有生命特性的情绪、感受、意识等。自古以来,中国“文以载道”的实用论思想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深深地积淀在人们内心深处,中国电影自诞生以来也深受“影戏观”的影响,鼓吹“含褒善贬恶之义”,因此,“说什么”向来比“怎么说”要更重要。与其说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的这场“文学革命”是与张艺谋神话的不期而遇,不如说小说给予了张艺谋创作的灵感。
二、从书面叙事到电影叙事
几乎是在电影诞生的初期,电影创作的先驱们就开始了陆陆续续的文学改编实践。1900年,乔治·梅里爱(Georges Méliès)将《灰姑娘》搬上银幕;1902,年他又参考儒勒·凡尔纳的《月球旅行记》和威尔斯的《第一次到达月球上的人》完成了著名的改编影片《月球旅行记》。与梅里爱同时进行文学改编实践的还有阿贝尔·卡普拉尼,他于1905年担任百代公司的导演,接连将《唐璜》《灰姑娘》《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等世界经典名著拍摄成电影。被电影史学家公认的大卫·格里菲斯(D.W.Griffith)正是以一部改编自小说《三K党人》的《一个国家的诞生》为电影艺术做出开创性贡献。另外,关于文学改编的相关理论也与改编实践相伴相生,作用于两种艺术形式之间的恩恩怨怨与分分合合。
许多文学改编研究武断地将电影术语引入文学文本研究之中,如用“特写”来形容文学作品中的细节描写;或频繁参照文学理论的概念来分析电影,甚至将此作为改编的缘由或基础,实属忽略了电影的本体特征,未将两者放在一个通用的比较平台上就强行建立联系。借用王志敏先生在《现代电影美学基础》中建立的表意系统,可以将文学囊括于内,以便于进行分析比较。电影和小说都是具有复杂结构的“多级表意生成系统”③,这个系统由两类功能性单元和三个逐级生成的层面构成。
两类功能性的单元是:(1)媒介单元(能指);(2)表意单元(所指)。
三个逐级生成的层面是:(1)知觉面(一级媒介)传达故事(一级表意);(2)故事面(二级媒介)表现思想(二级表意);(3)思想面(三级媒介)表现特征(三级表意)。
这三个层面是由四个单元组成的:(1)知觉;(2)故事;(3)思想;(4)特征。
在这里可以看出,知觉单元仅作为能指,特征单元仅作为所指,而故事单元和思想单元既可以是能指,又可以是所指。这四个单元之间的表意关系并非线性的,这样,在电影和小说文本三层次、四单元表意生成机构中就形成了六条表意线索:
(1)知觉面表达:故事;思想;特征;
(2)故事面表达:思想;特征;
(3)思想面表达:特征。
从艺术表现的角度看,知觉面负荷最重,其次是故事面和思想面。无论在电影还是小说中,以上四个单元密不可分且必不可少,但由于每个导演的创作个性不同,在创作过程中会有所侧重。当我们将电影和小说的表意系统并置在一起时,故事和思想又是小说和电影联系在一起的中介。
借用热拉尔·热奈特对叙事所下的定义,“借助语言,尤其书面语言再现一个或一系列真实或虚构事件”,我们可以把叙事的构成要素编录如下:“一个或一系列事件”意味着一连串行动;一个或多个施动者和被动者;一个环境(地点、物品,等等);一个时间顺序。上述“借助语言……再现”意味着有再现的配置,即一个公开或隐蔽的叙事陈述者(叙述者);一个或多个作为再现出发点的视点(叙述);一个叙事的接受者(受述者)及上述再现的观众。
(一)对素材的处理
在小说中,“对话特别要求空间组织,因为它不呈现,而是再现或虚构的话语”④。电影中的文字性的内容,无论是对白抑或是字幕都必须与影像联系起来才有意义,这与书面叙述显然是两种不同的程序。《妻妾成群》中,陈佐千多用短句,但他的每次对话或行为对陈家大院的女人都有决定命运的意义。除此之外,关于陈佐千的描述也围绕性的话题,陈佐千这一形象从书面到影像的移植就面临着一个较大的困难,因为在小说中动词意味着行动,而影像却展示行动。陈佐千妻妾成群,夜夜春宵,周旋于几个女人之间,颂莲身上的那股新鲜的性吸引力是陈佐千为之着迷的原因。而影像的展示性质使其无法完全照搬小说的描写,张艺谋对此做了极为精巧的处理。为了体现陈佐千是陈家大院的主宰,代表着封建势力的他如阴云一般笼罩着五个女人的命运,张艺谋对此进行了简化处理,全片几乎没有一个陈佐千的正面形象,都是背影或者侧面,将其放于前景的主导性位置,将女性置于后景,体现出被动的态势。除此之外,陈佐千的对白几乎全在“画外空间”,这种没有准确位置来源的声音强化了一种阴魂不散的掌控感,也符合张艺谋想要传达的主题,即封建文化、封建势力对女性的摧残。另一个男性角色大少爷飞浦在小说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叙事地位,他对女人怀有天然的恐惧,虽然喜欢颂莲,但却软弱无力、无可奈何,虽接受过新式教育但依旧无法成为权利的继承者,只能生活在对父权的尊崇与屈之下。在电影中,张艺谋也几乎删减了飞浦这个角色的情节段落,意在强化代表着新兴力量的男性角色的无力感。但与陈佐千的人物塑造相比,《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的飞浦无论是在知觉面还是故事面上都较为薄弱。
苏童将《妻妾成群》故事的发生地选在潮湿的江南水乡,潮湿的阴雨天气暗示着人内心最隐秘的欲望,如陈佐千和颂莲的第一次见面:
“那天外面下着雨,陈佐千隔窗守望外面细雨漾漾的街道,心情又新奇又温馨,这是他前三次婚姻中从未有的”,以及“秋天里有很多这样的时候,窗外天色阴晦,细雨绵延不绝地落在花园里,从紫荆、石榴树的枝叶上溅起碎玉般的声音。这样的时候颂莲枯坐出窗边,睬视外面晾衣绳上一块被雨淋湿的丝绢,她的心绪烦躁复杂,有的念头甚至是秘不可示的,颂莲就不明白为什么每逢阴雨就会想念床笫之事”。
“小说中的阴雨连绵的、湿乎乎、潮乎乎的环境中,有着欲望、冲动、阴晦、压抑、霉烂、腐朽、无聊、寂寞、惆怅、低沉、阴暗……等复杂的味道。”⑤张艺谋的《大红灯笼高高挂》将故事的发生地从江南水乡移到了他所熟悉的西北苍凉之地,这与他本人的创作经验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对于从小生长在陕西的张艺谋来说,这是他再熟悉不过的环境,闭塞荒凉的陈家大院放在这里,更能够凸显压抑人性的封建文化氛围,但对于人性隐秘欲望的表现则略显单薄。虽然张艺谋照搬了原著中描写颂莲雨天想念床笫之事的段落,也通过人物行为(陈佐千躺在床上,颂莲坐在镜前整理衣冠)突出性暗示的味道,但这场雨更多的是压抑、无聊与阴暗,并未触及人内心隐秘的对释放欲望的强烈渴望。
颂莲——对人物的道德化处理。与电影中被迫嫁予陈佐千不同,原著中的颂莲是主动选择嫁给陈家做小妾。小说中写道:“她很实际,父亲一死,她必须自己负责自己了。在那个水池边,颂莲一遍遍地梳洗头发,藉此冷静地预想以后的生活。所以,当继母后来摊牌,让她在做工和嫁人两条路上选择时,她淡然地回答:当然嫁人。继母又问,你想嫁个一般人家还是有钱人家?颂莲说:当然有钱人家,这还用问?”苏童笔下的颂莲更多了一种久经世故的沉稳与睿智,美好的爱情于她而言不及富裕条件带来的生存保障。电影中的颂莲是单纯又倔强的,剪掉卓云的耳朵,假装怀孕,让雁儿跪在大雪中导致雁儿死亡,虽然是主动选择加入争宠的行列,但导演都给出了转变的充分铺垫,凸显了腐朽的封建伦理纲常对人性的扭曲及同化。在小说中,颂莲是智慧又骄傲的,苏童并没有试图掩盖颂莲恶的一面,而是着重表现女性在深陷封建伦理绝境之中不自觉的意识状态和行为选择。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中,颂莲的年轻、热情、渴望、性欲被压抑,围绕着一个已然枯槁的男性,与四个女人之间产生矛盾、敌意,女性的心理与文化局限由此被揭示,实现了一种相对超越的审美意味。这是基于不同主题的传达对素材做出的调整。这类关于妻妾之间勾心斗角、争风吃醋的故事古往今来并不少见。鸳鸯蝴蝶派小说控诉封建文化对女性身心的迫害,在“五四”时期与反封建的题旨捆绑在一起,呼吁女性的自由解放。而小说《妻妾成群》则选择深入到女性内心的独特感受中去探寻文化氛围对人的意识状态和行为方式的影响。反观张艺谋的《大红灯笼高高挂》,却是重蹈鸳蝴、承继“五四”的意味更浓一些。
(二)对故事的叙述
从内聚焦向零聚焦叙事的转变。原著小说《妻妾成群》以主人公颂莲的视角展开,环顾陈家大院里的矛盾、冲突、敌意、渴望、冲动与呐喊,故事的展开尽量控制在颂莲的感知范围内,通过主人公的心理状态直达意识的最深层次,从而获得透视女性心理的效果。比如,颂莲第一次靠近井边时:
“走到井边,井台石壁上长满了青苔。颂莲弯腰朝井中看,井水是蓝黑色的,水面上也浮着陈年的落叶。颂莲看着自己的脸在水中闪烁不定,听见自己的喘息声被吸入井中放大了,沉闷而微弱。有一阵风吹过来,把颂莲的裙子吹得如同飞鸟。颂莲这时感到一种坚硬的凉意,像石头一样慢慢敲她的身体”。
苏童的描写从女性视角出发,他的笔触带有一种阴柔之气,细腻又敏感,借身边的意象感知人物的主体状态,生发出笼罩着阴云的诗意。颂莲第一次靠近井边似乎就被井中弥漫的死亡气息所吞噬。起先,紫藤架下蝴蝶飞过的惬意让她想起往日的校园时光,而这些代表着人自然天性中的美好、生命的纯真、青春活力的惬意之感,都在逐渐靠近井边的时候被一股坚硬的凉意所泯灭。在张艺谋的《大红灯笼高高挂》中,导演将第三人称的女性视角转换为上帝视角,让摄影机凌驾于人物之上。虽然影片也多次出现以颂莲的视角环顾陈家大院、望向远处的“死人屋”的镜头,但却时时以俯拍、固定长镜头的形式将“规矩”的陈家大院包裹在镜头之内,蓝灰色的陈家大院与整齐排列的灯笼所造成的强烈的明暗对比,给人以压抑困顿的恐慌感,镜头仿佛似上帝视角冷静地审视着被封建伦理纲常所固化着的陈家大院对女人们犯下的罪孽。“动词意味着行动,影像却展示行动”⑥,对心理活动的描写亦是如此。“坚硬的凉意”的不可传达性只能通过陈家大院高耸的青灰色墙壁,以及用唯一一个开放空间却是死人屋的叙事设定来传达一种难以逃脱的宿命感。
讲述一个以戏剧性为核心的故事,展现一场以民俗仪式为核心的影像奇观,是导演的主要目的。电影把小说中妻妾之间的冲突变成了五太太颂莲与其他几位太太之间的勾心斗角,并弱化了男性角色的叙述功能。陈佐千与飞浦更像是分别代表着封建势力与新兴力量的符号,没有任何感情流露。小说中的颂莲更像是一个不小心卷入纷争的闯入者,她既困顿、恐惧、挣扎,又嫉妒,但是这份心情并不是通过强烈的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展现出来,而是人与环境、人与自我。而在电影中,颂莲在受到雁儿的嘲讽、卓云的暗算、老爷的冷落以后,主动选择加入这场斗争中,假怀孕、让雁儿跪在雪地里导致了她的死亡,酒后泄露了梅珊与医生的私情。梅珊死后,她装神扮鬼报复陈家。电影中的颂莲更具有主动性,也增强了故事的戏剧性。
除了通过故事来增强故事的可观赏性,影片中的民俗仪式无论对中国观众还是国外观众来说,都是一场旧时代中国的民俗奇观。红灯笼是身份和地位的标志,红灯笼挂到哪里,哪位太太就可以得到老爷的恩宠。怀了身孕就可以点长明灯,犯了错误就要被永久封灯,点灯、灭灯、封灯成为陈家封建伦理纲常的执行规则。而捶脚既是一种奖赏,也是为了促进男女之间的情事,“女人的脚最要紧,脚舒服了,就什么都调理顺了,也就更会伺候男人了”。点灯与捶脚关乎陈家大院里女人们的命运沉浮,与叙述形成紧密的勾连,增强了影像的奇观色彩。除此之外,“捶脚与点灯既是性的指示,又是性的掩饰;既避免了在银幕上出现赤裸裸的场面,同时又不失含蓄地产生更强烈的刺激性与诱惑力”⑦。
三、结语
张艺谋携一场造型革命创造了中国电影史上不容忽视的神话。摄影师出身的张艺谋与20世纪80年代中期这场文学革命的相遇是文学与电影因缘际会最成功的标志。借由文学“本体”观念觉醒的启蒙,张艺谋将书面叙事转化为影像叙事,并用强烈的造型意识来凸显小说中对知觉的细腻刻画。张艺谋电影的横空出世,他本人形式主义大师的身份标识,与他的摄影师出身、中国电影观念的更新、80年代中期的文学革命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由此,张艺谋神话是创造的,更是被创造的。
注释:
①方贤绪.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和80年代小说研究[D].苏州:苏州大学,2003.
②[美]苏珊·朗格.艺术问题[M].滕守尧,朱疆源 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24.
③王志敏.现代电影美学基础[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6:162.
④⑥ [法]弗朗西斯·瓦努瓦.书面叙事·电影叙事[M].王文融 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47,74.
⑤⑦陈墨.张艺谋电影论[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5:118,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