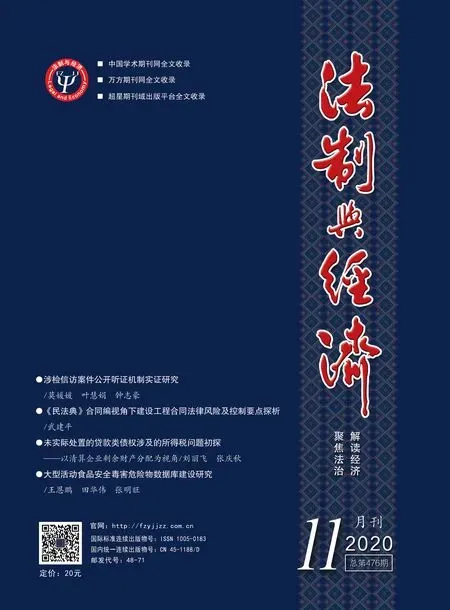惩罚性违约金的合理性探究与限制
2020-02-24刘成
刘 成
(江苏宏亮律师事务所,江苏 宿迁223800)
现行《合同法》和《民法典》中的违约金条款虽然没有明确禁止违约金的惩罚性功能,但显然在强调违约金的补偿性,突出对违约金条款惩罚性的限制。虽然有观点认为最高法所发的《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对违约金的类型划分为补偿性违约金和赔偿性违约金,但根据《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九条的适用,除非合同具备继续履行的可能,否则违约金条款产生的赔偿数额必然小于守约方以损害赔偿数额,即守约方在此种情形下无法通过违约金条款实现实际损失的全部救济。这也间接体现现行法限制守约方解除合同,鼓励合同有效、交易成立的立法目的。当原有合同难以继续履行,或者继续履行明显减损守约方利益时,守约方只能通过损害赔偿条款实现“止损”,实际上由于举证存在不充足的情形,损害赔偿请求受支持的数额在事实上大概率小于实际发生的损失。又因为间接利益在司法实践中不具有理论基础,所以现行违约金制度中的规定从形式上限制了守约方的合理期待利益,也难以在实践中填平守约方的损失,由此导致债务人虽然需要支付一定比例的违约金,但与合同利益本身在数量上并不匹配,不足以迫使债务人履行合同。
一、惩罚性违约金的性质认定
在1999年《合同法》诞生前的学理讨论中有观点支持违约金的担保属性。①当前学理通说认为违约金属于“损害赔偿的特殊形式”,其本质属于违约责任的范畴。也有观点认为违约金具有双重属性,即兼具补偿性和惩罚性。②但在惩罚性的判断标准上存在分歧。“损失比较说”认为,惩罚性应以约定的违约金数额是否超过实际损失为标准。③“责任并行说”认为,违约金是损害赔偿与担保功能的叠加。④
本文认为将违约金定性为“损害额赔偿的特殊形式”在司法实践中具有一定的促进意义,尤其对于普通民事主体和不规范的商事主体而言,在现实的案件中存在大量因证据不足而难以得到支持的案件,通过违约金条款简化债权人的举证责任,有利于实现对债权人的司法救济。但现行的违约金制度由于不承认惩罚性,又有违约金高于30%可以核减的限制,所以通过违约金条款的救济是有限的,难以实现对债权人主要损失的填平。
“损失比较说”解决了对债权人的救济与遭受损失间的不平衡问题。这种观点强调惩罚性违约金名不副实,应直接称为违约金。“惩罚”体现出来的是一种罪责,是社会伦理判断的价值范畴,而违约行为本身是一种普通的民商事行为,不具有道德层面的指责性。在违约金责任中,过错仅是归责要件,且违约金数额的大小与过错不具有直接的关联性,所以违约金责任与“惩罚”所体现出的理念是不匹配的。该观点认为当违约金数额超过实际损害时表现出惩罚性,在此情形下。债权人主张违约金后不具有损害赔偿的请求权;当违约金数额低于实际损害时表现为特殊形式的损害赔偿,债权人主张违约金后可以在扣除违约金范围内继续拥有损害赔偿请求权。本文认为,该观点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在事实层面承认了“惩罚性”违约金的存在,但该观点与现行司法实践中核减规则不匹配。若忽略现行司法解释所体现出的核减精神,又显然过分加重了债务人的负担,难以预防恶意利用违约金条款。此外,词语的语义是随着时代变迁会发生变化的,仅仅因为“惩罚”所体现出的道德性评价就否认其在经济交往中的价值并不妥当。即使认为商事主体的成立是为了纯粹利益行为,也不应认为商事主体就可以不考虑任何道德因素,忽视诚实信用原则不利于市场经济的长期稳定。虽然法律与道德当然应当具有明显的区别,但在公序良俗原则作为基本原则进入民法体系的背景下,不应忽视法的道德性,以及法律所体现出的社会引导价值。在特定的情形下,将经济交往中的违反商业伦理的行为进行道德上的否定评价具有合理性。
本文基本认同“责任并行说”的观点,但也同时认为应当对该理论进行限制性的修正。根据这种理论,损害赔偿和惩罚性违约金具有各自独立的请求权,即在适格主体约定明确的情况下,可以同时主张基于损失填补的损害赔偿和基于担保功能的惩罚性赔偿,但本文也同时认为,惩罚性违约金应是有限度的担保权能,通过惩罚性违约金获得赔偿应在法律的严格限制内。
二、惩罚性违约金适用的合理性分析
(一)基于意思自治产生的惩罚性违约金未违背公平原则
有学者提出,民法上的公平体现在使人得其所得的意愿得以最大程度地实现。从实质上说,民法的公平应是强调当事人双方承担对等的权利与义务,并且双方对这种分配方式均予以认可。在实践中,违约金责任往往是当事人对等约定的,所以违约金赔偿的数额从形式上大于实际的损失打破了当事人之间的平衡关系,违背了民法的填平规则,但这种形式的不平等不是臆造出来的,是基于当事人之间意思自治而产生的。违约金条款设立时,当事人已经就履行能力、期待利益等因素进行了综合的衡量,不能因为有限的惩罚性就否认民事主体对利益与责任权衡后认可的承诺。
当事人的缔约能力在事实上存在差异,高额的惩罚性违约金可能导致一方为了利用惩罚性违约金条款获得利益而恶意引诱对方违约。⑤现有的民法体系经过发展与完善,已经建立起比较完备的“显示公平制度”“格式条款制度”,过分加重过失违约方的责任的目的难以实现。而且,这种非现实的给付在缔约时是缔约者可以明确认识的内容,缔约后又以身处弱势一方而要求进行区别救济有违诚实信用原则。
(二)现行民法体系中相关概念的类比分析
反对惩罚性违约金的理论中有一个重要的观点是,民法上的救济应倾向于填平受害者的损失,而非惩罚。《民法总则》第179条对原有的民事责任承担方式就法定的惩罚性赔偿作出突破,这表明在立法中也已经修正了原有的“特殊形式损害赔偿”。王利明教授在理论探讨中曾指出,民法典的合同编应当结合违约金的多种功能,突破既有的补偿性,对违约金规则进行调整。这一学术观点虽然没有被《民法典》采纳,但总则编的立法倾向为约定惩罚性赔偿的发展提供了进一步的理论支撑。
(三)惩罚性违约金的本质在于担保权能
无论采用何标准,惩罚性违约金必然需要通过向违约方施加超额赔偿责任来实现。⑥这也是基于“填平原则”的理论反对违约金具有惩罚性的基本观点。本文认为,将违约金解释为特殊形式的损害赔偿当然具有合理性,问题在于违约金的内涵本身即是丰富的,不应将其仅限定在这一种特定的形式,即在约定明确的条件下惩罚性违约金具有担保权能。从违约金制度设立的历史环境和法律制度出发,其最初的功能就是侧重于债权实现的担保。⑦在实践中,当事人为了确保合同的实际履行效果而自愿缔结具有“对赌”性质的惩罚性条款,以此实现对债权的担保。从担保权能的性质分析,惩罚性违约金与定金制度,以及目前已被原则性认为有效的“对赌协议”并无本质区别,基于法律家长主义认为民事主体自愿作出的真实意思表示因未能充分预料风险而认定无效。显然违背了体系解释的要求,也不利于债权的实现。
三、惩罚性违约金的适用具有有限性
惩罚性违约金的适用并非没有限制的适用。本文认同“填平原则”是民事责任的基本要求,但也同时认为此处的民事责任应理解为狭义的与“商法”相对应的“民法”责任。我国虽然采用民商合一的法律体系,但民法的价值取向是公平,而商法的价值取向是效益。这种价值取向既体现出“填平原则”在狭义“民法”中的合理性,也体现其在“商法”领域运用的不合理。商主体作为一种特殊的民事主体,其活动本身即是以营利为目标的,这就决定了商主体比民主体具有更强的市场参与、风险预估和承担能力,因此当商主体基于自身的承受能力而作出的成熟决定应当予以尊重。
此外,惩罚性违约金适用的另一个重要前提是违约方有过错意思。合同责任的承担一般以无过错原则,补偿性违约金并不考量违约方的主观要素,而惩罚性违约金的主要目的在于通过惩罚和制裁的方式来担保合同的履行,这就要求违约方的行为首先应具有可惩罚性,即违约方的主观过错程度较高、恶意违约。在倡导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的社会背景下,如果相对人无奈违约与恶意违约所面临的责任成本是一致的,也显然不利于良好社会秩序的引导。
惩罚性违约金的适用应考量合同履行情况。惩罚性违约金设立的目的即是为了督促债务人积极履行合同,但在订立合同时,除合同当事人就合同履行中可能出现的情形订立部分违约条款外,当事人也难以全面准确预测违约情况。如果合同已经履行了主要的合同义务,最后违约方需要承担的违约责任却与未履行或只履行部分非主要合同的责任承担一致,显然缺乏合理性,也可能错误引导债务人拒绝履行合同。所以在适用惩罚性违约金条款时,应限制为违约方未履行主要的合同义务。
四、结语
违约金具有赔偿功能和以惩罚性违约金形式所体现的担保功能,现行法突出强调违约金的损害赔偿,忽略了担保职能的价值。当事人基于意思自由订立的惩罚性违约金,没有破坏公平原则,不应受到司法的直接否认,有必要确立惩罚性违约金的合理地位。当然,惩罚性违约金在司法适用中还应考量合同主体、过错程度和合同履行情况等因素。
注释
①郑立,姚辉.论违约金的担保属性[J].法律学习与研究,1990(6)。
②姚明斌.违约金双重功能论[J].清华法学,2016(5)。
③沈德咏,奚晓明主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理解与适用[M].人民法院出版社,2009:209。
④韩强.违约金担保功能的异化与回归——以对违约金类型的考察为中心[J].司法商研究,2015(3)。
⑤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负责人就《关于当前形式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答记者问(2009年7月16日)。
⑥王洪亮.违约金功能定位的反思[J].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4(2)。
⑦[意]彼得罗·彭梵得.罗马法教科书[M].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2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