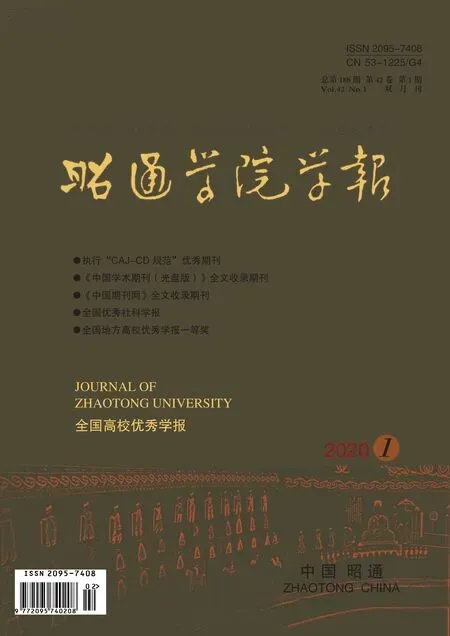莱蒙托夫的拿破仑组诗
2020-02-24姚荧
姚 荧
(云南民族大学 文学与传媒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在显示出一个作家作品中某些‘外国来源’时,最起码的收获应该是能使人更了解这个作家。比如能体现他的一些爱好,这在某种意义上说也就等于描述他本人了。”[1]64国内外关于拜伦、普希金对莱蒙托夫创作的影响研究已有创获。但关于三位作家笔下的拿破仑形象的异同及其原因的研究较少。文中所述的拿破仑组诗是以拿破仑·波拿巴为题材的诗歌。三人的拿破仑组诗同中有异,相同之处表征他们相似的理想志趣,不同之处彰显他们相异的文化传统、历史语境与个人境遇。
一、莱蒙托夫的“先见”:拜伦与普希金的拿破仑组诗
莱蒙托夫对拿破仑的“先见”之一来自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拜伦。拜伦的拿破仑组诗包括《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第一章(1809)第三十一节至第九十节、《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第三章(1816)第十七节至第二十节、第三十六至四十二节、《拿破仑颂》(1814)、《拿破仑的告别》(1815)、《译自法文的颂诗》(又名《滑铁卢颂》)(1816.03)、《青铜世纪》(1822-1823)。
拜伦在《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中表露了他对英国与拿破仑武装干涉西班牙民族解放运动的否定态度。他对拿破仑的态度比较复杂。潘耀瑔指出,一方面,拜伦视拿破仑为“暴君”“高卢的兀鹰”“野心的头子”,另一方面,诗人又视拿破仑为“超人”“盖世英雄”。[2]
拜伦在《拿破仑颂》(1814)中感慨拿破仑被迫退位并被流放至厄尔巴岛,将他与古今众多君王进行对比。诗人认为拿破仑的结局不如独裁后返回田庄的罗马执政官苏拉及让位后苦修的西班牙王查理五世。且他本可以像华盛顿一样仅任首任总统,但独裁野心使他践踏了人民的自由,也篡改了他原本可以遗留在历史的光辉形象。《拿破仑的告别》(1815)写于拿破仑“百日王朝”崩溃后被流放到圣赫勒拿岛时。拜伦以拿破仑口吻宣示“无论如何,我的声名却填满她最光辉或最龌龊的故事的一页”。他的赫赫战功使法兰西一时为世界瞩目,“尽管锁链缚住了我们,但有些环必能打破”,他向世界播撒的自由种子定会使人们在“自由再次跃升”、召唤新首领“那时记着我”。[3]65
拜伦在《译自法文的颂诗》(又名《滑铁卢颂》)(1816.03)中摆脱了个人英雄崇拜,不再诅咒使拿破仑覆没的“滑铁卢战役”,因为他坚信“血尽管洒了,却没有白遗弃——它又从每个充血的躯干升起”。虽然拿破仑“受野心怂恿”,但法兰西人民的“安全并不在于哪个卡倍或拿破仑的王座!而是需要平等的权利和法律”,“她需要自由,就是上天从人出生的那一天,连同呼吸赐予他的权利”。尽管拿破仑战败了,但不意味着后继无人,相反,“自由也何曾没有后继”,“她的大军一旦再揭竿而起,那些暴君敢不相信和颤栗?”拜伦拥护的是人民的自由而非帝王、英雄,反对的是独裁与暴政,因而他能辨证地看待拿破仑的功过荣辱。在《青铜世纪》(或名《世事的歌及平凡的一年》)中,拜伦将拿破仑等革命力量视为阿基里斯,并认为反动势力“并非阿基里斯的敌手”。
拜伦笔下的拿破仑形象是不断变化的。起初拿破仑之被理想化,是由于“拜伦和同时代的进步人士一样,把青年波拿巴视为法国革命军队解放传统的继承人。”[4]95拿破仑加冕称帝后拜伦的态度发生转变。他认为拿破仑帝国与复辟的波旁王朝一样无视人民利益。但拿破仑去世后,欧洲封建势力抬头,拜伦又重新推崇青年拿破仑。拜伦至始至终崇尚的并非拿破仑,而是其所代表的为民主、自由、平等而战的革命精神。当拿破仑与之相合时,他便颂扬他;当拿破仑与之相离时,拜伦便批判他;当时局需要它时,他便以拿破仑来唤醒民众。
莱蒙托夫对拿破仑的另一“先见”源自“俄罗斯诗歌的太阳”——普希金。普希金的拿破仑组诗包括《皇村回忆》(1814)、《厄尔巴岛上的拿破仑》(1815)、《自由颂》(1817)、《拿破仑》(1821)、《“沙皇门前的静止的守卫睡了”》(1824)、《“你负着什么使命”》(1824)、《致大海》(1824)、《英雄》(1830)、《“想从前”》(1836)。
普希金早年受强烈的爱国主义影响,对拿破仑的评析带有浓郁的激愤情绪。在《皇村回忆》(1814)中,青年普希金写道:“莫斯科啊,亲爱的乡土!……鲜血染红了你,火焰也曾把你吞没,/而我却没有牺牲性命为你复仇,/只枉然充满着愤怒的火!/”[5]50事实上,焦土政策是俄军主动采取的军事措施,并非拿破仑蓄意谋划。普希金的《厄尔巴岛上的拿破仑》(1815)与拜伦的《拿破仑颂》(1814)一样,书写的是拿破仑被迫退位并被流放厄尔巴岛的情形,他们都认为欲望之火毁灭了拿破仑。普希金此诗又与拜伦的另一首诗《拿破仑的告别》(1815)一样,都以拿破仑口吻行诗,不同的是,拜伦塑造的是在欧洲传播自由思想的拿破仑形象,普希金塑造的却是沮丧、孤独的“灾星”形象。此外,普希金的《自由颂》(1817)与拜伦的《译自法文的颂诗》(又名《滑铁卢颂》)(1816.03)都提出公民需要“强大的法理”和“神圣的自由”的庇护,但普希金认为处死路易十六僭越了法理,批评拿破仑逾越法理、施行独裁专政。而且不同于拜伦的是,普希金拥护君主立宪制,认为“人民的自由和安宁/才是皇座的永远的守卫。”
普希金在拿破仑死后开始反思他的历史意义,如《拿破仑》(1821)中“在你的骨灰安歇的瓮上,/人民的憎恨也随着熄了,/而你将闪着不朽的光芒。”他还在篇末写道:“赞扬吧!他给俄罗斯人民/指出了崇高的命运,/在幽暗的流放里,他死了,/却把永恒的自由遗给世人。”在南方流放时期,他还在《“沙皇门前的静止的守卫睡了”》(1824)中指责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专制,歌颂曾使沙皇屈首的“盖世之雄”拿破仑。在《致大海》(1824)中,普希金歌颂拜伦与拿破仑为自由而战的精神。
《“你负着什么使命”》(1824)一诗预示了普希金对拿破仑形象哲理性的思索:“善或恶,你是哪个忠诚的使者?”[6]9《英雄》(1830)的副标题是“真理是什么?”该诗以友人与诗人的对答布局,似理智与情感的双重对话,它似乎源于普希金内心两种矛盾的声音。普希金以“英雄”为题是为了重新阐释 “英雄”的定义:他认为体恤下士、与黑死病患握手的拿破仑比叱咤战场的他更具有英雄气度。并且他认为“崇高的欺骗,/胜过卑劣的真理的幽暗……”
对拿破仑态度的变迁折射出普希金从激情、沉静到超然物外的思想历程,揭示出他的多重身份:俄国人、历史学家、诗人和哲人。[7]15普希金的拿破仑组诗不同于拜伦,源于他的俄国文化传统与十二月党人身份。他对拿破仑的看法由入侵者、践踏法理的独裁者转向“自由”的化身、给俄罗斯人民指出崇高命运的“英雄”。
二、莱蒙托夫笔下的拿破仑形象:无视荣辱、心切未竟事业
正如莱蒙托夫在《不,我不是拜伦,是另一个》中所言“不,我不是拜伦,是另一个/天职在肩但还无人知的诗人,/如同他,我也是尘世的逐客,/不过我有一颗俄罗斯的心。”[8]44莱蒙托夫与拜伦一样被政府驱逐,但他意识到他们面临着不同的国情与历史环境,肩负着不同的职责。
莱蒙托夫的拿破仑组诗包括《拿破仑》(波浪冲击着高高的海岸)(1829)、《致……》(不要说:我在人世之上)(1830)、《拿破仑》(当蓝蓝的迷雾弥漫在海面)(1830)、《波罗金诺战场》(1830-1831)、《两个巨人》(1832)、《波罗金诺》(1837)。
莱蒙托夫似乎从普希金诗歌《厄尔巴岛上的拿破仑》中汲取灵感,借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上的灵魂之口表露其遭流放的心绪。在《拿破仑》(波浪冲击着高高的海岸)(1829)中既描述了一位“高尚而年轻的诗人”[9]60在圣赫勒拿岛上大肆评判拿破仑的功利心、好战、蔑视友谊与爱情、在岛上的自责与惨遭遗忘的命运,也描述了寄希望于后代继承其激情事业、“鄙夷那高声喝彩的歌颂”的拿破仑幽灵形象。前者代表了大多数人,也许涵盖拜伦、普希金等探讨拿破仑是非功过的诗人,但莱蒙托夫认为他们都是“高尚而年轻的诗人”,这些诗人令人尊敬却并不成熟。拿破仑阴魂的呐喊显示了莱蒙托夫的真实立场,他认为英雄拿破仑不在意后人的嘉奖或指责,却时刻关注着未竟的法国大革命事业。《致……》(不要说:我在人世之上)(1830)一诗与之一脉相承,该诗拟拿破仑口吻控诉时人:“不要说:我在人世之上/单单受崇高事业的激励……相信吧:人世间的伟大/与人们的想法截然相反/一桩恶行你干成了——伟人;没有成——坏蛋;/”[9]109莱蒙托夫此诗像普希金的诗歌《英雄》(1830)一样,重审世人的评判准则——成王败寇。莱蒙托夫认为时人对拿破仑的负面评价多源于拿破仑的失败结局。
《拿破仑》(当蓝蓝的迷雾弥漫在海面)(1830)一诗塑造了昼夜间双手交叉立于圣赫勒拿岛,遗忘帝王权杖、忧虑注视祖国的拿破仑幽灵形象。《拿破仑的墓志铭》(1830)一诗表露了诗人对拿破仑的看法:“懂得高抬你的人才能把你推倒:/但伟大却是谁也改变不了。”[9]154
莱蒙托夫在《圣赫勒拿岛》(1831)诗中痛斥复辟的法国专制政体:“那罪恶的国家还不配让/伟人将生命在国内结束。”而拿破仑“虽然被击败了,仍不失为英雄!”
《飞船》(1840)一诗具有典型的浪漫主义色彩——奇幻的想象。莱蒙托夫在诗中幻想拿破仑撑着飞船返回祖国,但他挚爱的精兵已葬身“刀山火海”,得力的元帅或阵亡或背叛倒戈,心爱的儿子早已凋残,他痛苦地踏上船重返孤岛。瑰丽想象与残酷现实融汇于一诗,带来无尽的悲怆。莱蒙托夫在诗中揭示了拿破仑完全丧失卷土重来可能性的现实,表露出对拿破仑的惋惜之情。
《最后的新居》(1841年)与《圣赫勒拿岛》(1831)的基调一致,莱蒙托夫对法兰西在拿破仑去世九年后从圣赫勒拿岛接回其尸骨并为之自鸣得意的举动嗤之以鼻。因为“人间所有伟大、神圣的一切、一切,/都遭到你们饱含稚气的怀疑的/愚蠢嘲笑的践踏和轻蔑。”他批判复辟的专制政权和愚昧的人民“摇撼被他选择的政权像释负那样”,他抨击人民背信弃义“他把亲生儿子留给你们当人质——/你们却把他交给了敌人!”而如今,法兰西轻狂的子孙恬不知耻地索要当年被他们抛弃的伟人尸骨。诗人遥想,渴求自由奋争的拿破仑面对新坟应会怀想那片 “和他一样伟大而不可战胜的大海!”
以上是莱蒙托夫对拿破仑进行正面描写的诗歌,下面是莱蒙托夫对拿破仑进行侧面描写的诗歌。它们都是以波罗金诺战役为主题的诗歌,包括《波罗金诺战场》(1830-1831)、《两个巨人》(1832)、《波罗金诺》(1837)。波罗金诺战役意义重大。拿破仑曾表露:“人们批评我没有死在滑铁卢,”他在圣赫勒拿岛上说,“我想我更应该死在莫斯科会战。”[10]737莱蒙托夫创作这些诗歌意在彰扬俄罗斯人民在外敌入侵时的英勇捍卫,也意在激励子孙保留民族精神与爱国热情。
莱蒙托夫在《波罗金诺战场》(1830-1831)中以参战老兵的口吻复现了波罗金诺战役的情形:俄军士兵为自由而战,宁愿“战死在莫斯科城下”也不脱逃,却不禁怀想起往昔挫败土耳其士兵的胜绩,因为“这里有的只是悲观绝望”。所幸的是“降临了一个寒冷的夜晚/……此刻敌人便撤退;/但这一天的代价更昂贵!”尽管损失惨重,但他认为“波罗金诺名声更显赫,/盖过波尔塔瓦、雷尼克/……不让它在北国子孙的/记忆中一旦磨灭。”莱蒙托夫认为法俄双方在波罗金诺战役都损失惨重,这付出昂贵代价的“胜利”值得后世子孙铭记。
莱蒙托夫汲取民歌元素,在《两个巨人》(1832)中以拟人手法描绘卫国战争的情景。一个是“年老的俄国巨人”,一个是异邦的“巨人”。战前“他俩都想用头颅,/决一雌雄拼一场。”但“三星期的勇士”“举起莽撞的手臂/便抓对手的冠冕。”不料 “俄罗斯勇士”“头一摇”,“狂夫惨叫——便摔倒!”莱蒙托夫在诗中调侃了法军的莽撞。
莱蒙托夫在《波罗金诺》(1837)中借波罗金诺战役老兵之口,道出他对当代子孙的不满:“是啊,我们那时候的人,/和现在这辈人不同,是好汉,/不是你们这样的脓包!/他们碰上了艰难的命运,/从战场回来的没有多少……/要不是上帝有这种旨意,/哪能把莫斯科扔掉!”在该诗中,莱蒙托夫赞扬了誓死捍卫首都的战士,他们虽未守住莫斯科,却不畏缩逃跑。
莱蒙托夫创作这三首诗歌,是对时人重视滑铁卢战役、忽略波罗金诺会战的一种反驳。莱蒙托夫认为俄罗斯人民在波罗金诺战役上的英勇奋战打击了拿破仑在欧洲的殖民扩张,却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但莱蒙托夫与普希金一样,反对成王败寇的评价准则。拿破仑在俄国乃至欧洲战场的溃败并不损害他在莱蒙托夫心中的光辉形象。
总之,莱蒙托夫不再像拜伦、普希金一样在诗歌中议论拿破仑个人的功过得失与荣辱成败,他关注的焦点转向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的心境及1840年法国迎回遗留于该岛的圣贤灵柩事件。莱蒙托夫在诗歌中开始将复辟的专制政体的法兰西与拿破仑分开评判,拿破仑被视为法兰西乃至欧洲复辟封建势力的迫害对象。诗人叱责的对象转变为破坏自由精神的邪恶力量。在艺术手法中,浪漫主义式的奇异想象使莱蒙托夫的诗歌异彩纷呈。
三 、莱蒙托夫的创作意图
莱蒙托夫的拿破仑组诗受到文化传统、历史语境、个人境遇的三重影响,这三重影响常交织在一起。莱蒙托夫笔下的拿破仑是思想与情感的共同产物,它源于拜伦与普希金,并与象征反叛的恶魔精神汇合,一同激励莱蒙托夫与俄国当时落后的农奴制、封建专制制度作斗争。
莱蒙托夫的拿破仑组诗受到文化传统的影响。楼均信认为法国大革命可分为开始、发展、高峰、转折、最后五个阶段。拿破仑统治阶段为法国大革命的最后阶段,以1814年拿破仑帝国的灭亡作为终点。[11]5在传统文化中,不论是拜伦还是普希金,拿破仑都曾被视作法国大革命成果的巩固者与发展者,莱蒙托夫也延续了这一传统认知。《拿破仑》(波浪冲击着高高的海岸)(1829)中塑造的是不在意世人褒贬、只期望后世实现其未竟事业的拿破仑形象。莱蒙托夫还在《圣赫勒拿岛》(1831)、《最后的新居》(1841年)中表露对践踏法国大革命成果的复辟波旁王朝的憎恶。在他看来,波旁王朝统治下的法兰西国土甚至不配安葬伟人的尸骨。
拜伦、普希金都曾在诗中痛斥毁灭拿破仑的独裁野心。可贵的是,莱蒙托夫能超越这一传统认知,不再探讨拿破仑的是非功过。安德鲁·罗伯茨认为,1804年拿破仑自封为“法兰西共和国皇帝”,它看似矛盾却切实刻画了其统治特征。拿破仑维护了法国大革命的成果,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理性政府、精英政权,丢弃了至上崇拜、共和国衰亡时出现的腐败、任人唯亲与超级通货膨胀。[10]985也就是说,拿破仑称帝却并未妨碍他对法国大革命成果的巩固与发展,拿破仑的独裁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时势所趋。
普希金曾斥责拿破仑1812年对俄发动战争。虽然莱蒙托夫也创作了三首以波罗金诺为题材的诗歌,但他的创作动机与普希金不同,他是出于激励俄国后世保留民族精神与爱国热情的考虑。如今,拿破仑对俄宣战的原因得到进一步的解释。安德鲁·罗伯茨指出,拿破仑所受的常见批判——1812年入侵俄国,并非出于其统治世界的傲慢愿望,而是为了强迫沙皇实行五年前在蒂尔西特做出的实施经济封锁的承诺。[10]991普希金早年鲜明的民族立场使得他对1812年法俄战争的看法存在偏颇,莱蒙托夫却避开了文化传统可能带来的偏见。
莱蒙托夫的拿破仑组诗也受到历史语境的影响。莱蒙托夫处于俄国殖民主义扩张时期,他看清沙皇专制统治的实质,不似普希金对沙皇抱有幻想,也不受民族主义情绪左右。莱蒙托夫对拿破仑的看法与拿破仑的自述比较相符。拿破仑说过:“我是一个新的普罗米修斯。我被拴在一块石头上,一只秃鹰在吃着我的肉。不错,我曾从天上偷得火种,并把它作为一份嫁妆送给法兰西:火种已经回到原来的地方——我却留下来了……”[12]161莱蒙托夫深处于沙皇尼古拉一世的暴虐统治中,因而他尤其珍视拿破仑对法国大革命成果的维护。
法国大革命宣扬的自由平等、反封建专制思想通过拿破仑“远征”俄国,最先撼动俄国贵族进步青年的内心。涅奇金娜提出,十二月党人在欧洲国家立宪机构中获得可供思考的精神资源,开始反思俄国落后的农奴制生活方式。[13]161825年12月14日,十二月党人发动了反沙皇专制制度的起义,即十二月党人起义。十二月党人对普希金、莱蒙托夫都有深远的影响。
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爆发,波旁王朝被推翻。莱蒙托夫在该年不仅创作了4首拿破仑组诗,也创作了《预言》 《七月十日(一八三〇年)》《一八三〇年七月三十日(巴黎)》《诺夫哥罗德》、长诗《最后一个自由之子》等为法国七月革命呼号、为国内反专制斗争呐喊的诗歌。
《预言》中诗人大胆预言沙皇黑暗统治将被强有力如拿破仑一般的人物推翻。《七月十日(一八三〇年)》中莱蒙托夫以七月革命为契机,为波兰、阿尔巴尼亚民族争取民族解放、国家独立、反对君主专制制度的运动呐喊呼号。《一八三〇年七月三十日(巴黎)》中他以七月革命后仓皇出逃的查理十世影射“沙皇”,诗人相信暴君终将偿还人民血债,历史罪人终将受到公正裁决,自由的旗帜终将迎风飘展。《诺夫哥罗德》中洋溢着反暴政思想,诺夫哥罗德是十二月党人心中使暴君颤栗、象征自由的沃土。长诗《最后一个自由之子》通过英雄为自由献身的传说颂扬十二月党人为自由牺牲的事迹。
莱蒙托夫的拿破仑组诗还受到个人境遇的影响。顾蕴璞先生提出,莱蒙托夫是沙皇尼古拉一世和俄国上流社会的叛逆者,他一生的创作大都贯穿着恶魔这一主导形象,洋溢着叛逆这一“莱蒙托夫原素”(别林斯基语)。[9]19十二月党人起义与普加乔夫农民起义,拿破仑、法国大革命与七月革命,各民族解放运动与叛逆的恶魔形象都是莱蒙托夫创作的重要题材,它们都浸透着诗人反农奴制、反专制、反侵略的思想,并与卢梭、孟德斯鸠、狄德罗的启蒙思想一同汇入莱蒙托夫的诗歌。涅奇金娜认为,西欧人人生而平等、一切封建特权必须消灭的思想加速了俄国解放思想的发展,它们共同对抗天赋君王恣意宰割臣民特权的谬论。并且人的理智和正确教育至高无上的思想与封建宗教、神秘主义、迷信展开了搏斗。[13]15启蒙思想使莱蒙托夫笔下的拿破仑形象富于乌托邦色彩。
总之,莱蒙托夫在审视与想象“他者”——拿破仑时,也对俄国进行审视与反思。诗歌中的拿破仑形象融合了主观与客观、情感与思想。他意在以此表达自己向往的自由、平等、民主的社会范式,它是注视者——莱蒙托夫在文化、历史、个人语境下与被注视者——拿破仑、法兰西文化交流互动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