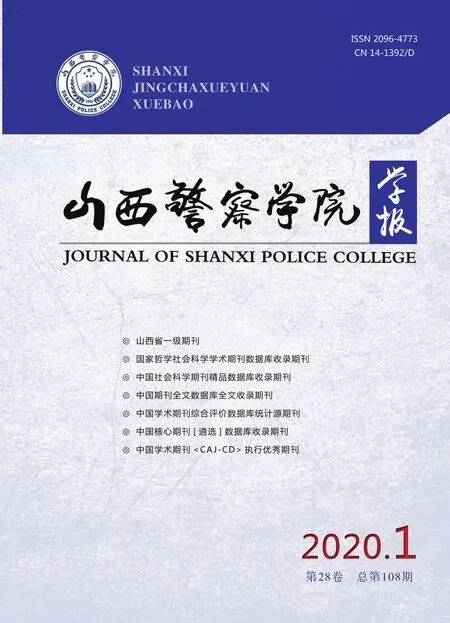人道主义干涉的合法性研究
2020-02-22王彦鹏
□王彦鹏
(中国人民警察大学,河北 廊坊 065000)
自冷战结束以来,国际维和行动已经由传统维和(traditional peacekeeping)转化为多维维和(multi-dimensional peacekeeping),冲突由最开始的国家之间的冲突(international conflict)转化到国内冲突(intra-national conflict)。因此,国际社会对于冲突的调节层面也从国家之间逐渐转移到国家内部各党派之间。其中建立于保护人权基础上的人道主义干涉在调节国家内部矛盾,保护冲突国国内人权的过程中会牵扯到冲突国自身的主权问题。人道主义干涉是由国际社会中的主权国家实施的以保护人权为目的的干涉行为,其存在的环境是国际社会。国际社会不是一个无序的环境,其内部存在着诸多规则,不过这些规则不是基于联合国或者某一个超国家组织强行制定的规则,而是各个国家之间由于习惯、惯例而形成的规则。但是这些规则的合法性却无法被国际社会一致认可。国际社会针对规则的合法性是基于一种假设:即对合法性的检验是国家实践。然而,国际社会在实践后发现很多规则是不合法的或者即使合法却对受害者造成更大的伤害。因此,我们需要一种新的理念来评判合法性,而不仅仅通过实践来检验。尤其国际社会面临的是重大人道主义灾难时,更加需要判断是否应该进行人道主义干涉,以及干涉是否合法。
一、人道主义干涉的缘起以及定义
自19世纪以来,基于人道主义为理由参与他国内政事务一直是国际法领域内讨论的一个主题。最初将人道主义干涉的武力行为合理化的动机是道德因素,而不是政治因素。但是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冷战的结束,国家主权意识越来越明显。理想主义在国际联盟成立时期就逐渐显示出对国际社会的约束是有局限性的。[1]因此,其他主权国家仅仅出于人道主义的原因而去干涉他国内政,以达到抑制人道主义灾难的目的是难以实现的。所以国际社会应该建立一套政治上的“现实主义”审查方式来约束各个主权国家以人道主义为理由干预他国内政的审查体系。
第一个以人道主义为由明确干预他国内政的案例是在19世纪初的希腊独立战争期间。那时英国、法国和俄罗斯果断干预了纳瓦里诺的海军战争。[2]1823年,英国外交大臣乔治·坎宁宣称:“当一个国家反抗它的征服者时,这个国家不能被认为是暴徒,而是一个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3]约翰·穆勒在1859年发表文章写道“似乎不需要重新考虑不干涉外国的整个理论,如果可以说它至今还被认为是一个真正的道德问题。如果战争是侵略性的,而不是防御性的,那么它就像为了领土或收入而进入战争一样是犯罪的。因为把我们的想法强加给别人是逼迫行为,迫使他人顺从其他人的意志。一个文明国家与另一个文明国家,文明国家与野蛮人之间遵循相同的国际习俗和相同的国际道德规则,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4]穆勒干涉的理由是公开的帝国主义。首先,他认为与“野蛮人”互惠是没有希望的“互惠”。第二,野蛮人会从被征服中受益,例如罗马征服了高卢、西班牙、努米底亚和达契亚。然而穆勒的观点并不符合现代国际法,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国际法确立了主权平等原则,[5]对拥有主权的国家进行外部干预一般被认为是违法的。
我们要明确,人道主义干涉与人道主义制裁之间的区别。人道主义干涉的三要素实施者、手段、目的分别为:国际社会中的其他主权国家;军事行动等“武力”行为;减轻或者结束人道主义灾难。而人道主义制裁是以货物禁运、贸易禁止、禁止资源交换等途径来迫使人道主义灾难发生国的政府进行自我治理。因此,本文中讨论的人道主义干涉是涉及武力使用的、影响他国主权并且以缓解或者结束人道主义灾难为目的的国际行为,而不是温和的制裁。这种武力使用可能是维和部队的进入,[6]也可能是国际联盟例如非盟、欧盟、北约等派遣部队对于发生人道主义危机的主权国家进行的基于人道主义原因的干预。
二、国际社会的性质
在讨论人道主义干涉的合法性之前我们必须认清国际社会的性质,也就是说我们所熟知的国际社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国际社会。国际社会就好比一张棋盘,而每个主权国家就是跳棋的棋手,大家遵循着相同的规则。
查尔斯·曼宁(Charles Manning)首次把国际社会看作是有自身的约束规则的游戏。他认为“正在进行的外交过程实际上正如一场游戏,它有自己的规则,而且参与者也必须遵守这些规则。”正如“圣诞老人”一样,“圣诞老人”是“真实的”,可是这种真实是建立在我们都有使他的存在成为可能的共识。可是为什么要遵守这些规则呢,遵守这些规则又可以带来什么好处呢?在此,我们首先要明确的是国家不是行为者,只是一些框架,[7]这些框架限制国家中那些负责人做出某些行为。这些限制是规范性的,从而产生对于特定负责人的约束。所以说在国际上活跃的不是国家,而是国家框架内的人。根据罗伯特·B·西奥迪尼(Robert B.Cialdini)的著作《影响力》所述,人是一种社会动物,会对自己做出的承诺负责。那些曾宣誓为国家负责的外交家们会为了自己的承诺,为了自己的社会信誉以及国际信誉而去遵守规则。
既然国际社会中真正起作用的是各国的领导人,或者说外交官,这就会存在另外一个问题,这些人有没有意识到他们在遵守规则。皮耶·布赫迪厄(Pierre Bourdieu)认为“没有什么事情比一个高手的行为更自由同时受到更多限制”。[8]由皮耶·布赫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战略化理解可以引出三个暗示:第一,国家有意识地谋划其行为是有局限性的,并且每一次谋划行为都存在国家内负责人习惯性的惯例行为。第二,国际社会的参与者即使想重塑国际规则,也必须首先承认曾经的国际规则,无论如何只要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员就会受到国际规则的约束。第三,当在国际话语体系中出现冲突时,仲裁人是不确定的。在国家法律体系内,可以是法官,不过在国际话语体系中,联合国更多的是一个道德约束,而不存在一种法律约束,这也是国际法的脆弱所在。
三、人道主义干涉的国际合法性
人道主义干涉的弊端会在以下情况中尤为明显:在政府利用国家机器对付他的人民的地方,或者在国家崩溃进入法律真空状态的地方,国际社会要帮助该真空国家过渡到有法律的国家,因为国际社会秉持着“善”的概念。[9]雷蒙德·约翰·文森特把人的基本权利界定为“不受滥用暴力(侵犯的)人身安全和最低限度的生存权利。”[10]用迈克尔·沃尔兹(Michael Walzer)的话来说,国际社会是由一个规则智力的框架构成的,它使得主权国家能在其边境范围内保护“个人生命的价值和共同的自由。”那么由此推论,一个国家如果肆意地侵犯其公民的权利,那么该国家主权是否还应当受到尊重。如果该国主权不应该受到尊重,那么这很可能成为国际社会中的其他主权国家干预他国内政的挡箭牌。但是如果在此种情况下依旧过分尊重国家主权,我们应该寻求一种标准来判定,以避免出现卢旺达的悲剧。
人道主义干涉自身就是秩序性和道义性的矛盾集合体。迈克尔·沃尔兹(Michael Walzer)认为“道义不是单边行动的障碍,只要当时没有其他可行的选择,他就是正义的。”虽然人道主义干涉是正义的,但是却是破坏了国际秩序的,其所干涉的是国家的主权。法律是正义以及秩序的集合体。国内法由于主权的存在,可以同时满足秩序性以及道义性。由于国际社会诚如上文所述,是按照大家都默认遵守的习惯而形成的社会,其中不存在一个权威性的仲裁者。因此国际法是一种弱约束,更偏向道义约束,所以说当进行人道主义干涉的时候很难既在道义上满足国际法又在秩序上满足国际法。由于对控制单边的人道主义干涉时间的原则缺乏国际上的一致,国际社会中的其他主权国家将会依照自己的道德准则来行事。这就削弱了建立在主权、不干涉、不使用武力原则基础上的国际秩序。然而,若要禁止人道主义干涉,国际社会显然是无法放任人道主义危机不管的。
那么到底该如何界定人道主义干涉在国际上是否合法?笔者认为不满足一定条件的人道主义干涉是非法的。尽管在上文的“国际社会性质”一部分中提出了“使得公民的基本权益被侵占(丧失)的主权国家主权还是否应该被尊重”的问题,但是依据主权平等的原则,哪怕一个主权国家的公民的基本权益受到侵犯,但是主权国家依旧有主权。[11]国家的主权不仅仅体现在保护公民的基本权益上,在领土完整,经济发展以及国家安全等方面国家的主权都是有所体现的,不能仅仅因为公民的基本权益被侵犯就认为该国家的主权是不值得被尊重的。正如前文所述,国际社会是一个“自身有约束规则的游戏”,所以针对发生人道主义危机的国家直接进行干涉是存在不妥当因素的,比如说如何让国际的“游戏规则”认可干涉行为。在进行人道主义干涉的时候,被干涉国家由于处于战乱或者法律真空情况下,对干涉国家的文化、制度输出是没有任何抵抗力的,这在未来极有可能对于国际社会的平衡以及当地的发展造成负面影响。同时,世界上有能力进行人道主义干涉的国家数量有限,如果历次人道主义干涉都是这几个国家进行干涉,那么过多的意识植入是十分可怕的。
如何在不得不进行人道主义干涉时保持其国际上最大程度的合法性?应当明确,人道主义干涉的合法性是建立预防更大的人道主义灾难的基础上。笔者认为至少应该从四个方面来判定是否是人道主义干涉:第一,必须有一个正当理由,或者说在一个主权国家的边界内,发生了大规模的公民基本权利的被侵犯(丧失);第二,在试用其他手段无效之后,采取武力手段,武力的使用必须是最后的手段;第三,使用武力必须被证明有极大可能取得实际的人道主义结果,而不会适得其反;第四,比例原则。它包含两方面:其一,进行人道主义干涉的武装力量要按照一定比例来组织,按照一定的比例从各个国家招募人员,而不能仅仅是一个国家进行干预,这样可以互相监督,同时方式意识的植入。其二就是按照相同的武力比例来干涉,受到多大程度的武力冲击,干涉的时候就按相应比例进行干涉,避免肆意使用武力。
四、人道主义干涉的国内合法性
人道主义干涉需要有施动方,以及被施动者,也就是人道主义干涉部队以及被干涉的国家。但是执行人道主义干涉的士兵是隶属于施动国家或者施动的国际组织内部的国家,即非被干涉国的其他主权国家。按照现实主义观点:除非重要的利益受到威胁,否则,如果国家行为将冒着丧失本国士兵生命的危险或者招致重大的经济代价,国家将不进行干涉。[12]这里讨论的是国家不会因为人道主义原因进行干涉,因为他们通常是为国家利益驱使的。毕谷·巴雷克(Bhikhu Parekh)把人道主义干涉界定为“全部或主要由人性、怜悯或感同身受的同情情感所引导的”行为。政府在进行人道主义干涉时可能将人道主义因素考虑其中,但是除非政府判定自身的重要利益受到威胁,否则国家将不会使用武力。这样我们可以从中得出折中的结论:保卫国家利益的同时也保卫了人权。这种立场承认了国家利益和权利的真实性,但是他的弱点是使人道主义依赖于被动的政治和战略因素。
另一个批驳人道主义干涉合法性的观点是:国家没必要为了拯救陌生人而使自己的士兵或者非军事人员冒生命危险。国家不会完全出于人道主义因素去干涉他国,这样会使自己与他国的政治关系紧张。然而在索马里和科索沃的人道主义干涉案例中,主权国家为了人道主义因素而使自己的士兵冒着失去生命的危险去保护人权。这些都是出于我们作为公民的认同主张,我们的士兵也是这个国家拥有特殊身份的公民。也就是说我们的公民认同性,决定了我们道义方面的外限。[13]国家领导人和公众没有义务去阻止“边界之外的野蛮行为”,而且假如一个政府垮掉,进入了法律真空状态,或者政府以粗暴的方式对待它的公民。阻止这种状况的义务不归属于任何一个其他主权国家。局外人没有义务去阻止人道主义灾难,即使他们有能力去阻止或者减轻。原因是“公民对他们自己国家负有专有的排外责任,他们国家的事务完全是他们自己的事。公民道义上讲只需关心他们自己国家的活动,而后者对它的公民负责、为它的公民服务”。只有在保卫国家利益时,国家使士兵冒生命危险才是正当的。塞缪尔·P.亨廷顿概括了这种极端国家主义的立场,[14]关于美国对索马里的干涉,他断定“使美国军人被杀害以阻止索马里人自相残杀,道义上是正义的,但政治上是站不住脚的”。大卫·亨德拉克森(David Hendrickson)提出一种说法,即“可预期的适当的伤亡”,然而这种预期的判断还是没有一个标准。在索马里的人道主义干涉中,18名美国游骑兵队员丧生,克林顿总统在那场冲突中起了决定作用。亨德拉克森主张,即使是温和的伤亡在政治上也是不正确的。
即使人们主张国家有权为了保卫人道主义价值而使它们的士兵冒险,仍然存在着反对的理由:这种干涉可能以灾难收场。当这种结果发生的时候,对于施动的国家决策体系是一个冲击,反而会对施动国政府公信力造成影响,进一步会影响国内政策的合法性讨论。这是因为政府做出了一个灾难性决策。出于正义目的的人道主义干涉无法保证行动一定成功。而且在观念上还存在危险的傲慢自大,即其他国家会认为自由的西方世界有责任去解决诸如索马里内战,卢旺达屠杀之类的国家问题。
五、本文结论
经过本文的论述,我们可以明确:国际社会是存在内部规则的,但是这种规则是习惯性规则,而不是权威制定出来的规则。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不是哪一个抽象的国家,而是一个个在国家框架下的对国际负有责任和义务的个人。而且进行人道主义干涉的时候可能会存在国家先进行了人道主义干涉之后在国际法或者联合国宪章内寻找相应条款来为自己辩护。所以进行人道主义干涉的前提是人道主义干涉只有在经过一定标准的检测之后才可以被认可为人道主义干涉。这四个检测分别是:最高级别的人道主义紧急情况;必要性或最后手段;比例原则以及确实的人道主义的后果。笔者认为,只有在能表明非人道主义的动机或者采用的手段削弱了实际的人道主义结果时,非人道主义动机驱动的干涉才不具备人道主义干涉的干涉资格。满足了人道主义动机、人道主义理由、合法性和选择性等标准的干涉比那些只符合最低限度的干涉具有更多的人道主义资格。一场干涉必须满足上述的所有要求才可以被看做是人道主义干涉。这里有三个回应:第一,自1945年以来的干涉案例中,还没有满足所有这些标准的案例,我们也不知未来是否存在满足这些标准的案例。第二,这里的论点不是我们应当赞扬只是满足了最低要求的干涉,而是我们应当尽我们个人和集体的全力去说服国家的领导者承担伦理责任。当面对特别紧急的人道主义情况时,政府应当首先确保安理会授权,对相似的案例采取类似的行动。第三,认为国家实践是检验人道主义合法性的决定要素的观点是不全面的。对这些行为的合法性的解释与国家冲突尖锐对立,这表明了冷战时期国际社会在道义方面的破产。但是随着苏联的解体,两极的崩塌,国际社会在道义上不断进行新的探索。所以随着时代的进步,国际社会对于人道主义干涉的合法性的认识也在不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