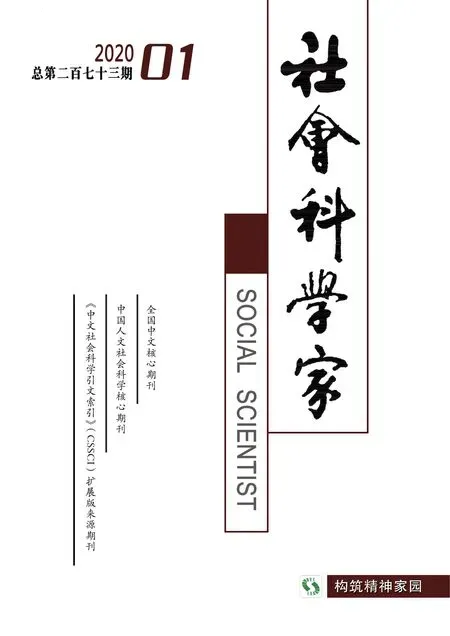高拱《论语》诠释的特色
2020-02-21唐明贵
唐明贵
(聊城大学 哲学系,山东 聊城 252000)
高拱(1513-1578),字肃卿,号中玄,河南新郑人。嘉靖二十年(1541年)进士。历任侍讲学士、文渊阁大学士、内阁首辅等。著述主要有《问辨录》《春秋正旨》《本语》《边略》《日进直讲》等。其中《问辨录》共十卷,六卷是关于《论语》的;《日进直讲》共五卷,三卷涉及《论语》,主要讲解《学而篇》至《宪问篇》的经文。兹以此为据来探讨高氏《论语》诠释的特色。
一、推阐精微
高拱曾担任过裕王侍讲,“裕王殿下出格讲读”,“拱说《四书》”;也曾担任过国子祭酒,因为其地位特殊,所以无论是《论语日讲》,还是《问辨录》都具有剖析入微的特点。
第一,先训句解,次敷大义。这一点在《论语日讲》中表现的比较突出。据《日进直讲序》记载,《论语直讲》是讲给皇太子的,在任国子监祭酒时“乘暇次序成秩”[1],整理成书。该书“如日讲例,先训字义,后敷大义而止”[1]。如《学而篇》“巧言令色,鲜矣仁”章,高氏注曰:“‘巧’是好。‘令’是善。‘鲜’是少。‘仁’是心之德。孔子说,辞色皆心之符,所关甚大,那有德的仁,辞色自无不正。若乃务为甘美之言,迁就是非,便利滑泽,而使听之者喜,便是‘巧言’。务为卑谄之色,委顺侧媚,迎承人意,而使见之者曰,便是‘令色’。这等的人,其仁必然少矣,何也?仁乃天理之在人心者也,人必笃实正大,而后此心可存,天理不失。今乃致饰于外,务以悦人,则心必不能存,而天理之断丧多矣,岂不鲜仁矣乎?是人也,不止丧德于己,而实有害于人,人主尤宜痛绝之,何也?巧言令色之人,最能窥伺奉顺,使人主喜之而不自觉,既喜之而不自觉,则遂能暗投微中,以移人主之意,于是倾陷正人,变乱国是,甚至于覆人之邦者有之,而人主堕其计中,不见其迹,犹反以为忠而不能舍也。所以尧舜至圣,尚畏巧言、令色、孔壬,况其他乎?故曰人主宜痛绝之。”[1]在这里,高拱先解释了其中的重点字词,接着串讲了经义,最后将其与现实政治联系起来,指出人主必须痛绝巧言令色之人。又,《子路篇》“一言而丧邦”章,高氏先对其中的个别字词予以了注释:“‘丧’是丧亡。‘乐’是喜乐。‘违’是违背。”接着串讲了句意:“定公又问说,一言兴邦既闻之矣,若说一句不好的言语,便可以丧亡其国,亦有之乎?孔子对说,一言之间便未可如此,遽期其效也,然亦有之。今时人有一句话说,我不是喜欢为君,只是为君时随我所言,臣下都奉承我,无敢违背,这便是所乐也。时人之言如此,自今言之,如其所言而善,有益于生民,有利于社稷,那臣下每都依着行不敢违背,则生民必受其福,社稷必得其安,岂不是好事?如其所言不善,有害于生民,有伤于社稷也,都要臣下每依着行不敢违背,则生民必受其祸,社稷必为之危,而国不可以为国矣。然则惟言莫违之一言,岂不可以必期于丧邦乎?”最后直陈经文之微言:“可见人君当以从谏为圣,而不可以人之承顺为忠,若不论理之是非,而只欲人之从己,则忠言不至,蒙蔽日深,实乱亡之道也。”[1]人君只有从谏如流,才能兼听则明;如果实行高压态势,迫人从己,无人敢言,实为乱亡之道。
第二,问题剖析,鞭辟入里。《论语》中有些探讨的问题时代久远,后世学者见仁见智,众说纷纭。高拱对其中的某些问题分析透彻,多给人以启发。如《泰伯篇》“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谓至德矣”章,朱熹注曰:“率纣之畔国以事纣,荆、梁、雍、豫、徐、扬也。惟青、兖、冀尚属纣耳。”[2]在高拱看来,这种以具体州数来划分的说法是不确切的。他首先分析了“何以见其为至德”,指出:“太王实始翦商,肇基王迹,于是乎传位季历,以及文王,人心系属已久,天下即可取矣。乃不取,文王为西伯,光于四方,显于西土,天下之人归心焉。天下益可取矣,乃犹不取。非惟不取也,而固以服事殷,止于敬者,自如也。非至德而能如是乎?”接着他又对涉及此事的《孟子》所言“取之而不悦,则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予以了分析,指出:“人心归向如此,岂谓‘取之而不悦’乃文王只是自守臣节,不论事势何如,毕竟只是不取,此所以为至徳也。文为至徳,武之所以未尽善也。”纠正了孟子的不当之说。进而他又对“孟子何为如此言”进行了说明:“孟子为伐燕之事,乃设论若此,盖借言也。若明说取之悦,而文王不取,则燕不必伐矣。”孟子此说是有特定背景的。最后高拱又对朱注予以了批判,并给出了自己的答案:“此文王为西伯,专征伐天下,有不服者,文王必为征伐之,是为率畔国以事纣。‘三分天下有其二’,是言人心皆归文王,以天下大势言之,已有三分之二云耳,非真画地而分也。纣尚为天子,荆、梁、雍、豫、徐、扬固纣之土宇版章也,岂遂皆不属纣乎?文王圣徳,青、兖、冀之人,固亦有人心也,岂遂无一人归文王者乎?要之,天下皆纣之天下,而人心则大半归文王也,故曰‘三分天下有其二’而。后人遂分六州以实之,则非矣。且当时天下九州固如此分向,使为十州也,又何如分乎?儒家拘泥强说乃如此。”[1]应该说,高拱对“三分天下有其二”这一疑难问题的解释,更加合乎商周之际的历史实际,《四书秕疏》就曾指出:“《集注》谓荆、梁、雍、豫、徐、扬,熊氏谓徐、扬无考。然文王质成虞、芮,虞、芮国在河中,今平阳府境。西伯戡黎,黎在今路安府黎城县。皆冀州之城。而孟津、牧野固属豫州,至武王时犹为殷有,则文王已兼有冀土,而豫州尚多属纣,则三分者约略言之,非专言六州明矣。九州之城,青、兖、徐、豫小,雍、梁、荆、扬大,非可合三州为一而三之也。”[3]
又,关于人性论的问题,历来是儒家争论的焦点,高拱剖析了自孔子以来的人性论史,并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观点。在他看来,人性论当以孔子所言“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为旨归:“千古论性断案莫的于此,学者必当以是为准焉。”高拱认为,理、气、性、心是一体的:“气具夫理,气即是理;理具于气,理即是气。原非二物,不可以分也。且性从生,生非气欤?从心,心非气欤?而后儒乃谓理属精纯,气或偏驳,不知精纯之理缘何而有?偏驳之气别何所存?气聚则理聚,与生俱生;气散则理散,与死俱死。理气如何离得而可分言之耶?”因此,“自孟子‘性善’之说出,有求其理而不得者,则遂曰‘性恶’,则遂曰‘善恶浑’,则遂曰‘性有三品’。宋儒欲扫去诸说,而还归孟子也,则又分理气言之,而以孟子之言合于孔子,曰‘此纯乎理者也’‘此杂于气者也’,乃亦卒不能合,而又有以启辩论者之纷纷”。在此基础上,他重点对程颐、张载、朱熹的人性论予以了批判,指出,程颐所言“此言气质之性,非言性之本也”,张载所说“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气质之性,君子有弗性焉者”,朱熹所言“有天地之性,万殊之一本也;有气质之性,一本之万殊也”,“此所谓性,兼气质而言也。气质之性,固有美恶之不同矣。然以其初而言,则皆不甚相远也”皆有失偏颇,因为“人只是一个性。此言气质之性,又有何者非气质之性乎?”,“人只是一个性,又有何者是天地之性?何者是气质之性乎?且气质非得之天地者乎?”“晦翁遵伊川之言,然不敢自定,故以为兼气质而言。人只是一个性,此所谓性兼气质而言,又有何所谓性者不兼气质而言乎?”人性本一,无所谓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之分。究其原因就在于,“但其求合孔孟处,未免强辞,强辞便费解说”,“孔子言‘性相近’,孟子言‘性善’,二说微有不同。后世儒者,乃欲比而同之。欲言‘性近’,则不合孟子之旨,故曰‘有气质之性’‘兼气质而言也’,以还却夫子‘性相近’之说。欲言‘性善’,则不合孔子之旨,故曰‘有天地之性’‘此性之本也’,以还却孟子‘性善’之说。其意固美,然终不能使孔、孟之说归于大同也”。那么,符合孔子本义的人性论应该如何表达呢?高氏较为认可程颢的说法:“惟明道先生有言‘性即气’‘气即性’‘善固性也,恶亦不可不谓之性’。有合孔子之旨,学者只求诸明道先生,则知孔子之说矣。”[1]从性一元论入手,高拱本孔子性论之本旨,剥茧抽丝,多维度确立了“人只是一个性”的观点,彻底否认了“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的区分,无疑从根本上揭穿了程朱理学披罩在人性上的神圣外衣。
从以上论述我们不难看出,高拱无论是对经文的诠解,还是问题的剖析,都具有层层深入的特色,语言平实通达,问题分析透彻,不胶固、不滞碍、不偏执,无怪乎嵇文甫曾这样来评价其学术,“大概可用‘通’和‘实’两个字来概括,平正通达,有实用而近人情”[4]。
二、辨诘朱注
高拱生活在程朱理学日趋式微、阳明心学方兴未艾的时代,为了挽救程朱理学的颓势,他力图修正《四书章句集注》,以期迎击阳明学的冲击,止住程朱理学的下滑趋势。因此,在《问辨录》中,他针对“后世学鲜融洽,成心未化,各持臆说,以符圣轨。既存执著,卒落方隅”的现实情况,决定“芟除繁杂,返溯本原,屏黜偏陂,虚观微旨,验之以行事,研之以深思”,以期“冀正真诠”[1]。
第一,指正朱注中的字词解释。在高拱看来,虽然朱子对《论语集注》信心满满,称“添一字不得,减一字不得”[5],但其中还是有失察之处。如《公冶长篇》“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章,朱子引程子注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吾亦欲无加诸人,仁也;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恕也。恕则子贡或能勉之,仁则非所及也。”朱熹在其后注曰:“无者自然而然,勿者禁止之谓,此所以为仁恕之别。”[2]“‘无友不如己者’‘无欲速,无见小利’,固皆禁止辞也。与‘勿’何异?而遂以此‘无’字为自然乎?亦只是恕耳。盖子贡以恕自任,而孔子谓其非所及也。”[1]高拱认为朱子将“无”与“勿”字分别加以解释是有问题的,不能以此来强调仁恕之别。又,《微子篇》“逸民”章中的“逸民”两字,朱注曰:“逸,遗逸。民者,无位之称。”[2]在高氏看来,朱注对这两个字的解读是有问题的,他指出:“逸,散也,亦安也,犹俗所谓自在人者也。逸民者,超然物外,无拘系之散人,不在常格之中者也,亦高人也。”[1]两相比较,高氏所注比朱子所注更符合时代和经文原意。
第二,纠正朱注中的经文诠解。高拱认为,《论语集注》中有些地方对经文的解释存在错讹之处,未能阐明孔子深意。如《学而篇》“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朱注中有“此特论其所存而已,未及为政也”[2]句,在高拱看来,此注释有误,他指出:“此出程说。伊川书云:‘敬事以下诸事,皆言所存,未及礼乐刑政。’夫礼乐刑政,为治之具,又何待言?今以五者但言所存,则岂以敬信只在心,而所行者尚未敬信乎?节爱只在心,而所行者尚未节爱乎?时使只在心,而所行者尚未时使乎?盖所存所施,举在于是,安得云‘未及为政也’?”[1]敬、信、节、爱并非只存在于心中,而是落实到了实际政治措施中,因此说“未及为政”是不对的。又,《里仁篇》“吾道一以贯之”章,朱注曰:“盖至诚无息者,道之体也,万殊之所以一本也;万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万殊也。以此观之,一以贯之之实可见矣。”[2]高氏认为此解释“殊未莹彻”,且举例予以说明:“譬之树然,千枝万叶,只是一根,万殊之所以一本也。一根而散为千枝万叶,一本之所以万殊也。一贯之义,则不如此。谓天下之事,有万其繁,而吾所以处之者,惟一理以贯通之。譬之索子穿钱,钱数虽多,惟用一条索子都穿了,非谓以吾心之一理,散为天下之万事,如所谓‘本立道生’云也,则何谓一本万殊?”[1]“一本万殊”和“一以贯之”是有区别的,前者不能很好地解释和说明后者。
第三,抉摘注文中的画蛇添足之笔。在高拱看来,虽然朱熹自称于《论语集注》“四十余年理会,中间逐字称等,不教偏些子”[6],但实际上其中不乏画蛇添足之语,影响了对经文意思的理解。如《学而篇》“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章,朱注中有“苟非生质之美,必其务学之至。虽或以为未尝为学,我必谓之已学矣”[1]句,高氏认为其中有添字为训之谬,他说:“加一‘生质之美’,便非子夏论学之意。只云‘能是四者,必其务学之至,虽或以为未尝为学,我必谓之已学矣’。乃子夏论学之意也。”[1]加上四个字,就改变了经文的原意。没有这四个字,就去掉了先天性的因素,更多的强调了后天的努力,这更符合子夏之意。《为政篇》“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章,朱注中有“况由此而求之,又有可知之理乎”[1]句,高拱认为此句为多余之语,指出:“考亭务多闻见,故于圣人直截之言之外,为此画蛇添足,失其意矣。”[1]又,《八佾篇》“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章,朱注云:“居上主于爱人,故以宽为本。为礼以敬为本,临丧以哀为本。既无其本,则以何者观其所行之得失哉?”[1]在高氏看来,“又是画蛇添足。夫宽也乃即宽,以观其居上之得失;敬也乃即敬,以观其为礼之得失;哀也乃即哀,以观其临丧之得失。则是为宽、为敬、为哀,固不若不宽、不敬、不哀之无责也。意既深刻,语亦沾滞,圣人之言断不如此”。“观其所行之得失”超出了原文之意,是多余之笔。那么,此句该做何解释呢?他指出:“宽者居上之体,乃不宽;敬者为礼之体,乃不敬;哀者临丧之体,乃不哀。吾何以观之哉?如曰‘吾不欲观之矣’云尔,即世人所谓如何看得上也。”[1]如此说解,乃得仿佛。
尽管高拱对朱注有所辨诘,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反对或否定朱注,他曾指出:“濂、洛、关、闽,发明圣学,以训后世,厥功伟矣。”[1]在讲解过程中,高氏也多处袭用朱注。如《学而篇》“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章,朱注曰:“有子,孔子弟子,名若。善事父母为孝,善事兄长为弟。犯上,谓干犯在上之人。鲜,少也。作乱,则为悖逆争斗之事矣。此言人能孝弟,则其心和顺,少好犯上,必不好作乱也。与,平声。务,专力也。本,犹根也。仁者,爱之理,心之德也。为仁,犹曰行仁。与者,疑辞,谦退不敢质言也。言君子凡事专用力于根本,根本既立,则其道自生。若上文所谓孝弟,乃是为仁之本,学者务此,则仁道自此而生也。”[2]高氏注曰:“‘有子’是孔子弟子,姓有,名若。善事父母为‘孝’。善事兄长为‘弟’。‘犯’是干犯。‘鲜’是少。‘作乱’是悖逆争斗的事。‘务’是专力。‘本’是根本。‘道’是道理。‘生’是生发。‘为仁’譬如说行仁一般。有子说,人皆有至亲之伦,亲长是也;有至真切之心,孝弟是也。人惟失其真切之心,而薄其所亲,于是不和不顺,将背戾而无不至矣。若其为人也,善事父母而能孝,善事兄长而能弟,则其心常和顺。心既和顺,则自不至于背戾……所以君子于天下之事,不泛焉以求之,只于那根本所在,专用其力,根本既立,则道理自然生发出来……仁是心之德、爱之理,凡事亲、事兄、事君、事长,仁民爱物,皆仁之用,固不止孝弟之一事也。然人惟孝弟,则自无犯上作乱之事。可见爱敬之施此,其根柢由是充之,则事君便能忠,事长便能敬,便能仁民,便能爱物,而仁不可胜用矣,岂非为仁之本乎?若人能务此,则仁道自此而生矣。盖学莫大于求仁,而仁莫先于孝弟。故有子揭以示人如此。”[1]两相比较,不仅好多字词注释袭用朱注,而且经文大义亦基本袭沿《集注》。对此,四库馆臣也曾指出:“又论‘贤贤易色’一章,谓人能如是,必其务学之至觉,‘生质之美’四字,朱子可不必加。亦未深体抑扬语意。如斯之类,皆不免有意推求。至如伊川谓‘敬事而信’一章皆言所存而不及于事,拱则谓节用使民,非事而何?又谓孔子之责臧文仲,正以其贤而责之备。如斯之类,则皆确有所见,足以备参考而广见闻。郑汝谐《论语意原》,颇与朱子异同,而朱子于汝谐之说反有所取。朱子作《周易本义》,与程《传》亦有异同,世未尝以是病朱子。拱之是编,亦可作如是观矣。”[7]这就是说,虽然高氏之作与朱注有所不同,但并非是“病朱子”。
三、别生新意
在高拱看来,在学术上,唯程朱马首是瞻,“一字一句,一步一趋”,虽然可称得上“确守程、朱之辙”,“笃信好学”,但这只是“升程、朱之堂,而不复求入孔、颜之室,故不能得圣人之大,鲜超脱处。”[1]因此,他主张对于“圣人之书,必须潜心体会,务得精微之旨,然又须得其言外之意,方可循之以入道”[1]。依此精神,高氏在诠释《论语》时,常常生发出新意。
第一,将为己之实学与为国之实政结合起来。在高氏看来,“圣人有为己之实学,而祸福毁誉不与焉。圣人有为国之实政,而灾祥不与焉”[1]。职是之故,“拱乃于所说书中,凡有关乎君德、治道、风俗、人才、邪正、是非、得失之际,必多衍数言,仰图感悟,虽出恒格,亦芹曝之心也”[1]。
一方面,他讲求“为己之实学”,视之为圣学第一义。在诠释《学而篇》首章时,高拱指出:“夫圣门之学,始诸立心,立心只在为己。故门人首记焉,所谓第一义者也。”[1]在他看来,“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此圣人自述,其为己之学如此。盖人之修徳,便要求福于天,为学便要求知于人。既而天果福之,人果知之则已矣。若不得于天,不合于人,则有以拂其初心,而怨尤生焉。圣人灼见,夫为学修徳是自家的事,与天之祸福、人之荣辱不相关涉,故发愤忘食,乐以忘忧,孳孳汲汲,只是下学人事而上达天理,做自家的事而已,而原无一毫求福、求知之心,故虽不得于天,不合于人,惟知有学而已,而又何所怨尤乎?此其学所以纯而不已,‘遯世不见,知而不悔’也。夫有为人之心,则便务为形迹;务为形迹,便有所表著,而人便知之。既是纯乎自修,不与于人,则自无形迹表著,人将何以知之哉?盖非惟不能知,亦宜乎其不知也。然则知我者,其天而已乎?人则孰知之?”[1]“不怨不尤,此圣人为己之实学也。君子敬以持己则徳立,恕以待物则道弘,徳立道弘,仁即斯在,是皆尽其在我者也。至于人有不合,则不必怨尤,在邦亦无怨于邦之人,在家亦无怨于家之人,惟知自尽而已,不可有为人之心也。‘在邦无怨,在家无怨’,犹云‘正已而不求于人则无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者也。如此则志定而功纯,心安而理得,才是为仁之道。一牵于外,便非仁矣。”[1]两次提及“不怨不尤”为“为己之学”,强调为学修德为自家的事,“不可有为人之心”。
另一方面,他讲求“为国之实政”,“《日进直讲》一书,保存了他透过阐释和演绎儒家经典向穆宗灌输政治思想的文字”[8]。在高拱等人看来,之所以对皇帝或皇太子进行经筵日讲,究其原因就在于,“自昔圣主贤臣,治天下之大经大法,具载六经,不可不讲也。讲之则理明而心正,措之政事,无不得其当。宜择老成名儒,于朔望视朝之际,进讲经书一篇,敷陈大义。使上下耸听,人人警省,兴起善心,深有补于治化也”[9]。通过经筵、日讲的机会对皇帝施加影响,向皇帝灌输儒家的政治思想,希冀实现儒家的仁政德治。如《学而篇》“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高拱释曰:“‘道’是治。‘千乘’是诸侯之国,地方百里,可出兵车千乘者也。孔子说,治国最难,而国之大者尤难。若治那百里的大国,有五件要道:其一要敬事。盖人君日有万机,若一时不谨,或以贻千百年之忧;若一念不谨,或以致千万人之祸。故必翼翼小心,事无大小,皆须敬慎,而不敢乘以轻易苟且之心,则所处皆当,自无有败事也。其一要信。盖信是国之宝,若赏罚不信,则人不服从;若号令不信,则人不遵守。故必诚实不贰,凡出言行事,内外如一,而不敢杂以猜疑虚假之意,则人皆用情,自无有敢于欺罔也。其一要节用。盖国以财为命,若不节用,岂能常给乎?故凡奢侈的用度,冗滥的廪禄,不急的兴作,无名的赏赐,都裁节了,只是用其所当用,则财货恒足,虽有水旱之灾,军旅之费,亦不至于匮之也。其一要爱人。盖国以民为本,若不爱人,岂能无怨乎?故必民之所好也去好他,民之所恶也去恶他,保之如子,惟恐有以伤之而不得其所,则民心固结。自将爱其君如父母,护其君如腹心,而不至于背叛也。其一要使民以时。盖春夏秋皆是务农之时,若妨其时,则作田者无以自尽,而公私皆不得其利矣。故凡造作营建,举兵动众,不得已而为者,必待那农功已毕之后,才去使他,则生之者众,为之者疾,而五谷不可胜食也。这五件是治国的要道。人君若能行此,岂止干乘之国,虽于治天下何有哉?”[1]在这段文字中,高氏先在对其中的重要概念“道”和“千乘”进行解读的基础上,逐段详细诠解了“敬事”“信”“节用”“爱人”“使民以时”的具体做法,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的确够得上“实政”之说。
第二,创造性的诠释经权关系。作为儒家方法论原则,经权思想由孔子首提后,在历代儒者的解读下,逐渐成为儒家的核心思想之一。高拱在批判前贤经权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独具特色的经权统一思想。他指出,经和权之间的关系,就如同秤星子和秤锤的关系:“经者,称之衡也,斤两各具星子,有定而不可易。如父子之必亲,君臣之必义,以至其他,莫不皆然者也。权,称之锤也,往来取中,变通而不穷。如亲,务得乎亲之正;义,务得乎义之正。以至其他,莫不皆然者也。”[1]经是不可易的,秤星子也是固定不变的,就像父子之间有亲、君臣之间有义一样;权是可以变易的,秤锤在星子之间“往来取中,变通不穷”,就好像行亲务得其正,行义务得其正。秤锤之移动总是围绕星子展开,而秤星子的作用在秤锤的往来移动中得以体现。因此,二者是密不可分的,“盖无常无变,无大无小,常相为用,而不得以相离”[1]。高氏反对汉宋诸儒所谓“常则守经,变则行权”[1]的说法,认为此说“是常则专用衡而不用锤,变则专用锤而不用衡也”[1],“且开且合,而不得其理也”[1]。在他看来,“汉儒的权变、权术之说,乃是无衡之锤,无所取中,故其旁行也流,亦任其诡窃,何可以为权也?”[1]汉儒的“反经合道”说也是自相矛盾的:“既曰反经,安能合道?既曰合道,何谓反经?若曰反经可以合道,是谓背其星子而可以得其分两也,有是理乎?”[1]因此,“其缪固不足辩”[1]。而宋儒程颐之说“权者,经之所不及也。经者,只是存得个大纲大法,正当的道理而已。其精微曲折处,固非理之所能尽也。所谓权者,于精微曲折处,曲尽其宜,以济经之所不及尔”“于义未莹。夫权以称轻重,非以尽细微也。正理所在,莫非经;称之而使得轻重之宜者,莫非权。孰为专立其大?孰为独尽其细?孰为之阙?孰为之补?若曰经可自用,用之而有所不及,则以权济之。是谓衡可自用,用之而有所不及,则以锤济之也,而可乎?”[1]如果说衡可独立运行,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再加入“锤”,这本身就十分荒谬。朱熹所云“经者,万世常行之道;权者,不得已而用之。须是合义”“权者,不得已而用之,大概不可用之时多”“斯言愈远。夫谓‘经乃常行之道,权则不得已而用之’,是谓衡乃常用之物,锤则不得已而用之者也。谓‘权之于事,不可用之时多’,是谓锤之于称,不可用之时多也,而可乎?且义即是经,不合义便是拂经,拂经便不是权,非经之外别有所谓义,别有所谓权也。”[1]从衡和锤的角度来看,朱氏之说是不合乎逻辑的。
在此基础上,他指出,经权之间理应是权不离经,经不离权,“权自是权,固也,然不离经也;经自是经,固也,然非权不能行也”[1]“盖经乃有定之权,权乃无定之经”,这就是说,经和权不是截然对立的,二者之间“无定也,而以求其定”,而“定”乃以“无定”“为正”[1]。这即是高拱的经权统一观。嵇文甫就此评价说:“这里面牵涉到一般原则和具体运用的问题,无大无小,无精无粗,处常处变,都需要具体分析,‘权’它一下,真理总是具体的嘛。高拱很得力于这个‘权’字,所以他讲道理都很切合人情事变,平正通达,和那班迂滞偏执的道学家大异其趣。”[4]
综上所述,高拱在《论语》诠释过程中,由于受众特殊的身份,所以,一方面,他不仅释读难词,而且逐段串讲,使得经文解释较为通俗易懂,明白易晓;另一方面,他为了让皇太子从中学习修齐治平之道,也对经文进行了创造性解读,使其释放出了更多的新意,“论时事,率切中明季之弊”[6]。同时,他为了重振程朱理学,也对其中的在他看来有误的地方予以了辩驳,其中不乏精当之处。诚如四库馆臣所言:“辨诘先儒之失,抉摘传注之误,词气纵横,亦其刚狠之余习。然颇有剖析精当之处,亦不可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