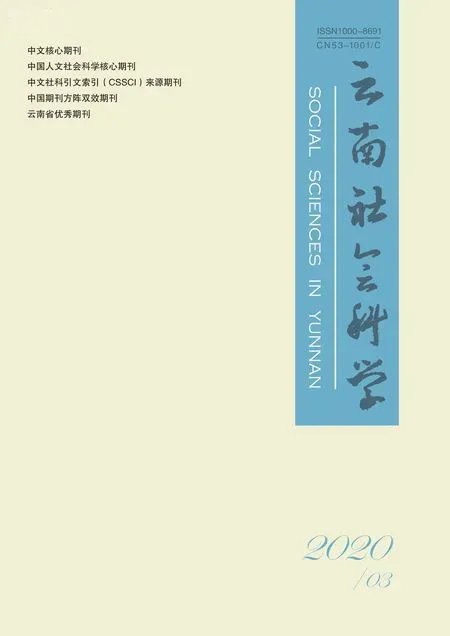从原真的物品到现实的展示:关于现代博物馆传播秩序的景观幻象
2020-02-20宋厚鹏
宋厚鹏
“博物馆”(Museum)一词源自希腊文“Museion”,它指的是“缪斯女神的圣地”①严建强、梁晓艳:《博物馆(MUSEUM)的定义及其理解》,《中国博物馆》2001年第1期。,即代表着艺术与知识的神圣殿堂。自古希腊的柏拉图学院、亚里士多德学堂以及公元2 世纪埃及托勒密王朝的亚历山大博物馆,到14—16 世纪文艺复兴时期,博物馆一直都是作为珍藏、展示和研究艺术、知识与人类文明的殿堂,而直到18 世纪末法国大革命打开了卢浮宫的大门,博物馆才真正步入社会化,即从过去仅供贵族和富人观赏的珍藏室,转化成了向公众开放的文化机构。②王宏钧编:《中国博物馆学基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61页。公共博物馆诞生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盛行的欧洲,而在此种认识论——承认世界存在着恒久不变的绝对真理,力求把公众看作均质的整体,并创造一套价值体系,统一规格——的影响下,博物馆逐渐形成了以分类和排列的方式展示物品,并以此传递不容置疑的“真理”③“真理”(The truth)在此所指的是用来讲述“现实”(Reality)的话语体系。根据南开大学周志强教授的观点,现代人和这个世界的“真实”(The real)相距最远的就是真理(或真相),“真理”就是为了让人获得强烈的现实感而制造出来的具有现实感的经验陈述。详见周志强:《现实·事件·寓言——重新发现“现实主义”》,《南国学术》2020年第1期。来对公众实施规训。也就是说,公共博物馆是在按理性主义的分类原则组织文物,并使自身从专制权力的象征转变为教育公民和服务国家集体利益的工具。
“物品”(Thing)是博物馆展示系统的核心要素,也是它传播文化时所需的重要媒介。然而,在现代博物馆按秩序对“物品”进行展示以教育公民和服务国家时,观众在饱览那千百年来的文化荟萃过程中,都会在受到如雷击般震撼的同时,随着民族志修辞和意识形态嵌入至文化表征所实现的展示模式下成为“被构设的主体”。换句话说,现代意义上的博物馆总是在按某种标准对“物品”进行重构,即使“物品”向“展品”(Showpiece)转化,以构成承载权力话语和现实意义的文化景观来对公众实施规训。那么在以展示进行知识生产和主体建构的过程中,当博物馆将“物品”作为叙事元素置于展厅中时,它是否还有“原真性”(Authenticity)?如果展示脱离了“物品”本身的环境,其所拼合而成的文化景观还能否呈现完整的“真实”?并且公共博物馆作为一种文化实践活动和主体身份建构,其弥漫着民主气息的空间又是如何在展示秩序中对公众加以规训的?为此,本文将围绕“物品”“展示”和“空间”三个维度来尝试论述以上问题。
一、“物品”的嬗变:展示媒介的异化
博物馆是什么?针对这个问题,或许可以引用美国学者斯维特兰娜·博伊姆(Svellana Boym)评述俄国作家纳博科夫(Vladimir Vladimirovich Nabokov)的短篇小说《博物馆之旅》(The Visit to the Museum)中的一句话来回答,即“博物馆是宇宙的二手模型,它是由许多物品和神话所组织起来的某种诺亚方舟”①[美]斯维特兰娜·博伊姆:《怀旧的未来》,杨德友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第302页。。事实上,在人们的普遍认知中,博物馆通常都是一组物品的抽象集合,就像城市是一组建筑物的集合一样,而它作为重要的记忆场所,其所汇聚的来自不同时间和空间的物品,可以说是一种“回归过去”的表征,它们既赋予了博物馆权威和神圣感,同时也在聚光灯的照射下唤起人们对历史的回忆,传达无穷且有价值的信息。从某种意义上说,物品不仅捍卫了博物馆的客观性和中立性,而且它所建构的文化景观,也使得公众不会轻易对博物馆发出质疑或挑战。然而,在博物馆展示物品方面,艾塞克斯大学艺术史系教授彼得·弗格(Peter Vergo)曾就此提出:“物品被挑选为展品的标准并非随机的或任意的,相反,它们是根据特定的目的而被筛选出来的”②Peter Vergo,The New Museology,London:Reaktion Books Ltd,1989,p.2.。由此,这里便会产生一个疑问:一旦物品被嵌入展示体系,成为了辅助展览讲述某个故事的元素时,它是否还能保持其原有语境的原真性?并且它在昭示一个令人炫目的文化盛景时,是否还具有稳定的和客观的物质性?
作为一个集艺术、历史、文化与科学为一体的公共机构,当博物馆在对各类物件实行管理和利用时,首要环节就是要对原真的物品进行“展品转换”,即使之脱离原有的历史背景成为带有现实意义的传播媒介。因为,作为一个以“过去”为内容的“展览综合体”,博物馆所面对的无疑是一个犹如“大熔炉”般的文化群落,因而在这种情况下,它必然无法将其原封不动地挪用过来,而唯有根据展览的主旨对其进行选择、抛弃、改造和美化,从而使之承载某种现实话语来发挥启蒙功能。就此而论,当博物馆站在某一立场取消了物品原有的(部分)实际意义时,这些物品便成为了特定时间在当下空间中的结晶,成为了更具抽象的文化象征,而这一现象也印证了卡尔·马克思(Karl Marx)所说的“异化”——“导致疏离或成为其他”③[英]彼得·奥斯本:《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导读》,王小娥、谢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年,第67页。——即物品一旦承载着某种意义参与迎合政策、教育、市场和意识形态的文化生产时,其原真性就会被展示中的现实性所弱化,从而产生一种嬗变。
所谓“物品”的嬗变,在博物馆的语境中所指的就是被展示的物品已不再是存在于物理时空中的客观实在,借用阿多诺和本雅明的批评话语来说:博物馆剥离了物品与其原有环境间的联系,使其丧失了原真的意义。④Daniel J.Sherman and Irit Rogoff,Museum Culture:Histories,Discourse,Spectacles,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4,p.xiv-xv.在此,可以以天津博物馆的常设展览为例。天津博物馆的常设展览共设有3 个主题,分别是“天津人文的由来”“中华百年看天津”和“耀世奇珍”。其中,前两部分是依照历史发展的顺序来陈设的,前者所选之物概略展现了天津自旧石器时代至清朝中后期上万年的历史进程,展示了天津从不毛之地到运河城市的曲折发展过程;后者通过所选文物配以文字史料和拟真场景,呈现了天津自鸦片战争后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这100年间的风雨历程——这种展示凸显着一种“以当下为终点,根据历史发展的顺序来安置物件”⑤[英]贝拉·迪克斯:《被展示的文化:当代可参观性的生产》,冯悦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54页。的观念——而当公众跟随展示系统逐步深入,并对展品加以解读时,多数人都会随着被构建的客观历史不自觉地萌发民族意识,从而形成一种共鸣。至于“耀世奇珍”,它的目标和指向更加清晰,从它对古代青铜器、玉器、书画和工艺等最具代表性的文物珍品的选择和设计来看,其所隐含的意义就更不言自明了。
因而,本文在此所论及的有关“物品”到“展品”的过程,就是物件在与其原始事件和功用分离后,伴随所赋予的新意义在封闭性空间和系统性秩序的作用下所生成的“全景式景观”。具体而论,当策展方将具有历史价值之物从特定的语境中提取出来,并在遵循一定原则且利用各种方式将其陈设在展厅中时,这个原始物件的“本我”就会发生质的改变,即它会在显现自己部分原初事件的同时,通过与他者的相互作用形成一个彻底历史化的物与人的总体秩序①Tony Bennett,The Birth of the Museum:History,Theory,Politics,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5,p.96.,从而引导人不自觉地走进从普通物件到展品转化所无限放大的“历史”。或许,通过借用北京地铁8 号线的南锣鼓巷站厅层中的公共艺术作品《北京·记忆》②《北京·记忆》由中央美术学院王中教授主持设计,该作品位于北京地铁8 号线南段的南锣鼓巷站站厅层,其整体艺术形象由4000 余个琉璃铸造单元立方体以拼贴的方式呈现出来,用剪影的形式表现了老北京特色的人物和场景,如街头表演、遛鸟、拉洋车等。可以更好地解释这一点。《北京·记忆》这一以拼贴方式所表现的具有老北京特色的人物和场景,其构成的每一块琉璃方块中都藏有一个北京人所提供的老物件(如徽章、粮票、顶针等),也就是说,当这其中的某一物件在被市民使用时,它是一种“物”的表现,但当它被装入到玻璃单元体,并与其他事物构成体系被公开展示时,这件物品便会从物质存在的属性转变为“展品”生成意义,从而让观者解读出“北京过往岁月的温暖记忆和历史情怀”。因而,按照亨里埃塔·利奇(Henrietta Lidchi)的说法,一个物品物质存在的固定性并不能提供意义层次上的担保,而正是在博物馆(以及各种展示平台)的语境中,存在的稳定性和意义的稳定性的归并才会受到鼓励。③Henrietta Lidchi,The Poetics and the Politics of Exhibiting Other Cultures,in Stuart Hall eds, Representation:Cultural Representation and Signifying Practices,Los Angeles and Washington D.C:SAGE,1997,p.162.
由此来看,博物馆中所陈列的一系列圣化之物,其价值并非全然在于它们的原真性,而是更多地体现在它们同主题、空间、思想和观念所形成的呼应感。因此,在这个过程中,博物馆往往会更加注重提高展示的形式(如复原或模拟真实的场景)从而再现“真实”,即通过讲述更广阔的背景故事,来引导观众相信其展示的内容是客观的和合理的。但遗憾的是,由于展示往往会不自觉地脱离物品原初的语境,所以博物馆展示的真实性不免会卷入讨论的漩涡之中。
二、展示的“真实”性:被建构的文化景观
到这里,在原初语境中成长的物品,均在展览中经过了深刻的重构或再造,成为了所谓“事物”,而博物馆对事物的掌握或控制,则构建了观众所熟悉的“展品”(非“单纯”的物质)。展品是博物馆叙事图景的核心要素,它建立在博物馆的自然条件和展览主题上,换言之,它是在围绕政策导向(不免也会受到策展人本身价值观的影响)和教育目标来参与概念、观念和情感的生产,而在这一运作中,虽然展品可以将“被展示的文化”无限放大,但其他原有的事件则已在很大程度上被弱化或掩盖了。由此可见,博物馆展示的真实性仿佛仅是被设计的,它建基于对原始物品进行某种程度的改造,就像博物馆学家丽莎·罗伯茨(Lisa C.Roberts)所说的:“展览本身就是一种阐释性行为……选择和摆放物件的过程实质上就是一种虚构,它是虚构者试图表现出一个物件所能阐述的故事。”④爱德华·P.亚历山大、玛丽·亚历山大:《博物馆变迁:博物馆历史与功能读本》,陈双双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年,第258页。所以,博物馆展示已不再像16 和17 世纪那样是独立物件的个体集合或堆砌——它们在那只是体现着(永恒的)自然奇迹那令人难以置信的多样性和相关性——而是成为了承载着各种意义的文化景观。
(一)文化景观的制造
关于“景观”⑤“景观”一词的英文在学术界有两种译法,分别是“landscape”和“spectacle”。首先,“landscape”根植于广泛的自然、应用和社会科学,它作为艺术活动中的审美和再现对象,最早出现在希伯来的《圣经》旧约全书中,被用来描写梭罗门皇城 (耶路撒冷)的瑰丽景色;其次,“spectacle”来源于居伊·德波的《景观社会》,该词被译为“景观”,体现出了此概念所指称的事物不为主体所动的那种静观性质。,根据行为地理学的理论,它存在于两类不同的环境之中,即“现象环境”与“行为环境”,在这两者当中,前者所包含的是自然现象、文化环境以及人类活动所改变或创造的建筑环境,后者则是指从现象环境中通过人类价值准则筛选传承出的社会和文化事实所构成的环境。①戴伦·J.蒂莫西、斯蒂芬·W.博伊:《遗产旅游》,程尽能译,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8页。那么基于这种观点,可以肯定,博物馆所制造的文化景观无疑存在于行为环境中,因为只有被认可为观赏景观的客体才能进入展厅,成为旅游吸引物,并同观众形成看与被看的关系,从而完成价值的交换。所选物品凝聚而成的文化景观,构成了博物馆旅游吸引物的核心部分,而由于这种吸引力隐含着一种“被凝视”的特性,所以这与居伊·德波(Guy Debord)所提出的“社会景观”(Spectacle)有着更多的耦合。
德波所论及的“景观”,实则是那种为取代存在而刻意“制造”的表象,即人们明知道景观是“被制造”出来的,但却依旧对其不断沉迷且难以自拔。英文中的“Spectacle”一词出自拉丁文“Spectaculum”“Spectae”和“Specere”等词,意思是与人的视觉相关的“观看”“被看”与“重复地看”②[法]居伊·德波:《景观社会》,张新木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译序第13页。。可见,景观乃是一种基于视觉传播机制的现代社会统治形式,即它为治理者提供了一种视觉传播化的控制。因而,基于“Spectacle”一词的词源,通过取其“观看”与“被看”之意,以弱化景观(Landscape)的地缘性而强调其“被制造性”,则可尝试深入推演博物馆这一将原初语境中的艺术、历史和自然当作商品一般来展示的形式。
博物馆作为一种话语体系,它所涵盖的内容和结构是一组丰富的文本,而在其中,展示则是在视觉上使这组文本客体化的重要表述,即它是在一定空间内,以从原初语境中抽离出来的物件为媒介,按照某个特定的文化主题,以秩序化和艺术化的形式所组成的展品群落。因此,展示本身虽无形,但其所构成的“景观”却是一种规则和顺序,即通过物的组合和碰撞来以视觉形式表达某种预设的内涵。换句话说,博物馆以陈列所拼合而成的视觉图景,也可以被看作是米切尔(William John Thomas Mitchell)所说的那种“经由文化调解”的景象,就像他所主张的,“景观”这个概念应作为一个动词来理解,而非名词③William John Thomas Mitchell, Landscape and Power,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2,p.1.。
(二)被展示的文化:“真实”抑或“现实”
当人们已经意识到,博物馆作为由一系列展品所聚合而成的景观,实际是来自对文物的组合和再处理,且已经论证了物品的再塑造属于博物馆这一文化景观的演变过程,那么应该如何来评价以物品的选择和信息的阐释所建构的展览呢?如果从动词角度来理解经由展示在博物馆中所构建的景观,那么这种星罗棋布的展览究竟是在呈现一种“真实”还是在模仿“现实”?博物馆展示是由包罗万象的物品所构成的,且每一件物品的展示价值都与意义相伴而生,因为物品本身并无固有价值,而且它也并不像博物馆所鼓吹的那样可以“为自己发声”④Spencer R.Crew and James E.Sims,Locating Authenticity:Fragments of a Dialogue,in Ivan Karp and Steven D.Lavine eds,Exhibiting Cultures: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Museum Display,Washington D.C:Smithsonian Institution,1991,p.159.。事实上,博物馆对物品的展示方式就是它对观众的阐释方式,是它作为公共景观的独特语言,它能依照历史的脉络和空间的变化,来以原始物为媒介展现悠久的文明,也可以旨在突出主题或风格的共同特征,对物品进行分类和组合,即从星辰大海中遴选出吻合某种特质的物品来展示。所以从这层意义上看,众博物馆的展示都是一个建构的事件,是一种复杂的意指系统。⑤屈雅君、傅美蓉:《博物馆语境下的性别文化表征——以妇女文化博物馆为例》,《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
博物馆展示是一系列冥思苦想的行为产物,而在这一连串的环节中,无论是从搜集材料到重写文本,还是从建构意义到精心策划,管理人员、参展者、组织方甚至赞助方和媒体,都会对这一过程的实际效果起着重要的影响和制约,正如英国后马克思主义学者托尼·本尼特(Tony Bennett)所言:“我们不仅要关注博物馆都展示了什么,而且还要注意都有谁参与了展示及其过程。”①Tony Bennett,The Birth of the Museum:History,Theory,Politics,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5,p.103.一方面,为迎合和满足展览主题的需要,这些施为群体往往会对物品精挑细选,并通过改写和重塑来使之顺应按照主流观念所设计的叙事文本;另一方面,他们通过展品转化来生产意义,更是一个引导观众在面对文化时,要从单纯的惊异过渡到静观默察的创作过程。可以说,博物馆的展示语境本身就代表着一定的立场、裁决及对展品事件的改写,并且,它并不是简单地发表客观的描述或形式逻辑的聚合体,而是要生产含有主观因子的各种表象,并根据历史上具体的特定视角来确定价值和意义。②Henrietta Lidchi,The Poetics and the Politics of Exhibiting Other Cultures,in Stuart Hall eds, Representation:Cultural Representation and Signifying Practices,Los Angeles and Washington D.C:SAGE,1997,p.160.
在此,借用一部看似搞笑但却能反映现实的影片,或许可以更加形象地阐明这一观点。例如,在肖恩·利维(Shawn Levy)所执导的《博物馆奇妙夜》(Night at the Museum,2006)中,位于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庄严的大厅里,陈列着这个世界让人惊奇的所有事物——如狂暴的史前生物、野蛮的古代战士、被时间流沙埋掉的原始部落以及改变了历史的传奇英雄等——而当这一切被并置在所建构的语境中时,它们就无形中变成了栩栩如生的展品和标本,并为这个公共机构服务,甚至,它们还在影片中被赋予了生命,在月光映照的午夜中以历史的面貌上演着现实世界的图景。就好比影片中一位很重要的历史人物,即美国第26 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由罗宾·麦罗林·威廉姆斯(Robin McLaurim Williams)扮演——在博物馆处在白天时,他只是一尊平凡的蜡像,要靠解说员来诉说他的历史伟绩,但当夜幕降临,月光为历史开通了一条通往现下时空的隧道时,复活了的罗斯福则背着猎枪,穿梭在博物馆的夜景中,站在远方深情款款地凝视着那位印第安美女萨卡加维亚(Sacagawea,由米苏·贝克,Mizuo Peck 扮演),并在其遇难之时奋不顾身地救了她,从而获得了爱情。这一情节乍观之下的确发散着喜剧的色彩,但或许很少有观众能想到,正是这位总统曾在历史上说过“只有死了的印第安人,才是好的印第安人”,而这一幕虽说是以戏谑的方式模糊了历史的真相,但它却以巧妙的方式复活了美国现实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印地安人和美国西部只有在美国的保护下才会幸福,也只有在美国的照耀下那里的一切才会有价值。③黄慧:《博物馆里的历史再现——对影片<博物馆惊魂夜>的意识形态分析》,《电影评介》2008年第21期。那么透过这部影片所呈现的幻景,也可以反观现实世界的展览:现实中的博物馆虽然承载着许多知名的历史文物和艺术品,可它们显然与其原初记载有所出入,因为在治理机制的选择和建构下,它们仅是一个历史符号被整合在了现代性的发展链条中,并在转喻时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即作为叙事的形象语言——从而诉说着新的“历史”且阐释着国家的意识形态。
正是选择和建构的主观性行为,使得博物馆展示信息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发生了改变。面对类似的情况,暨南大学赵静蓉教授认为:“在博物馆的参展行为中,孕育了很多偶然性、随机因素和虚假行为……公共领域所呈现的东西一定是局部的、被规约的和统一的。所以说,承担着文化治理责任的博物馆,在开放‘公共性’之前,实际上首先已经进行了自我审查,同任何一种公开展示的社会行为或社会机构一样,博物馆也是既‘发扬’又‘遮盖’。”④赵静蓉:《从文化遗产到审美资本:论博物馆文化治理功能的形成机制》,《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2018年第1期。由此而论,任何展示在这种情况下都仅能以物品反映出社会真实文化的一小部分,而这一部分必然是社会所推崇的主流价值观和精英文化。所以,当博物馆管理机制在按主旨对物件进行筛选、美化和赋予一定的观念、情感和倾向时,展示就在秩序化的建构中成为了一个非客观的“他者化”的过程——即它已无法中立地还原真实性,而是在按照某种意图以制造景观来模仿现实,且隐匿着主观的决断和偏见。
通过分析现代博物馆展示所潜藏的事件建构和意义制造,不难发现,博物馆展示所传达给观众的信息在很大程度上都含有主观因素,它既是一个阐释性和生产性的过程,也是一个对真实性过滤和改编的过程。那么借助这一系列的运作,博物馆也默无声息地标榜了它作为一个情境主体的态度,并也借此映射了它自身的治理规则。因而立足这样一种姿态,便可以在推演的过程中找到一个思考的反向路径,即质疑潜藏在“可参观性”背后的那些“看不见的手”是如何在制造文化景观的同时对观众实施治理的?借用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分析话语,现代博物馆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国家权力的附属品与象征物,是展示国家荣耀与民族历史的舞台,是对“现代人”进行规训、教育和监视的场所,它的空间是开放的,背后的目的却是隐蔽的。①转引薛冰清:《美国建国初期的公共文化空间与国族构建——以皮尔博物馆为中心》,《史学月刊》2019年第3期。
三、空间的权力话语:秩序中的身心规训
就现代博物馆这一由展品所聚合而成的公共景观而言,对其本质的深入讨论仍需回溯到米切尔所提倡的“景观”动词化上。在《风景与权力》一书中,米切尔要求读者不要从“景观是什么”或“它是什么意思”来解读,而是要思量它作为一种文化实践活动和主体身份的建构过程到底做了什么?②William John Thomas Mitchell, Landscape and Power,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2,p.1.那么针对博物馆这一景观,本尼特的观点似乎标注了它的动词属性,正如他在《博物馆的诞生》中所谈到的,博物馆里的每一个物件、每一间精致的展厅、每一根优雅的立柱,都在按照秩序谋划着营造旨在训导参观者身心的“检视和管理空间”(Space of Observation and Kegulation)③Tony Bennett,The Birth of the Museum:History,Theory,Politics,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5,p.24.。
(一)理性秩序下的展示
关于秩序,福柯提出,它既是作为物的内在规律和确定了物相互间遭遇的方式的隐蔽网络而在物中被给定的,秩序又是只存在于由注视(Regard)、检验和语言所创造的网络中④[法]米歇尔·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莫伟民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前言第8页。。由此而论,秩序对博物馆而言不只是对物的有序陈列,它还涉及着整个空间的布局,而在这一方面,1851年由伦敦为举办世界博览会所建设的水晶宫,则可谓是这一建构的表率。对此,本尼特在《博物馆的政治理性》(The Political Rationality of the Museum)一文中评论道:“水晶宫的建设对随后一系列展览性建筑的发展都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首先新材料(铸铁和玻璃板)的使用为大型空间的封围和照明提供了条件;其次清除展览区的边缘和中心的空地,以允许留出畅通通道以供公众流动,并且把一堆乱哄哄的人群安排成有序的公众流动;最后,以回廊形式提升了观众的优越位置,使观众观看自己,从而将自我监督和自我调控的规则引入博物馆建筑,公众不仅成为了控制观赏的主体,而且也成为了客体。由此看来,博物馆具体化了全景敞视主义(Panopticism)的主要目标——即让这个社会以透明的形式处在自己控制的凝视之下。”⑤Tony Bennett,The Birth of the Museum:History,Theory,Politics,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5,p.101.因而,基于这样一种分析,可以肯定,秩序化不仅是博物馆内部一切事物的有序表现,而且它也是建筑空间的一种治理手法。
从某种意义上说,公众步入一座公共性博物馆参观,看似是一个自主性的行为,但事实上,从他踏进这一公共领域时起,他会看到什么,会遵循怎样的顺序去看,也许会生发怎样的感觉,甚至他如何以观览来完成自我规训和教育……这些都早已被那些“看不见的手”预先设定了⑥赵静蓉:《从文化遗产到审美资本:论博物馆文化治理功能的形成机制》,《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2018年第1期。。具体来说,博物馆在向公众开放以前就为其划分好了不同性质和功能的区域空间,规定了其在展厅中的观看方式,并以此引导他们在观览时进入指定的区域,接受特定主题所宣传的文化及内涵。那么在这种先在的规范下,现代博物馆显然隐含着一个“看与被看”的视觉结构。
(二)看与被看:作为被凝视与构设的主体
“看与被看”是一个辩证的关系,它是现代建筑中主动与被动相交织的视觉结构,即体现在“人看物”与“人被看”的互存关系上。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曾以埃菲尔铁塔为例描述过这种视觉关系,他写道:“当人们向埃菲尔铁塔投以目光的时候,它是对象,而当人们登上它时,它则成了目光,并把刚才看着它的巴黎变成身下既宽广又集中的对象。”⑦[法]罗兰·巴特:《罗兰·巴特随笔选》,怀宇译,天津:百花奇艺出版社,2005年,第333页。现代博物馆与其有着某种相似之处,因为当它处在人群目光鸠集中被凝视时,它所承载的游客也成了被审视的对象。确切地说,博物馆自步入公共化后,它作为建筑不仅在外观上依旧保留了象征性的功能,同时其内部也以各种变化构成了一系列空间与视觉的新关系,在其中,公众可以看到为审视而安排的展品,而建筑也可以以它的展示来调控和启蒙公众的行为与认识。可见,这种公众与被看物之间的流动关系作为一种现代性的视觉模型,既自反性地说明了公共博物馆空间的特征,又自明地揭示了公众作为观者在博物馆空间中的“第二身份”:即被凝视的“景观”和被构设的“对象”。
首先,就观众于展厅中作为被凝视的“景观”而论,现代博物馆一直在承担着一个管理者的身份,并潜移默化地规定着主体的行为。而在这种情况下,身处博物馆秩序中的绝大多数观众,都会在权力话语所提出的各种要求下——如有序的排队准则、珍贵展品的拍照方式等——调整自己的行为。“看与被看”的视觉结构隐喻了空间中所潜在的目光治理术,无论是博物馆监控系统的上层目光,还是展厅内无序错乱的他者目光,它们都是公众在跨入展厅后所更多依赖的力量,即在目光凝视的施为作用下完成自我管理。然而,针对这两种治理目光来看,由于博物馆空间自身存在着某种局限性,所以它往往会更多地借助于他者的目光(人群的目光)来对观者实施治理。
按照之前本尼特的说法,现代博物馆无疑已经具体化了全景敞视主义的目标,但若从空间的视觉结构检视,博物馆同监狱那种“全景敞视建筑”①“全景敞视建筑”(Panopticon)是指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于1791年首次倡导的圆形监狱,其基本结构是监狱的四周是一个环形建筑,中心是一座瞭望塔,瞭望塔有一圈大窗户,对着环形建筑。详见[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224页。还是有着局部的不同,即它并无一个由中心瞭望塔所确立的垂直视觉结构,从而使之以一个全能的视点将人群归入其中。与环形监狱的结构不同,博物馆空间是呈以平面化特征,这同它对物的展示是在遵循一种线性的进化论序列有着直接的关联;此外,立柱、廊台及隔板等元素的存在,铸成了博物馆展示空间的不透明性,而在这种格局下,上方管理者也很难立足一个视点将目光无限延伸。因此,当这种散落式的目光无法发挥瞭望塔的视觉功能,从而让个体处于绝对主体的目光下时,博物馆对观者的规训无疑需要诉诸他者的目光。举例来说,博物馆规定了公众观览过程中的行为规范,但它碎片化的管理目光却无法保证每一个个体都能自觉地接受它,而这时,他者的目光往往可以起到实时的作用,即使得同一展厅中的每一个“被凝视的人”都能警惕自己的行为不会冲破空间中的秩序与规则。因而从这个角度看,他者的目光是在辅助管理者共同维护博物馆有序的环境,及规训其所容纳的游客以合理的姿态接受“被展示的文化”——这便是被看的境况作用于观众行为及展示秩序的表现。
其次,在观众作为被构设的“对象”方面,现代博物馆所扮演的是一个双重角色,借用美国学者卡罗尔·邓肯(Carol Duncan)的话说,“公共博物馆既是观览者获得精神提升的公共空间,也是意识形态强有力的机器。”②Carol Duncan,The Aesthetic of Power:Essays in Critical Art Histor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p.191.现代博物馆的展示建基于国家话语的宏大叙事中,它旨在让艺术、历史、自然和科技像商品博览会一般向公众传递美与知识。然而,综合前文所述,现代博物馆本身并不是对历史和信息的完整还原,而仅是一种选择性的建构,即更多地展示符合国家话语的历史“片段”,从而使公众在凝视展品的过程中达到对国家和民族文化的合理认同。国家话语“力量”之强大,使得个体力量在面对公共空间以媒介所宣扬的积极意义前显得微乎其微。或许可以说,多数参观者在“观看”展品时,个人思考时常会处于离线状态,而只能对包蕴在权力话语内的知识和观念表示认同与接受。虽然,观众在观览博物馆时可以从展品中收获美感与知识,但不可否认,这一切并非源自观者自身对客观世界的体验与思考,而是经由拥有一定文化资本和社会地位的主体通过设计所生产出来的。
关于“话语”(Discourse),根据福柯的观点,它是由一组符号序列构成的,它们被加以陈述,被确定为特定的存在方式③Michel Foucault,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2,p.121.。现代博物馆的话语建设,可以说是创造主体将权力转化为知识的工程。例如法国卢浮宫,它作为加强新构建的国家特征的工具(自18 世纪后期开始),其话语设计是旨在向公众宣传这个国家的内在“天赋”神话及伟大历史使命的形象①Kirk A.Denton、宋向光:《博物馆的记忆、叙述和意识形态作用》,《中国博物馆通讯》2016年5 月总第345期。;再好比中国国家博物馆,它作为中国最高的历史文化殿堂,其展示话语是意在代表国家反映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珍藏民族集体记忆、传承国家文化基因,荟萃世界文明成果,构建与国家主流价值观和主流意识形态相适应的中华文化物化话语表达体系,引导人民群众提高文化自觉、增强文化自信,推动中外文明交流互鉴和发挥国家文化客厅作用。②详见中国国家博物馆官网:http://www.chnmuseum.cn/gbgk/zndw/.可见,话语所代表的隐形权力,从根本上决定和构设着公众可以在博物馆看到什么,以及他们在观览时应该如何认知国家、社会和文化——当然,在权力主体所创建的文化景观中,也并不意味公众的独立判断能力会在观览中全然尽失,因为知识的获取更多地取决于感情层面的认知能力,而且一个人能否从展品中获得精神的升华,还要取决于一个人的移情(empathy)能力,甚至包括他在生活世界中的各种积淀与自我定位。
简言之,现代博物馆是民主政治的产物,其展示始终都在围绕“人类如何认识世界”来设计,但从另一个层面看,这种现代性的公共博物馆也迎着浪漫主义的怀旧情绪,成为了一部维系国家历史、民族遗产与文化传统的宣传与治理机器,就像胡柏—格林希尔所指出的那样:“公共博物馆从一开始就被塑造成了含有两种矛盾的机构,即艺术精华的殿堂和民主教育的功利主义工具。”③Eilean Hooper-Greenhill,The Museum in the Disciplinary Society.in Susan Mary Pearce eds,Museum Studies in Material Culture,Leicester: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1989,p.63.由此看来,现代博物馆的运行,一方面是在以公共性明示一种不同文化价值可以在此平等交流的民主,另一方面它也意在引导公众在品味“民主修辞”下的文化精品时,其身心要被空间的种种秩序和话语所“塑造”,使人在公共景观的迷入中走向单向度的默从。④[法]居伊·德波:《景观社会》,张新木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译序第19页。细想一下,这的确是一种相爱相杀且互生共存的玄妙关系。
综上所述,在现代博物馆展示语境的建构系统中,“物品”被人们剥离出了它原初的事件,而被重塑为了脱离了其(部分)原真性的“展品”,即沦为了博物馆展示语境中的叙事要素。在这样的主观建构中,一切“可参观性”背后的“不可参观性”都隐匿着某种权力话语的治理与规训。
然而,沿着这一分析,也可以反向洞察到,博物馆力求以建构景观把自身的意义关闭在人们的视觉美学之中,并通过引导公众审美地看待其所谓“自然层面”的形象,让人们遗忘其内部的权力与资本所造就的享乐、霸权和欲望的空间内涵⑤周志强:《景观化的中国——都市想象与都市异居者》,《文艺研究》2011年第4期。——而并非去坦然呈现其背后的结构差异与权力失衡等问题。正如美国斯顿霍尔大学教授珍妮特·马斯汀(Janet Marstine)在论述怀疑者立场时所谈到的:新科技,并非旨在创造真正的互动经历,而只是将参观者转移开,以防止他们提出更多有关博物馆权威性和真实性的问题。⑥[美]珍妮特·马斯汀:《新博物馆理论与实践导论》,钱春霞等译,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08年,第32页。那么对此,文章最后尝试提出一个倒立性的问题:即当面对全面解构展示秩序的权力话语时,博物馆自身可以做些什么呢?如果它能够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来解构其潜藏的意识形态和检视景观化知识的真实面貌——如“后博物馆”⑦受后现代主义影响的博物馆,胡柏-格林希尔将其定义为“后博物馆”(Post-Museum)。按照她的解释,在后博物馆中,知识已变成了一种片段式的和多义的形态,它旨在化解不必要的统一观点,而呈现一系列的见解、体验和价值观。详见Eilean Hooper-Greenhill,Museums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Visual Cultur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0,p.152.的发展——是否就意味着它可以在真正意义上被大众所拥有,以及在今后更加积极和持续地发展呢?这仍有待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