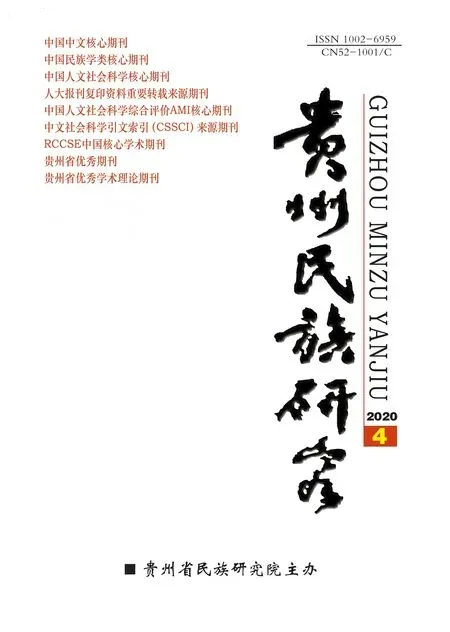基于多元文化视角下对少数民族文学“文化寻根”的探析
2020-02-16徐桁
徐 桁
(陕西中医药大学 人文管理学院,陕西·咸阳712046)
近些年来,随着社会不断地发展,各种文化之间的交流更加频繁,信息流通越来越发达,新的文化层出不穷。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全球化不断地深入,在多元文化的影响和冲击下,少数民族文学的民族文化意识逐渐觉醒,少数民族文学“文化寻根”潮流逐渐兴起[1]。同时,随着全球文化、资本的流动加速,在多元文化格局中,少数民族具有身份局域解构性和混杂性等新特征,少数民族文学在这样的新文化语境下成了第三者“窥视”和消费的文本。因此,在全球化时代的多元文化格局中,为了促进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少数民族文学“文化寻根”运用文化的形式来书写、丰富中华文化,促使其向多元文化转变,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建构。
一、少数民族文学“文化寻根”的兴起
少数民族文学“文化寻根”始于20世纪末,近些年来,随着全球化深入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我国的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产生了文化碰撞,并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在这种环境中,少数民族文学也曾经试图用西方文化来创作文学作品,但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在此过程中,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者越来越迷茫,导致很多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者产生了文化寻根和文化认同的需要[2]。20世纪80 年代,在我国改革开放的背景下,一些外来文化涌入国内,对我国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和影响。在这些外来文化的冲击下,我国文学界兴起了一股“理性主义启蒙”的全球化浪潮,爆发了寻根文学思潮。在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少数民族文学逐渐获得了自我的文化个性,涌现出了一大批具有“文化寻根”的优秀作家,如乌热尔图、张承志、吉狄马加、扎西达娃等[3]。少数民族作家开始进行了自身的文化觉醒和身份建构,创作开始倾向于关注本民族文化、自觉地吸收本民族文化,或表达多元文化碰撞的困惑与迷茫、或挖掘民族文化传统,民族身份认同意识逐渐觉醒,启动了少数民族文学的“文化寻根”,开始由书写政治转向书写文化。随后伴随着多元文化的不断融合和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复兴的潮流,为了推动少数民族文学的“文化寻根”不断走向纵深与广阔,这些少数民族作家致力于多元文化与民族文化的融合,对族群文化进行了重新建构,“文化寻根”呈现出繁荣景象。
进入新世纪后,在少数民族文学中,读者窥探到了一个装饰性文化区域,民俗以空间化的形式,成了大众文化语境中传统文学话语向消费文化话语的一次缴械,民俗在少数民族书写中,为读者提供一种平面化、无深度的消费场景,并成了所有文本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随着文化寻根思潮的兴起,少数民族文学的“文学寻根”成了中国文学“文化寻根”队伍中一支重要的力量。少数民族文学开始真正寻找本民族文化的根所在。面对多元文化的冲击,本民族文化身份意识也开始觉醒,文学创作开始关注本民族的族群心理和思想,开始更多地关注本民族文化,挖掘本民族传统文化中有生命力的东西。
二、多元文化视角下少数民族文学“文化寻根”的价值体现
(一) 构筑了中华文化的多元图景
20 世纪末以来,少数民族作家逐渐走向对族群文化传统的关注,随着民族文化认同意识的觉醒,少数民族作家开始自觉地开掘族群文化传统,尤其是在全球化趋同性加剧、多元文化的冲击境遇下,民族传统文化逐渐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因此,为了唤醒族群的情感与记忆、凝聚族群的合力,致力于“文化寻根”的少数民族作家开始捍卫族群文化的独立地位,维护族群文化传统。
一方面,以扎西达娃、张承志、石舒清等为代表的作家们开始关注少数民族宗教信仰,开始挖掘与呈现各民族传统文化。扎西达娃的《西藏,隐秘岁月》 《西藏,系在皮绳扣上的魂》等作品都有对族群宗教信仰的书写,他对藏传佛教在多元文化冲击下的境遇最为关注[4]。小说彰显了藏族人对宗教信仰的虔诚与执着,通过实有与虚无的纠葛,讲述了主人公次仁吉姆忍受贫穷、放弃爱情,次仁吉姆终其一生虔诚供奉修行大师的故事,不但表达了作者对藏族宗教文化传统的肯定,还表达了作者对藏族宗教文化传统的否定,但到头来次仁吉姆得到的却是一堆白骨。而回族宗教信仰中的核心内容是大无畏、洁净精神,张承志、石舒清等通过深入挖掘回族文化传统,以回族宗教信仰为核心,表达出了对洁净精神的追求,刻画出了坚守信仰的大无畏精神,充分展现出了回族文化传统的精髓。如张承志的《心灵史》以强烈的理想主义精神,表达出了即使遭遇血雨腥风,信仰永不变的决心,倾心表现了历史进程中回族对宗教信仰的坚守,描述了清代回族哲合忍耶教派的发展历史。石舒清的《清水里的刀子》则从现实出发,对回族宗教与百姓日常生活进行了描述。马子善的儿子准备宰杀家中的老牛,用来祭奠自己的母亲,但在宰杀之前,老牛就开始不吃不喝,就好像知道要宰杀自己。马子善于心不忍,在他看来,这是老牛为了保持内里的洁净,而选择的一种不吃不喝方式,最终老牛平静、安详地死去。作者通过关注回族的宗教信仰,充分体现伊斯兰教教义。作者还借助马子善对老牛之死的感悟,向人们展现出了一种庄严感与神圣感,表达了回族人对洁净精神的追求。
另一方面,致力于“文化寻根”的少数民族作家还注重从少数民族口传文学中吸收养分,如阿苏越尔、张承志等少数民族作家,他们从口传文化中充分开掘了族群文化传统。口传文学是广大民众集体创作、口头传承的文学作品,是“族群记忆的代代相传,是富有道德感的生活内容和感情历史,是一种传统精神、人生教育方式。”作为一位彝族诗人,阿苏越尔善于从彝族创世史诗中吸收养分。他的很多创作中注入了关于“雪”的诗歌,尤其钟爱彝族史诗《勒俄特伊》。彝族人对雪极为崇拜,“雪”承载着彝族文化内涵的意象,该史诗认为一场红雪衍生出雪子十二支。为了充分体现作者对古老民族渊源的诗性阐释,阿苏越尔将祖先对“雪”的崇拜意识注入诗歌创作中,借助“雪”与“我们”终身相伴关系的书写,将“雪”置于人的成长历程中,凸显出了诗人对以“雪”为代表的彝族文化的“一往情深”,如《雪中自述》 《最后的雪》 《第二号雪》 《雪线》等。在阿苏越尔诗歌中,“雪”的描写随处可见,充分表达了诗人对彝族文化强烈的认同感,展现了诗人对古老民族渊源的诗性阐释。如《雪祭》中“第九十九片雪张开巨嘴/扑向断奶的等待……”“有人说,生命的气息/最早泊于雪谷的唇……”“天时间遥远,雪谷苍茫/何不与我共同一生?”而张承志的《黑骏马》 则运用蒙古族民歌《钢嘎·哈拉》,将叙事与抒情相互交织在一起,表达了白英宝力格的悔恨、忧伤情感,铺陈了白英宝力格与索米亚的故事,小说具有盎然的诗意。
由此可见,20世纪末,在多元文化的冲击下,致力于“文化寻根”的少数民族作家们,执着地挖掘各民族文化传统,从各自的人生体验出发,推出了一批具有民族文化特质的文学作品,构筑了中华文化的多元图景,拓展了中国文学的话语空间,推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复兴[5]。
(二) 丰富了中国文学的表述形式
1980 年后,随着时代风气和文化语境的变化,少数民族作家在创作实践中表现出徘徊和犹疑,呈现出复杂和纠结的局面。许多作家开始致力于探索“怎么写”,将对文学形式的探索推向了高峰,将“怎么写”提到了文学创作的最重要位置上,如马原、格非、孙甘露等先锋作家。1988年,色波在《得与失——关于本期专号小说》中指出:“在传统精神与现代观念之间,在地区意识与世界文化之间,年轻的西藏小说像时钟的摆锤一样,左冲右突,焦灼不安。”20世纪末以来,在寻民族文化之根上,众多少数民族作家也尝试运用各种现代艺术形式,毫不例外地参与到了文学形式的探索中,并为之做出了很多贡献,如阿来、扎西达娃、阿库乌雾、潘年英等。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许多外来文艺思潮逐渐涌入我国,为了确保民族文学的发展,许多致力于“文化寻根”的少数民族作家开始对民族文学进行了思考,开始积极尝试以各种现代艺术形式寻民族文化之根。
1980 年,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创作手法传入中国。在文学形式探索上,致力于“文化寻根”的少数民族作家力图将魔幻现实主义本土化。为此,一些藏族作家自觉地将其与充满神秘色彩的藏文化相结合,借助魔幻现实主义手法,制造出亦真亦幻的叙事效果,将藏族神秘宗教文化与现实生活相叠加,如阿来的《尘埃落定》、扎西达娃的《西藏,隐秘岁月》等。阿来的《尘埃落定》将古老的神话、传说、歌谣等描写得淋漓尽致,活灵活现。作家从藏族民间人物阿古顿身上吸收营养,塑造了一个亦魔亦幻的“我”。小说中人的耳朵里可以盛开花朵、没有舌头的书记官能重新开口说话,死囚穿过紫色衣服后,具有了神力。这些神奇的人、物、事使小说具有了魔幻色彩,也充满了神秘的藏族生活气息。而扎西达娃则是最早接受魔幻现实主义手法的一位少数民族作家,他致力于将魔幻现实主义本土化探索,制造出了亦真亦幻的叙事效果。此后,魔幻现实主义手法成了中国作家文学创作的常用手法,其中国化获得巨大的成功。
1980 年以来,随着改革开放不断地深入展开,在多元文化的冲击下,少数民族作家日趋关注“写文化”。在文学形式的探索上,致力于“文化寻根”的少数民族作家追求一种杂糅性语言,这对中国文学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在汉语书写中,杂糅性语言是指具有杂糅性和混杂性等语言风格,携带母语思维的作家们运用特有的词汇对汉语句式进行创造,并且在汉语创作中,语言的杂糅性具有本民族文化特征,常表现为具有大量文化异质性的语词。在《心灵史》中,张承志运用了诸如拱北、多斯达尼、卧里、口唤等大量伊斯兰教(回族) 的词汇。这些陌生于汉语的词汇,负载着浓厚的伊斯兰教内涵和色彩,是回族语言体系中的语言表述,充分展现了回族特殊的民族心理和文化感受,极大地提升了汉语整体的宗教表现功能,扩展了汉语词汇的范畴。在汉语表述中,具有异质文化的陌生词汇是对汉语表述创新的表现,也是对汉语词语范畴的极大拓展。并且在结构、内在逻辑、语法等方面,少数民族作家利用母语思维或母语表述对汉语进行了解构与重组,这也是语言杂糅性的表现。彝族诗人阿库乌雾的诗歌大量使用了双语、双音节的词语,甚至创造了“第二汉语”。他一直坚持双语写作,诗题常常以单音节、双音节和三音节为主,并且为了将母语文化融入到诗歌中,他或通过母语文化重组、解构汉语表述,或运用彝族传统词法、句法的即兴倒装。
另外,随着全球化不断深入,面对日渐衰微的本民族传统,为了重构民族文化传统,人们对写文化更加重视,使得部分致力于“文化寻根”的少数民族作家具有了写民族志的倾向。1980年以来,“写文化”被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作家所关注,民族文化认同意识逐渐觉醒。1990年后,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一些外来文化涌入我国,这对我国传统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少数民族文化传统也不例外。面对现代性冲击,为了重构民族文化传统,部分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开始转向民族志的方向,力图通过写文化来振兴日渐衰微的本民族传统文化。他们吸收了人类学的民族志写作方法,采用人类学走进田野的方式,借鉴了人类学“深描”的方法,以纪实的方法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所见所闻进行了记录。并且这些“文化寻根”的少数民族作家将地方性知识的写作成为彰显民族个性的选择,极大地推进了中国文学文体的创新,越来越重视“写文化”,这是少数民族作家们对文学文体的一种探索。
由此可见,20世纪末以来,在多元文化冲击下,为了拓展、促进本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创新,致力于“文化寻根”的少数民族作家通过不断地创新艺术形式,推进了文学体式的创新,有意识地将文学体式与人类学的民族志体式相结合,将本民族文化与汉文化、外来文化相结合,为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创新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0]。
(三) 促进了中华多民族文学史格局的建构
少数民族文学的“文化寻根”成了中国文学版图中一支重要的文学力量,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作家,极大地丰富了“寻根文学”思潮的创作,有力地促进了少数民族文学“文化寻根”现象的发展。“寻根文学”思潮倡导以现代意识寻民族文化之根,强调以现代意识来审视自己的文化根脉。一些少数民族女作家将民族意识与女性意识融合在一起,如央珍、梅卓等。她们以现代女性的生活体验为基础,秉承少数民族身份赋予的民族意识,从表达独立个体女性性别意识出发,创造出了具有民族文化意蕴的文学世界。寻民族文化之根的理念影响着少数民族的“文化寻根”,很多少数民族作家将现代意识融入到了创作实践中。霍达的《穆斯林的葬礼》中,主人公梁君璧是一位传统穆斯林,他不允许自己的女儿与非穆斯林男子谈恋爱,认真地固守着伊斯兰教教规,认为女儿的恋情触犯了穆斯林与“卡菲尔”结婚的禁忌,最终导致女儿带着遗憾死去。霍达以一种文化自省的精神对民族传统文化进行了审视,对主人公的偏执、固守进行了批判,充分体现出作者的现代意识。张承志的《黑骏马》中充分表达了作者对草原底层百姓坚韧的生命力与博大胸怀的敬佩之情。小说中的“我”长大后,离开了草原,他不理解抚养其长大的额吉奶奶与女友索米亚对黄毛无耻行为的宽容。但经过多年之后,“我”终于明白了他们对困难生活的坚忍,理解了他们对生命的挚爱。这是作者对人文主义情怀的真挚表达,是以现代意识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审视。由此可见,“寻根文学”思潮以现代意识寻民族文化之根的倡导,促使“寻根文学”思潮倡导与文学实践的并存,提升了少数民族作家对本民族文化的自觉认同。他们将民族性与人类性融为一体,创作了很多文学经典,极大地促进了少数民族作家与世界的接轨,推动了少数民族文学“文化寻根”的发展。进入21世纪以来,鄂伦春族的敖长福、撒拉族的韩文德等人口较少民族作家也执着于挖掘族群文化的根脉,先后推出了很多文学作品,如《北方女王》 《家园撒拉尔》等。这些文学现象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文学的版图,拓展了“寻根文学”思潮的创作路向,促进了中华多民族文学的繁荣发展[11]。
三、多元文化视角下促进少数民族文学“文化寻根”的策略
(一) 坚持民族特色,增强少数民族文学的文化认同感
“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中”。在当前的多元文化语境中,应使少数民族文学成为主流话语有力的组成部分,源源不断地为中国文学及主流话语注入新的生机,丰富少数民族文学和文化的活力,并在保持本民族文化的基础上,使其进入到中国文化的舞台之上,融入到主流话语中去,增强少数民族文学的文化认同感,促进少数民族文学“文化寻根”在多元文化环境下不断发展。
一方面,在多元文化格局中,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应重新建构少数民族传统,重新构建和改造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中的思想、观念、行为等,增强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现代社会适应能力,从而将少数民族文学融入到主流话语中,增强其文化认同感,促进少数民族文学多元化发展。
另一方面,在多元文化格局中,少数民族的民众精神缺乏,部分民众甚至忘记了民族传统。因此,在促进各民族发展的同时,少数民族文学应积极地引导民众,想方设法地对民族传统进行最大程度的激发,引起他们对过去传统文化的思念和追求。“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在现代化、多元化的发展中,不仅要扶持和发展各民族自己的优秀作家和杰出作品,还应使民众发现民族传统所蕴含的巨大文化价值,尤其是历史极为悠久的口头文学传统,从而使民族传统释放出巨大的文化魅力和价值,使少数民族文学自觉回到本民族文化中寻找自我,增强民众对少数民族文学的文化认同感。
(二) 以“流散视角”书写少数民族文学,提升民族文化水平
目前,“流散”现象是一种跨民族、跨语言、跨地区的情感和文化状态,随着城市化和全球化不断发展,“流散”现象成了必然产物,少数民族作家的生活和文化状态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以跨民族、跨文化的眼光,以“流散视角”书写少数民族文学,能够对本民族进行新的文化实践和文化建构。同时,为了使共同文化记忆不至于流于表面,作家应抵制主流文化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同化,借助普通人的生存冲突和思维方式,通过展示出少数民族村庄社会内在与外部的文化冲突,描写一系列人物的命运,并使其成为少数民族文化的展演符号。在多元文化环境中,使各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冲突展现在读者面前,增强民间思维和民族习惯面临的挑战和困境。另外,在多元文化环境中,环境内部各种文化也为少数民族文学“文化寻根”带来挑战。因此,少数民族文学应不断提升自身的民族文化水平,尽可能地通过各种方式增强抵御他文化碰撞和冲击的能力,促进民族文化发展,发出民族文化自己的声音,促进少数民族文学自身发展的同时,完善民族文学批评,及时反省,形成更为完善独立的民族文学批评体系,使少数民族文学在思想内容、语言表达等方面都能进一步提升,宣示民族文化的独立存在,及时发现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中存在的问题,明确民族文化的话语权,督促和提升少数民族文学的“文化寻根”,推动少数民族文学开阔思路,最终推动少数民族文学“文化寻根”的发展。
(三) 增强民族文化身份,重新构建和实践民族文化形象
多元文化环境中,少数民族文学的“文化寻根”应建构民族文化身份。这意味着民族文化身份是少数民族文化和其他文学的区别,人的意识思想反映或写照的文学具有了民族性。民族文学是以民族文化为基础而进行的文学创作,在多元文化环境中,为了增强与其他文化之间的交流沟通,每一种文化都必须要阐释自己的文化思想、文化观点,强调自身与众不同的文化身份。因此,在多元文化环境中,为了促进民族文化的独立发展,少数民族文学的“文化寻根”在多元文化环境中,更应通过文学方式,将自身的民族文化身份向世界表明。在多元文化环境中,少数民族文学会不自觉地融入“他者”的痕迹,促使他们的文化身份越来越复杂、模糊。也就是说,民族文化身份是民族文学因民族文化基础而形成的身份标志。因此,少数民族文学的“文化寻根”必须要支持民族文化的独立性,突出作者的民族身份以少数民族思想文化为主创作作品,以文学的方式增强自身的民族文化身份。在他文化的闯入过程中,会导致少数民族文学的创作偏离少数民族思想文化主题,是少数民族文学内在文化性的突出反映。因此,在对其他文化吸收创新的基础上,少数民族文学的“文化寻根”必须强调少数民族思想文化,保持民族文化的基调,才能避免其他文化对少数民族文学质的改变。少数民族作家应察觉少数民族生活表象下面的文化新动向,利用自己对少数民族敏锐的感知,促进少数民族文学的“文化寻根”,探索少数民族社会的未来发展[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