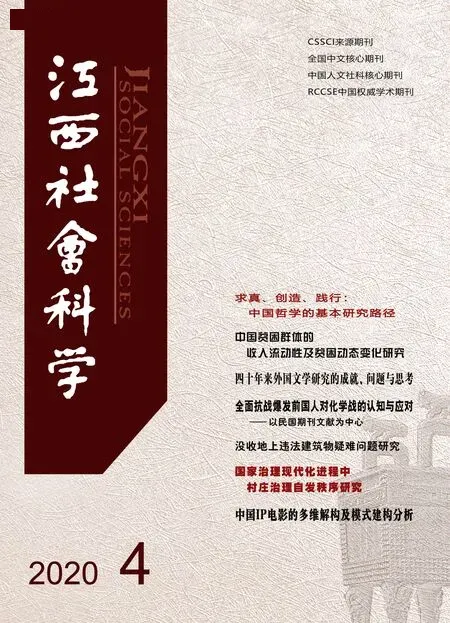刑法一元化立法模式的批判性思索
2020-02-11李怀胜
■李怀胜
刑事立法渊源的一元化与多元化之争不是纯粹的立法技术之争,它牵涉立法的价值取向等深层次问题。法典具有政治、文化整合的历史功能和独立的形式理性,但是形式理性让位于价值理性是时代的必然抉择。盲目拒绝附属刑法,导致行政法律中的刑事责任指引条款没有对应的刑法罪名,令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脱节,破坏了法律责任的完整性,弱化了刑法的规范机能,还降低了行政法律的威慑力。法定犯时代,应当正视引入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的客观需求。附属刑法有必要配置独立的法定刑,摆脱附属刑法对刑法典分则的附属性。单行刑法的立法功能在于解决类罪的体系性位置和维护刑法典的完整性,因而应避免单行刑法对刑法典的直接修改。
自1997年刑法修改以来,我国刑事立法领域大体坚持了以刑法典为唯一立法渊源的一元化立法模式。①这种立法现象不仅在我国其他法律部门中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刑事立法史上也是比较罕见的。尽管理论上对此争议不断,批评和维护者都有之,国家立法机关对此似乎保持了足够的定力。立法模式的一元化与多元化之争,是否仅仅属于法条的摆放位置这种技术性之争,甚至是单纯的形式美感问题,还是具有立法的价值取向、法律规范的功能性发挥等更具实质性的内容?答案显然是后者。笔者认为,单一刑法典的立法道路固然有其优势,其特定历史背景下的立法价值值得肯定,但是在刑事立法领域固执拒绝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的做法,造成了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的割裂,破坏了法律规范的完整性,已与法定犯时代法律规制社会生活的要求相去甚远。
一、法典化的历史价值与时代功能的再反思
追求多元化立法模式,并非要贬低法典的立法意义,相反,对于法典的功能承载、价值构造、精神塑造等都应有充分的尊重和认可。“法典是制度文明的显赫篇章。”[1](P3)但也正因为如此,真正尊奉法典,防止法典超出其应有功能之负载,才是需要认真思考的。
(一)刑法法典化历史价值的知识考证
不管是多元模式还是一元模式,刑法典都在刑事法律体系中占据着不容藐视的权威地位。选择一元模式还是多元模式,主要取决于对刑法典承载价值和精神的认识。应当清醒地看到,法典化作为世界各国共同存在的立法现象,是人类理性能力提升的标志,但更多的还是反映了法典诞生初期的特定的政治需求。
1.完成民族国家的政治与文化整合。政治整合的目的是将不同的政治力量纳入到统一的政治共同体,文化整合则是建立统一文化体的必经步骤。在人类历史上,军事征服是政治整合的前提,而只有真正实现了文化整合,统一的、具有内聚力的民族(国家)实体才能稳固存在。政治与文化整合,将次级群体“狭隘的忠诚”变为国家意识,形成多元一体的国家忠诚。[2]尽管中西方政治与文化整合的方式各异,但是,法律尤其是成文化的法典在政治整合中的作用却获得了中西方的一致承认。
法律作为一种社会控制手段,服务于某一社会系统的整合目标。在传统中国社会,“百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如何将风俗各异的群落凝结为统一的政治实体,是统治者必然考虑的重要问题。为了保证对王朝的高度忠诚,以明确成文法形式体现的法律在贯彻国家意志方面具有无与伦比的优势。“故天子诸侯之传世也,继统法之立子与立嫡也,励世用人之以资格也,皆任天而不参以人,而以求定息争也。”[3](P451)法律的目的,就是定分止争。法律的恒常性、规范性、强制性所带来的优势是任何其他社会规范所无法代替的。臣民们借由对法典的遵从表达对统治权力的顺从与忠诚,法典提供了政治正当性的法律基础。
在西方,法典的整合功能表现得更为明显。早在罗马共和国时期,《十二铜表法》的颁布大大缓解了平民与贵族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开创了成文法的新时代。在罗马帝国时期,系统的成文法典的编纂没有发生在罗马帝国的鼎盛时期,而是发生在西罗马帝国已经灭亡的衰败时期。带着恢复往日罗马荣光的崇高政治理想,优仕丁尼皇帝主持推动了法典编纂运动。在法律规范已能实现对生活秩序的规范功能的基础上进一步寻求法律的体系化并非法律的内生性需求,而藉由一部法典传达“一个国家”的政治需求,是外源性的政治动力催生了法典的诞生。到了近代,在法国大革命的激荡岁月中诞生的1791年法国刑法典和1789年《人权宣言》,更被认为标志着彻底敲响了封建主义的丧钟。
2.明确立法机关与司法机关的权力分配。不成文法时代的法律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这种专门为有特权的少数人所知道的法律……是一种真正的不成文法。”[4](P9)但是,所谓“临事制刑”的快感和“法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臆想随着“铸刑书于鼎,以为国之常法”的全面铺陈开来而成为历史的遗迹。[5](P203)在西方,法国近代刑法典的诞生带有明显的新旧政治势力倾轧的痕迹。在思想上,法国刑法典是理性建构主义的产物。在这之前的数个世纪里,“人们所公认的一项原则乃是,君主或者其他的权力机构只能宣布或发现已经存在的法律,或纠正其间所隐含的对既存法律的种种滥用情况,而绝对不可能创制法律。只是在中世纪晚期,经由主观构设而制定法律——亦即我们所知的立法——的观念才开始渐渐为人们所接受”[6](P204-205)。经历了革命的血雨腥风,如何遏制以巴黎高等法院“巴列门”(Parlement)为代表的王权势力,是法律改革的首要课题,因而约束法官,提高立法机关的权威是法典化在政治上的主要意图。[7](P50)为了防止法官在法律解释的名义下创制新法,法国1810年刑法典采用绝对确定法定刑的立法技术,“各种犯罪均作硬性规定,没有最高限与最低限之分,法官的职能实际上就是确定是否犯罪,若构成犯罪,即对犯罪者处以法典规定的刑罚”[8](P434)。这是绝对罪刑法定诞生的历史背景。1794年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编纂的《普鲁士邦法》为达到限制法官的目的,其条文总数竟然有17000多条。一般的法律既无法获得政治上的权威地位,更无法承载如此之多的条文,法典化的立法模式实在是当时立法者的最优政治选择。然而,绵密的法律条款不但没有实现法网的周延,反而制造了更多的漏洞。随着政治形势的变迁,法典限制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历史使命宣告终结,西方国家逐渐走上了多元化的刑事立法道路。
(二)立法法典化的时代走向: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抉择
法治主义要求权力机关内部具有明确的责任分派,各司其职、互相制约。法典的存在固然限制了司法机关权力的过度膨胀,迫使司法机关从立法的权限范围内退出来,但是与此同时,它也明确了司法机关的职权,消除了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侵入司法领地的模糊空间,这反过来促进了司法机关权力的成长,因为“独立的刑法典,是刑事司法职权独立性的要求”[9](P293)。法典“所关心的是系统地制定法典和使法律趋于一致,并主张将法律交由一个力争公平、地方均等之升迁机会的、受到合理训练的官僚体系来执行”[10](P174)。定罪处刑权从其他权力中分离出来,尤其是从行政权力中分离出来,促进了法官政治地位的提高与职业化的发展。法典打击了习惯法、不成文法、行政机关命令等其他规范形式的地位,在分权体制下,法典限权功能逐渐过渡到授权功能。原本为限制司法权力而设的法典,最后却受到了法官的青睐。
由此回顾法典化的历史进程,最初法典化的存在具有强烈的工具理性的导向,法典是逻辑自洽的规范体系,法典逻辑体系的完整性使其摆脱了政治、经济、宗教、道德、文化等外在因素的束缚,并形成了自成一格的形式理性,法典的形式理性有助于法治主义的形成。不过,当法典化获得主导地位之后,工具理性又必然要让位于价值理性。在当今社会,法典的政治整合与限制权力的功能被分散到了各种形式的法律中,法典在政治上的宣示意义已经大大弱化,因而不必过于偏好法典的形式美感,而应当根据时代的发展选择灵活机动的法律载体。过于执着法典的形式理性,不但不会增加法典的生命力,反而会遏制其活力。在刑事法律部门,上述判断已经不断得到事实印证。
二、单一刑法典化的规范难题:“行刑割裂”造成的无盾之法
刑事立法领域的单一立法模式已经造成某些难以掩盖的问题,典型的是规范空置现象。排斥附属刑法造成同一行为模式的不同法律后果被强行分布在不同的法律部门中,甚至因为立法的不同步,经常出现在行政法律中明确指引某种行为可以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在刑法典中却没有与之对应的罪名条款。“行刑割裂”造成的无盾之法遍布许多行政法律之中。
(一)“行刑割裂”的客观表现
在司法层面上,行刑割裂通常是指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的不畅,导致案件不能顺利进入司法程序。如果行政法律中明确指出某些行为情节严重的,可以追究刑事责任,在刑法典中却没有对应的刑法条款,这也是一种行刑割裂,是立法层面的行刑割裂。司法的行刑衔接不畅是污染了河流,而立法的行刑衔接不畅直接污染了水源。当前行刑衔接不畅遍布各类行政法律中。例如,《招标投标法》第50条规定,“招标代理机构与招标人、投标人串通,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其他人合法权益的,……,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但刑法第223条关于串通投标罪的犯罪主体却只有投标人、招标人,而没有规定招标代理机构。②类似的现象在行政法律和经济法律中还有很多,例如《商业银行法》第76条等。
目前稍微乐观的现象是,行政法律在生效实施多年之后,为其“特供”的刑事罪名才姗姗来迟。2003年10月28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第89条规定,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有该法第20条所列的五种行为之一,“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但直到2006年的《刑法修正案(六)》增设的违法运用资金罪,才间接涉及广义上的基金犯罪,而直到2009年的《刑法修正案(七)》规定了老鼠仓犯罪,才算是真正意义上确立了基金犯罪。[11]
(二)“行刑割裂”的主要原因
为何行政法律的刑事责任指引条款没有对应的刑法条款,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进一步的推论是,如果该问题能够得到很好的解决,则以此为由主张在行政法律中确立附属刑事条款的结论也就丧失了重要立论基础。实际上,通过对我国立法的经验性考察我们可以发现,行刑割裂是由我国的立法机制决定的,其解决方案,只能是真正确立附属刑法。行政法律、经济法律与刑事法律的起草部门不同。尽管按照《立法法》的规定,所有法律均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表决通过。但是“出口”的统一不意味着“入口”的统一。不同类别的法律有不同的起草机关,通常是由与该法律职权最接近的中央部委主导起草,其所对应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律工作委员会的内设部门也各有不同,这导致的直接问题是,虽然非刑事法律规定某种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但是等到酝酿起草刑法修正案时,法律的起草人员完全是另一拨人马,刑事法律的起草人员很有可能对此前行政法律留给他们的“作业”毫不知情,自然不可能专门为行政法律的某个条款进行刑事立法。即使某个刑法起草人员记得其他法律需要配套刑法条款,是否愿意主动作为也存在疑问。立法起草人员的更新换代、非刑事法律与刑事法律出台时间的错位等因素,都可能导致行刑割裂。这表面上看是技术性难题,其症结还在于立法缺乏相应的回应机制。由于其他部门法律与刑事法律制定、生效时间的不同步,即使刑法事后填补行政法律的漏洞,依然会造成一段时间内行政法律中的刑法指引条款的空缺。
即使不考虑立法机制的缺失,退一步讲,刑事立法是否必须受到非刑事法律的刑事责任指引条款的约束也是存在疑问的。按照我国的立法实践,行政法律和经济法律的制定过程是不可能有刑法专家参与的。如果某些行政法律和经济法律的刑事责任指引条款没有经过严格论证,那么以此为由去要求刑事立法岂不是一种变相的立法绑架?即使非刑事法律中的规定具有合理性,非刑事法律立法时做一次论证,然后刑事立法时再做一次论证,又造成立法资源的巨大浪费。
需要注意的是,“行刑割裂”不是1997年刑法修改之后才有的现象,在1997年刑法之前就存在了。例如,1988年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曾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进行修订,在当时的第49条、第54条增加了依照刑法追究刑事责任的条款,而直到1997年刑法修改时,才在刑法增加了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罪等罪名。[12]可见,即使将所有刑法规范收归刑法典所有,也没能杜绝此类现象。
(三)“行刑割裂”的后果:没有“牙齿”的法律
诚然,法律规范作为一种定型化的规制手段,期冀其完全周延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是无法实现的。德国学者考夫曼认为,制定法的不完备“并不是一种缺陷,而是一种先验且必然的结果。制定法不能也不可以明确地规定,因为它需要适合于各种无穷尽的案件”[13](P142)。话虽如此,放任制定法的不完备性也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行刑割裂的本质,就是法律责任配置的分离,将同一行为模式的不同法律后果,硬生生拆到不同的法律部门,但又为了维护某种法律规范的聚合性,而强行将更适合放在其他法律中的规范统一到一个法律中。为了追求刑法典的统一性,却忽视了责任配置的完整性,而由于刑法更新的不及时,又迫使行政法律和经济法律不得不将民事责任作为替代措施,但缺乏刑法手段作为后盾的法律,终究是没有“牙齿”的法律。
最近几年,行政法律和经济法律在刑事责任配置方面有一个显著的变化,即逐渐放弃过去在多个条文中分别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做法,而是辟出专条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例如,2019年8月26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114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甚至2019年6月29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法》第79条还要刻意强调,违反本法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从重”追究刑事责任。然而,不管是依法追究还是依法从重追究,其最终是否追究、如何追究,都有赖于刑法。
如果说在立法语言上的改进是非刑事法律在技术上的“救亡图存”的话,另一条更具实在意义的“救亡图存”路线就是具体化、严格化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解决责任配置偏“宽松软”的问题。例如,2014年4月24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59条增加了“按日连续处罚”的规定,另在第65条增加了民事连带责任的规定。2015年修改的《食品安全法》与2009年的旧法相比,新增了6处民事连带责任。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的具体化与严格化的主要初衷是解决过去法律责任配置不足,特别是刑事责任缺位的问题,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这是违法与犯罪的二元化立法体系的副产品之一。二元化立法体系的缺陷与不足,我国刑法理论虽然讨论较多,但是鲜有论述它对法律责任的影响。在笔者看来,二元化立法体系的更严重后果是,它割裂了法律责任之间的关联,不但将同一行为模式的法律后果人为划分为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还令其分属不同的法律部门中。刑法的二元化立法体系,在实际的司法运作中变成了二元化的三分法甚至四分法。具体而言,对于已经确定为犯罪的那部分行为,司法机关会着重于严重犯罪行为的处罚,将轻微行为剥离出来,施以程序上的免责(酌定不起诉等)。而对于需要行政处罚的那部分行为,行政机关又会进行二分法,只处罚严重的行政违法行为。例如,《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1条规定:“胁迫、诱骗或者利用他人乞讨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反复纠缠、强行讨要或者以其他滋扰他人的方式乞讨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警告。”反复纠缠才处以治安管理处罚,那么一个理论逻辑当然的结论就是:偶尔纠缠、强行讨要或者以其他滋扰他人的方式乞讨的就不是任何违法行为。二元化立法体系似乎造成了这样一种暗示,即凡是规定刑事处罚内容的,都应当由刑法“专供”,凡是存在拘留等限制人身自由内容的,则属于《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禁脔。③如此一来,其他行政法律和经济犯罪只能依赖罚金的威慑效力。然而无论罚金数额设置得多高,都无法弥补法律制裁力度不足的问题,剥夺自由与剥夺财产,在性质、处罚位阶上无法相提并论,对当事人的心理威慑也是截然不同的。
三、法定犯时代需要什么样的刑法规范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刑法规范?当前刑法学界对此问题的争论日趋白热化。一种观点认为,集中性、统一性的刑事立法模式并不现实,中国应由刑法典、单行刑法、附属刑法、轻犯罪法分别规定不同性质的犯罪。[14]与之针锋相对的观点认为,中国刑法的法典化应当在大陆法系国家刑法法典化的基础上再进一步,追求所有刑法规范的全面法典化。[15]笔者认为,不同类型的刑法规范各有其特点,对刑法规范的取舍应当结合刑法的发展阶段、刑法的时代使命和需求、法律责任的功能等作出审慎的选择。
(一)法定犯时代与附属刑法的功能发挥
自然犯与法定犯是意大利学者提出的犯罪类型。加罗法洛认为,只有那些道德异常、侵害怜悯或正直等基本情感的人才是真正的犯罪人,该类犯罪为“自然犯”;仅仅与特定时代的环境或事件相关而与行为人道德无关,仅由立法者根据时势需求规定于法典中的犯罪,则是“法定犯”。[16](P67)加罗法洛的自然犯、法定犯二分法虽然也受到一些学者的质疑,但作为一种分析框架依然被普遍接受。我国1979年刑法共有192个条文,从分则罪名内容看,是比较典型的自然犯的刑法典,而1997年刑法修订时,为了追求“统一而完备”,将大量的单行刑法、附属刑法整合进刑法典,这导致刑法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和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急剧扩容,加上分则贪污贿赂罪、渎职罪、危害公共安全罪、军人违反职责罪等章,可以说,1997年刑法已经是法定犯占据主导地位的刑法典。在1997年刑法规定的罪名总数中,法定犯罪名占到85%左右。[17]我国刑法自此进入法定犯时代。[18]1997年之后的刑事立法,依然延续了法定犯的趋势。根据笔者统计,目前十个刑法修正案共新增条文37个,④其中分则第二章有10个,第三章有10个,第四章有6个,第五章有1个,第六章有8个,第八章有1个,第九章有1个。另修改条文共95次,其中分则第二章有9次,第三章有38次,第四章有9次,第五章有3次,第六章有30次,第七章有1次,第八章有3次,第九章有2次。而分则第一章和第十章至今未见任何改动。从以上数字可以看出,分则第三章和第六章在1997年刑法修改中占有绝对比重,其比例远超半数,而从修改和新增条文数量占本章原条文数量的比例看,分则第二章的相对比重亦遥遥领先。如果再将分则第八章、第九章的新增、修改条文数合并计入的话,1997年刑法至今的十个刑法修正案主要是围绕法定犯展开的。
在法定犯时代,刑事立法模式的选择必须考虑法定犯的特点和需求。为了适应统一刑法典的立法模式,刑法典不得不出现了大量的空白罪状,对具体犯罪构成要件的认定就依赖于作为前位法的行政法律或者经济法律。例如妨害动植物防疫、检疫罪中的“违反有关动植物防疫、检疫的国家规定”、污染环境罪中的“违反国家规定”等。在刑法典中的法定犯的构成要件内容需要行政法律来填补的情况下,理论和实务中出现了许多难以解决的尴尬。诸如刑事违法过度受制于行政违法的判断⑤、行政案件向刑事案件的流转不畅等问题已经严重妨碍了有关罪刑的适用。
法定犯时代拒绝附属刑法规范,还造成权利、义务与责任的割裂,破坏了法律规范的完整性,不利于刑罚威慑的功能发挥,也不利于法定犯的认定。[19]同一行为模式的法律后果在不同的部门法中配置,无法兼顾不同类别法律责任之间的协调,影响法律责任的整体效果,而在不同法律由不同机构起草的背景下,这种分离倾向更加明显。片面强调法律形式上的统一性,却忽视了法律规范的统一性,是典型的丢了西瓜捡了芝麻的做法。
(二)修正案模式:不可荒废,亦不可独宠
以修正案模式修改主要法律,目前已广泛适用于宪法、刑法和刑事诉讼法领域。“刑法修正案与刑法典二者之间是内容替代、形式统一、层级效力等同的关系。”[20]刑法修正案是对刑法条文的直接修改,有助于维护刑法典的统一性,令刑法典不断适应变化的社会生活,维护刑法典的权威性。对于刑法典条文的修改,没有比刑法修正案更合适的了。然而,正如再精美的食物也不能暴饮暴食一样,修正案模式的刑法修改路线依然要坚持,却不等于只能采取这唯一的途径。事实上,随着时间的推移,修正案模式的弊端日趋明显。
1.逐渐流逝的形式美感。刑法修正案既可对原有罪名进行修改,又能新设罪名,对于前者可以直接在原刑法典上进行修改,对于后者可以通过增加款的方式来解决。刑法典条文是按照犯罪客体类型分类排列的,相同性质的罪名一般依序排列,具有大致的逻辑关联,因而新设罪名的体系性位置是大概固定的,如果强行在某些条文后面附设款的话,可能造成条文规模过于庞大,承载的罪名个数过多等问题,而且也有可能打破原有条文内部的逻辑联系。因此对于不便在原条文放置的法条,刑法开创了“第××条之几”的条文标识,但这直接破坏了刑法典应有的形式美感。而《刑法修正案(九)》甚至出现整个条文删除的情况(原刑法第199条)。
2.逐渐混乱的规范结构。纵观十次刑法修正案,刑法修正案的主要功能在于解决类罪的完善性问题。例如《刑法修正案(三)》对恐怖主义犯罪的修改完善、《刑法修正案(八)》对经济犯罪的修正、《刑法修正案(九)》对网络犯罪的修改完善等。对某一个类别的犯罪的集中性、系统性修订,是刑法修正案的重要功能和使命之一,个别罪名的新设或者修改只是立法的附带之举。新型危害行为的不断涌现以及随之而来的立法回应导致的直接后果是,刑法典难以为新型犯罪找到合适的体系性地位。例如刑法第253条之一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立法者将本罪放置于分则第四章,似乎认可本罪侵犯的是人身权利或者民主权利,又将本罪置于刑法第253条私自开拆、隐匿、毁弃邮件、电报罪,似乎又认为本罪的法益与通信权利比较接近。个人信息是否人身权利,民法学界尚无定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放置在本章,显然名实不符,而通观刑法典分则,也实在找不到更合适的位置了。传统的刑法典难以容纳新型权利犯罪,在信息化时代,这个矛盾将会日趋突出和尖锐。
3.逐渐脆弱的正当性基础。立法权限分配,是国家权力制衡的重要内容,亦和公民合法权益密切相关。刑法是关于犯罪与刑罚的法律,攸关公民基本权利、个体尊严,是国之大典,刑罚的制定与发动均须严格的程序限制与规则制衡。我国《立法法》第7条规定:“……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进行部分补充和修改,但是不得同该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而从1997年刑法的413个罪名发展到现在的468个罪名的规模看,恐怕早就超越了“部分补充和修改”的范畴了。尽管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修改刑法存在立法程序繁琐、立法资源耗费巨大、立法反应不及时等苦衷,但是二十多年来对刑法典零敲牛皮糖式的修改,早就积沙成塔了,目前是否还属于“部分补充和修改”恐怕值得反思。也就是说,采用刑法修正案模式修改刑法的立法正当性早已存疑,而附属刑法不失为一种理性的替代选择。
四、确立多元化立法模式的具体思路与限制性规则
按照刑法修正案大约两年一出台的节奏,《刑法修正案(十一)》恐怕等不了多久就会面世。只要立法回应社会现实的客观需求还在,则是否确立附属刑法规范的争议就不会停止。笔者认为,确立附属刑法规范,即使称不上迫在眉睫,也是势在必行之举了。当然,历史决不能简单重复,一定要总结1997年刑法修改之前的立法得失,避免曾经的立法乱象再次出现。
(一)立法模式现状:名义上的一元化、实质的二元化
部分学者津津乐道的“统一而完备”的刑法典模式,实际上目前既不统一也不完备。法律规范的完备性暂且不提,仅就统一性而言,1997年刑法通过后不久,199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出台了《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此后又在2000年出台了《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也就是说,目前已经是实质上的二元化立法体系了。那么,既然单行刑法早就存在了,附属刑法为何不可接受?对刑法的所谓权威性应当有辨证、科学的认识。刑法典的权威性不来自于其一家独大,而来自于内容规范的合理性与科学性。刑法典的统一性不来自于刑法形式的唯一性,而来自于法条规范没有交叉冲突。多元化立法模式不但不会损害刑法典的价值,反而有助于提升刑法的威严。法典具有安定性需求,频频修改有损国民的信赖利益,法典调整最重大的利益需求,构建最基本的秩序规则,承载最普世的伦理观念,让法典直面变动最剧烈的社会生活,是对法典的滥用。
作为参照,德日等国刑法都广泛采用了附属刑法规范和单行刑法。德国除了刑法典之外,还有大量的单行刑法,法国的附属刑法规范分布在各类的专门法典中。日本320多部行政法中规定了行政刑法内容,涉及罪名2000多个,且日本还制定了独立的《轻犯罪法》。[21]在我国的宪法法律部门中,宪法并不排斥《立法法》《国旗法》《国籍法》等单项法律的存在。在民商法部门,也没有学者要求将所有民商事法律都收归到民法典中,那为何偏偏在刑法部门中存有如此执念呢?
(二)附属刑法与单行刑法模式的限制性要求
1.从“附属”的附属刑法向“独立”的附属刑法转变。1997年刑法修改之前广泛存在的附属刑法,是一种所谓的“附属”的附属刑法模式,即法律规范的行为模式部分由行政法律或者经济法律的某个条款确立,而具体的量刑规则依然比照刑法的某个条款。例如,1985年《计量法》第29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制造、修理、销售的计量器具不合格,造成人身伤亡或者重大财产损失的,比照《刑法》第一百八十七条的规定,对个人或者单位直接责任人员追究刑事责任。”这里的《刑法》第187条就是1979年刑法中的玩忽职守罪。[22]法官在适用过程中,要同时参照附属刑法、刑法总则和刑法分则,确实徒增很多麻烦。附属的“附属刑法”的找法困难以及过去特定历史时期司法人员参差不齐的司法素质决定了,刑法典收编附属刑法和单行刑法具有历史合理性。而且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相互分离的做法导致刑法原有罪名构成要件内容的膨胀,不符合罪刑法定的明确性要求。创制犯罪行为却不创制法定刑,平添了关于附属刑法是独立罪名还是纯粹的刑事责任条款的无端争议。过分强化附属刑法的附属性,反而遏制了附属刑法功能的发挥。而世界各国附属刑法的共同特点,是在行政法律中规定专门的行为类型,并配置独立的法定刑,即附属刑法附属于行政法律而不是附属于刑法典分则。附属刑法引用刑法某个条款的法定刑,主要是考虑到刑法条款与附属刑法在行为方式上的相似性,但为刑法条款配置的法定刑未必能精准反映附属刑法规定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而独立的附属刑法模式就不存在这个问题。
2.单行刑法立法技术的改进:避免直接替代刑法。单行刑法的历史教训是,避免直接替代刑法,因为这样很容易架空刑法典的原有规定。例如,1979年刑法规定了偷税罪和抗税罪,199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惩治偷税、抗税犯罪的补充规定》,该规定新增了骗取国家出口退税罪,同时对1979年刑法的偷税罪和抗税罪进行了修改。基于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偷税罪和抗税罪不再适用1979年刑法,1979年刑法的偷税罪和抗税罪没有废止却实质上失效了。类似的例子还有,199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惩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对1979年刑法第141条的拐卖人口罪在犯罪对象、犯罪目的和法定刑等方面进行了修改。[23]单行刑法替代而不修改刑法条文,刑法条文形式有效却实质无用,人为造成法律条款的叠床架屋,并增加了法律适用的繁琐。这段不佳的历史体验恐怕是目前部分学者包括国家立法机关抵触多元化立法模式的重要原因之一。笔者认为,多元化立法模式要注重吸收历史的经验教训,关键在于明确刑法典、单行刑法、附属刑法各自的功能界限。对于刑法典已有条款的,继续用刑法修正案模式对刑法进行修改。行政法律中需要配置附属刑法的,则配置独立的行为模式和法定刑。对于某些新型的类罪行为,例如网络犯罪等,则可以在单行刑法中作出规定。
注释:
①如后所述,现行有效的刑法渊源除了刑法典,还有单行刑法,只是单行刑法的数量有限,因而当前只能算是“大体”坚持了一元化的立法模式。
②一种变通的做法是,将招标代理机构的工作人员以帮助犯的名义处罚,但是这毕竟是变通措施,即使如此也与《招标投标法》第50条的原旨相去甚远。
③这种状况在近年的行政立法中才得以缓解,例如《疫苗管理法》第80条、《食品安全法》第123条、《药品管理法》第118条均设置了行政拘留条款。但是相比我国目前有效的700余部行政法律,上述法律的数量还非常有限。
④以序号为准,原条文增加新款的视为对原条文的修改。
⑤例如,赵春华案件中对枪支鉴定的行政标准的采信以及法益侵害性的判断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