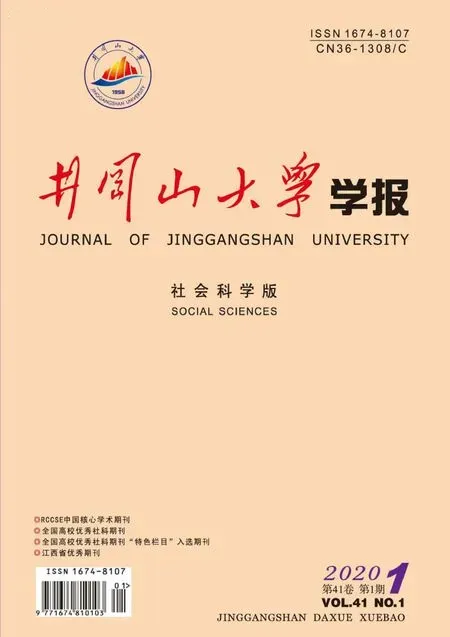王阳明的《诗经》观及其学术价值
2020-02-10王公山
王公山
(井冈山大学庐陵文化研究所,江西 吉安343009)
自汉代《诗经》被尊崇为儒家经典后,便成为学界用以解读与“还原”的重要对象,也由此产生专门研究《诗经》的学问,并演绎成为中国经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王阳明(以下简称阳明)不仅是宋明心学的集大成者, 其对经学的理解与把握亦不乏独到之处,特别是对《诗经》的认知与阐发,启人深思,影响甚远。
一、阳明与“删诗”之说
关于“孔子删诗”之说,首先需要追溯到汉代的司马迁,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写道:“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雄》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 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 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 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 ”[1](P1937)在司马迁看来,孔子时代社会上流传了很多诗歌,内容广博、瑕玉并存,孔子删其瑕而存其玉,以企教化后人、敦厚世风。 东汉的班固也在《艺文志》中提到:“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 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也。 ”[2](P1708)这段述论与司马迁的观点基本一致,不仅认为《诗经》是由历代的乐官采集各地诗歌集合而成,并指出孔子对《诗经》进行了筛选取舍后整理成册,所以后世所看到的《诗经》并不是原始之诗。 东汉郑玄为《毛诗》作笺,亦信采此说,并为之作了必要的阐释:“故孔子录懿王、夷王时讫于陈灵公淫乱之事, 谓之变 《风》、变《雅》。 ”[3](P3)三国吴人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也说:“孔子删诗授卜商。 ”[4](卷一)根据当代学者洪湛侯的观点,班氏、郑氏、陆氏等人的观点都源于《史记》,并非独创[5](P7),而司马迁的这种观点在学界上持续了千余年而少有人质疑。至到唐代,则出现了与司马迁不同的声音, 孔颖达在《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诗谱序·孔疏》 中说:“如《史记》之言,则孔子之前诗篇多矣。案《书》、《传》所引之诗,见在者多,亡逸者少,则孔子所录,不容十分去九,马迁言古诗三千余篇,未可信也。 ”[3](P3)对司马迁的观点提出了质疑。而由此为导火索,揭开了历时一千余年对“删《诗》说与非删《诗》说”的论战,并演变成为《诗经》学史上的一大公案,每朝每代的大学者几乎皆有论涉。
作为心学家的阳明,对“孔子删诗”的认知与理解有着自己的观点。首先,阳明肯定司马迁所提出的“孔子删诗”之说。 在阳明看来,天下之大乱,皆由虚文胜而实行衰的缘故,假使道明于天下,则《六经》不必述。《六经》尚且不必述,删除《诗经》繁文,又何吝之有。因此,阳明基本认同徐爱之“孔子删述《六经》以明道”[6](P7)的观点。 依阳明的认知,天下说《易》之人多了,“纷纷籍籍,不知其几”,于是《易》道大乱。 孔子排除众家之说,仅仅选取文王、 周公之说而赞续之,“而天下之言《易》 者始一。 ”[6](P8)以此类推,“《书》、《诗》、《礼》、《乐》、《春秋》皆然。《书》自《典》、《谟》以后,《诗》自《二南》以降,如《九丘》、《八索》,一切淫哇逸荡之词,盖不知其几千百篇;《礼》、《乐》之名物度数,至是亦不可胜穷。 孔子皆删削而述正之, 然后其说始废。 如《书》、《诗》、《礼》、《乐》中,孔子何尝加一语? 今之《礼记》诸说,皆后儒附会而成,已非孔子之旧。 至于《春秋》,虽称孔子作之,其实皆鲁史旧文。 所谓‘笔’者笔其旧;所谓‘削’者,削其繁;是有减无增。孔子述《六经》,惧繁文之乱天下,惟简之而不得,使天下务去其文以求其实, 非以文教之也。 《春秋》以后,繁文益盛,天下益乱。 始皇焚书得罪,是出于私意,又不合焚《六经》。若当时志在明道,其诸反经叛理之说,悉取而焚之,亦正暗合删述之意。 ”[6](P8)言外之意,在阳明看来,文以明道,道明以后,自不需要繁文的连篇累牍;并且强调,繁文往往是天下大乱的祸根, 因为繁文的背后隐藏着对虚名的追求, 对淳朴之道的摒弃,“天下所以不治,只因文盛实衰,人出己见,新奇相高,以眩俗取誉,徒以乱天下之聪明,涂天下之耳目,使天下靡然,争务修饰文词以求知于世,而不复知有敦本尚实、反朴还淳之行。 ”因此,在阳明看来“圣人只是要删去繁文”,是要人明道,天下恢复天平;“后儒却只要添上”[6](P9),是导致繁文糜烂、大道晦暗的原因。 为了回归自然,倡明大道,阳明甚至肯定秦始皇焚书的部分合理性,呼吁学人抛弃空文,敦本尚实。
其次,在处理司马迁的“孔子删诗”与“淫诗”之说的矛盾时,阳明认为,“淫诗”为后世儒者附会之作,非孔门家法。 众所周知,《诗经》中存有不少男女情爱之作,被后世儒家学者称为“淫诗”。 而《诗经》 一直被认为是孔子用来教育学生的教材。若“孔子删诗”之说是正确的,可为什么孔子要选取如此淫乱之作教育后代呢? 历代学者都从不同的角度来诠释这种现象, 但似乎没有一家之说完美无缺,因此造成后学的疑惑,正如徐爱所云:“恶可为戒者,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奸,何独于《诗》不删郑、卫?”[6](P10)。 阳明遵循司马迁之说,认为孔子从三千多首删除了“一切淫哇逸荡之词”,仅保存三百零五篇来教化后世。对于《诗经》中郑、卫之《风》 这些淫靡之作的保存原因, 阳明的观点是:“《诗》 非孔门之旧本矣。 孔子云:‘放郑声, 郑声淫。 ’又曰:‘恶郑声之乱雅乐也。 ’‘郑、卫之音,亡国之音也。’此本是孔门家法。孔子所定三百篇,皆所谓雅乐,皆可奏之郊庙,奏之乡党,皆所以宣畅和平,涵泳德性,移风易俗,安得有此?是长淫道奸矣。此必秦火之后,丗儒附会,以足三百之数。盖淫泆之词,世俗多所喜传,如今闾巷皆然。”[6](P10)不难看出,阳明认为,今本《诗经》非孔子所删定的旧本,乃后世儒者依己之意附会而作;而孔子删定的旧本,在秦火时已经失传。 在阳明看来,根据孔子的一贯理念,诗教的作用非常巨大,是敦人伦、厚风俗、宣畅和平、涵泳德性的重要渠道,孔子也十分反感郑、卫之声,主张“放郑声”,因为“郑声淫”(《论语·卫灵公》)、“恶郑声之乱雅乐也”(《论语·阳货》),而《礼记·乐记》直接将郑卫之声斥之为“亡国之音”,孔子岂能选用这样“亡国之音”来传之后世,风化万代呢? 在阳明看来,这显然有悖孔子的一贯理念。因此,阳明得出上述结论,即郑、卫之《风》,非孔子所选,乃后世儒者附会之作。 这种观点显然与明代所流行的主流观点,即朱熹的“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遗志”[7](P42)的观点背道而驰。 然而,阳明的理论也仅仅是一种预设,似乎缺乏足够的实物证据,这也是被清人抨击的“把柄”之一。
二、《诗》 与史的关系——《诗经》亦史
众所周知,《诗》在汉代以前虽然广为流传、地位显要,甚至在《庄子》[8](P532)、《荀子》[9](P11)内被称为“经”,但其“经”的地位其时并没有被普遍认同;“经”的地位被真正确立并得到普遍认同,应该是在汉文帝置经学博士之后(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八《经说》)。 自此以降千余年,《诗经》学进入注重训诂的“诗经汉学”时代;随着社会思潮的演变,至于南宋朱熹《诗集传》闻世后,《诗经》一变又成为注重义理的“诗经宋学”时代。[5](P4)但无论是“汉学”抑或“宋学”,《诗经》的注解内涵与理解视角虽有变化,《诗经》原文基本为主流社会奉为圣经,难以撼动。 自元延祐二年《诗集传》被官府确定为科举取士的指定教材后,直至明末,《诗经》之学,几为朱熹《集传》一家所囊括。[5](P4)人们对《诗经》的领悟几乎变成机械地接受, 朱熹的一家之说也就变成了普世的“真言”,其对当时文人学者的影响几乎是根深蒂固的。可以想见,其时王阳明提出与朱熹相反的见解所冒的风险是巨大的, 所付出的成本亦是很高的。
阳明弟子徐爱曾就朱熹对《六经》包括《诗经》的看法请教过王阳明,徐爱问:“先儒论《六经》,以《春秋》为史。 史专记事,恐与《五经》事体终或稍异。”[6](P10)就此提问,阳明顺势阐明自己的经典观。阳明指出:“以事言谓之史, 以道言谓之经。 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经,《五经》亦史。《易》是庖羲氏之史,《书》是尧、舜以下史,《礼》、《乐》是三代史:其事同,其道同,安有所谓异? ”[6](P10)不难发现,阳明的观点是,就《五经》所阐发的道理而言可称之为“经”;同时《五经》中保存了先人具体的社会实践与生存经验,这些事实应该称之为“史”。但从辩证法的角度审视,实事蕴含着道理,而道理也深藏于实事之中,也就是说《诗经》不过是以侧重于艺术的形式,记录着先人“歌咏性青”方面的 生 存 经 验 的 史 书 而 已[6](P254),这 与 程 氏“《诗》、《书》载道之文,《春秋》圣人之用,《五经》有《春秋》,犹法律之有断例”,将经史断然分裂的经史观显然“如炭投冰”[10](P264),也与朱熹将“经与史界判鸿沟”[10](P265)的作法截然相反。
虽然阳明持“经亦是史”之理念,阳明亦极为重视《五经》的编纂原则:“《五经》亦只是史,史以明善恶,示训戒。善可为训者,时存其迹以示法;恶可为戒者,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奸。 ”[6](P10)在王阳明看来,《五经》的编纂原则是劝善惩恶,对于有益于人类进步的“善”事,编纂者会保存其历史真实以为后世效法的榜样;而将反人类的“恶”事却省略其历史真实而仅仅凸显其对后世的警示,这种观点其实与原始儒家所强调的“扬善隐恶”是一脉相承的,也是阳明的“删诗”学说的理论深化。
不仅如此, 阳明在自己的学术实践中亦一直遵循自己的这种“《六经》亦史”的理念。如在其《五经臆说》中,阳明在阐释《时遇》《执竟》《思文》等《诗经》篇章时,基本将这些诗篇的内容视为真实存在的史料, 作为自己政治理念与哲学原理的依据进行陈述与阐发, 从而探讨经学对现实社会的警示与启迪。如阳明认为:“《时迈》十五句,武王初克商,巡守诸侯,朝会祭告之乐歌。 ”[6](P980)同时又将《执竟》视为“祭武王、成王、康王之诗”[6](P981),将《思文》八句视为“郊祀后稷以配天之诗”。[6](P981)除此之外,阳明在《山东乡试录》对《小雅·采薇》的阐释[6](P848)、在《鸿泥集序》中对《大雅·抑》的阐释[6](P1039),与《诗》《小序》的观点基本一致,然而在《诗经》学史上,《诗经》《小序》大都采用“以史证诗”的方式去阐释《诗经》本文,其很多观点被认为是牵强附会而遭到批判,郑樵就斥《诗序》“皆是村野妄人所作”(《朱子全书·诗纲领》引),朱熹对《小序》的批驳也是丝毫不留情面,如在对《大雅抑》篇的《小序》评价时云:“然则《序》说为刺厉王者,误矣。”[7](627)但阳明并不为这些主流观点所左右,而是根据自己的体悟与理解,阐释其心学视野下的《诗经》“真意”, 阳明在 《五经臆说序》 中强调:“得鱼而忘筌,醪尽而糟粕弃之;鱼醪之未得,而曰是筌与糟粕也,鱼与醪终不可得矣。《五经》,圣人之学具焉,然自其已闻者而言之,其于道也,亦筌与糟粕耳。 ”又说:“意有所得”“盖不必尽合乎先贤”[6](P876)。在阳明看来,筌与酒糟就像《五经》一样,是获得“真意”的工具而已;一旦获得了真意,它们也就失去了价值。 可见阳明的《诗经》亦史的经史观绝非一时冲动的临场发挥, 而是其学术思想一以贯之的侧面显现。
三、《诗》 与心的关系——《诗》为心之记籍
作为心学的集大成者, 阳明的主张无疑是他思想成果的最精华部分。 他不仅承袭了陆九渊的学说,更重要的是将“致良知”等王学的核心理念融入了心学思潮, 并最终使陆九渊所创立的心学成为中国宋明理学史上的一个能与程朱理学分庭抗礼的一极。 阳明的心学主张, 可以通过他关于《诗经》与心的关系的阐述加以理解。
在《稽山书院尊经阁记》一文中,阳明说道:
经,常道也。 其在于天谓之命,其赋予人谓之性,其主于身谓之心。 心也,性也,命也,一也……故《易》也者,志吾心之阴阳消息者也;《书》也者,志吾心之纪纲政事者也;《诗》也者,志吾心之歌咏性情者也……故《六经》者,吾心之记籍也,而《六经》之实则具于吾心;犹之产业库藏之实积,种种色色,具存于其家。其记籍者,特名状数目而已。而后世之学者,不知求《六经》之实于吾心,而徒考索于影响之间,牵制于文义之末,硁硁然以为《六经》矣。[6](P254)
由上所述, 阳明在此文章中所表述的经学思想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首先,“经”是“常道”亦是“心”,这个道从时间上讲亘古不变,从空间上说充塞宇宙,从社会学的角度看,道即蕴含于“四端”、“五常”之内并通过“四端”、“五常”表现自己的存在,从心与物的关系讲,道运行于天为命,赋予人为性,主于身为心,心、性、命都是一物异名;换言之,道即心、即命、即性,亘古不变,充塞宇宙,蕴含于“四端”、“五常”,表现于道德伦常之中。 其次,《六经》 是记载吾心之“常道”。 在阳明看来,《易》即记载阴阳消息,《书》即记载吾心之纪纲政事,《诗》即记载歌咏性情,《礼》即记载吾心之条理节文,《乐》即记载吾心之欣喜和平,《春秋》即记载吾心之诚伪正邪,《六经》 从不同的角度记载了吾心之“常道”。 换言之,阴阳消息之行,纪纲政事之施,歌咏性情之发,条理节文之著,欣喜和平之生,诚伪正邪之辩,都发生在“吾心”之内,离开心去追求常道,即是舍本趋末,只能背道而驰,离道愈来愈远。 因此,阳明得出如此结论:尊经就是反求于吾心,在寂静的心态中体悟《六经》的主旨,这也是治经的科学路径;反之,习训诂,传记诵,“徒考索于影响之间,牵制于文义之末”[6](P255),即是侮经,是错误的治经之路。
如果单单从就《诗经》的角度来审视,首先,与“吾心”相比,“吾心”是第一性的,《诗经》是第二性的。 在阳明看来,“经”虽然是常道,但仅仅是记载心的常道,因此,在《诗经》与“吾心”相比较之时,“吾心”为第一性的,《诗经》为第二性的,因为常道就存在于“吾心”,而《诗经》仅仅是记载了“吾心”之常道的“歌咏性情之发”,离开“吾心”,也就谈不上《诗经》的歌咏性情了。 因此,在阳明看来,离开“吾心”去研究《诗经》,离开心体去谈“歌咏性情”,都是舍本趋末,背道而驰的。 有鉴于此,阳明告诫后学:“须于心体上用功,凡明不得,行不去,须反在自心体上体当可通。盖《四书》、《五经》不过说这心体,这心体即所谓道。心体明即是道明,更无二:此是为学头脑处。”[6](P14)阳明在《次栾子仁韵送别》诗中云:“从来尼父欲无言,须信无言已跃然。悟到鸢鱼飞跃处,工夫原不在陈编。 ”[6](P744)在《送蔡希颜》诗中又云:“悟后《六经》无一字,静余孤月湛虚明。 ”[6](P732)在《夜坐》一诗中亦云:“千圣本无心外诀,《六经》须拂镜中尘。 ”[6](P787)“鸢鱼飞跃”出自《诗经·大雅·旱麓》一章,原文为“鸢飞戾天,鱼跃于渊”,意谓想彻底体悟出《诗经》的道理,仅仅停留在经文的字义训诂的“陈编”中,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回归心体。其它两首所讲,大致也是这个意思。 可见,与“吾心”相比,《诗经》是第二性的,是“吾心”常道的反应。
其次,《诗经》仅仅是记载心体的工具。在阳明看来,《六经》是“吾心之记籍”,是自家“财产”(心体)的“名状数目”,每部经虽然所记侧重不同,但都是对心体运行的记载,如果说《书》是记载吾心之纲纪政事、《礼》是记载吾心之条理节文的话,那么,《诗经》便是记载吾心之歌咏性情。 因此,阳明在《林汝桓以二诗寄次韵为别》中云:“万理由来吾具足,《六经》原只是阶梯。 ”[6](P786)“万里具足”与孟子的“万物皆备于我”有异曲同工之妙,“吾心”本具足万理,《六经》只不过是了解“吾心”的“阶梯”。当然,虽然阳明诗中并没有提及“性情”二字,但根据阳明“心即理”,“心即性”的哲学理念,“万理”之中自然包含了“性情”。但“阶梯”一词,却揭示出阳明对《诗经》的定位,即相对于“心体”而言,《诗经》仅仅是工具。在《应天府重修儒学记》一文中,阳明又云:“圣贤之学,心学也。 道德以为之地,忠信以为之基,仁以为宅,义以为路,礼以为门,廉耻以为垣墙,《六经》以为户牖,《四子》以为阶梯。 求之于心而无假于雕饰也,其功不亦简乎? ”[6](P900)“户牖”与“阶梯”虽然名称有异,但实质都是工具,都是体悟自家心体“筌”与“糟粕”,是手段,而非目的。 因此,在阳明看来,正确的学习《诗经》的方法应该是反求于吾心,结合《诗经》本文,从静定中体悟《诗经》的伦理内涵,感悟其中所蕴含的“常道”至理,而不是将全部精力放在具体考索《诗经》的字义训诂、 探求名物典章的含义、 追索历史典故的出处上。 而阳明的《五经臆说》即是对此种方法的具体实践,通过反求诸心,对《五经》内涵作出了自己的判断。
四、阳明《诗经》观在学术史上的价值
阳明《诗经》观的最大亮点无疑是其对《诗经》中“淫诗”的解释。在阳明看来,若今本《诗经》为孔子所定,就不应该保留郑卫“淫诗”;今本《诗经》留有之“淫诗”,乃汉儒附会之作。 其说似乎独到新颖,但阳明之论,亦非其独创,仅仅是两宋疑古之风的延续。 早在宋代,陈鹏飞作《诗解》,就因为“不解《商颂》、《鲁颂》,以为《商颂》当阙,《鲁颂》当废”[11](P216);程大普《诗论》也提出《国风》之名,出自 汉 儒 之 附 会[11](215)。 而 南 宋 王 柏《诗 疑》,使 疑《诗》之风几乎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王柏非但怀疑《诗经》中的“淫奔”之《诗》非孔子存录,并且断定今本《诗经》为汉儒在秦火焚书后的附会之作,并以此为理由,将今本《诗经》删除三十二篇。虽然王柏之说一经出世就遭到学界的抨击, 但作为朱熹的三传弟子,其说理应有所师承,其论所造成的影响应该是实实在在的。阳明“淫诗汉儒附会”说,与其说是阳明自己的创造, 倒不如说是阳明直接吸收了王柏《诗疑》的“淫诗汉儒附会”的核心理念,然后加以解释与推广。 因此,阳明对“淫诗汉儒附会”说的最大贡献不在创立,而在于传播。 由于阳明思想的深刻与自身社会地位的显要,使《传习录》一经问世便广泛流传,其对社会影响的广度与深度是王柏《诗疑》无法比拟的,结果使王柏的“淫诗汉儒附会”说伴随着《传习录》在知识界广泛流传。 王柏之说虽然没有得到学界主流的普遍认同,却被阳明后学广泛接受。如果说王柏之说扰乱了学界对今本《诗经》神圣地位的尊崇的话,阳明之论却动摇了学子对今本《诗经》 神圣地位的信心,其对《诗经》学界的冲击,应该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例如明代翰林学士丰熙之子丰坊就作《鲁诗世学》,变乱经文,诋非旧说;而明代李经纶《诗经教考》甚至删去《诗经》四十二篇,认为这些“淫诗”本非孔子旧典, 是汉儒将孔子本来已经删去的重新补加之诗作。顾炎武在《日知录》有《〈诗〉之世次必不可信》一篇,专门讨论《诗经》的次序问题,认为“今《诗》亦未必皆孔子所正”[12](P175);而作为清代疑古思潮的代表人物阎若璩,竟然在其名著《尚书古文疏证》中,差不多用了一个章节、半卷的篇幅来讨论“淫诗”问题,认为今本《诗经》所存“淫诗”绝非孔子所选:“孔子何人,岂录淫辞以诲万世哉?故程篁墩决然谓今《诗》出汉儒所缀缉,非孔子删书定本。汉儒徒见三百五篇名目散轶不存,则每取孔子所删所放之余一切凑合以足其数,而《小序》者不察,亦一切以其得于师者,概之曰刺淫。 此其所由失也。 ”[13](P300)更有甚者,阎氏强烈呼吁“有力者请于朝而再放黜之,一洗千古之污秽”,并且,阎氏胪列《野有死麕》、《静女》等三十一篇作为删除的对象。[13](P315)值得注意的是,阎氏在胪列“淫诗”非孔子所选的证据时,竟然将阳明《传习录》所论“淫诗汉儒附会”一段全文抄上,而王柏、程大普更成为阎氏反复出现的“证人”。可见,“淫诗汉儒附会”说对阎氏的影响是很大的, 而阎氏的疑古理念显然亦受阳明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阳明是明末清初的疑古思潮的“幕后推手”。
其次,“《六经》亦史”对学界的影响。其实“《六经》亦史”也并非阳明发明。早在战国时期,《庄子·天运》篇就记载了老子之语:“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岂其所以迹哉? ”这句话被钱钟书先生认为是“《六经》皆史之旨”的开端。[10](P265)隋唐时的王通亦云:“圣人述史三焉,其述《书》也,帝王之制备矣,故索焉而皆获;其制《诗》也,兴衰之由显,故究焉而皆得;其述《春秋》也,邪正之迹明,故考焉而皆当, 此三者, 同出于史而不可杂也, 故圣人分焉。 ”[14](卷一《王道》)经史不分的经典观至元人郝经时理论雏形基本完成。 郝经在其著名的《经史论》中提出:“古无经史之分。孔子定《六经》,而经之名始立,未始有史之分也。 《六经》自有史耳,故《易》即史之理也;《书》, 史之辞也;《诗》, 史之政也;《春秋》,史之断也;《礼》《乐》,经纬于其间矣,何有异哉! 至于司马迁为《史记》,而经史始分矣。 其后遂有经学、有史学,学者始二矣。 ”[15](卷十九)明初宋濂在其著作中亦提到:“或问龙门子曰:‘金华之学,惟史学最优,其于经则不密察矣,何居? ’龙门子曰:‘何为经? ’ 曰:‘《易》、《诗》、《书》、《春秋》是也。’曰:‘何为史?’曰:‘迁、固所著是也。’曰:‘子但知后世之史,而不知圣人之史也。 《易》、《诗》固经矣,若《书》若《春秋》,庸非虞夏商周知史乎? 古之人何尝有经史之异哉?凡理足以牖民,事足以弼化,皆取之以为训耳,未可以歧而二之。 谓优于史而不密于经,曲学之士固亦有之,而非所以议金华也。 ’”[16](P1803-1804)在这里,龙门子认为圣人之史本来就在《易》、《诗》、《书》、《春秋》诸经之内。文中虽未提及《礼》经,但却反映了中国古代经史不分的经典观,也可以看作诗“《六经》(或《五经》,因为《乐经》失传)皆史”观的理论进一步延伸。
阳明重提“《诗经》亦史”的意义在于有明一代在朱说几乎成为不可动摇的金科玉律的时代,敢于提出异于学界主流的异端之论,不仅需要勇气,确实也需要智慧。 阳明巧妙地将《诗经》亦史的观念融汇入其心学体系之内,从身边的弟子开始,灌输一种有异于官方学说的新内容, 无疑为当时学术界带来了新鲜的空气。除此之外,“《六经》亦史”的观念逐渐被学术界所接受, 比阳明稍晚的王世贞就认为:“盈天地间无非史而已。三皇之世,若泯若没;五帝之世,若存若亡。噫!史岂可以已邪!六经,史之言理者也。[17](卷一)李贽亦云:“经史一也。史而不经,则为秽史矣,何以垂借鉴乎?经而不史,则为说白话矣,何以彰事实乎? 故《春秋》一经,春秋一时之史也。《诗经》,《书经》二帝三王以来之史也。 而《易经》则又示人以经之所自出,史之所自来,为道屡迁,变易匪常,不可以一定执也。 故谓《六经》皆史可也。 ”[18](卷五)而“《六经》皆史”借助清人章学诚一下子成为学术界普遍接受的观点,这不能不说其中也有阳明的功劳。
最后,在《诗经》与心的关系的认识上,阳明上承陆九渊,对明代后期的《诗经》学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自陆九渊提出“《六经》皆我注脚”的经学理念后, 经学界从理论上进入朱学与陆学分庭抗礼的时代。但从学术实践的角度审视,陆氏心学从来就没有动摇过朱氏理学的地位, 黄宗羲在研究明初学术之后, 感慨朱氏地位的牢不可动:“有明学术,从前习熟先儒之成说,未尝反身理会,推见至隐,所谓‘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耳。 ”[19](P179)而陆九渊的“《六经》皆我注脚”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也仅仅限于陆氏后学的范围之内。 真正开创“《六经》皆我注脚”时代的还从阳明开始。 阳明在陆九渊学说的基础上进而提出《诗经》是心之歌咏性情的记籍的观点,这就更加凸显了《诗经》是“吾心”之工具的理念。 工具意味着手段,换言之,《诗经》仅仅是认识“吾心”的手段,并非目的。阳明如此定位《诗经》,其实已经将《诗经》从神坛之上拉了下来,将其还原成助人明道恢复“良知”本体的“阶梯”“窗牖”的普通工具;相反,“吾心”的地位却一跃而成为人必须明了的“本体”,即价值目的所在。
在此理论的影响之下,阳明以后的《诗经》学者似乎迸发出罕见的创造力。 刘毓庆先生从明代后期所出现的颇为怪异的《诗经》学著作名称,诸如 《葩苑》《诗墉》《诗逆》《葩经旁意》《葩经约说》《葩经心印》《诗经鞭影》《诗经主意冠玉》,推测出《诗经》 学界所焕发出的创新热情:“他们每个人都想标新立异,写出自己的个性,故而在其新著的命名上大作文章,唯恐不足以震世骇俗。”[20](P54)如钟惺《诗经图史合考》不仅名不副实,而且所隶之事,如同现代蒙太奇,如《桃夭》篇,首引《本草纲目》所载“桃仁去淤血,桃枭疗中恶腹痛”一条,次引《家语》“六果桃为下”一条,次引《管子》“五沃之土宜挑”一条,次引《盐铁论》“桃实多则岁穰”一条,次引江淹《桃颂》一条,次引“昆仑山玉桃”一条,次引“唐明皇目桃为消恨花”一条,次引《酉阳杂俎》王母桃一条,最后引《列仙传》绥山桃一条,而后《合考》之文戛然而止,“于经义一字无关……不知其所取也。”[11](P221)又如凌濛初的《言诗翼》“列《诗传》、《诗序》于每篇之前。 又以《诗传》、《诗序》次序不同,复篆书《诗传》,冠于篇端。”[11](P222)而杂采徐光启等六家诗评,直接用选词、遣调、造语、炼字等文学评论诸法讨论《诗经》本文,被四库馆臣称为“明人经解,真可谓无所不有。 ”[11](P222)顾懋樊之《桂林诗正》,四库馆臣谓其“博采众说,参以己见,然多不根之创建。如谓《郑》之《丰》及《风雨》篇皆齐诗,而误入于《郑》。 《风雨》诗以鸡鸣失时,比齐之昏乱。桓公兴,仲父相,乃晦明指大际。孔子删诗录《风雨》,亦犹微管仲之意也。 ”[11](P224)何凯《诗经世本古义》,不仅完全打乱了《诗经》原有的次序, 而且将《诗经》 的时代上推到夏代少康之世。《诗》之作者及各篇的具体时代,本皆茫然,后儒弗传,“楷乃于三千年后,钩棘字句,牵合史传,以定其名姓时代。如《月出》篇有‘舒窈窕兮,舒忧受兮’之文,即指以为夏征舒,此犹有一字之近者也,《硕鼠》一诗,茫无指实,而指以为《左传》之魏寿余,此孰见之二孰传之……以《草虫》为《南陔》,以《菁菁者莪》为《由仪》,以《缗蛮》为《崇丘》,又孰传之而孰受之?大惑不解,楷之谓乎?”[11](P203-204)明人之《诗经》学研究之所为,虽近于荒诞,但从侧面也反映出他们已经将《诗经》视为抒写自己心灵的手段,借助《诗经》来印证自家的体悟。所有这些都说明一个问题, 即如同理学从朱熹时代迈入阳明时代一样,《诗经》 学确实也走出朱熹的时代而进入一个更为广阔的世界, 这虽然是复杂的历史合力的必然趋势,但阳明《诗经》观的助推作用亦不可忽略。①本文部分观点借鉴了或启发于刘毓庆先生的《阳明心学与明代诗经研究》(《齐鲁学刊》2000 年第5 期)与吴伯曜先生的《王阳明的诗经观》(《诗经研究丛刊》2008 年第1 期),在此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