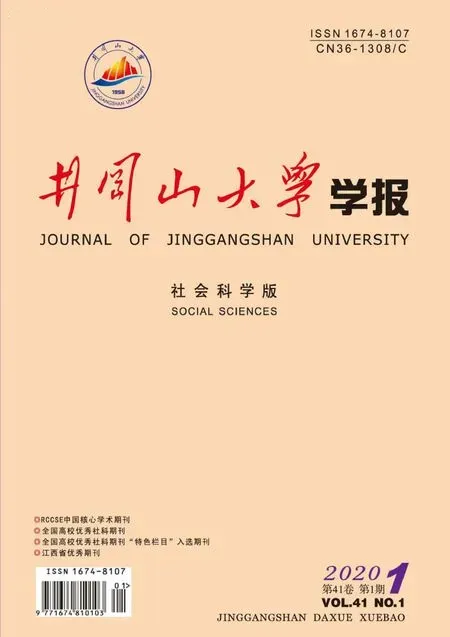朱熹、王阳明的“格物致知”论比较
——以其《春秋》《左传》学为视角
2020-02-10樊智宁
樊智宁
(同济大学人文学院,上海200092)
宋明时期, 由于理学的兴起与发展, 当时的儒者往往通过理学的方式解读 《五经》, 从中发明诸多新意。 作为宋明时期理学和心学的集大成者, 朱熹和王阳明也不例外。 朱熹十分重视经学, 从他本人著 《四书章句集注》 《诗集传》《周易本义》 和委托弟子蔡沈作 《书集传》 就能看出这一点。 在《朱子语类》 中有他讨论读书治学的方法:
只就文字间求之, 句句皆是。 做得一分, 便是一分工夫。 非茫然不可测也, 但患人不子细求索之耳。 须要思量圣人之言是说个甚么, 要将何用。 若只读过便休, 何必读
从这段话中我们能够看到, 朱熹的治学之道将对文本的研究看作重要的工夫着力之处。 这就不难理解他为何如此重视经学。 但是王阳明的观点与朱熹大相径庭, 他被贬谪至贵州龙场时曾著有 《五经臆说》, 这部著作的序言充分表达出王阳明对经学的看法:
得鱼而忘筌, 醪尽而糟粕弃之。 鱼醪之未得, 而曰是筌与糟粕也, 鱼与醪终不可得矣。《五经》, 圣人之学具焉。 然自其已闻者而言之,其于道也, 亦筌与糟粕耳。[2](P965-966)
王阳明认为 《五经》 乃是圣人传道的载具,圣人之道是 “鱼” 与 “醪”; 《五经》 相对于圣人之道而言则是“筌”与“糟粕”。 《五经臆说》的序言可谓王阳明经学观的总纲, 其核心在于“得鱼而忘筌,醪尽而糟粕弃之”,其目的“主要是批评朱子后学的拘泥于朱子文字蹈旧的风气。 ”[3]
朱熹与王阳明分别作为理学与心学的集大成者, 其学习分歧肇始于对 《大学》 中 “三纲领”与 “八条目” 理解的不同, 尤其是 “格物致知”论。 当代学者大多从理学本身的视角对朱熹与王阳明的“格物致知” 论进行比较研究, 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 不胜枚举。 但是, 儒学的形式不单只有理学, 经学也是一种重要的形式。 朱熹与王阳明对儒家之经典, 尤其是 《春秋》 与 《左传》的理解皆有其特色。 目前学界鲜有基于经学的视角, 通过对比他们的《春秋》 学与《左传》 学来研究他们“格物致知” 论的差别。 因此, 本文讨论的是: 朱熹和王阳明的《春秋》 和 《左传》 学有何异同? 他们之所以产生异同之处的缘由何在? 这种异同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他们对经学的理解以及其“格物致知” 论?
一、 天理与人欲: 朱熹、 王阳明关于 《春秋》 和 《左传》 评价的异同之处
《春秋》 在儒家 “五经” 之中可以说是义理较为艰深的, 其中关于《春秋》 的解释派别也很多。 汉代今文经学有 《公羊传》 《谷梁传》, 古文经学有《左传》, 宋代又有胡安国作《传》。 并且, 《公羊传》 《谷梁传》 和《左传》 都被列入儒家“十三经” 之中。 《春秋》 的三部《传》 都升格为“经”, 这是“五经” 中所独有的。 其中,《左传》 以详叙事件始末的方式注解经文, 在各类《春秋》 的《传》 中显得较为特殊。 因此, 朱熹和王阳明在论及 《春秋》 时往往兼评 《左传》的价值。
(一) “天理” 的载体: 朱熹、 王阳明对《春秋》 评价的相同之处
在《朱子语类》 中, 朱熹有大量和弟子的对话涉及 《春秋》。 在论 《春秋》 的纲领部分中,有一段其弟子周谟所载的语录, 基本可以代表朱熹对《春秋》 的评价。
《春秋》 所书, 如某人为某事, 本据鲁史旧文笔削而成。 今人看 《春秋》, 必要谓某字讥某人。 如此则是孔子专任私意, 妄为褒贬! 孔子但据直书而善恶自著。 今若必要如此推说, 须是得鲁史旧文, 参校笔削异同, 然后为可见, 而亦岂复可得也?[1](P2146)
朱熹认为《春秋》 的内容乃是孔子根据鲁国史书的旧文“笔削” 而成, 其中未必字字含有褒贬。 《春秋》 的价值在于孔子秉笔直书, 其是善是恶自然明于经文之中。 因此, 后儒对 《春秋》“大义” 的解释大多出自个人的臆测。 如果 《春秋》 诚如有后儒所释的义理, 则必须与鲁国史书旧文相对照方能察验, 这显然已经是 “死无对证”。 换言之, 朱熹“实持一史家立场”[4]来审视《春秋》 的价值。
在《传习录》 中, 徐爱问王阳明如何评价王通和韩愈时, 有一段关于“拟经” 和“著述” 哪一种治学方式更利于明道的讨论。 王阳明以孔子删述 《六经》 为例, 其中就有对 《春秋》 的评价。
至于 《春秋》, 虽称孔子作之, 其实皆鲁史旧文。 所谓 “笔” 者, 笔其书; 所谓 “削” 者,削其繁: 是有减无增。 孔子述 《六经》, 惧繁文之乱天下, 惟简之而不得, 使天务去其文以求其实, 非以文教之也。 《春秋》 以后, 繁文益盛,天下益乱。[2](P9)
王阳明在《春秋》 成书的基础上与朱熹看法一致。 并且, 他进一步阐释 “笔” “削” 之意。“笔” 即秉笔直书, “削” 即删繁就简。 《春秋》其旨就是务求以简明扼要的语言阐述大义所向,以此警戒后人。 《春秋》 书 “伐国”, 那便是罪责某人僭越天子之权以征伐他国; 书 “弑君”,那便是罪责某人以下犯上弑杀君长。 “大义” 一目了然, 解释和注疏反而增加许多不必要的内容。 换言之, 王阳明将《春秋》 “一则视之为鲁国记事之史, 此乃史学; 二则强调‘圣人作经之意’, 是为经学”。[5]
综上所述, 朱熹和王阳明对《春秋》 的评价大致是相同的。 其一, 《春秋》 是孔子基于鲁国史书旧文“笔削” 而成, 朱熹和王阳明都赞成这种表述方式。 其二, 孔子作《春秋》 目的在于拨乱反正、 除弊私欲、 肃正人心, 这也是 《春秋》的价值所在。 其三, 《春秋》 的“大义” 在经文中已经昭然若揭, 后儒对经文义理的解释实际上是画蛇添足, 甚至曲解孔子的本意。 质言之, 朱熹和王阳明都把孔子作《春秋》 之举视为“存天理” 之道, 《春秋》 是承载“天理” 的器具, 其中经文所言的大义都是“天理”。
(二) “天理” 和“人欲”: 朱熹、 王阳明对《左传》 的评价的差异之处
朱熹在讨论完《春秋》 的纲领之后, 又与弟子们详细阐述《春秋三传》 的得失之处。 其中关于 《左传》 的内容最为详实, 这里选择潘时举、辅广、 黄义刚所录的三条为例:
看《春秋》,且须看得一部《左传》首尾意思贯通,方能略见圣人笔削,与当时事之大意。[1](P2148)
《春秋》 之书, 且据左氏。 当时天下大乱,圣人且据实而书之, 其是非得失, 付诸后世公论, 盖有言外之意。 若必于一字一辞之间求褒贬所在, 窃恐不然。[1](P2149)
左氏之病,是以成败论是非,而不本于义理之正。尝谓左氏是个滑头熟事、趋炎附势之人。[1](P2149)
朱熹对《左传》 的评价具有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 首先说《左传》 的积极方面, 朱熹认为他是《春秋》 的重要参考资料, 有助于理解孔子的“笔削” 之处和历史事件的大意。 很显然, 朱熹以 《左传》 替代鲁国史书旧文, 将它视为展现《春秋》 所载史料全貌的材料。 事实上, 朱熹并不赞成对《春秋》 经文作直接的义理阐释, 他评价《公羊传》 《谷梁传》 曰: “据他说亦是有那道理, 但恐圣人当时当初无此等意。”[1](P2151)相反,他更赞同从事件的全貌入手, 探求孔子的言外之意。 《左传》 很少直接对《春秋》 的经文作义理上的判断, 而是尽可能叙述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 至于其中的是非功过则自待后人评说。 其次则是《左传》 的消极方面, 朱熹认为是“以成败论是非”, 这是它不如 《公羊传》 和 《谷梁传》的地方。 但是朱熹只是在治学态度上批评 《左传》, 并未否定它的价值。 由此可见, 朱熹对《左传》 的评价总体而言是认可的。
王阳明在论述《春秋》 之后, 徐爱又进一步询问他对 《左传》 的看法。 徐爱引用程颐将《经》 视为“断”、 《传》 视为“案” 的观点, 认为《春秋》 中的“大义” 可以通过《左传》 的文本探明。 王阳明则不以为然, 他认为:
圣人述 《六经》, 只是要正人心, 只是要存天理、 去人欲, 于存天理、 去人欲之事, 则尝言之; 或因人请问, 各随分量而说, 亦不肯多道,恐人专求之言语, 故曰: ‘予欲无言’。 若是一切从人欲、 灭天理的事, 又安肯详以示人? 是长乱导奸也。 世儒只讲得一个伯者的学问, 所以要知得许多阴谋诡计, 纯是一片功利的心, 与圣人作经的意思正相反, 如何思量得通?[2](P10)
王阳明对《左传》 的评价与《春秋》 截然相反。 他认为孔子删述 《六经》 就是要做存天理、去人欲之事, 对于《春秋》 而言“笔削” 就是如此。 孔子所 “笔” 者, 就是 《春秋》 中的经文,这些被保存、 转述的经文就是“天理”; 所“削”者, 就是鲁国史书的其余旧文, 这些文本就是“人欲”。 然而《左传》 叙述经文背后事件的本末与鲁国史书旧文的作用如出一辙, 这就相当于把“人欲” 又找回来。 这种 “人欲” 饱含阴谋诡计和功利之心, 是人内心的私欲。 如果以 《左传》为途径探求 《春秋》 中的 “大义”, 无异于是通过私欲去体察至善, 以“人欲” 去追寻“天理”。因此, 《左传》 不但不能有助于我们追寻圣人之道, 反而会腐化人心, 与孔子作《春秋》 的本意背道而驰。
综上所述, 朱熹和王阳明对《左传》 的评价是截然相反的。 在朱熹看来, 《春秋》 所载圣人之道, 是“天理”; 《左传》 虽然未达到“天理”的高度, 但它是人们体察、 获知、 追寻 “天理”的必要途径。 此外, 朱熹推崇《左传》 更是因为它在解释经文的时候不会妄加揣测孔子的心意,而是以平铺直叙的方式记载史实, 至于经文中的大义所在, 应当由后人在文本中做工夫去体察。在王阳明那里, 《春秋》 “大义” 固然也是“天理”, 但是《左传》 所载尽为“人欲”, 后儒拘泥于《左传》 的文本, 反而是“存人欲, 去天理”。换言之, 王阳明认为要探知圣人之道不应当于《左传》 的文本中做工夫。 圣人之道是敦实尚质、务求精一的, 这在 《春秋》 的经文中已有明示,根本无需再向外求索。
二、 格物致知: 朱熹、 王阳明《左传》 学的差异之由
朱熹和王阳明对 《春秋》 的评价大同小异,这是因为他们都将其所载之道视为 “天理”。 但是朱熹认为 《左传》 是探知 “天理” 的必要途径, 王阳明则认为 《左传》 是 “人欲”。 我们需要讨论的是, 他们对《左传》 的评价为什么会存在如此重大的差异? 宋明理学家把《大学》 的中心论点概括为 “三纲领” 和 “八条目”, “格物致知” 隶属于“八条目” 之下。 “格物致知” 是修养工夫, 是为学之始、 成圣之基, 在朱熹和王阳明的哲学体系中都具有重要地位。 正是因为他们对“格物致知” 的理解的不同, 所以才导致他们对《左传》 评价的差异。
(一) 即物穷理: 朱熹“格物致知” 的思想
朱熹将 《大学》 的内容分为 “经” 与 “传”两个部分。 其中首章提出 “三纲领” 和 “八条目”, 是为 “经”。 其余的十章是解释 “三纲领”和 “八条目” 的, 是为 “传”。 在大学的 “传”中并没有出现对“格物致知” 的解释, 朱熹认为这是 “阙文” 造成的。 于是朱熹就在 “格物致知” 条目相应的位置上补写了 《传》, 以填补所谓的“阙文”:
所谓致知在格物者, 言欲致吾之知, 在即物而穷其理也。 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 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 惟于理有未穷, 故其知有不尽也。 是以《大学》 始教, 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 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 以求至乎其极。 至于用力之久, 而一旦豁然贯通焉, 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 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 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6](P7)
朱熹填补的《传》 文是他“格物致知” 思想的重要体现, 要理解他这段话中的思想, 就要从他对“格”、 “物”、 “致”、 “知” 四个字的解释着眼。 首先看“格” 与“致” 这两个动词。 朱熹曰: “格, 至也”[6](P4), “致, 推极也”[6](P4)。 朱熹将“格” 训为至极或穷尽, 将“致” 训为将某物推至极点。 再看“物” 与“知” 两个名词。 朱熹曰: “物, 犹事也”[6](P4), “知, 犹识也”[6](P4)。朱熹将“物” 理解为世间的万事万物, 这些事物包括山川草木、 鸟兽鱼虫等自然存在的事物, 同时也包含诸如仁义、 忠信、 孝悌等归属于人伦范畴的事物。 此外, 朱熹还认为 “天下之物,则必各有所以然之故与其所当然之则, 所谓理也”[7](P1389)。 与 “物” 相对的是 “理”, “理”是“物” 得以存在和变化的根本原则, 并且逻辑上是优先于“物” 的。 朱熹将“知” 理解为对万事万物的知识, 与 “物” 和 “理” 相同, 他的“知” 所涵盖的范围也包括自然知识和伦理知识两个方面。 因此, “格物致知” 就是到物上穷极事物及其背后的道理。
在明确朱熹对“格”、 “物”、 “致”、 “知”的解释之后, 就不难理解他这篇《传》 文所要表达的意思。 每个人的心灵都有认知能力, 世界的万事万物背后都存在相应的 “理”, 人就是要穷尽认知这些 “理” 方能正其心、 诚其意。 因此,《大学》 将 “格物致知” 作为 “八条目” 的基石就是要求人将为学的工夫从 “即物” 开始体察事物背后的 “理”, 然后再将 “理” 推及到自身的认知之中, 这就是 “即物穷理”。 “即物穷理”有两个特点。 其一,“即物穷理”并非是一蹴而就的, 而是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 为学之人应当将工夫用力做足,“若是穷得三两分,便未是格物, 须是穷尽到得十分, 方是格物。”[1](P294)其二,“即物穷理” 中所“即” 之“物” 是外在于自身、与 “吾心” 之 “知” 相对的。 朱熹认为 “知在我, 理在物”[1](P291)实际上就是将物我两分, “格物致知” 成为由外及内的过程。
朱熹对 《左传》 的评价明显带有 “即物穷理” 的这两个特点。 “《春秋》 以道义。 拨乱世反之正, 莫近于 《春秋》”[8](P3297)。 在朱熹那里,《春秋》 所道之“义” 就是“理”。 一方面, 要探知《春秋》 所载的“理”, 人们不仅要在《春秋》的经文中做工夫, 《左传》 同样也是工夫着力之处。 《左传》 将历史的完整面貌呈现在世人的眼前, 这就是完整的载 “理” 之 “物”, 只有通过阅读这些 “物” 方能穷尽其中的 “理”。 所以朱熹认为, 理解《春秋》 需将《左传》 看得“首尾意思贯通”。 另一方面, 《春秋》 的经文和 《左传》 都属于 “物”, 都是外在于人心中的 “知”。《春秋》 中的“义” 在经文之中, 相对经文而言,《左传》 又更显得是外在之“物”。 朱熹主张的治学方法也要求人们向外 “即物穷理”, 并且这个向外的过程是必不可少的。 因此, 欲明 《春秋》中的 “大义” 必须要 “格” 《春秋》; 欲明 《春秋》 又必须“格” 《左传》。
(二) 致良知: 王阳明的“格物致知” 思想
王阳明不认同朱熹的观点, 他认为 《大学》的《传》 在“格物致知” 的条目中并无“阙文”。他不尊崇朱熹所补之《传》, 而是以古本《大学》为依据提出他的“致良知” 说:
知是心之本体。 心自然会知: 见父自然知孝, 见兄自然知弟, 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 此便是良知, 不假外求。 若良知之发, 更无私意障碍, 即所谓“充其恻隐之心, 而仁不可胜用矣”。然在常人不能无私意障碍, 所以须用致知格物之功。 胜私复理, 即心之良知更无障碍, 得以充塞流行, 便是致其知。[2](P7)
如果说朱熹的“格物致知” 重点在“格物”,王阳明更关注的则是 “致知”, 他对 “格”、“物”、 “致”、 “知” 的解释与朱熹也有差别。王阳明将 “格” 训为正; “致” 训为至; 将“物” 训为事; 将 “知” 理解为 “良知”。 所谓“格物”, 就是 “去其心之不正, 以全其本体之正。 但意念所在, 即要去其不正以全其正, 即无时无处不是存天理, 即是穷理。”[2](P7)所谓 “致知”, 就是 “非若后儒所谓充广其知识之谓也,致吾心之良知焉耳。 ”[2](P1070)我们能够看到, 王阳明所理解的“格物致知” 与朱熹相比几乎是相反的。 其一, 在“物” 与“知” 这两个名词的解释上, 王阳明将它们所包涵的概念范围缩小了。 他说: “身之主宰便是心, 心之所发便是意, 意之本体便是知, 意之所在便是物。 如意在于事亲,即事亲便是一物; 意在于事君, 即事君便是一物”[2](P6-7)。 可以看出这里的 “物” 和 “知” 只涉及伦理领域, 并不包括自然领域。 其二, 由于王阳明将“物” 和“知” 仅作伦理上的理解, 那么“格” 和 “至” 就不再指向外部世界, 而是指向每个人自身的心灵, 这就意味着“理” 其实就在我们的心中。
实际上在王阳明那里“格物” 和“致知” 是一回事。 “物” 背后的 “理” 也是事亲、 事兄、事君等人伦之理, “格物致知” 就是要除去个人的私欲, 使每个人心中与生俱来但却被遮蔽的“良知” 重新显现出来进而将其扩充流行, 这就是所谓的 “致良知”。 与朱熹 “即物穷理” 的两个特点相对, 王阳明的 “致良知” 也有两个特点。 一方面, “良知” 是向内求的, 而非向外求。 所谓“心即理也。 天下又有心外之事, 心外之理乎?”[2](P2)人要求知事君、 事父、 事兄、事友的 “理” 不能从君、 父、 兄、 友的身上探求, 而是要从自身的心中探求, 心中有这些“理” 自然也就能够躬行这些事。 另一方面, 王阳明虽然也赞同用力之久的工夫, 但是他也不排除人能够顿悟体察到“良知” 的可能性。 见到父亲自然就明白“孝” 的道理, 见到兄长自然就能明白 “悌” 的道理, 见到君上自然就明白 “忠”的道理, 其他的德性也是如此, 这是因为 “良知” 本来就在人的心中。
王阳明对《左传》 的评价同样也体现“致良知” 的这两个特点。 对于 《春秋》 所承载的“理” 而言, 《左传》 是外在的文本。 为学之人如果拘泥于《左传》 的词句, 沉湎于对经文的文字、 名物和史料的考据无疑是将工夫用错地方。《春秋》 中的 “大义” 不必通过 《传》 而后明,其经文本身就是圣人之道。 “良知” 本就在人们的心中, 人可以凭借《春秋》 简明的经文向内求索, 探知圣人之道。 故而也无必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充斥功利之心、 满载 “伯者的学问”的《左传》 中。 诚如王阳明对钱德洪所言, 他治学一生“只‘致良知’, 虽千经万典, 异端曲学,如执权衡, 天下轻重莫逃焉, 更不必支分句析,以知解接人也。 ”[2](P1075)
三、 “格物致知” 论视角下解经的差异: 以《隐公元年》 为例
“格物致知” 论的差异是朱熹与王阳明对《春秋》 与 《左传》 评价产生异同的根源。 尤其是在对待《左传》 的态度上, 朱熹与王阳明之间的分歧亦深刻地影响了他们对《春秋》 经文的解释。 在 “五经” 之中, 朱熹与王阳明对 《春秋》经文的阐释与讨论的文字并不多, 但他们都涉及《春秋》 开篇关于 《隐公元年》 的两段重要的经文, 即 “元年春王正月” 和 “郑伯克段于鄢”。以下就围绕朱熹与王阳明对这两段经文的阐释与讨论, 进而管窥二人将“格物致知” 论应用于解经中的差异。
(一) 朱熹对经文的讨论: 从礼法到天理
朱熹对《隐公元年》 的经文有一段总论, 其曰: “《春秋》 一发首不书即位, 即君臣之事也;书仲子嫡庶之分, 即夫妇之事也; 书及邾盟, 即朋友之事也; 书 “郑伯克段”, 即兄弟之事也。一开首, 人伦便尽在。 ”[1](P2160)换言之, 在朱熹看来, 《隐公元年》 的经文将儒家的“五伦” 关系尽数含摄于其中, 可见其重要性。 然而, 朱熹与其弟子的讨论主要围绕礼法与天理之间的关系展开。 比如关于“元年春王正月” 的经文, 朱熹与陈淳、 黄义刚、 叶贺孙的讨论如下:
问: “‘春王正月’, 是用周正? 用夏正?”曰: “两边都有证据, 将何从? 义刚录云: “这个难稽考, 莫去理会这个。” 某向来只管理会此,不放下, 竟担阁了。 ……”[1](P2159)
据今周礼有正月, 有正岁, 则周实是元改作“春正月”。 夫子所谓 “行夏之时”, 只是为他不顺, 欲改从建寅。[1](P2159)
惠公仲子,恐是惠公之妾。 僖公成风,却是僖公之母,不可一例看,不必如孙明复之说。[1](P2160)
从朱熹与弟子们的讨论中可以看出, 不论是历法的正朔还是仲子的嫡庶, 涉及的都是礼法和制度层面的问题。 从这个层面上来看, 朱熹解读《春秋》 似乎带有浓厚的考据色彩, 他对《春秋》中的 “大义” 并不做过多的阐发。 相似的, 在“郑伯克段于鄢” 之经文上, 朱熹与弟子的讨论亦体现了这个特点。
庄公见颍考叔而告之悔, 此是他天理已渐渐明了。 考叔当时闻庄公之事而欲见之, 此是欲拨动他机。 及其既动, 却好开明义理之说, 使其心豁然知有天伦之亲。 今却教恁地做, 则母子全恩, 依旧不出於真理。 此其母子之间虽能如此,而其私欲固未能莹然消释。 其所以略能保全, 而不复开其隙者, 特幸耳。[1](P2160)
此段文字是黄义刚请教朱熹的语录, 涉及的亦是颍考叔劝谏郑庄公于母重修旧好之事。 虽然黄义刚此论被朱熹批评 “恁地忒细碎, 不济得事”[1](P2160)但 是 从 中 可 以 看 出 朱 熹 与 弟 子 的 讲 学依然是立足于礼法, 只不过此段文字体现出其解经思路从礼法入手, 进而探知母子之情的天理之中。
此外, 朱熹在与弟子的讨论中所言及的仲子的嫡庶问题和颍考叔劝谏郑庄公等话题皆出自《左传》, 换言之朱熹及其弟子的《春秋》 学主要是立足于《左传》 的文本。 这也更进一步证明了朱熹甚至其门人对《左传》 的态度。 《左传》 偏重于礼法、 史实和制度的描写, 朱熹亦从这些“物” 入手, 进而逐步获知 《春秋》 中所蕴含的“理”。 由此可见, 朱熹这种从礼法到天理的解经方式与其“即物穷理” 的“格物致知” 论是密不可分的。
(二) 王阳明对经文的解读: 以正心为核心
相似的, 王阳明的解经方式亦受到他“致良知” 思想的影响, 体现出心学化的特点。 其具体应用同样在《隐公元年》 的“元年春王正月” 和“郑伯克段于鄢” 两条经文的解读上。 王阳明开篇即言:
元者, 始也, 无始则无以为终。 故书元年者, 正始也。 大哉乾元, 天之始也。 至哉坤元,地之始也。 成位乎其中, 则有人元焉。 故天下之元在于王, 一国之元在于君, 君之元在于心。……心生而有者也, 曷为为君而始乎? 曰: “心生而有者也。 未为君, 而其用止于一身; 既为君, 而其用关于一国。 故元年者, 人君为国之始也。 当是时也, 群臣百姓, 悉意明目以观维新之始。 则人君者, 当洗心涤虑以为维新之始。 故元年者, 人君正心之始也。 ……”[2](P1075-1076)
王阳明开篇即将 “元” 训为 “始”, 同时构建天、 地、 人三个维度的 “元”。 在 “人元” 之中, 他又将 “天下”、 “国”、 “君”、 “心” 构成一个“元” 的层次不断深入序列, “心” 又是最为根本的层次。 那么《春秋》 何以强调“君之元在于心”? 王阳明认为君王的一举一动皆关乎国家的命脉, 因此必须要先以“正心” 为端修养自身的心性。 而在王阳明的 “格物致知” 论中“正心” 的核心即在于“致良知”, 质言之, 《春秋》 开篇即书“元年春王正月” 之“大义” 在于君王 “致良知” 之教。 同样, 在 “郑伯克段于鄢” 的解读中, 王阳明亦阐述其“正心” 之义。
郑伯之于叔段, 始焉授之大邑, 而听其收鄙, 若爱弟之过而过于厚也。 既其畔也, 王法所不赦, 郑伯虽欲已焉, 若不容已矣。 天线之人皆以为段之恶在所必诛, 而郑伯讨之宜也。 是其迹之近似, 亦何异于周公之诛管、 蔡。 故 《春秋》特其意而书曰: “郑伯克段于鄢”, 辨似是之非,以正人心, 而险谲无所容其奸矣。[2](P1077)
王阳明对郑庄公与共叔段的评价是褒是贬,这里不做过多阐述。 从这段文字中, 可以看出的是王阳明在解经之时更关注于经文的义理。 此外, 王阳明所重视的义理与 《公羊传》 《谷梁传》 亦有所区别, 他并不关注经文的书法和条例, 对“郑伯克段于鄢” 的责任者亦不关心, 他注重于经文整体的辨别是非之用。 这也使得王阳明在解经的时候需要参考部分的史实内容, 但这些内容权且作为其论证的材料, 是为其“辨似是之非, 以正人心” 的目的所用。
在王阳明《春秋》 学中仅存的两条解经文字中, 都出现了 “正心” 的内容, “元年春王正月” 强调的是自我 “正心”, “郑伯克段于鄢”强调的是他人 “正心”。 不论是自我的 “洗心涤虑” 还是对他人的 “辨似是之非”, 无疑都是向内求索的 “致良知” 之教。 由此可见, 以 “正心” 为核心的解经方式是王阳明“致良知” 工夫论在经学方面的具体应用。
四、 余论:
综上所述, 通过对比研究的方式阐明朱熹、王阳明关于《春秋》 和《左传》 学的异同, 同时揭示他们对《左传》 评价存在差异的原因在于对“格物致知” 理解的差异。 朱熹主张以 “即物穷理” 作为工夫修养的方法, 王阳明则以 “致良知” 反其道而行之。 他们“格物致知” 论的差别也直接影响了他们的解经方式。 事实上王阳明早年也信奉朱熹的 “格物致知” 学说, 他曾依此“格竹”。 结果不仅一无所获反而 “格” 坏了身体, 从此便另寻 “格物致知” 之解。 王阳明的“格物致知” 论也时常被当代学者批评, 罗安宪认为, 在对《大学》 文本的阐释上, 王阳明“虽然富有新意, 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创造性的诠释,但这种诠释并不符合 《大学》 原意”[9]。 侯帅认为在对朱熹的“格物致知” 论的理解上, “王阳明的判断有断章取义之嫌”[10]。 甚至陈来亦论曰: “绝大部分理学家, 尽管可以不赞成朱子格物理论, 但还没有人把朱子思想误解到这个程度。”[11](P122)
王阳明为什么会如此误解朱熹, 其中原因不得而知。 但是, 王阳明不认同朱子的 “格物致知” 理论并不意味着他反对朱子。 如果将视野置于当时的思想学术环境中, 王阳明对朱熹理论的批判、 反对甚至误解也应当得到后人一定的理解, 后人对王阳明思想的批评也不必过于苛刻。当时的朱熹学说被官方奉为圭臬, 影响士人的思想和学风, 其结果“扼杀了学术争鸣的空气……成为士子们死背硬记的教条”[12](P26)。 王阳明一方面只能凭借较为极端的方式批判当时僵化的朱子后学的理论体系, 另一方面也需要通过批判朱熹的方式来彰显自身理论的独创性。
在对待经学的态度上也是如此, 王阳明所批判的不是朱熹的经学, 而是当时僵化的朱熹经学。 实际上王阳明并不否认 “五经” 的重要性,否则他也不会撰写《五经臆说》 以阐述自己对儒家经典的理解。 只是对于王阳明而言, “致良知” 是最为根本的成圣之方, 王阳明也担心自己的解读会成为后人修身养性的 “障蔽”, 故而将这本著作付之一炬, 仅存序言和十三篇残文。 尽管从这些残存文献中可以管窥王阳明解经的思路, 也能够对我们研究相应的经文有所裨益, 但是我们无缘看到王阳明的整个经学体系, 这对经学研究来说确实是很大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