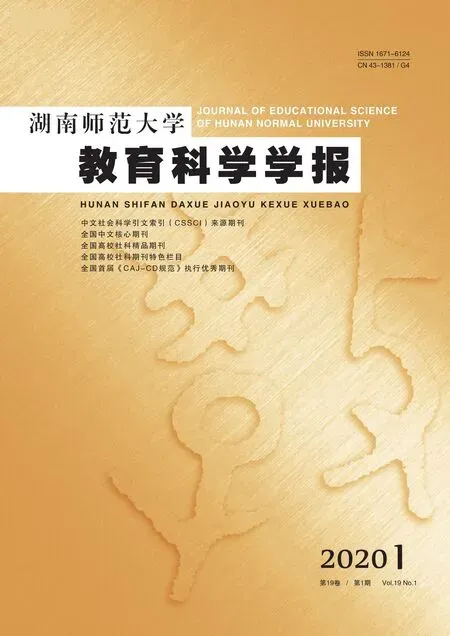“率性之谓道”:《中庸》的古典生命哲学思想及其教育意蕴
2020-01-19李卯
李 卯
(安徽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 安徽 芜湖 241000)
《中庸》是先秦儒学的哲学纲领,相传为孔子之孙子思所作。毫不夸张地说,《中庸》仅用 3 544 个汉字就直抵中国思想的核心①。《中庸》首章开宗明义:“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三句话提纲挈领,环环相扣,“从生命自然观的角度回答了教育何以发生、如何发生以及教育发生的基础等问题”[1]。其中,承接“天命之谓性”和“修道之谓教”的“率性之谓道”清晰地回应了人究竟该如何“教”的问题,蕴含着十分丰富而深刻的古典生命及其教育哲学意蕴,至今仍有宝贵的启迪与借鉴价值。
《中庸》虽旧,其命维新!
一、“性”与“道”
“性”与“道”是“率性之谓道”的关键词,也是《中庸》一以贯之的思想主线。言“性”主要是讲天命的下贯,天是宇宙万物本源性的存在;言“道”主要是讲天命的完成,是对天命的积极接受与回应,两者实际上是在讲“人”与“天”的关系。“‘性’与‘道’乃是‘教’之发生的通‘道’”[2]。“不知性则不知中庸所自来,不知道则不知中庸之所由在。”[2]那么究竟什么是“性”“道”?
关于“性”,《哲学大辞典·中国哲学史卷》指出,“性一般指人性,亦有天性、本性等涵义”[3]。许慎《说文解字》解“性”:“人之阳气性,善者也。从心,生声。”(《说文解字》卷十)另外,人们还分别从天、理、五行说、心、生等多重视角解读“性”:一是从天的视角而言:性被看作是天命下贯而成的产物。如荀子言:“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王夫之言:“性者天道。”二是理学的视角:性是天理的秉受,即“性即理也,所谓理,性是也”[4]。“性,即理也。在心唤做性,在事唤做理。”(《朱字语类》卷五)。三是用汉代五行说解释性:“天命,谓天所命生人者也,是谓性命。木神则仁,金神则义,火神则礼,水神则信,土神则智。”[5](东汉郑玄)四是心学的视角:“性即心”;“心之体,性也”;“知是理之灵处,就其主宰处说,便谓之心,就其禀赋处说,便谓之性”(《传习录》上)。五是生的视角:如《礼记·乐记郑注》中的“性之言生也”;“性者,生之质,命人所禀受”[5]。《论衡·初禀》中的“性,生而然者也”等都蕴含生、生命的含义。
从字源而言,“性”字由“生”字孳乳而来,“独立之性字,为先秦遗文所无,先秦遗文中,皆用生字为之”(《性命古训辩证》)。“性”“生”在先秦古文中常常互训相通。“为炮烙以伤民性”(《韩非子·难势》)和“性者,生也。既生有禀,曰性”(《说文系传通论》)之“性”均可理解为“生命”。“性”是《中庸》的核心概念范畴之一。《中庸》里虽然对“性”没有直接具体地做内涵式的表述,但“天命之谓性”实则从本源的层面界定了“性”。“天降是于下,万物流行,各正性命,是所谓性也”[4],“性则赋于天”,“性自命出,命自天降”。“性”由“天”而来,由“命”所托,是一种“真实无妄之谓,天理之本然”,可理解为上天所赋予的天然的、本质的、固有的、与生俱来的东西,具有“生命”“性命”之意。分析《中庸》全文,“性”不仅指人性,也包括万物之性。按牟宗三先生的观点,“天所命给吾人者即是叫做性”[6]。而如果从“修道”“教化”来释解“率性之谓道”②中的“性”,则侧重指人之性(生命)。既然要“修道”与“教化”,其实隐含一具体的修饰定语——“人”。“人”是“修道”与“教化”的逻辑前提与实施主体,“修道”与“教化”则是人的行为表现。
关于“道”,最初意义是指人所行走的路,后引申出道路、方法、途径和本体、法则、规律,以及方向、目标、措施等意。“道”是中国思想史的一个重要概念范畴。儒、道、墨等诸子百家对“道”有着不同的理解③。由于致思旨趣不同,各家虽都强调“道”,但关注焦点不一。道家之“道”(侧重本体论层面)主要指“天道”,被看作是一种超验的本体性存在,有时也指宇宙本体运行的最高法则和运动规律;儒家强调“人道”(强调伦理层面),即社会人伦方面的秩序、规范、道义等;墨家的“道”(突出实利层面)既指天道亦指人道,但更关注日常操作层面的具体规范。《中庸》谈及“道”多达45次。《中庸》论道,大体有以下三个显著特点:
其一,把性看作是道之体。按朱熹的解释,天命之性就是道之体,“性与道相对,则性是体,道是用”(《朱子语类》卷第六十二)。道就是先天禀赋在日常生活中的具体体现,即“率性之谓道”。
其二,把诚看作是道的至高追求,即“诚者,天之道也”[7]。
其三,把“中”“和”看作是道之存在与呈现的状态,即“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7]。
从字面含义来讲,“率性之谓道”的“道”可理解为规律。从具体内容而言,“率性之谓道”的“道”实则表达了自然规律(天道)和社会法则(人道)两层意思,体现了天人合一的中国传统哲学精神。“人道”由“天道”下贯而来,彼此相互贯通、渗透与映照。“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7]“性与天道,一也。天道降而在人,故谓之性。”[4]一方面,作为宇宙形上本体的天道是万物之源,具有孕育化生、生生不息的功能,通过起委托作用的“命”赋予人道之内容,人道来源于天道;另一方面,作为人存在意义上的人道是天道的具体表现,天道需要通过人道来体现,人道应积极效法并回应天道。
此外,“率”字有沿着、循着、顺着,遵循、遵行、顺从,统率、直率、坦率、率真等意。郑玄在这里将“率”字解释成“循”“顺”,即“循性行之,是谓道”。也就是说,遵循“性”行事,可以称为“道”。二程认为:“循其性而不失,是所谓道也。”[4]“循性”“循其性”“率性”均是符合生命发展规律的表现。朱熹《中庸章句》亦云:“率,循也。”[8]从内在理路上看,郑玄的注解、二程的观点与朱熹的阐释是相通的,都主张“循其性之自然”。“自然者,道也。”(《无名论》)“率性”是表现“道”的过程,即遵循天命自然之性合乎自然规律去行事。在这里,《中庸》提出的“率性之谓道”实则揭示了生命发展的真谛。
二、“率性之谓道”:《中庸》的古典生命哲学思想阐释
以《中庸》为代表的中国古典生命哲学更多呈现的是宽裕雍容、博大宽广的整体生命观,具有独特的概念命题、范畴体系、言语方式。与当代生命哲学语境对“生命”概念的表达与理解不同,《中庸》是在“天—地—人”“人—物—我”的互动结构、“天—命—性—道—教”上行下达的逻辑循环中对生(性)、生命(性命)等问题与现象展开深入论述的。它纵贯天人,横通群己,字里行间洋溢着浓郁的生命意识,囊括生命自然本源观(“天命之谓性”)、生命过程表现观(“率性之谓道”)、 生命实现路径观(“修道之谓教”)、生命价值功能观(“成己—成物—赞天地之化育”)、生命完善方法观(“诚明”与“明城”)、生命理想境界观(“极高明而道中庸”)等方面,并最终形成了完整生动的义理逻辑和展开模式。
开篇的三句话是对《中庸》古典生命哲学思想的总体概括和集中表达。其中,“天命之谓性”是《中庸》作者思考生命问题的逻辑起点,回答了生命(性)之所以来的问题(“天生德于予”);“修道之谓教”勾画了生命(性)之所以成的具体路径(“下学而上达”);而“率性之谓道”,是生命(性)之所以行的根本,深刻揭示了生命活动的真谛和规律。西方人本主义学者罗杰斯曾言:“不去干扰存在物的自然生长规律,他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人,但他能促使‘万物自化’。通过自身的谐和,他引导万物趋向谐和,他使它们自由地表现自己的本性,自由地趋向自己的归宿,他把它们固有的‘道’释放出来。”[9]这可看成是对《中庸》“率性”思想的现代注解。在某种程度上,两者形成了跨越文化时空的遥相辉映,都表达了要顺应自然天性、激发主观能动性、展现自由本性的生命哲学思想。
1. 顺应生命自然天性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7]一方面,作为“天下之大本”的“未发”“中”可看成上天赋予人的且不受外力干扰的一种本然性实存状态,是自然天性的真实反映,是人之“所是”,人也是通过生命本身固有的“中”去实现与宇宙其他生命的和谐共处;另一方面,作为“天下之达道”的“发而皆中节”“和”是人之“能是”,亦表明人之生命发展若要达成“天地位”“万物育”的理想境界就必须要充分利用天性资源,恪守并遵从天道,也就是《中庸》讲的“率性”。孟子则主张要“尽心”。“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此“心”便是“本心”“本性”。紧接《中庸》“率性”的“修道”即是弥合人之“所是”与“能是”间隔的过程。
首先,“道”贯注于宇宙万物之中,是生命存在运行的最高法则。“道”与生命须臾不可离,草木虫鱼春生夏长,万物生命新旧变化,“四时之错行”“日月之代明”皆循道而行。“道,犹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则其日用事物之间,莫不各有当行之路,是则所谓道也。”(朱熹语)[8]“宇宙生命万物各循自然之性而动、各在‘日用事物之间’依照其‘当行之路’行事,都是一种遵循自然符合规律的行为,这即‘道’。”[10]人的生命发展活动又何尝不是如此?“中庸之道,出于人性;实现中庸之道,即是实现人性;人性以外无至道。违反人性,即不成为至道。”[11]依《中庸》的观点,这种中庸之道始终与人的生命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渗透在日常生活实践之中。中庸之道亦是生命发展之道,从根本上而言即依循上天所赋予的自然天性,尊重生命发展的内在逻辑。生命的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率性”即要求“遵道而行”[7],需从近、低、易、细处着手,由简易到繁难、由细小④到精深,需循序渐进,不可操之过急或“半途而废”[7]。若违背这一逻辑法则,则欲速不达,适得其反。《中庸》在这里运用“行远必自迩”“登高必自卑”的生活实例对如何践行中庸之道作了具体说明:“君子之道,辟如行远必自迩,辟如登高必自卑。”[7]辟通譬,意思是譬如,如同;自,从也;迩的意思是近。君子实行中庸之道,如同走远路一样,必定要从近处开始,由近及远;如同登高山一样,必定从低处开始,由低向高。如果能够做到这点,便能水到渠成地实现“诚则明矣,明则诚矣”。“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7]也就是说,这样的中庸之道虽然普通常见,但其所达的境界却十分广大,影响非常深远。
其次,性由天所命赋,各得其形、各得其性,但此形此性有着本质的不同,是唯一而独特的。个体生命在体格、态度、兴趣、气质、潜能等方面均存在一定的差异性,有其个性特征。“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笃焉,故栽者培之,倾者覆之。”[7]郑玄注“材,谓其质性也”,“材”由“性”决定,“因其材”正是对“率性”的回应。原意是说:上天孕生化育万物,必须关注自然天性和基本材质,生命才得以“笃实”,对根正干直可以成材的树木需要用心地呵护培育它,对斜曲不正难以成材的树木可以选择放弃让其倾倒。换言之,自身天性是万物生命成长的基本前提。这实际上体现了《中庸》尊重个体差异、包容独特性的生命思想。不止如此,《中庸》对人应如何“因其材”还有着更为具体详尽的论述:“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7]“生而知之”(安而行)、“学而知之”(利而行)、“困而知之”(勉强而行)代表了三种不同类型的个体生命。《中庸》作者根据其特点个性化地设计了“诚明”(尊德性)、“明诚”(道问学)、“诚明合一”(尊德性而道问学)三种路径不同、旨向一致的实现途径,经过不同程度的努力付出,最后都能达成“及其成功一也”[7]的效果。不难发现,《中庸》将自然天性看作是生命目标实现的根基,彰显了对生命的应然性尊重和敬畏。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语)在《中庸》看来,“性的呈现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12](比如《中庸》言“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等),生命的发展就要遵循“道”(“率性”)的要求。所谓“率性”,就是要合乎自然之理,顺应自然天性,即“循其本性”“遵其本性”“顺应本性”。按老子的说法,就是要“以道为度”“唯道是从”(《老子》第二十一章),“我之教人,非强使人从之也,而用乎自然”(《老子》第四十二章)。在这里,《中庸》“率性之谓道”实际上揭示了第一层生命哲学内涵:若想达成促进个体生命发展之目的,就必须顺应和遵循个体生命发展的自然天性和内在逻辑。
2. 激发生命主观能动性
顺应自然天性是一种《中庸》之“道”,但这是否意味着循着自然天性展开的生命行为就是完整的《中庸》之“道”呢?这是否表明,作为能动主体的人在自然(包括“天”“天命”的“性”)面前完全被动无所作为了呢?其实不然,如果说草木鱼虫是本能遵道的话,那么人则是主动遵道而行。与道家老庄更加强调“顺应”“无为”不同,作为古典性命之学代表的《中庸》与孔子“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等儒家入世哲学的思想一脉相承,“并没有否定人的主体性;正好相反,它是从德性实践的意义上肯定了人类的主体性,肯定了人的作用”[13],还强调了生命的“积极有为”和“率性而为”,认为生命的达成不是完全被动的外塑,需要主体自我的主动创造。如果说,“天命之谓性”承认了人之主体性存在的先天合理性,那么“率性之谓道”则是肯定甚至鼓励了人之主体性的发挥和张扬,主张积极能动地回溯自我生命。
天道与人道相贯相通是中国伦理精神发展的前进路径。在天人的转换过程中,除了“诚者,天之道也”[7],《中庸》还言:“诚之者,人之道也。”[7]“诚”强调的是属于本体世界的天道,而“诚之”体现的是建构意义世界的人道。作为天道法则的“诚”通过“诚之”落实在人道的建构上。“诚之”是“率性”的另一种表现,“意味着人试图主动地感通、应合于物,而这恰恰是人生存于世界之中的价值所在”[14]。“只有通过‘诚之’‘尽性’的过程,推广含而未发的本性,方可使其固有的‘善端’得到充分的展现”[15]。如何“诚之”?《中庸》言道:“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7]换言之,人之“率性”还需要凸显其主体能动精神,释放生命自身固有的、天然的、内在的冲动,自主地去“择善”,做到“固执”(不放弃、不终止)。“择善”与“固执”亦是人自身主动性的体现。“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7]自成的“诚”与自道的“道”亦表明:“‘诚’与‘道’都具有内在的动力资源,不假外因、外力便能够自成、自道。”[16]“诚”上承于天,生发于心,是“一种精神状态,而且还是一种能动的力量,它始终在转化事物和完成事物,使天(自然)和人在流行过程中一致起来”[17]。“诚之”是生命的一种自然展现,是生命自身固有的、天然的、内在的冲动。后来,孟子在“诚”的前面加了一个“思”。“思”字更为充分地体现了生命能动性的意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孟子·离娄上》)其实,《中庸》的“诚之”与孟子眼中的“思诚”都表明,生命本身并不是一味颓然的顺应天命,还需把天命赋予人类生命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发挥出来,积极、主动、自觉地进行生命的自我陶炼,才能实现人之道,并通达天道之诚,感悟到“天地之道”的“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7]。人只有经过主观努力,才更有可能接近这种真实无妄的生命本然状态。
“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也。有弗问,问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笃弗措也。”[7]“有”可理解为除非,“弗”解释为不,“措”即罢休、搁置、终止。意思是说,除非不学习,倘若学习了还没有掌握,不能罢休(要继续学习)。除非不去问,倘若提出疑问尚不能理解,不能罢休(要继续刨根问底)。除非不去思考,倘若思考了仍未能获得正确的结论,不能罢休(要继续认真思考)。除非不去辨别,倘若辨别了未能明白,不能罢休(要继续仔细甄别)。除非不去做,倘若做了还不够坚定,不能罢休(要继续坚定信念)。《中庸》在这里实际上谈到了坚韧不拔、持之以恒等内在的意志品质对个体生命学习行为的重要性,也对如何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提出了非常具体的要求。这即表明“率性之谓道”蕴含的第二层生命哲学思想:生命的最终实现不能只靠外在的强加和一味地他为,还需“自诚明”,即充分激活个体生命内在的主观能动性,积极主动地“自为”“自发”“自主”“自动”地打开与呈现⑤。
3. 展现生命自由本性
按照朱熹的理解,“率性”即“尽性”。根据吴怡《<中庸>诚的哲学》中的观点,整部《中庸》发挥的乃是尽性之学。“尽性”之“尽”与至诚之“至”意义想通,有最、极、充分、完全等意涵。依循《中庸》的语境逻辑,“尽性”亦是生命“率性”的一种表现,体现了对天命的落实与贯彻,即根据天命之性而引导自身生命发展,是实现人之生命或人之为人的过程。《周易·说卦传》言:“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理学大师张载提出:“尽其性然后能至于命”(《正蒙·诚明》)。“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与“尽其性然后能至于命”将“尽性”与“天命”联系起来,均表达和表明了人首先应尽其性,然后再达成命的意思,即徐复观先生所言的“尽性,即是性与命的合一”[18]。具体来说,“‘尽性’就是要充分彻底地发现生命、发掘生命、发挥生命、发展生命,将上天赋予的生命天性发挥到极致”[19]。“唯天下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7]这是从本体论发生学的角度对生命本性及其生成过程的形上描述,进而形象地勾勒出一条自内在本体至外在现象的因果锁链。“尽人之性”与“尽物之性”是对“天地之化育”及其运行规律的尊崇、发现与唱颂,正是在与天相通、与物相接,并始终参与天地万物生化的过程中实现“尽人之性”→“尽物之性”→“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矣”,天下万物达成各得其所、各得其自然而然,各得其自由自在,宇宙生命由此得以解脱与自由,也就是《中庸》首章末句所言的“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7]。
在中国传统哲学中,老庄是崇尚自由的典型代表。老子描绘了自然无为、纯真质朴、无知无欲的生命自由状态。庄子追求的则是一种精神世界的自由,他用蝴蝶和鲲鹏寄托了对自由的向往,即《齐物论》和《逍遥游》中所描述的游六合、驰骋宇宙、无牵无挂、无拘无束、自由超脱的那种生命境界。《中庸》“率性”表达的也是这种遵循生命本然状态且要尽情唤醒生命自由天性的意思,其主张达成的至诚境界意味着生命自由自在、本性纯真理想的实现。“鸢飞鱼跃”便是这种和谐美妙图景的真实写照。“鸢飞戾天,鱼跃于渊”[7]、“言其上下察也”[7],上自天空中的飞禽鸟类,下至江河湖海中的各种鱼类,都能自由自在地飞翔遨游。这里,《中庸》引用《诗经》中的话语描述了自然界无所不在、随处可见的生命之自由状态,突显了自然界的丰富多样性与生命活力。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中庸》“率性”还有追求自由、超然和崇高的意思。
关于自由,亚里士多德提出“人本自由”⑥。马克思认为:“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20]而在《中庸》看来,生命是由上天赋予,自由就是上天所赋予生命的固有的、先在的基本品质,是“天命之性”自然而然的流露,体现了生命至高无上的价值。“率性”与“尽性”首先要基于“天命之性”,遵循生命内在的自由品质,在尊重顺应生命的基础上,展现、激活、超越生命。“《中庸》所追求的理想人格在最现实的意义上讲就是自由。只有在自由的境界中,人才能一以贯之地循性而行。”[21]用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的话来说,这里的“率性”就是要不断地“去蔽”;在生命哲学家叔本华眼中即是“障碍的消除”。“去蔽”和“障碍的消除”实际上都体现了对自由的诉求。自由是实现《中庸》之“诚”、“明”及“至诚无息”的前提,只有实现自由,博、厚、高、明、悠、久⑦等各种生命形式及样态方可自然而然地显现,“如此者,不见而章,不动而变,无为而成”[7],天地秩序方能正位,万物得以养育发展。于是,“率性之谓道”蕴含的第三层生命哲学思想呼之欲出:生命的发展需突破各种限制自由的有形与无形的藩篱,摆脱外在野蛮的强制束缚,尽最大可能唤醒个体生命内在的自由本性,让生命潜能得以整全、最大限度地自由展现。
三、教育意蕴
梳理“人何以接受教育”这一中国古典教育哲学基本命题的内在理路,“性”⑧是很多思想家论证该命题难以回避的逻辑前提。其中,被宋儒称为“群经之统会枢要”的《中庸》之“率性”观点对后世影响深远。“《中庸》关于‘天性’‘ 气禀’‘ 修道’论证体系的核心体现在‘率性’二字。”[22]“在《中庸》‘天性—率性—修性’的生命发展轨迹中,起点是‘性’;过程则要求率性而为,遵道而行,不得违逆与背离;终点即‘修道’之‘教’。”[23]也就是说,“性”为原点和归宿,“道”是具体要求,“教”是实现“性”的过程,“‘教’在‘性’与‘道’中降临并达到自身”[24]。整个过程既是在探讨生命问题,又是对人生教化的积极回应。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庸》里的“率性”不仅是一种生命自由自然发展并最终实现最大限度绽放的历程,也是一种基于生命而能动展开的教育过程,同样蕴含了深邃旷达的教育意蕴。
1. 自然天性是教育活动展开的逻辑起点
“出自造物主之手的东西,都是好的,而一到了人的手里,就全变坏了。”[25]在法国自然主义教育学家卢梭看来,“出自造物主之手的”即是自然天性,“到了人的手里”即是背离自然天性而人为设计的,是“强使”且“不愿意”的,这样的教育活动更像是练马场中对马的训练,自然“就全变坏了”⑨。于是,“我们将造成一些年纪轻轻的博士和老态龙钟的儿童”[25]。而我国儒家古典性命之学之一的《中庸》在更早的时候便表达了与之相比丝毫不逊色的观点,在呈现“天命之谓性”的命题后,对“天命”与“性”“不加任何界定”,紧接着就抛出了“率性之谓道”的命题,这意味着“直接从性出发”,体现了“性”之主动能动。可以说,“‘性’是《中庸》由‘命’至‘教’的重要基础和前提,为顺利展开人生的修炼(‘教’)提供了可能”[10],“它清晰地界定并确立了教育的自然法”[26]。“性者,天理之混然。道者,循性之自然。教者,圣人因其自然而品节之,使学者有所持循也”[27]。“如果能‘率’而循其性,则自然‘中节’”⑩。“性之所能,不得无为也;性所不能,不得强为”(《外物注》)。道是率性的过程,教是遵道的体现。遵道的根本在于对生命自然天性的尊重。只有循着自然天性(“率性”)而为才能使生命内在潜能得到最大限度释放。“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7]“道”亦表达了基于生命的教育活动须臾片刻不能离开生命自然天性的道理。庄子《至乐》篇中鲁侯养鸟的寓言同样告诫我们:不尊重或者背离生命自身天性的活动,必然会造成不可想象的后果。而我们当下周遭教育中的诸多弊端和误区恰恰在于我们对这种《中庸》之“道”的偏离。在“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等功利绩效思维的驱使下,忽视了对生命自然天性的应然尊重,居高临下地、越俎代庖地强制扭曲和改造个体生命的差异性,违背生命发展的正常轨迹和成长规律。在这里,“率性之谓道”无疑重申了自然天性是教育活动展开的逻辑起点这一朴素的基本观点。换言之,“教育只能根据人的天分和可能性来促使人的发展”[28],要遵循生命发展的自然规律及个性特点,以更加宽容的胸怀不断丰盈、提升生命。后世夸美纽斯、卢梭、裴斯泰洛齐、福禄培尔、杜威等西方教育学家主张的“教育即自然发展”与之相互会通、相互呼应。
2. 自主能动性是教育作用发挥的动力源泉
鲁洁先生曾言:“理想的教育,是要使人从现实性中看到各种发展的可能性,并善于将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29]这种可能性实际上就是夸美纽斯高喊的“种子”,康德眼中的“胚胎”,哲学人类学家所说的“未完成性”“未特定化”。而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何以实现?“《中庸》所憧憬的似乎是一种自我实现的创造性过程,它是由一种自我生成的力量源泉所孕育和推动的”[30],即在自生、自在的活动中点燃生命内在的可能性,进而感通天地之存在化育。《中庸》“自诚明”的“自”亦活灵活现地勾勒出了生命的这种存在论样态。其“率性”的观点:既“不得强为”(《外物注》),又“不得无为”(《外物注》)。即在尊重生命发展基本规律的基础上,只要肯持续付出努力,不轻言放弃,充分激活内在的自主能动性,我们就有机会最大限度地唤醒生命发展的各种可能性,并逐步将这种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也就是说,每个个体生命都具有自发的不断向外发展的内驱力,自然的生命既是上天的赋予,又通过“诚之”来激发生命内驱力而不断进行自我创造和趋向完善,它指向“生生不息”的连续的生命活动,即《中庸》所言的“至诚无息”。
杜维明先生释《中庸》:“实现天人合一理想的可能性是每个人的本性中所固有的。”[30]这种固有的上天赋予的生命禀赋虽不完全相同,或“生知”、或“学知”、或“困知”,或“安行”、或“利行”、或“勉强行”,但勤能补拙,即“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7]。别人一次就能做到的,我宁愿用百倍的努力;别人十次能完成的,我甚至可以花上千倍的努力。如果真能做到这样(《中庸》言:“果能此道矣”[7]),即使再愚笨懦弱的人,通过坚持顽强不懈的艰苦努力,也最终能够取得成功(《中庸》言:“虽愚必明,虽柔必强”[7]),即“及其成功一也”[7]。换言之,不管我们是采取循循善诱的启发方式,还是强制生硬地推行规训与催逼,生命价值的达成、教育意义的实现均需要依赖生命自身的活动。“《中庸》自始至终都未放弃‘率性’意识,它清醒地意识到‘知识—理解’归根结底只能是每一个当事人‘亲自认知—亲自理解’。”[31]这就与《大学》主张的“外在监督—意志持守”意识下的“教—学”形成了鲜明的反差。“生命超出生命”(齐美尔语)、“对于有意识的生命来说,就是要连续不断地进行无尽的自我创造”[32](柏格森语)等西方生命哲学家对生命本质的认识亦表明,能动性、冲动性是生命本身所具有的典型特征。君子实施中庸之道亦是《中庸》生命修道的另一种表达,修道的过程亦是对生命进行教育的过程。因此,教育活动若要充分发挥作用,就必须依赖这些内植于生命内部的“能动”,重视生命的每一次可能性“冲动”,让学习成为个体生命积极主动的自主行为。
3. 自由发展是教育生活不断追求的理想愿景
审思当下周遭的教育活动,目中无人、无视生命自然天性的教育现象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划一的制度、规训的纪律、线性的方式、压迫型的师生关系等无情地侵蚀着生命主观能动性和自由本性,生命的真正实现成为空中楼阁。这与《中庸》之“道”明显背道而驰。在《中庸》看来,“人之生命的自然天性得以无拘无束且真实无遗地展现,也是一种合自然、合规律、合中庸之道的表现”[10]。于是,我们看到《中庸》第二十二章在描绘出“至诚→尽人之性(不息则久)→尽物之性(征则悠远)→赞天地之化育(悠远则博厚,博厚则高明)→与天地参矣”(不见而章,不动而变,无为而成)的生命发展愿景的同时,也传递了其高远旷达的立意:让生命自由成长和全面绽放!而这无疑也是《中庸》“率性”之教的理想诉求。具体来说,就是要尽可能地摆脱无所不在的枷锁,避免对个体生命的各种无理规训,保护其自由天性,让其自由地接受大自然的阳光雨露。《中庸》不只停留于此,还用“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7]深入回答了何以实现的问题。无论是内发型的“诚明”教育模式,还是外铄型的“明诚”教育模式,作为生命内在本性的自由都是重要的前提条件之一。“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7]换言之,生命就是要充分激活主观能动性,让自然本性率真自由展现。自由“乃是人性的产物”[33],是人之本性。只有充分享有自由,生命才有可能处于最大限度的激活状态,内在潜能才有可能得以最大限度地兴发,最终实现“成己”“成物”“尽性”“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矣”“不见而章,不动而变,无为而成”的生命自由之境。按西方人本主义教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话来说,“教育,是人对人的主体性的灵肉交流活动……使他们自由地生成,并启迪其自由天性”[28]。
注 释:
① 如陈赞在其《天下或天地之间:中国思想的古典视域》中就认为,《中庸》直接指向了中国思想触摸实体的独特方式,以一种令人惊讶的方式抵达了中国思想的核心。而法国汉学家弗朗索瓦·于连(Francois Jullien)也指出,《中庸》用很少的篇幅就让读者进入中国思想的核心。
② 关于“率性”,很多学者从不同维度提出了不同的观点,看法不一。比如,宋代理学大师朱熹认为,人与物皆可率性。现代著名学者徐复观先生与钱穆先生在20世纪50年代香港《民主评论》杂志社还围绕这个话题展开了深入的学术探讨。徐复观先生认为,“天命”仅与人有关;钱穆先生指出,“性”兼指人性与物性,等等。
③ 如《中庸》谈到:“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其为物不贰,则其生物不测”“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君子之道,辟如行远必自迩,辟如登高必自卑”等等。
④ 《中庸》言:“其次致曲,曲能有诚。”“致”,即用力加以推广。关于“曲”,郑玄注解为:“犹小小之事。”朱熹言:“一偏也。”所谓“致曲”,意思是说实现化育万物的最终目标需要先从具体细小的局部事情着手。
⑤ 正所谓:“自诚明,谓之性”,主张依靠主体自我的内在力量去明白道理,率性而为,遵道而行,实现“明达性天”之目的。
⑥ 在西方,亚里士多德率先在其经典著作《形而上学》中提到,人本自由,为自己的生存而生存,不为别人的生存而生存。后来的法国自然主义教育家卢梭也提出人生而自由的命题。他认为自由是人性的产物。
⑦ 《中庸》第二十六章言:“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其为物不贰,则其生物不测。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
⑧ 如于伟在《“率性教育”:建构与探索》(《教育研究》,2017年第5期)中便提出,西周之节性、孔子之习性、子思之率性、孟子之养性、告子之生性、庄子之返性、荀子之化性等均是论证“人何以受教”的思想原点和无法回避的逻辑前提,并由此文化养分中滋生出不同的教育学说。
⑨ “出自造物主之手的东西,都是好的,而一到了人的手里,就全变坏了。他要强使一种土地滋生另一种土地上的东西,强使一种树木结出另一种树木的果实……他不愿意事物天然的那个样子,甚至对人也是如此,必须把人像练马场的马那样加以训练;必须把人像花园中的树木那样,照他喜爱的样子弄得歪歪扭扭。”
⑩ “中节”即是和,和者和谐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