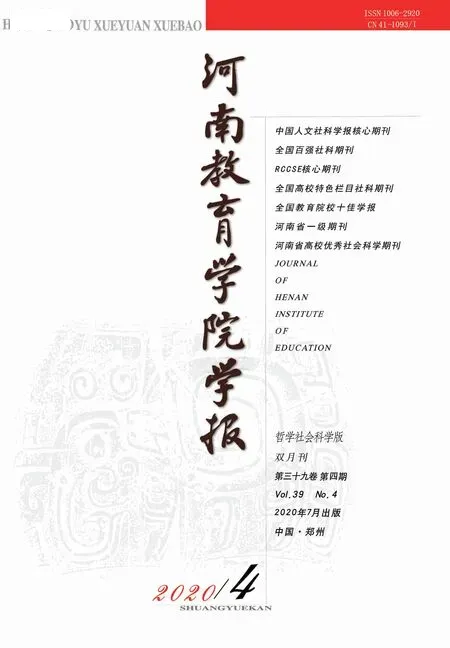论儿童绘本的图像教育特征
2020-01-19韦慧伊
韦慧伊
图像是人类认识和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从原始岩画、汉画像石、敦煌壁画、版刻艺术、小说插图、儿童连环画,到电视、电影、网络、广告牌、商品包装,各种各样的图像吸引着我们的眼球。人类正处于图像时代。这个时代不仅改变了人们看世界的方式,也在教育领域开启了图像教育的新路径。儿童绘本作为图像教育的实践范式,是指以儿童认知心理学为基础,通过系列连贯性的图像和较少的文字(甚至没有文字)叙述,共同演绎一个完整故事情节的童书。儿童绘本起源于欧洲的“图画书”,日本将其命名为“绘本”,20世纪90年代经我国台湾地区传入大陆地区,随即引起全社会的高度重视。本文以图像学为研究视角,通过对儿童绘本的图像思维本质、图像叙事艺术、图像教育价值的探索,尝试深入揭示绘本的图像教育特征。
一、儿童绘本的图像思维特征
儿童是一个特殊的群体,是一群完整、独立、有思想的人。对儿童绘本进行学理考察,必须以儿童心理学知识为基础,深入探究儿童思维的奥秘。瑞士儿童心理学家皮亚杰将儿童认知发展分为四个阶段:感觉运动阶段(0~2岁)、前运算阶段(2~7岁)、具体运算阶段(7~11、12岁)、形式运算阶段(11、12~13、14岁)。这一理论科学揭示了儿童认知的特点和规律,深刻指出儿童心理发展是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由感性到理性的渐变过程,儿童主要以图像思维方式认知世界。2017年,华东师范大学周兢教授团队利用眼动仪追踪记录了115名3~6岁儿童自主阅读图画书过程中的眼动情况。分析结果显示:“在限定的阅读时间里,儿童大部分时间都在注视图画形象区域,且随年龄增长儿童在图画形象上的注视时间和次数比例显著增加;随面积等级由小到大、语义表征难度由高到低,儿童首次注视图画形象的时间由晚到早,在图画形象上的注视时间由短到长、注视次数由少到多;儿童在图画形象上的回视次数随年龄增长而显著增加,5岁后逐渐在具有语法关系的图画形象之间产生更多回视。”[1]可见,图像是儿童绘本阅读的重心,丰富多彩的图像吸引了儿童的注意力,即便是重复阅读,儿童关注的依然是图像的细节。这与儿童思维发展图式密切吻合。
概括起来,儿童绘本的图像思维特征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一是直观性,即对事物的直接观察、瞬间把握和整体生成。与《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古代蒙童读物单纯的背诵记忆相比,现代可视可感的绘本图像更能吸引儿童的注意力。鲜艳明亮的色彩、夸张变形的线条、优美流畅的整体设计尤能激发儿童强烈直观的感受。例如,绘本《玛德琳》中,主角玛德琳的头发被设计成火红色,在统一着装的幼儿园小朋友中显得特别醒目。绘本《春节》《过年啦》等,选择“中国红”做基调,突出了民族特色和吉祥喜庆的氛围。绘本《臭臭的比尔》中,那只名叫比尔的狗狗,喜欢在垃圾堆、烂泥地里打滚玩耍,却不愿意洗澡、不讲究卫生。作者设计封面时别出心裁,小狗比尔毛发卷曲、肮脏不堪,手绘的标题字体像小狗一样长着茸毛,画面上苍蝇乱飞、嗡嗡作响,似乎让人闻到了臭烘烘的味道。作者运用通感的手法,打通了视觉、嗅觉、听觉等多种感觉,以诸多意象构造出如同在场的直观感受。[2]
二是形象性,即以生动具体的形象为主体感官所感知。鲁迅先生曾在《阿长与山海经》一文中回忆,儿时印象最深刻的书是图绘《山海经》,那“九头的蛇,三脚的鸟,生着翅膀的人,没有头而以两乳当作眼睛的怪物”深深地吸引了自己,并留下了终生难忘的美妙记忆。[3]18在儿童的情感世界里,大自然的一切都是新鲜的、新奇的,活泼可爱的小动物激发了他们强烈的好感。绘本《小白兔》《喜羊羊与灰太狼》《我是彩虹鱼》《三只小猪盖房子》《三只捣蛋猫》《十二生肖的故事》中,小兔子、小猫、小羊、小猪等友善可爱的小动物,直接拉近了儿童的心理距离。绘本《快活的狮子》《老虎拔牙》《老鼠嫁女》《好饿的小蛇》《好饿的毛毛虫》中,狮子、老虎、老鼠、小蛇、毛毛虫等动物也褪去了原本可憎恐怖的面目,增添了让人忍俊不禁的喜剧色彩。再比如,绘本《圣诞老爸》把圣诞老人设计成滚圆肥胖的形象,作者还通过压缩身高比例来使其身体更接近孩子。红衣服、白胡子的装扮对比也十分明显,让人感觉可敬可亲又可爱,具有意象表达的所谓“切身性”。[4]
三是单线性,即时间连贯,情节单一,因果效应明显。儿童的认知思维相对简单,复杂逻辑思维尚未形成,倒叙、插叙、多线并置、交叉叙事等不适合儿童绘本,故而采取单线性的“原因-结果”叙事模式较为理想。系列类的绘本,尽管围绕同一个主题,主要人物也不发生变化,但一个篇章往往只设置一个故事情节。例如,《可爱的鼠小弟》系列绘本中的《鼠小弟的小背心》篇,讲述的是鼠妈妈给鼠小弟做了一件新背心,鼠小弟的动物朋友们羡慕不已、纷纷试穿的故事。可是,背心被越撑越大,几乎变得不成样子,鼠小弟伤心极了。故事最后出现了情节反转,鼠小弟以大象朋友为支架,以变形的背心为绳索,开心地荡起了秋千。文本叙事简洁,风趣幽默,浅显易懂。需要注意的是,有绘本作者尝试打破单线叙事模式,但实践证明,复杂叙事绘本很难获得成功。毕竟,绘本设计必须与幼儿接受心理和思辨能力相符合。[5]
二、儿童绘本的图像叙事艺术
儿童绘本必须坚持“幼者本位”原则,把关注儿童、理解儿童、尊重儿童、服务儿童作为创作之本,把能否恪守图像叙事本位、展现儿童日常生活、关注儿童所思所想、传达儿童喜怒哀乐作为评判绘本好坏的基本标准。那么,好绘本是如何成功进行图像叙事的呢?这是一个“表意”和“释意”的过程,“首先由传播者对信息源进行编码加工,形成信息编码(图形),通过媒介发送、传播,然后由受传者解释编码,产生信息”,并获得阅读快感。[6]
一是图像和文字共同完成故事叙事。儿童绘本是以图像为主的艺术,图像在故事讲述中占据主导地位,文字则处于相对从属地位。市面上也有一些针对0~2岁婴儿设计的有图无文绘本,这类绘本故事情节更加简单,以培育婴儿图像感知力为主要目的。本文关注的重点是图文结合绘本,这类绘本图像和文字相互补充、相互配合,演绎生成新的意义。就图像来说,背景交代、因果不明的地方,需要文字来补充。就文字来说,空间布局、色彩线条等不易表现的地方,需要用图像来补充。图像和文字的关系,犹如鱼和水的关系,水乳交融、须臾不分。理想的阅读效果不是“1+1=2”而是“1+1>2”,图像和文字相互避让,保持一定的张力,读者通过想象完成意义建构。例如,德国绘本《快活的狮子》描述的是狮子来到镇上,人们惊恐万分、四处逃窜的场景。图像以夸张、变形的手法,生动形象地再现了人们惊惧的表情举止,非文字表述所能企及。第11页、12页,画面仅呈现了在食品杂货店附近潘松太太把买来的蔬菜扔在狮子脸上的画面。配套的文字却叙道:“你好啊,太太!”一边是快活的狮子又鞠躬又打招呼,一边是潘松太太的高声尖叫。狮子打了个喷嚏,心想“我发现这城里的人真有点儿可笑了”。文字在这里补充了画面的不足,把狮子的快活和人类的惊惧之间的张力,恰到好处地表现了出来。再如绘本《小黄和小蓝》,以黄色块和蓝色块为主角,黄蓝融合为绿色块,故事相对比较抽象。儿童若没有相应的色彩变化背景知识,很可能遭遇阅读障碍。面对这种情况,配套的文字叙述就显得格外重要了。黄蓝色块融合变化为绿色块的过程,使图像呈现更直观明晰,图文合谋完成了故事叙述。
二是通过前后画面符号的串联记忆完成故事叙事。绘本中的图画既是静止的,又是流动的。所谓静止,是要求每页画面构图完整、画面精美、形象突出,画出最富于孕育性的顷刻,富有一种阐释的美感。所谓流动,是指每页画面中的图像符号通过某种内在逻辑紧密勾连,使读者阅读时很容易感知各个符号并通过想象串联起来,以此在脑海中完成故事叙事。因此,是否能够关注每页画面的关键图像符号,是否能够把握该符号在不同画面中的运动轨迹,是否能够实现图像信息从文本到读者的传递,是绘本阅读的关键所在。竹内雄寒《图画书的表现》归纳了连接前后图像的四种符号:类似“事物”的照应、类似“色彩”的照应、类似“事件”的照应、类似“情绪”的照应。读者阅读绘本时,只要能感受到上述符号在不同页面中的动态呈现,就意味着信息已经被读者把握并开始传递了,自然也就实现了前后续接的故事讲述。绘本《好饿的毛毛虫》讲述毛毛虫一周内从虫卵孵化,到又瘦又饿的毛毛虫,到胖嘟嘟的大毛虫,再到破茧成蝶的过程。每个图画页面中都有毛毛虫,毛毛虫牢牢占据了图像叙事的中心,同时配有毛毛虫吃的食物。第一天,一个苹果;第二天,两个梨子;第三天,三个李子;第四天,四个草莓;第五天,五个橘子;第六天,巧克力蛋糕、冰淇淋蛋筒、酸黄瓜、瑞士奶酪、萨拉米香肠、棒棒糖、樱桃馅饼、红肠、杯形蛋糕、甜西瓜。读者能够强烈地感受到,主角毛毛虫不仅在吃东西,而且食量越来越大。不同食物的递次出现,让读者意识到空间场景转换了。毛毛虫长得越来越大,让读者意识到时间不停地往前推移。通过主角毛毛虫、配角各种食物等符号的迁移变化,绘本成功实现了信息传递并完成了线性叙事,在读者心里建构起完整的故事图式,具有一种内在的“对话性”。
三是在图画中设置相应的暗线串联起故事叙事。儿童绘本的图像叙事,除主要图像符号的连续性呈现外,一些绘本还设置了细节性的点状线索,以暗线形式配合主线叙事、串联故事情节。例如,绘本《嚓—嘭!》讲述的是一只小鸟寻找自我价值的故事。封面上,三只小老鼠仰天而望,目光注视着一只小鸟,似乎想说什么。此后,在第4页右下角、第5页右上角、第11页、第12页均出现了小老鼠的身影。尽管绘本没有关于小老鼠和小鸟的对话,也没有相关的情节介绍,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小老鼠和小鸟是好朋友,它们形影不离、默默扶持,彼此分享着各自的喜怒哀乐。小老鼠作为暗线存在,一方面增强了画面的趣味性和吸引力,另一方面增强了故事的连贯性和整体性。
三、儿童绘本的图像教育价值
尽管中国儿童绘本教育起步较晚,但在儿童教育工作者、出版商、绘本阅读馆、绘本网络推广平台的共同努力下,近年来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2015年,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婴儿画报》《幼儿画报》《嘟嘟熊画报》等阶梯阅读平台,对全国0~9岁幼儿家庭绘本阅读情况进行了调查分析。结果显示:关于儿童年龄分布方面,0~3岁占比29%,4~6岁占比61%,7岁以上占比10%;关于绘本阅读在家庭阅读中的占比方面,70%的家庭绘本占所有读物一半以上,只有14%的家庭绘本阅读在1/4以下。[7]绘本教育的价值日益受到重视,绘本在幼儿家庭阅读中的地位可见一斑。
一是有利于启迪儿童的认知把握能力。儿童是以感性直觉的方式来认知世界的,在儿童眼里,他看到了什么世界就是什么,他看到的世界什么样世界就是什么样。儿童绘本题材广泛,涉及自然社会、天文历法、科学技术、风土人情等各个方面,是儿童感知世界、了解世界、认识世界的一扇窗户。比如,绘本“奇妙的身体”系列,通过牙齿爱逃学、了不起的小脚丫、捉住声音、嘿鼻涕虫、指甲尖尖、头发不见了、手指好兄弟、会笑的眼睛、小脑瓜真聪明等故事,帮助儿童认识身体器官带来的视觉、听觉、味觉、嗅觉等感受。绘本“大自然的奥秘”系列,通过讲述奇妙的昆虫、神奇的植物、小水滴历险记、风是怎样形成的、石头的故事等,引导儿童了解大自然的千变万化、神奇奥妙,有助于培养他们亲近自然、拥抱自然的美好情感。有了欣赏绘本的体验,当儿童在现实中遇到类似的事物时,情感可能一下子就被调动起来,从而增强他们认识和把握事物的能力。
二是有利于激发儿童的审美想象能力。儿童的内心尚未受到外界环境干扰,是未泯之童心,是赤子之心,犹如一张可以在上面随意作画的白纸,具有了丰富的想象力和无限的可能性。儿童的思维不受时空限制,可以天马行空地想象,可以驰骋纵横地遨游,在他们眼中万事万物皆是有灵动的生命。方卫平说:“儿童读者之所以能够再建文本,不仅是由于儿童已经具有并不断发展着的文本感知能力,而且还由于他们能够根据文本所提供的已知的图式或框架来破译、填补、丰富、完成那些空白和未定点。”[8]例如,绘本《艺术大魔法》通过画家达文蜥和想成为画家的小蜥蜴米开关于艺术极限的对话,告诉孩子们要放飞想象、不受拘囿、敢于尝试。因为,人人都是天才,艺术创意无处不在,任何尝试都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
三是有利于提升儿童的情感体验能力。阅读绘本是一个审美体验的过程,儿童心理处于未定型时期,绘本阅读能帮助他们净化情感、陶冶情操、提升境界,推动心理趋向平和、行为趋向真善美,展现出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9]例如,绘本《猜猜我有多爱你》《逃家小兔》能帮助儿童理解母爱的伟大,体验亲情的温暖。绘本《菲菲生气了》能帮助儿童正确认识情绪,学会宣泄愤怒和悲伤,并进一步控制自己的情绪。绘本《大脚丫跳芭蕾》通过大脚丫学跳芭蕾的励志故事,帮助儿童树立坚定信念,培养坚持不懈、永不言弃的优秀品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认为,童年体验会对人的一生行为产生重要影响。绘本阅读能够帮助儿童“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从一开始就培育形成健全的人格,为正确面对未来生活中的喜怒哀乐做好准备。这样,即使遭遇困难和挫折,他们也能很快地调适自我情绪,而不至于无法应对甚至走极端。
四是有利于增强儿童的实践创新能力。模仿是儿童的天性,优秀绘本一定是儿童的行动指南,一定会在儿童日常生活中留下浓重的痕迹,一定会在儿童习惯形成上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例如,绘本《小泥人》《大纸箱》讲述的是手工制作的故事,对处于涂鸦阶段的幼儿非常具有吸引力。家长陪同儿童阅读完绘本后,可以鼓励孩子复述故事情节;幼儿园老师引导幼儿集体阅读完绘本后,可以围绕同一主题举办讲故事比赛,全面提升儿童的语言表达能力。现实中,我们常常惊奇地发现,一些孩子不是纯粹照搬原文,而是能够添枝加叶地丰富故事情节;一些孩子能够将不同故事嫁接起来,熔铸出新的故事;一些孩子模仿绘本人物的言谈举止,养成了良好的吃饭、睡觉、学习习惯。家长和教师还可以鼓励儿童自己创作绘本,按步骤完成创意、构图、绘制、涂色、编排、装订等各项工作,切实提升其实践操作能力。
总之,绘本是符合儿童认知科学规律的童书,是振兴儿童教育事业的希望所在。当前,尽管我国原创儿童绘本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与日本以及欧美国家相比,还存在民族特色不够鲜明、构思创意不够巧妙、整体制作不够精良、推广机制不够健全等问题。因此,我们要进一步发展壮大儿童绘本事业,充分认识绘本的图像教育特征,积极发挥绘本的图像教育功能,努力探索一条符合儿童教育规律的新的教育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