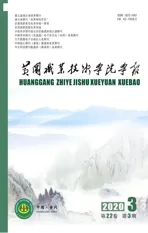“抚视三书,即觉此生不虚过”
——苏东坡“功业”内涵新探
2020-01-18郭杏芳
郭杏芳
(黄冈职业技术学院 学报编辑部,湖北 黄冈 438002)
近千年来苏东坡都不缺少热爱者和研究者,他的生平经历、文学成就和人品精神都被广泛地大量地挖掘和研究。苏东坡的成就如蕴含深厚的矿藏,如他《赤壁赋》中所写的“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很多人可能会有同感:对苏东坡无论从哪一个方面做出评价,都难以尽言;对东坡的成就和为人,无论做出何等高大的评价都不为过。但是苏东坡自己对其一生却只有十二字总结:“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他所指为何,却让人不得而知,或知之不全,或知而不确切。
苏东坡21岁中进士,26岁通过制科考试走上仕途,到65岁大赦从海南回到内地,病逝于常州。一生从政和被贬40年,其中被贬三州加起来也就10年时间,为什么回顾自己一生时,苏东坡认为功业只在三州。到底什么才是东坡先生最看重的功业呢?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对苏东坡所言的三州功业或其中一州的功业,已有不少人作过探究,大多也都是概述其三州的所有成就。笔者认为苏东坡所指的三州功业应该有特殊的内涵,是他特别在意的在三州完成的东西,主要应该是他始于黄州、完成于儋州的《易传》《书传》《论语说》三部经传著作。
给经书作注,是古代知识分子在学术上安身立命的要务。苏东坡在文学、艺术方面的成就,足以光耀后世,但他明确表达自己的观点:“抚视《易》《书》《论语》三书,即觉此生不虚过。如来书所谕,其他何足道!”[1]可见在东坡心目中文学作品并无太重位置,甚至是不足道的;著书立说才是正道,才可以称为“功业”。
一、从苏东坡的思想内核来审视,儒家思想是其根本
北宋时期儒释道三教融合,思想开放,知识分子虽然主要接受儒家的思想文化教育,但大多又接受了道家和佛教思想,苏东坡也不例外。作为科举考试进入仕途的文人官员,对三教也可能有偏颇,但其思想内核大多还是儒家的。苏东坡也是这样,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思想是他为官和处世的指南。如果说“兼济天下”是儒家的入世思想,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指导;“独善其身”则是退守之方,其思想武器主要就是道家和佛家的无为和忍受。其实儒家是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修身”放在首位,至于用什么手段并没有限制。“吾日三省吾身”可以,借助道家和佛家的手段修炼也未偿不可。
苏东坡从小的家教和学校教育都是儒家的,思想形成的内核自小就打下了基础。即使在被贬谪期间,他主要以道家和佛家的思想来修养自己的身心,但内心深处仍忘不了儒家。他在海南写的《过黎君郊居》诗:“万事思量都是错,不如还叩仲尼居。”此诗题中的“黎君”指东坡在儋州结交的朋友黎子云,“仲尼居”也是指黎家。网上查阅到“天涯社区”名为longmenlang的作者这样介绍了黎子云及其与东坡的关系:
黎子云,世居城东。《儋州志》述,子云“有欲僻举者,固辞,优游田里,率乡人子弟以孝悌忠信,人多化之。寿八十余”。又有注云:“黎人向化,符姓为始,亦符姓为多,而符姓之后又有改称黎姓者,黎子云辈是也。”由此知黎子云为黎民贤士无疑。东坡有诗《被酒独行,遍至子云、威、徽、先觉四黎之舍》;葛立方诗句:“四黎善善君子类”,则知黎子云等四人皆为淡泊乐善者。
绍圣四年十一月,东坡抵儋不久,便与州官张中同访黎家,有诗云:“城东两黎子,室迩人自远,呼我钓其池,人鱼两忘返。”为方便东坡讲学和聚客之便,黎子云不顾家境贫寒,与众友生提出为东坡“醵钱作屋”;东坡感其盛意,欣然同意,取《汉书·扬雄传》中“载酒肴从游学”典故命此屋为“载酒堂”。
此后,东坡与子云往来频繁,无拘无滞。有出访诗云:“半醒半醉问诸黎,竹刺藤梢步步迷。但寻牛矢觅归路,家在牛栏西复西。”“总角黎家三四童,口吹葱叶送迎翁。莫作天涯万里意,溪边自有舞雩风。”苏轼还明确表示愿与黎氏兄弟为邻:“借我三亩地,结茅为子邻。”
上述文字既介绍了黎子云为何许人,又说明了东坡与他不一般的关系。正因为黎子云是当地的贤达又是儒者,苏东坡才将黎宅比作“仲尼居”;当他感到困惑时,想到的还是追随仲尼的儒者。尽管“载酒堂”的建造有与上文完全不同的说法,有说是东坡提议为黎子云建造,而子云不独享,拿来做东坡讲学聚会的地方。不管是谁提议建造的,对苏东坡与黎子云的关系,及东坡自己的思想核心都没有影响。儒家思想既是东坡出世为官的指导,也是解决他思想困境的钥匙。
明代琼山进士唐胄在《重修儋州儒学记》中说:“琼之有士始乎儋,琼之有士莫盛乎儋。”《琼台纪事录》中评价道:“宋苏文公之谪儋耳,讲学时道,教化日兴,琼州人文之盛,实自公启之。”可见,苏东坡为海南的文教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教育的根本仍是儒学。
方星移教授的论文《论安国寺对苏轼的精神引领——兼论苏轼对佛道的态度》摘要:
苏轼在黄州期间的很多活动都与安国寺密切相关,游处于安国寺,他享受净垢安心、隐退闲居之乐。同时,他常瞻仰“韩魏公祠”,深受韩琦等名臣的家国情怀的鼓舞,他有着坚定的儒家思想,故他在黄州的思想是立足于儒,兼取佛道。而他对佛道采取通达的态度,希望做到“静而达”,为求实用与超脱,有明确的取我所需的目的性。
笔者很赞同方教授的观点:“他(苏东坡)有着坚定的儒家思想,故他在黄州的思想是立足于儒,兼取佛道”。在黄州苏东坡为了调适自己的心态,形式上更多借助道家的闭关修炼和佛家的潜心修养,内心却一直在关注国家和社会的前途和命运。他在《与李公择书》所言:“吾侪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直须谈笑于死生之际。”在《与腾达道书》中说:“虽废弃,未忘为国家虑也。” 由此可见,儒家的入世思想还是苏东坡的精神内核,一有适当的机会或朝廷有召唤,他便会全力以赴。
在黄州,苏东坡除修炼、创作、郊游、交友、耕种外,他自己说“惟以书史为乐”。他主要读什么书、治什么学术呢?手抄《汉书》《金刚经》,还有“寂寞闲窗《易》粗通”。苏东坡在与友人的书信中说:“到黄州,无所用心,辄复覃思于《易》《论语》,端居深念,若有所得”。实际上他已经“了得《易传》九卷,《论语说》五卷”,而且还“下手作《书传》”。
在儋州苏东坡完成了注解儒家经典的《易传》《书传》《论语说》三部著作。中国苏轼研究会理事、海南省诗词学会名誉会长林冠群先生提出,这些著作的核心,实际上也是深刻阐述儒家以人为本的观念。《易》《书》《论语》本身就是儒家的经典著作,苏东坡为之作传,足可见其思想倾向了。其实,儒家学子最想传扬的还是儒家经典,崇佛道只是解人生困厄的权宜之计。因此,为儒家经典作传文,也极受东坡重视,被其视为一生的主要功业也是讲得通的。
二、对东坡“三州功业”的不同解读
苏东坡于北宋神宗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底,因“乌台诗案”被贬谪至黄州。四年后量移汝州,很快又回到京城,担任了平生最高的官职翰林学士知制诰,成为皇帝身边起草文书的近臣。但好景不长,不久自请外任。因朝中派别争斗,元祐党人遭秧,1093年苏东坡被贬惠州,1097年再贬至海南儋州。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正月,哲宗崩逝,徽宗即位,大赦天下。五月,苏东坡被赦免了流放海外之罪,并被提举为成都玉局观。建中靖国元年、公元1101年3月,苏东坡从海南北归,由虔州出发,经南昌、当涂、金陵,五月抵达真州(今江苏仪征),六月经润州拟到常州居住,未料卧病,最终未能走出常州,七月二十八日,在常州逝世。
苏东坡在真州游金山龙游寺时看到了李公麟十年前为自己画的像,便《自题金山画像》:“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对此诗的理解自宋以来,见仁见智,各有评说。有人对此诗笼统解释说:“《自题金山画像》以自嘲的口吻,抒写平生到处漂泊,功业只是连续遭贬。诗人面对当年自己的画像,抚今追昔,感慨万千,既有对目前垂垂老矣的描述,也有对自己一生的总结,多重感情交织在一起。造语苍凉,寓庄于谐,言有尽而意无穷。”[2]岳希仁《宋诗绝句精华》:“这是诗人生命最后阶段的作品,精炼地概括了他一生的悲惨境遇。一代文豪,英才天纵。回首往事,唯存贬谪。其遭际之坎坷遂成千古伤心事。”[3]
上面的观点都认为诗意是自嘲与感伤的。也有认为此诗是东坡自嘲也是自我肯定,贬谪在这三州期间是他政治上最为失败,生活上遭受苦难最多的时期,却也是他文学创作的高峰时期,更是他人生精神升华到极致、对人生意义哲思体会最为深刻的时期。正是因为这个时期才成全了苏东坡,成全了一种伟大的人格,一种进退自如、超然人生的文人士大夫的最高精神境界。
有关东坡“三州功业”的研究文章不是很多,主要有:江苏科技大学学报编辑部喻世华教授的《自嘲与自豪——从〈自题金山画像〉看苏轼的“功业”》[4],海南海洋大学人文学院李景新教授的《苏东坡的海南功业之综论》[5],黄冈市东坡文化研究学会副会长谈祖应教授的《论苏东坡的黄州“功业”》[6]等。另外,写到苏东坡对“平生功业”总结的有,兰州大学文学院庆振轩的《问汝平生功业,黄冈惠州儋州——苏轼被贬谪辞、谢表探论》[7]。老干部网上有一篇《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从三地作品中看苏轼旷达的历变》(李海瑞,《开封教育学院学报》2010年),从标题就可以看出,作者要论述的内容是“苏轼的旷达历变”,而不是“功业”所指。还有一篇《回首平生事 得失我自知——苏轼《自题金山画像》赏析》的文章,作者陈璐也认为:“这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奇才苏轼对自己的人生总结和评价。”“人往往经历过挫折,才能对是非名利等外物以及自身的真正追求有更透彻的认识,相信苏轼经历了这么多风浪和困苦,已经达到了圆融的心境。努力实现政治理想,留下千古名篇,在磨难中得到修炼和成长,这或许就是苏轼把他平生功业归于三处失意之地的原因吧。”对东坡“三州功业”的这种解释,也是笼而统之的,好像也不够确切。
研究苏东坡“功业”并撰写论文的,就笔者所知,主要就是喻世华、谈祖应、李景新三位教授,看看他们所持的观点吧。
(一)一生的总结:自嘲、自豪与超然
喻世华教授在《自嘲与自豪——从〈自题金山画像〉看苏轼的“功业”》一文中的观点,应该很有代表性,不少论者都持这些看法。他说苏东坡这首《自题金山画像》,“平静的叙述中蕴含着对一生波澜壮阔的生命历程的回顾, 有感伤, 有矛盾, 有自嘲, 有更多了然与超脱。短短 28 字, 可以看成苏轼一生的真实写照。黄州、惠州、儋州是苏轼人生的三个重要驿站, 记录了苏轼生活的得失、事业的成败, 展现了诗人高尚与圣洁的情怀”。这个只是概述,没有具体的内容,他还有一段论述:
中国古代士大夫追求“人生三不朽”:“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当仕途遭受挫折,“立功”之路被堵死之后,苏轼将其才华转向文学创作领域,取得了举世公认的辉煌成就,达到了“立言”的目的。因此,从宦海浮沉角度说,贬谪到黄州、惠州、儋州,无疑是苏轼事业上企图“致君尧舜”的失败;但如果从文学成就说,苏轼的文学事业正是在黄州、惠州、儋州的流放中取得了空前绝后的成就。从这个角度说,苏轼无疑是成功的。
喻教授这段文字论述了苏东坡的“功业”内涵是指“立言”,与我国古代士大夫所追求的一致,这个观点笔者也赞同,但喻教授把东坡的“立言”看成是三州所取得的巨大文学成就,笔者不全认同。
喻教授的文章有个结尾:
《自题金山画像》的确可以看成苏轼最好的人生总结。苏轼在黄州、惠州、儋州的生活,由于物质层面、事功层面与精神层面存在巨大反差,“平生功业”究竟是自伤、自嘲, 还是自诩、自豪,容许也必然存在多种理解和解读。笔者认为,将它看成一份全面的人生总结更为合适,它展示了苏轼一生的生活、事业、情怀: 笑对生活磨难的顽强生存意志, 旷达的生活态度,艺术化、审美化的生活方式,文学事业上的辉煌成就, 博大的人生情怀。这些为黄州、惠州、儋州的“功业”书写了华美的篇章, 彰显了一个大写的人的尊严、追求与人生。
这里所强调的还是东坡一生的自我总结,“自嘲”还是“自豪”允许有多种理解和解读。在三州苏东坡的生命个体有最真实的体验,是其创作和人生况味最丰富的地方。至于苏东坡所指的“功业”到底是什么,不同的研究者有不同的观点,正如“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千个读者也会有一千个苏东坡。因此,苏东坡所说的“功业”,后人有各种不同的理解和解释也是学术探讨的范围。所以,笔者仍持保留意见。
(二)黄州功业:哲思构建,自我反省,亲民爱民,创新精神
谈祖应先生在他的《论苏东坡的黄州“功业”》一文中提出,苏东坡为何舍去“历侍五朝,三忝侍读,两入翰林,三除尚书,八典名郡”的功绩不计,而偏把投闲置散,进退维谷的“贬谪三州”之地,作为“平生功业的”的举证?究竟应如何评价苏东坡在黄州的“功业”?谈先生认为苏东坡在黄州的“功业”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其一,初成三传:建构哲学思想体系;其二,书牍三百:自我超越的自省美德;其三,躬耕三载:亲民为民的遗爱风范;其四,赤壁三咏:“反常合道”的创新精神。笔者认为这几个方面概括得很好,既概括了苏东坡在黄州的主要功绩和成就,又有评论者的精炼提升,可以说全面而精到。但这仍然是评价性的,是不是苏东坡自己所说“功业”的内涵,还可以探讨。
儒家对“功业”的解释有“三立”(三不朽)之说,立德、立功、立言,这大概是古人对完美人生的概括或是要求标准,一个人有其中之一项就应该是不枉此生了。但是,立德自己很难做到,也难以评判,在个人来说是无形的精神品质的东西;立功,即建立有助于国家社稷的战功或事功,也不是任何人可以做到的;立言,是无数读书人的理想追求。苏东坡在黄州创作了丰富的文学作品,这算不算是他的“立言”呢?谈先生认为这还不算,苏东坡本人极为看重的《易传》《论语说》《书传》才算是他的“立言”之作。谈先生认为“苏东坡建立在初成于黄州‘三传’基石上的哲学思想,是他走出逆境人生的精神支柱;是他登顶文学高峰的基石;是他人格和文格的依归。故而,我们在评价苏东坡黄州功业时,既要承认他是杰出的一代文豪,更应该肯定他是优秀的思想家和经学大师。以此作为苏东坡在黄州的功业之冠,至当不易,无可置疑”。
如果说只将“三传”作为苏东坡在黄州的功业,似乎是远远不够。苏东坡在黄州的自我修炼和反省,也是尽人皆知的。思想的觉悟,认识的提高,人格的完善,境界的升华,也是人生的重要课题,古代君子孜孜以求。苏东坡在黄州既有往返于安国寺,让自己身心安放平静的修炼,也有思想上的自我反省,自我批判,这些在他与友人的书信中都有记载。尤其是元丰三年(1080年)十二月他在《答李端叔书》中对自己因何获罪,以及时人如何评论他,都作了深刻地剖白。谈先生说这篇书信“可以算作是他自我反省的思想总结,堪称苏东坡的‘忏悔录’”。这种自我反省、自我超越,也是完美人生的楷模。
苏东坡在黄州的生活是以往从未经历过的,他躬耕东坡、与“渔樵杂处”、与老幼相嬉,体恤民情、关心民生的大爱精神;笔耕不辍,“反常合道”的创新精神以及硕果累累的文学成就,无一不可以称其为“功业”。但这些又都是后人的评价,能否可以代表东坡本人心中所指的“功业”呢?笔者还不完全认同,仍持保留意见。
(三)惠州功业:个人成就,文教地位,东坡书院,文化价值
李景新教授的《苏东坡的海南功业综论》,从苏东坡居儋期间的个人成就、在文教事业上的崇高地位、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现代文化建设价值等四个方面论述了苏东坡在海南的功业。尽管文章全面论述了苏东坡在海南期间的功业,但也是从文学艺术创作和学术成就方面评论的,而不是为了探讨苏东坡所说“功业”的真正内涵。
李教授对苏东坡《自题金山画像》的解析也是概述式的。他说:“虽然苏东坡把自己的功业定位在黄州、惠州、儋州,但是事实上诗中的感情是复杂的。他的一生被政治风浪抛来抛去,没有自由,随时有倾覆的危险,而最严重的就是被贬谪到这三地,总计长达十年之久,他的政治生命在这十年中被剥夺,他的政治理想完全破灭。从这个意义上看,此诗的前两句可谓实写。与之相照应,诗的后二句不免包含有一些反讽自嘲的意味。这首诗实际上有浓重的悲剧色彩。”李教授还说:“苏东坡总结一生经历,看到了他在这三个地方的生活必将对三地产生巨大的影响。事实上,他个人的许多文学艺术的创作成就和学术成就也是在这三个地方建立起来的。经过九百多年历史的证明,苏东坡在这三地所做出的历史功绩,确实非常突出,对区域文化的影响力,也比其他地方更加深远。”李教授的这个观点应该是对苏东坡三地功业的一种新解释,过去还没有人提出这样的论述。暂且存论。
从文章标题就可以看出,李教授对苏东坡在儋州的功业也是总结性的、全面的概述。在个人成就中首先强调了苏东坡的学术著术,与谈教授观点一致,认为“苏东坡的主要思想凝聚在《易传》《书传》《论语说》之中,这三部书代表着苏东坡一生在学术方面的最高成就。”尽管有如此高的评价,但在李教授文章中这只占苏东坡在儋州功业的很小一部分。在苏东坡海南功业中,个人成就有“学术著述”“文艺理论”“文学创作”“书法创作”,“三传”只是其四分之一,也没有提出三传就是东坡所说的三州“功业”。
文章第二部分论述了苏东坡在海南文化教育发展史上的崇高地位,第三部分论述了“东坡书院与五公祠:苏东坡留下的宝贵遗产”。首先强调儋州东坡书院和桄榔庵是苏东坡为儋州乃至海南留下的有形宝贵遗产。李教授在他以前论文《李光在海南岛贬谪文化中的贡献和地位》(《琼州大学学报》2006第3期)中就提出:“以载酒堂为依托的东坡书院,并不仅仅是一座古典建筑物的遗存,而是凝聚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成为儋州及海南岛贬谪文化最重要的纪念载体。”第四部分论述了“东坡文化在现代文化建设中的价值”,作者认为最重要的在四点:“民本精神”“创新精神”“独立精神”“旷达精神”(17-20)。
李景新教授不仅全面论述了苏东坡在儋州及海南的“功业”,还提炼发挥,指出其在现代文化建设中的价值,这些也应该是苏东坡在海南成就研究的新观点,但好像还不是苏东坡本人所指的“功业”。
总之,以上对苏东坡三地或某一地功业的几种解读和论述,应该说都很全面也有深度,但笔者不揣简陋,还是想继续作些尝试,谈谈个人的看法,以就教于方家。
三、我国传统知识分子对功业的认定及苏东坡的自我认定
晋国执政者范宣子问鲁国大夫叔孙豹说:“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谓也?”叔孙豹说:“豹闻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唐人孔颖达在《春秋左传正义》中对德、功、言三者分别做了界定:“立德谓创制垂法,博施济众”“立功谓拯厄除难,功济于时”“立言谓言得其要,理足可传”。这些解释言简意赅,古代文人每以“立言”为第一要务,以求自己的思想和主张得以传诸后世。诚如曹丕《典论·论文》中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自传于后。”[8]
我国传统知识分子对功业的认定都以“立言”为主,苏东坡是否也有这样的心结,并没有理由排除。他的文学创作成就斐然,他自己可能不一定当成是他立言的“功业”,起码不全是。盖棺定论是由生者或后人论的,苏辙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中对东坡读书写作的过程和炉火纯青的写作技能都有简要概述,而对东坡作三传的缘由和经过及东坡自己的评价则有更多的陈述。
先君晚岁作《易传》,未完,疾革,命公述其志。公泣受命,卒以成书,然后千载之徽言,焕然可知也。复作《论语说》,时发孔氏之秘。最后居海南,作《书传》,推明上古之绝学,多先儒所未达。既成三书,抚之叹曰:“今世要未能信,后有君子当知我矣。
苏东坡著三传,首先是受父命完成未竟之《易传》,受此启发,又欲作《论语说》和《书传》。
贬谪黄州时期,苏东坡45岁,已在官场做过20年,有了丰富的人生阅历,对《周易》理解和领悟更加透彻;更主要的是“不得签书公事”,使他有充足的闲暇时间,于是便开始撰写《易传》。元丰三年(1080)东坡《次韵乐著作野步》诗中说“废兴古群诗无数,寂寞闲窗《易》粗通”。在给友人滕达道的信中说:“某闲废无所用心,专治经书。一二年间,欲了却《论语》《书》《易》”(《与滕达道六十八首》之二十一),可事实并未如东坡所愿,黄州贬谪期满,他的《易传》还未完稿。元丰五年,他在《黄州上文潞公书》中说:“到黄州,无所用心,辄复覃思于《易》《论语》,端居深念,若有所得,遂因先子之学,作《易传》九卷;又自以意作《论语说》五卷。穷苦多难,寿命不可期,恐此书一旦复沦没不传。意欲写数本留人间,念新以文字得罪,人必以为凶衰不详之书,莫肯收藏;又自非一代伟人,不足托以必传者。莫若献之明公,而《易传》文多,未有力装写,独致《论语说》五卷。公退闲暇,一为读之,就使无取,亦足见其穷不忘道,老而能学也。”可见,苏东坡在黄州用了不少时间和精力于撰写《易传》和《论语说》上,而且十分看重,担心不能传下来。直到晚年被贬到海南,苏东坡还继续对《周易》进行探究,对《东坡易传》进行修订,最终定稿。绍圣四年(1097年)东坡作《夜梦》:“夜梦嬉游童子如,父师检责惊走书。……自视当与丘熟贤?《易》韦三绝丘犹然,如我当以犀革编。”[9]由此更可知东坡对《易传》的重视,唯恐不能完成父命,梦中犹惊觉;又自认不如仲尼,孔子解《周易》尚且“韦编三绝”,东坡说“如我当以犀革编”。东坡既自谦不如孔子,又可见其慎重其事,深入钻研。
苏东坡从承父命著《易传》到自觉著《论语说》和《书传》,整个过程就是他被贬三地的过程,也是他一生思想成熟的过程,可以看成是他一生著述的心血结晶。在儋州完成三传后,东坡又给李端叔写信说:“所喜者,海南了得《易》《书》《论语》数十卷,似有益于骨朽后人耳目也。”(《答李端叔十首》三)元符三年(1100)四月,苏东坡为他的三传作《题所作书易传论语说》的跋文:
孔壁、汲冢竹简科斗,皆漆书也。终于蠹坏。景钟、石鼓益坚,古人为不朽之计亦至矣。然其妙意所以不坠者,特以人传之耳。大哉人乎!《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吾作《易》《书传》《论语说》,亦粗备矣。呜呼!又何以多为!
事实上,苏东坡直到儋州时期,才著述了《书传》,修订完成了《易传》和《论语说》。他对自己这几十年的心血结晶十分看重,北归之时始终带在自己身边。渡海北归时遇到极大困难,苏东坡说:“自海康适合浦,连日大雨,桥梁大坏,水无津涯。……所撰《书》《易》《论语》皆以自随,世未有别本。抚之而叹曰:‘天未丧斯文,吾辈必济!’已而果然”(《记合浦舟行》)真是天未丧斯文,东坡和他的著作安然北归。至常州,东坡一病不起,临终前,他把三书托付给好友钱济明,说:“某前在海外了得《书》《易》《论语》三书,今尽以付子。愿勿以示人,三十年后会有知者”(何薳《春渚纪闻》)。可见,苏东坡确实把三书看成是他“立言”之作了,临终只郑重其事地托付三书,其他作品从未见有如此看待的,正如他所言“其他何足道”。
李公羽先生在《论千年苏学的传承、转化与创新》(下)中说:
在海南完成的三书,提出大量新的哲学观点,是东坡一生心血结晶,是他生命实践的体验与总结,是北宋“蜀学”重要的代表作,代表了他臻于成熟的哲学思想,是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东坡著述和整个苏学体系中占有最重要的位置,是至今尚可考述最早的宋人经学著作之一,也是东西方哲学界、文化界、宗教界等高度评价、极为珍视的世界性学术成果[10]。
只可惜,东坡如此看重的,饱含其思想结晶的著作,近千年来研究者少,研究多的乃是东坡的文学作品和他本人的品性情怀。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舒大刚教授认为:“现在的哲学史家把苏轼完全让给了文学史家去研究,而文学史家又只研究其文学作品,苏轼这些自负不浅的著作无人问津了。”[11]这大概就是东坡三传不被今人重视、被人研究较少的主要原因吧?
值得称道的是,辽宁省图书馆编篡了《东坡易传·东坡书传· 诗经》,2017年1月由中华书局出版。其介绍:本书为“辽宁省图书馆藏陶湘旧藏闵凌刻本集成”系列之一。《东坡易传》是苏轼哲学思想集中完备的体现,也是蜀学的核心著作。苏轼一生惟重三传——《东坡易传》《东坡书传》《论语说》。可以说,离开《东坡易传》,苏轼思想及其诗文词赋无从谈起[12]。
辽宁图书馆的善举或许会引起一些研究者对苏东坡三部儒家经典著作的重视吧,惟愿如此。
注 释:
文中所引苏东坡的诗文书信,大多来源于《东坡志林、仇池笔记》《苏轼文集》和《苏东坡黄州名篇赏析》(饶晓明,方星移,朱靖华,饶学刚 编著,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7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