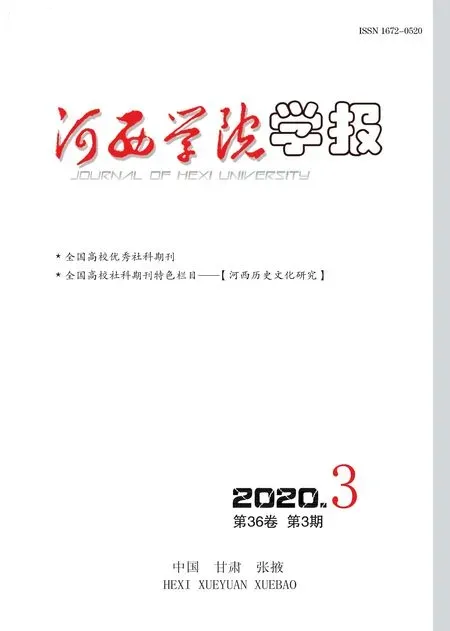一部挑战“成见”的“新编”小说
——评《奄吞秦汉:隋炀大帝》
2020-01-17哈建军
哈建军
(河西学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研究中心,甘肃 张掖 734000)
王守义所著《奄吞秦汉:隋炀大帝》初版于2016年,以上、中、下三部的长篇叙事,给读者塑造了一个励精图治的封建帝王形象,这也是隋炀帝杨广在史传类作品中的新形象。
一、作者要承受诸多挑战
《奄吞秦汉:隋炀大帝》是一部知难而上、承受挑战的文学作品。围绕真实的历史人物进行创作,既要运用必要的虚构,又须遵循“非虚构创作”的客观性和真实性要求,得一个“好”字还真不容易。
《奄吞秦汉:隋炀大帝》不走寻常路,特意为千年来“背负恶名”的隋炀帝杨广“翻案”“正位”,属于重新评定历史人物、重新塑像的史传小说。因为,自唐以降,官方和民间在各类记述中对隋炀帝这个帝王的评价都不是很高,文献中的隋炀帝给大家的印象总是与横征暴敛、骄奢淫逸联系在一起。作者王守义也不无自信地说:“小说完全脱开以往表现帝王故事的窠臼,以恢宏的气势、严谨的构思谋篇成章,在矛盾纠葛中展现人物性格,进行形象塑造。以极富传奇色彩的大故事来正面叙述大帝王打造历史伟业的英勇悲壮,是史家和史诗的笔触,扫除迷雾,再现一个‘奄吞秦汉’而沉冤千载的历史雄杰。”[1]11“新编”故事会面临很多挑战,王守义给一个被人诟病的帝王人物重新造像,一定程度上说,是想纠正人们对这个帝王人物的一贯看法,也就等于要改变人们对那段帝王历史的传统认识。这种纠正和改变的刻意,会在激起当下读者反思历史的同时,附带上对千年来民众认知接受的批判,并且散发着政治隐喻的气息。扭转隋炀帝形象,无疑要重述隋炀帝时代政治集团的政绩功过,也就等于反转后世统治阶层对隋炀帝的印象和评价。作者如此“新编”隋炀帝形象,可能会出力不讨好,这是《奄吞秦汉:隋炀大帝》在主题定位方面就要面对的第一大挑战。
站在《奄吞秦汉:隋炀大帝》叙事立场来看,隋炀帝杨广一生做了很多事情是值得肯定的,譬如主政开凿京杭大运河、联通西域在张掖召开“万国交易会”、科考举才、巡游迁都、厘定雅乐等,至少今天的读者看客可以认同。《奄吞秦汉:隋炀大帝》便是围绕着隋炀帝这几件大事来书写的。
但是,《奄吞秦汉:隋炀大帝》是文学作品,属于对1400多年前帝王的想象性书写,一定离不开必要的虚构,需要靠虚构来填补1400多年前的很多生活细节,如此才能使得“历史雄杰”的故事具有完整性和连贯性。虚构得好,才能使作品精彩而感人,才能令读者信服,因为读者信服的作品也才可能是传播得久远的好作品。当代人要虚构1400 年前的帝王生活、帝王心理和帝王气象,秉持当代人的政治理念和政治预期来写历史人物,这是本部作品要面对的第二大挑战。这种虚构就需要作者熟谙封建帝王生活、熟知封建社会各种制度和惯例,需要掌握大量的史料,如此才可能真实地还原汉末隋初文化流脉中成长起来的旧朝帝王的形象。这种虚构还需要把握准当时及随后民众的政治观念和政治预期,要把握准当时民众的主体需求与社会主要矛盾,才能解透封建时代民间社会对一个“奄吞周汉”之“大帝”的认知心理和接受期待。
若要在同类同题作品中出彩、获得较大的吸引力,就需要给读者展示一些新鲜而得力的看点,以此来迎合读者。编织和创造使读者眼睛一亮、心头一热的新鲜点,一方面需要挖掘新史料,另一方面需要使用新方法——我们姑且将新立场、新视角也算在新方法之中。然而,历朝历代的各界人士,多年来对隋炀帝杨广差评不少,包括李渊李世民政治集团,譬如魏征主编的《隋书》,还有《旧唐书》,包括文人墨客的修辞性书写,譬如唐代的李白,以及唐代白居易的《隋堤柳》、李商隐《隋宫》、颜师古的小说《大业拾遗记》,宋代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明代齐东野人的小说《隋炀帝艳史》、褚人获的小说《隋唐演义》、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和野史小说《大业杂记》等,这些书著中对隋炀帝杨广的评价可以说是批评有余而赞美不足、否定较多而肯定较少,沿袭至今渐成定论,鄙薄隋炀帝的思维模式已成定式。今人要把杨广塑造成一位曾被历史淹没、今被“全世界人民赞扬和认可”的“不可战胜”的有为帝王,要恢复杨广所谓的“正面”,选择哪些故事、以哪些史料中的实例为基础,如何设计新鲜的看点,是王守义先生书写隋炀帝杨广的第三大挑战。
作者在“前言”中旗帜鲜明地将《隋书》中对杨广的评价称为是“恶谥”,认为诗人、史学家、政治家对杨广的评价定位“失真失实”,认为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捏造”和“臆想”,属于“伪史家”的“卑鄙”,王夫之的《读通鉴论》也是对杨广“不合历史事实”的“丑化”[1]10,这些观点鲜明而尖锐的按语,带有明确的引导性,也具有强烈的暗示性。从李氏父子和杨氏父子的情缘关系上讲隋唐改朝换代、王权更替,取“忠”“义”立场,无所掩饰主观倾向性,不能否认是让道德评判占了主位,今天的读者会不会认为作者王守义先生的关怀立场带有政治意识形态的“偏执”?会不会对作者叙事立场的客观性产生质疑?会不会因为《奄吞秦汉:隋炀大帝》轻视了对历史人物评价的辩证性和塑造人物形象的立体性而招致诟病?但是作者似乎没有过多地考虑这些,这也是作者王守义先生要面对的第四大挑战。可以说,挑战多,书写难度就大,面临的风险也多。
二、牵引受众难免“牵强”
从《奄吞秦汉:隋炀大帝》看来,杨广是一位放眼天下、心系社稷、胸怀民生的英雄,作品在塑造隋炀帝的勤政时,铺陈有序,结构松弛有度,布局可谓宏大,特别是在对话之中,显现了隋炀帝杨广的“天下”观和“大帝王”气度,可谓高调赞誉隋炀帝是本作品的基本基调。
《奄吞秦汉:隋炀大帝》同时又是一部史传小说,一定程度上又需要遵循非虚构写作的基本要求。非虚构作品的两大核心要素是客观和真实,也即故事中的主要人物和主要事件须为真实的史实,对事实的叙述要讲求客观。《奄吞秦汉:隋炀大帝》参考了《隋书》(魏征)、《旧唐书》(刘昫、张昭远等)、《资治通鉴》(司马光)等大量的史料,以及《隋炀帝传》(袁刚)、《河陇历史地理研究》(刘满)等现代学者的研究资料,对核心人物所经历的事件重新进行了组织。《奄吞秦汉:隋炀大帝》显然旨在彰显杨广的丰功伟绩,这就涉及到李唐王朝及后人对隋炀帝及其政治集团的政绩功德的考量问题。对似乎已成“定评”的话题要重新立论,是《奄吞秦汉:隋炀大帝》的预设——在前言中,作者开宗明义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认为李渊李自成父子对隋炀帝的政绩评价较低,认为李唐官方主持编撰的《隋书》对隋炀帝的贬抑较多,不满于唐代至清代文人对隋炀帝揶揄或批判,持反驳立场。读者看到此会产生这样的疑问:难道真是旧时社会各层人士对隋炀帝的评价都有失公正吗?到底哪一种评价意向更接近于客观真实?
从技术上讲,文学作品面世后,让“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让“一千个读者”看到“一千个哈姆雷特”,这样的处理可能会让作品的传播生命久远绵长。作品中涉及到对历史人物的塑造时,叙述者所持的价值标准和关怀伦理往往是绕不过去的技术难题。也即读者在评价文学作品时,一定会带上对作者、叙述者的价值标准和关怀伦理的评判。因为作者附于一部作品的前言、后记、序、跋,都是作品的一部分,与作品正文是“共生”关系,也是“互文”关系。如何让作者、叙述者的价值标准和关怀伦理不影响读者对作品的准确解读,不误导读者,不绑架读者,不无视读者的创造性阅读,这是接受批评派所警示的批评理性,也应该是《奄吞秦汉:隋炀大帝》创作中的应有警醒。
这部《奄吞秦汉:隋炀大帝》给人一个印象是:作品正文是对“前言”的注解,预设在先,对读者的价值定位和期待指向在前,而且是不避讳、不隐藏,显山露水。作品的立意在于期待读者对“前言”的高度认同,甚至说这部作品可能就只有一种答案,已经被作者在“前言”中声明了。
如果作品是这样的一种结构,作品主题、主旨和大致情节等占作品六七成的叙述内容都已在简短的“前言”中有答案了,洋洋130万字的作品留给读者的“神秘性”和“陌生感”就只剩细节了。可是谁能保证读者在已经知晓作品主体内容的情况下还会继续感兴趣?谁能保证一部作品在叙事和描写细节上就一定能赢得读者?读者给读者推荐作品时,或者读者在书架前选择作品时,在阅读了结论性的“前言”,还能耐着性子读完130万字的长篇,这样的几率有多少?
也或许,作者如此设计就是想为本书获得极好的市场销量,也未可知。无论怎样的构思设计,接受读者的检阅和筛选是任何作品都会遇到的宿命。可以说,《奄吞秦汉:隋炀大帝》在很多方面处理得不是很理想:在“正文”和“前言”的补释关系上,在把握和指引读者的阅读心理上,在作品和读者的互动上,在作品的市场化选择策略层面,都有装上“鼻圈子”牵牛走的嫌疑。
三、只设双轨便是设阈
如果说李渊父子对隋炀帝杨广的评价具有“贬多褒少”的故意,这种倾向的基点是李氏王朝取代杨氏王朝的合法性,以此为出发点的话,可以增加唐初政权的自信,那么后世司马光、王夫之等文人史家缘何要沿袭唐代李氏王朝的论调呢?后世的文人史家是不是也认为杨广政权的覆亡还有某些未入史册的缘由?当代作家王守义在《奄吞秦汉:隋炀大帝》中对杨广和李渊父子的叙述话语明显地带着倾向性,偏向于杨广的这一边,如同《三国演义》中“尊刘贬曹”的基调一样。作者王守义先生的这种倾向性是处于何种缘由呢?
浏览整部作品后会发现,作者用了“两幅眼镜”来看待主要人物和主要事迹的:一幅是涂有道德色彩的眼镜,另一幅是抹有政治色彩的眼镜。这两幅过滤色彩和光芒的眼镜,标注了《奄吞秦汉:隋炀大帝》这部作品的“小说伦理”色调,如同沙盘上闪着光带的“双轨”,指引着读者,也亮出了隋代“沙盘”中历史人物的底色。正因为标明了色调、亮出了底色,就像溪水清澈见底,溪中有鱼还是无鱼,谁来看答案都是一致的。作者的立场、价值标准、修辞策略和观念指向共同浇筑了作品中的叙事伦理,正如李建军所说:“一部小说的成败、优劣,最终决定于作者能否以最佳的方式处理小说所涉及的伦理问题和伦理关系。”[3]
从道德标准来看,《奄吞秦汉:隋炀大帝》赋予杨广的话语带有推崇和捧的意味——这种“捧”有作者的刻意,但是作者把这种刻意不说成“拔高”,而是表述为“还原”在今天看来应有的高度,“还原”其应该被新时代高举的光环。
在作者看来,多年来杨广的政绩和帝王形象是伴随着“骄奢淫逸”和“暴戾”话语传播的。隋炀帝一直被“歪曲”着。不关注隋炀帝杨广的历史功绩,是不合客观事实的,也是不公正的。在作者看来,或者结合当今的主流话语来说,隋炀帝杨广推行科举制、开挖大运河、联通丝绸之路都是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举措,是泽被后世的历史贡献,后人是从中受益的。客观地说,对隋炀帝该有的、充分的肯定还是不能少。也即,在历史上认为的“罪过”——在今天看来,可能已经变成“功德”了。
另外,《奄吞秦汉:隋炀大帝》正是处于对杨广历史功绩的高度肯定,才站在推崇的立场,采取了“英雄史诗”般的叙述。但是,《奄吞秦汉:隋炀大帝》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对杨广的“劣迹”叙述不多,有的也属于轻描淡写,致使读者从《奄吞秦汉:隋炀大帝》看到的是一个功绩卓著、鲜有缺点的封建帝王。这样塑造的人物是扁平的,不能算完全遵循了唯物主义史观,也非严格意义上的“非虚构文学”观。人类学强调站在“当事人”和“本土人”的角度看问题,马克思主义强调辩证地看待人物的“功过”,史学家注重历史地看待“他者”的行动与言论。不失偏颇便不失公信。《奄吞秦汉:隋炀大帝》显然带上了作者明确的情感好恶色彩,从整体上看来,使得作品的叙事带上了个人好恶的道德评判。
《奄吞秦汉:隋炀大帝》中的政治标准是指:作品中对隋炀帝杨广的礼赞集中于三大件事上,这三件事虽说都是大事,但是杨广还有其他方面的事,如统军灭陈、西平吐谷浑、南平林邑等,这些行动在“统一论”中是有助于国家统一的大事,但从民族学的立场来看,这是强势政权对弱势民族的“改编”,甚至是搁置“文化多样性”、摒弃多族互生和邻族共生的文化“改造”。《奄吞秦汉:隋炀大帝》对这些复杂事件的叙述和描写不够充分。
从东汉末年到隋朝的建立,地方豪强实力争霸斗强,南北各地受繁多的赋税和争战影响,人民负担沉重、疲惫不堪。隋朝建立到隋炀帝即位,“长期以来周边草原民族所结成的对抗中原王朝的强大军事联盟并未彻底解除。平陈以后,南方长期分裂而形成的割据势力和不安定因素依然存在。对此,隋炀帝采取了武力威慑和军事征服相结合的策略,打着‘观省风俗’,‘宣扬风化’和‘尤勤兆庶’的旗号巡游各地,试图实现其‘混一戎夏’的抱负。”[4]其时,最需要的是“休养生息”,最需要安民、养民,而杨广急于完成“大业”,对老百姓生活的改善和安抚远远不够,致使老百姓觉得“改朝换代”并没有真正改善百姓生活,人民心中旧恨未消、又增新愁,怨愤叠加相续。杨广体察民生和体恤民情都很有限,疏远民心基础,而这可能是隋炀帝杨广不被好评的历史原因。《奄吞秦汉:隋炀大帝》对此叙述欠详、剖析不深,对隋炀帝之失误、“恶政”就简从略,没有细致地叙述隋炀帝杨广的失误与失败。
《奄吞秦汉:隋炀大帝》高度肯定了杨广主政时推行科举、开挖运河、联通丝路这三件事,但这几件全国性的大事费时长、涉及范围广,在当时也都是劳民伤财的事,当时的老百姓受益有限,有的区域还不是直接受益的。至少当时老百姓对这三件事的认同度没有今天这样高,也没有今天这样一致。而从当今国家发展的需要来看,隋炀帝杨广当年推行的科举制、开挖大运河、联通丝绸之路这几件事,为当今中国的经济流通、全面发展奠定了基础,也提供了历史经验,在当下国家发展大局上是需要肯定的。
《奄吞秦汉:隋炀大帝》初完成于2008年,修订稿完成于2014年,这期间中国提出并推行“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也是全民审视“一带一路”文化的重要时期,营造和谐的国际关系、引领国际趋势与走向,联通中国与周边国家,都是国家意志中的重点。经济发展需要全民理解并认同顶层设计和国家战略,这意味着发展经济还要营造良好的友邦关系,这是在当今新的国际局势中审视和处理邻国关系的导向,是以大国担当的姿态对国际形势走向的一种引导。回溯隋炀帝的时代,如若1200年前隋炀帝杨广已有竞争中发展经济、沟通邻邦、引导“国际局势”的前瞻意识和谋略,并进行了布局和实践,那不能不说隋炀帝具有宏大叙事能力和穿越时空的远见。《奄吞秦汉:隋炀大帝》能专注并高度肯定隋炀帝的这一历史贡献,想必高明之处不一定在隋炀帝,而在于《奄吞秦汉:隋炀大帝》的作者具有高度的政治敏锐性,给作品赋予了政治价值。
而对道德评价和政治评价的强调,无疑会制约《奄吞秦汉:隋炀大帝》这部作品的“大众欣赏指向”,也会因轻疏了历史上的“当下性”、偏离了“还原”历史的客观性而影响了作品的艺术性。因为《奄吞秦汉:隋炀大帝》写历史真事,讲真人故事,据史料而做,不可回避“非虚构”也是这部作品应有的基本属性特征。如果有人说《奄吞秦汉:隋炀大帝》是一部虚构的文学作品,或着说借助虚构才突出了英雄故事的传奇性,那么,这个英雄是一个虚构的英雄,他就不是历史人物,那作者就没必要强调史书和历代文人志士对杨广评价的中肯与否。
这个关于“历史雄杰”的传奇故事是一个非虚构故事,人物性格和性情应该因其多面性而使作品的内涵呈现出丰富性,应全面地诠释时代人物的人格特征才更合情合理。作者注入过多的评价话语无疑减弱了非虚构作品应该有的客观性,更不是非虚构文学作品常见的“零度叙事”。也即,若是《奄吞秦汉:隋炀大帝》客观地展示出人性的多面性,公正地展示出一个有善有恶、有功有“劣迹”的杨广,那可能才是一个完整的、全面的杨广,也才是真实的杨广。
如果一部作品以道德标准和政治标准为组织叙事的主要路线,说明作者凭借先验植入对读者的阅读期待,并试图干预读者的心理。这样“先入为主”地叙事是有阈限的,甚至说对读者是有选择性的,也是较为挑剔的,或者说此创作就是针对于某一部分读者来写的。这样的话,就给作品的传播预设了范围,这种设限无疑压缩了作品的受众群体。而一部作品最大限度地获得读者群体,是任何一个作者都会有的创作期待。故而预设倾向标准也就是对作品生命力的框定,这与通常意义上的创作期待不是一种路向。
此外,既然《奄吞秦汉:隋炀大帝》是以隋炀帝杨广的三大功绩为主线来写的,那么,就该写出杨广功绩的惠民之处,就应该写出老百姓具体得到了哪些实惠。可是作品以先验的观念串出大故事,设计对话,或“概述”,或“转述”,或对话,描述性细节是呈现不足的。可以说,作品的“写意性”似乎制约了作品中重要事件的具体性和重要人物形象的逼真性,显得是“观念”大于“形象”反而削弱了作品本身应有的品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