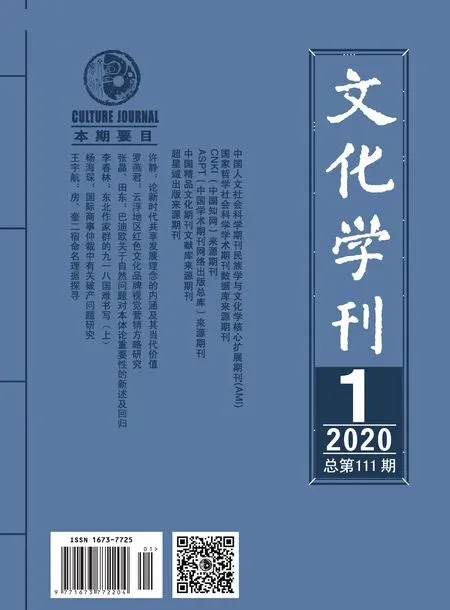再说“河母”
2020-01-17王炳海
王炳海
一、卜辞中“河母”的相关记录
甲骨卜辞中对“河神”进行祭祀的记录有很多,据统计,有关“河神”的卜辞有700余条(1)数据是笔者检索《殷墟甲骨文原文与释文对照数据库》所得,检索时间为2019年1月。。在这700余条“河神”卜辞中,多次出现“河母”“河女”等词。关于这些语汇的解释,目前学界主要有两种观点。
一种认为“河母”即河神的配偶。杨升南[1]持此说,其谓“甲骨文关于先公和先王的配偶,自示壬、示癸才开始以天干为庙号”,故河的配偶可以不以干支名而直接以“妾”或“母”来表示。饶宗颐[2]亦同此说,认为“卜辞河女、河妾、河母观之,河之有配,由来久矣”。常玉芝[3]也认为“河妻”“河母”当为“河之配偶”。然而,也有一些学者认为“河母”是人祭之礼的体现。罗琨[4]认为“于河妾”“于河妻”应解作以女性祭河。朱彦民[5]也认为“河妻”应解为“女子为牺牲对河神进行祭祀”。两派的学者因对“河母”一词理解不同,因而在释读上有所分歧。笔者分析后认为罗琨、朱彦民的说法更为合理,故对此详加论证。
卜辞河祭关于“河女”“河母”“河妾”的记录主要见以下几例:
(1)丁酉卜,贞于河母。
叀四牛。……奭……(H683(2)本文所用甲骨文编号,H为《甲骨文合集》,B为《甲骨文合集补编》。)
(2)癸卯卜,史,贞来辛……于河母,王十月。
贞……侑……
贞勿乎归,五月。

(3)辛丑卜,于河妾。(H658)
(4)御方于河妻。(H686)
这里的“河”都是指祭祀对象,即所祭之“河神”。按早期万物有灵说的观点来看,原始社会人以为万物山川必有神灵主宰,由此产生了自然崇拜,各种崇拜仪式也随之而来,这里的“河”就是殷人当时所崇拜的一位神。
饶宗颐先生在论证过程中对《甲骨文合集》19977号拓片释读有误(3)查阅原拓片释文应作“……侑母……”“……河百……”,饶先生误释作“侑母于河”。,其结论也就难以成立。杨升南认为,商祖先公的配偶,示壬、示癸才开始以天干为庙号,言外之意是其余诸先公配偶可直接称为“某母”,由此推知,“河母”当为“河神配偶”。但是此前诸多先公的配偶均未见卜辞,即使是一些貌似先公配偶的记录,也不得径直释作先公配偶先妣[6]。这样的话,杨先生的推论逻辑上就不能成立了。常玉芝先生在论证观点的过程中引了以下几条卜辞:
(5)侑于咸、大丁、大甲、大庚、大戊、中丁、祖乙……
来辛亥尞于王亥三十牛。
酒五十牛于河。
侑于河女。
贞:翌乙卯酒子汰。(H672+H1403=B100)
(6)我侑于河女(B100正)
常玉芝先生认为,例(5)中第三辞是关于祭祀河的卜问,第一辞侑祭的祖先神们未见牲品;例(6)是在卜问侑祭“河的配偶”。但常玉芝先生没有注意到的是,例(5)中的第一辞乃是残辞,无法判断出祖先神后面是否有祭品,后来根据《甲骨文合集补编》100号拓片可知,实际上记录了祭品。例(6)的释文似乎也有误,应作“侑于河我女”。此外,常玉芝先生认为“王亥女”为“王亥配偶”,由此推知“河女”当为“河神的配偶”。但“王亥女”为“王亥配偶”的观点争议太大,此说由于省吾[7]先生提出,后胡厚宣[8]、罗琨[9]驳之,可见此说还颇有争议,未成定论。
由此看来,以上种种例证都不能证明“河母”当是“河神配偶”义,故“河母”一词应作他释。下面将详细讨论“河母”为何当释“以女祭于河神”。
二、殷商“人际”山川之礼习见
殷人有用人祭山川之法,卜辞习见,如以下几例:
(7)己巳卜,彭,贞御于河羗三十人,才十月,又二卜。(H26907正)
(8)丁巳卜,其尞于河牢沈。(H32161)
例(7)中的“羗”为羗人,用为人牲,殷人有将战俘献祭于神的习俗,此条可证。例(8)中的“沈”乃沉祭之法,《周礼·大宗伯》载“以狸沈祭山川林泽”,故可知两辞中羗、显然是人牲,是以人为牺牲向山川之神行祭礼。其实,用人祭于神灵不仅见于殷墟卜辞,后代文献也有记录。《小孟鼎》载:“折兽于□。”郭沫若[10]先生谓:“斩酋于某地也。古人以俘馘献于宗庙,本铭即其一例。”又见《春秋》记曰“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师灭蔡,执蔡世子有以归,用之”,《左传·昭公十一年》注载“冬十一月,楚子灭蔡,用隐大子于冈山。申无宇曰:‘不祥。五牲不相为用,况用诸侯乎?王必悔之。”《左传·昭公十年》载“秋七月,平子伐莒,取郠,献俘,始用人于亳社。臧武仲在齐,闻之,曰:‘周公其不飨鲁祭乎!周公飨义,鲁无义。《诗》曰:德音孔昭,视民不佻。佻之谓甚矣,而壹用之,将谁福哉?’”。《史记·滑稽列传》中记有“西门豹治邺”的故事,记述了祝巫“为河伯取妇”的暴行。可见,人祭山川之法在上古社会历代沿袭,尤以殷商为盛。以女俘祭于山川神灵在殷商乃是常态,这就为“河母”释作“以女祭河”提供了可能性。
三、句式上的考察
《甲骨文合集补编》100正有两辞云“酒河五十牛”“酒河三十牛氏我女”。“酒”即为“酒祭”,“氏”为“致”义,“女”即“女奴”。大意是在问“用五十头牛酒祭河神呢?用三十头牛酒祭河神呢,还是用我地的女奴呢?”[11]此外,同版还有两辞云“侑于王亥四十牛”“侑于王亥女”,也是在询问祭品是用四十头牛呢,还是用女俘呢。从“四十牛”与“女”在句中出现的位置来判断,“女”当是与“牛”一样,为祭品无疑。同样是这一版,出现了“于河我女”的卜辞,这样就更加清楚地揭示出了“女”不应当与“河”连读,因为“我”在卜辞中多为殷人自称,“我女”就是“殷人本地的女奴”,有时候表示范畴含义的“我”略去就成了“河女”,但意义不会有太大差异。另外,这一版还出现了“贞酒于河报”的卜辞,“报”即为俘虏,“河报”就是准备将“报”献给河神,因为是同版卜辞,我们可以推测“女”与“报”关系密切,又可证“河女”一词中“女”为“女奴”义。
笔者认为,“于河女”这样的句式和“于河五十牛”(H672)在结构上是一样的,是可以从“五牛于河”(H00811反)变换而来。如果是“祭牲+于+神名”的组合方式,就成了“……(以)女于河”的句式,反之,“于+神名+祭牲”的组合方式就成了“……于河(以)女”的句式。笔者认为,这样的变动本质上并不会造成意义上的不同,只会让句子的焦点发生迁移。“焦点”是语用学的术语,笔者借用这个名称,把卜辞命辞中表示占卜重点的词语叫作焦点,通过同版选贞卜辞的对比来确定焦点,以以下两辞为例:
(9a)酒五十牛于河。
(9b)勿五十牛[酒]于河。
(10a)侑于王亥女。
(10b)侑于河我女。 (B100)
这是《甲骨文合集补编》100版上的四句卜辞。(9a)与(9b)的焦点显然是在“五十牛”,但是当介词结构“于+神名”前移之后,(10a)与(10b)的焦点就成了“王亥”和“河”这样的神。沈培[12]先生曾做过这方面的统计,认为变动介词结构的语序是突出句子的一种方法。有时候,语序变化过程中作为介词性质的“以”是可以略去的,所以“御方于河妻”很能是从“(以)妻于河”或“于河(以)妻”变化而来,意义上都是表达要以女子为牺牲向河神祭祀。
四、余论
需要注意的是,甲骨文“女”作,本就像屈膝交手之人形,乃“奴”的本字,三体石经中“怒”字之“奴”就作“女”即是一证。甲骨文中“女”“母”常可通用,意义上有时没有差别,而“妾”也可读如“母”,用作人牲。另外,上古有劫掠妇女为妻之俗,“妻”字即为此反映[13],而劫掠的对象也一般就是俘虏或奴隶,可知“妻”与女奴有密切联系。故“河妻”“河女”“河母”等词是存在意义上相同或相关可能性的,均可释作“以女子或女奴献于河神”。而有人根据卜辞中的这些词判断说,殷代所祭河神是有完整体系、庞大队伍的,祭祀对象包括河神的配偶、母亲、子女,以此推知河神在殷人鬼神世界中地位之崇高,现在看来,这些说法都是有待商榷的。
综上所述,卜辞中凡是“河母”“河妻”一类的词都应释作“以女祭河”,不得径直释作河神配偶。如今看来,《史记》所记“西门豹治邺”故事中的人祭川河的习俗乃是殷商遗风,而后代所记“为河伯娶妻”等传说显是殷商人祭之滥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