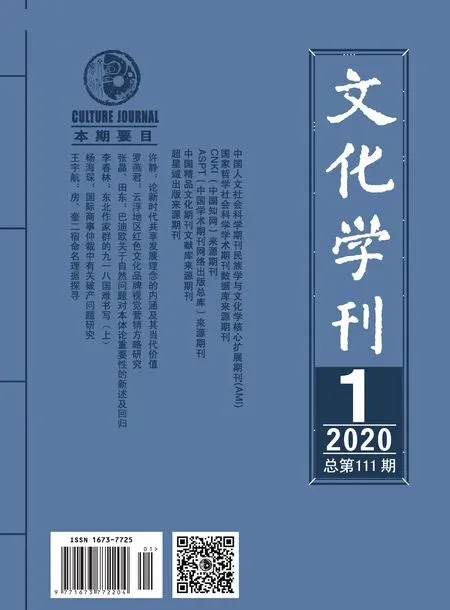从同人作品的合法性看著作权法的限制与例外
2020-01-02杜昱萱
杜昱萱
一、同人文学作品的概念与特性
“同人”二字,意通“同好”,多指“志同道合者”,代表着拥有相同爱好的一类群体。同人作品,则是该类群体基于对特定作品或角色的喜爱对原作品进行创新所形成的产物。同人文学作品的灵感来源是已经存在的特定作品,创作过程难免涉及对原作元素的引用,而这种与原作品之间的特殊联系,正是同人文学作品大行其道的原因[1]。在表现形式上,同人文学作品的原作品既可以是小说、诗歌,也可以是影视作品、漫画、游戏等,这些非文学类作品的文学化,无不体现了作者的匠心。此外,既然是创作者“二次加工”的产物,同人文学作品的内容便不可避免地染上加工者的个人色彩,从而与原作区分开来,如红楼梦同人作品《一代文豪林黛玉》中,因受作者激进思想影响,原著中的闺阁女子黛玉被描绘成一个“出走的娜拉”式人物,在腐朽的贾府掀起一场变革。因此,同人文学作品常被称为一种“半原创”(part-original)、“半借用”(part-borrowed)的文学创作形式[2]。
二、同人文学作品的著作权问题分析
(一)有“独创性”的外在表达——同一标准的不同应用
只有著作权意义上的作品才能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一部同人文学作品,想要获得著作权法上的保护,必须同时满足两个要件,即构成对思想的具体表达与具备著作权意义上的独创性。是否构成具有独创性的外在表达,同样也是同人文学作品著作权侵权认定的标准,只是在著作权侵权领域,该项标准针对的对象,是被公开引用的原作品的元素。
在“金庸诉江南”一案中,我们不难看出,同人文学作品的侵权认定需遵循两个步骤:(1)依“思想与表达两分法”与著作权法上“独创性”的要求判断同人作品所使用的原著元素是否属于著作权法保护的对象;(2)按照“接触+‘实质性相似’”标准判断这种使用是否构成侵权。
(二)同人文学作品受著作权法保护
如前所述,同人文学作品是一种“半原创”“半借用”的文学创作形式。著作权法上的独创性须包含“独”“创”两方面:“独”意指“独立创作、源自本人”,要求劳动成果是本人独立完成的结果;而“创”则要求劳动成果必须具备一定的智力创造性,而不仅是“额头流汗”的结果[3]。不同于原作品的“复制件”,任何文学作品都是作者智慧与心血的结晶,同人文学作品也不例外,即使对于某些文学价值不高的作品,也不应该否定其智力创造性。
值得注意的是,在同人文学作品创作过程中,因引用程度不同,其独创性也存在高低。有的同人文学作品虽籍原著之名,实际联系却相当微薄,如某些角色衍生类作品,仅以原作边缘角色展开,或所借用的只是原作的角色名称,外形、性格、人物关系等都与原作大相径庭[4]。而另一些同人文学作品,则更接近于在原著的基础上“建房子”,如《乱世佳人》的同人后传《斯佳丽》虽然撰写的是斯佳丽在白瑞德走后远走爱尔兰等地的经历,却多次涉及斯佳丽与白瑞德感情破裂、梅兰妮死亡等事件的回忆。此类作品虽然也存在同人作者的匠心雕琢,却与原作联系密切,或构成演绎作品中的改编作品,因其未经许可的改编行为侵犯原作著作权。
(三)同人文学作品受著作权规制
既然同人文学作品属于著作权意义上的作品,那么,同其他原创作品一样,在受到著作权法保护的同时,必然也要受到著作权法的规制,在此意义上,同人作者对原作品作者负有不得侵害其著作权法上权益的义务。
1.“思想”与“表达”的区分
“思想”与“表达”的区分是确定著作权法保护范围的基本原则,即著作权法保护的仅是“思想的表达”,而非“思想”本身。如前所述,无论是作品本身还是作品所包含的元素,只有同时具备“独创性”且满足“具体表达”的要求,才能被归入著作权法保护的范畴。在“金庸诉江南”案中,法院认为,在文学创作领域,只有当具有特定性格特征与人物关系的人物名称以具体的故事情节在一定的时空环境中展开时,其整体已经超越了抽象的思想,才属于对思想的具体表达;反之,脱离了具体故事情节的人物名称、人物关系、性格特征的单纯要素,往往难以构成具体的表达。在“天下霸唱《摸金校尉》”一案中,法院作出了同样的认定,即认为“只有当人物形象等要素在作品情节展开过程中获得充分而独特的描述,并由此成为作品故事内容本身时,才有可能获得著作权法保护”(1)参见上海市浦东新区法院(2015)浦民三(知)初字第838号。。不难发现,两个案件中,法院判决均涉及对美国版权法上“故事讲述标准”与“充分描述标准”的参考。虽然在实际操作上各自存在限定过严与法官主观性较强[5]的弊端,但在“思想、表达两分法”过于抽象时,将这两项标准作为司法实践的参照仍具有一定的意义。
2.“实质性相似”的分析
正如李明德教授所说,著作权侵权的认定包括作品与行为两方面[6],要判定同人作者公开引用原作品元素的行为构成著作权侵权,除了判断所引用元素是否受著作权法保护外,还应当对这种引用行为的正当性加以讨论,即同人作者是否接触过原作品,以及该作品是否与原作品构成“实质性相似”。
在“实质性相似”问题的分析上,“抽象概括法”与“整体观感法”是最常用的方法。在前者,审判者将作品自上而下地解构为从作为思想的主题到作为表达的语句的不同层次,且将不同层次内不受保护的“思想”排除出去,将最终保留的部分进行相似性比较得出结论;而在后者,相似性的比较则不必区分内容,只需要从一个普通、理性的观众或读者角度作出整体性判断即可。
“抽象概括法”与“整体观感法”的应用并非相互排斥。同人文学作品的读者往往先入为主地将原作品的阅读体验带入同人作品的欣赏过程中,从而造成一种“相似”的错觉,因此,单独适用“整体观感法”作为判断标准,易形成对同人作者的苛责。如《此间的少年》中,女生“黄蓉”娇生惯养、聪明活泼,看过《射雕英雄传》的读者很容易将她代入桃花岛主之女。而“抽象概括法”的问题在于,对原作品的解构越是细致,就越容易将原作品中本应该受到保护的作品元素给过滤出去[7],从而缩小著作权法保护的范围。同人文学作品对于原作品元素的使用很少是整体性的,多为“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碎片化式借用”,当这些“碎片”分布在不同的情节中时,可能不属于著作权法保护的范围,但是当这些“碎片”排列组合起来,构成一个不存在于其他作品中整体性的要素时[8],该要素本身可以具有“独创性”。因此,对于这两种方法的应用,更应当根据作品本身的特点,从鼓励创新兼顾公平的立场作出相应的调整。
三、结语
正如前述,同人文学作品是借“他山之石”而行“攻玉之事”,在因其独创性受到著作权法保护的同时也负有不得侵害原作品著作权的义务。但法律对于著作权的保护,并非是筑起高墙、画地为牢式的垄断。中国历史上,文学艺术的瑰宝大多并非创作者横空出世创作出来的,而是长期“层累”的结果[9],《三国演义》之于《三国志》,《西厢记》之于《莺莺传》,皆属同人。对原作者,优秀的同人文学作品固然是对自己智力成果的肯定,也能成为后续创作的灵感源泉,甚至对一些并未接触过原作品的读者,出色的同人文学作品能激发其阅读原作的欲望。因此,不少原创作者会选择默许非商业性同人作品的存在,或以“CC协议”(2)“CC协议”即“Creative Commons协议”,是原作者许可同人创作的最普遍形式。等方式告知同人作者权利的边界。除了这种私法自治内的平衡,法院在司法审判中,也应当抱以宽容的态度,灵活处理,而不能将这种特殊的创作形式,与抄袭、剽窃作品等而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