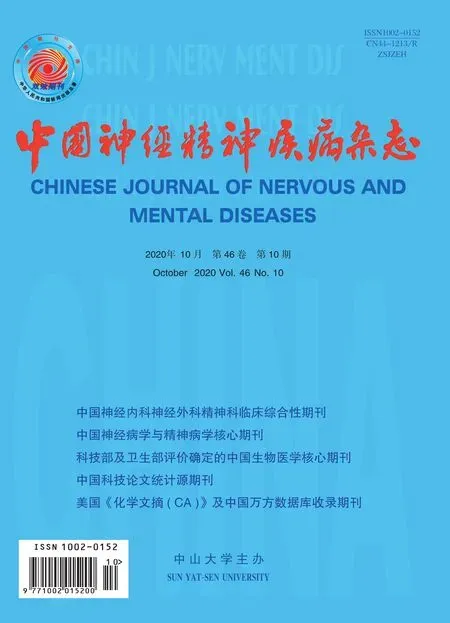抗血管内皮生长因子靶向治疗难治性垂体腺瘤和垂体腺癌研究进展
2020-01-11马丽媛代从新
马丽媛 代从新
垂体腺瘤(pituitary adenoma,PA)约占颅内肿瘤的10%~20%,大部分为良性,生长缓慢,手术可以全切[1]。然而,仍有部分PA呈现出侵袭性,生长速度较快,经过手术、放疗、药物等常规治疗后无法控制肿瘤生长、降低激素分泌水平或肿瘤仍然复发,预后极差,严重危害患者健康甚至危及生命[2],我们将这类PA定义为难治性垂体腺瘤(refractory PA)[3-4]。此外,大约0.2%的垂体肿瘤会出现中枢神经系统或其他系统的转移,我们称之为垂体腺癌(pituitary carcinoma,PC)。PC预后极差,平均生存期为1~3年。目前,难治性PA和PC的标准治疗方法尚不明确,手术、放疗以及替莫唑胺(temozolomide,TMZ)的治疗效果仍然有限[5]。近年来,越来越多基础和临床研究[5-12]表明,抗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VEGF)靶向治疗在难治性PA和PC中可能有效,或可成为难治性PA和PC的新型治疗选择之一。本文就抗VEGF靶向治疗难治性PA和PC的研究进展作一综述。
1 抗VEGF靶向治疗难治性垂体腺瘤和垂体腺癌作用机制
VEGF在多种组织学亚型的PA细胞中呈现高表达。一项纳入了148例PA及PC的研究,通过免疫组织化学方法发现VEGF蛋白在未经治疗的生长激素细胞腺瘤、寂静型 ACTH(adreno-cortico-tropic-hormone)细胞腺瘤、无功能腺瘤和PC中的表达更高[13]。另一项纳入197例PA的研究发现VEGF高表达占58.9%,且在促性腺激素细胞腺瘤(78.4%)、泌乳素腺瘤(60.7%)、无功能腺瘤(57.1%)和ACTH细胞腺瘤(51.9%)中更常见[6]。在多发性内分泌腺瘤病 1 型(multiple endocrine neoplasia type 1,MEN1)小鼠模型中,用VEGF单克隆抗体G6-31治疗后,催乳素瘤生长明显受抑制,血清催乳素水平也明显降低[14]。多种类型PA患者外周血VEGF水平较正常对照明显升高,且在手术、放射治疗后可明显下降[15]。还有研究表明PA中VEGF及其受体(VEGF receptor,VEGFR)的高表达与PA侵袭性和复发有关[16]。这些研究均提示VEGF在PA发生发展中可能起着重要作用。
因此,抗VEGF靶向治疗PA成为了人们日益关注的领域。靶向VEGF有3种途径:①利用中和VEGF的抗体;②靶向VEGFR;③阻断下游途径,抑制VEGF的激活和信号转导[17]。靶向VEGF旨在阻止新血管形成、生长,从而抑制肿瘤的生长。目前,抗VEGF靶向治疗中研究最多的为VEGF中和抗体——贝伐单抗(bevacizumab);其次,一些酪氨酸激酶抑制剂(如阿帕替尼、阿昔替尼)可以靶向VEGFR途径;此外,PA的常规治疗药物(如生长抑素类似物、多巴胺受体激动剂)也可通过影响VEGF途径来抑制肿瘤细胞[13,16,18-20]。
2 VEGF中和抗体治疗难治性PA和PC的临床研究
迄今为止,评估抗VEGF靶向治疗对难治性PA和PC临床治疗效果的报道仍较少,其中,以关于VEGF中和抗体——贝伐单抗的研究居多。贝伐单抗是一种重组人源化单克隆抗体,它可以抑制VEGF与VEGFR的结合[21]。作为一种血管生成抑制剂,其可延缓肿瘤生长,被推荐用于治疗结直肠癌、非小细胞肺癌、肾细胞癌、乳腺癌和神经胶质瘤[17]。近年来,众多报道也证实了其对于PA的疗效[12]。贝伐单抗可以单药或与其他药物联用治疗难治性PA和PC。难治性PA和PC的标准治疗方法目前尚不明确,主要包括手术切除、放疗以及替莫唑胺。自2006年以来,大量研究已证明TMZ在难治性PA和PC中有效,缓解率约为60%[22]。为进一步探究PC的有效治疗方法,有研究者评估了贝伐单抗或TMZ与贝伐单抗联合治疗的效果。目前,贝伐单抗作为单药治疗[7,12]或联合治疗[8-10]已应用于 5例ACTH垂体肿瘤病例(其中4例为PC),有4例取得了病情稳 定[7,8,10,12]。
贝伐单抗单药治疗或可用于其他治疗方法均无法有效控制病情的难治性PA和PC。ORTIZ等[12]2012年首次报道了贝伐单抗单药治疗PC且长期控制病情的病例。1位侵袭性ACTH垂体瘤患者在进行了7次手术、放疗和3个疗程的TMZ治疗后仍无法控制肿瘤生长并进展为PC,由于该患者肿瘤表现出VEGF免疫反应性,故开始了每2周静脉注射贝伐单抗10 mg/kg的治疗,26个月随访未见疾病进展,肿瘤活检显示严重细胞损伤、血管异常和纤维化[12]。
贝伐单抗与TMZ、放疗或帕瑞肽联合用药可以有效控制难治性PA及PC进展、延长患者生存期。TOUMA等[9]报告了首例将贝伐单抗和TMZ联合放疗作为一线治疗功能性ACTH分泌型PC伴肺部转移的病例,TMZ 75 mg/m2每日服用,联合贝伐单抗每2周10 mg/kg治疗,8周后患者获得了完全缓解,且5年长期随访未见复发。ROTMAN等[8]报告了1例经手术、放疗治疗转移灶后使用贝伐单抗和TMZ联合治疗ACTH分泌型PC病例,患者无进展生存期为8年。此外,欧洲内分泌学会(European Society of Endocrinology,ESE)报道了7例贝伐单抗单药或联合TMZ治疗难治性PA和PC的病例[5]。其中,1例患者在接受了贝伐单抗联合TMZ治疗后取得了部分缓解,另外6例先前接受第一程TMZ治疗后效果不佳的患者中,有3例之后接受了贝伐单抗联合第二程TMZ的治疗,其中1例获得部分缓解;另外3例在其他治疗失败后应用了贝伐单抗作为二线或三线治疗,1例获得部分缓解,1例病情稳定,1例疾病进展。O'RIORDAN等[10]报道了1例其他疗法无效后经帕瑞肽和贝伐单抗联合治疗6个月后出现临床改善和ACTH水平降低的转移性ACTH分泌型PC病例,这种组合或许可提供一种新的治疗选择。
除了在侵袭性ACTH分泌型PA中的应用外,贝伐单抗在其他类型PA中也可发挥有效作用。DUTTA等报告了1例通过手术、奥曲肽、放疗、TMZ、贝伐单抗和培维索孟多模式治疗控制病情的伴芳香烃受体相互作用蛋白(aryl hydrocarbon receptor interacting protein,AIP)突变的侵袭性儿童生长激素瘤病例[11]。
此外,贝伐单抗可以用于治疗放疗带来的并发症。有报道[17]表明贝伐单抗可以改善鞍上垂体瘤患者因放疗或伽玛刀手术所引起的放射诱导性视神经损伤,还可用于治疗脑放射坏死[23]。
贝伐单抗治疗的副作用可能包括高血压和蛋白尿,但是也有少量报道动脉血栓形成(包括急性心肌梗塞)、静脉血栓栓塞、出血、胃肠道穿孔和伤口愈合不良等并发症[17,24]。因此,贝伐单抗的应用仍需谨慎。
3 其他靶向VEGF机制治疗PA的研究
酪氨酸激酶抑制剂可以通过抑制VEGFR来靶向VEGF途径,治疗难治性PA。如阿帕替尼(YN968D1)可以高度选择性地竞争细胞内VEGFR-2的三磷酸腺苷结合位点,阻断下游信号转导,从而抑制肿瘤血管生成。WANG等[25]报道了1例侵袭性生长激素PA的患者,其在3年内经手术和放疗治疗后均无效,后经阿帕替尼联合TMZ治疗1年,生长激素水平降至正常,肿瘤大小减少了90%,且31.5个月随访无复发。
体外实验表明多巴胺受体激动剂可通过抑制VEGF信号通路来抑制多种PA。GAGLIANO等[20]用卡麦角林干预无功能PA患者来源原代培养物,结果证明多巴胺激动剂可通过抑制VEGF的分泌来抑制细胞活力。LUQUE等[26]观察到在多巴胺激动剂耐药性催乳素瘤小鼠模型中VEGF表达增加,而抗VEGF治疗可以使催乳素水平下降、肿瘤血管减少及肿瘤体积变小。因此,抗血管治疗或可作为该类PA的补充治疗靶标。CHAUVET等[27]用溴隐亭单药、阿昔替尼单药及两种药物联合治疗出血性催乳素瘤小鼠,发现溴隐亭和阿昔替尼单药均可以抑制肿瘤的生长并改善血管重塑,而两药联合治疗还能抑制肿瘤内出血并恢复血管灌注。因此多巴胺激动剂有望成为一种新型的通过稳定异常血管、提高其他药物疗效来发挥作用的抗血管生成疗法。
多项体外及体内研究[13,16,18-19]均报道生长抑素类似物治疗可以下调VEGF的表达,从而对PA产生抗血管生成作用,而且与生长抑素(somatostatin,SST)受体亚型 SST1和SST2的表达可能有关[18-19]。
4 总结与展望
综上所述,VEGF这种关键的促血管生成因子在多种PA中均有高表达,且与PA的侵袭性有关,抗VEGF靶向治疗在多种类型的PA中都有一定疗效。其中,抗VEGF靶向治疗与放化疗联合应用对难治性PA和PC患者的治疗有更好的疗效,不但能够控制疾病进展、还能延长患者生存周期。因此,抗VEGF靶向治疗或可作为难治性PA和PC新的治疗选择,但是这方面的研究仍较少,需要更多的研究来评估其有效性及安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