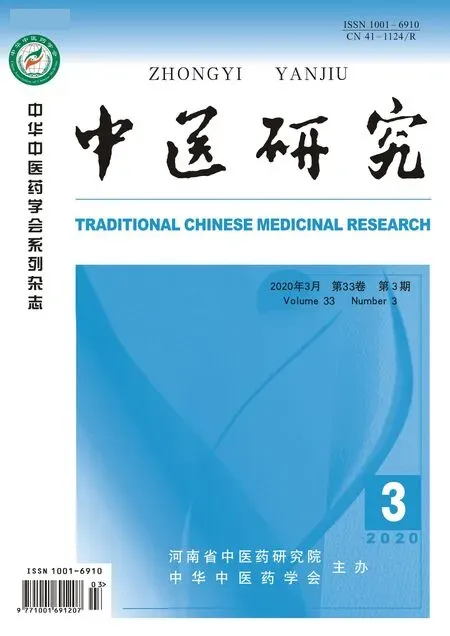论张仲景运用人参、黄芪之异同
2020-01-10王建康谷红苹张熊斌鲍平波
王建康 ,谷红苹 ,张熊斌 ,鲍平波
(1.宁波市中医医院, 浙江 宁波 315010; 2.余姚市中医医院, 浙江 余姚 315400;3.宁波市奉化区锦屏岳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浙江 宁波 315500;4.宁波市海曙区中医院, 浙江 宁波 315000)
人参、黄芪属临床常用补气药,均收藏于《神农本草经·上品》,是“主养命以应天,无毒。多服,久服不伤人”的上品中药。在《伤寒论》与《金匮要略》中,张仲景创制之方剂含人参者35方,含黄芪者8方,但未见两药合用方,且《伤寒论》不用黄芪,可见两者补气功效有异。
1 人参、黄芪之药性异同
《神农本草经》谓人参“主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止惊悸,除邪气,明目,开心益智。久服,轻身延年”。汪昂曰:“苦属火入心,甘属土入脾。”“黄属土入脾,白属金入肺。”“人参黄润紧实。”故又称其为黄参。《神农本草经》谓黄芪“主痈疽久败创,排脓止痛,大风,痢疾,五痔,鼠瘘,补虚,小儿百病”。汪昂曰:“甘属土入脾。”“黄属土入脾,白属金入肺。”“黄芪皮黄白。”
综合历史研究,人参性味甘,微苦,微温,归脾、肺经,具有大补元气、补脾益肺、生津止渴、安神增智功效。黄芪性味甘,微温,归脾、肺经,具有补气升阳、益卫固表、托毒生肌、利水退肿功效。两者性味归经基本相同,均能补肺、脾之气。人参大补元气和五脏之气,调中助后天之精气,入肺助纳清气,故能固守五脏之气但不走卫表经脉,其在内者,守而不走;黄芪善补中阳,固卫气,益气兼能利水行血,善走卫表经脉,其在外者,走而不守。这是两者之异。张仲景对此深有研究,在遣方用药上重视异同,各取其长,示人法度。
现代药理学研究显示:人参的活性成分主要为人参皂苷、多糖、有机酸和蛋白质等[1];黄芪的活性成分主要包括多糖类(黄芪多糖)、三萜皂苷类、黄酮类、氨基酸类和微量元素等[2]。目前对人参、黄芪的药理研究主要集中于单体人参皂苷、人参多糖、黄芪多糖、黄芪皂苷等的药理作用及分子机制研究,这对中医药体系而言,不能阐述其补气内涵之异同。刘俊秋[3]通过实验及系统药理学方法对黄芪、人参的补气内涵异同首次进行全方位展示,结果发现:黄芪、人参都与甘油磷脂代谢相关,但侧重点不同,黄芪偏向于调控嘧啶代谢和鞘脂代谢,人参偏向于调控糖代谢;黄芪的免疫调节内涵可能与视黄醇代谢和甘油磷脂代谢有关,人参则主要是调控氨基酸代谢(精氨酸与脯氨酸代谢)、三羧酸循环。此外,系统药理学结果显示了黄芪、人参免疫调节相关酶不一致性。
2 人参、黄芪之功用异同
2.1 扶正祛邪人参见长,祛风胜湿黄芪为上
《素问·热论篇》曰:“伤寒一日,巨阳受之……二日阳明受之……三日少阳受之……四日太阴受之……五日少阴受之……六日厥阴受之……”邪入少阳,正气已有不充,小柴胡汤巧用人参扶正祛邪。正如喻昌在《寓意草》所言“所以虚弱之体, 必用人参三五七分 ,入表药中,少助元气, 以为驱邪之主,使邪气得药 ,一涌而去”“和解中之用人参,不过藉之以得其平,亦非偏补一边之意也”“藉人参之力,领出在外之邪,不使久留,乃得速愈为快”。外感病并现气阴两虚之象,张仲景善用人参助益气养阴以扶正助驱邪。又如桂枝新加汤治太阳病邪伤营阴之身痛,白虎加人参汤治汗法不当而助热化燥或阳明气分热盛、损及气阴,竹叶石膏汤治伤寒解而未净、气阴两伤,均为发挥人参的扶正祛邪作用。
表虚卫气不固,风湿之邪伤及肌表,张仲景用防己黄芪汤祛风胜湿治表虚不固之风水或风湿证。张秉成的《成方便读》云:“然病因表虚而来,若不振其卫阳,则虽用防己,亦不能使邪迳去而病愈,故用黄芪助卫气于外。”罗美在《古今名医方论》中称黄芪为“补剂中风药”。因黄芪固表功能较强,故风寒或风热之邪在表者不宜黄芪,以免闭门留寇而贼不出[4]。
2.2 阴阳两虚人参首选,虚劳诸损黄芪在前
人参健脾益气,又可养阴生津、温养心气,且补气作用迅速,张仲景首选人参阴阳双补以安神定魄。如炙甘草汤峻补心阴,温通心阳,使气血充养,阴阳平衡,悸止脉复;茯苓四逆汤回阳益阴,人参壮元气、补五脏、安精神且能益阴,治汗下后阴阳俱虚致烦躁。气为阳,血为阴,阴阳互根,气血相依,气虚血亦虚,气旺血自生,补血剂中配以人参,意在“阳生阴长”。张仲景用四逆加人参汤治痢止亡血证,开后世益气生血法之先河。《金匮要略·血痹虚劳病脉证并治》曰:“虚劳里急,诸不足,黄芪建中汤主之。”黄芪善补脾胃之虚,以治气血阴阳俱亏之慢性消耗性疾病。喻昌在《寓意草》中言:“金匮遵之而立黄芪建中汤,急建其中气,俾饮食增而津液晚旺,以至充血生津,而复其真阴之不足。”《本经疏证》曰:“黄芪色黄味甘,直入中土而行三焦,故能补中气。”可见,虚劳诸损善用黄芪建中焦为先。
2.3 固元补气人参力宏,固表益卫黄芪效专
人参为补气上品,补益之长在于大补元气,复脉固脱,为拯危救脱之要药。《本草经疏》载:“人参能回阳气于垂绝,却虚邪于俄顷。”张仲景常将其与附子、干姜相助而用,既固护元阴,又助补元阳,以达补益防脱之效,如四逆加人参汤、茯苓四逆汤。《本草述钩元》曰:“人参益元气, 肺脾先受之, 以入五脏, 五脏俱入, 则诸虚皆补, 所以人参大补元气, 实则为大补后天之气, 以滋先天元气。”张仲景喜将其与白术、干姜相须而用,既健脾益气又温中理气,以达补益固元之效,如理中丸、人参汤等。
黄芪补益之长在于固护卫气,实表止汗。张景岳谓黄芪“因其味轻,故专于气分而达表……气虚而难汗者可发,表疏而多汗者可止”。张仲景常用桂枝、芍药配伍而用以和营卫,使在表之湿随汗而解。表虚之人,虽取微汗,犹恐重伤其表,黄芪可固表益卫,使汗不伤正,补不留邪,如黄芪芍药桂枝苦酒汤和桂枝加黄芪汤治黄汗病。
2.4 运脾化湿人参效佳,健脾行水黄芪功强
《长沙药解》谓人参“入足阳明胃、足太阴脾经。入戊土而益胃气,走已土而助脾阳,理中第一”。 马裔美等[5]统计分析得出张仲景善用的与人参配伍的前几位药物是甘草、姜半夏、大枣、生姜、干姜、桂枝。 仲景善用人参与大枣、甘草等配伍以顾护脾胃之气,与桂枝、生姜、干姜等配伍以温中扶助脾阳;与半夏配伍补中有降,健脾运脾,燥湿化痰。方如大半夏汤、干姜人参半夏丸、麦门冬汤、旋覆代赭汤、桂枝人参汤、大建中汤、半夏泻心汤、干姜黄芩黄连人参汤等。以上诸方均存在共同病机:或寒或热,或寒热夹杂,或外邪内陷,或下焦浊阴上扰,中焦均受痰湿之邪困扰而虚,故用人参运脾化湿。另与厚朴、陈皮理气之品配伍,更体现消补兼施,兴利除弊,运脾化湿之意,如厚朴生姜半夏甘草人参汤、橘皮竹茹汤。
陈修园的《神农本草经读》云:“黄芪入三焦而助决渎之用,入脾而救受克之伤。”脾肺气虚、水湿内停、阳气被遏所致皮水证,为表湿水肿之病,张仲景用防己茯苓汤通阳利水,益气消肿。其中黄芪助茯苓健脾益气,助防己利水除湿,助桂枝通阳化气利水,可谓一举三得之功。黄芪擅长治表湿而不宜于内湿。单纯脾虚湿困于内之腹胀、泄泻等证,运用黄芪有壅滞脾机之弊,可致腹胀、泄泻更甚,舌苔白腻更厚。
2.5 益气复脉人参专长,运血通脉黄芪擅长
心主血脉,血脉之正常运行,需兼具脉道通利、血液充足、心气充沛。人参既能补益心气,助脉中阳气推动血液之运行;又能使脉中之阴血得以化生充盈。张仲景用人参益气复脉有三方:一为炙甘草汤,方中气血阴阳并补,共奏益气养血、复脉定悸之效;二为四逆加人参汤,救阳亡阴竭之危证,人参意在益气助养血以复脉;三为通脉四逆汤,脉若不出加人参,人参意在益气复脉之功。
张璐的《本经逢源》载有黄芪“性虽温补,而能通调血脉,流行经络,可无碍于壅滞”,故其善治历节肿痛等。乌头汤治寒湿痹阻之历节病,黄芪桂枝五物汤治营卫俱虚之血痹,两者病在筋脉骨节,黄芪与温散之药相助,益气温阳,活血通脉;与芍药相佐,柔阴和营,养血通脉,补中有通,散中有固,共助运血通脉。故后世王清任的《医林改错》常重用黄芪与活血药相配,名曰“补阳还五汤”,治气虚血瘀之中风偏瘫,临床常用。
3 人参黄芪之配伍异同
探讨张仲景运用人参黄芪之异同可指导于临床,配伍可为后世效仿、发挥。效仿张仲景之人参与附子相须而用,可达回阳救逆之效。如《校注妇人良方》之参附汤(人参一两,附子五钱)、《重订严氏济生方》之参附汤(人参半两,炮附子一两,生姜十片)、《医方类聚》引《济生续方》之参附汤(人参半两,附子一两)、《景岳全书》之一气丹(人参、制附子各等分)、《辨证录》之独参汤(人参三两,附子三分)。效仿黄芪固表益卫之效,创当归六黄汤治疗阴虚火旺盗汗、玉屏风散治疗表虚自汗或体虚易于感冒。效仿黄芪益气温阳、运血通脉之效,创三黄汤治疗中风之手足拘急、四神煎治疗鹤膝风、补阳还五汤治疗气虚血瘀之中风等。
人参与黄芪同为补气药物,张仲景未一方同组,但后世医家升华发展,配伍相须而用。李杲挖掘黄芪益气升阳之功,创补中益气汤、升阳益胃汤、黄芪人参汤、调中益气汤、补脾胃泻阴火升阳汤、清暑益气汤等,其中黄芪量大于人参,体现其“升阳举陷”之效;其他如保元汤、黄芪当归人参汤、黄芪人参汤等治虚损劳怯、元气不足之证;归脾汤、十全大补汤、人参养荣汤、泰山磐石散等治气血双亏之证。张仲景未予人参与黄芪合用,除两者合用易致气机壅滞之弊外,可能源于东汉年代对黄芪之功效认知局限。顾志荣等[6]本草考证:唐代、五代首提黄芪“补血”之说;宋、金、元时期提出黄芪“补五脏诸虚不足、益元气”;明清时期提出黄芪有“补中气、升阳举陷”之功。
4 结 语
张仲景对人参、黄芪的运用具有明显的学术特点:①两药同为补气之药,但未同方合用;②虚证外感多用人参扶正,不用黄芪,以免固表留邪;③运用时灵活配伍,人参具有调补气血阴阳津精之多重效用,黄芪具有补气通阳、养血活血之功;④人参运脾化湿长于治内湿,黄芪行水利湿治表湿;⑤人参补气固元力宏效速,为阳气外脱危重症之专药,黄芪为治疗慢性虚劳之圣药。深入研究张仲景对人参、黄芪的功能认识和运用方法,对临床有指导、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