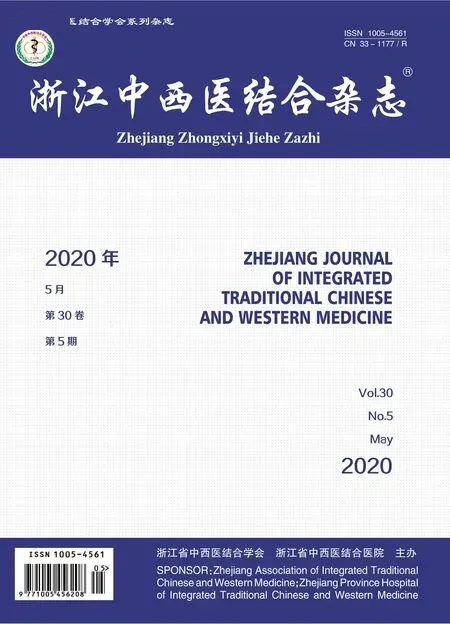中医药防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进展
2020-01-09张燕燕周胜利
张燕燕 周胜利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属于中医“疫病”范畴,《瘟疫论》[1]指出“瘟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异气属疫毒概念,具有强烈的传染性和一定的季节性。冠状病毒以其高传播效率、严重感染后果以及不可确定的流行时间对人类健康构成了持续的威胁[2],COVID-19 目前暂无特效药治疗,国家卫健委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已更新至第七版,对于中医药治疗COVID-19 实时动态调整具体诊治方案,肯定了中医药在此次“战疫”中的重要地位。现对中医药防治COVID-19 综述如下。
1 病因病机
何威华等[3]通过对两则临床医案的辨析,认为其主要病机为湿毒为患,有寒湿和湿热之分,早期以寒湿为主,日久向湿热发展;亦有平素湿热体质者,疾病初期即表现为湿热证。张伯礼[4]将该病的基本病机概括为疫毒外侵、肺经受邪、正气亏虚,病理性质涉及湿、热(寒)、毒、虚、瘀,病位主要在肺,其次伴有胃肠道症状,危重期多见多脏器损伤。叶放等[5]提出该病属瘟毒上受,湿困表里,肺胃同病为基本病机,病机传变因人而异,多兼夹复合。过建春等[6]提出COVID-19 的中医病名为“肺疫”,该病病因是寒、湿、热、毒等不同属性病邪,初起核心病机是外邪郁肺困脾,病变过程存在热(火)、寒、湿、毒、痰、滞、结、瘀、燥、虚等病机变化。
综上所述,大多中医学者均将该病归属为疫邪致病,病性与“湿”关联,病位主要在肺,故根据病机其治法应以“祛湿、化湿”为主,具体应在辨证的基础上拟相应的治法。
2 中医治疗COVID-19
2.1 中医基础理论 唐凌等[7]从“肺与大肠相表里”角度探讨肺肠同治在重型COVID-19 中的临床意义,认为胃肠道症状是除呼吸道症状外的又一主要表现,尤其在重症患者中,肺肠同治收效尤为明显。阐述了重症COVID-19 患者肺肠同治的合理性与可行性。总结出肺肠同治的代表方有承气汤类(包括大承气汤、小承气汤、调胃承气汤、宣白承气汤)、凉膈散、升降散等,可用于重型COVID-19 的治疗。舒劲等[8]认为COVID-19 的致病因素为“湿邪”,通过调理“后天之本”不仅可调节脏腑功能还可提高抵抗力,充分体现了中医治未病的思想。分期治疗COVID-19时选用恰当的化湿药,日常生活中要调畅情志避免七情失和,适度运动调和脏腑气血提高免疫力。杜宏波等[9]团队赴武汉疫区开展中医药临床救治,发现该病病变虽核心在肺,但肝脾在辨治中的作用对于改善预后亦有重要作用。用药当兼顾调肝安神,调护情绪,有利于病情恢复。肝郁脾虚应当作为COVID-19中医辨治上需要纳入考虑的重要病机,注重肝脾的调理,或是提高疗效及防止复发的另一个切入点。蒋凡等[10]认为伴随疫情蔓延的还有感染者内心的焦虑、恐惧等不良情绪,会引起脾肾功能失常,导致水湿代谢失常,及时介入中医情志疗法来消除紧张、恐慌等不良情绪,可以增强“正气”,保持“精神内守,病安从来”的状态。可融入中医情志疗法,主要包括情志相胜法、移情易性法、中医认知疗法、中医行为疗法、五行音乐疗法等。周洪立等[11]认为中医“治未病”思想的核心内涵为“未病先防、已病防传、瘥后防复”,适用于传染病防治的各个阶段。
2.2 中医“三因制宜”治疗体现 杨华升等[12]通过分析北京佑安医院COVID-19 患者的临床资料,探讨北京地区COVID-19 患者的中医证候特点和发病机制,认为北京地区COVID-19 患者的中医病性为“湿热证”,“热重于湿”更多见。中医药治疗COVID-19要本着“三因治宜”的原则进行辨证论治。魏本君等[13]通过对甘肃COVID-19 临床诊疗及治疗规律的总结,认为COVID-19 在不同地区、不同患者群有不同的临床表现和中医证候群,发现其病机变化多端,并以三焦辨证为基础进行辨证治疗,总结出COVID-19有常有变,湿邪贯穿于始终,建议在常规治疗基础上,需注意辨证的治疗。张侠等[14]认为南京地区COVID-19 初步分析以湿困肺卫证为主,病理因素与湿、热、毒、虚相关,湿毒是其病理核心。徐旭等[15]分析湖北省武汉市COVID-19 疫情蔓延后各地区发布的中医药预防方案,探究其规律,认为北方8 个地区多使用麦冬、玄参等滋阴润燥中药,南方5 个地区多用苍术、藿香等芳香除湿中药,预防方案体现因地制宜的原则;根据人群体质不同采用不同处方,体现因人制宜的原则。根据不同气候、不同地区、不同人群辨证用药,重视综合预防,灵活运用各种措施,达到最佳预防效果。
2.3 经典方剂治疗 薛伯寿等[16]结合蒲辅周先生经验,总结此次疫情为寒湿疫,其治疗需善用麻黄剂。认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推荐在中西医结合救治COVID-19 中使用的清肺排毒汤,实为张仲景相关经方的融合创新运用,可为疫情防控和临床救治发挥重要作用。田野等[17]认为随着COVID-19 符合出院标准的患者逐日增多,恢复期的中医治疗应受到关注,发现气阴两虚证为恢复期的主要证候,生脉散为气阴两虚证的代表方剂,对其用于COVID-19 恢复期的可行性进行探讨,以期为患者恢复期中医治疗提供参考。苏捷等[18]结合荆门市中医医院专家组根据该病的病因病机特点,在全面考虑本地区天时气候、地域环境等因素的基础上,认为“十味清瘟汤”集治未病、解疫毒、防传变、保胃气四法于一体,融伤寒治法与温病治则于一炉,具有益气固表,清泻肺热,燥湿健脾,扶正祛邪之功效,在荆门地区疫情前期发挥了重要的预防作用和部分治疗作用。
2.4 名老中医治疗经验 叶放等[5]根据周仲瑛教授多年抗疫经验,经过仔细斟酌,提出该病属瘟毒上受,湿困表里,肺胃同病为基本病机,进而拟定四期(初期、中期、重症期和恢复期)常见证辨治方案。周仲瑛认为COVID-19 病邪虽涉上、中二焦,甚或三焦,但总以肺为主,临证当审证求机,以化湿浊、开肺气为中心,用药不宜过重,当随证变法,方能取得更好的临床疗效。张巍岚等[19]通过整理邓铁涛治疗非典系列经验后,对比此次COVID-19 汲取部分诊疗经验,以探讨COVID-19 的中医诊疗思路,为后续的感染性肺炎中医治疗提供思路借鉴。
3 讨论
中医药在此次防治COVID-19 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各地区、众医家在防治COVID-19 中大多认为疫病多为湿邪所致,充分遵循中医基础理论,运用三因制宜实施辨证施治,指导临床更好地遣方组药。通过临床论证,中医药作为防治COVID-19 的重要干预手段,在“减轻发热症状、控制病情进展、减少激素用量、减轻并发症等方面具有疗效”[20]。
但是目前临床资料及实验数据均有限,中医防治理论还需进一步积累并深入研究。在中医药治疗COVID-19 的研究中,要注意发挥中医学整体治疗的优势,发挥中医治未病的思想,抓住病情由轻症转为危重症“关键点”,积极进行早期干预,提高临床治愈率,降低病死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