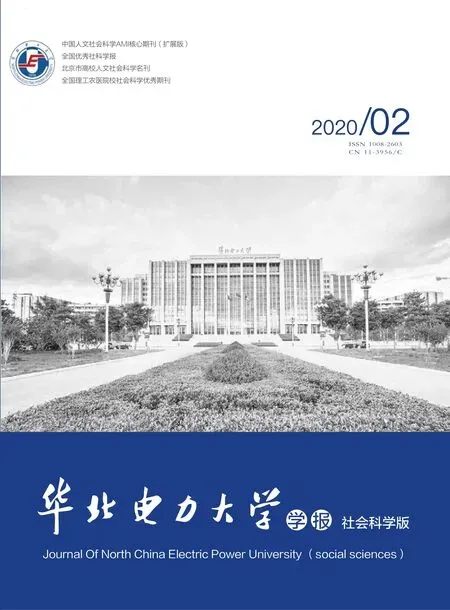“逸品”理论的形成与发展辨析
2020-01-07梁红燕
梁红燕
(华北电力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2206)
在中国艺术史上,尤其是在文人画传统中,“逸品”一直享有极其崇高的审美地位。从美学视角来看,“逸品”艺术是我国一笔巨大的文化遗产。它为我们构筑了一个永恒的审美意象—率性而不失法度、朴素而不乏韵味、洗练而不乏绚烂、唯美而不失德性的中国传统艺术范式。这种美一直引领着中国传统美学的审美方向;也成就了中国传统审美取向在世界美学史上的崇高地位。
一、“逸品”之“逸”的审美内涵
“逸”作为审美范畴,在中国传统美学的范畴发展史上有其非常独特之处。其本意是逃避、散开;作为形容词—开始是一个贬义词,即“逸豫”—形容好吃懒做。从历代艺术批评的资料来看,“逸”作为正式的审美范畴用于艺术品鉴是开始于东汉至魏晋期间,分别用于书法、绘画、诗歌领域的审美品鉴。
(一) 书法之“逸”
东汉时期,崔瑗在《草书势》中说,草书之审美特征与“逸”相契合:“草书之法,盖又简略;……观其法象,俯仰有仪,方不中矩,圆不副规。抑左扬右,兀若竦崎,兽跛鸟踌,志在飞移,……状似连珠,绝而不离,高怒怫郁,放逸生奇……若山蜂施毒,看隙缘巇;腾蛇赴穴,头没尾垂。是故远而望之,漼焉若注岸奔涯;就而察之,一画不可移。”(卫恒《四体书势》)也就是说草书的书写遵循“简略”的原则,“逸”就是“方不中矩,圆不副规”的风格,注重的是书法家的个性。
到了两晋之时,我国书法艺术进入首个巅峰时期,王羲之父子、钟繇、卫恒等人在书法艺术领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他们打破了秦汉以来朴茂方正的风格特征,代之以行云流水般的妍美飘逸风格。书法家就将“逸”作为书法创作中一种较高追求,王羲之要求“望之惟逸,发之惟静”(王羲之《记白云先生书诀》)。“逸”也已被用来评价书法作品的审美特质:“王羲之书,字势雄逸”(萧衍《古今书人优劣评》),孔琳之书“天然绝逸”(王僧虔《论书》)等。这些评论中已暗含了“逸”重视个性、简率的审美特征。
(二) 绘画之“逸”
魏晋的绘画理论著作中提到了两汉时期所倡的“出入离奇,纵横逸笔”(谢赫《古画品录》),在讲求以形写神、极重形似的基础上也强调了用笔的独创性。所以,曹衣出水,顾、陆入神的“放逸”画风是当时画家的宗趣。我国山水画起源于魏晋时期,但当时的山水绘画水平普遍不高,凸现出了这样一个矛盾,即绘画技巧跟不上艺术品鉴和艺术领悟能力。魏晋时期的山水画原作现在已然是看不着了,但在唐朝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卷一《论画山水树石》中有对魏晋山水画的描述:“魏、晋以降,名迹在人间者,皆见之矣。其画山水,则群峰之势,若钿饰犀栉,或水不容泛,或人大于山,率皆附以树石,映带其它,列植之状,则若伸臂布指。”说的就是魏晋山水画的技巧粗陋、画面布局并不好看:群山排列的就像梳齿一样,比例不协调;画中的人物树石都比山水要大,水中之人比例远远大于画中河流;树皆简单,树干就像人伸开的手臂,树枝或树叶就像五指张开……可见,当时山水画面空间感的效果并不好。这种画面效果与山水画的产生和主要创作群有关,一方面,山水画的最初形态是人物画的背景;另一方面,山水画的主要创作群多是“拟迹巢、由”的隐逸之士或喜寄情山水之人。他们普遍受过良好的文化教育,但并没有受过专业的绘画训练,如宗炳、王微。他们绘山水意在于卧榻“神游”;在加入绘画队伍之时就主动将自己与画工(多是人物画家)相区分,志在表达个体的思想情怀而忽视技巧性的构图等形式表征。这种创作风格一直延续到了唐宋时兴起的文人画,就发展为了对“人品”的重视,这也是后来“逸”发展为审美范畴时的核心内涵。
(三) 诗歌之“逸”
魏晋的文学批评可以说是我国艺术批评退去“比德说”而独立的开端。曹丕超越了“文以载道”、“诗言志”的文学评论取向,提出了“文以气为主”的观点。他把“人物品藻”中的个性美与文学作品联系起来,强调作品风格是受作家个性影响的,不可外力强求;主张文学作品是有个人风格的:“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曹丕《典论·论文》)在品评“建安七子”的作品时,就用“气”之不同来评价他们。如“徐干时有齐气”、“孔融体气高妙”等。在富有个性的“文气”中,他提出了“逸气”—“公干有逸气,但未遒耳。其五言诗之善者,妙绝时人”(曹丕《与吴质书》)。“公干”(即“建安七子”的刘桢)的文学作品风格就是“有逸气”,但略欠技巧、文体用辞不够精妙。后来的文学评论家们正是因为其文“有逸气”,给予了很高的品第地位。如曹植因刘桢诗有“逸气”给予了“妙绝时人”的极高评价。钟嵘也因此称赞刘桢“仗气爱奇,动多振绝,真骨凌霜,高风跨俗”(钟嵘《诗品上》),将其诗列为上品。
钟嵘褒扬了“逸气”作为人格美渗透到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美,所谓“逸气”就是指的作家超凡不俗的精神气质渗透到作品所表现出来的审美特征。对“逸气”的高扬似乎也预示了此后文人艺术的审美取向。在论及谢灵运和颜延之时,他也以主体人格之“逸”来评论诗作高低。认为“谢诗”源于曹植,掺杂有张协的诗风,“故尚巧饰;而逸荡过之(指张协)”(钟嵘《诗品上》)。以“虽乖秀逸,是经纶文雅才”(钟嵘《诗品中》)来评价颜延之,认为他违背了诗歌“秀美清逸”的原则。这也就是“谢诗”为上品、“颜诗”为中品的原因;这也证明了人格之“逸”对艺术之“逸”的影响。因为谢灵运本人极具隐逸人格,他率性自然,“好山水、肆意遨游”因而写诗时“内无乏思,外无遗物”。而颜延之则是拘于做应诏应制诗,在人格上就较谢灵运稍逊一筹。是故,“汤惠休曰:‘谢诗如芙蓉出水,颜如错彩镂金。’颜终身病之。”(钟嵘《诗品中》)此时,“逸”的艺术美特征已向“自然”靠近。钟嵘还把陶渊明奉为“隐逸诗人”之宗,说陶诗:“文体省静,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辞兴婉惬。每观其文,想其人德。世叹其质直。至如‘欢言醉春酒,’‘日暮天无云。’风华清靡,岂直为田家语耶!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也”(钟嵘《诗品中》),这对陶诗风格—“省静”、“真古”、“清靡”—的概括相当准确。
总之,魏晋之时,艺术品赏中已开始重视“逸”的风格和“清新简澹,闲适自然”的艺术境界。“逸”的审美涵义作为文学艺术品赏的一个范畴已有了初步的确立,并且作为一种审美标准在此后文人艺术中的地位日趋重要,促生了中国传统艺术批评理论相当重要的“逸品”理论。
二、“逸品”范畴的提出
我国最早的品第范本是前文提到的南朝钟嵘的《诗品》,他依照汉魏九品论人的模式分上、中、下三品来论诗的。同时期以“品”命名的理论著作还有庾肩吾的《书品》、谢赫的《画品》、沈约的《棋品》。唐代是各艺术理论研究的成熟期,相关论著达60 余种。其中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百科全书式的绘画通史—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第一部断代画史—朱景玄的《唐朝名画录》;第一部书法美学论著—孙过庭的《书谱》;继南朝钟嵘的《诗品》之后又一部伟大的诗歌美学论著—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等。[1]
唐朝的艺术创作就相当讲究“法度”,所以,魏晋时盛行的“逸”美风格在理论上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如唐朝书法艺术创作成就最高的就是极善“法度”的楷书而不是“损隶之规矩,纵任奔逸”的草书;即便草书也是极重视“法度”的。有“草圣”之称的张旭正是在极尊重“法度”的训练下技艺臻至完美,有了“意逸于笔”、“纵逸不羁”的狂草。又如皎然说谢灵运诗“真于性情,尚于作用”(皎然《诗式·文章宗旨》);即在强调“高、逸”之思的重要性时,他同样看重“尚于作用”的苦心经营、遣词造句。在他看来“不要苦思,苦思则丧自然之质”的看法是有偏颇的,指出:“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取境之时,须至难至险,始见奇句。成篇之后,观其气貌,有似等闲,不思而得,此高手也。有时意静神王,佳句纵横,若不可遏,宛如神助。不然,盖由先积精思,因神王而得乎。”(皎然《诗式·取境》)但是在书画批评领域,已有了重视创作主体精神品格、尤其是隐逸人格的表现主义倾向。
(一) “逸品”范畴的出现
唐代时,“逸”的理论地位虽还未明确化,还停留在人格、艺术美的“形容词”阶段,但皎然和司空图都已将之作为审美范畴来论述。皎然的《诗式》用“逸”标目,列于“高、逸、贞、忠、节、志、气、情、思、德、诫、闲、达、悲、怨、意、力、静、远”等十九字之中,并认为“高”、“逸”是其中最重要的:“夫诗人之思,初发取境偏高,则一首举体便高;取境偏逸,则一首举体便逸。”(皎然《诗式·辨体有一十九字》)司空图在皎然的基础上专注于谈诗的风格,著有《二十四诗品》,其中专有“飘逸”一格:“落落欲往,矫矫不群。缑山之鹤,华顶之云。高人画中,令色絪缊。御风蓬叶,泛彼无垠。如不可执,如将有闻。识者已领,期之愈分。”前四句写仙人独来独往,超迈不群;中四句写高人率性自然,随性而行;后四句写仙人逍遥于太空之中,飘忽不定。虽然在这“二十四品”中,司空图并没有分出主次,但他特别在“飘逸”一格强调了该品的主要审美特征就在于自然而无定规,在于与“道契”而与人力无关。
“逸品”范畴的正式出现是在初唐之时,书画家李嗣真首次以“逸品”之目品评画作。他的《画品》原作没有保留下来,无法找到对“逸品”画的确切论述;在存留下来的《后书品》中,以“逸品、上品、中品、下品”四品论书,且每品都有一段“赞语”。收入“逸品”的有李斯、张芝、钟繇、王羲之和王献之,有云:“赞曰:仓颉造字,鬼哭天廪;史籀湮灭,陈仓籍甚;秦相刻铭,烂若舒锦,钟、张、羲、献,超然逸品。”(李嗣真《书后品》)这五位杰出书法家,是中国书法体系中的典范;可见,李嗣真对“逸品”的定位是相当高的。
书画评论家张怀瓘在其著作《书断》中,以“神、妙、能”三品论书。虽没有“逸品”,但文章中多次以“逸”评论书法作品,且大都集中用于最高的“神品”,也有用于形容“妙品”的,但“能品”中却没有任何“逸”的审美特征。如他在评论钟繇、张芝、杜度、王羲之、王献之(此五人皆被目之于“神品”之列)的书法之高低时,写到:“若真书古雅,道合神明,则元常第一;若真行妍美,粉黛无施,则逸少第一;若章草古逸,极致高深,则伯度第一;若章则劲骨,天纵草则,变化无方,则伯英第一;其间备精诸体,唯独右军。”(张怀瓘《书断》)在主张五人书法各有自身优势时,指出“古逸”是草书最重要的品质。他在评论草书时,多次强调了“逸”之于草书的重要性,如:“存字之梗概,损隶之规矩,纵任奔逸,赴俗急就,因草创之义,谓之‘草书’”(张怀瓘《书断》)。还多次强调了“逸气”之于书法创作的重要性,如:“若逸气纵横,则羲谢于献;若簪裾礼乐,则献不继羲。”在评论各“神品”书法时常用“雄逸”、“宏逸”、“纵逸不羁”等语汇来形容。可见,张怀瓘虽然没有单列“逸品”范式,但李嗣真目之以“逸品”书法家全在其“神品”之目下,且将“逸”作为了“神品”的重要审美特征。
(二) “逸品”发展为正式的“美的范畴”
张彦远和朱景玄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专业绘画理论批评家。张彦远生活在李嗣真之后,他在品评绘画作品时,应该对李嗣真所列“逸品”有所了解;他将“自然”置于绘画的最高境界—“上品之上”,开启了宋元时代兴起的文人画创作的理论先河。他在评顾恺之画时说:“遍观众画,唯顾生画古贤,得其妙理,对之令人终日不倦。凝神遐想,妙悟自然。”(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后来,宋人黄休复就将“自然”作为“逸品”范畴的核心特征。之后,朱景玄在《唐朝名画录》单列“逸品”一格;他将王墨、张志和、李灵省三人归为“逸品”画家,并明确依据是他们“非画之本法,故目之为逸品,盖前古未有之法也。”(朱景玄《唐朝名画录》)他在中国美学史上第一次将“逸品”同其它各品一起论述,他以神、妙、能、逸分格,指出神、妙、能格之外“有不拘常法,又有逸品,以表其优劣也。”(朱景玄《唐朝名画录》)朱景玄虽没有对“逸品”作高下的比较,也没有给出明确的定义;但他已指出了“逸品”的本质特征:“‘逸品’多出于隐士或鄙弃功名富贵者之手,创作在于艺术之自由、自主,而非功利之营求;相应地也破除规矩法度之拘限,为获得更大的创作意兴,常借助于酒;不贵五彩而重水墨,尤以泼墨见长,随物赋彩,出于自然……而朱景玄将三位画家单独列出,实也看到绘画从礼教和宗教中独立,从皇室、贵族和寺院中走出来,就画而言是‘非常之体’,就画家而言是‘自得其趣’,这就是文人画的艺术精神。”[2]
唐朝的山水画在技巧上已远远超越了魏晋“水不容泛、人大于山”的粗陋,到了出神入化的境地。唐代绘画成就最高的是以吴道子、王维、张璪为代表的文人山水画。其中,张璪的“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创作心得更是成了后世文人画创作的标尺;开创了中国画“最高的画境,不是摹写对象,而是以自己的精神创造对象”[3]的时代。虽然,在尚“法度”的唐朝,“非画之本法”的“逸品”并没有得到推崇,但“逸”的美学理论在唐朝已基本成形,已初步明确了“逸”的“不拘常法”、“意逸于笔”的审美形式特质以及推崇隐逸人格的“人品”先行于“画品”等重视造境写意绘画风格的文人画倾向,奏响了宋代文人画理论成形和发展的号角。唐朝末年的画家孙位,以其“性情疏野,襟抱超然”,不尚礼义和“天纵其能”,创造出“情高格逸”(黄休复《益州名画录》)的画作,助推了追求超脱、冲淡、飘逸的画风,“畅神”、“写意”逐渐成为文人山水画的主旨。
宋初黄休复在其《益州名画录》中仅将孙位一人列入“逸格”:先强调了他的人品“性情疏野,襟抱超然。虽好饮酒,未曾沉酩。禅僧道士,常与往返。豪贵相请,礼有少慢,纵赠千金,难留一笔,唯好事者时得其画焉。”接着指出了其作品的特征:“人鬼相杂,矛戟鼓吹,纵横驰突,交加戛击,欲有声响。鹰犬之类,皆三五笔而成;弓弦斧柄之属,并掇笔而描,如从绳而正矣。其有龙拏水汹,千状万态,势欲飞动,松石墨竹,笔精墨妙,雄壮气象,莫可记述,非天纵其能,情高格逸,其孰能与于此邪?”黄休复《益州名画录》)。其“逸品”理论,延续了朱景玄以“四格”评画的形式,明确了“逸品”的地位,并首次在中国绘画批评理论史上将“逸”格置于“神”、“妙”、“能”三格之上,确定了“逸品”的基本审美范式:
“画之逸格,最难其俦,拙规矩于方圆,鄙精研于彩绘,笔简形具,得之自然,莫可楷模,出于意表,故目之曰逸格尔。”(黄休复《益州名画录》)
这一概述相当全面完整且有条理,对绘画技巧和创作者的人格要求都有明确的阐述,这种审美理论上的自觉也开启了宋人对“逸品”的推崇时代。如果说朱景玄的“逸品”论述只停留在绘画技巧层面的话,黄休复则将绘画艺术鉴赏从绘画技巧层面提升到了创作者的创作态度乃至“人品”层面;明确了“人品”决定了“艺品”的中国传统艺术审美原则。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黄休复的“逸品”理论并没有丝毫轻视绘画技巧的意思。首先,能收录于《益州名画录》的作品都是有相当艺术成就的作品,即“名画”。其次,看他给最后一品“能格”下的定义:“画有性周动植,学侔天功,乃至结岳融川,潜鳞翔羽,形象生动者,故目之曰能格尔。”要创作出“能品”,需要作者必须“性周动植,学侔天功”。只不过“逸品”界定强调的“得之自然,莫可楷模”,是不受技巧、规矩的羁绊,创作的重心在对“自然本性”的表现;但并未轻视构图、笔法技巧。否则,何来“龙拏水汹,千状万态,势欲飞动,松石墨竹,笔精墨妙,雄壮气象”般栩栩如生的画面效果?只是说明“逸品”画家有更高的形式质料驾驭能力,达到了“技进乎道”的水平;所以“画之逸格,最难其俦”。
南宋的邓椿在《画继》中说:“逸之高,岂得附于三品之末?”认同了黄休复将“逸格”置于诸品之上的品第标准。此后,“逸品”理论得到了中国传统艺术界尤其是文人艺术家的肯定和推崇,并积极将之付诸艺术实践,使得“逸品”理论成为中国文人艺术最高的审美标准和艺术指导。
三、“逸品”理论的完善与成熟
随着文人画创作进入鼎盛时期,元代的“逸品”理论也更趋成熟。被后人称为“逸品”画标杆画家的倪瓒提出了“不求形似”、“聊写胸中逸气”以“自娱”的重在“表现”的绘画美学观。他的“逸笔说”和“逸气论”将绘画中的“逸格”从品评艺术的审美风格上升为艺术的创造态度和艺术家的精神境界,还指出这是一般俗人无法企及的—“仆之所谓画者,不过逸笔草草,聊以自娱耳。近迂游来城邑,索画者必欲依彼所指授,又欲因时而得,鄙辱怒骂,无所不有。冤乎矣。讵可责僧人以不髯也!是亦仆自取之耶?”(倪瓒《答张仲藻书》)—是艺术家人格魅力的自然外现。这正是“逸格”意象“最难其俦”之所在。他的“逸气”说是两宋文人“画意不画形”、“忘形得意”审美情趣的发展和理论化;更是唐宋“逸品”理论的升华,其主旨在于淡化外在形式、技巧;而着重强调创作者的情绪表达和精神追求。这正是“逸”本原的回归—讲究个性自由、品格高尚。“逸品”风格非刻意所为能达到的,它是创作者本身修为的天成之作;也就是说,自如驾驭“逸笔”的是画家内在的精神境界—“逸气”。正所谓“逸笔纵横意到成,烧香弄翰了余生。窗前竹树以苔石,寒雨萧条待晚晴。”(倪瓒:《题画竹》)即倪瓒孤傲的性情与迫于生计不得不附媚于权贵或俗世而卖画的矛盾冲突的无奈,反映在作品中就是侵染其中的清冷与肃索!
所以,明代董其昌认为“元四家”之中只有倪瓒是“逸品”中人,清代石涛进一步强调了倪瓒的用笔和造境简淡的才能是无法模仿习得的。倪瓒的绘画美学思想对中国的文人艺术的发展起到了非常大的导向作用—绘画评价与创作都认同“人品”高于“画品”的审美导向—“学画者,先贵立品。立品之人,笔墨外自有一种正大光明之概;否则画虽可观,却有一种不正之气,隐跃毫端。文如其人,画亦有然。”(王昱《东庄论画》)明清两代画论家们除了呼应倪瓒的绘画美学思想,还进一步完善了“逸品”理论。
(一) “逸品”画发展为独立的流派
文人画有被区分为“逸家”和“作家”:“山水有二派,一为逸家,一为作家,又为之行家、隶家。逸家始自王维、毕宏、王洽、张璪、项容,其后荆浩、关仝、董源、巨然及燕肃、米芾、米友仁为其嫡派;自此绝传者几二百年,而后有元四大家黄公望、王蒙、倪瓒、吴镇远接源流;至吾朝沈周、文徵明能宗之。……作家自李思训、李昭道……至于兼逸与作之妙者,则范宽、郭熙、李公麟为之祖……”(詹景凤《跋饶自然〈山水家法〉》)该文论作者历数了自古以来属不同风格流派的画家,其中被目之于“逸家”的都是历代公认的文人画家,这就确立了“逸品”与文人艺术的关联性。“逸品”不再是某些画家的绘画风格,而是文人画派这一流派的整体绘画风格。
恽南田在黄休复的定义基础上,详细分析了“逸品”的风格特征。“逸品其意难言之矣,殆如卢敖之游太清,列子之御冷风也。其景则三闾大夫之江潭也,其笔墨如子龙之梨花枪,公孙大娘之剑器。人见其梨花龙翔,而不见其人与枪剑也。”(恽格《南田画跋》)他一方面从画史、笔墨、技巧等角度概括“逸品”的定义和特征,另一方面明确了“逸品”的本质不在于笔墨繁简,而在于人品的高逸。这对于绘画创作来说具有相当重要的指导意义—超越创作的外在形式表征,直指创作的内在本质蕴含。更难能可贵的是,他结合自己的创作实践,还将该理论上升到了哲学高度。他从道家哲学思想的高度指出“逸品”画尚“简”的特征在于主体的高逸之情,即画面的“简”完全是主体“技进乎道”的自然结果:“云林画天真澹简,一木一石自有千岩万壑之趣。今人遂以一木一石求云林,几失云林矣。”(恽格《南田画跋》)并阐明了“逸品”画作来自造化又胜于造化、有无相生的道家审美特征:“须知千树万树,无一笔是树。千山万山,无一笔是山。千笔万笔,无一笔是笔。有处恰是无,无处恰是有,所以为逸。”(恽格《南田画跋》)从“逸品”画的表现力方面与道家“有无相生”的哲学思想相联系,使理论从艺术批评层次上升到了哲学思考层面而趋于成熟。
(二) “逸品”理论的个性化分析和理论推广
唐志契有感于艺术创造的发展和绘画形式的多样化,对“逸”的诸多个性化范畴做了总结性的概括,指出“逸”是对“浊”、“俗”、“模棱卑鄙”的超越,又明确了“逸”是独立的审美范式区别于“奇”、“韵”等范畴:
盖逸有清逸,有雅逸、有俊逸、有隐逸、有沉逸。逸纵不同,从未有逸而浊,逸而俗,逸而模棱卑鄙者。以此想之,则逸之变态能尽矣。逸虽近于奇,而实非有意为奇,虽不离于韵,而更有迈于韵。(唐志契《绘事微言》)
石涛指出倪瓒的“人品”渗透到作品中,表现出的“画品”;连他自己也只能习得皮毛。他给“逸品”理论作出总结陈词:
唐画,神品也;宋元之画,逸品也。神品者多,而逸品者少。后世学者千般各投所识。古人从神品中悟得逸品;今人从逸品中转出时品,意求过人,而穷无过人处。吾不知此理何故。岂非文章翰墨一代有一代之神理,天地万类各有种子,而神品终归于神品之人,逸品必还逸品之士,时品则自不相类也。若无荆关之手,又何敢拈弄笔墨,徒苦劳耳。[4]
这一陈述极具现代性,从艺术的个性和时代相关性的角度强调只有宋元之画才是“逸品”!明确了“逸品”画作的实体范本。
黄钺有仿司空图而作的《二十四画品》。其中,专有一品为“澹逸”,云:“白云在空,好风不收。瑶琴罢挥,寒漪细流。偶尔坐对,啸歌悠悠。遇简以静,若疾乍廖。望之心移,即之消忧。于诗为陶,于时为秋。”就像每一理论成熟都要经历“正、反、合”的辩证过程一样,黄钺列出的“澹逸”一品又回归了魏晋人格美品赏中将“逸”作为对隐士人格美的界定。属于“澹逸”一品的绘画作品就像陶渊明的诗和四时之秋一样:清新、自然、悠远、简洁;欣赏这样的画作能使人心旷神怡、淡泊宁静。
至此,经历恽南田的升华、石涛的总结、黄钺的回归,“逸品”理论发展成为了中国艺术批评史上的重要理论成果;“逸品”艺术创作成为了文人追求自由的道路;从而成就了独具中国文化魅力的文人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