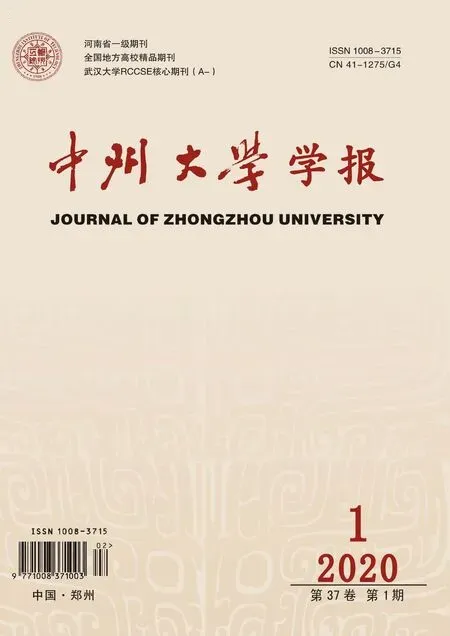记忆的动机、途径与伦理
——从《十七岁》到《模糊》
2020-01-07张翼
张 翼
(河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7)
田中禾是个现实感十足的作家,他擅长从纷繁的现象中抽取关键问题,代表作《五月》《枸桃树》直击农村改革中存在的“卖粮难”“资源短缺”“青年出路”等诸多实际问题,通过现实问题的探讨向人情、人性的深处掘进。田中禾也是一个关注记忆的作家,在直面现实的同时,他不断追忆个人的往昔与历史的过往,尤其是行至人生暮年,回忆逐渐成为作家创作的重心。从2011年的《十七岁》,到2013年的《父亲和她们》,直至新作《模糊》,田中禾沉浸于对亲人和往事的追怀。因为这些独特的个体的记忆追溯总与“历史”保持着微妙联系,在个人经历、经验的光影闪回中,一桩桩重大的社会历史“事件”,抗战、内战、建国、“反右”等等也纷至沓来、借机登场,历史因此成了以文字为载体、糅合诸多经验的“记忆”。
田中禾的记忆书写事实上触及了新世纪非常重要的文学史、思想史命题,即面对20世纪中国这样一段容量丰富、脉络稠密的历史,文学是否有义务记住过去的人与事?又应通过什么样的路径来使严谨的历史记录成为有质感、有弹性的历史“记忆”?此外,由于在历史结构中的位置不同,不同的人对于同一历史的记忆存在差异,这种差异有时甚至是南辕北辙、相互抵牾的,那么又该如何认识、交流差异化的“记忆”?我们或许可以田中禾近十年的写作为切入口,打开对这一系列问题的思考。
一、记忆历史的冲动
文学与记忆的关联深刻细密,有作家曾经指出,文学本质而言就是记忆。如果以此解释田中禾近年来的写作与记忆的缱绻,也是有效的。但这一常识性答案可以解释田中禾为什么写记忆,却不足以阐释他的记忆及记忆书写的特征,无法回答他何以反复记忆某些东西却并没有记住另外一些东西,何以某个人、某桩事、某段历史在他的记忆中是如此这般而非其他模样。记忆的成型受到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其中记忆之所以发生的动机至关重要。动机触发了回溯,特定的动机从最初就已经决定了记忆的独特走向与特殊纹理。
田中禾的频频回首源于个人的情感伤痛。他在长篇小说《十七岁》中以日记为序言,解释了为什么要写这样一部追怀之作,那是因为:“此时此刻我才明白,从此以后我要独立承受人世降临的一切,我真的要做大人了。在甲子年二月初七这天之前,我并不知道人世究竟是什么。母亲离开我的时候世界还像往日一样,可我知道往日已经不复存在。”[1]1亲人的离去成为个人生活史中的一个转折点,构成了生命观念的断裂,“我”的记忆之门由痛苦而开启。痛楚将离去的一切推向笔端,通过一遍遍重现往昔、回味过去,作家的写作事实上也是情感的宣泄,他自觉或是不自觉地以移情的方式抚慰自身的情感重创。正如《父亲和她们》中的“我”所言,“让自己在述说中得到安慰”[2]4。不得不面对的告别,也使作家较之常人对正在流逝的、不可挽留的诸种人事更为敏感。同时,相对于变动不居的现在和难以预测的未来,过往即便再多繁乱也已是固定了的,它总能使人经由怀想寻找到安适感、意义感,这就是为什么“过去的一切终将是美好的”,也是所谓的“诗意的栖息地”因何而生。田中禾之所以一再书写记忆,或许也可循此心理线索找到答案。因情感创伤而开启的记忆总是细节饱满、情绪充沛,也常常因物是人非、流逝不止流露出沧桑感慨,并隐隐掺杂着时不我待的内在紧张感。
除了情感的因素之外,对现实的困惑、不适也督促作家有意识地追根溯源,追问来路,通过审视来路辨析“现在”如何成为“现在”,思考“现在”应该成为怎样的“现在”。简而言之,所有向过去的回望都关联着尖锐的“现在”的问题。田中禾在新作《模糊》中,有意识地安排两个叙事者讲述二哥张书铭的故事,其中“我”作为主要的叙事者,把握全文的叙述基调。两次叙述的起初,“我”都会特意向读者说明,之所以执意回顾并不愉快的过去,是希望借此与现实中的缺陷形成对抗。“当金钱、享乐成为时代主流,人们忙于赚钱、忙于购物、忙于旅游、忙于性享受,沉醉于花花世界的时候,谁愿意陪你为陈年旧事感叹,被过往的伤痛扫兴,耽搁了当下的快乐时光?”[3]110“忧伤是人类情感中高贵的情愫,我不敢滥用它。在这物欲横流、追求金钱享乐的时代,忧伤非但不合时宜,还会被人讥为有病。”[3]184两段表述虽然存在反问与陈述的语气差异,但内在的逻辑却保持一致,都是要构筑过去——现在、记忆——遗忘、忧伤——享乐、沉重——轻松的落差张力,以此表达了自己的价值判断和立场倾向,是要以记忆对抗遗忘,以沉重质疑轻松,以伤痛警醒快乐。作者借叙事者激烈地发声,有力地展示出作者介入现实、探索历史的意志力,使读者感受到写作者内在的使命感。正是因为使命感的贯穿,文本中情绪的经验的个人回忆,繁复却并不破碎,伤感却并不空泛,它们仍是有质感、有深度的文化记忆。
作家个人的情感与责任,驱动其创作不断回望往昔、书写记忆,这为作家的记忆刻下了鲜明的个人标识。同时也应注意到,记忆的产生既源于个体的情绪与体验,也潜在地受到时代语境、文学传统的影响与规约。田中禾寻找自己的方式,书写个人的记忆,但他始终作为历史的亲历者处于特定的历史结构之中,作为写作者处于中国文学尤其是当代文学的传统之中,某些既定的机制、规律注定会对他的记忆有所触动,也有所示范。以文学传统为例,中国文学中向来就有非常强烈的史传传统,这促使中国的写作者回顾过去时总是不由自主地以“历史”为鹄的。当代文学在历史书写方面的积累也十分丰厚。十七年文学致力于革命历史合法性的叙述,新时期文学对共和国历史的反思,90年代以个体、欲望解构宏大历史观念等等,近年来逐渐形成了以个人史写大历史的写作趋势。纵观田中禾近十年来关于记忆的思考和书写,发现他也在这样的思想延长线上与文学脉络之中。
二、历史如何成为记忆
人生活在“历史”之中,也以自己的方式叙述“历史”,但人对“历史”的叙述并不完全受制于“历史”本身,或者可以这么说,人叙述“历史”的过程本身就是“历史”的一部分。叙述历史的方法有很多种,文学之所以能够成为其中一种,并不取决于它对“历史”的拓印,而在于它对“历史”的再认识、再创造,即遵循文学特有的逻辑与方法,以情感之维、思想之维对事件、史实进行重新观照,如此才能变记录为“记忆”,丰富并超越历史。文学记忆历史不存在绝对完美的方法,各种方法的优点与缺陷也几乎是显而易见的。以下将主要从特征的角度出发,探讨田中禾通过自身的创作实践,把历史记录转换为文学“记忆”,于此提供了哪些路径,并尝试指出这些方法具体的功能。
其一是以细节恢复历史实感。田中禾的记忆伴随着20世纪中国的诸多重大社会历史事件,作者并没有采取正面强攻的方式去写时代风云的变幻,多沉潜在日常生活的细处、深处,以细节还原历史现场,以细节展现历史运行的细密轨迹与隐秘褶皱。《十七岁》对乡间生活的描绘,既注重审美意义上的细腻描写,以场院旁飞扬着的雾一般的蜢虫,池塘里小树与灌木的倒影,从林子里飞奔而出的肥大的黄狗,黄狗滴着口水的热乎乎的舌头,石碾上密布着的星星点点的麻坑等渲染田园风光;也选取具有时代标志的细节,如土地上铁轮车的辙印,洗脸用的铁面盆与家织布方巾,疗伤用的墨鱼骨等等为田园生活烙下旧日的标记,提醒读者这田园、乡村的时代属性。与此相似,《模糊》中章明所穿的“苏联花布衬衫”“毛料中山装”,所使用的“蘸笔”,所读的路翎的《洼地上的战役》、屠格涅夫的《初恋》,假日里所去的工人俱乐部、舞会等等,共同营造出建国初期特有的生活景观与时代精神氛围。
除了描绘可触可观的生活景观细节,作者还把握到了语言作为细节所凸显历史的阶段性特征,并由此展示历史更迭对人们日常生活的根本性改造。谈及20世纪的中国,无法回避绵延不绝的战争——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捻军起义,20世纪初的军阀混战,三四十年代的抗日战争,40年代中后期的国内革命战争,50年代初期的抗美援朝战争,在田中禾的创作中都有涉及。频繁的战争,使人们无法安守家园,四处流散,躲避战乱成为生活常态,人们为此特意启用了一个新词“跑反”。作者在文本中写过战争中尸横遍野,也描述日本军机轰炸中国平民的惨烈场面,然而当他抓住人们的语言系统中出现了“跑反”并将之熟练地运用于交流的时候,才真正剥出了战争的残酷,将战争对人的生存、精神的渗透控制全息式地推至读者眼前。长篇新作《模糊》中,“下放”“审查”“材料”“检查”“批判”等词汇,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广泛辐射,同样起到了构筑历史实感的作用。
其二是以经验丰盈历史维度。由于细节的灌注,历史不再仅仅是遥远的过去事件、抽象的宏大规律,而是有实感的,可触摸的。又由于细节往往建立在个体独特的感受和经验之上,因此数量庞大、类型庞杂的经验也得以汇入有关历史的记忆之中。各种经验从各自的角度、立场出发,叙述自己对于过去的印象与感觉。在被不同角度、不同立场反复描述之后,历史不再是单一的、平面的,而成为多维的、立体的。《十七岁》通过叙事时间的横纵组合,将经验化这一方法发挥至极致。文本的叙事时间既没有以历史的物理时间为序,也没有单独地围绕某一个个体的成长经历推进,而是巧妙地将“十七岁”设为时间节点,通过讲述母亲、大姐、六姐、大哥、二哥,以及“我”的“十七岁”,以点阵的方式在推动时间前进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保留了重大的社会历史事件与个体特殊成长经验的微妙关联。由于历史被不同的个体经验叙述、勾勒,它的演进不再是清晰的线索,而是交叉、重叠,它的不同侧面得以显现、打开。
譬如在如何认识战争的问题上,战争的残酷毋庸置疑,它随意掠夺人的生命,迫使人们不得不在跌宕起伏中艰难求生。但残酷、暴虐远非战争的全部,还有许多难言的悲欣交集。如“我”的家道因战局莫测而中落,却也因为同样的原因通过囤积食盐再次积累了财富。战争使人颠沛流离,但动荡也使原本坚固的礼教秩序有所松动,六姐与订婚对象因此有了接触的机会,二人逐渐建立起扎实的感情基础,避免了像大姐一样因包办婚姻不如意而抑郁身故的悲剧。战争是集体的罪恶,但罪恶的集体中也存在着无辜的个人。作品在铺陈日本兵残暴荒淫行径的同时,还从孩子的视角写一个爱和街坊邻居开玩笑的“老头太君”,在孩子的眼里他除了是日本人之外与众乡邻并无差别。“老头太君”的存在解释了——为什么当母亲目睹日本人战败撤退枪毙伤员时,几乎忘记了日本人是怎样毁了自己的生活与家园,对这些垂死之人表示出了同情而不是感到一朝雪耻,大快人心。经验的驳杂,立场的交错,帮助叙事者打开了探讨战争性质的众多角度与空间,战争不再只是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暴力对抗,也不仅只用来激发读者的憎恨、厌恶,它还蕴含着人性复杂、命运无常等等难解的命题,推动读者由此展开对自身与他人,个体与众人的深思。
其三是以想象补充历史留白。在田中禾的记忆书写中,时常出现另外一个词“想象”。如:“我想象着民国十二年的那一天,那似乎是一个很遥远的从前的日子……”[1]1“在我从小长大的过程中,老家经常诱发我的想象。我想象着在很早很早以前……”[1]2“以我的想象,父亲和母亲当年走过的路,应该是由伏牛山南麓逆汉水北上……”[2]25“对于我,库尔喀拉是一个牵系着半生惦记、诱发着我的想象的地方,在我的心底留下了不堪触碰的记忆。”[3]112虽然人们总强调记忆是对过去实有之事、实存之人的再现,但记忆实质上是想象之一种,或者说记忆就是幻象。过去的一切无法克服时间、空间的局限再次真实地发生,却可在人的头脑中、通过对所储存的既有形象进行再次加工,使前尘旧事得以复活。独特的想象机制决定了记忆是自由的,它不会被时空所局限,更不会被动地接受现实逻辑的解释,而是穿梭自如、自成体系的。
记忆的自由特质赋予它虚构的特权,使它以虚构填补“真相”“规律”无法笼罩的“历史”的留白与间隙。记忆之于历史的想象、虚构不单指填充真实发生过的历史的细节,还有可能弥补未曾发生过的历史的遗憾。概括地说,记忆在解释历史的已然、必然之外,也尝试解决历史的未然、或然。如《十七岁》中关于早逝的大姐的想象。大姐因包办婚姻不如所愿郁郁而终,生命永远停留在了十七岁。为了避免难过,她并不被家人经常提起,并且大姐去世时,我尚在襁褓之中,对她本应该没有太多印象,可是大姐却奇迹般地存活在了我的记忆之中。我对她的记忆远非印象,而在很大程度上是想象。在“我”的记忆里,她不仅笑颜如花、青春永驻,还在我的想象中不断成长——我常常在现实人生中寻找与她相似之人,也在脑海里为她假设种种不同的生活走向,推测她假若还活着将会在随后的时代风云中经历怎样的人生。关于大姐的记忆与想象是全书的精华所在,这段并不能够被“如实”所阐释的亦真亦幻、虚实相间的叙述,细腻而灵动,感人至深;也使对大姐的记忆得以漫漶为对这一代女性、这一类型女性的生存境遇和精神世界的描摹与思考。充分发挥记忆的想象与虚构这一具体的叙述行为,已经彰显了作者的历史观,他并不想一丝不苟地搬运历史,而是要对历史做出猜想性的解释。作家田中禾已经不仅仅是探索历史的规律,他还关心历史的诸多可能性。关于历史记忆中真实与虚构的微妙辩证,是一个可以无限阐释的话题,田中禾以自己的创作,对这一话题做出了精妙而独特的回答。
三、历史记忆的差异与融合
如果仅从记忆呈现的效果考量,《十七岁》已然显示了记忆书写所能够到达的高度,它所描述的历史记忆实感、质感与立体感兼备,个体经验与宏大历史交相辉映,文本情绪饱满、细节丰沛、叙事灵动。可如果从对记忆的本质思考来看,《模糊》却较《十七岁》更深一层。《模糊》仍述说往事,但呈现记忆、借记忆抒情怀旧、思考现实已经不是文本叙事的全部目的,文本围绕记忆所展开的叙事行为是技巧,更是一种观念——它要讲过去的故事,更要提取“记忆”本身,要将“记忆”拉到一定的高度对它进行审视和追问。这事实上已经深入到了记忆的伦理层面。
文本叙事结构的变化,体现了作者由记忆结果向记忆伦理的深入。和以前的作品相比,《模糊》在结构上有明显不同。
首先,叙事重心发生了转移,出现了由回忆过去到现实求证的转换。虽然如前所述,所有向过去的回望都包含着现实的、现在的需要,但此前田中禾的记忆书写基本是过去时态的,无论是《十七岁》还是《父亲和她们》的叙事都专注于讲述往事,而将“现在”作为讲述往事的背景,是为“过去”建立的叙述的角度。《模糊》的基本叙事结构却是“过去+现在”,且两者之间并非简单的叠加。它由两个故事构成,第一个故事是章明的故事,主要是他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经历;第二个是“我”对章明的原型——“我”的二哥张书铭的回忆与寻找,具体涉及“我”如何因神秘邮包唤醒被刻意封闭的记忆,如何将作为“记忆”的章明与“真实”的张书铭进行比照、阐释,又如何通过探访张书铭的旧迹、故人尝试解开他的失踪之谜,期间更遭遇了是否应该以过去的“记忆”打扰现实生活秩序的问题。虽然从篇幅来看,章明的故事占据了整部小说的三分之二,但这一段“过去”却被有意识地处理成“戏中戏”“书中书”,使它嵌套在“我”的现实行动之中,章明的“过去”故事始终被“我”的“现在”行动所统摄。同时,还应该注意,章明的故事虽曲折坎坷,但对于读者而言,由于既有阅读经验的影响,并没有构成“陌生”的惊异感。章明遭遇种种不公,成为右派的故事,事实上在《黑骏马》《绿化树》等小说中已经有了成熟的叙事形态,其中的常见元素在《模糊》的“书中书”里都有所体现,比如章明的英俊潇洒、谈吐不俗、不凡见识等等都吻合此类型作品中卡里斯玛式的主人公设定。再如章明在社会生活中的浮沉总伴随着私人领域中的爱情、婚姻的分合,也遵循这类小说以爱情、情爱等私人情感解说时代风云、社会事功的叙述模式。相较而言,“我”的现实寻找篇幅虽然不长,但对于读者而言却是陌生的、难解的,尤其是其中头绪庞杂,歧义丛生,给读者造成困惑,也吸引他们思考有关记忆的一系列问题。借助“过去+现在”的叙事结构,并通过“过去”“现在”的比重差异,作品将叙事重心放置在“我”如何在当下的语境中处置过去的“记忆”,而不是“我”通过回顾过往看到了什么。“现在”在这样的结构安排中脱颖而出,不再是背景或者角度。
其次,叙事立场出现位移,出现了由推崇往事正义到向辨析记忆话语结构的过渡。在之前的创作中,“往事”占据天然优势,感伤含混也美好难忘,是情感所系,是探索历史的思想沉积层;但在《模糊》中,作者对待“过去”的态度已经有所保留。他已经意识到了“记忆”,尤其是文学的“记忆”是被叙述的。这同样可以从“戏中戏”“书中书”的结构安排里得到展示。虽然作为主要叙事人的“我”,在讲述故事的过程中,一再强调“过去”之于现在的重要性,但作品并没有采取线性的叙事方式,由过去写到现在;也没有按照作家之前的叙事习惯,由过去的某一个时间发散开来;而是将过去与现在通过“戏中戏”“书中书”的结构设置,放置在了两个不同的叙事层级上,有意识地使之在叙述立场上表现出分裂。“戏中戏”往往与主线构成互文,发挥对主线故事进行提示、解释、类比、渲染等功能,但这也使戏中之戏多是主线故事的衍生物。具体到《模糊》中的“书中书”来看,章明的“过去”事实上是被多次叙述的对象。在神秘的书稿里,它被叙事者用第三人称叙述了一次,而这本书又是以被“我”阅读的方式呈现出来的,因此它还同时被“我”进行了第二次叙述。双重叙述使章明与“过去”成为叙述中的叙述,是被叙述的对象的对象。“过去”的自我叙述能力较之此前已经明显减弱。“戏中戏”的另一个功能是制造间离,提示读者文本中所有的戏剧性冲突及由此所构成的故事是被叙述出来的,它实际上是由叙述背后的话语及话语结构决定的。饶有意味的是,这部“书中书”的作者是匿名的,书也并无题名,是“无名作者的无名书稿”,由“英雄”到“无名”的转换,稀释了“书中书”浓郁的悲情和理想的情调。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书中书”是个未竟的故事,停止于章明恢复工作。《模糊》的后半部分,“我”的一系列行为,虽强调是想寻找二哥的下落,解开二哥失踪之谜,但事实上通过真实人物与虚构形象的对照、真实档案的呈现、故人访谈的引入等多种形式,文本真正完成的是对章明故事的修正。在这个过程中,诸多与二哥有关联的人物纷纷讲述了自己对他以及那个时代的感受,章明这一苦难英雄、落难才子的形象,逐渐被二哥鲜活却也复杂的面貌所模糊。
《模糊》之所以将叙述重心由过去转向现在,将叙述立场由推崇过去正义转向辨析记忆话语结构,是因为作者发现记忆是什么固然重要,但记忆本身尤其是如何处置“记忆”及如何对待“记忆”的差异也已经迫在眉睫。
在小说的后半部分,对“现在”的寻找中,“我”遭遇了一系列有关“记忆”伦理的问题。首先是“小说里的事儿,能当真吗”[3]186,即记忆的真实性问题。对此,文本中的“我”寻找记忆、尝试解开谜团的执着,以及作者写作的行为本身,已经做出了回答。真实并非记忆的唯一要义,记忆之所以生成更多地在于给人提供情感慰藉。在真实性问题之后,“我”马上遭遇了记忆的差异化问题,这个问题对“我”造成的困扰,远超记忆的真实性问题。文本中叙述了这样一个场面,在安葬母亲、为父母合坟的时候,父亲的骨殖因种种原因散乱不全,众人都小心翼翼予以回避,可是二哥却捧着父亲的一颗牙齿放声痛哭,让众人陷入尴尬之中,引来我的伤心与埋怨。这个场面既写实也充满隐喻的意味,它实际上指出记忆更多是个体的。正如同为儿女,如何缅怀逝去的父母,存在巨大差异一样。事件之所以能够成为记忆,依赖的是人与事件之间的个人性联系。人可以共享记忆,但未必有完全一致的共同记忆;并且,共享记忆也远远不是诸多个人记忆的简单组合,而是重叠、交错、抵牾的,是盘根错节的。对于同一事件的记忆,并不取决于事件本身,而取决于人们对事件的阐释。
在明确了记忆因个人性而存在差异的事实之后,文本很快提出另外一个问题——假如记忆没有达成共识,那么是否存在一种记忆优先于其他记忆?又该如何处理各种记忆之间的差异?在“我”的寻找过程中,“我”找到了二哥的两个女儿,在“我”看来,她们是二哥的孩子,是“我”的亲人,理应知晓自己的血缘。而二哥的两个女儿,一个对二哥还有稀薄的印象,愿意相认;另一个却因为当时年幼,已经完全遗忘了二哥,不愿意被打扰。认还是不认,这是文本中人物的困境,也是作者面对存在巨大差异的“记忆”时的困惑与焦虑。这个情节也同样充满了隐喻。
因个体所处具体语境的差异,即便对同一人、同一事的记忆,也存在着精度与强度上的巨大差别。当记忆有冲突之时,到底应该如何取舍?差异化的记忆是否存在融合的可能?又该如何融合?虽然文本中因亲情,三个亲人终于得以团聚相认,然而这一解决方案又在多大程度上是作者充满善意的假想?文本中的多个情节都涉及记忆的竞争与冲突的问题,比如二嫂李春梅与二哥,薛兰英与二哥,赵苑民与二哥等等。这些冲突较之上述情节不那么具有戏剧性,却更难解,亲情、人性显然难以完全将之解释清楚、处置得当。这些未解的难题恰恰是《模糊》的可贵之处。
四、结语
正如俄罗斯小说家希什金曾就记忆、语言与文学所做的思考,当记忆不再是记忆,语言不再是语言,小说就诞生了。记忆书写中的种种问题迷人也难解,从《十七岁》到《模糊》,田中禾有效地变历史记录为历史“记忆”,并有意识地由记忆呈现深入至记忆伦理的探索,他的创作为中国当代文学如何书写记忆提供了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