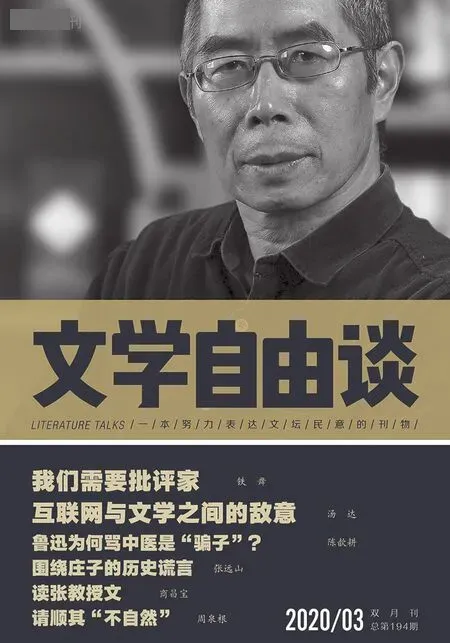欧美文学中的疯女人
2020-01-02刘世芬
□刘世芬
读《简·爱》,无疑是多年以前的事了。不知从何时起,我的书房里又多了几本这样的书:先有简·里斯的《藻海无边》,后是D.M.托马斯的《夏洛特——简·爱的最后旅程》,这两本书都和囚禁在桑菲尔德庄园阁楼里的那个疯女人伯莎·梅森有关。然后是美国两位女教师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古芭,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版的文学评论集《阁楼上的疯女人》,还有2016年国内出版的美国作家弗吉尼亚·安德鲁斯的《阁楼里的女孩》……由此而观,欧美文学及其作家身边的各类疯女人,自成“风景”。
伯莎·梅森自然属于这类最为典型的文学形象。《巴黎圣母院》中的隐修女,《法国中尉的女人》中的莎拉,《月亮与六便士》中的勃朗什,也“疯”度不低。除此而言,现实生活中的许多著名作家、艺术家身边,也不乏疯女人:雨果的小女儿小阿黛儿、罗丹的情人卡米尔、加缪的母亲卡特丽娜,以及海明威、塞林格身边的诸多女人,她们多次出现在各类版本的作家传记中。无论哪一种情形,在大部分读者的心目中,疯女人得到了太多同情、怜惜、悲悯,同时也引发了对人性的深思。而对于那些天才男人,她们何尝不是一种天然养料,成为文豪成长路上不可或缺因素,也可以说,她们撑起了欧美文学的一缕天空。
幽禁在桑菲尔德庄园顶楼里的疯女人伯莎——《简·爱》中男主人公罗切斯特的前妻,虽着墨不多,却令人印象深刻。我们始终没能看到伯莎的面容,而是通过四个场景记住了她,并对这个疯女人产生强烈的好奇心。
伯莎的第一次出现,是在简·爱到桑菲尔德庄园任家庭教师后的某天半夜。她躺在床上,忽然听到可怕的响动,接着传来“魔鬼的笑声”,更为恐怖的是,当她走出房门发现罗切斯特的房间失火,她救了他,他却对那骇人的笑声和纵火人讳莫如深。显然,谁发出的魔鬼般的笑声?门外是谁的脚印?为什么在她来后,要特意做一扇门把通往阁楼的楼梯口锁起来?阁楼里有什么秘密?谁在罗切斯特屋里放火?这些很难再让读者平静。
后来,又在半夜时分,阁楼里不但传出“狂野、刺耳、尖锐”的声音,而且还听到一场殊死搏斗。直到罗切斯特请求简帮忙,为一个访客理查·梅森包扎伤口,她这才大致看到一团模糊的“似人非人又类似动物”的影子。显然,这就是那个变形甚至变了态的疯女人。至此,疯女人虽未露面,其形象已呼之欲出。
疯女人的第三次登场是在简与罗切斯特婚礼的前夜,她干脆直接来到简的房间:“又高又大,又多又黑的头发长长地顺着她的背披下来,不知她穿着什么衣服,又白又直,可是究竟是长袍?是被单?还是裹尸布?”简直像个“魔鬼”。这个鬼“是紫的,嘴唇又肿又黑,额角上有深深的皱纹,宽阔的黑眉毛竖起在布满血丝的眼睛上”,把婚纱撕成两半,“灰黄的脸”把简吓昏过去。
直到婚礼现场,理查·梅森出示文件,证明十五年前罗切斯特在牙买加与伯莎结过婚,罗切斯特才不得不把众人带到阁楼,看到了那个似人非人的“淫荡的妻子”伯莎。罗切斯特终于证实伯莎是个“恶劣的野兽般的疯子”,“粗俗,陈腐,乖戾,低能,邪恶,淫荡”,可怕之极。
有人觉得夏落蒂·勃朗特对疯女人的刻画稍有不足,其实这恰恰为读者留下想象的空间。果然,《简·爱》出版近一个世纪后,出生于多米尼加首府罗素城的女作家简·里斯,被疯女人伯莎的形象鬼魂附体般日夜缠绕。简·里斯几代人生活在西印度群岛,直到十六岁到英国求学,后来嫁人辗转欧洲大陆。她对那片具有神秘色彩的土地的记忆,让她在写作《藻海无边》时驾轻就熟。对于那些具有历史烙印的名字:大屠杀村、白蟑螂、奴隶解放宪章等等,我曾在一部《美洲历史》中求证过,此间发生的殖民者对土著的残酷杀戮,白人、土著、混血、黑人之间的爱恨情仇,使疯女人这个角色有了合理的时代背景。1966年,简·里斯出版了以疯女人身世为主线的《藻海无边》。
这部十余万字的书,成为《简·爱》的前传——罗切斯特在马提尼克岛与伯莎相遇结婚。伯莎在这本书中叫“安托瓦内特”,而“伯莎”是她母亲的名字。母亲是马提尼克岛人,在整个加勒比海,“马提尼克”就是“疯”的代名词。母亲“竟想杀死自己的丈夫”而被关起来折磨至死。那时安托瓦内特尚未成年,她先是被送去修道院,后被同父异母的哥哥嫁给一个英国贵族,即《简·爱》中的罗切斯特。但二人各怀心境,并无爱情。婚后,罗切斯特从当地土著那里得到许多安托瓦内特“疯”的暗示,比如她经常对着一轮满月整夜欣赏,而西方人认为,人的发疯受月光的影响,因而她的佣人(通巫术)痛斥她“满月时分睡在月光下很不吉利”……罗切斯特就在这诸多暗示和“意念”中把安托瓦内特逼疯,强行让安托瓦内特成为“伯莎”,并粗暴地带回英国,囚禁在桑菲尔德庄园顶楼。
《夏洛特——简·爱的最后旅程》是《简·爱》的“续篇”。在这本同样十余万字的书中,简和罗切斯特并未过上王子公主般的幸福生活,他们婚后并不和谐。罗切斯特因“怀念”疯妻子,经常去找伯莎当时的女佣格蕾斯·普尔,格蕾斯掌握着伯莎与罗切斯特的所有秘密。当罗切斯特又一次去找格蕾斯时,不幸坠马身亡,简绝望地走向池塘意欲自杀时,格蕾斯救了她,并向简出示了一张伯莎生前相赠的照片:一个白种女人抱着一个黑人男孩,即伯莎与罗切斯特留在马提尼克岛的儿子梅森·马雷沙尔·内伊。
伯莎的祖母曾因与家庭对抗,有过一个黑人情人。因为隐性遗传,黑人基因“显性”到伯莎的孩子内伊身上。成为孤儿的内伊被一位神父收养,神父给了他“良好教育”,却让他八岁时变为自己的娈童。内伊伺机逃脱,四处流浪。这时绝望中的简,因遗产问题约格蕾斯一起去马提尼克岛寻找内伊。二十三岁的内伊已经长成一个健壮英俊的大男孩,他竟向简求婚,以欲弥补父亲对简的过失。二人在风光旖旎的岛屿别墅成为神仙眷侣,一直到简感染风热病离世。
相较之下,这本书“续”得极为蹩脚,使用了不太顺畅的“穿越”手法——从书的中部开始,简是以“鬼魂”出现的。人物散乱,人称混乱,加之荒诞、离奇的情节,显得狗尾续貂。
多年前,我买过一套上下册的《阁楼上的疯女人》。这套书出版于1974年,是作者桑德拉和苏珊二人在印弟安纳大学讲授一门女性文学课程的结晶。然而,不知是翻译缘故,还是我的知识障碍,阅读过程极为艰涩,其超乎想象的超长句式让我屡屡放弃。两位作者坦言,这套书的标题暗含了《简·爱》的有关内容,粗略阅读,才知《简·爱》占据着这套书的中心位置,她们为这部书加了副标题——“女性作家与十九世纪文学想象”。吸引我的,当然首先是“疯”,但这个副标题却给我汹涌的联想:“女性作家”一旦与“十九世纪”并列,这些名字是逃不掉的:勃朗特三姐妹,简·奥斯汀,艾米莉·狄金森,伍尔芙,普拉斯……蓦然发现,这些作家所处的地理位置、历史时间和心理环境,其实有着极为相近的气息:囚禁和逃跑的意象、身体不适的隐喻、女性的焦虑等等。作者对疯女人意象的开掘,聚焦在十九世纪女性作家身份的焦虑上。这时,蓦然回首,原来十九世纪的小说和诗歌中还有众多意象或隐喻,比如火与冰,月光,水,精灵,面纱,蜘蛛网、肺病等,都成为女性文学的混合体,而这又与“疯”这个意象有着藕断丝连的联结。除了被高度重复使用算是诸词之首的“疯”,还有洞穴、幽灵、恐怖、地狱、监禁、意识、漂泊、孤独、愤怒、狂暴、焦虑、率真、呼啸、火苗、呼喊、分裂、咆哮、哀伤、女巫……这些词语又集中指向——疯。疯的智慧意象,则是一颗颗不甘不屈的女性灵魂。那么一点疯魔,一点浪漫,一点不甘,一点向往,当然,托起它们的是汩汩不竭的文学智慧。
还有一种疯,属于那种“无害”的疯,无需囚禁的铁窗,但她们却终生处于一个黑暗失常的世界,并在那里承受着无尽的苦难。这类女人,不但值得同情,还令人五味杂陈,比如雨果的小女儿小阿黛尔和加缪的母亲卡特莉娜·加缪。
作为雨果的小女儿,父亲的声望本该使小阿黛尔成为快乐幸福的天使,然而这却是个不幸的女孩。少女时期父母已貌合神离,因而造成她孤僻古怪,郁郁寡欢,经常陷入自我幻想的泥潭。青年时期又随母亲来到泽西岛陪伴流亡的父亲。那个孤岛,可以是雨果的文学天堂,却成为本该求偶寻恋的小阿黛尔的地狱。为了给女儿营造一个良好的社交环境,母亲不惜与雨果吵翻也要离开泽西岛,雨果却置若罔闻。长此以往,小阿黛尔只能以音乐自慰。她神色忧郁,眼帘低垂,惶恐不安,掩藏着一个饱受痛苦煎熬的灵魂,幻想着不现实的爱情。
终于有一段时间,在雨果的访客中,有一个叫本松的英国中尉引起小阿黛尔的注意,她打算嫁给本松。但这时小阿黛尔已经有了幻象——觉得自己已经是本松的未婚妻。雨果大发雷霆,不允许她与法国之外的男子结婚。而这几乎把小阿黛尔逼到疯狂的境地。悲伤至极的小阿黛尔偷偷准备了行李,在母亲暂回巴黎的时候,一个人去了英国。其实本松并没在英国,而是随着军队去了加拿大。执拗的小阿黛尔一路狂追,她写信告诉父母,他们已经举行婚礼。雨果只得认可,还在报纸上公布了雨果小姐与本松中尉结婚并共赴加拿大的消息。雨果在给朋友的信中自豪地说:“我们这个家族将会是,岳父老迈苍苍,却代表未来;女婿少年英俊,却代表过去……”
而事实呢,这只不过是小阿黛尔的一厢情愿、精神臆想,本松从来就没想过要娶她。可怜的小阿黛尔发现本松已经结婚,甚至已做了父亲。雨果的小儿子弗朗索瓦找到小阿黛尔的房东,发现妹妹过着修道院一般的生活,孤苦伶仃,深居简出。她唯一的出行是到军营门口等待本松,尾随到家。她认为本松“背叛”了她,“侮辱”“抛弃”了她。雨果气得把本松叫作“野蛮的丘八”,但本松辩解,他“从未引发雨果小姐的痴情,从未向她求婚”。可小阿黛尔拒绝离开,她这时更接近了“疯”,臆想着与本松举行婚礼,朝思暮想着他的回归。久而久之,她成为全家一个令人不安的遥不可及的幽灵。后来本松调防巴巴多斯,小阿黛尔又尾随而去。她孤单一人,身无分文,陷入疯痴状态,最后被一个女黑人带回巴黎。滑稽的是,即使这个时候,雨果依然对女人来者不拒,声称只有写作和性事才能使他从梦幻中脱身,但小阿黛尔使他终生都带着隐痛:“我可怜的女儿,她比死人还要死……”直到雨果去世,小阿黛尔才被转到苏雷斯纳城堡,直到1915年八十五岁时去世。
加缪出生前,已有一个大他三岁的哥哥。1914年10月,加缪不满一岁,父亲吕西安在巴黎远郊马恩河战役中阵亡。这让加缪的母亲卡特莉娜受到强烈刺激,几近痴疯。她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回到阿尔及尔的娘家,家人注意到她的语言表达有些不顺畅,“面对生人时非常胆怯”。此外,她开始“失聪”“错乱”。在加缪眼里,外祖母桑代斯是个“粗暴、乖戾的女人”。外祖父早逝,一个舅舅还是残疾,显然加缪母子给外祖母带来了负担。为了更加严厉地管理着这个六口之家,外祖母用牛筋鞭子抽打加缪兄弟成为家常便饭,而卡特丽娜由于劳累和惧怕,又不能清楚地表达,只能呆呆地看着这一切。
对于母亲,加缪有一种特别复杂的情感,这在《第一人》《局外人》《堕落》中均有表达。初读《局外人》时,我对加缪笔下的母亲颇为不解;待读了《加缪传》,终于有些知晓了加缪和他母亲的既往。
《巴黎圣母院》中的隐修女是因为女儿的丢失而疯。
年轻的妓女花喜儿是一位美丽迷人的姑娘,至于她的美丽程度,书中虽未正面写出,但有了爱斯美拉达惊艳的美,母亲还能平平吗?花喜儿因丢失了襁褓中的女儿而崩溃,在绝望中皈依宗教,变成了石头般的隐修女。每当她听见婴儿的哭喊,才会从“石头”变成“活物”,从希望又转为绝望、悲恸。隐修女的疯,是命运的疯。十五年,这对一位失去孩子的母亲来说,每一天都会肝胆俱裂。一只小绣花鞋对她来说就是整个宇宙。为了这迷人的鞋,她曾经恶意地诅咒、深情地申诉、虔诚地祈祷、悲伤地哭泣……找到女儿,成为她活下去的唯一动力。当分隔了十五年的绣花鞋合而为一,这对苦难母女终于相认;而相认的结果却是她们共同赴死,雨果只能让她们在天国团聚。从年轻时的娇艳,到慈母的魅力,再到恐怖的、满头白发的隐修女,这是一个年老色衰的恐怖形象。
《法国中尉的女人》所处的十九世纪英国,是一个极富侵略性的国家,对内对外均无自由可谈。而地位卑贱的莎拉争取自由的过程,就是站到公众对面,成为“疯女人”。她从一开始就是“悲剧”的,“渔民们给她起了个下流绰号——法国中尉的……荡妇”,说她“有点神经错乱”。莎拉出身下层,受过一些教育,这使她“心比天高,身为下贱”,与她所处的时代和环境格格不入。但她不顾一切,我行我素,不愿离开莱姆镇,因而处处碰壁,陷入孤独。对于尚在摇摆的查尔斯,莎拉像个谜团。因为莎拉的存在,查尔斯一步步离开了贵族阶级,走上了孤独求索的道路。
意大利作家亚米契斯,在《卡尔美拉》里“拯救”了一个无辜的疯女子。在西西里附近的一座小岛驻扎着一支小分队,每三个月换防。当又一次换防后,年轻的新任中尉在回寓所的路上,他军服的下摆被人轻轻地拉扯了一下。那是一个身材苗条、容貌俊秀的姑娘,但衣着破烂,头发凌乱。她一动不动地,痴痴地,向他敬礼——她是半年前那一任中尉的女友。那个中尉信誓旦旦地保证三个月回来接她,姑娘信以为真,然而他却一去不返。可怜的姑娘病倒了,当她慢慢恢复了健康,却得知那中尉结婚的消息。她疯了……此任中尉对这个可怜的姑娘充满同情,他给了她爱情,更给了她新生。
塞林格说,长大是必经的溃烂。疯女人多体现出强烈的命运感,而她们相当部分的“疯”,是来自于男人。海明威、塞林格、巴尔扎克、莫泊桑们,身边总是不乏高颜值高智商高才艺的女人,而这些女人又因爱慕才华男人,几乎无一例外地被男人的才华所灼伤。她们用自己的美艳、智慧甚至金钱,涵育着一个个光芒四射的男人,无怨无悔地充当了参天大树的养分。那些洒脱转身的名男人,留给她们的,除了疯,还有死。而“先走一步”的葛尔红是唯一的例外——她主动甩了滥情的海明威,算是个奇迹。
这个世界记住的,是《红与黑》《羊脂球》《永别了,武器》《麦田里的守望者》,是高更的《大溪地少女》,罗丹的《思想者》……关于情色,关于遗弃,关于疯掉的女人,统统都成为天才必备的养料。唯如此,最后的天才以及天才的创造才具有意义。至于罗丹的卡米尔、塞林格的克莱尔、海明威的玛莎以及福楼拜的路易丝、大仲马的卡特琳(女裁缝)……幸与不幸,最好自己评判——谁让天才遇到的不是别人,正是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