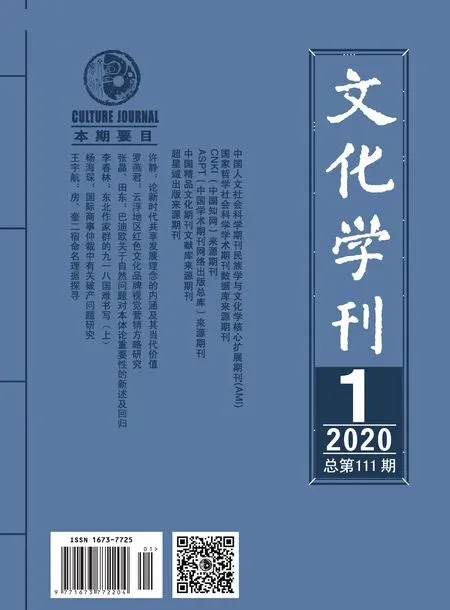“音声相和”与老子、孔子音乐观之比较
2020-01-02董玫
董 玫
老子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哲学家,他的哲学思想集中体现在五千字的《道德经》中,其中,涉及音乐的内容有四处:“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1]“乐与饵,过客止”[2]“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广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质真若渝,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3]“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4]。前两处从字面上看,老子对音乐形式持审慎甚至有些否定的态度。他认为,音乐会迷乱人心,使人们耽于短暂的感官享受而忘却对深远质朴的“道”的追寻;后两处字面上出现了“音”和“声”,仿佛老子就是在阐发他的音乐本体论。然,非也。
“听之不闻名曰希,不可得闻之音也。有声则有分,有分则不宫而商矣,分则不能统众,故有声者非大音也。”[5]“美者,人心之所进乐也;恶者,人心之所恶疾也。美恶犹喜怒也,善不善犹是非也。喜怒同根,是非同门,故不可得而偏举也。此六者,皆陈自然,不可偏举之数也。”[6]
这是王弼对老子《道德经》体现其音乐观四句中后两句的注释,第一句“大音希声”是指毋用听觉器官接收普遍意义上的艺术化音乐,这种音乐非大音也;第二句将六组对立相反的存在并列呈现,意在推出“不可得而偏举、不可偏举之数”。有无、难易、长短、高下、音声、前后既对立统一,又互相依存。不难看出,老子的音乐观是其哲学体系的一个部分,或者说是他哲学观阐释的一个切入点,是点与面、部分和整体的关系,不可割裂解读,要在整本书中把握其实质。反观四句中的前两句,也并非如字面表达那样,老子反对音乐、排斥音乐化生活。事实上,他反对的是“音”“色”与“欲”的结合,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具有表演性和展示性用来满足感官的存在形式而已。这种对音乐的认识角度是高屋建瓴的俯瞰视角,一如老子对其他天地万物的认识角度和思路,具有深邃的思辨、高度的概括,将具体的艺术形式以哲学化认知。老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也是最伟大的哲学家,他的认识论起点之高,为后世思想史的研究、中国文化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他的音乐观立论基础是音乐作为具体学科,除了实践性、技术性之外,更重要的当是美学标准和哲学内涵。
一、“音声相和”的逻辑展开和思辨精神
在对音乐认识论阐发之前,老子首先推出“音”和“声”这样一对概念。他将声音的存在形式二元分法,继而展开音声关系,得出自己的结论,一气呵成,逻辑严密,符合他整个哲学体系的辩证思维。音者,程式化、装饰化的艺术之声;声者,自化无为的自然之声所传递的道之声也。音、声概念的确立是老子音乐观的原点,以他一贯的辩证性、反推式思维脉络为轴线,形成其独特的音乐认识论:“音”发展到高级的“大音”则衍变为新的形态,即听之却不闻的“声”也(以心替代耳去感受);“音”只要以现实化呈现,无论多么高妙的演奏都会变成“五音”,迷乱人心,令人耳聋,令人沉迷于感官的满足。“声”,不能因为不闻否定其存在,我们可以借助对“音”的认识来初步感知它的存在,但真正能领会“声”,必须超越听觉器官,以“心”感知。也就是说,它所谓的无形是听者有限的听觉能力造成,并非自身属性的无形,不能因为耳朵听不到而否定其存在。若想感知其玄妙之境,前提是脱离“五音”(音乐的物质化),用心领会。由此,“音”与“声”的“和而不同”才是最高级、最可取的音乐认识论。
音乐的存在和发展遵循世间万物的普遍规律,即遵循“道”。“道”本身无形、无限,却无处不在。老子《道德经》第三十七章曰:“道常无为而无不为。”[7]老子认为,一切应顺乎自然之力自然而然地发展,不该有外力干涉,这样事物的发展才会呈现出本有的面目。这也进一步解释了老子“五音令人耳聋”的真正涵义,即艺术化、加工的音乐带有强烈的物质属性,会破坏声音的自然之美,将剥夺“音”成为“大音”的可能性。同时,他认为物质化音乐(经过人为加工并加以演奏的音乐)使听者在享受的过程中心生懈怠,耽于享受,背离“道”的自然精神。这种认识论立意高远,跳出了就事论事的狭义认识论,将对音乐的认识提升到哲学层面,符合老子的整体宇宙观和辩证精神。
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简史》中说道:“哲学就是对于人生的有系统的反思的思想。”[8]音乐观作为老子哲学体系的部分内容,同样折射出了强烈的反思精神。“反者道之动。”[9]一方面,事物总是朝对立面发展;另一方面,这种转化带来的是周而复始、推陈出新的过程。音乐亦遵循“道”的规律,“音”与“声”既相生相合,又互相发展。音乐若以“音”的形式出现并且仅限于该形式,这种音在老子看来不足取,不合乎道。通俗点讲,音乐一味追求形式之美,结果必然丧失音乐的本真。认识音乐,首先肯定“声”的存在,要超越外在的音响层面,追求音乐的内在核心。也就是说,先要确立“声”和“音”二者关系中,“声”是第一性,“音”是在“声”的基础上创作、依托于乐器(包括人声)演奏出的“非自然之声”。其次,在音乐表现的形式化过程中,将“声”看作音乐创作表现的原动力和审美标准,努力将道之“声”落实在“音”,不断追求“音声相和”,是音乐走向自由王国的必由之路,这样的音乐如生命般新陈交替,生生不息。实际上,“音声相和”的境界永无止境、周而复始,如对“道”的追求一样永远在路上,是体验的过程,而非结果。
二、“音声相和”的事实展开与“乐内礼外”之由来
“音声相和”音乐观对后世音乐思想的发展影响深广。继老子之说最高成就者当属庄子,庄子将前者的哲学体系进化完善,使其具体易行。较之老子的“音”“声”概念,庄子“天地有大美而不言”易理解体会。庄子之“大美”在这里近似老子之大音,即“声”,它们皆是“道”的体现。老子认为的音乐要无限追随“声”(道)的方向,这一点在后继者看来总是那么晦涩艰深形、难以领悟。而庄子切换了对“大音”“大美”的认识角度,以人的主观感觉“不言”来表达审美的主观能动性——“大音”“大美”不是“听而不闻”而是“听之不言”。前者强调主体自身属性,后者强调听者的主观感受。庄子依旧强调“和”的概念,他的“和”体现在人的“心斋”与“大美”“天道”极尽可能地靠近。可以这么说,庄子秉承老子“道”为万物之始的宇宙生发理论,但将“道”的存在性更具体化、现实化,这无疑大大发展了道家学说,是老子之说在后世之事实展开的重要部分。东晋中散大夫嵇康的《声无哀乐论》是中国音乐史中巨擘之作,嵇康的思想受道家影响颇深。其一,他的立场是赞同老庄的“至乐”,即“无声之乐”,类似于“大音”“大美”的概念。其二,他将“音声”概念合二为一,就是具体的音乐,这明显区别于老子的音声二分法,此“音”亦不等同于彼“音”。他亦不否定“音”的存在价值,认为艺术之音和自然之音一样源于天地宇宙,是自然之产物,与人的喜怒哀乐无关。同时,他否定将音乐工具化、功能化,反对音乐具有教化功能。这极大地丰富了“音声相和”的内涵,使之事实展开呈现多元性,将老庄晦涩艰深的音乐观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述出来,并有所发展,同时不失其真意,为老子音乐观的传播推广起到积极作用。老子思想作为出世之学,在历代文人士大夫群体中不乏推崇者,一部分不得志的贵族还有像陶渊明般天生旷达、洞悉人生的高逸志士成为道家的继承者,在追求隐逸的同时,以老子思想体悟人生、并作为艺术审美标准,因此,“音声相和”“大音希声”的音乐观同样对中国音乐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以庄子和嵇康为代表的音乐美学理论家积极践行老子音乐观,同时集百家之长,赋予老子学说新的内涵,为老子音乐哲学的事实发展提供了新的空间和角度。
在中国思想史上,但凡提到老子,往往会联想到孔子。孔孟儒学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力堪比老庄为代表的道家思想。孔子关于音乐的论述很多,他的音乐观可用“乐由中出,礼自外作”八个字来高度概括。
“乐由中出,礼自外作。乐由中出故静。礼自外作故文。大乐必易,大礼必简。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10]该句字面意思是:乐产生于心,礼体现于外。纵览全篇,礼乐概念并列出现,外在表现内心,乐是礼的表现形式之一。
孔子的思想核心源自西周礼乐文化,孔子认为,乐是礼的外在表现形式之一,礼是乐的表达主题内容。自此,“乐”被赋予了社会功能——弘扬礼制、教化众生。“礼”的核心含义包括“等级贵贱”“内敛谦退”“自卑尊人”等,孔子将这些周礼的主体思想进一步发展,从外部规范约束上升为人心之内在需求,从而衍生出儒家核心思想内容“仁”。“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11]仁、礼、乐三者密切相关,仁乃义之本,义为人之节,而仁义之上是礼。礼的内在即自卑尊人,内敛谦让。礼的实现方式分内、外两种,外部约定的礼是道德规范,内心自觉而发的礼是自我修养,这种自我修养的方式以“习乐”为最佳。在孔子看来,自觉而发的礼高于外部强加的礼。由此而得出的结论是:孔子追求的向仁之心是可以通过礼乐教化达到的。
《论语》记载,鲁国权臣季氏僭越礼乐制度,用了天子使用的“八佾”乐队,孔子忿忿道:“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12]孔子尊崇周礼,把礼乐制度上升到国家制度层面。同时,他要求统治阶级积极推行“礼乐”教育。《史记·孔子世家》记载:“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13]既然乐与礼不可分,那么音乐世俗化也被一并否定。孔子强烈反对当时被称为新乐的郑声,原因是郑声节奏鲜明,曲调不够庄重,刺激感官会令人忘乎所以,轻薄忘礼。与之相对的是孔子极力推广典雅醇厚的雅乐。基于以上观点,孔子的音乐论述自西汉独尊儒术始,与他的主体思想一并成为官学的核心内容,得以广泛传播,成为自汉代后诸封建王朝的主流意识形态。儒家的音乐本体论和功能论也被统治阶级发扬光大,成为国家宣扬礼教、士人立德修身的必要手段。
三、音乐历史语境下的“音声相和”与“乐内礼外”
中国古代音乐史发展可以划分出几个大的发展阶段:夏、商、周时期(约5000年前—前11世纪)的音乐与生产、原始崇拜密切相关;西周、春秋战国时期(约前11世纪—前221)尚周礼,礼乐成为主流音乐形式;秦汉魏晋南北朝(前221—公元589)时期是统一到分裂的动荡时期,音乐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展现出民族融合、世俗音乐兴起的局面,音乐思想从尚周礼的儒家当道变成儒道互补,主张“玄学”的新形态;隋唐五代(581—960)是中国历史上文化大繁荣时期,音乐随之步入极其辉煌的阶段,宫廷音乐和世俗民间音乐共同发展,音乐的形式美和娱乐性优于音乐的教化功能,东西方音乐融合交汇;宋元明清(960—1911)时期音乐蓬勃发展,明清戏曲高度发展,宫廷音乐没落,音乐更加世俗化。由此不难看出中国音乐的历史脉络:第一,音乐从上流社会的小众艺术形式逐渐世俗化、娱乐化,开始为普罗大众服务;第二,从礼乐到雅乐,雅俗乐共生到雅乐几乎没落的一个发展过程。那么,造成礼乐和雅乐在音乐史发展逐渐颓败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笔者认为,是以孔子“乐内礼外”为核心思想的儒教音乐观长期占据主导地位造成的。孔子将音乐视为礼教的外化,势必将其他非“礼乐”划分到对立面,否定非“仁”为核心、非“礼教”为目的音乐形式,譬如孔子反对“郑卫之音”,晚年亲自编订《雅》《颂》等。这种过早的划分音乐形式是弱化审美性、强调功能性的表现,这种“实”将音乐发展引入确定的方向性和指向性,剥夺了音乐自由发展更多的可能性和多维性,如套上枷锁的奔马,驯化规范使之丧失自由行走的能力,只能沦为人类行走工具,剥夺其作为自然物的天然属性,而生命力、创造性、可能性是艺术发展的动力之源,百川异源,方能成海,拘泥于一种发展趋势,势必失去勃勃生机复归凋敝,这也恰。好可以解释自唐以后为何世俗民间音乐会蓬勃发展的原因所在。
反观老子的音乐观,其提倡音乐审美价值和悠游自为,审美第一性,坚决反对音乐物质化、功能化,始终以追求“大美”为至高境界,提倡“音声相和”的内在体验和外在现实意义。假设“音声相和”以及之后的继承者如庄子、嵇康等的道家音乐观在中国音乐史发展、尤其是在以公卿士大夫为主流群体的音乐生活中占一席之地的话,那么以礼乐和雅乐为代表的高雅音乐应该是另一种发展景象,既有儒家音乐可操作性的一面,又有道家音乐观的高度审美性能、哲学思辨,二者互补依存,使得中国之雅乐、宫廷音乐发展到新高度。叔本华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一书中对音乐本质的阐释非常深刻:“音乐不是现象的,或正确一点说,不是意志恰如其分的客观性的写照。所以对世界上一切形而下的来说,音乐表现那形而上的;对一切现象来说,音乐表现着自在之物。”[14]这段对音乐美学价值的论述和老子的“音声相和”“大音希声”相似,强调音乐的形而上,与老子“道”之宇宙生发论如出一辙。孔子对音乐的认识角度的层次较之老子过于低浅,起点太过具体,导致音乐发展“尚实”而“乏美”,没有领悟到音乐内在属性的深邃内涵,从而导致了中国礼乐和雅乐形式化发展,即从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始逐渐走向衰落,而世俗音乐繁荣发展、生机勃勃。
当然,这不是唯一原因,其他几个因素也不容忽视。中国传统音律学侧重“以数相求”之法,不免使音律过于教条严苛,晦涩难懂,轻视听觉之愉悦和谐,失去音乐本身的形式之美感,不足以广泛流传,喜闻乐见。另外,工尺谱、减字谱等中国传统的记谱法均以文字记谱,精确性低,随意性大,音乐的传承和发展多以口耳相传、师徒相承的方式展开,即使以文字记谱法流传下来,也是见仁见智,没有统一的表演规范,非常不利于音乐的传承,再加上战乱、“文字狱”等外力因素,大多数经典作品失传,非常可惜。但是,造成礼乐、雅乐走向没落的根本原因还是儒家音乐思想中将音乐绝对“礼化”“实化”“功能化”。任何事物的发展一旦走向绝对的道路,也就趋于静止。假设音乐“虚实相间”,儒家主张与道家观念同时存在、互补相生,使音乐发展符合普遍发展规律,中国传统音乐的发展道路是否更加宽广呢?
四、结语
孔子将音乐与礼教紧密结合,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具有积极意义,统治阶级利用儒家学派“人治”的过程助推了音乐的发展繁荣。孔子作为音乐教育家、儒家思想的开创者,他的话语权使得其音乐著述也被奉为后世经典。孔子重视音乐的美好以及由此生发出的对人性的教化功效,强调音乐的实用性,随之涌现大量音乐精品和技艺精湛的音乐家,进而推动中国音乐(文人音乐和宫廷音乐)的发展,然而,孔子音乐观作为认识论却无法超越其先天的局限性,不仅未将音乐上升到哲学范畴,甚至连美学意义都不凸显。儒家思想宣扬的“乐内礼外”反成为制约以礼乐和雅乐为代表的宫廷音乐、文人音乐的长效发展;老子音乐观寥寥数语,从字面意思来看,老子似乎不重视音乐,甚至反对音乐,其实这是将老子音乐观与他整体的哲学体系割裂开来的一种错误认识。恰恰相反,老子对音乐本体的认识是深刻而高远的,老子认为音乐是高于其他艺术表现形式的更高层次的存在,与“道”的存在一样无形却无处不在,需要用心体察其意义。在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人们对物质的追求已逐渐转向以文化、艺术为核心的精神层面的需求,音乐作为重要的艺术形式显得尤为重要。在笔者看来,老子在几个世纪之前提出的“音声相和”音乐观具有超越时代性特征,应该成为当下音乐发展的核心内容,具有现实意义。追求音乐形式之美的“音”始终要以表达音乐内涵之美的“声”为最高理想和价值评判标准,只有在“音”与“声”之“和”中,才可能创造出有既有艺术价值又经得起历史考验的优秀音乐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