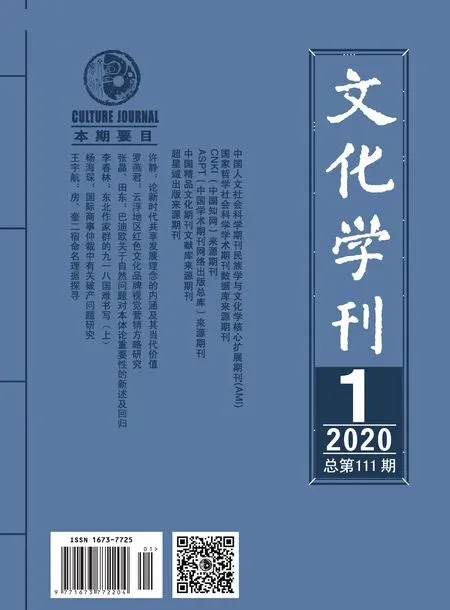从《诗人与死》看郑敏的死亡观
2020-01-02王沛婧
王沛婧
20世纪40年代初,郑敏曾在西南联大读哲学。求学期间,她在冯至的引导下开始了诗歌创作。因受冯至和奥地利德语诗人里尔克影响,郑敏偏爱在诗歌中书写具有哲学意味的文字,融入对生命的思考。在关注“生”的同时,郑敏并不避讳对“死”的解读。她将死亡同样视为生命的组成部分,在诗歌中审视死亡。本文将通过猜想诗歌主体身份、归纳《诗人与死》中的死亡定义和郑敏诗歌中死亡观的流变,分析郑敏诗歌中的死亡观。
一、“诗人”身份的猜想
《诗人与死》创作于1990年,师承冯至《十四行集》和里尔克《致奥菲亚斯十四行》,由十九首十四行诗组成,是郑敏为纪念老友唐祈之死所写的挽歌,但此诗意涵复杂,“诗人”可以指郑敏的旧友唐祈,也可以是郑敏本人,甚至可以指向受难的知识分子群体。
《诗人与死》的第九节中,“第六十九个冬天”正是指唐祈在人世间度过的六十九个年岁,其后的“电火”与“铭刻”,暗示尽管唐祈的遗体已被火葬,但他因坚毅深刻的品质而在火焰中涅槃。这些都表达了九叶诗人唐祈意外死亡之后郑敏对友人的哀婉之思。据此,可以认为,“诗人”的身份就是唐祈,此诗是纪念唐祈的发愤之作。但以此解释诗人的身份,说服力不强。根据唐祈在黑龙江农场劳改期间的经历,可以认为《诗人与死》其实是写给唐祈和唐祈的右派同伴歌唱家莫桂新的悼念诗,哀叹这二人的离奇死亡。在诗歌的第十五节,紧随在唐祈身后无辜受难的“愤怒的人们”则指向了更大的群体,而非个人。他们可以是还活着的难友,但因“死亡跟在身后”,所以更多地指向同为冤鬼的知识分子们。
此外,还可以将“诗人”理解为郑敏本人,《诗人与死》表达的是郑敏对知识分子非正常死亡的忧虑和思考。“那双疑虑的眼睛/总不愿承认黑暗/即使曾穿过死亡的黑影/把怀中难友的尸体陪伴”[1],郑敏将自己的立场融入诗中,尝试用理性的眼光认识所谓的生离死别。虽然诗句所写的内容可以被认为是唐所经历的一次生死体验,然而主人公的生活经历确实有郑敏的影子。如此一来,《诗人与死》不应单纯被视为悼念诗,而应有更多值得探求的方向与可能。
实际上,不论是哪一类猜想,都有相应的道理,并不一定要区分对错。“这两个解,是复义的,能互相补充互相复合,组成一个丰富的整体。”[2]如果能将不同的理解综合起来,当然能更为全面地认识这首诗歌。正是因为“诗人”身份的多义,才延伸出不同的认知取向,发展出丰富的意涵。笔者认为,辩证对待这些猜想,才能更深刻地理解《诗人与死》中的身份问题,一窥郑敏在诗中流露的死亡观。
二、《诗人与死》中的“死亡”定义
研究《诗人与死》这首诗,第二个需要探讨的问题是“何为死亡?”郑敏在诗歌创作中,时刻以冷静客观的态度直视死亡的阴影,然而,在不同的篇目中,死亡的具体意涵仍存在一定的差异。《诗人与死》的情绪相对复杂,不能以某一诗节简单概括死亡在诗中的具体指向。在此诗中,对于“死亡”的定义,可从以下三方面去理解。
第一个方面是对死亡的诗化。“你已经带走所有肉体的脆弱/盛开的火焰将用舞蹈把你吸吮/一切美丽的瓷器/因此留下那不谢的奇异花朵。”[3]在这段诗里,郑敏诗化了死亡,甚至认为死亡不过是以肉体脆弱的消散获得了新生。读者可以将此理解为暗藏着强烈悲愤之情的反讽,但不能由此深化郑敏对死亡的思考。郑敏习惯用超现实的语句隐喻现实生活中蕴含的哲理,此段不应该只是物伤其类的愤怒,而是将肉体死亡当作精神的延续和升华,是表达人类对光明未来的共同渴求。
第二个方面是借描绘死亡表达自己压抑于心头的愤怒。在第十节,郑敏将“我们”比作“火烈鸟”,并认为“火烈鸟”们终生都与地狱之火战斗,且十分坚强,并不会因为痛苦呻吟。可在现实生活中,火烈鸟可以获得生存的土壤,作为知识分子的“我们”,或者说曾经蒙受不白之冤的人们,却无法获得应有的生存空间,所以诗人给了这些人“损坠无声”的结局。这是对特殊时代人的命运的反思和慨叹,也是压抑的愤怒嘶吼。面对他们的死亡,郑敏没有过度剖白自己的愤怒情感,她选择将深沉的情感融入字里行间,供读者体味。理智面对生命中的不幸,也是郑敏直面生死的一种态度。
第三个方面是接受死亡的普遍性,并尝试作出积极理解。接受死亡的普遍性,并不意味着放弃愤怒、放弃反讽、放弃深度思考的权利,而是将死亡的负面因素化为春天到来前的影子。尽管诗人承认春天不会轻易到来,也曾慨叹过冬天之无穷尽,但还是愿意追求炫目多彩的北极光。在郑敏眼里,诗人最后的沉寂就是“无声的极光”[4],是自由自在的、向死而生的境界,是对死亡的超脱,在完善诗情的同时,赋予了诗歌生命之美。
在《诗人与死》中,只有从不同的角度认识郑敏所讲述的死亡,才能理解诗人的真实意图。将死亡诗化,表达悲壮、愤怒的情感,进而展开哲思和反讽,这是郑敏升华诗意的创作方式。不仅是在《诗人与死》中,郑敏的其他作品中也流露出复杂的死亡观念。分析其成因与流变,是探求郑敏死亡观的重要环节。
三、《诗人与死》中死亡观的成因
郑敏诗歌中所展现出的死亡观,与她的人生经历关系密切。郑敏年轻时师从冯至,深受奥地利诗人里尔克的影响。诗哲相融的创作方法与对语言文字的探索精神,都激励郑敏在诗歌中建立自己的哲学。1942年至1947年间,郑敏的《时代与死》《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三日的死讯》等作品,都有借死说哲学的成分。1979年至今,经历过时间的洗濯,郑敏对于死亡的态度已经不再是简单的逻辑推论,更加重视书写生命的感触。
除却上文中提到的《诗人与死》中的复杂感情,《圣桑的死亡舞》《死的幻象》《开在五月的白蔷薇》等诗,则以理性的勇气逼视负面的情绪,直面死亡带来的痛苦。在《死亡第二次浪漫地歌唱着》中,诗人写道:“死亡,那纯洁的白衣裙/如生命的云片飘立在床前/那最华美的四马之车。”[5]在这首诗里,死亡不仅代表恐怖的终结,亦可以被看作纯洁的象征,甚至是美好的象征,区别于之前的苦难身份。
在这种语境下,死亡能带给人类的是母爱式的感受,赋予死亡宁静之美,认为它“像秋天的麦束在田野列队/欢送一个单纯的灵魂归去”[6]。郑敏曾在《金黄的稻束》中将“母亲”比作“麦束”,如今又给了死亡这样的身份象征。诗化的死亡在诗人的眼中单纯静美,有意义的人生在迎来死亡后就如同沉甸甸的麦穗。中国化的天人合一与西方化的向死而生逐渐交融,形成了郑敏式的死亡观。
“90年代的诗人、知识分子,经常纠缠于自我在文化上的尴尬地位,自我怀疑和无力感已远远超出诗歌的范畴。”[7]郑敏没有将目光纠缠在“小我”上,她更愿意在关注现实的前提下,在诗歌中融入对生命的思考,反复质询自己的诗歌哲学。她的诗歌里透露出了文化自信,具有胆识和力量。在这种背景下,简单将郑敏的死亡观归类为几个词语并不贴切,应将其理解为流动的有机体,再展开讨论。
四、郑敏死亡观的现实意义
“五四”以来,中国现代汉诗一直深受西方诗歌的影响。郑敏的诗歌正是学习西方诗歌的写作技巧,借助西方经典意象表达诗情的产物。即便如此,郑敏仍然能敏锐地意识到,想要让现代汉诗保持活力,必须重视中国的诗歌传统。《诗人与死》中死亡观的塑造,就是郑敏所做出的一次尝试。“她对死亡的崇高揭示与礼赞,对死亡所表现的人文主义的救赎情怀,以及对死亡与生命的辩证思考,都深深地打上了时代、民族和文化的烙印。”[8]里尔克的《致奥菲亚斯十四行》启发郑敏将现实中的死亡与伊卡瑞斯之死相联系,以传统的诗歌思维来处理现代的诗歌语言,写出对死亡的深刻认识。这种雄厚的悲剧美,是郑敏死亡观特有的魅力。
“郑敏笔下的死亡意象没有局限于个体感受的抒发,而成为时代的某种缩影。”[9]在《诗人与死》中,郑敏基于国家问题和现实问题展开对死亡的思考,在所用的西方意象中融入中国传统诗学的成分,使诗歌更趋近于文人画,具有更简洁的线条,而不仅是以色彩对比取胜的鲜明之美。在这样的场景设置里,她对死亡的描述显得热烈浪漫,死亡既可以是生命中的黑影,也可以是无声的极光,是丰富的感情的聚合物,而不囿于做沉重的抒情诗中一尊凝练的雕塑。
重视发掘传统诗艺,在现代汉诗的创作中寻求传统审美与现代语言的制衡,就是郑敏《诗人与死》中死亡观的确立和表现方式。在某种程度上,郑敏的死亡观,在探求现代汉诗发展方向的同时,也能为现代汉诗的创作方式提供参考和帮助。立足现实,重视文学传统与西方诗论的有机结合,是郑敏死亡观为建设现代化的新诗所做出的努力与尝试,也是这一观念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