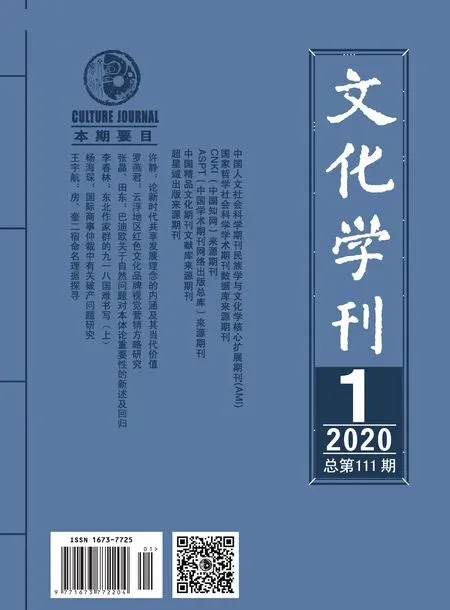芥川龙之介与三岛由纪夫武士道精神之比较
——“和魂”与“武魂”的冲突与调和
2020-01-02乌博林
乌博林
武士道意为武士在其职业上和日常生活中所必须遵守之道,简而言之就是“武士的训条”,也就是随武士阶层而来的义务。武士道是“国民全体的景仰和灵感,虽然平民未能达到武士的道德高度,但是‘大和魂’终于发展成为岛国帝国的民族精神的表现”[1]。由此我们便可得知武士道如何演变成为日本国民精神,以及近现代日本文坛以芥川龙之介和三岛由纪夫为代表的作家无论就其个人还是创作因何原因深受其影响。
一、二者同处日本近现代社会变革时期,均体现日本国民普遍充满怀疑的精神
首先,由于芥川所处年代稍早于三岛,社会与战争的洗礼有本质的不同,因此芥川龙之介(1892—1927)的怀疑更多是来源于他成长的被“黑船”敲开国门后的明治末期到大正时期充满复杂动荡、激烈剧变、闭塞明朗相互交织的历史时期,与之相伴的是日本在三次战争胜利后的加速“欧化”带来的经济政治的深刻变化,这使得芥川的创作立足资本主义体制层面思考日本文化的弊端,潜意识弱化了传统文明中“武魂”对他的影响,并站在“和魂”立场对其批判,因而他的创作中存在“武魂”与“和魂”的冲突,而三岛由纪夫(1925—1970)看待日本传统文化的视角与视野就与芥川不同,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本经历了自主发展与二战扩张野心的破灭,再次受制于西方国家。三岛在二战的经历过程以及战后的种种,既使他在战争影响下产生趋亡倾向,又促使他的“皇国观”走向极端。这种政治的虚妄促使三岛的创作立足振兴“武魂”,激发了他用剑来平衡菊的欲望。但他没有实现“武魂”与“和魂”的平衡,并在平衡点偏于“武魂”时坠入深渊。
其次,芥川龙之介与三岛由纪夫的个人经历有一定的相似性,在二者的成长过程中母亲均处于缺席状态,这对芥川与三岛的人生观、文学观都产生了影响。母亲的缺席,使芥川龙之介与三岛由纪夫在“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即“武魂”与“和魂”间没有保持稳定的平衡,但是,二人的差异性也在成长进程得以显现。芥川身上并未凸显出厚重的“男性气质”,芥川由于个人、家庭、社会三方面的境况陷入苦恼的深渊,企图通过艺术观照现实,来使自己成为“精神上的强者”。三岛由纪夫则由于家庭的影响,同时又得到了栖川宫家的皇家家风熏陶,自觉不自觉地养成一种武士的骄矜和皇族的孤高气质。面对着与芥川同样柔弱的身躯,三岛采取的是截然不同的态度与方法,他不仅仅局限于精神上的创作,还加强了对肉体的锻炼,进而推演到一种浪漫主义的想法:作为一名武士,剖腹自杀,实现对“文化概念的天皇”效忠。
二、二者的武士道文学作品凸显“和魂”与“武魂”的冲突和调和
芥川龙之介在其短暂的三十六年的人生里,创作了大量涉及武士道的作品。有单纯将武士作为描写对象的,还有以揭示武士道精神为主题的作品,但是,在芥川的作品中,武士与武士道精神并非完全歌颂的对象。例如:在《大石内藏助的一天》中,芥川描写四十七义士在为主人报仇后的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内心充满孤独,这是对英雄形象的颠覆。《手绢》中通过西山夫人的表现强调她是日本女性“武士道”的精神楷模,这足以表明芥川肯定武士道追求名誉可引导人走向正途。在《竹林中》,三个当事人都说自己是凶手,除了出于人性的自私,更是出于对名誉的维护。这部作品中或多或少地流露出芥川对武士道精神的痛恶,为了追求武士道精神即求死之道而弃生命于不顾。
芥川在作品中显现的对武士道精神的矛盾态度,正是体现了他自身“和魂”与“武魂”的冲突和调和,但芥川在作品中对武士道精神更多是持反对态度的,对日本“武魂”更多是在进行批判。他批判日本的传统道德价值体系,他在个人随想集《侏儒警语》中直言不讳地对此进行评论:“支配我们的道德,是流毒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封建时代的道德。我们除了遭受损害之外,几乎没有蒙受任何恩惠。”[2]这表明了芥川对日本传统道德的反叛。
三岛由纪夫骨子里的武士道精神的血脉,对他的创作心理与审美产生了深刻影响,这集中体现在他创作中后期的诸多作品中。如果说社会与个人经历使武士道精神在他人生中扎下根基,那么被三岛由纪夫奉为圭臬读本的《叶隐》就是浇灌这种精神茁壮成长的雨露。这是三岛唯一一本几乎一直经常翻阅的书,这本书的作者是山本常朝,书中内容是关于武士修养,宣扬忠君的大义。受《叶隐》的影响,三岛写了《叶隐入门》一书来揭示日本战后青年的危机,简言之就是日本青年尤其是男性丧失了男子气概,取而代之的是柔弱的女性气质。为了解决这一危机,三岛提出的方案就是重新培养符合武士道精神的“爱国忠君”思想,随时准备为国赴死,显然这是不符合时代主题的,逆流而上只会迎来死亡。三岛的《忧国》中明确表明了武山与丽子即使在性爱的极度欢愉中依旧没有忘记武士道带给他们为国赴死的决心,三岛借助武山这一人物形象将“忠诚”这一主题表现得淋漓尽致,以此激发日本青年。《太阳与铁》中三岛立足个人的皇国观以及对武士道的向往而探究如何达到文武均衡,形成了个人独特的“行动哲学”。三岛对太阳的崇拜首先源于在日本古代传统中太阳是天皇的象征,其次是因为太阳是具有生命意味的。由此他改造自己的肉体,希望身体能够强壮如“铁”。“太阳与铁”的结合成为三岛实现精神与肉体统一的重要因素,当二者真正实现结合之时,也就是三岛迈向死亡之时,自杀成为三岛的归宿已经明朗。绝笔之作《丰饶之海》就是一份遗书,它的题目就证明了三岛已经距离生命越来越远,他借用开普勒和第谷·布拉赫时代星象天文学家的古老月球学的概念。“丰饶之海”实际上是月球上的巨大坑洞,没有生命、水、空气的荒芜之地。作品的构成与风格和前期也有显著不同,《春雪》《奔马》《晓寺》与《天人五衰》四卷书构成了一个序列,并且显然从一开始就被引向了某种结局——三岛已打算自杀并通过轮回转世来实现自己的理想。总体来说,在这部作品中三岛由纪夫依旧在努力实现“武魂”与“和魂”的调和,但流于虚幻,一切的铺垫都是为了“忠君爱国”这一永恒主题。
三、武士道精神对二者均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武士道精神对芥川龙之介与三岛由纪夫的生死观、无常观、战争意识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死亡意识、生命无常结合战争形式贯穿两位作家人生与创作的始终,但二者的体现方式有所不同。首先,二者形成生死观与无常观的根源在于作为日本民族传统信仰的神道教是关于生与生活的宗教。生死观是日本民族性的根本问题,日本人有着独特的生死观,他们普遍认为死是生的一部分,从生到死没有绝对的距离,并且认为死亡是一种解脱,是很美丽的事情。
芥川武士道精神的构成在上述基础上又受到了基督教的影响。他自幼接触基督教,与基督教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创作了一系列的殉教小说,芥川自杀的原因不无对名誉的维护,因他的不安包括担心遗传母亲的精神失常,这也是他追求自由的权利。三岛由纪夫身上则完全体现了在“纯粹武士道精神”影响下的生死观。他接受了禅宗认为的不应拘泥于生死问题的观念,三岛追求的是生命不在于长久,而在于闪光。芥川文学中涉及“无常”的作品较多,芥川拥有一系列佛教题材作品,而三岛则是一方面通过他的怪异美学来展现他的无常观,另一方面他个人时常怀疑生命是否有意义。
在武士道精神的影响下,芥川与三岛形成了两种大相径庭的战争意识。芥川的《将军》《金将军》等作品明显反映了芥川的战争观,这些作品表现的都是芥川强烈的反战意识。三岛的《忧国》与《奔马》等作品中表现出的是好战意识,企图通过战争来实现推崇武士道精神的目的。值得一提的是,三岛对芥川所处于的明治维新时期充满向往,并对这一时期的武士的作为十分了解,他迷恋日本民族英雄西乡隆盛,但是芥川却对这一时期的武士道文化进行了严厉的批判。这也体现了芥川与三岛“和魂”与“武魂”的冲突。
四、结语
武士道为芥川与三岛的写作提供了素材,武士道精神影响了他们的世界观。三岛由纪夫认同本尼迪克特对日本文化得出的结论:日本文化是一种不同于欧美的“罪感文化”的“耻感文化”。芥川龙之介作品中也体现着对日本耻感文化的认同,这种耻感文化的来源正是武士道。大正时期的芥川与昭和年间的三岛随着时代的推移伴随着民族文化的变迁,一位大力批判武士道精神,而另一位不遗余力地推崇着武士道精神,无论肯定与否定,武士道精神都深深刻印在他们的骨血之中。对于日本文化,人们已经有了普遍的共识,从个人到整个民族,若过多强调“菊”之艺术美而忽略“刀”的尚武传统,会使整个民族过于软弱;若过分集中“刀”的一面而忽视“菊”,又会使整个民族走向极端。近现代日本社会既传承了古典美学,又带有尚武的烙印,如果忽略了“菊”与“刀”平衡,日本就会失去民族身份,消解了与历史的联系。这一点,时间给出了最好的证明。因而只有感知日本传统文化的双重性,领悟日本民族独特的矛盾特性,实现“和魂”与“武魂”的调和,才能呈现一幅完整的“日本全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