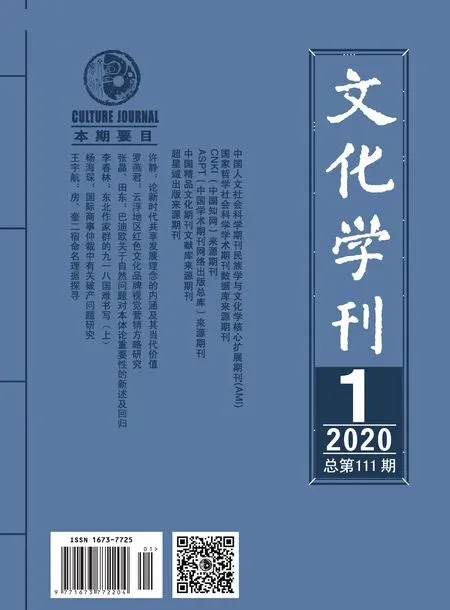民族社会的清醒者
——大江健三郎与鲁迅比较
2020-01-02范晶
范 晶
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具有强烈爱国情感的作家出现,用作品表达情感,用作品发出声音。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与中国现代伟大文学家鲁迅都是关注社会、关注民众命运的具有强烈的人文主义的作家,大江健三郎与鲁迅虽处于不同的国家,但是他们所在的社会大环境是相同的。鲁迅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革命时期的作家,大江健三郎则是20世纪50年代日本战后作家,他们以不同的笔触、相同的关怀,深切关注国民性问题。
一、大江健三郎与鲁迅
大江健三郎是1994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他以强烈的使命感关注人的存在,关注社会问题。二战后的日本社会动荡,严重的经济危机困扰着人们,其大多数处于绝望的悲观情绪中,这种悲观情绪在知识分子阶层尤为严重。大江健三郎作为一个有强烈民族感情的大学生,将目光转向了西方存在主义,以寻求一种新的思想拯救这个颓废的社会。他将精力投入了创作之中,将目光投向了失去了理想信念、沉浸在迷惘与绝望深渊中的日本青年一代,企图用文学唤醒他们,使其振作起来,所以他创作了《奇妙的工作》《死者的奢华》《饲育》等强烈关注社会及人类命运的思想的作品。
“五四运动”前夕,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狂人日记》,揭露了中国“吃人”的封建社会,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声。鲁迅以笔代戈,奋笔疾书,创作了多部享誉世界、流传后世的作品,有散文集《朝花夕拾》,散文诗集《野草》,小说集《呐喊》《彷徨》等。鲁迅的作品真实描绘了从辛亥革命到“五四时期”的社会生活,用幽默又带讽刺意味的语言,激励着当时半梦半醒的中国人,揭示了植根于中国的社会矛盾,对国民生存问题表现出了强烈的忧患意识以及对社会变革的强烈渴望。
二、不同的笔触,相同的情感
从大江健三郎和鲁迅的作品中可以清晰深刻看到,他们把焦点放到了社会和国民的身上。大江健三郎注重揭露社会的阴暗面,鲁迅也一直致力于揭出病苦。大江健三郎关注个体的生存状态,希望找到一条精神救赎之路,而鲁迅一生都在探求理想的人生,从事国民性改造的伟大事业。两位作家笔下不同作品不同形象表现其强烈的人文主义关怀,他们以不同的笔触、相同的关怀,深切关注国民性问题。
(一)青年一代
在大江健三郎的初期作品《奇妙的工作》中,“我”是一名大学生,到医院应聘,结果被要求屠杀实验室为实验而圈养的150只狗,在小说中展现了一幅幅残忍且血腥的画面。结局中,“我”所做的所有努力都没有结果,没有意义。作品中故事所处的时代背景是二战后,国民迷惘空虚,尤其是日本青年阶层被囚禁在厚厚的“墙壁”之中,他们眼中的世界是荒诞不堪的,人的主体性已经丧失,只能颓然地活着。大江健三郎以敏锐而清晰的感受,勾勒出了日本当代青年的形象轮廓,宣泄了他们的徒劳感和挫折感。在这一时期,人们认为人所做的一切都是徒劳的,人无力改变自己的命运。日本青年一代需要被拯救,需要有人站起来发出声音、响彻社会的声音,所以他将自己所要表达的放到了作品中,用作品警醒国民,用文学关注社会。
鲁迅一直致力于“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与大江健三郎笔下空虚迷惘的青年不同,在《记念刘和珍君》中,青年女大学生刘和珍英勇爱国,敢于反抗政府的暴行,揭露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相勾结屠杀爱国群众的滔天罪行。《记念刘和珍君》以散文的形式,纪念与反动派对抗而英勇就义的爱国青年,借对爱国青年的赞颂与怀念,反面映衬出那些庸俗市民的麻木不仁,对那些反动文人学者的恶意污蔑感到愤慨。同样是对国民,尤其是对青年一代的关注,鲁迅作品中所透露出的是希望。中国青年是有希望的,虽然社会中还存在一些“苟活者”,但爱国青年的流血牺牲也能使他们从死者的血色里依稀看到未来微茫的一点希望。在这篇散文中,鲁迅更想表达的是希望。
(二)麻木一类
大江健三郎的笔下有着“看客”这一类人物。在小说《人羊》中,“看客”的形象非常鲜明,个性突出。大江对“看客”的描写是细致鲜明的,售票员“壮实的脖子上长着一块像兔子性器般的粉红疙瘩,透着些许女性温柔”[1]。看客们用手摸着涨红的脸,望着这群“羔羊”。他们身份各异,却无一例外表现出麻木、虚伪、懦弱、冷漠自私的性格特征。大江健三郎笔下的“看客”是在日本二战后形成的,多数国民特别是知识分子阶层处于悲观、失望、彷徨的颓废状态中。《人羊》中悲观困苦的人们面对“威风十足”的外国大兵时,看客们像绵羊一样温顺,而被看的人也只能像待宰的羔羊一样,不敢反抗。这是人性的病态,是大江健三郎想要疗救的“病”,这样的民众让大江健三郎感到痛苦失望,他想要将“看客的心理”从国民的身上剔除,因而他将焦点放到麻木的民众身上,企图唤醒国人。
鲁迅作品中“看客”的形象也是深入人心,栩栩如生。与大江健三郎笔下的看客形象不同,鲁迅所描述的是看客群体“漠然却饶有兴致地去观赏别人的不幸,痛苦,尴尬,而脸上带着或满足或遗憾的笑容”[2]。鲁迅看到了太多麻木不仁的国民,所以他做出了弃医从文的伟大壮举,改用文学拯救、唤醒国民。在《阿Q正传》中,阿Q即将被枪毙,去刑场的道路两旁是许多张着嘴的“看客”,是蚂蚁似的人,他看向那些喝彩的人们,想起了他曾经遇到过的饿狼,有着又凶又怯眼睛的要吃他肉的饿狼,“这回他又看见从来没有见过的更可怕的眼睛了,又钝又锋利,不但已经咀嚼了他的话,并且还要咀嚼他皮肉以外的东西,永是不近不远的跟他走”[3]。这可怕的眼神正是看客们的眼神,他们看着阿Q伏法,没有同情和思考,反而是不满足,他们认为这次的枪毙并没有杀头好看。在中国社会腐朽没落的时代,鲁迅从揭示这些落后群体的灵魂深处落笔,显现出国民的劣根性,引起疗救者的注意。这种看客形象的形成是千百年来的历史积淀,是腐朽黑暗的封建社会的产物,他们面对自己的血肉同胞也以近乎冰冷的姿态面对。鲁迅正是看到了社会中大批这样的“看客”,才将他们写入作品中,给那个时代处于精神混沌的人们以振聋发聩的警醒,让他们清晰看到自己丑陋、低俗的一面。鲁迅作品中“看客”形象的形成,就是为了拯救麻木的那一类人。
(三)不安定的社会
二战后的日本失去了自主权,被美国所“统治”,不安、焦躁是此时的大氛围,人们的生存状态是恐惧、痛苦的,尤其是经历了广岛、长崎的原子弹爆炸,这突如其来的灾难更是为已经阴暗的社会添加了一抹黑。大江健三郎非常关注原子弹爆炸的问题,考察广岛和冲绳后,他写了《广岛札记》和《冲绳札记》。在访问当年原子弹爆炸灾难中幸存的受害者时,他感受到了核武器对人类社会的全面威胁以及人类生存所面临的普遍困境,由此创作了多部有关核武器威胁人类的作品。在这里,大江健三郎关注的不仅是日本社会,更多关注的是整个人类社会。他站在人本主义的角度凝视整个人类社会,倡导和平,将战争的恐惧从人类生活的环境中抹去。
鲁迅的作品中更多关注的是腐朽破败的中国社会。鲁迅是一位怀着强烈社会责任感和民族危机感的作家,在批判社会的过程中更望拯救这个社会。在小说集《呐喊》《彷徨》中,皆可看到鲁迅对中国社会危机的担忧与反思:中国人不走出愚昧,中国社会就不可能真正走向未来。他以锋利的笔触抨击腐朽的封建社会。在鲁迅的杂文中,也表现出其强烈的揭露病态社会的人们,反对旧道德旧制度和一切封建卫道者。鲁迅不似大江健三郎是现代作家,所以将目光放在了本国社会上,当然,在那个时代,中国腐朽的社会是摆在眼前的大问题。
三、结语
大江健三郎是受到鲁迅影响的战后作家之一,虽然国别以及所处的社会背景不同,但是他们作品中所流露出来的批判意识和对社会、对国民的深深忧思是相同的,他们都是立足于现实社会,从麻木的人群中脱离出来,清醒地思考着社会的命运、民众的命运。“从这两位作家的现实生活看来,他们自身就是时代的孤独者、寂寥人,他们分别用言语和行动,对个体生存的状况和人类的发展进程进行着深刻地思考和探索。”[4]所以他们用作品发声,发出振聋发聩的声音,拯救麻木、困苦的民众,批判荒诞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