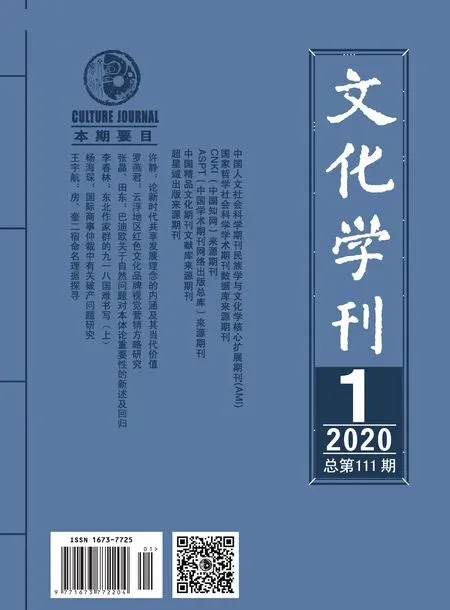《布里尔小姐》中人物存在状态的及物性分析
2020-01-02许敏
许 敏
凯瑟琳·曼斯菲尔德(1888—1923)被誉为100多年来新西兰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布里尔小姐》是其精心雕琢的短篇小说之一,充分体现了其独具匠心的语言风格和叙述技巧,奠定了曼斯菲尔德作为一名杰出的现代文学大师的地位[1]。及物性是一个语义系统,其作用是“把人们在现实世界中所见所闻、所作所为分成若干种‘过程’,即将经验通过语法进行范畴化,并指明与各种过程有关的‘参与者’和‘环境成分’”[2]。通过及物性系统,人类的经验可以分为六种不同的过程:物质过程、心理过程、关系过程、行为过程、言语过程和存在过程。及物性系统是经验功能的体现形式之一,经验功能指的是“语言对人们在现实世界(包括内心世界)中各种经历的表达”[3]。以此来看,对小说的及物性系统分析有利于反映人物在主客观世界中的活动状况。因此,本文将从语言特征层面入手,分析布里尔小姐在故事中三个典型场景的及物性过程,即在家为去公共花园做准备的场景、在公共花园中的场景、从公共花园返回家中后的场景,从而挖掘文本所蕴含的深层主题含义。
一、布里尔小姐在家为去公共花园做准备的及物性分析
故事第一段为布里尔小姐周日为去公共花园做准备的描写。通过对在此场景中以布里尔小姐为参与者的及物性过程分析得出以下结果。此场景中有九个物质过程,四个心理过程,一个行为过程。体现物质过程的动词分别是“抬起”“触摸”“拿出”“抖掉”“刷亮”“摩擦”“取下”“放在”“抚弄”,这九个体现物质过程的动词所延及的目标对象依次是“手”“狐皮围巾”“狐皮围巾”“防蛀粉”“狐皮围巾”“生气”“狐皮围巾”“狐皮围巾”“狐皮围巾”,与之相关的环境成分有“从盒子中(拿)出来”“(抖)掉”“恢复(生气)”“(放)在腿上”。体现心理过程的动词分别是“觉得”“感到”“心想”“很高兴”,与之对应的目标对象依次是“小淘气”“刺痛”“自己还是戴上了狐皮围巾(从句)”。体现行为过程的动词是“呼吸”。由此可见,此场景中表示做事的物质过程和反映人物内在意识活动的心理过程被高频率使用。下面内容将对这两个及物过程进行详细分析。
一方面,从九个物质过程可以看出,布里尔小姐在家为去公共花园做了很多准备活动,表现出她对日常周日出行活动的重视以及她内心深处极度渴望引起他人的关注和认可。此外,仔细观察会发现,九个体现物质过程的动词延及九个目标对象,在这九个目标对象中有六个目标对象是“狐皮围巾”,其余两个目标对象虽然是“防蛀粉”和“生气”,但也与狐皮围巾紧密相关。这表明:“小淘气”狐皮围巾是布里尔小姐唯一的玩伴以及她对狐皮围巾的喜爱。在此场景中不涉及以布里尔小姐为说话者的言语过程,她的所有活动仅仅局限于与狐皮围巾的互动,所以也反映出布里尔小姐孑然一身的孤独状态,而“小淘气”则是她孤独内心世界的情感依托。
另一方面,就心理过程的整体范畴而言,心理过程包括“知觉”“认知”“情感”等[4]。“知觉”属于较低层次的心理意识,而“认知”属于较高层次的心理意识。心理过程一般有两个参与者,即“感知者”(Senser)和“现象”(Phenomenon)。“感知者”一般是被赋予意识的主体,“现象”可以是“事物”或“事实”(the fact)。例如:以布里尔小姐为“感知者”的属于“知觉”心理过程的小句“她感到手和胳膊略微有些刺痛”[5]和属于“认知”心理活动的小句“她想可能是由于走了路的缘故”[6],这两个小句表明,作为具有主体意识的布里尔小姐本人能够清楚地意识到衰老给她身体方面带来的痛苦。
正如韩礼德所言:“表达经验的概念功能有利于揭示小说人物生存活动的性质。”[7]作者主要通过以上两个及物性过程的运用清晰地向读者展现了布里尔小姐年老体衰、孤独寂寞的生活状态。“在《勃里尔小姐》中,作者真切地写出了勃里尔小姐的心态与情绪,反映了她对在冷漠的社会中孤独寂寞的老年人的深切理解与同情。”[8]
二、公共花园中布里尔小姐的及物性分析
故事第二段到第十六段均为布里尔小姐在公共花园中的描述。通过对布里尔小姐在公共花园中的及物性模式分析得出此结果:物质过程三个,心理过程十二个,行为过程三个。体现物质过程的动词有“抬起”“摇晃”“充满”,前两个动词对应的目标对象分别是“头”“她”(一对老年夫妇中的女士),而与第三个动词相关的环境成分是“眼泪”。体现心理过程的动词包括“知道”“期待”“觉得”“真想”“注意到”“知道”“称赞”“想着”“欣喜”“喜欢”“想到”“(不)知道”,所涉及的目标对象有“谈话”“坐在这儿”“看着这一切”“我们明白(从句)”“他们所明白的”。体现行为过程的动词有“笑了”“斜视”“发笑”,涉及的有关环境成分是“侧面”“大声地”。下面内容将重点分析这三种及物过程和其所涉及的环境成分。
总的来说,与布里尔小姐在家为去公共花园做准备的各类过程(共计十四个)相比,她在公共花园中的及物过程明显增加,共计十八个,但值得注意的是,物质过程减少到三个,心理过程增加到十二个,行为过程增加到三个。首先,在仅有的三个物质活动过程中,有两个体现物质过程的动词有与其相对应的目标,第一个动词“抬起”延及的目标是布里尔小姐的头部,这说明她的活动仅限于自身的肢体活动,第二个动词“摇晃”延及的目标虽然是一对老夫妇中的女士,但也因前面体现心理过程的动词“真想”而被剥夺了其实际效力。由此可见,在公共花园中,布里尔小姐所行使的都是无效活动,在人群中也并不活跃,并没有和公园中的其他人物进行实际的互动。
其次,在此社会场景中,反映布里尔小姐内心意识活动的心理过程被高频率使用,占整个及物性过程的百分之五十,这反映出她与公园中其他人物之间没有实际上言语方面的互动交流,而是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在观察着周围人们的一举一动,以此来丰富自己的内心情感,排解长期郁积已久的孤独感。从体现心理过程的动词(期待、喜欢、想到)和其分别所指涉的“现象”(谈话、坐在这儿、看着这一切、我们明白)来看,布里尔小姐内心深处极其渴望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交流和理解,但这似乎很难实现,她只能通过偷听周围人的谈话,观察公园中来来往往的人,以及通过幻想把公共花园想象成为一个剧场,公园中的所有人物以及包括她本人都是剧中演员,以此来建立起她与公园中其他人物的联系,从而暂时消除社会边缘人身份给她带来的痛苦与焦虑。最后,“行为过程指表哭笑等的生理活动的过程”,一般只有一个参与者即“行为者”[9]。在这一场景中,主要揭示布里尔小姐行为举止的动词有“斜视”和“发笑”,与其所对应的环境成分是“侧面地”和“大声地”,前者表现出她观察身旁的老夫妇,以防被他们发现的小心翼翼,而后者则表明布里尔小姐幻想自己也是戏剧演员中的一名成员时的开心与喜悦,同时这暗示她内心深处极其渴望与周围的人们建立联系,被自己所处的社会环境所认可和接纳。
在公共花园这一社会空间中,作者主要通过减少物质过程,增加心理过程和行为过程等及物性系统选择来勾勒布里尔小姐被边缘化的孤独生存状态。从小说中公共花园取名为“Jardins Publiques”可以看出布里尔小姐侨居在异国文化背景之中。“在这种异域文化的气氛之中,她不能真正融入到这种文化环境中,而是处于一种被边缘化的生活处境中。”[10]
三、布里尔小姐从公共花园返回家中后的及物性分析
故事第十八段是布里尔小姐从公共花园返回家中后的场景。通过对该场景中布里尔小姐的及物过程分析得出此结果:物质过程三个,心理过程两个,行为过程一个。体现物质过程的动词有“解下”“放进”“盖上”,所延及的目标对象依次是“狐皮围巾”“狐皮围巾”“盒盖”,有关的环境成分包括“迅速”“看也不看”“里面”“(盖)上”。体现心理过程的动词有“觉得”“听见”,第二个动词所延及的目标对象是“哭声”。体现行为过程的动词有“坐下”“坐了”,与第二个动词相对应的环境成分是“很久”。
以下内容主要分析对比布里尔小姐在第一场景和在第三场景中的及物性过程以及这两场景中所涉及的环境成分的差异变化。
在故事结尾,当听到一对年轻的法国恋人对自己及狐皮围巾的嘲笑之后,布里尔小姐内心受挫,垂头丧气,只身一人返回家中。第三场景中有三个物质过程,两个心理过程,两个行为过程。整体上来说,这一场景中三个及物过程的分布频率相差不大,但与第一场景中布里尔小姐在家为去公共花园做准备相比有明显差别。就物质过程而言,其所延及的目标对象明显较少。在第一场景中,九个体现物质过程的动词延及九个目标对象,其中有六个目标对象是“狐皮围巾”,而在第三场景中,三个体现物质过程的动词延及三个目标对象,其中只有两个目标对象是“狐皮围巾”。此外,经对比发现,在这两个场景中布里尔小姐所发出的动作和涉及的环境成分也截然不同。如“抚弄”与“解下”相对,“拿出盒子”与“放进盒子”相对,以及“放在腿上”与“看也不看”相对。这些变化暗示她内心世界经历了由去公园时满心期待到返回家中后心灰意冷的情绪变化。再者,从体现行为过程的动词(“坐下”和“坐了”)和与其相关的环境成分(“很久”)可以看出回家后布里尔小姐的静止和呆滞,这与第一场景中布里尔小姐为去公园忙碌准备形成鲜明对比。而体现心理过程的动词(“觉得”和“听见”)和其目标对象(“哭声”)更加表明布里尔小姐精神沮丧,情绪低落。
年老体弱的布里尔小姐独自一人生活在法国小镇,作为一个社会边缘人的她无法融入充满排斥情绪的异域文化环境中。索普指出:“通过与狐皮围巾建立亲昵关系,布里尔小姐可以感受到她生活中从未能感受到过的关爱,理解和同情。”[11]然而,年轻恋人的讥讽让她深受打击,使其迫切渴望融入法国小镇群体生活的一丝丝幻想破灭。
四、结语
侨居在异域文化环境中的布里尔小姐不被所处的社会环境所接纳和认可,处于孤独和被边缘化的生存状态中。造成她这种生存状况的原因或许是异域文化氛围中充斥的排外情绪和法国小镇人们的冷漠无情。“来自他人或社会的冷眼、恶意、偏见以及与此伴随而来的孤独感是曼斯菲尔德作品中探讨的重要主题之一。”[12]通过对文本进行及物性系统分析,我们也可以感受到作者对社会边缘人物的同情与理解。“曼斯菲尔德一生都处于生活的边缘。”[13]通过对布里尔小姐边缘生存状态的描写,作者也抒发出其内心深处驱之不尽、挥之不去的边缘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