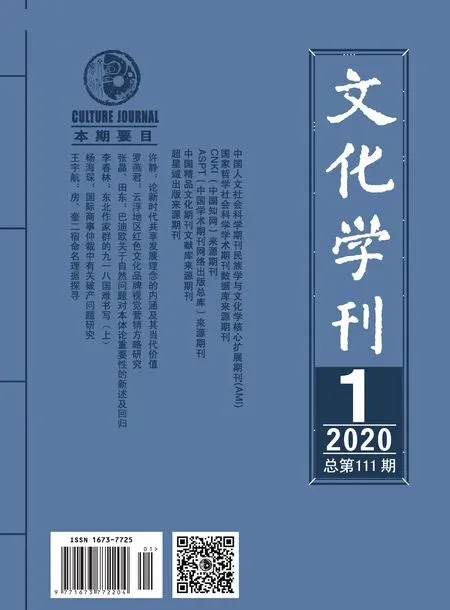罗尔斯契约论与传统契约论辨析
2020-01-02林劲博
林劲博 周 凡
在传统契约论的框架下,思想家们往往更多地去讨论政治权威和政治义务。作为传统契约论的集大成者,罗尔斯继承了其中的一些想法,但更多的,他将自己的研究重点放在了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的正义与公平这种基础性、根本性问题上,因此,本文的重点便是辨析罗尔斯的契约论与传统契约论之间的差异。
一、从自然状态到原初状态
(一)传统契约的自然状态
传统的社会契约论首先对人类的发展作了一个假设,认为人类最初来自原始社会的“自然状态”。在这其中,不得不提的便是英国著名的经验主义哲学家洛克。以洛克为开端和代表的传统契约论,提出在自然状态下人们从上天那得到了自由和平等。他也明确指出,这种权利来自自然状态下的自然法,而自然法来源于上帝。也正由于一切都来源于上帝,因此在上帝面前理应人人平等。
在洛克这里,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到其并不能回答自然法又从何而来的问题,那么自然法就必须也必然要作为一个先验的存在。洛克为了他的社会契约论的理论而预先设计了一个形而上学的先验的存在,这也成为传统契约论的一个理论基础。在这种语境下,自然状态要比社会国家先一步存在,在逻辑上自然状态也更容易成为人类的本真存在,成为在自然法引领下发展出来的良好状态,但是,毫无疑问,这种做法为传统契约论埋下了隐患,一个并不能被证明的存在是难以说服人的。
近代以来,随着哲学的进一步发展,对形而上学的质疑和批判一直都没有消散,新的理性与经验催生了新的思维方式,使得传统契约论的形而上学的基础开始出现松动,契约论者们也似乎难以自圆其说。在这种情况下,罗尔斯试图通过一种有别于形而上学的方法去重新考量契约论的合理性,尝试给权利的来源和契约的旅行寻找一个更加合理的解释。
(二)罗尔斯的原初状态
罗尔斯的原初状态,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它应被理解为一种用来达到某种确定的正义观的纯粹假设的状态”[1]。在原初状态下,人们处于一种被预设的纯粹自然状态下,一种“无知之幕”遮蔽了人们对于外部世界的认知。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能了解自己真实所处的阶级、自己拥有的财富等情况,甚至不知道自己的天赋才能的优劣。所以,无论作出偏袒任何一边的抉择,最后都是有可能使自己的利益受到不合理的损失。这样的话,由于“无知”,人们完全脱离具体的社会环境和历史环境,处于一种原初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人们作出的选择才是最真切的,才能体现最真实的想法。
为了作出理性客观的决策,罗尔斯提出“两害相权取其轻”的说法。人们出于理性判断,会在各种可能出现不同结果的选择当中选择出最好的,或者说最能接受的一种结果,来避免遭受更大的损失。而这种“最好的结果”正是人人平等。这种基于理性的抉择方式和现代的“博弈论”也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三)二者的辨析
从上文我们可以看到,在传统契约论看来,自由与平等的问题是被一个先验的形而上学的“自然法”所解决掉的,但他们难以回答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自由与平等就是必要的”,而在罗尔斯这里,他试图通过一种“原初状态”,一种最开始大家都混沌无知的预设状态来进行阐释。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都必然要担心相互之间讨论出来的结果在“无知之幕”揭开之后会对自己产生不合理的不利影响。那么,对于任何人来说,最保险的方法不过就是去设定人人平等、人人自由的法则,使“无知之幕”揭开之后自己一定可以接受。
对于这一部分,一方面需要做的是主体知识的限制,在这其中的无知并不是指人类在智力上的无知,而是有意识地排除一些可能会影响人们制定社会法则的信息的一种方式;另一方面是各方都了解一种“弱的善理论”,这是他所假设的“基本善”,而这其中包括对机会、对财富的渴望等,因此,他们为了达成这些目标也势必会作出一些选择与取舍。除了主体知识的限制,还需要重视的便是主体特性的设计。在这个时候,罗尔斯的设想是所有人都是自由、平等和理性的,他们可以平等参与构成真实世界中平等基础的讨论,同时在讨论中他们也拥有表达自身权益和需求的自由,这种自由是一种建立在义务和责任的基础之上的自由。当然,各方在参与讨论的过程中也必须是理性的,能够合理地衡量自己和他人之间的利益,最终可以作出适当的让步与妥协以达成统一的规则。
“无知之幕”的覆盖要求所有人都必须回到一种原初的状态。选择者所能了解与清楚的只有他们必须在他们将共同生活的社会之中达成合作,他们也必须保护自己的自由,扩大自己达到自身目的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就会选择“自由”“平等”,把公正和正义作为建设社会的基础。
二、从直觉判断到反思平衡
(一)传统契约论的直觉判断
西方契约论发展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便是直觉判断。通过这种方法,哲学家们试图通过直觉经验来逐步挖掘到一种可以指导人们道德实践的合乎规律的合理道德原则。但是,想要通过直觉判断的方法来使理论能够被大多数人所接收,“这种直觉就必须满足表述的明确性、规则的不可解释性、基本道德原则之间的协调性以及原则内容的共识性这四项条件”[2]。只有这样,直觉判断所产生的结果才具有自身的自明性。但是,从长远来看,这又是短见的,不能形成一个牢固的理论基础。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理解传统契约论为什么塑造了“自然法”这样一个概念。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自然法”是一个很难感觉或者说确定存在的东西,但是却又必须存在才能为其他学说打下基础。“自然法”的意义自然是有目共睹的,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自然法”的存在,使整个西方的政治思想充满了光明,但在时代进一步发展之后,“自然法”以及直觉判断方法的局限性日益显现,如何破局,成了罗尔斯思考的一个问题。
(二)罗尔斯的反思平衡方法
“反思平衡法是罗尔斯在批判和吸收直觉主义方法论的基础上结合契约论的理性主义传统而创立的。”[3]关于反思平衡法,罗尔斯自己也有一些论述:“它是一种平衡,因为我们的原则和判断最后得到了和谐;它又是反思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判断符合什么样的原则和什么前提下符合。”[4]
在这个地方,罗尔斯提出的反思平衡法,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直觉主义的发展。他对直觉主义的态度是复杂的。罗尔斯指出了直觉主义在原则问题上的一些矛盾以及其他的一些问题。在此批判的基础上,罗尔斯开始进一步论证自己的反思平衡的方法。他的反思平衡理论更像是一种直觉主义方法的一种批判性继承,通过将直觉主义与契约精神、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这些看似对立的方法进行适当的结合,来重新审视契约论。传统契约论通过直觉直接确定其存在的自然法与自然状态,在罗尔斯的语境下,是必须通过反思平衡然后最终得出的。罗尔斯尽量避免一种偶然性,而是试图将一切都建立在一种可靠的,可以确定、可以探究的必然性上。在推理的过程中,虽然罗尔斯偶尔还是会使用到直觉主义的一些方法,但更多的,罗尔斯是通过前提推出结论,一个环节推导到下一个环节,这样的话最后的结论是必然的,毋庸置疑。
总的来说,罗尔斯的方法就是将直觉主义和理性的反思相综合,通过不断的审慎、质疑、反思,以便最后能够进一步推导,而最后推导出的结论也将成为必然。在这种情况下,各种说法也就达到了一种平衡。
三、结语
罗尔斯的《正义论》从传统的契约论形式出发,在反思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对契约论的理解和新的阐释。事实上,传统的契约论诞生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在许多方面已经显现出自身的漏洞和不完美。在理论上,现代哲学甚至已经开始“釜底抽薪”,作为契约论基础的难以证明的自然状态和人性判断方式已经受到了剧烈的冲击。而本身的契约论对弱势群体的忽视,在一个更加强调关心和照顾弱势群体的现代社会,也难以继续保持自己的地位。通过原初状态的全新设计,罗尔斯重新确立了新的契约论基础,给契约论注入了新时代的活力,也指出了一条不一样的发展道路,而在思维的方式上,罗尔斯也完成了创新,以全新的反思平衡法的变革带来了思维方法的变革。总之,罗尔斯开启了契约论的全新时代,在自由主义的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