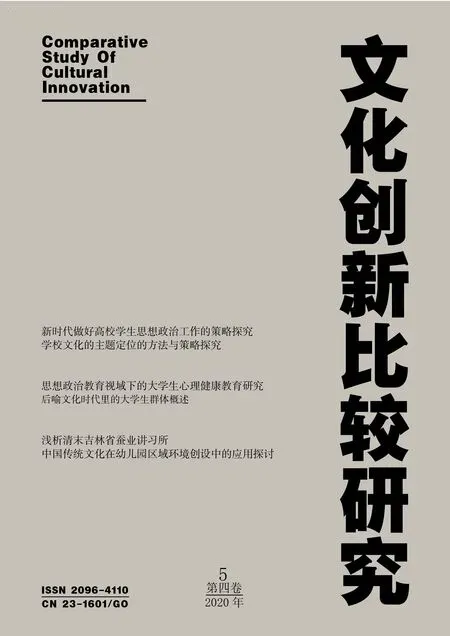浅析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布鲁”及其现代价值
2020-01-02银山
银山
(内蒙古师范大学民族学人类学学院,内蒙古呼和浩特 010022)
在世界文化的大板块中,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在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形成了不尽相同的文化特质。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早在20 世纪就已经受到关注。 随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了一系列的公约、条例,相继各国也陆陆续续制定了一些符合本国国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 与此同时, 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也给学术界带来了新的研究领域和研究视野。
“布鲁”作为蒙古族的一种体育文化项目,在2014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成了蒙古族重要的文化标志。 然而,直到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布鲁”才进入到专家学者们的研究视野。 目前“布鲁”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运动体育学研究,“布鲁” 作为民族体育项目的文化内涵研究,以及“布鲁”的分类和功能研究,而对现代价值以及传承发展研究相对不足。
随着人类生产力的解放,“布鲁” 从一个简单的狩猎工具到融体育、 娱乐、 竞技为一体的综合性活动项目, 它的演变某种程度上揭示了蒙古族文化的历史进程。因此,对其进行研究有利于让更多人了解这一独特的民族文化,也为“布鲁”文化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更大的空间,以响应国家对非物质文化的重视及保护。
1 布鲁及其演变历程
“布鲁”在蒙古语中是“投掷”的意思,其来源与其功用密切相关。布鲁通常用榆木、蒙古栎和柏等坚硬的木材制作。 前端弯曲的镰刀柄状形态, 全长65 cm 左右。 制作时直接选取形态类似布鲁的树或者在较粗的树上刻画截取, 有时也会把生长的树苗掰成布鲁的形态固定,待成熟后加工制作。
据史料记载,“布鲁” 最早是蒙古族祖先为了生存所需创造的狩猎器具。当时的“布鲁”只是一根小木棒,在热兵器还没有传入到内蒙古草原之前,日常生活中人们就用它狩猎、护身,战争时期还充当着作战武器。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 御敌防身这些功用逐渐地被其他工具代替。 于是人们又开始把它当成是一种强身健体、娱乐交流的竞技活动——布鲁。
内蒙古通辽市库伦旗是蒙古族传统“布鲁” 的故乡。在当地对于布鲁比赛由来流传着这样一则故事:在很久以前,王爷府有个叫海日图的公主,她从小练就了将布鲁投远投准的本领。有一天,公主想找个与自己能力相当的人来比试一番,并决定谁要赢了公主,就以身相许。 结果只有一个家境贫寒的叫巴特尔的人投的比公主又远又准。 王爷不愿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一个贫穷的牧民,并派人暗杀了巴特尔。草原上的人们听了十分同情这对苦命的情侣,于是为了纪念他们,每年都开始举行“布鲁”比赛。由此,这项活动便在蒙古族东部地区流传开来。
在近代以来,“布鲁”正式成为比赛项目是在1953年在赤峰市举办的内蒙古首届全运会上,从此“布鲁”得到了新生,以至于此后的现代“布鲁”更是像男儿三艺一样成了蒙古族民众的一种休闲娱乐的游戏方式,甚至更后来成了草原男儿们比技巧和力量的比赛形式, 以一种有趣的身份成了逢那达慕大会必举行的蒙古族传统体育运动项目。 至今,在科尔沁草原“布鲁”都很受欢迎, 很多蒙古族从少年时代开始把布鲁当成是一种随身技能在学习。 在民间,投掷“布鲁”不受时间、地点的限制,因此“布鲁”也成了少数民族运动会必不可少的竞技项目。
2 布鲁的分类及其功能
蒙古族在日常生活中根据自己的用途制作各种各样的布鲁,虽然布鲁的作法和种类很多,常见的布鲁可以大致分成杜争布鲁、恩根布鲁、图勒嘎布鲁、海木勒布鲁。
(1)杜争布鲁——是用铜、黄铜、铁、铅等金属分炼成心的形状, 布鲁的弯弧的一端上打孔用皮子连接在布鲁上。 大多时候连接的金属是朱如很(“朱如很”是蒙古语中“心”的意思)形状,所以也称朱如很布鲁。 杜争布鲁在短距离内杀伤力最大,适合打狼、野猪等猎物。放牛羊时不用朱如很布鲁, 孩子们也不能用朱如很布鲁, 荒郊野外和赶夜路的人为防身起见平常带朱如很布鲁。
(2)恩根布鲁——是把铅、铁、铜等金属固定在布鲁的头部而成的。 有的地方根据固定在布鲁头部的金属名称叫铅布鲁、铜布鲁等。恩根布鲁的掷距远易于打狐狸、兔子、野鸡等猎物。
(3)图勒嘎布鲁——是在布鲁的尖头上面刻好又细又深的“吉祥结”,后注入炼好的铅制作而成。 图勒嘎布鲁掷程远,易于猎杀兔子野鸡等猎物。
(4)海木勒布鲁——是布鲁的头部扁宽,边沿呈圆形,头部镶少量金属或不镶金属以保它的掷距和速度。海木勒布鲁常用于打兔子、野鸡等猎物以外,放牧、赶牛羊、娱乐、儿童的玩具等日常生活中常见。
传统娱乐活动中, 布鲁比赛项目主要有掷远和掷准,掷准又分为骑马掷准和徒步掷准。现代比赛专用的布鲁其长短、轻重等已具有了统一的标准和规格,在全国各类民族体育盛会上普遍使用。
3 布鲁的传承危机与现代价值
3.1 布鲁的传承危机
3.1.1 传承方式的局限
虽然“布鲁”经过了一个“原始形态”到“现代性能”的转变,尽管它的内涵及功用发生了变化,但在社会迅速发展的今天,“布鲁” 仍然以古老的形式被人们传承着。 可以说,“布鲁”的传承基本上靠着习俗的惯力,人们并没有随着时代的发展对其文化体系进行重塑和重构。所以在日趋多元化的现代社会里,“布鲁”在其利用方式以及管理方面显露出很大的缺陷,主要表现在:缺少对“布鲁”的认识和整理、观念陈旧,对于“布鲁”的开发应用过于追求经济效益, 没有捋清其本身蕴含的文化内涵,缺乏对其技术理论的指导和研究,导致后继无人, 无论是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角度还是运动项目的角度,传承人与继承人之间、教练员与运动员之间都缺乏系统的传授方式,这使得“布鲁”的发展滞后于时代发展,本以为是蒙古族传统项目的“布鲁”在热烈的市场竞争当中发挥着自己薄弱的作用和力量。
3.1.2 文化内涵的淡化
“布鲁”作为一种民族文化现象具有丰富的文化底蕴,是蒙古族祖先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通过实践来创造、积累并传承至今的,它作为一种历史的产物,必然也反映了当时的自然状态和社会的经济、政治、科技、文化等状况, 它是蒙古族人民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结晶。
如今,在现代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冲击下,所谓的现代文明对传统文化的影响越来越深, 不断发展更新的现代思想以及生活方式使得“原始文化”的生存空间不断萎缩,传统的那些思想以及观念日趋瓦解。随着人类生活水平的提高,如今在乡村,各种文化设施越来越健全,涌现了很多有趣的现代性悠闲娱乐方式,对“布鲁”的传承发展带来了强有力的冲击,使得“布鲁”这一蒙古族传统运动项目的发展空间日渐缩小, 开始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与此同时,“布鲁”所蕴含的文化底蕴也逐渐地淡出现代舞台。也许,这就是“布鲁”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挖掘、传承、保护、发展的重要原因所在。
3.1.3 传承主体的缺失
“当前在非物质遗产保护热潮中,‘传承’ 是核心,是灵魂。”(祁庆富《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传承及传承人》)非物质文化并不是强调“物”与“非物”的差别,而在于“传承”俩字,其实质就是传承文化的人。 而“物”与“非物”的根本差别也在于前者不依赖于“人”而存在,而后者的发展却离不开“人”,也就是说“传承人”不在了,非物质遗产也就不复存在了。
如今随着电子设备以及各种现代设施的出现,人们对传统运动项目的兴趣逐渐削弱,年青一代人们宁愿花钱去健身房锻炼身体也不愿意出去投掷“布鲁”,导致传承人与继承人直接出现年龄断层。 这种后继无人导致了“布鲁”传承主体范围的不断缩小,使其在发展传承中面临着较大的困境。
3.2 布鲁的现代价值
3.2.1 布鲁与生态保护意识
布鲁是蒙古族传统狩猎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用具,它同时也蕴含着蒙古族传统狩猎文化的富有创造力。蒙古族传统狩猎文化不是乱杀、杀绝猎物的野蛮文化,而是有打猎时间、猎杀禁忌的。蒙古族狩猎文化中包含着保护生态平衡的科学内容和对猎物的繁殖、关爱、保护等和谐共处的文化。蒙古族狩猎文化当中,有动物繁殖季节不能打猎、禁止打单行或一对行走的动物、禁止打单雄性动物群中的雄性等禁止。 布鲁不像直接致命的狩猎用具,布鲁一般是打伤或打晕,这不仅能防止打错猎物,而且易于活捉猎物,也是布鲁文化的生态意识体现所在。如今自然环境的退化导致,各种野生动物日渐变少。 蒙古族传统狩猎用具布鲁功能从打猎转变成体育娱乐项目。 这也是一种适应自然, 保护环境的体现。 传统用具的消失和功能转变体现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显现出人们逐渐意识到保护大自然, 跟大自然和谐共处。
3.2.2 予当代体育的深刻文化内涵
在奥林匹克更高、更快、更强的理念下,挑战人体极限的速度、力量、耐力项目占领主流. 在这种极度追求极限的西方体育文化的主导下, 中国体育变得极度浮躁、急功近利,频繁的兴奋剂问题、年龄门、球场黑哨等丑闻像毒瘤频发。 道德缺失、信仰缺失,造成体育界拜金、享乐主义盛行。 竞技体育出现的问题是社会问题的缩影,板不能只打在中国体育的身上. 现代标枪为运动项目列为奥运会项目, 蒙古族传统狩猎用具如同奥运会项目标枪,这是投掷武器不同发展的路径。经常锻炼有利于增强手臂的力量、灵敏度和准确度。掷布鲁承载的集中、耐心和背后的狩猎文化,可以赋予现代体育竞技深刻的内涵。
3.2.3 培养青少年尚武自强的素养
现在的中小学生,学业压力、升学压力、沉迷电子产品等外部因素和学校、 家长的重文轻武思想的干预下,青少年的身体素质和视力越来越下降的趋势。学校教育要面向未来、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 新时代不排斥历史,传统文化是我们的血脉。将蒙古族传统狩猎工具作出现代性的转形式诠释,将掷布鲁中推崇的掷远、掷准体现在体育教育中。布鲁作为一种体育文化运动,它对人的体力、眼力、全身的肌肉力量以及对身体的协调性,甚至对思想意志的训练都有很独特的要求。青少年作为祖国的未来, 需有尚武自强的心理素质和身心条件。 因此对于他们来说,通过“布鲁”的专项训练,可以提高他们对蒙古族传统文化甚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也可培养他们对于自己民族体育项目的热爱程度及参与程度,已逐渐达到中华民族的健康未来与安全。
3.2.4 促进民族团结和谐
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重建》一书中强调,将来的世界不是西方文明的独尊,而是一种不同文明的共存。虽然,在现代社会,西方文化已经成为主流,艺术、体育、经济各个领域深受影响,但是人类本身的历程已经说明,文化的多元性与趋同性是并存的, 也正因为文化的多元性才使人类发展多姿多彩,具有多种可能性与进步性。每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 自古以来掷布鲁比赛便是蒙古族非常有趣的传统活动,在“那达慕”节日聚会中开展,祈求国泰民安、人丁兴旺;通过比赛竞技,激发拼搏和竞争的精神;通过比赛严格的程序和礼节,培养民族谦让团结、 共同进步的文化氛围, 增强社会凝聚力、增进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具有积极作用。。
4 结语
“布鲁”从最初的狩猎器具,到现在的传统体育项目, 不论从历史渊源看还是从原始使用范围来看,“布鲁” 作为一种蒙古族传统的生活工具都具有一定的文化内涵和价值意义。
“布鲁”曾经在蒙古族人民的历史生活中扮演过重要的角色,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功能价值。随着时代的发展,“布鲁”的防身御敌功能已经成为历史,而面对现代社会,“布鲁”却以全新的“体育项目”留存并发展至今。这是时代进步、 社会文明发展的结果。 虽然与过去相比,“布鲁”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布鲁”,但是围绕“布鲁”这一器具发生的蒙古族历史文化印记不会消失,对探索蒙古族传统文化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们更应该保护和发扬这个灿烂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