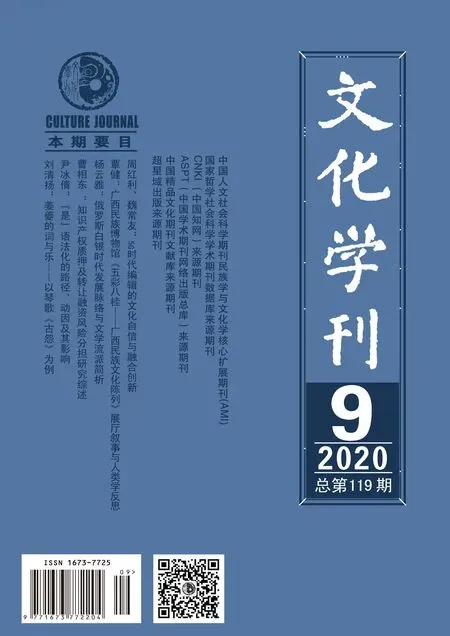雁归有时 潮来有汛
——《穆斯林的葬礼》中楚雁潮多重人物身份解读
2020-01-01钱毅珺刘祥安
钱毅珺 刘祥安
一、时代身份:复杂家族环境的见证者
曾有评论指出,《穆斯林的葬礼》在厚重的历史背景、沧桑的民族书写、开阔的时空氛围中,以独特的文学魅力征服了读者[1]。除却对京城穆斯林“玉器梁”一家三代人、60年兴衰沉浮的沉痛刻画这条主线,时代变迁所引发的创伤体验也成为其中重要的元素。在时代、民族与个人的悲剧三位一体地统一于“不幸”这一点时,个人的悲剧便不可避免了[2]。作为一种超民族、跨文化的产物,时代的创伤体验在楚雁潮的典型遭际中得到了集中体现与承袭、发展。
楚雁潮简单而复杂的家庭悲剧,是土地革命时期封建家庭的影射。简单与复杂并存是楚雁潮家庭构成的主要特点。从简单角度审视,楚雁潮的母亲一直担任小学教员,小学毕业后的姐姐在商店做会计工作;从复杂角度看,楚雁潮父亲的历史背景特殊,20世纪30年代的文化变革时期,身为中学国文兼英文教员的楚父在期间突然失踪,就此音讯全无,多年以来等同亡故。楚父的遭遇并未成为过去,反而不断刺激着楚雁潮的旧有创伤。在新社会,品学兼优的楚雁潮在考取北大并留校任教后在工作中接连受挫,这些经历虽然与楚雁潮的个人性格有关,但也与复杂的家族环境有着直接关系。特殊的历史时期以及传统伦理的影响,就令楚雁潮的悲愤化为普通知识分子对时代的无声反思。诚如马丽蓉所言:“楚雁潮的未老先衰,折射出了畸形生存环境下苦求生存与发展的一代知识分子注定悲剧的命运与结局。”[3]作为其中的典例,楚雁潮的个人遭际真实地反映了个体价值在当时特殊家族环境作用下的弱化。
二、社会身份:现代文明的追求者、传承者
徐其超认为,长篇小说的文化含量,在于以多元文化较大规模的整合,塑造出纵结历史、横参世界文化的典型形象[4]。据此标准,《穆斯林的葬礼》之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人物形象之丰满、多面。楚雁潮的人物形象无疑为此作出了卓越贡献——通过对他的角色塑造,现代知识分子的典型人格获得了极具张力的表现。他的一系列学术活动与情感经历的构建,也成为全书文化象征的有机组成和贯穿始终的情节线索。而在中西文化的横向比较与传统、现代意识的纵向交锋中,楚雁潮的社会身份又可据此细分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与“传统伦理秩序的挑战者”两类。
(一)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
作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毕业于北大西语系英语专业的人才,楚雁潮原本应在外文出版社的点名录用下,成为一名优秀的专业笔译员。然而,出于对北大师资缺乏的考虑,楚雁潮的恩师严教授挽留了这位得意门生。恩师对教育事业的奉献精神,在楚雁潮留校任教期间得到了极大的传承与发扬。与此同时,他仍倾注课余精力进行翻译工作,以求借此扩大中国文学的影响力,进一步实现中西文化的互通有无。
“冷峻的狄更斯、悲愤的哈代、幽默的马克·吐温、忧郁的夏洛蒂·勃朗特”[5],年轻的楚雁潮对20世纪60年代北大图书馆的英文原著如数家珍。令人喟叹的是,促使中西文化间这架鸿桥得以搭载的动因,却是让这位青年学者沉湎与追思的身世创伤。除了对母亲望子成龙的殷切、弥补姐姐为他中途辍学的遗憾,更多的是对父亲未竟事业的继承。基于此,楚雁潮对中国文学的英译这项生涯事件便不单是一位青年学者强盛的事业心与开阔学术视野的反映,更蕴含着作者借学术形式所寄托的时代忧思背后“强烈而深沉的历史使命感和忧患意识”[6]。楚雁潮翻译鲁迅《故事新编》中的《铸剑》,就是对其心灵深度所进行的一种全方位表现:
而更激起楚雁潮渴望一见的却是那个未曾出场的父亲干将,那个铸了剑又死于剑的人。……他给儿子留下了剑也留下了遗恨,留下了永难满足的愿望。儿子需要父亲。……他竟是这样一个只有鲁迅才写得出的“父亲”![7]
倘若中国文学的英译过程多维度地丰富了楚雁潮的人格内涵,那么他对外国文学的引介则为全书提供了中西交融、贯通的宏阔文化背景,并在现代语境中完成了对一系列人类母题的深度阐释。在他身上,知识分子所接受的现代教育熏陶与浸沐创伤后敏感、细腻而多情的人格特质以完美的比例调和,使他得以洞悉哈姆雷特跳入莪菲莉娅墓穴时自灵魂深处爆发出的深沉的绝望;使他得以《拜伦诗选》中海黛与唐璜古老的爱情母本,为韩新月构建起柏拉图式的美好理想;使他得以杰克·伦敦对生命韧性的礼赞,鼓舞韩新月击败无情的病魔与宿命……爱情、理想、生命、死亡,楚雁潮每一次对外国文学的引介都赋予了人类母题以跨文化、越时空的深层诠释,也成为他对理想世界寄以憧憬和期许的象征。然而,时代与自然命运的盘根交错又一次次将他推回现实的深渊。
值得关注的是,虽然肩负追求与传承现代文明的重任,但楚雁潮本身并不是“五四文化”模具简单的复制品。他已然摆脱了极端西化的时代遗流之裹挟,开始在冷静的反思中理性寻求文化的再定位。
(二)传统伦理秩序的挑战者
除却构建一方横跨中西、纵结古今的文化参照系,借此实现人物形象之丰满、主旨意蕴之深刻,现代文明更是以其突出的自由精神缔结了楚雁潮与韩新月的情缘。然而,基于传统社会角色的定位、越族隔教的矛盾与特定时代下空前强化的阶级轨界,这段恋情必定因挑战伦理、越界教门与悖逆时潮而重重受阻。
作为人最可贵的自由本质,“爱情”这一人类的神圣母题在小说真挚虔诚的书写中,激越地展现出人对高层次价值的执着追寻,但在楚、韩之间,它始终以一种深沉而压抑的表现形式存在。这是因为楚雁潮始终被其身世创伤所影响。由此观之,特定事件的激发效应,极具契机地爆破了横亘在楚、韩间的世俗壁垒。与此同时,楚雁潮身上所象征的知识分子人格得以完成更深层次的现代转型。
刘白羽认为:“楚雁潮突然而来的爱情,由于铺垫不够,过分突兀,从而不能出神入化,精韧至微,则隔矣。”[8]暂且不论全书所营造的象征氛围,单就楚雁潮的心路变化就足以推动情节的进一步发展。特殊的时代背景让楚雁潮正视自己的感情,韩新月的病情间接弱化了楚、韩二人的“师生”角色,为楚雁潮向韩新月表白提供了可能。在此期间,为传统宗教文化所重视的民族之别、教门之隔始终不曾纳入两位当事人所代表的现代文明体系的考量中:“我们之间,可以谈……爱情吗?您是老师,我是学生……”[9]楚雁潮丰沛的感情却在这青涩之问中冲破了世俗道德的框架、阶级轨界的束缚,双方心灵轨迹的推演正是伦理与阶级秩序在现代话语结构下重塑的表现:
他期望新月在事业和爱情上都取得圆满成功,而这些都不必非他楚雁潮莫属,因为他比谁都明白,自己在出生之前就命中注定要走一条坎坷的路,……但是,后来的情况发生了太大的变化,……该做的,他都做到了;能做的,他也都尽力做到了;他所余的,只有自己的一腔热血和一颗赤诚的心,现在,他决计把这些也都献给她![10]
除此之外,在“舆论误解”与“倾诉心声”两阶段,楚雁潮先后以超越革命史观的纯文学视角,对鲁迅的打油诗《我的失恋》和马克思献燕妮的情诗予以解析与吟咏,在彰显现代知识分子所独具的前瞻性视野、批判性思辨能力之余,也以颇为戏谑、揶揄的口吻,张弛有度地调整了情节节奏,并寓以作者对左倾时代氛围的反思情结。
三、民族身份:伊斯兰文明解构与重建的推动者
徐其超、吕豪爽评估作品价值时认为:“小说不仅将回族置于中华民族这个参照系中,写了回族的历史和现状,还将中华民族置于世界各民族这个人类圈中,力图勾勒出所有民族在寻求民族性与世界性、民族性与现代性契合的过程中所必经的共性意义上的矛盾与尴尬,展示在战争与文明、传统与现代决斗中人性的复杂和人生的困惑,启迪人们领悟到‘重塑民族魂’应当是包括回族在内的整个中华民族所共同面临的历史抉择。这就使作品具有了更广泛的普遍意义。”[11]这一观点尝试对文化新生的定律作出阐释,即唯有从内部自我否定,予其内涵以与时俱进地调适或延展,古老的文明成果方可以生生不息的活力代代相衍。作为全书重点展现的民族特色,伊斯兰文明在新时期的解构与重建自然成为作品多元主题的有机组成。楚、韩之间的爱情元素,除却对特定时代氛围中固化的伦理道德与阶级秩序产生冲击,更成为民族文化解构、互补与重建的重要动因。
杨文笔指出:“没有悲剧就没有悲壮,没有悲壮也就没有崇高。一部真正深沉的文学是崇高精神悲剧演绎下的升华。于是为了激扬荡魂的悲壮,塑造撼魄的崇高,挖掘悲剧展现悲剧成为了霍达文学创造的至高境界的追求。”[12]作为浓缩了悲剧精神的载体,楚、韩的跨族爱情对解构伊斯兰文明的研究,需要立足于韩新月生身父母——韩子奇与梁冰玉间的“战时爱情”。
路文彬在对中国小说悲剧精神的研究中指出,悲剧深刻而隐秘的来源,始于心灵寄寓与生存执念的对抗[13]。面对回、汉文化与传统、现代范式的激烈碰撞所引发的痛苦,韩子奇的一生都在两种力量的消长中盘桓。发妻梁君璧所代表的伊斯兰文明和东方传统伦理,与爱人梁冰玉所象征的西式现代文明矛盾重重。前者于平时所重视的“是以西方的传统观念为原则的,并非国人所理解的世俗意义上的悲剧。它浸含着某种形而上的宗教情怀,是人类针对自身原罪的宣泄与救赎”[14],在悲剧性的时代命运中被人欲本能的觉醒和解放所取代。藉以局外的现代视域不难做出这样的归结:“韩子奇同梁氏姐妹超越道德伦理的纠葛,实则反映了人在时代的灾难中对良好生存环境的渴望与呼盼。”[15]然而,作为深陷家庭风暴的当事人,在回文化的宗教熏陶与汉文化的世俗经验中成长起来的韩太太,绝不可能理解战乱的时代因素如何释放了持久压抑的人性,更不必说以理性的现代视域去审视自己的苦难之源和这段不伦之恋了。时代、伦理与教义的综合统一所形成的强大保守势力,在韩子奇退守型主位人格的襄助下,成功镇压外部的剧烈冲击、动荡,暂时遏制了现代文化解构与改造古旧伊斯兰文明的可能。
然而,在霍达的理解中,“这种撞击和融合都是痛苦的,但又是不可避免的,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这样延续发展的,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16]。上一代对束缚人性自由的古教义、旧伦理的改造,却以爱情悲剧收场。然而,楚雁潮破世俗、逾教门的无畏勇气与抗争精神,首次沉重撼动了韩太太心中坚不可摧的文化防线,逐渐建构起回、汉文化与传统、现代文明的引桥。在此期间,因身世创伤而压抑已久的刚强魄力自楚雁潮的灵魂深处爆发,这种美学描写不仅塑造了新知识分子的不卑不亢的风骨,也体现了对回族传统文化进行改造的决心。面对韩太太咄咄逼人的教门之问,楚雁潮从容宣称:“我不信‘菩萨’,不信任何宗教,但是,我尊重你们的宗教信仰,伊斯兰教主张和平和仁爱,这其实也是人类的一个共同的美好的愿望”[17];面对郑晓京来势汹汹的阶级责问,楚雁潮坦然为爱发声:“无产阶级应该比任何阶级都更认识‘人’、尊重‘人’!请你不要用不知从哪儿捡来的尺子来丈量我,你不具备这个资格!”[18]相较外部保守势力的重重阻挠,楚雁潮更无法接受恋人不战而败的卑微自弃。他质问新月:“我是一个感情泛滥、随处抛洒、随处赐予以换取别人的感激的伪善者吗?你是一个精神世界一贫如洗、仰赖别人感情的施舍的乞丐吗?”[19]可他披荆斩棘的昂扬斗志与铿锵决心,最终却化为一串落在新月遗容间的吻:“这和着泪水的吻,是他们的第一次吻,也是最后一次;是初恋的吻,也是诀别的吻!”[20]吻别之中的深烈爱意绝望得疯狂,拷问着压抑的时代,也拷问着不幸的命运,拷问着“博雅”宅中的未亡人,更拷问着不容他们结合的刻板伦理、僵化阶级、愚昧传统与滞重的伊斯兰文明!楚雁潮身上象征的灭礼破俗的叛逆炙烤着韩太太庇荫于宗教道德下的灵魂,新月的死本该是她恪守传统教义的证据,如今却成为她不安与负罪感的来源——她“惊醒”般地将楚雁潮推出“博雅”宅,本能地想要捍卫自己最后的文化防线,殊不知,这位知识青年的泪吻有如千年古尸开棺时窜入的一缕空气,就此不可逆转地开启了伊斯兰文明在现代语境下解构重建的秘钥。
倘若楚雁潮这个异教徒的吻仅仅震荡了“博雅”宅在伦理旧秩与狭隘教义规束下僵滞的空气,他在回民公墓为新月履行丧俗、刻立墓碑的一系列逾矩之举才真正从广义上实现了回、汉文化体系交融下重建伊斯兰文明的可能。
被痛苦粉碎了的楚雁潮跳下墓穴!……没有任何人阻拦他。除了天星和陈淑彦,谁也不认识他,谁也不知道他不是穆斯林,这个墓地上也绝不会有汉人来。他们认为,这个人毫无疑问是新月的亲人了![21]
在这非常规的、宗教伦理失序的语境下,汉人楚雁潮从穆斯林中获悉了身份认同。自这一刻起,楚雁潮与韩新月的爱情在超越宗教伦理的语境中得到承认和祝福;回、汉文化与传统、现代文明泾渭分明的隔阂,在昏暝幽冷的墓穴里骤然消逝。现实意义上,这“四近无生人气,心里空空洞洞”[22]的地方是亡人新月的墓穴;文化意义上,这也是伊斯兰文明在自我解构与不同文化体系的互补重建中得觅新生的摇篮;情感意义上,这是楚雁潮与韩新月共同躺过的一块土地,是他在葬礼仪式中亲手布设的婚房。这种爱是超越国界、民族、伦理乃至现实的,“是岁寒不凋、风雨难摧、根枝连理、花开并蒂的长青之树。”[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