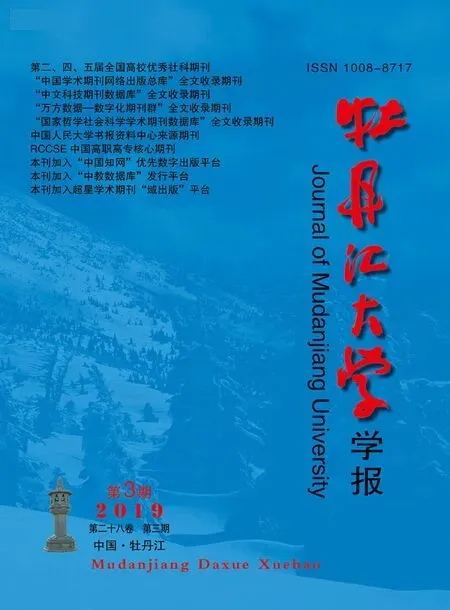从《母语唤醒的词》看鲁若迪基诗歌的民族性和现代性
2019-12-30崔晓岚
崔 晓 岚
(云南师范大学,云南 昆明 650500)
普米族诗人鲁若迪基,是云南少数民族诗人中一颗璀璨耀眼的明星。曾荣获两次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的经历是对他创作的肯定。他的家乡地处小凉山,正是这片特殊的土地孕育出了动人心弦的诗歌。美丽的泸沽湖,神秘的玉龙雪山,奔腾不息的金沙江和绵延不绝的小凉山,这些充满魅力的景象在他的诗歌中频繁出现。把家乡的独特景物带入诗歌,让他的作品有了明显的地域和民族色彩。在这些诗中,也充满了他对民族的过去和未来的思考,对民族美好品质的歌颂和对民族文化发展的忧虑。
一、 对民族性的展示和歌唱
文学是对社会生活的反映。一定的民族,在繁衍生息的发展过程中,由于长期生活在一个固定的地域,经受相同的地理环境、气候、自然环境的陶冶,养成了共同的生活方式,形成一定的风俗习惯、民族心理和民族精神,他们的生活从而呈现着鲜明的民族特色。阅读鲁若迪基的诗歌我们会发现,在他的诗歌中对家乡小凉山地区的描写有大量的笔墨,对民族的生活习俗和节日的呈现为读者提供了一扇了解普米族文化的窗口,也使其诗歌具有了民族性的特征。他曾说,“少数民族文学最重要的特性是它的‘民族性’。民族性不仅是民风民俗、民族服饰,还是一种内在精神。我们少数民族作者就是应该去书写这种最内在的,只属于这一民族的东西”。[1]对于民族性的书写是基于作者对本民族文化的深深认同感。在《三江之门》中,作者写道“让我自豪的说/我是天的儿子/我是地的儿子/我是天地间站立的普米人。”[2]这几句诗直抒胸臆,利用“我是……”的句式,直接抒发内心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只有对本民族文化有着发自内心的认同和热爱,才会说出这样饱含浓烈感情的话语。
总有一棵树属于我/某天,人们会将它砍伐/劈开后垒成9层/让我在棺木里/端坐成母腹中胎儿的模样/在烈火中顺着指路径/找到祖先的天堂/人们会把我的13节骨头/用蒿枝做成筷子/捡拾在羊毛上/装进土罐中/送到祖先聚集的罐罐山上……/那天,当一位族内的长辈/指着一座山/说我们家族的罐罐山就在那里/我久久望着他手指的方向/怕将来走错了路/那里森林茂密/山脚下溪流淙淙/我莫名地感动起来/呵,今后无论身处天南地北/我最终都会走向这里/见到那些骑虎射日的人——《罐罐山》[3]
这首短诗用白描的手法,向读者展示的是普米族的丧葬仪式,这是普米族特有的风俗习惯。“我久久望着他手指的方向/怕将来走错了路”体现出诗人对民族的根的坚定和热爱,“今后无论身处天南海北/我最终都会走向这里/见到那些骑虎射日的人”这里的“骑虎射日的人”是指普米族的祖先,无论走多远,都不会忘记自己普米族的身份和历史,因为这是自己的民族,自己的根,表现了诗人对本民族文化的强烈认同感。只有发自内心的对祖先和民族的尊敬和热爱才会心甘情愿的死后回归故里。小诗字里行间充满了作者对本民族的热爱,读来感人肺腑,令人深思。
在我国的少数民族中,有许多民族拥有自己的母语。语言不仅仅是交流的工具,更是维系一个族群重要的纽带。普米族也有着自己的母语。鲁若迪基在诗歌《母语》中写道“这时候,他相信/有些事物/更需要用母语沟通”“他每指一样东西/祖先命名的词就随口而出/这个石头城唯一的普米老人/用普米语让我感受了/石头的温度/石头的爱情/石头的顽强/他让我品尝自酿的酒/临走还送了满满一壶/我拎在手里/感到它比一座城还沉”。[4]这是作者在异乡遇到同族人的场景。有的话语,需要有共同的记忆才能产生共鸣,有些事物,更需要用母语沟通才能简单明了。在异乡,听到熟悉的音调和词语,可能会一瞬间热泪盈眶,因此许多读者会对这一感情产生共鸣。诗中的母语是连接两个同族人沟通的桥梁,通过用熟悉的母语的交流,表达了作者对于母语的信仰和崇敬。满满的一壶酒比一座城还沉,按照客观规律是不可能存在这样的现象。这里诗人用夸张的手法写出了手里的酒的分量,不仅仅是一壶酒,更是深重的同族人的情谊。同时也表现母语的不可替代性和顽强的生命力,在作者心中重要的地位。
信仰是对某种思想或者宗教的信奉和敬仰。鲁若迪基曾说,“我的诗歌的民族性,表现在我的诗里有普米族文化的烙印:人不是这个世界的主宰,万物有灵,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等。”[5]他在《神的模样》中写道“无数个山神的名字/河流一样/从父亲口里流出来/浇灌着我梦幻的世界/袅袅香火里/我睁大眼睛/希望能看到山神显灵”“如今,在遥远的地方/每次默念道‘果流斯布烔’/眼前就会浮现出/父母慈祥的面容”[6]。诗人小时候从父母那里得到对于神的幻想,父母对神的供奉和崇敬深深地影响了诗人,这是传统文化信仰的潜移默化。“果流斯布烔”是护佑族人的村庄和山神,普米族人敬奉着大自然的行为,是万物有灵概念的延伸。如今,每次听到山神的名字,诗人脑海中就会浮现父母的面容。将神和父母联系到一起,不仅表达了诗人对于神的崇敬,从中还可以体会出作者对于父母的尊敬和信仰。
鲁若迪基的诗歌中还有很多地方都表现出了他对民族的热爱,对村民美好品质的歌颂。作为普米族文化对外宣传的代言人,他在诗歌展现了普米文化的丰富多彩之余,也在深深地思考着民族文化的出路。
二、 对于现代性的批判和追求
文学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它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发展,不可避免地被打上时代的烙印。在鲁若迪基的诗歌里,读者不仅可以感受到民族性,还可以感受到时代的气息。社会中的种种问题,在诗歌中一一呈现。透过这些短短的诗行,读者可以依稀感受到诗人对于民族现状的焦虑和对于未来的思考。当然,对于现代性的展示是文学发展的必然要求,用现代眼光审视地域和民族文化,从中深刻地表现出民族自省意识和批判意识,是一个民族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起点。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速,需要越来越多的资源来支撑经济的增长,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态问题。大气污染让蓝色的天空变成一种奢侈的体验,过度砍伐让从前茂密的丛林变成光秃秃的山岗,对野生动物的生活的影响导致其数量锐减甚至走向灭绝……这些问题都是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在鲁若迪基的诗歌中也有着清晰的呈现。在《老人的山岗》中作者是这样描写的,“高高的烟囱/整日里冒着白烟/远远望去/就像一个老人坐在那里吸烟”“山肚子里的石头/被渐渐掏空/一个夜晚/我听到了几声山的咳嗽/然后是一声巨响”[7]。这些场景无一不暗示着生态环境的岌岌可危。“老人”“吸烟”“掏空”“咳嗽”简单的几个词将一个年迈的健康状况令人担忧的老人的形象跃然纸上。当然,这里的老人指的是山岗,是自然生态。山岗如同一位生命垂危的老人,艰难地支撑着身体。而造成生态恶化的是过度开采的人类,这是现代化带来的恶果。在《洋涧槽》中,作者用回忆的视角带我们回到三十年前的伐木地,那里曾是茂盛的密林,有着雀跃的小摊贩和系着围裙在食堂忙碌的女工。而今一切都不在了,周围都是空荡荡的。今夕的对比,更能体现出如今场景的凄凉与落寞。昔日的热闹与今天的荒凉,这正是现代化进程带来的负面影响。“我木桩一样站着/仿佛在等待/一场浩劫后/荒芜和落寞的判词。”[8]究竟是谁来评判这场浩劫,谁应该承担这样的后果,诗人并没有说明,而是留给读者无尽的回味,反思人类所犯下的罪行。
现代化带来的不好的影响不仅仅表现在生态问题上,就连平日里生活的也和过去不同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疏远和陌生。曾经寨子里的木匠“勒勒”无私为他人制作精美的箱子,轻巧的鞍子,却没有为自己考虑,甚至为自己做棺木的板子都没有留下一块。在他去世的时候,“男人们默默含着伤悲/女人们数着你的好/伏倒成片/哭声比火焰还高”[9]。村民之间的感情是那么真挚和纯粹,没有伪装和勾心斗角。而如今在一条偏僻的路上,“我”的前面走着一个穿着短裙的女孩子,当她发现我的存在后紧张不安的心情让“我”不知所措,即使放慢了步子,同她保持一定的距离也不能让“我”感到自在,“索性蹲在路边/成为一块石头”。人与人之间的信任随着现代化社会的推进变得脆弱不堪,距离让我们越来越陌生,只能退回自己相对比较安全的领域。这是现代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之一,面对这样缺乏人情味的社会,诗人只能发出沉重的叹息。
如今,社会问题也层出不穷。对于少数民族地区,人员的流动量很大,外出务工问题也曾一度成为社会的热点的问题。在鲁若迪基的诗歌中也反映了这一个现象,“乡长说这个村缺水/饭也吃不饱/妇女都外出打工了/是个光棍村/有七八五十六个光棍/县长戏说请他与寡妇村联系一下/然后拍板解决了人畜引水问题/水引来了/温饱问题自然解决了/可是,那些外出打工的妇女/还是没有回来/听说有几个在春节回了趟家/又把在家的小妹带走了。”[10]作者单纯用白描的写作手法,向读者陈述着客观事实,并没有夹杂着个人的态度和情绪,却传达了社会问题的严重性。由于缺水等问题,传统的生活方式已经不能满足乡里人民的日常生活,为了更好的生活,妇女们只好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外出务工。即使是解决了水的问题,人们也不愿意再回到乡村里过以前的生活,甚至回来带走了家人。人们这样的追求自然无可厚非,可是现代化给乡镇带来必不可少的转变,转变过程中带来的问题也是不容忽视的,现代性带来的结果有好有坏,应当向好的结果迈进而把坏的伤害降到最低。
人情味在这个经济迅速发展的社会变得越来越少了。弱肉强食,强者对于弱者的侵略和征服已经达到了人们无法想象的地步。对于处在弱势的民族文化和边缘文化也是如此。诗人在《一群羊从县城走过》中写道“一群羊被吆喝着/走过县城/所有的车辆慢下来/甚至停下来/让它们走过/羊不时看看四周/再警惕地迈动步子/似乎在高楼大厦后面/隐藏着比狼更可怕的动物/它们在阳光的照耀下/小心翼翼地走向屠宰场。”[11]羊,本应在乡村的草地上吃着草,而它们被人“吆喝”着走进了县城,一个它们完全陌生的地方。面对路上为它们减速甚至停靠的车辆,并没有让它们感到舒适,而是更加警惕地迈着步子,好像在现代化的城市的背后,隐藏着更加可怕的东西。最后一句特别触目惊心,在灿烂的阳光的照耀下,它们小心翼翼地走向死亡。“屠宰场”是噩梦的终点,对于这群羊来说,走进县城就是一场噩梦,如今,噩梦要结束了,却没有让读者松一口气,而是更加痛心和无力感。这里的“羊”的隐喻意非常多,在此我理解为面对全球化文化的入侵,处于劣势地位的少数民族文化和边缘文化。在全球化的大潮中,它们不能自主,难以自控,只能任人宰割直至结束生命,看似对少数民族和边缘文化的尊重(“车辆慢下来/甚至停下来”),其实并没有什么平等的待遇,依然不能自已。短短的几句诗歌将现代文明对少数民族和边缘文化的吞噬场景勾勒得淋漓尽致,带给读者的不仅是痛心,还有深思。
对于现代化出现的这些问题,鲁若迪基的诗歌中不仅有展现,还有自己的思考。在诗歌《那些偶然的事物》中关于冰和水流动与固守的看法,面对全球化的大潮,不同的人,不同的民族都有自己的做法。一些民族跟随着主流大军努力地融合进去,像诗中的水一样相拥前行,无疑,如果跟随大家而不加思考地融合,可能会丧失自己的个性,但是结伴而行的人众多。而那些固守自己特点的民族,因为一些不同而被留了下来,可能它们意识到的时候已经是和大众有一段距离了。为此,他们也迷茫过,也挣扎过,面对自己的特殊特质,是选择改变还是坚守,处于那个时期的民族还是迷茫不知的。这首诗形象地用冰和水写出了面对世界大潮来袭时作者内心的挣扎状态,选择的后果和未来的未知。诗的基调有些悲观,可是正是这些忧虑的思考让他的诗歌有了重量。
对于现代性,鲁若迪基不是一味的批判。因为处在这个变化剧烈的时代,不是一味地拒绝就可以避免一切悲剧的发生。要想发展,还是要作出相应的对策来应对这一趋势。诗人一方面不希望家乡和民族美好的事物被磨灭和吞噬,另一方面又希望全球化大潮为家乡和民族带来美好的契机。这位肩负着普米族文化传承任务的新星,在当下这个全球化的时代,为普米族的诗歌和文化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民族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