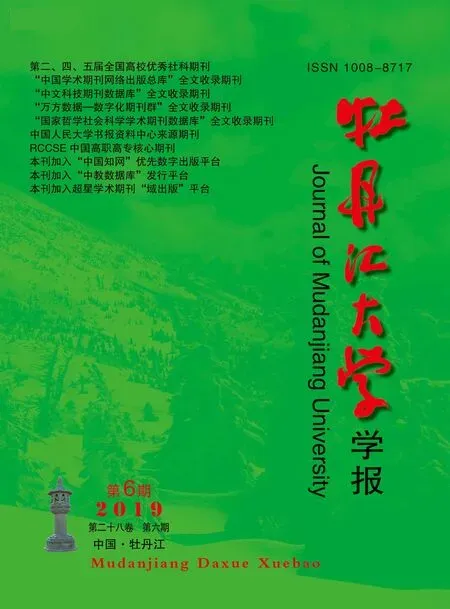《孟子》中“天”字涵义辨析
——兼论“天”在孟子哲学中的地位
2019-12-29张玉杰
张 玉 杰
(上海师范大学 哲学系,上海 200234)
“天”是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在《孟子》之前,一些经典如《诗经》《尚书》《左传》《国语》《论语》中出现了大量的“天”字,并且涵义不一。《孟子》一书也不例外,“天”字共出现289次,除去“天下”(172次)和“天子”(35次)等具有特定涵义的词外,还有“天”字82次(杨伯峻先生统计“天”字出现81次,[1]据笔者统计应该是82次。)。这82个“天”字的涵义不尽相同,其具体内涵很值得我们去辨析。人们(如冯友兰)[2]一般认为天有四义:自然之天、主宰之天、命运之天和义理之天(冯先生在《中国哲学史》认为“天”有五种涵义,其实他所说的物质之天可以归到自然之天中去,所以大体上说“天”有四种涵义。),《孟子》之中的“天”兼有上述四种涵义,除此之外,孟子的“天”还有“民意之天”一义。
一、 自然之天
“天”的第一层涵义即所谓自然之天,它既可指与地相对的物质之天,又指整个自然界。“天”的这层意思在《孟子》中共出现10次。在孟子之前,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此处的“天”既包括四时,又包括自然界中的各种事物,显然指整个自然界。孟子继承了孔子关于自然之天的思想,他说:“七八月之间旱,则苗槁矣。天油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浡然兴之矣!”(《孟子·梁惠王上》,下引《孟子》只注篇名,下同。)此处的“天”既能干旱,又能“作云”“下雨”,很明显指的是自然之天。
孟子还认为自然之天是有其客观规律的,而这种客观规律是人可以掌握的并利用它来服务于人类。孟子说:“天之高也,星辰之远也,苟求其故,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至也。”(《离娄下》)对此,朱子解释说:“故,其已然之迹。”(《四书章句集注》)“天虽高,星辰虽远,然求其已然之迹,则其运有常。虽千岁之久,其日至之夜,可坐而得。”(《四书章句集注》)即说只要掌握了自然的运行规律,那么即使一千年后的冬至,也都可以坐着推算出来。这颇像后来荀子所讲的“制天命而用之”,只是孟子没有荀子“天人之分”的理论那么精细。
二、 主宰之天
孟子的“天”不仅指自然之天,还有主宰之天的涵义。“天”的这层内涵在《孟子》书中共出现12次。孟子引用《诗经》中的话说:“畏天之威,于时保之。”(《梁惠王下》)此处的天有威严,显然指的是主宰之天。不仅如此,世界上的事物都是天所产生出来的,孟子说:“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滕文公上》)既然世上的事物都以天为本源,那么人事当然也不例外:“非天之降才尔殊也”(《告子上》),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告子下》),在此处,人的“才质”和“大任”都是天所赋予的,这样的天就类似于西方宗教中无所不能的上帝,从而具有主宰之义,这个意义上的天也可以称之为宗教之天。
孟子的“天”虽然具有主宰之义,类似宗教中的神灵,但是孟子并不否认人的主观能动性。如他说:“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公孙丑下》)初看起来,孟子好像强调天平治天下,强调天对人的主宰,但其实这句话的最主要的内涵是“平治天下,舍我其谁”,这只不过是用天的神圣性来突出孟子本人“平治天下”的大志。这样主宰之天的存在,不仅没有否认人的积极努力,反而是借天的至高无上性来强化人的主体性。更进一步他认为人意高于天意,他两次引用《尚书.太甲篇》的话说:“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分别见于《离娄上》和《公孙丑上》)即说,天所造成的罪孽还可以逃开,自己所造的孽却躲不开,这样天的主宰性就从属于人的主体性。
三、 民意之天
如上所述,孟子的主宰之天主要强调的是天意之后的人意。更进一步,在政治问题上,他还用“天”来代表“民意”,以突出民意的可贵性,此即所谓的“民意之天”。这层含义的“天”在《孟子》中共有25处。《孟子·公孙丑下》载:或问曰:“劝其伐燕,有诸?”曰:“未也。”沈同问“燕可伐与?”吾应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则将应之曰,“为天吏则可以伐之。”在上述引文中,孟子强调只有“天吏”才可以讨伐无道的燕国,那么“天吏”到底指的是什么呢?孟子说:“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则天下之商皆悦,而愿藏于其市矣;关,讥而不征,则天下之旅皆悦,而愿出于其路矣;耕者,助而不税,则天下之农皆悦,而愿耕于其野矣;廛,无夫里之布,则天下之民皆悦,而愿为之氓矣。”(《公孙丑上》由此可知,所谓“天吏”即能给百姓以幸福安康生活的君主,这就将天的神圣性虚化了,代替它的是民意的至高无上性,这表明孟子的天意不过是民意的另一种表述方式罢了,目的是为了突出民意的可贵性。
孟子在评论尧把帝位禅让给舜这件事上,对于民意之天解释的更加清楚。据《万章上》载:“万章曰:‘尧以天下与舜,有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然则舜有天下也,孰与之?’曰:‘天与之。’‘天与之者,谆谆然命之乎?’曰:‘否。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曰:‘以行与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荐人于天,不能使天与之天下,……昔者尧荐舜于天而天受之,暴之于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曰:‘敢问荐之于天而天受之,暴之于民而民受之,如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与之,人与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尧崩,三年之丧毕,舜避尧之子於南河之南。天子诸侯朝觐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讼狱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尧之子而讴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而居尧之宫,逼尧之子:是篡也,非天与也。泰誓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此之谓也。”初看起来,上述这段引文中的“天与之”貌似君权神授,但从“以行与事示之”来看,这里的“天”实际上还是民意的代名词:所谓“天与之”实为“民与之”,“尧荐舜于天”实为“尧荐舜于民”或“暴(即“曝”)之于民”,“天受之”即“民受之”。孟子最后引用《尚书》中的“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就更加说明了天意即民意,揭示出民意之天的内涵。
四、命运之天
除了上述几种意思之外,孟子所谓的“天”还有命运之天这层含义,这样的“天”在《孟子》一书中出现了6次。所谓的命运之天,指的是人力所不能决定的东西,所以孟子说:“非人之所能为也,天也。”(《万章上》)孟子在回答滕文公关于“齐人将筑薛”这件事情上说:“君子创业垂统,为可继也。若夫成功,则天也。”(《梁惠王上》)即说,君子开创出一番事业以传之子孙,至于能不能最终实现王道,则取决于上天。这里的上天显然是人力所无可奈何的,是人力之外的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就是命运之天,又可称之为天或命。孟子总结命运之天说:“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万章上》)在这里,孟子虽然区别了天和命,其实两者没有多大区别,两者都是人力所无可奈何的,所以我们也可将孟子的命运之天称作“命”。简言之,命运即人力所无可奈何所不能主宰的东西。
如前所述,命运之天是人力所无可奈何的,那么人是不是应该消极地等待命运的到来呢?孟子的答案是否定的,他提出“顺受正命”的思想:“莫非命也,顺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于岩墙之下。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尽心上》)所谓“正命”即在命运之天的范围内积极发挥人的主体性以实现人的价值,而“非正命”就是没有充分发挥人的主体性,从而也没有完全体现出人的价值。所以“知命”的人是不会因为有人力所不能主宰的东西就放弃人的努力的,正如张岱年先生所说的“人事已尽,而还不能成功,便是命所使然。此一则非人力不到,二则非环境中某一人或某一事所致。知命则既可不自悔自憾,又可不怨尤任何个人。如此便能保持快乐的态度,而不至于忧闷了。”[3]
五、义理之天
义理之天是孟子的“天”的另一层含义,这层含义的“天”在《孟子》中出现了29次。孟子认为,作为义理之天的“天”是道德法则的本体。孟子说:“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告子上》)心的功能是反省,心的反省功能是人性善的原因(“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而心的反省功能是天赋予的,这样天便成了人性善的最终根源。在另一处,他引《诗经》的话说:“天生蒸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告子上》)即说,人之所以喜欢美好的品德,是因为民众把握了天所赋予的法则,这样“天”便成了道德法则的本体,是事物之所当然的最终依据,这样的“天”具有形上学的意义,此即所谓义理之天。由于“天”是道德法则的本体,所以一些道德范畴(如仁义礼智信)都跟天联系起来了。孟子说:“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告子上》)“天爵”即“德义可尊,自然之贵也”(《四书章句集注》),那么“天”便成了道德法则(“德义”)的代名词了。
如上所述,天是至善道德的本体,所以人们修养功夫的最终目标就是为了“知天”。循此理路下去,孟子提出:“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尽心上》)赵岐在解释这话时说:“性有仁义礼智之端,心以制之。惟心为正,人能极尽其心,以思行善,则可谓知其性矣。知其性,则知天道之贵善者也。”[4]人们“尽心”、“知性”的目的是为了“知天”“事天”, 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天是至善道德的本体、“天道贵善”。
作为义理之天这层含义的“天”,除了具有道德法则的意义,还有客观规律的意思。关于这一点孟子说:“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天下无道,小役大,弱役强。斯二者天也。顺天者存,逆天者亡。”(《离娄上》)此即说,政治清明的时候,人们的社会地位是由道德决定的;而政治黑暗时人们的社会地位则是由力量所决定的。这两者都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具有客观必然性,所以我们要遵循这个规律,所谓“顺天者存,逆天者亡”。
六、“天”在孟子哲学中的地位
在探讨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必须弄清楚这样一个问题,即《孟子》中“天”有自然之天、主宰之天、民意之天、命运之天和义理之天五层涵义,那么在这五者中何者为主?何者为辅?换句话说,在这五层涵义中,“天”最主要的内涵是什么?这是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如前所述,自然之天指的是自然界,它只在《孟子》中出现过10次,并且大多出现在一些类比推理中(如“天无二日,民无二主”、“宜若登天然”),实际上它也可以用自然界别的东西(如“地”)来代替,因而“天”的这层含义显然不是其主要涵义。主宰之天具有宗教神灵的意味,但孟子只不过是用它来强化人的主体性,这样天意便成了人意,它很多时候可以包含在民意之天中,并且主宰之天只出现过12次。因此主宰之天这层含义也就不是很重要了。而命运之天是人力所无可奈何的东西,但并不具有什么神秘性,它只是“环境一切因素之积聚的总和力量所使然”[5],具有客观必然性,这层意思可以归到义理之天的名义之下;并且命运之天这层涵义在《孟子》中只出现了6次,因而也不是很重要。而义理之天和民意之天在《孟子》出现的次数最多(分别为29次和25次),孟子对这两者论述的最详细,这构成了孟子“天”的最主要的涵义。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义理之天和民意之天这两者在孟子哲学中的地位如何呢?
我们一般都认为孟子哲学的核心思想是性善论及其政治思想,此即所谓的内圣外王之道。孟子认为人性本善,他以心善说性善,认为“仁义内在,性由心显”。心所以为善是因为心内在地具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等四端;心所以具有这四端,是因为“心之官则思”。而“心之官”是“天之所与我者”,这样“天”(义理之天)便成了性善的最终依据,成为道德法则的本体。所谓“天生蒸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这里的“天”也是道德法则的最终来源。所以我们可以说义理之天成了孟子性善论的形上依据,而性善论是孟子哲学的核心命题,因而义理之天在孟子哲学中的地位就不言而喻了。劳思光先生说:“宇宙论问题及形上学问题,皆非孟子留意所在。”[6]因而劳先生认为“天”在孟子哲学中不是很重要。诚然,宇宙论问题不是孟子留意所在,但形上学问题——性善论的最终依据则不能说不是孟子所关心的了,因为它构成孟子整个哲学的理论基础。而劳先生用先秦南北方理论形态的不同(他认为北方文化重视道德政治问题,而南方文化重视形上学问题)来论证其观点,[6]则显得苍白无力。
孟子重要的理论观点还有以民本论为代表的政治哲学,孟子继承了周朝以来的“民为邦本”的观点,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和“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的民本观。在论述一些政治问题时(如尧是否将天下禅让给舜的问题等),孟子用“天”来代替“民”来进行论证,认为“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最终决定因素是民意之天。孟子之所以要那样做,是要突出民意的重要性(因为在中国古代天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劳思光先生说孟子“以民心释天意,故并非提高天对政治生活之重要性,实是削减天观念之分量”,[6]这话值得商榷。其实,孟子以“民心释天意”并未“削减天观念之分量”,而是借用天之地位来说明民心的重要性,以此来论证其民本观。
总之,义理之天是孟子性善论理论基础,民意之天则被孟子论证其民本思想,而义理之天和民意之天是《孟子》中“天”的主要内涵,因而“天”观念在孟子哲学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构成孟子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