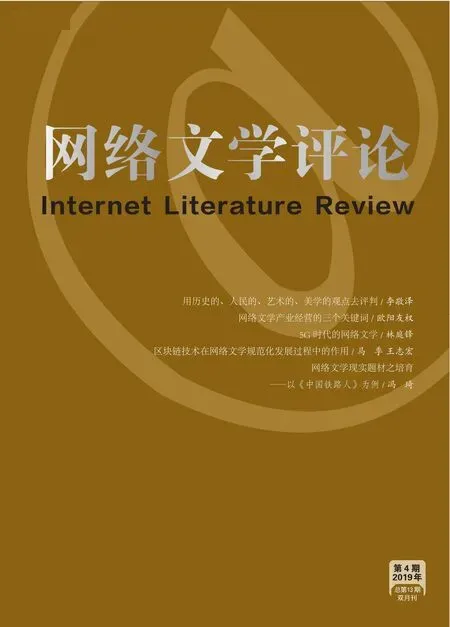《彼岸花》:城市的逃离与故乡的寻找
2019-12-27吴明健
吴明健
安妮把自己的小说定位成“都市小说”,以弥补“中国文学一直有缺陷空白的断层①”安妮对都市小说的描写并不止于城市结构的浮光掠影的描述,她注重对“城市边缘人”的生活状态的反映。安妮也对“城市边缘人”进行了解释:“不归属于任何一个团体,没有固定的工作,居住地和城市,靠某种专业能力谋生,长期处于孤独和不安定之中。他们有着强大而封闭的精神世界。性格分裂并且矛盾。他们始终在思考,但和现实对抗的力量并不强大。所以有时候他们显得冷酷而又脆弱。①”“城市”里的人与物、情与爱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往往都是重点阐述对象。
安妮在“写城市”中也逐渐地深入对“城市”进行剖解,她自身通过行走在偏远地方(如西藏墨脱、越南乡镇)来积累写作素材,以此比较城市与乡村、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并自省人在城市文化下的态度,不能为喧嚣制造娱乐,也不为娱乐而娱乐。“在城市中生活得越久,你就会发现它的很多畸形之处。比如现在越来越喧嚣的娱乐化倾向……他们如此热衷于制造娱乐取悦读者,用娱乐解构和贬低一切,他们是否依旧意识和具备着最基本的职业精神和道德标准,是否对社会和人群起着一个正确的引导作用。他们想给予读者的到底是什么?②”另外,这也暴露出城市对人的个性的吞噬,人要对城市存有警惕之心。“丧失独特的创造个性,只有复制能力和急功近利的欲望。这恐怕是现在城市文化里最大的诟病。②”而面对城市的消极影响,安妮试图寻找一个理想地来补偿对城市的失意,故乡也就成为安妮创作中想要追寻的彼岸之地。
一、故乡的此岸——城市
安妮喜欢把城市比喻成一个容器,但对“城市是容器”的比喻进行溯源,第一次使用这样的比喻是在《八月未央》的《夏天幻灭事件》中,而非《彼岸花》。“听到窗外磅礴的雨声,整座城市变成空洞的容器。③”只是与《彼岸花》有所不同的是,《夏天幻灭事件》中的城市是“冷漠”的城市,但依旧探寻的是城市里的“爱情”以及情感保持的有效性话题。从喻词看,《八月未央》的是“变成”,《彼岸花》的是“是”,从“变成”到“是”,前者的判断语气显然比不上后者的肯定,“变成”是一种外在形式的修饰,说明城市和容器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性,只是把陌生的人的爱情容纳、汇聚,是有交集的集合而已。而容器本身是“空洞”的,意指情感的“幻灭”。到了《彼岸花》,城市就是容器,并且拥有多重层次。外在是“巨大的”,内里是“静寂的”和“黑暗的”,是对人以及情感的吞噬和覆灭。
城市在《彼岸花》中被想象为诸多的意象。例如连续三次将城市比喻成一个“容器”。首先是“荒芜”的城市,“而这个城市是一个巨大的容器,任何人任何气味掉在里面就不见了”④,这里体现的是容器的吞噬性。掉进去的是“人”,消失的也是人,吞噬的程度扩大到人的气味则表示人的任何存在感都会被消灭,容器不是适合人们生存的环境。另外,“气味”指的是爱情(情感的一种),而非具体的人与物的气味,城市的人与爱情会被物质化和世俗化,卓扬试图用婚姻和家庭去吸引乔,而在乔的观念里,这是一种束缚和禁锢,这是陌生的气味。容器是巨大的,里面是深不见底的黑暗,吞噬一切人与人之间有所联系的纽带,而这吞噬的动力则是人的占有欲。安妮并没有具体解释爱情是什么,而是从反面提及爱情不是什么。“不是婚姻,不是诺言,不是家庭。④”在小说中,乔和Ben的“婚姻”便是无稽之谈,他们迅速领证,也迅速分离。当乔清醒过来想要脱离这种关系时,Ben却拒绝了。但是在法律上并没有解散夫妻的关系,只是因为靠着那结婚证而形式存在。所以认为婚姻并不意味着爱情,婚姻只是一种配合和合作。当人与人之间充满了利益的占有欲,从而失去了最本质和纯粹的“爱”时,这座人的城市则是“荒芜”的。其次是“孤独”的城市。文中提及乔做了一个“新的梦”,“新”相对“旧”而言,在此之前,我们可以猜测乔做的梦是反复的旧的梦,新的梦无疑是给了她新的启发。梦的发生是在乔决定为电影写小说的时刻,它是对城市叙述的开始。她梦到在一辆公车里,车厢是“空荡荡”的,乘客是“起起落落”的,乔在梦里遇见了电影里的女子,便是林南生。值得注意的是梦的环境,公车是“旧”的,空气是“臭”的,雨声是“喧嚣而空洞”的,水滴是“支离破碎和荒凉”的。梦的环境充满着腐烂和颓靡,人与人之间是互不相干的关系,你来我往,没有交集。关系都是人创造出来的,当乔试图想对车上的女子询问“到哪里去”时,女子并无回应。为了弥补这种孤独的存在,在电影里面,乔和南生却是相知的。“容器”在这里除了强调它的“巨大”,更突出的是它的“寂静”,呈现的是人的孤独感。从雨声滑落、掉进容器的声音——“喧嚣而空洞的雨声”,进而表现出人与人之间情感反馈的缺失和徒劳,声音营造的则是孤独。最后是“别离”的城市。在再次提出这个容器是“巨大的寂静的”的后文中,南生同样是梦见自己在一辆公车上遇到了一个女孩。在小说中,这里的内容较为隐晦——分不清是真实的现实还是虚假的梦境。南生不能“靠近”也不能“离开”车上的女孩,而是在一次突然的清醒后发现那个女孩是“她的少年”,然后便下了车。“在车上”与“下车”的过程便是一次“别离”的过程——南生离别她的少年所对她的影响。而在此之前,试图寻求安稳的南生选择了和罗辰在一起,但两年后便离开了他,因为她和罗辰之间并无幸福可言。她离开罗辰时便做了这个梦,不过梦见的是自己,是自己的过往。
在安妮看来,对城市的情感态度是怎样的呢?似乎又是矛盾的。“安妮对都市的态度则更加暧昧,她对都市是既爱又恨;既想享受它,又想逃离它……⑤”但纵观安妮的写作历程,这暧昧也渐渐揭开了帷幕。安妮对城市的态度更偏向批判的一方。《彼岸花》描述过的城市有很多,比如上海、N城、杭州、广州、南京……这些城市对人的可塑性极强,书中南生对在广州的和平的描述是“如果不能改变这个城市,那么势必已经被这个城市改变。④”这是处于人与城的关系和一个时代环境的缘故。城市是物质享受和获得贫乏的双重矛盾,进而讨论人在城市的价值判断。身体的饥饿促使对物质的渴求,物质的诱惑又促使人的恐惧,人的价值在城市中必须以工作的形式而依存。但安妮对工作的意义提出了疑问,体现在乔的身上——对毫无创造性的机械重复的工作的否定。
这与安妮的经历有着莫大的关系。对待城市的态度也在一次又一次的旅行中发生了质疑。在去过越南或西藏的旅行后,安妮回到自己所在的城市生活,感到不适应,并且认为奢侈的物质消费是一种象征,但这种象征与她无关。早期的安妮的作品对待城市的物质是占有的,试图弥补某种空白,以得到安慰。再到后来的自我审视中说明“情感不足的人会格外注重物质”。但从《城市画报》上的专访来看,安妮对物质的需求并不过分占有,而是出自本能的对美的欣赏。这种美是在“畸形”的城市影响下的对个性的磨灭,而充满个性的物质总会吸引到安妮。即便是送礼物,现在的安妮的观点亦是“物有所值”“环保的”。安妮对物质的需求是“必要的生活品,没有其他消费。”面对安妮笔下的作品(尤其早期作品),有部分学者便给安妮贴上“小资作家”的标签,确然是没有考虑和理解到安妮的写作内核和作为写作家的成长阶段。安妮也回称道“小资”在他们的概念里其实也是不清晰的,写的“酒吧”和特定名牌的用品也不过是安妮作为表达的一个不必要过分关注的意象而已,作品的思想才是最值得深究和思考的。当明白物质是一种意象后,我们发现“重复”的人名、地名、穿着打扮等外在形式分别散落于诸多作品。如《八月未央》的“乔”和《彼岸花》的“乔”,人物通常的衣着打扮是洗旧的棉麻布上衣、牛仔裤和球鞋……只有撇开外在的意象伪装,才能明白《彼岸花》追寻的是一种空间的现实和幻想之间的流离、时间的童年和成年伤痛的面对方式,和城市之下的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关系……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待,物质也是安妮对事物的细腻的观察和个人独特的审美。这种审美是对城市“趋同”的抵制,也是反映追求生命的真实性和差异性而做出的努力。
安妮从银行离职后便流离在不同的城市,而北京和上海便是她最为集中的居住地。在《城市画报》的专访中也明显表达她对城市的态度:“城市依旧是我的基地,对城市生活的麻木与残酷,依旧是有痛感的,所以愿意与它对峙。”“大城市会让你感觉到它与你之间的距离,不会有被包裹的压迫,不会让人有窒息之感。②”在此基础上,则是安妮对城与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探究。人对于城市过于寂寞和脆弱。人可以随时轻易地从城市消失,但城市不可以。《彼岸花》中的小至便是无声无息地在城市里消失。具体的人可以迅速消失,实际上,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也可以迅速产生和分离。卓扬和羊蓝的爱情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像由混凝土构建成的城市那般坚固,当一方不再满足另一方的需求时,两者的关系便逐渐崩塌。
那么,为何安妮喜欢将城市比喻成“容器”呢?安妮并没有给出答案。但从安妮对“容器”的功能和喻体来分析,我们可以得知安妮对这个“容器”的评价是贬义的。因为安妮并没有具体地指出这个容器是什么,而是用了这样一个具有普遍概括意义的“容器”概念,便可以推测容器具体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容纳”的功能。从对“容器”的修饰语来看,有指城市是“空洞的”(《八月未央》)“巨大的”“寂静的”(《彼岸花》),也有指人“空空荡荡”(《夏摩山谷》)。由此总结出容器的两大基本属性:容纳性和无声性。这与安妮所描述的城市印象相一致:城市是一个汇集形形色色、四面八方的人群的地方,体现了容器的容纳性;而正因为容纳的体积大、成分杂、层次多,城市里的人与人的感情关系也就复杂多样。安妮为了突出人在城市漂泊的“孤独感”,便赋予生活在城市里的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一种无力回击或无法回应的孤冷感,容器的“无声”属性便能体现这一点:无论你在里面投入什么,它都无法给予回应。也正因为如此,为了逃脱这个容器的束缚,在容器里的一部分尚未完全沉沦的人便有了逃离的计划和行动,去寻找作为城市的对立面——故乡。
二、城市的彼岸——故乡
《彼岸花》的讲是“痛苦,追寻,孤独和解脱的人本问题”①。安妮对城市的批判实际上流露出了对故乡的“追寻”。在《彼岸花》中,故乡指的是离开曾经居住过的熟悉的(通常时间两年以上)地方去往另一个陌生的地方,只要发生“离开”,就会产生新的“旧地”,这个旧地,便是故乡。离开故乡的原因往往是“迫不得已”和“被动”的(例如《彼岸花》中的南生、《七月与安生》的安生、《莲花》的内河)。安妮也把笔触聚焦在“城市边缘人”的生活上,他们久而久之的居无定所、四处漂泊的常态背后则是对故乡的无限憧憬。
《彼岸花》中,故乡分为三种。
(一)异乡是故乡。异乡通常是流浪、暂居的城市。林南生一共在四个城市居住过,分别是N城、杭州、广州、南京。N城是她的过往,杭州是她的彷徨,广州有她的爱情,南京是她的妥协。辗转在各个城市之间,但并未久居和安定,可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城市生活。她的大多记忆也是城市。相对应的写作者乔,则是恐惧“走了很远,走了很久,可最终没有一个地方一个人,可以让我回去④”“回去”是一种“返程”,是相对于“出发”“起航”之类的字眼,从故乡出走是出发,从城市回到故乡是返程。但乔和林南生同样的共同点是“流浪”,她们没有定居的地点,异乡也便成为她们的故乡。
(二)乡村是故乡。林南生的故乡在小镇枫桥,她的美好的童年便在乡村里度过。但这样的故乡往往是回不去的,它有空间和时间的双重尴尬。正如林南生的出走,在各个城市辗转,但从未回到过小镇枫桥。再到本来计划在上海住两年但只住了几个月的乔,面对卓扬“以后还会回来吗”的询问,却回答“估计不会,这里不是我的故乡”,并坦言故乡是乡村,常居城市却又不适,但也感觉“故乡是回不去的地方④”。
(三)自然是故乡。在《彼岸花》中有一个细节,乔在延安路天桥用10元的纸币跟小乞丐换了一份报纸,报纸的内容是在城市机关工作的男子辞职去往贵州深山里支教。这与《莲花》中的内河去往墨脱支教如出一辙。无论是贵州还是墨脱,都是远离城市的偏远地方,是脱离于喧嚣的大自然。在这样的大自然生长和生活,对物质并不过多需求,而内心却是充盈的。在深山的孩子,是“天堂里的花朵”“生命只有在这短暂的瞬间远离了悲欢④”。在《八月未央》中,靳轻对“物质”“利益”的心理是“我知道它很合理,却一直痛恨”的无奈与矛盾,而“物质”“利益”无法满足欲望或无力获得时,偏远的山区很容易成为失意的人生的栖息地。在《莲花》中,墨脱亦是这样的存在。另外,《莲花》也对当下城市的消极因素进行了批判。比如穿着“精良装备”来拉萨旅游的人,他们的目的不是旅行,而是为了拍下“平庸的照片”以在城市中炫耀。甚至在深山来开会的领导,调研也不过是形式,只是留下照片以作为形式的证明。对城市的“虚伪”和“形式”感到失意,大自然也就成为可以重塑自我的精神故地。那里的一切都是朴素和真切的,这与城市中的功利、物欲、虚伪形成了对比,是现代精神匮乏之人尝试救赎的“殊途同归”之处。
在三种故乡的形式中,安妮的笔触落在大自然上显然是最多的。原因是儿时的安妮在乡村度过一段时间,乡村的自然风光给予了她许多与生长在城市的人的不同的看待事物的方式。“一个孩子拥有在乡村度过的童年,是幸会的际遇。无拘无束生活在天地之间,如同蓬勃生长的野草,生命力格外旺盛。⑥” 这句话强调了人在大自然的养育下的心灵健康的重要性。基于在乡村生活的童年,能更多地接触大自然的养育,而城市无法提供这种环境。大自然代表着顺其自然的秩序,人有遵循和违背的意愿及能力。一个失去大自然的人,如同失去庇护,失去土地给予的“不一样”的能力,从而“物化”趋同在大自然影响下的人的性格,安妮赋予了人物一种具有“自然”的气息,分别体现在女性身上的 “野兽”和“植物般”的两种属性。女性通常是桀骜不驯的,男性则是循规蹈矩、不敢触碰社会规则的人。女性往往在某种程度上是牵引着男性逃离被社会规则所规训的方向。“假若一种近于野兽纯厚的个性就是一种原始民族精力的储蓄,我们永远不大聪明,拙于打算,永远缺少一个都市中人的兴味同观念,我们也正不必以生长到这个朴野边僻地方为羞辱。⑦”沈从文提到的“野兽”个性与“纯厚”特征相联系,因此更多的是展现“不大聪明”“拙于打算”的性格特征,而安妮则是从大自然的变幻多端的角度(既包括稳定的一面,也包括不稳定的一面),从而使女性人物更具“野兽”的本性:服从本能(行为决定主要受自身喜好影响)。除此之外,也赋予了女性人物“植物”的特性——善良、忍耐,所提到的植物大多是远古时期的锯齿形蕨类植物——带有泥土的厚实芬芳。
女性的不可估摸代表着自然的变化莫测,男性的循规蹈矩代表了社会的规章制度。因此,具有“自然属性”的女性常常与“主流”的观念和行为不一致,也便很容易成为社会的“异类”。当卓扬试图用具有“人间烟火”的家庭温暖来安定乔时,乔在努力适应到最终不能适应的过程中表现出一种十分不自在的姿态,并最终抛弃这样世俗的爱情模式。这样的角色在安妮的作品中比比皆是,如《告别薇安》的林、《莲花》的苏内河、《春宴》的沈信得……她们都共同地表现出人的天性带有一种动植物顺应大自然并与之反抗的合理力量。
三、抵达不了的故乡
既然故乡分别可指异乡、乡村、自然,那说明寻找对象的结果具有可实现性。但故乡是否可以抵达呢?安妮对此的答案却是否定的。故乡是在彼岸不可到达的地方,不仅仅是空间,也是时间,两者紧密联系。自从在银行离职后,安妮也在不同的城市里漂泊。长期的漂泊需要不固定地变更地址,“搬家”也成为安妮的常态,而搬家需要对房子的物质大动干戈,因此安妮的物质需求确是必要和简单的。同时,这也致使习惯的养成——对城市生活的逐渐习惯。但安妮并未停止对故乡的寻归,体现在一次次旅行和写作上。但探究和寻找的结果,却是得出“人的故乡,是他不能再回去的地方”的结论⑦。
为何故乡回不去?
从城乡发展角度看,当故乡作为一个确定的地点的时候,它往往是乡村。若把范围划分得更大些,则是大自然。20世纪80年代以来,城市的发展势必以乡村和自然作为代价。到了90年代,网络的崛起和覆盖一方面使得人与故乡的联系变得更紧密,也让人与故乡变得生疏和冷漠。当故乡放在时间上衡量,时间的“过去时”决定了故乡的追寻无果,故乡成为童年的专属记忆。甚至对于一大部分从乡村迁徙到城市的人来说,他们的孩子从一出生就失去了故乡。在异乡生活的人,故乡从来就是遥不可及的事。时间使一切都物是人非,故乡的人与物都经不起时间的磨洗,故乡也就成为记忆的凭吊。
从书名“彼岸花”分析,彼岸花是一种先开花再长叶的植物,它的生长习性与其他一般的花有很大的差异性。其他的花是在长叶的基础上再开花,彼岸花则反其道而行之,这也是一种对“常规”的对抗。因而这差异便导致了悲剧的产生。花与叶永不相见的特性引申为男女之间的爱情无法终得善果。森对乔说:“你要的是彼岸的花朵。盛开在不可及的别处”④,从而否定了森和乔之间并无爱情的发生。因彼岸花的特殊习性则衍生出许多传说。其中有一个传说便称彼岸花是开在路上的花,一条是通向地狱的路,意为死亡。另一条通向天堂,意为新生。《彼岸花》的基调是“死亡的”暗沉,但结局最终依旧是获得了一定的新生。实际上,《彼岸花》的基调和结局都是次要的,它更多的是具有“指引”作用,是为在路上寻找归宿的人的指引,由此理解为“故乡的寻找”。彼岸花是“盛开在不可及的别处”,故乡则是“回不到的地方”,他们的共同点是确实有这样的事物存在,但人们永远接触不到。
安妮也试图从基督教的思想去解释“回不去”的原因,安妮在接受采访时回答说,《圣经》对她的写作影响很大。《彼岸花》的南生在离开小镇时,奶奶叮嘱她需把《圣经》带上,此后有关基督思想的内容则只出现在电影小说的尾声:南生梦中的唱诗班的歌声,仿佛只是偶然为之的情节需要。事实上并非如此,在南生辗转在各个城市之间的时候,也是南生执拗地不断填补心中缺失的情感的过程。为了填补内心巨大的虚无,一直为自己的“罪”滋生着更多的“恶”,以至于最后在酒店用刀扎进了和平的腹部。基督思想讲究“爱”与“救赎”,常常在人绝望的时候给予一丝希望。因此,和平没有死,乔走出看守所后尝试的割腕自杀也并没有成功。最后她也与和平在异乡相见,但并未在一起。其实这样的结局已算是一个好的结局。乔与森提及电影剧本的另一个结局:南生自杀未遂终身残疾,而和平重伤痊愈下落不明。相比之下,另一个结局的悲剧性显然更强。《启示录》第二十一章有一句话体现了对希望的引领:“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乔的离开,那无法抵达的“故乡”就如同“新天新地”,以往经历的一切都过去了。
小结
《彼岸花》中的各人物的流离实际上是对故乡的寻归。从此岸到彼岸,从流离到落根,都需要一座桥梁使之连接。安妮在《彼岸花》中找到了桥的出路——行走,只是不知行走的结果,甚至忽视行走的结果。故乡的无法寻归也就成为永远行走的理由。在《彼岸花》的结尾,“是时候出发了”这一句话饶有滋味。它是对这所城市“倾诉的完成”,是离开这所城市,将出发下一个未知归宿的开始。“路到头了,但这种终结并未使路消失,而是将路规定为这一条现成的路。”⑧对于乔而言,她的离开造就了她对这所城市的记忆,她的记忆如这所城市是确确实实地存在着,并不是没有意义可言。“出发”也是一种“离开”,“离开”则是因为“完成”,海德格尔认为“完成的事都将达到它可能的结束,完成是基于结束的一种结束的样式。”张汝伦解释为“结束不必是完成,完成一定是结束。⑧”安妮给予乔的离开实际上是对这一条从此岸到彼岸的路的总结,而处在彼岸的时候则能更加看清走向彼岸的路,因为可以在路的终点观望来路,这观望的过程带着一种思考的意味,或许也是一种妥协,它代表着下一段路的启程和漂泊的仪式感的完成。
通过寻找故乡,倾诉城市“边缘人”流离的伤痛,去展现人的心灵问题。在探寻故乡的过程中,安妮在《彼岸花》中也建立了一种矛盾关系:故乡的出走与抵达不到的故乡。因此,“彼岸”作为一个寻找的方向,就代表着一种徒劳。目前,安妮创作的长篇小说共有五部,除《彼岸花》之外,其中有两部长篇小说对叙述“城市”与“故乡”的关系和态度较为明显(分别为《莲花》《夏摩山谷》)。《彼岸花》可以说是为读者初步描绘了一种寻而不得的失落的迷惘,但作者的思考并没有止步挣扎与矛盾的心态,而是沿着“彼岸”的方向不断地寻找,因此在《莲花》中则通过行走墨脱的方式去进一步探寻结果。安妮在《莲花》中似乎寻找到了希望,即从宗教角度(主要是佛教)去探索一条新的道路来。而值得注意的是,2019年的新作《夏摩山谷》似乎给读者展现出了故乡的理想地——夏摩山谷。
从这三部长篇小说中,佛教禅宗的思想分量不断地加重,对城市的直接描绘却不断地减少。若是想从“故乡”角度去重新弥补都市文学的空白,这样的力度也终究是不够的。但不可否认的是,安妮的小说确实一直针对着“城市”与“故乡”的角度,去展开她对填补“都市文学”的空缺处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