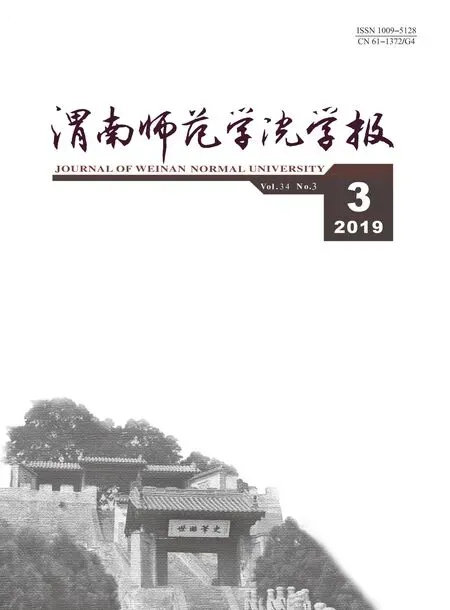关于我的文论、文评写作
2019-12-27段国超
段 国 超
(渭南师范学院,陕西 渭南 714099)
我的文论、文评写作,严格地说,是“文革”结束后开始的。当时有如严冬过后,春天来临,百花齐放,百业兴荣,文艺事业也是这样。首先是党和国家在“文革”中遭到严重破坏的各级大小文艺机构,纷纷恢复建制,工作人员陆续回到机关上班。在“文革”中被停办的各种文艺杂志纷纷复刊,像通常一样照样发行。还未等到完全恢复平静,人们始料不及的思想解放的潮流汹涌澎湃,各种文学流派纷呈,作家分化重组,新老作家勤奋提笔,大批优秀的作品出现了,一大批有争议的文学作品,诸如“朦胧诗”和“意识流小说”也有了,整个文坛出现转机,出现新面貌。当时党的教育事业也和党的文艺事业同样,生机勃勃,欣欣向荣,处于大发展的态势。1978年4月,渭南师专创立,我作为第一批教师调进,在中文系主教现当代文学和写作。由于教学和文学潮流发展的需要,我很自然地开始了文论和文评的写作。
一
“文革”结束以后,社会生活恢复正常,混乱的社会秩序随之结束。但是“文革”十年“四人帮”把人们的思想意识特别是文艺理论领域里的是非观念弄得相当混乱,要恢复正常,得有个过程。这个过程就是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把“四人帮”颠倒了的理论是非重新颠倒过来。在这个过程中,我做了些工作,除了参加省文联、省作协、省文化厅和省委宣传部召开的一系列有关会议外,还写作并发表了一些文章,如《“四人帮”为什么要全盘否定十七年?——斥“四人帮”的“文艺黑线专政论”》(《凤山文艺》1978年第1期),《岂有此理——再斥“四人帮”“文艺黑线专政论”》 (《凤山文艺》1978年第2期),这两篇是批判“四人帮”“文艺黑线专政论”的,《一个半抄袭的“神话”——批“四人帮”的“空白论”》是批“四人帮”大搞文化专制主义,否定从30年代至今我们的文艺创作成就的;另外,还写作并发表了《无耻的歪曲》(《陕西日报》1978年4月16日)、《江青为什么“最不喜欢民歌”?》(《群众艺术》1977年第3期)、《“写女主角”析》(《群众艺术》1977年第7期)、《为“带头文学”叫好》(《西安日报》1978年11月9日)等文章。这些文章都是就“四人帮”在“文革”中有关文艺的一些谬论展开辩论,澄清是非,以正视听的,为后来在文艺界展开正常的、正面的文论写作、文评写作清扫道路、端正风气起了一些好的作用。但现在看来,虽理直气壮、口气凌厉,但有不少篇章说理不透,水平相当有限。
二
不破不立,先破后立。我记得在做了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清扫理论道路的工作以后,就解放思想,大胆构建起新时期自己的理论体系来。文论写作是有关文艺理论问题的写作。在文论写作方面我也做了一些工作,写了一些文章。有些文章在社会上还小有影响:
一次由省委宣传部和省文联在西安召开的理论座谈会上,重点讨论“伤痕文学”。有人提出:社会主义时期有没有悲剧?有人说有,有人说没有,讨论非常热烈,几乎人人都发了言,我也发了言。我认为有。这个问题,在“文革”前曾经讨论过,大家一致认为是没有。因为悲剧是社会制度的产物,而社会主义制度无比优越,怎么能说有?就是有,也不能说有。但是,改革开放后的今天可以实说了。散会之后,《延河》编辑部理论组组长陈深叫住我,让我尽快把我的发言形成稿件寄给他。这就是《延河》1979年第1期讨论悲剧的两篇文章之一《关于社会主义时期的悲剧》(另一篇是胡义成的《试论悲剧》)一文。我的文章肯定社会主义时期有悲剧。因为经过“文革”10年,事实证明:社会主义制度并不完善,还需要不断改革,不断创新。1989年,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陕西文学十年》一书的第194页有这样一段描述:
1979年胡义成的《试论悲剧》和段国超的《关于社会主义时期的悲剧》即对社会主义的悲剧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接着高起学的《悲剧形象应该多样化》论述了悲剧艺术形象的塑造规律。之后,刘建军、费秉勋、焦文彬、黎风等各自又从上古神话、元杂剧、《红楼梦》及现当代作家作品中的悲剧因素入手,广泛地总结了中国悲剧范畴的历史传统和民族风格。
你看,《关于社会主义时期的悲剧》这篇文章在陕西悲剧的这场大讨论中是起了开场作用的。在这篇文章中,提出“社会主义时期也有悲剧”的观点,只是它“产生的根源和性质与旧时代的悲剧有所不同”。观点比较新,即使放在今天看,也不过时。这是我在“文革”后写作并发表的第一篇论文。
1961年7月8月合期《剧本》发表老剧作家孟超的昆曲剧本《李慧娘》。剧本的故事情节是:南宋德祐元年秋,奸相贾似道昏聩淫侈,窃权误国。一天贾似道寿庆,携姬妾李慧娘等泛舟西湖,不料遇到太学生裴舜卿,被裴当面斥骂,这场景被李慧娘看到,李慧娘发出“美哉!少年!”的赞叹。贾大怒。贾回府杀死李慧娘,囚禁裴舜卿;后李慧娘的鬼魂与裴舜卿幽会,救出裴舜卿,斥责贾似道,烧死贾似道。作品惩恶扬善,揭露了贾似道误国害民的罪恶,歌颂了李慧娘的爱情和反抗斗争精神。这本来是一出好戏,不料受到康生、江青等人的批判。此时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化名繁星在《北京日报》发表了一篇短文《有鬼无害论》,为其鸣不平,结果引火烧身,一同遭到批判。这本是“文革”前和“文革”中的一桩冤案(剧作者孟超含冤而死),当时我就想就此写一篇文章为其申辩,但当时水平不够,没有及时写出。1982年,我终于将这篇文章写成,这就是《试论鬼魂戏》。文章谈了鬼魂戏是怎么回事,从鬼魂戏的内容、形式、特点、历史,一直说到鬼魂戏来自社会生活,其实质是“人戏”。还说到鬼魂戏并非封建迷信,只要它宣扬的不是腐朽没落的东西,是完全可以搬上舞台的。此文共计两万余字。初稿发表在《西安戏剧》1982年第2-3期合期,修改稿发表在《阜阳师范学院学报》1984年第3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戏曲研究》1984年第12期全文转载。东北师范大学老学者、老诗人蒋锡金教授看后给我来信说:“你这篇谈鬼魂戏的论文,长而精,是我看到的谈鬼魂戏最有水平的一篇文章。功夫不负有心人,您写这篇文章,是下了功夫的。”这篇文章是我早期写得比较好的一篇文章。
1980年《西安戏剧》载有张骅同志《戏剧与历史》一文,文虽长但没有新意,其意无非是“历史剧是‘剧’,不是‘历史’”,“可以采用不见正史的传说、异说,乃至凭想象来虚构一些人和事”,这说法和过去“历史剧可以取材于历史,但不是历史”等一些老观点没有什么不同。我一直不同意这样的观点。在读了张骅同志的文章以后,就写了一篇表述我自己观点的文章,这就是《也谈历史剧》一文,发在《西安戏剧》1981年第2/3期合期。我意以为:“历史剧是‘历史’和‘剧’的统一体,是二者有机结合的产物。”我在文中把它和“报告文学”作比。众所周知,“报告文学”是一种新闻体裁,“报告”是新闻内容,必须绝对真实,不能虚构,“文学”是表现形式,是艺术手法。“报告文学”有好内容+形式,“历史剧”也是有好内容+形式,二者的结构同样。既然“报告文学”的“报告”不能虚构,为什么“历史剧”的“历史”就可以虚构呢?这逻辑上的错误是显而易见的。我的文章发表后,引起刊物不同意见的争鸣。争鸣文章十多篇,时间长达两年半。最后以戏剧理论家苏育生的文章作结(苏文总的观点是支持我的)。1987年,我将《也谈历史剧》改题为《关于历史剧的几个问题》发表在《宁夏师范学院学报》第4期上,由于观点比较新,论证手法有独到之处,很快被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戏剧研究》的当年第3期全文转载。
在文论的写作方面,《浅论柳青提出的三个问题》(《人文杂志》1983年第2期)、《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的几个问题》(《延安文艺研究》1990年第2期)、《引导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前进的指针——纪念毛泽东同志〈讲话〉发表45周年》(《延安文艺研究》1987年第2期)、《浅谈文艺批评——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90周年》(《语文学报》1982年第2期)等文章,短者6000余字,长者万余字,在刊物发表后,均为《光照文坛五十秋》《追寻与坚持》《继往开来》等专书所编用,社会反响比较好,也是我费心竭力之作。遗憾的是,在文论方面这样比较大、我本人比较满意、社会反应也比较好的文章,我写得太少了,大约只有十几篇吧。
三
文评写作,是以文艺作品为评论对象的写作。因为我是主教现当代文学的,不是搞文艺理论的,所以我关于现当代文学的评论文章的数量要比关于文论的理论文章的数量大得多,稍有些影响的文章相应也要多一些。虽是主教现当代文学,但是涉及古代文学作家作品的评论,以及涉及艺术作家作品的评论也有一些。这里我都想择要做些简略介绍。
(一)关于古代作家作品的评论
《齐鲁学刊》1979年第4期发表刘乃昌先生《横槊气概·英雄本色》一文,关于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一词的主题,刘文认为:寄托作者振兴北宋积弱局面的殷切期望,透露了作者有志报国、壮怀难酬的感慨,我读刘此文后觉得不是。我即写了《似是一种失败的心理——就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的主题与刘乃昌同志商榷》一文,迅即投寄《齐鲁学刊》,提出与刘商讨。我认为,联系当时王安石变法的大时代背景和苏轼当时遭到贬谪的心境,《念奴娇·赤壁怀古》的主题应是托古讽今,抒发作者顽固守旧派反革新潮流的强烈的思想感情。《齐鲁学刊》迅速将此文刊出,即该刊1980年第1期。不料此文刊出后,很快引起了一场学术争鸣。《齐鲁学刊》1980年第2期发表颜中其先生《关于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的主题——与段国超同志商榷》一文,他不同意我的意见,认为苏轼这首词的主题应是:一支战斗胜利者的凯歌,是人民渴望战胜辽、夏侵略者,英勇保卫赵宋王室,必胜自豪心理的曲折反映。王元明先生在《东坡词论丛》发表《试论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的主题》一文,认为苏轼这首词的主题应该是:通过对壮丽山河、英雄人物的歌颂以及作者抗敌御侮、誓灭“强虏”的壮志豪情的抒发,表现了作者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周本淳先生在《淮阴师院学报》1980年第3期发表《“似是一种失败的心理”吗——与段同志论旧史,为苏学士洗新冤》,认为苏轼这首词的主题应该是:发思古之幽情,寄托人世无常,不如及时行乐之慨,等等。他们都不同意我的看法,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连有的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之类的刊物也参加了讨论。1988年,闫笑非先生在《求是学刊》第6期发表《〈念奴娇·赤壁怀古〉主题新探》一文,对这次学术讨论作了总结,认为这次学术讨论将苏轼的名作《念奴娇·赤壁怀古》的主题挖掘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是很有意义的。而我的看法,作为苏轼该作五种主题之一,亦被其肯定。我的《似是一种失败的心理——就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的主题与刘乃昌同志商榷》一文,在《齐鲁学刊》刊出后,迅即被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80年第6期全文复载。2001年12月,三秦出版社编印出版《百年陕西文艺经典》一书,我的这篇文章,被收进该书上部第二册。
关于古典文学作品的评论,我还有《不屈的斗争精神——柳宗元〈江雪〉的诗意辩证》《〈史记〉——一部以人为中心的伟大史著》《使〈史记〉得以公开面世的杨恽》《岳飞的诗词》《毛主席对白居易诗词的评点》等篇,在此不一一细说。
(二)关于现代作家作品的评论
因为我一直在讲授现代文学,这方面的文章自然比较多一些。关于现代作家作品的评论,我主要围绕如下几个方面进行的。
一是围绕教材,如《杂文创作的高峰》(《商洛学院学报》1992年第2期),这篇万余字的论文,评论的是20世纪30年代的杂文创作,本身就是《新编中国现代文学简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中的一章。《乡关之思,战士之情——读吴伯萧散文〈马〉》《现代戏剧的先声——胡适〈终身大事〉评析》《中国现代报告文学的丰硕成果——夏衍〈包身工〉评析》《从昏睡到奋起、抗争、胜利——读姚雪垠〈差半车麦秸〉》等,虽散落在各地学报上,但都是给高校教材《中国现代文学名著选讲》(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提供的讲稿。
二是围绕延安文学研究,如《吴奚如在延安》(《延安文艺研究》1988年第1期)、《战斗的激情,大众的诗风——柯仲平延安诗歌品赏举隅》(《延安文艺研究》1989年第2期)两篇长文刊出后,即引起社会关注。老作家周而复读过《吴奚如在延安》后给作者来信称赞此文,并将信发表在《延安文艺研究》1988年第2期。《战斗的激情,大众的诗风——柯仲平延安诗歌品赏举隅》一发表即被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10月所编之专书《让历史告诉未来》收编,柯仲平夫人王琳从昆明来信表示感谢。当时延安文学研究进入热潮,我购买湖南文艺出版社1988年10月出版的全套“延安文艺丛书”及其他有关延安文艺研究之类的图书共30多册,阅读之后,拟参与其研究。计划首先编出《延安文艺名人录》和《鲁艺史话》两著书稿。我利用一个暑假,在两个儿子的帮助下,按姓氏笔画编写出了2 600多人的名单一册,即《延安文艺名人录》。寄往西安一熟人征求意见,不料石沉大海。后见此名单列入他《现代作家与延安》(三秦出版社1995年10月出版)一书中,只是将我的书名《延安文艺名人录》改为《延安文艺工作者名录》,并在名录之后注明“多为段国超同志所供”即了事。关于《鲁艺史话》,终由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5月出版。此书由我拟定书目,并提供全部资料。我将资料分配给我和我身边的三个青年人。全书由我们四人共同写完(其中我写10篇)。最后我将全部书稿寄往西安我熟悉的两位同志,由他两位跑出版社,联系出版。自然,他俩虽与书稿无涉,也是第一、二主编,我虽负责全部书稿,也只能位居第三。
三是围绕鲁迅研究。这我单列在“鲁迅研究系列”中,有《我的鲁迅研究》一文。这里就不多谈了。
在现代作家作品的评论中,除鲁迅研究外,我虽撰文不少,但多为随笔、杂感之类的短文,大约近百篇。突出的,为世人所称道的大文章不是很多。特别是没有把“延安文艺研究”一项坚持下来,我内心感到十分愧疚。
(三)关于当代作家作品的评论
这大约是我写作的重点,原因一是我一直讲授中国当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的产生和发展,一直在我的视野中;二是我是陕西作协和中国作协的老会员,属搞评论的一类,有这方面的写作任务。我在写作方面,自感是勤奋的,总想写也总在写。写作数量包括随笔、杂感,大约也是一百多篇到二百多篇。这里的情况与现代作家作品的评论相似,分有计划和无计划两种。
先说无计划的文评写作。所谓“无计划”,即碰到什么就写什么,一时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原本就没有计划。这样的写作,针对性强,时效性也强,往往能写出较好的作品,能产生影响的作品,因为它能引起人的注意。例如1979年,改革开放伊始,有一北京来的京剧团在西安演出《送肥记》,还在继续宣传“农村有自留地,有集体地,一筐粪,是先送自留地,还是先送集体地,都是有斗争的。这是两个阶级的心理,是两个阶级的思想,是两条道路的表现,是阶级斗争的表现”,这显然是不合适的。我即写作并发表《从〈送肥记〉的演出说起》,加以批评。又如1981年,《长安》杂志第1期发表了老诗人孙静轩的长诗《一个幽灵在中国大地上游荡》,诗中“幽灵”喻指我们逝去不久的开国领袖和他的思想。我读后总觉不是滋味,就想写一篇批评文章。当时有同志劝我说,“这文章您不能写,你想想,现在正大讲‘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这风头上的文章,你能写吗?”但我“想想”的结果,还是写了。文章寄出以后,编辑部来人,给我做思想工作,让我“私下撤回”这篇稿,我坚持未撤。此稿在这年第6期登出后,《陕西日报》《文汇报》等新闻媒体发动态消息。上级有关部门对“孙诗”问题高度重视,曾组织多次研讨会,以提高大家的认识。事实证明,我写这篇文章的态度是对的,文章的观点也是对的,完全符合我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关于我写这篇批评文章的事,贾平凹后来还提起过。他说,段国超先生“是搞文学评论的,文章写得很好,他批评孙静轩一首长诗的那篇文章,就在文学界引起了一场辩论。他的这篇文章登在《长安》上,我当时就在《长安》当编辑。我还记得,20世纪八九十年代,省作协、文联、文化厅和省委宣传部搞的活动,就是开会吧,座谈吧,讨论吧,他都参加了。他在当时的陕西文艺界很活跃,是很有名的。”(《段国超先生》)这种本是无计划的,只是碰到什么就写什么,有感而发的评论文章,以后还写得不少。如1980年,有人在全国范围内禁唱红色民歌《东方红》,说这是歌颂“救世主”,否定毛主席的伟大历史功绩和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威信,我即写作并发表《要正确对待〈东方红〉》;1981年,《长安》杂志发表短篇小说《出于幽谷》,以肯定和赞赏的语气和眼光宣扬“乡下人”进城与“有钱人”比吃喝,比穿着,比阔气的浮靡之风,我即写作并发表《作品要有正确的思想道德评价——评短篇小说〈出于幽谷〉》加以指正;1982年,有人宣扬“性解放”,借写青年男女爱情而大写色情,我即写作并发表《莫把色情作爱情》加以抨击,等等。对当时文坛一些错误的思潮,我也同样没有客气,如1979年下半年,某文艺杂志青年编辑李剑同志发表《“歌德”与“缺德”》的千余字短文,对有些文艺作品不敢大胆暴露社会矛盾,只知一味歌颂有所非议,结果招来一场全国性的大声讨,这显然是“文革”遗风作怪,我即写作并发表《一点看法》提出异议,等等。这些文章在当时社会上起到了辨明是非的作用,在社会上是有一定影响的。
再说有计划的文评写作。所谓“有计划”,即按原定计划写作,计划写什么就写什么,有时间写就写,无时间就暂时放下,时效性不强。如杜鹏程研究,我是有计划的。已采访、收集了不少资料,并已编出章节,准备有时间就写,写完一篇是一篇,到时总会写完,写完了一本完整的《杜鹏程评传》就出来了。但这事颇费周折,总是因为很忙,总是在“写最紧急的”“把不急的暂时往后放一放”,就长久地“放”下来了。因为总是“没时间”,这“有时间”最后都落空了。但经过这么多年,现在已大部分写出来了。就这已写出来的一部分来说,效果还可以。如《试论〈保卫延安〉对李振德老人一家的描写及其意义》(《信阳师范学院学报》1985年第4期),这万余多字的文章,杜鹏程同志看过后来信(《伊犁教院学报》1985年第4期《杜鹏程与教师》)说:
学报上登的《试论〈保卫延安〉对李振德老人一家的描写及其意义》,我仔细读过。评《保》的文章不少,但从这个角度,这样有见解、有感情的文章,我连一篇也想不起来。特别是关于描写李一家人的不足之处,你讲了几点意见,真是太宝贵了——特别是第三点。你只要想想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是如何描写军民生活的,就能看出我这样人水平之低。年轻时希望当作家,现在六十有五,有人喊作家,我便汗流浃背。
杜老看过后,能从心底发出上面这样一通感慨,可见他对我此文基本上还是满意的,再联系此文在社会上产生的影响,我心里也颇感欣慰,也自觉满意。又如1991年10月27日,杜鹏程不幸逝世,享年70周岁,我赶写成《他在这里步入文坛——浅谈杜鹏程在延安时期的文艺创作》一文,发在《延安文艺研究》1992年第1期,其意表示悼念。也许此文感情色彩比较重吧,长达万余字,内容也比较充实些,竟被国家文化部主办的《新文化史料》改题为《在延安步入文坛的杜鹏程》,加上“编者按语”,发在该刊1992年第3期上,亦用来表示对杜鹏程病逝的悼念。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同年第8期全文转载。此文是我在当代文学评论方面写得比较好的一篇。
在当代作家作品评论中,还有些我自感满意、社会影响比较好的文章,如《读〈大地杂咏〉》(《延河》1990年第5期)、《人·生活·美——读西戎〈喜事〉》(《语文园地》1983年第2期)、《〈花环〉人物论》(《和田学院学报》1986年第2期)、《历史真实和艺术虚构的统一——读杨立哮长篇小说〈腥秋〉》(《小说评论》1992年第1期)、《杜鹏程与〈讲话〉》(《新文学研究》1992年第3期)、《〈张俊彪论〉散论》(《特区文学》1993年第6期)等,大概也有二十多篇吧,它们不是发在核心期刊上,就是被专书收录,或者被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转载。其数量要比古代作家作品评论和现代作家作品评论多得多。
在艺术评论方面,如书法评论、影视评论、美术评论等,我也写作并发表了20多篇文章,如谈史高尧的毛体书法、张施民的花鸟画、田永昭的楷书,我都发表过文章,但影响和数量都有限,在这里就不做介绍了。
2003年,我曾将各类文论、文评文章,择要编选出版了一册《文艺论稿》,计35万多字,著名文化学者、当时陕西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肖云儒为之作序。印数一千,后来又重印了一次。
四
1981年暑假,我参加了在北京举办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第一期讲习班”的集训学习。这是中宣部、教育部在“文革”结束后委托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为培训全国高等院校的当代文学教师而举办的。全班共120多人,班主任是文学所所长、著名文艺评论家张炯,由曹禺、姚雪垠、陈荒煤、张庚、徐怀中、孟伟哉、张骏祥、朱寨、蒋守谦、吴元迈、谢冕等一批著名作家和学者授课。时间虽只有一月,但我感觉收获甚大,决心回校以后把当代文学课教好,并在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上做出一番成绩。但想不到的是,这一年暑假学校扩大招生,师资力量不够,我一回校即有一大堆课程等着我:一开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写作三门课程同时由我上,中间还有几周分段轮教中学语文教学法,一周几十节课,我还哪有时间搞文学评论、写文学评论文章呢?我记得当时中国作协鲁迅文学院举办青年作家培训,通知我参加第一届高研班的学习(现在已是第34届了),当我向学校主管领导请假时,这位领导的第一句话是:“我们这是学校,不是作协,你还是教师么?你走了你的课谁上?”又适逢这年开始评职,这位领导规定:文学评论不算学术成果,不能用来评职。这位领导作如此规定,也许是害怕我走了吧,因为我们是新建院校,全校教职工不足二百人,搞文学评论者唯我一个。有人确实劝我调走,但我就想当教师,而当教师又怎能不考虑评职呢?最终只有安下心来。当时号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时期,随着时间的推移,文艺创作越来越繁荣,好作品也越来越多。我记得当时在陕西,新的作品研讨会特别多,今日在商洛开,明日在汉中开,后日在延安开,省作协不断发开会通知,寄送新作品,搞文学评论的同志像赶场一样,跑来跑去。像我这搞业余评论,天天上课,哪有时间读书?阅读跟不上,怎么搞评论?最后只有安心哪儿也不去了。怎么办?文章不能不写,唯少而已!后来我只有转移阵地,搞“鲁迅研究”了。我崇敬鲁迅,乐意研究鲁迅,使我逐渐养成至今也改不了的不到晚上三点,就不睡觉的习惯。1984年我凭着《鲁迅与胡风》《鲁迅与朱安》和早几年就发表的《关于社会主义时期的悲剧》《似是一种失败的心理》《诗人,你的这些思想至少是糊涂的》《试论鬼魂戏》《从柳青提出的三个问题说起》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的几个问题》等20余篇文章,评上了副教授。后来很长时间坚持研究鲁迅,于1991年出版了我的第一本学术著作《鲁迅家世》,这是一本填补空白的鲁迅研究著作。1991年我被评上了我校第一批教授(共3人)。
关于我以上从热爱文论、文评到逐渐疏于文论、文评的这段经历,著名作家陈忠实后来曾在《一个甘于寂寞,潜心研究学问的人》一文中有过这样一段话:
我跟段国超老师初识,大约是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就是中国的号称文艺复兴时期,也就是陕西新时期文学发展的伊始,陕西跃上来了一批包括我在内的青年作家。这一批青年作家的创作发展势头很好,在全国都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陕西的老一代评论家,还有中青年一代的评论家,对这一批新跃上来的青年作家的创作非常关注,常在一起共同研讨这一批青年作家的新作品,交流总结创作经验。我记得段国超老师是当时陕西中青年一代评论家中,最为活跃和最有实力的一个。在我还没有当专业作家之前,我在灞桥区做干部。有一次我下乡到渭河边上给农民落实土地责任制,分田到户,段国超老师在我下乡的公社里头找到我。当时他们的学校叫渭南师专,他让我跟同学们做文学交流,跟同学们谈创作,我印象很深,这是我和段国超老师接触时间最长的一次。后来,像这种跟同学做文学交流,跟同学们见面谈创作的事,他还请过我多次,具体有多少次我记不清了。还有,我们还多次在西安开会,有一次还同住在一个房子里。当时省文联、省作协、省委宣传部经常组织各种会议,作家、评论家常在一起交流,学习党在新时期的方针、政策,研究问题,讨论创作。我听过段国超老师的会议发言,也看过段国超老师发在报刊上的文章,都是关于文学创作的。他当时很活跃,很有名气。
段国超老师对文学的关注,对青年作家的关注,我印象很深刻。他是一个非常严谨、热情的文学评论家。但后来段老师参加陕西文学界、评论界的活动越来越少了。后来除了几次他请我到他们学校,和同学们见面谈创作外,我很少见到他了。我曾问过朋友,打听段老师为什么现在很少见了?朋友说,段老师现在搞鲁迅研究了,我听后心里还多少有点遗憾。因为这样一个很有文学理论修养的老师,一个已经较有影响的中年文学评论家,离开了我们陕西当代文学评论界,离开了我们陕西当代文学研究,就我们这些搞创作的人来说,不能不是个遗憾。我确确实实感到有些遗憾!但是我也很清楚,段老师能投身到鲁迅先生的研究,而且主要偏重于鲁迅先生的家世研究、生平研究,如果做出了成绩,也是贡献!
陈忠实上面这些话,不仅说清了我和他交往的过程,我和他的友谊,也说清了我从积极热情搞文学评论到疏于搞文学评论而转向搞鲁迅研究的事实。具体原因他未说,那也许是因为我从未跟他谈过,他不了解这里的原因吧!
五
再往后来,也即进入21世纪之后,我虽说淡出了文学评论的大部队,这类一般文论、文评文章,我还是写了些,如《一项文化工程》《门外楷书谈》《党家斌与鲁迅》《谈谈对清代剧作家李芳桂的发掘、整理、研究与传承》《漫谈蔡静波的散文》等,但更多的是给别人写序,至今前后共百余篇。2006年底,就有50多篇,我选出40多篇,连同几篇跋文一起,编集出版,书名为《序跋集》。这本序跋,长者万余字,短者数百言,除有几篇,文本作者未提出要求,只有随书本出版外,其他皆应文本作者要求,还交由《孔子研究》《汉字文化》《延河》《报刊之友》《小说评论》《唐都学刊》《渭南师范学院学报》《陕西日报》《渭南日报》《教师报》等十几种报刊发表。这些序文的内容较杂,除文艺外,还有少量涉及学术、教育。我写序,其文本作者我大部分都认识,我完全可以做到“知人论文”“人文互论”,有什么问题,坦诚相见,不必讳饰。文学批评家吴泰昌说,“序文是文学批评的一种方式”,我给别人的文学作品写序,决不丢开文本而东拉西扯,都是作为文学评论文章来写的。这是我的第二部文学批评文集,是序跋体的文学评论文集。由于年龄的关系,这本书出来后,我本来就决计不再给别人写序,即使是再好的朋友也不写。但这事总由不得自己,正如文学评论家李星《文章无新旧,相尚在风义》文中所说:“序跋文的写作,常常是一种不期而遇的写作,甚至是本不愿写而不得不写的写作。”这老李是老资格的写序专家,深有体会,说的是大实话。
文学批评是有其思想标准和艺术标准的。我是遵循这两个标准的,决不以“我”为标准,随意妄说。我看一部文学作品,首先看它的思想内容是否健康,它的思想倾向是否进步,是否给人民的民主权利和道德意愿提供正能量。是,即肯定;否,即批评。如在前面我提到的1979年我对某剧团在西安演出剧本《送肥记》的批评,1980年我对有人在全国禁唱红色民歌《东方红》的批评,1981年我对《长安》上的短篇小说《出于幽谷》的批评,1982年我对有人在文艺作品中宣扬“性解放”的批评,等等,都是例子,在这里我就无须再举例了。众所周知,文学艺术不仅要反映社会生活,更要高于社会生活,一定要在“高于”两字上狠下功夫。不讲究艺术,即使思想性再强的文学作品,也行之不远,有如雄鹰没有翅膀,怎么也不会飞起来;但是,如果不讲思想性,那就更要不得了,因为文学,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它要为人民服务,给人民以前进的力量。
读者也许已经发现,我的评论,我写的序对有些初学写作者,特别是青年作者,好话是说得比较多的,这主要是受了老作家杜鹏程一次谈话的影响。1988年底,渭南有一位诗人出诗集找老作家杜鹏程写序,杜身体欠佳,让他回渭南找我代笔。我看过散乱的书稿后,觉文字粗糙,缺少诗意,没有出版价值,不值得给这样的诗集写序。于是就携诗稿去西安见杜,说明来意。杜沉思了半会对我说:“你看这样好不好?这位是个业余写诗的作者,××人,我熟悉。他几十年坚持写诗也不容易,不妨多说些好话,多鼓励。如果你说的严了,他就觉得他不是写诗的料,就不写了,以后就没有这个诗人;你肯定一下他,鼓励一下,他就能坚持写下去,说不定以后还真能写好,真的是个诗人哩!对专业作家、专业诗人不妨严一些,你越严他越高兴,因为这有利于他创作水平的提高。不会因为你严了,好话说得少了,他就不再写了。我看写序,不妨把业余和专业的分开,看对象说话。你看咋样?”我看杜老说得很辩证,很合情理,也是出于一个文学批评工作者对作者的关心和爱护,我就回来照杜老所说,给这位诗人写了序言。这位诗人很高兴,以后越写越勤奋,水平也大有提高。这“看对象说话”,好话说多点,给别人以希望;把问题提出来,指点别人以提高的路径,以后成了我给一些写作时间不长的同志,特别是一些青年作者写序时的指导思想。
搞文学批评不容易。一方面,如鲁迅所说,“文艺必须有批评”,文学批评家在文艺园地要做“剪除恶草”“灌溉佳花”的工作,而这需要学问,如努力不够、学习不够,这文艺批评工作要做好,很难!再一方面,写文学批评文章,往往吃力不讨好,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时代。现在人出书很容易,但不看价值,只图名利。你说好话,他高兴;你不说好话就得罪了他。更令人不解的是,你并没有说他的作品不好,只因为你说了别人的作品好,你照样得罪了他。但文学批评家搞文学批评是有原则的,只能实事求是,“好处说好,坏处说坏”。怎么办?这文学评论家不仅写文章难,做人亦难!好在是,历史是公正的,时间是公正的,公道自在人心,我们也大可不必计较!
我这个已属耄耋之年的中国作家协会的老会员,一不写小说,二不写诗歌,三不写戏剧,之所以是中国作协老会员,就是因为我在教学之余还搞点文论、文评写作。这个中情况,上述文字,已述大概。如有不妥之处,请读者诸君,肯于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