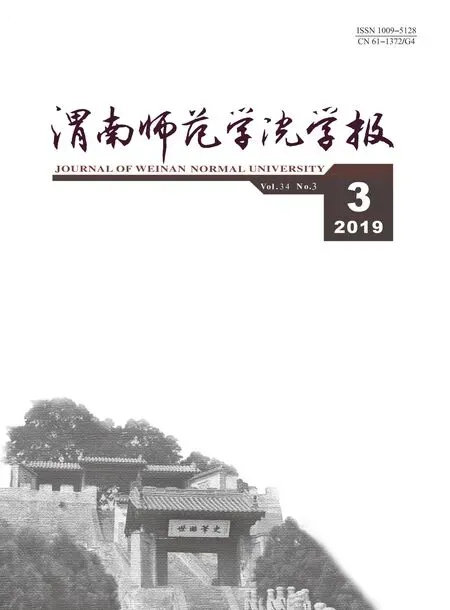羿与河伯故事中英雄形象的建构与偏离
2019-12-27毕漾晴
毕 漾 晴
(北京语言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部,北京 100083)
一、问题的提出
神话是早期文明最初发展出的一种文化形态,是人类历史早期的一种文化整体形式,“是原始信仰加上原始生活的结果”[1]32。“羿”神话故事及其形象的出现,是先民反抗自然意识发展的结果之一,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先人的价值观念及其内在的文化建构。而“羿”形象的发展也反映了不同历史阶段民族精神、社会生活、价值观念的变迁。研究“羿”的双重形象,就是研究其形象分歧背后所隐含的自然、文化因素。
在主流神话故事中,羿首先是作为替先民消除灾害与猛兽的英雄出现的。羿射十日作为中国四大神话之一[2]85广为人知,其英雄形象作为主流贯穿古今。羿的英雄形象是流变多年的主流形象,是其双重形象中的主要方面。但在射十日,除猛兽的英雄事迹之外,另有些许零星的神话传说作为“补充材料”丰富了羿的形象。其中,羿与河伯的传说便在流传中被不断重述,“由较简朴到较复杂,由缺乏系统到逐步有系统,由神话性很浓到逐步净化成人性,由纯神话逐步变成历史故事”[3]5,其中所要表达的深层含义不断被覆盖、重建。羿从象征实力的二神争斗关系陷入了感情上的三角关系,这种转变很大程度地削弱了羿的正面形象,世俗人性在作为神的羿身上有了显现。而这种世俗化的倾向,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羿英雄属性的剥离。
吕微先生认为,神话研究的关键在于弄清“历史中的人们如何通过操纵一个古老的型式来表达新时代的、与古人迥异的意图,并据此攫取新的话语权力”[4]428。从这段神话最初出现到袁珂先生在《中国古代神话》中的梳理,期间神话的重述重建实在不可谓少。理解射日英雄在与河伯、宓妃的三角关系中英雄形象的建构与偏离、把握后世对此段传说及人物形象的重述与展衍以梳理羿与后羿的联系,将是本文的研究重点。
二、射日英雄与河神的直接矛盾
(一)羿与河伯、宓妃故事
《山海经》被认为是现存最早、保存上古神话资料最多、最完整的著作。羿在《山海经》中共出现四次。《海外南经》:“羿与凿齿战于寿华之野,羿射杀之。在昆仑墟东。羿持弓矢,凿齿持盾,一曰戈。”[5]241《海内西经》:“海内昆仑之虚……方八百里,高万仞……在八隅之岩,赤水之际,非仁羿莫能上冈之岩。”[5]344-345《大荒南经》:“大荒之中,有山名曰融天,海水南入焉。有人曰凿齿,羿杀之。”[5]428-429《海内经》:“帝俊赐羿彤弓素矰,以扶下国,羿是始去恤下地之百艰。”[5]530可见,在原始神话中,羿抚恤民间百艰,为百姓的守护神。但羿同时又因为射伤天帝的九个儿子而被留在人间,革除神籍,与妻子嫦娥日日争吵。宓妃“肩若削成,腰如约素。延颈秀项,皓质呈露。芳泽无加,铅华弗御。云髻峨峨,修眉联娟。丹唇外朗,皓齿内鲜。明眸善睐,靥辅承权”[6]402-403,美貌倾城,丈夫河伯却日日“与女游兮九河”[7]75,丢下妻子不管不顾。伤心的宓妃与羿相遇,互相吸引。河伯知道了二人的暧昧关系,内心愤恨。《楚辞·天问》中记载羿“射夫河伯,而妻彼雒嫔”[7]97。汉代王逸注曰:“河伯化为白龙,游于水旁,羿见射之,眇其左目。河伯上诉天帝曰:‘为我杀羿。’天帝曰:‘尔何故得见射?’河伯曰:‘我时化为白龙出游。’天帝曰:‘使汝深守神灵,羿何从得犯?汝今为虫兽,当为之所射,因其宜也,羿何罪欤?’……羿又梦与洛水神宓妃交接也。”[7]97从战国至汉代,羿与河伯、宓妃的故事未有大的变动,可见三人的故事在战国时期已大致定型:羿与河伯因为宓妃而大动干戈。
但这个故事并非神话的原始面貌,其内在含义被“不同的力量出于不同的目的、需要和旨趣”[8]24,不断加以重建,成为具有新的深层含义的神话传说。羿与河伯的故事大约于汉代逐渐停止了演变,其后文人似乎更为关心与宓妃产生恋情的羿,而非与河伯争斗的羿。那么最初的神话中,是羿与河伯的关系更为密切,还是羿与宓妃的关系更为直接?这将是本章讨论的重点。
(二)羿与河伯的直接矛盾
《山海经·海内北经》郭璞注:“冰夷,冯夷也,《淮南》云,冯夷得道,以潜大川,即河伯也。”[5]369《楚辞·九歌》注引《抱朴子·释鬼篇》:“冯夷以八月上庚日渡河溺死,天帝署为河伯。”[7]77由此大致可知,河伯名为冰夷、冯夷,原为世俗之人,后因服药修道或某些意外而成为“河伯”,也就是水神。屈原《九歌·河伯》详细地描述了河伯的生活:
与女游兮九河,冲风起兮横波,乘水车兮荷盖,驾两龙兮骖螭。……鱼鳞屋兮龙堂,紫贝阙兮珠宫。……乘白鼋兮逐文鱼,与女游兮河之渚,流澌纷兮将来下。[7]75-76
屈原的想象虽多夸张,但亦有其根据。据这段文字,大致可推知河伯居于水中,生活环境也较为奢靡。虽然屈原对河伯有相对积极的描述,但是大部分中国神话、历史故事中的河伯都是贪恋美色,风流成性的。《水经注·独漳水》记载战国之世,魏国邺这个地方就有每年为河伯娶妇的风俗,后来因西门豹的强硬行为吓退了河伯,地方上才停止了这种风俗。在卜辞中就已有“河妾”一词,可推想在那时便有了河伯纳妾的故事,并成为春秋战国之时为河伯娶妾恶俗的由来。《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及《博物志异文录》中还记载着河伯因觊觎孔子弟子子羽价值千金的白璧,派人在其渡河时掀起滔天巨浪,最后却被羞辱一事。
河伯虽为水神,却在人世兴风作浪,带来灾祸。神话的基本主旨是人的社会生活的投影。从这一角度看,河伯的贪婪好色应是民间频遭河水侵袭现象的投影。人类依水而居,靠水而生,但也被河水夺取了无数生命,甚至连河神自身也被部分人认为是渡河溺死的。河流的泛滥带走了无数的生命,也吞噬了人类的财富与丰收。基于这种负面影响,河神被打上了贪婪暴戾的标签。
《山海经·海内经》记载:“帝俊赐羿彤弓素矰,以扶下国,羿是始去恤下地之百艰。”[5]530羿善射,帝俊赐以弓矢,命其帮扶人类。从这段文字看来,帝俊派羿来至下国并非只是为了射落十日、除去恶兽,而是“恤下地之百艰”,也就是负责清除人间的一切灾害。羿是射日英雄,又不仅仅是射日英雄。羿替天帝维护下地的安稳,在一定程度上成了民众的守护神。《淮南子·氾论训》写道:“羿除天下之害,而死为宗布。”[9]461高诱注“宗布”即“今人室中所祀之宗布是也”[9]461。《集解》引孙诒让云:“宗布,疑印《周礼党正》之祭禜,族师之祭酺。”[9]461“禜”祭与“酺”祭是古代攘除灾害的两种祭礼。羿因生前为民除害,所以也附带着成了这两种祭礼的祭祀对象,久而久之便成了家家户户供奉的诛邪除怪的宗布神。[10]213,215由此可见,河伯仗着自己的权力,在下地兴风作浪,实实在在地挑战羿作为守护神的权威。神羿承担着天帝交予他的任务,不可能对河伯的所作所为一次又一次熟视无睹。
《楚辞·天问》王逸注载有羿射河伯的故事。王逸《楚辞章句》注:
洛嫔、水神,谓宓妃也。传曰:河伯化为白龙,游于水旁,羿见射之,眇其左目。河伯上诉天帝曰:“为我杀羿。”天帝曰:“尔何故得见射?”河伯曰:“我时化为白龙出游。”天帝曰:“使汝深守神灵,羿何从得犯?汝今为虫兽,当为之所射,因其宜也,羿何罪欤?”深,一作保。羿又梦与洛水神宓妃交接也。[7]97
另洪兴祖注《天问》又云:“河伯溺杀人,羿射其左目。”[7]97《淮南子·氾论训》高诱注云:“河伯溺杀人,羿射其左目。”[9]461这些记载明确地显示,羿与河伯之间的确有过激烈的矛盾冲突,这三段叙述均提及了羿射河伯左目,在这一细节的叙述上详细、确定,因此大致可以认定三段文字讲述的应是同一个故事。王逸记载天帝对河伯颇有微词,替羿辩解;后两个版本提及河伯滥杀无辜,这些细节都表明羿射河伯并非是为私情。河伯代表着破坏的一方,羿代表着守护的一方,二者的冲突无法避免。由此可见,羿与河伯之间并不需要宓妃来作为联结点,二神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直接的。
三、英雄形象的建构与偏离
羿与河伯的故事被后世不断重述,在先秦之前,羿的英雄形象得到了强化;进入先秦时期后,羿的形象在神话重述的过程中逐渐开始偏离;直至战国时期,这个偏离的羿的形象从口头进入了文本,逐渐流传开来,产生了新的深层含义;而至汉代,学者则开始用社会伦理去解读、用笔墨去掩饰羿的“不齿行径”。羿的英雄形象在这段神话的不断重述中由建构走向了偏离。
(一)羿与河伯争斗中英雄形象的建构
《淮南子·本经训》记载:“逮至尧之时,十日并出……尧乃使羿……上射十日下杀猰貐。”[9]254-255羿作为射日英雄的形象一直深入人心,但是羿并不只是射日英雄。羿与河伯斗争的传说从另一个角度体现了羿的英雄能力及品性。
羿与河伯的斗争实际上是两方力量的较量,是二者的实力象征。二神相争的故事在中外神话中都能找到类似的例子,其主旨往往都是对胜利方实力的赞美与凸显。现代人类学家认为,史前人类的精神发展具有普遍的模式,由于人类所处的环境和基本生存需要的类似性,不同文化群体的成员在走向文明社会的进程中会表现出许多趋同的思想和行为。类似于羿与河伯这样二神象征的神话并不是少数。希腊神话英雄赫拉克里斯与河神争斗的神话故事便是这一类型的。
Grace H Kupfer的《希腊罗马神话故事》写道:
河神使出了他的魔法,变成了一条大蛇,从他的手里溜走了;……(赫拉克里斯)一把把大蛇抓住,正待要扭断它的头颈,大蛇又不见了,代替它的是一只凶恶的公牛;……他抓住了公牛的两只角……角被拉断了。[11]64
斯威布《希腊罗马的神话传说》则更加具体地描述了河神的三次变形:
阿刻罗俄斯河曾变为三种形象向她(得伊阿尼拉公主)求婚。最初变形为一只牡牛,其次变形为有着闪光的龙尾的龙,最后则是一个有着牛头的人形,在多毛的面颊上流着泉水。……(赫刺克勒斯)将大力气的河神摔在地上。他即刻变形为毒蛇。但赫刺克勒斯正是捉蛇的对手,假使不是阿刻罗俄斯又突然变为牡牛,他真的会将他打死。……他紧握着他的一只角,要他跪下,因用力过猛,这只角折断在他的手里。[12]183-184
赫拉克里斯与河神决斗的场面被细致地描绘了出来,这是故事叙述者试图增强神话故事可信度的手段,同样也是凸显赫拉克里斯的英勇与绝对实力的方式之一。不论是争斗河神的多重变形,还是掰断公牛牛角,都是为了服务于这段神话的主旨:赞美赫拉克里斯的英雄能力。
推及到羿与河伯的原始神话,虽然其中并没有详细的、对于斗争内容的描写,但是河神的凶残、变形都从侧面推动了神话里羿的英雄形象的建构。羿的善射、射中河伯左眼都是对英雄形象的正面建构。羿的胜利是自然的,为了守护民众而射伤河伯的羿带着神的品性。整个神话是社会理想的象征性表达,是上古时代人类心理活动的投影。而建立起一个高大的“守护英雄”形象以控制民众,其实是利用神话攫取话语权力的方式之一。上古人类在迷信的时代,极容易产生英雄崇拜。这种英雄崇拜对于民众的控制能力不容小觑,在渺小无力的人类面前总是需要有一个能撑起天地的存在,而这种存在就是由一个又一个英雄拼合而成的。羿英雄形象建构的意义和原因也因此得以解释。
(二)宓妃形象介入的意义:对英雄形象的强化
羿与河伯的神话传说在时间的推移中由简单变为较复杂,吸收了新的人物——宓妃。宓妃,据传是伏羲氏的女儿,溺死于洛水,又称雒嫔、洛神。在王逸记载的版本中,羿在梦中与洛水神宓妃相交,记于射河伯一事之后。王逸记载的叙事顺序则恰好隐晦地表明羿与宓妃的相遇是其战胜河伯后摘得的胜利果实,而非二者争斗的源头。羿与宓妃的恋爱关系是从与河伯的争斗关系中生发出来的,是后世对二神争斗故事的展衍。
宓妃并非二神矛盾冲突的核心,反而处于这段神话的边缘地带。作为胜者的附属战利品,宓妃甚至可以说是可有可无的。她的出现及惊世的美貌无非是为了强调英雄的两性魅力,从而体现其英雄能力。
纵观全球范围内上古时代的神话,旺盛的生殖能力和广泛的两性关系往往象征着英雄的超凡能力。[8]146因为只有拥有着超凡能力的神祇才能战胜敌方,征服并获得更多的女性。弗雷泽很早就发现了原始人类处死衰老帝王的风俗。他通过列举俄罗斯南部喀萨尔王国、乌干达境内布尼奥尔等例子来证明杀死衰老的帝王以解决部落的食物供应问题,是原始社会普遍的风俗。而在这些例子中旧王的妻妾都被新王所“享御”。这似乎透露出一个信息:旧王死后,妻妾归属于新王。
羿射伤河伯迎娶宓妃就是原始初民对“杀君主妻王妃”这一习俗的神话表述。河伯作为河神,掌管着河流,自然被视作是具有相当大权力的首领。从文献记载来看,他的妻妾也绝不会少。羿射伤河伯,对其权力掌控有着相当大的冲击。河伯作为河流的掌控者不能被完全消灭,为了弥补英雄形象的不足,强化羿的超凡能力,所以在战国之前的神话重述过程中加入了宓妃的形象。相比起那些被河伯掠夺作新妇的人间女子,宓妃美艳高贵,也更被原始初民所熟知,于是便成为河伯众多妻妾的代表,以一个附属战利品的身份进入了神话叙述中。
(三)三角关系下英雄形象偏离
自宓妃介入羿与河伯的争斗,经过战国时期至汉代这段时期的演变,宓妃的位置从边缘地移动到了核心,这也就表示羿是为了抢夺宓妃才与河伯相争。这样,羿射河伯为初民驱邪除害的神话性质就受到了污染,守护下国成了次要目的,夺取美人成了最终目标。这显然曲解了上古神话的原始含义。羿的神性被削弱,带上了一丝“人味儿”,英雄形象发生了偏离,英雄属性也被逐渐剥离。
进入文明时代后,严格的伦理标准日渐产生。羿与宓妃私下产生恋情在充斥着伦理道德标准的社会里为人所不齿。第一次出现类似批判倾向的文本是战国时期的《楚辞·天问》。屈原《天问》中写道:“帝降夷羿,革孽夏民。胡射夫河伯而妻彼雒嫔?”[7]97针对此叙述看来,屈原所处时代的伦理观念已然与上古神话观念不相适应了。神话中的主人公已不再是一名拥有超凡能力的守护英雄,而是一个品行低劣的强者。中国社会自周代以来,文明逐渐发展,封建立法和宗法制度逐渐完善;至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若想招募更多的人才、赢取民心,需诸侯王以德服人。文明发展之后,圣人趋于神圣,而其神圣性来源于其德而非其能。文化掌控者为了攫取新的话语权力,对许多上古神话中的英雄人物进行了改造,令其承担了创制文明的重任,带有美好的品性,使得世人对德行愈来愈重视。
在对“德”极度推崇的社会氛围下,羿与宓妃私通款曲,显然越出了“德”的范畴。羿射伤河伯一事文献叙述详细,无可辩驳;二者矛盾的源头却模糊不清,似直指宓妃。两相联系之下,羿陷入三角关系的低劣品行已板上钉钉。
汉代王逸在《楚辞章句》中注:“羿又梦与洛水神宓妃交接也。”[7]97此乃王逸对屈原《天问》中所写的“胡射夫河伯而妻彼雒嫔”的注释,但却与原句有着相当大的差异。屈原在记述时明确使用了“妻”字,即娶妻之意,强调了羿夺取宓妃的举动,非常明确,与王逸所说的梦中交接全然不同。王逸的注解试图淡化羿娶宓妃为妻这一事实,掩饰其不当行径。宓妃乃美貌惊人的女神,羿梦到美人也能理解,至少并未与她发生实际的关系,合于“发乎情止乎礼”的道德规范。王逸笔下的羿依旧保持着相对完美的英雄形象,但在他心里羿已然只是一位不德的强者了。可见,直至汉代,文本中的羿只能通过淡化、隐藏这些不合乎社会道德的行为来维护自己的形象。
羿在这段神话中逐渐被扭曲,神话所要投射的社会内容和其表述方式已经超出了阶段文明所能承受的范围。不论是改动神话以适应道德规范,还是强烈批判神话中的低劣行径,显然都偏离了羿的英雄形象,“用以表达新时代的、与古人迥异的意图,并据此攫取新的话语权力”[4]428。射河伯妻雒嫔的行为被后世曲解,是以文明社会的逻辑来解释上古神话而产生的结果。
四、射河伯之羿与后羿
中国古书上记载的“羿”有两个:一个射日杀怪,守护民间,称夷羿;一个却荒于田猎,行事令人不齿,是一个负面形象,也称后羿。于是,后世文人学者在善恶对立的基础上提出,英雄之羿与后羿并非为同一人。
但这种观点仍值得推敲。除了善射之外,后羿的事迹与羿射河伯的故事有大量的重叠,而后羿所做之事或许亦如羿一般因为社会文明的进步而被后人所误解了。
首先,羿(此节中皆指射伤河伯的羿)与后羿都射杀了一个贪婪的负面人物。羿射伤河伯,而后羿射杀封狶。虽《天问》及某些文本中对“封狶是射”持否定态度,但《左传·召公二十八年》载,伯封“实有豕心,贪惏无厌,忿类无期,名曰封豕(注:楚人谓封豕为封豨)”[13]1661。后羿射杀伯封并无过错,这一点并不能成为后羿残暴的证据。
其次,羿与后羿都曾“强娶人妇”。羿妻雒嫔不用再多加叙述。而后羿则是射杀封狶强娶了玄妻。《左传·召公二十八年》:“昔有仍氏生女,黰黑而甚美,名曰玄妻,乐正后夔取之,生伯封……”[13]1661《楚辞·天问》言:“浞娶纯狐,眩妻爰谋。”[7]98
顾颉刚、童书业《夏史三论》(见《古史辨第七册》下编)说:“这‘玄妻’(指《左传·召公二十八年》)当然就是《天问》的‘眩妻’,……‘纯狐’就是黑色的狐狸,也就是‘玄妻’。”[14]227“爰谋杀羿”即指玄妻与寒浞共谋杀羿。玄妻先后嫁给三位男性,也体现了强者夺取败者之妻(或其母)的习俗。后羿强娶玄妻之事与羿妻雒嫔实乃同一性质,虽然玄妻为伯封之母,但她与宓妃所代表的内核是一致的:原是败者的财产,后成为战利品归属于胜者。
此外,“后羿代夏”作为后人谴责后羿的主要事件,极有被误解的可能。《左传·襄公四年》:
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迁于穷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兽……寒浞,伯明氏之谗子弟也,伯明后寒弃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为己相。浞行媚于内而行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树之诈慝而取其国家,外内咸服。羿犹不悛,将归自田,家众杀而烹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诸,死于穷门,糜奔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浇及豷,恃其谗慝诈伪而不德于民……有穷由是遂亡。[13]1027-1029
翦伯赞的《中国史资料汇编》记述,夏朝太康在位之时,荒淫误国,民不堪其苦。仲康立为王,但能力较弱。在此情况下,羿遂废仲康,代理夏朝政事,史谓之“太康失政”。从此段记述可知,羿取代仲康治理夏政,实出于救国之好心,本为义举,无可指摘。在夏启之前,尧舜禹之时皆推举禅让制度,举贤者以治天下,而非实行后世的继承制。羿代理夏朝事务之时,距离禅让时代未久,古风犹存,不似后世封建社会,视密谋篡位、僭越为大逆,必为后人诟病。因此后羿代夏的初衷原本无过,后羿之过唯在于淫于田猎、所用非人。细读《左传》的载述,可以发现愚弄国民而不德于民的,其实是窃国的寒浞,并非后羿。后羿也是整个事件的受害者。[15]此中,后羿只能说是昏庸、识人不清,而不至于被贬低为品行低劣,成为众矢之的。
后羿的事迹并非如后世所记载的那么恶劣,那么在善恶对立的基础上认为羿与后羿并非一人的论点便失去了效力。更何况福祸相依,善恶好坏亦非绝对之事,该论证的前提基础便已然有了错误。茅盾在《中国神话研究ABC》中指出,中国古书上的羿只有一个,人性的羿就是历史化了的神性的羿。另外,还阐明《天问》中“革孽夏民”之“夏”,乃是华夏之“夏”,非夏朝之“夏”。“后世史家将这神话的羿来历史化,就成为尧之臣的羿,再变而为有穷后羿了。”[1]105-106
五、结语
在羿射河伯这段神话的流传过程中,羿的英雄形象逐渐被解构,成为一个行径低劣的小人。然而羿的射日英雄的形象实在太过深入人心,民众的英雄崇拜不会轻易消散,世人开始无法接受两段神话中羿的差距;至汉代,羿的形象完成分化,分别往两个方向发展。射日之羿仍旧光鲜亮丽,保持着英雄形象,死后则化作宗布神,继续为世人驱邪除害;而另一个羿则趋向另一极端,逐渐历史化,成了“后羿”。
羿形象发生分化,是神话流传产生的一种正常表现,但总有人拒绝接受羿善恶对立的两个形象。神话的原型是社会,神话的所有基本主旨都是人的社会的投影,自然学派和心理学则将神话看作是自然现象的隐喻化表达和人类深层心理结构的外在投射。社会与人类心理的复杂在神话上自然也有所投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