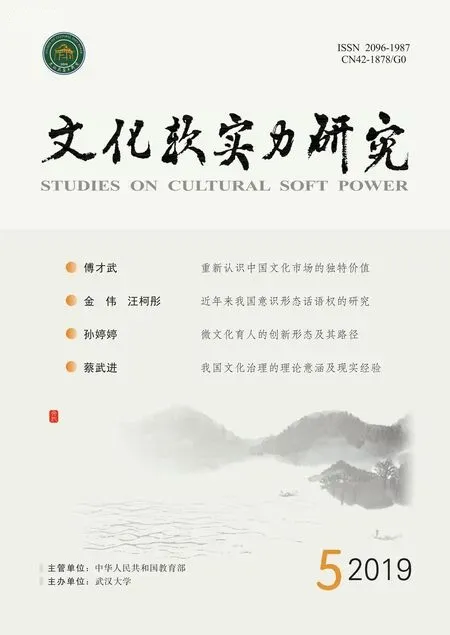春节文化的软实力价值及其发掘
2019-12-27王谦
王 谦
春节又称元日、正旦、元旦、新元等,是中国旧历的新年年节。春节产生于人们对于新年的庆祝活动,据考证,早在夏代以前,古人就有了“年”的时间概念,春节自然也就可以溯源于此(1)杨琳:《中国传统节日》,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版,第5页。。在数千年的流传演变中,春节成为中华民族最为盛大传统节日。它持续时间长,囊括的民俗活动多,受到海内外华人华侨的广泛认同。面对这笔文化遗产,如何在现代社会继承发展春节文化,并将其转化为国家的文化软实力,是一个需要深入探讨的命题。
一、春节文化的价值
传统节日背后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和文化精神,是特定历史条件下民众心态和生活愿望的写照,具有深厚的文化价值。春节文化的价值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
(一)春节文化揭示出中华民族的传统价值观念
春节中的民俗与仪礼传达出古人关于人与自然、人与家庭、人与祖先等关系的看法,从中颇能窥探出中华民族的价值理念。
1.天人和谐,顺天守时
在春节的祭祀礼俗中,有祈谷、迎春、鞭春等仪式。这些仪式往往与农事活动相关,旨在迎接新春,祈求丰收,其背后,体现出中国人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先秦时期,文献中常以“天”指代自然,而最为古人所重视的一大思想主题就是“天人合一”。天人合一的思想,认为人与天是紧密相关的一个整体,都是组成宇宙秩序的重要因素,这在《易·序卦传》中讲得十分清楚:“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
基于这样的认识,人要充分尊重自然的秩序,顺应其规律来从事各种活动。《易传》中多次申明这一点,它提出,人应“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观象于天”,“观法于地”;“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易·系辞下》),这些观念都旨在强调天人关系的紧密,追求天人关系的和谐。古代中国以农立国,追求天人和谐,落实在农业生产上,则格外重视顺天守时。《齐民要术·种谷》讲:“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农书·授时篇》讲:“各有其务,十二月各有其宜。先时而种,则失之太早而不生;后时而艺,则失之太晚而不成。”这种顺应天时的思想,在春节中以种种迎春仪式表达出来,其背后凝聚着中华民族对于自然的尊重和敬畏。
2.伦常至上,和睦团圆
儒家将不同的人际关系归纳为五种: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合称“五伦”。在和不同身份的人交往时,根据自身角色的不同,孟子将理想的伦常关系定义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在具体做法上,《礼记·礼运》篇提出要践行“人义”,即做到“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五伦的核心思想是追求人际关系的和睦,而家庭成员之间的和睦意义尤重,因为“齐家”乃是“治国”与“平天下”的基础。春节中的许多习俗都体现了对于伦常的重视。如长辈给晚辈发“压岁钱”,晚辈给尊长亲友拜年,丈夫陪妻子回娘家,都是借助春节走亲访友,通过一系列礼俗活动来明确自己的社会角色,营造和睦的家庭关系。
节日的意义,还在于为离家在外者提供了回归家庭的理由和时间。传统节日中,犹以中秋和春节最为强调团圆。春节更是因在外者纷纷还家而形成了“春运”这一我国特有的文化奇观,年俗中的吃年夜饭、守岁等活动也都强化着团圆这一主题。对于团圆的向往,看重的是家庭和伦常,这一点在春节中体现得十分明显。
3.礼尚往来,尊祖敬宗
中国自古就是礼仪之邦,礼是中国古代社会最主要的行为规范。孔子云:“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礼也是人际交往中必须具备的基本素养。《礼记·乐记》曾对礼乐之别进行区分:“乐也者,施也。礼也者,报也。”礼区别于乐的特点在于讲究回报,正是《礼记·曲礼》中所言:“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春节旧有“团拜”之礼,团拜分为不同的形式,有围成一团互相行拜礼的团拜,有聚在一起互相祝贺的团拜。无论是哪种形式,都体现了“礼尚往来”之意。用恭敬之心回报受到的礼遇,用行礼来传递自己在新春的欣喜之情,中华民族重礼的精神在春节礼俗中展示得淋漓尽致。
重礼精神还体现在对祖先的祭祀上。《礼记·乐记》认为礼的一项重要作用是“反其所自始”,即追念报答祖先,感谢他们赐予我们生命,为我们现在的生活打下基础。用祭祀的方式感念祖先之德,是春节的一项重要礼仪活动。民间多有春节祭祖的风俗,一般会在厅堂之内立祖先牌位,用以祭拜。春节的祭祖仪式昭示了中华民族尊祖敬宗,不忘先德的价值观念,这一观念不应归于迷信之流,即便是在当代社会依旧有其文化意义。
(二)春节展示出中国传统艺术的魅力
春节囊括了许多形式各不相同的民俗活动,这些民俗活动的开展往往离不开中国的传统艺术。就连春节本身,也成为文学艺术创作的一大文化主题。与春节相关的一些民俗和文学作品,充分展示出中国传统艺术的独特魅力。兹以春联、灯谜和诗歌为例加以说明。
1.春联
春联成型于唐代,宋以后逐渐流行。民间流行的春联多为传达新年气象、寄托生活期盼为主,如“东风吹出千山绿;春雨洒来万象新”“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而文人学士则往往借助春联创作,表达人生感悟、生活境遇以及时代风貌等内容。近代翻译家林纾在他逝世那年(1924)春节,曾写一联抒发自己的人生感慨:“遂心唯有看山好;涉世深知寡过难”(2)蒋竹荪等编著:《分类名联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年版,第553页。。1995年春节,广东京剧名旦新谷莺探望史学家陈寅恪,后陈先生亲书一联:“万竹竞鸣除旧岁;百花齐放听新莺”。“新莺”一语双关,既象征新的希望,又意指新谷莺,将自己的见闻感受巧妙地写入联中。1984年春节,《人民日报》刊登数学家苏步青所撰写的一副春联:“春满九州,大庆新逢卅五载;人迎四化,小康看定两千年”(3)两则春联相关信息,见陈书良:《楹联之美》,作家出版社2016年版,第128页。。联中“大庆”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小康”则为当时政府提出的,要在2000年使人民生活水平达到小康的目标。此联以时代精神言新年春意,极富特色。春联受到各阶层人民的喜爱和重视,还因为自其出现开始,这一艺术形式就与书法结缘,百年来无数名家留下了手迹墨宝。春联不仅寄托了中华民族对于新年的祈盼和愿望,还肩负着传承传统文学、书法的文化责任。书写张贴春联,继承的不只是一项节日民俗,更是传统文化中的艺术精华和审美情怀,这对于培养我们民族的文化认同感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2.灯谜
元宵节素有猜灯谜之俗。灯谜作为一种流行于民间的文学形式,具有雅俗共赏的文化内涵,自宋以来,就有不少知名的文人学士参与灯谜的创作。以晚清学者俞樾为例,其《春在堂全书》卷49《曲园杂纂·隐书》中,就收录了许多由其创作的灯谜。他曾以杜甫《绝句漫兴九首·其五》中“轻薄桃花逐水流”为谜面,猜一汉人之名(朱浮);又以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尾联“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为谜面,猜一春秋人之名(杜回)(4)邵滨军、赵首成著:《百年谜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第5页。。这两则谜题以诗文为谜面,又以历史人物为谜底,从中颇见俞樾的深厚学养。即便是民间流传的一些灯谜,也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有人以王维《桃源行》“两岸桃花夹古津”为谜面令人猜一诗歌流派(花间派);以《水浒传》中“金眼彪复夺快活林”为谜面令人猜一成语(恩将仇报)(5)赵首成、邵滨军编著:《新时期灯谜佳作集》,海天出版社1990年版,第2页、第9页。。灯谜艺术展现了中国语言文字的灵活和多变,反映出中国民众幽默风趣和含蓄深沉的性格。灯谜中许多谜面取材于历史文化典故,猜灯谜对于丰富民众知识,提高传统文化素养意义重大。
3.诗歌
春节的意义既在于辞旧,也在于迎新。处在这一特殊的时间节点上,千百年来,无数文人骚客言志抒怀,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关于春节的诗词佳作。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王安石的《元日》:“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王安石以一系列极富节日特征的民俗活动为线索,描摹出辞旧迎新之际春节的热闹和欢腾。这首诗也几乎成了古诗中春节的代名词。清人孔尚任《甲午元旦》一诗,则写出了人在暮年之时被春节唤起的童心:“萧疏白发不盈颠,守岁围炉竟废眠。剪烛催干消夜酒,倾囊分遍买春钱。听烧爆竹童心在,看换桃符老兴偏。鼓角梅花添一部,五更欢笑拜新年。”春节传达出的蓬勃朝气和昂扬的春意,令人“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也。董必武于1942年元旦写于延安的《元旦口占用柳亚子怀人韵》一诗,将革命家的豪迈融入春节的欢庆气氛:“共庆新年笑语哗,红岩士女赠梅花。举杯互敬屠苏酒,散席分尝胜利茶。只有精忠能报国,更无乐土可为家。陪都歌舞迎佳节,遥视延安景物华。”(6)以上三诗录自景俊美:《中国传统节日当代精神价值研究》附录二《节日诗词举例》,中国文联出版社2015年版,第177~179页。在日寇入侵国难当头之际,祖国的革命家将自己对于国家前途的乐观与信心,通过欢度春节的方式表达了出来。以上关于春节的诗作都足以说明,传统节日在文人的文化生命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展示出中国文人的审美修养和家国情怀。应该说,传统节日影响了一个民族的文化创作和文化表达,培育出中华民族的文化归属感。
(三)春节彰显出中华文化的包容性
东汉时期佛教西来,将印度的宗教文化传入我国。一些富有宗教意涵的宗教活动也被纳入到传统节日的庆典中来,成为我们今日习焉不察的民俗风景。春节中腊月初八吃腊八粥的习俗,就来自于佛教。腊八节兴起于宋代,并逐步取代了传统春节中的“腊日”这一节日。佛教为了传播教义,吸引信众,选择在“腊日”这一天开办佛事活动,借助节日气氛大兴浴佛会,积极融入汉族的春节庆祝活动。其中最大的创举,也是留给腊八节最大的遗产就是吃腊八粥之俗。
腊八粥最早出现在宋代,因在腊八这日施舍,所以又叫“腊八粥”。至清代,腊八节和腊八粥已经成为其时春节文化的一部分。吃腊八粥更是腊月初八这一天民众最为广泛参与的一项节庆活动。清代人李福写有《腊八粥》一诗,细致生动地描绘了腊八施粥的场面。首四句云:“腊月八日粥,传自梵王国。七宝美调和,五味香掺入。”可见,清代人很清楚腊八粥是印度佛教文化带来的“舶来品”,并非汉族人的传统风俗。这一风俗伴随着腊八节逐渐固定下来,即使年成歉收也依旧沿袭:“此风未汰除,歉岁尚沿袭。”对于荒年中的百姓来说,年节腊月里,一碗腊八粥映照出了生活的艰辛与凄苦:“吾家住城南,饥民两寺集。男女叫号喧,老少街衢塞。问尔泣何为?答之我无得。”饥民因无法吃到施舍的腊八粥而嚎啕大哭,固然辛酸,但同时也可以想见,对于分到粥的饥民来说,节日里的一碗腊八粥,无疑为生活带来了一份幸福和安慰。腊八粥在清代不仅受到下层百姓喜欢,也受到上层贵族钟爱。道光帝曾作《腊八粥》一诗,记腊八粥“谷粟为粥和豆煮”(7)以上两诗录自景俊美:《中国传统节日当代精神价值研究》附录二《节日诗词举例》,中国文联出版社2015年版,第204~205页。,证明腊八粥在清代已成为社会上下欢度腊八节必不可少的特色食物。腊八节以及极富特色的腊八粥,这一由佛教发展而来的节日民俗,在佛教组织的推动下积极融入中华民族传统节日,成为当代春节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其过程正体现了中华文化兼收并蓄的包容性。中华文化对于外来文化非但不排斥,而且能够在互相尊重的前提下,为其创造出本土化的发展空间。外来文化的加入丰富了传统节日的内容,为我们民族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历史记忆,更体现了中华文化博大的胸襟和开放的气度。
二、春节习俗与当代文化的冲突
传统节日是历史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其中所包含的许多文化意涵需要倚赖特定的民俗活动加以彰显。而随着时代的变迁,传统节日民俗与当代文化之间的冲突也越来越激烈,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民俗活动与现代价值理念的冲突
民俗活动与现代价值理念的冲突,在春节中展现得十分明显。以烟花爆竹为例,燃放烟花爆竹来庆祝春节的习俗源远流长。早在南朝时期,就有了爆竹的记录。到了南宋时期,又出现了火药爆竹和烟火(8)杨琳:《中国传统节日》,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版,第61~68页。。以烟花爆竹庆祝春节的民俗自此流传下来。至今日,燃放烟花爆竹所带来的安全隐患和环境污染,与当代文化所重视的生命财产安全、生态保护等观念无疑存在着矛盾,呼吁对其实施“禁放”的声音也层出不穷。
民国时期,政府就曾发布过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政令,但由于执法人员的放任与百姓的反对,终成一纸空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86年北京市人民政府颁布了《北京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暂行规定》,对烟花爆竹的生产、储存、运输、销售、燃放五个环节作出了限制和规定,主要目的在于维护公共安全。1992年、1993年,广州和北京两座城市先后出台了禁放烟花爆竹的政令,开了城市实施“禁放令”的先河。2015年,环境保护部发出《关于做好2015年春节期间烟花爆竹禁限放工作的函》,要求各地做好春节期间烟花爆竹禁限放工作。与此前不同的是,此文件对烟花爆竹采取限禁的主要原因是基于烟花爆竹产生的环境污染问题,而非强调公共安全问题。不管出自何种考虑,对烟花爆竹实施禁放政策,都体现出现代价值理念与传统民俗活动的冲突。针对这种冲突,对民俗活动简单地采取限制甚至取缔的手段,无疑没有考虑到其背后承载的文化价值。
烟花爆竹是春节到来最明显的民俗信号。“爆竹声中一岁除”,千百年来,正是噼啪噼啪的鞭炮声渐渐唤起我们对年节的期待,提醒我们进入到一个有别于日常时节的特殊阶段。一个值得思考的现象是,爆竹在传承中逐渐丧失了其宗教上的内涵:它最初被用以驱除鬼魅,民国时期,据《呼兰县志》记载,燃放爆竹又成为接神的宗教手段。到今天,放爆竹所代表的宗教意涵已被人们所淡忘,但是这项活动仍然受到人们的热衷和喜爱,其中的原因值得深思。节日需要有特殊的文化气氛,烟花爆竹能够制造出绚烂热闹的喜庆氛围,春节辞旧迎新的主题需要仰赖它来彰显,这才是这项简单的民俗活动能够经久不衰甚至屡禁不止的深层原因。如果利用行政力量进行禁限,最终无疑能够达到万籁俱寂、百里无声的效果,但告别了烟花爆竹,面对节日气氛的空缺,春节又该如何创造出喜庆欢快的文化氛围呢?从目前来看,这一问题依旧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答案。如何处理现代文化价值理念与传统民俗间的冲突,远比想象的要复杂。
(二)民俗信仰与科学观念的冲突
民主与科学是五四以来的两大思想主题。科学在中国思想界的主导地位于五四之后逐渐得到确立。胡适曾对于科学在近代中国取得的地位如此形容:“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它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9)胡适:《〈科学与人生观〉序》,收入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3》,《胡适文存二集》卷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52页。随着近百年来的发展,科学已然成为整个人类社会公认的基本思想法则之一。
如果我们以科学的眼光来打量传统节日,那么其中许多民俗信仰都应该被置于迷信之列。在春节的传统民俗中,充斥着各种祭祀活动。萧放曾把这些祭祀活动分为四大类:国家公祭、民间家祭、天地祭祀、祖先祭祀。其中每个类别下又有数种不同的祭祀对象,如民间家祭的对象就包括灶神、门神、喜神、穷鬼、财神等鬼神(10)萧放:《传统节日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学苑出版社2011年版,第69~84页。。显然,这些祭祀活动背后大多存在着对于各种鬼神的信仰,而这种信仰往往被定性为与科学相对立的迷信。以科学破除迷信,在社会上最大的表现,就是取缔这类民俗活动以达到移风易俗的作用。在这样的形势下,传统民俗中,很多被贴上“迷信”标签的信仰和活动,在社会改造面前自然岌岌可危。
民俗学家对于传统民俗的这种危机早已有所意识,因此他们着力在概念上将民俗与迷信划清界限。这其中,乌丙安对于两者的区分很具有代表性。乌先生认为俗信(即民俗信仰)区别于迷信的特征主要有三个方面:(1)是否强调神秘色彩;(2)是否获得社会群体的普遍认可;(3)是否对于社会人生具有积极的影响(11)乌丙安:《俗信——支配中国民俗生活的基本观念》,收入氏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论与方法》,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 年版,第218~ 220 页。。应该说,这种区分比较充分地论证了民俗在当代社会存在的合理性,正是基于这种合理性,一些民俗信仰和活动才没有被政府以强制手段取缔,得以继续传承。但另一方面,这一区分也有意淡化了民俗信仰和科学之间的矛盾。江绍原曾对于迷信这样定义:“一切和近代科学相冲突的意念、信念以及与它们并存的行止,我们皆呼为迷信。”(12)江绍原:《中国礼俗迷信》,渤海湾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4页。依此定义,即便是与迷信相区别的俗信,我们也不能否认它们中间存在着许多与科学相冲突的“信念”以及“行止”。以科学为参照系,俗信与迷信之间的区别似乎不甚明显,在科学的眼光下,俗信不过是一种有正当理由存在、有一定积极意义的迷信罢了。
当代青年是在科学观念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对于科学的笃信,已经成为他们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政府和社会对于民俗信仰采取了包容的态度,但新一代的青年们对于传统节日民俗不感兴趣,也是显而易见的。春节中的许多祭祀活动在青年人眼里是落后、迷信的象征,这与科学观念带给他们这代人的影响是直接相关的。传统节日对于年轻人失去吸引力,其中的一个重要背景,是近代以来科学对于迷信的全面胜利。如何消解民俗活动中的“迷信”意味,以新的内涵赢得青年人的认可,这在当前节日文化建设中是值得重视的。
(三)传统节日与全球化的冲突
自地理大发现以来,世界逐渐结为一个整体,国际化、全球化成为现代国家开放发展的普遍趋势。全球化带来的不仅是经济层面的外来资本,更有文化层面的西方潮流,在这一过程中,本土化的传统节日受到了全球化的挑战。这种挑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西方节日对传统节日的冲击,以及国际法则对传统节日的干预。
西方节日受到当代文化的追捧是不争的事实。当前社会流行的西方节日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表达人类普遍情感诉求的节日,如母亲节、感恩节、情人节,这类节日代表着人类对于亲情、爱情、恩情等价值观念的认同和强调,一般较少受到本土文化主义者的抵制与反感;另一种节日则是起源于西方宗教、历史和文化的节日,如圣诞节、愚人节、复活节,由于中国并没有相应的文化基础,也缺乏宗教上的认同感,许多本土文化主义者对这些节日的流行极其反感。然而无论是哪一类型的西方节日,对于传统节日的冲击都是十分明显的。这种冲击体现在,西方节日的流行,导致了传统节日的遇冷,西方节日取代了传统节日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角色。但“恶紫之夺朱”不能成为我们否定西方节日的理由。传统节日在当代社会的式微主要在于社会形态的变迁。传统节日中许多习俗适应的是农业社会的需要,比如春节中的“祭灶神”,目的就是祈求食物丰足,这一信仰背后反映出传统社会物质匮乏的现实。但在工业社会,对于基本物质资料的需要已经可以得到满足,这种信仰失去了现实基础,自然容易被人淡忘。而顺应全球化趋势传入的西方节日则适应了工业社会的需求,引导人们通过购物消费、游玩享乐等方式来释放生活的压力,获得精神的愉悦。
除此之外,西方节日的涌入使得人们有更多节庆日可供选择,客观来说,这会造成民众对传统节日的心理期待有所下降。但民众对于西方节日的青眼有加与近代以来中国的历史演变也有很大关系。鸦片战争后,与中国的愚昧贫弱相对比,西方民主国家文明强盛的形象深入人心,当西方文化被塑造为先进、时尚的代名词,传统节日受到冷落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因此,传统节日在与西方节日的文化冲突中节节败退,这一事实背后既是社会形态发展的选择,也与近代以来,西方在民众文化心理上的强势有关。
全球化对中国的影响还体现在,为了与国际接轨,中国政府有意以西方的社会法则和生活方式改造中国。这些改造措施亦波及传统节日。辛亥革命胜利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宣布改用西历,将西历一月一日定为“元旦”节,而农历新年则改称为“春节”。同时,政府还禁止传统农历的节庆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亦采用西历纪年,并在规定的“法定节假日”中确立了“春节”作为传统节日的合法性。但使用国际通用的公元纪年,导致了元旦从春节中分出,成为应公历而生的一个新节日,这一节日又因社会对于公历的逐渐习惯,转而取代了旧有春节“辞旧迎新”的内涵。“春节”更像是单纯对于新春的庆祝,而标志着新旧年份交替的意义已经被元旦夺走。全球化的代价,是人为地导致了春节重要意涵的缺失,这是令人感到遗憾的。但必须承认的是,全球化进程无法逆转,只有为传统节日注入新的生机,才能发挥出它在文化软实力建设上的潜力。
三、为传统春节文化注入新的文化活力
传统节日民俗与当代文化之间的冲突提醒我们,在当代社会继承发展传统节日,需要对其中的文化理念进行改造和更新,使其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为传统节日注入新的文化内涵关键要做到以下两点:
(一)保护传统节日遗产
为传统节日注入新的文化内涵,首先要对传统的节日遗产进行继承和保护,保留春节文化的地域多样性和民族多样性。
1.保护春节文化的地域多样性
“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我国地域广袤,不同区域的人民具有不同性格,不同地域的文化具有不同的特色。古人对这一问题早有认识。成篇于战国中期的《礼记·王制》(13)关于《王制》的成篇时间问题,参考王锷:《礼记成书考》,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88页。就提出“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的深刻见解,至《汉书·地理志》,则更是对每个不同地域的民俗有一番精练的概括:周地之民“巧伪趋利,贵财贱义”;宋地“其民犹有先王遗风,重厚多君子”;楚地之民“信巫鬼,重淫祀”。中国地域文化的多样性同样体现在节日习俗中,娄子匡《新年风俗志》对于各地新年风俗多有搜罗,其中有些极具地域特色,如苏州春节有拜喜神、送“飞帖”、看风云、烧“欢喜团”、饮春酒、接路头、食春饼、迎紫姑等风俗;广州有迎财神、放鲤鱼、逛花地、打春、开灯、完灯、请等之俗;海南有献槟榔、装军、做年、游灯、打秋千之俗。在各地风俗愈发同质化的今天,保护文化习俗的地域多样性,对于丰富春节的文化内涵,格外具有现实意义。
2.保护春节文化的民族多样性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少数民族不少也有过春节的习俗,这些独特的民族文化,展示出与汉族不同的节日风情。蒙古族春节分为“过小年”与“过大年”,农历腊月二十三过小年,有祭火祭灶之俗,又称为“祭锅撑子”。腊月三十开始“过大年”,有祭祖、供佛、做手扒肉、唱民歌等风俗。藏族依藏历过新年,年节要制作青稞酒、“喀赛”“切玛”等食物,团圆饭为一种特殊的粥,称为“古突”;还有用面粉撒上“八吉祥图”,在大门画吉祥符号“卐”等年俗。彝族亦有过“彝年”之俗,其特点是不同村寨过“彝年”的日期不同,由秋收后择吉而定。节期为三天,第一天称“库施”,有燃火升烟之仪,意在祈求丰年;又要制作“尔察苏”挂在祖先神位上方来祭祖,另有以猪肉祭祀祖先的仪式,称作“松母”。第二日称“多博”,进行赛马、角力等娱乐活动,还要走访亲友庆贺新年。第三日称“阿甫博基”,有送祖先、祈平安的仪式(14)参考毛公宁主编:《中国少数民族风俗志》,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第25~26页,108页,254~255页。。各民族的春节习俗有其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表现着不同民族的生活方式和民俗信仰,然而其生存处境却令人堪忧。随着社会的发展变迁,不少习俗逐渐消亡,对其进行抢救性保护迫在眉睫。
(二)推动传统节日走向现代化
为传统节日注入新的文化内涵,还要推动传统节日的现代化,改造传统节日风俗,创造节日新风俗。
1.引导节日风俗适应当代社会文化
正如前文所指出的,春节里许多民俗活动,如贴年画春联、放爆竹、祭灶神等,其背后存在着鬼神信仰。这种信仰在当代社会没有取信基础,如何重新诠释其内涵,成为继承传统民俗、服务现代社会亟待解决的问题。淡化信仰,突出文化意义或许是值得尝试的处理办法。面对春联年画,侧重背后的书法绘画艺术传统;面对烟花爆竹,强调使其产生的科技史背景,以此展现以“四大发明”为代表古代科技成就;面对祭灶神等民俗活动,着重阐释祭祀活动寄托的,古人对于健康、丰收、平安等愿望的追求,对于自然和祖先的敬重,以此来号召现代社会重视天人和谐,感恩铭记祖先。总之,以要文化意义消解鬼神信仰,强调其中蕴含的当代价值。另外,引导节日风俗适应当代社会文化,还要肯定以现代方式改造节日民俗的积极意义。信息技术的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社交方式,以往春节中的拜年、祝福、发压岁钱等习俗,大有被电子贺卡、短信祝福、电子红包等取代的趋势。这种变化适应了当代社会的生活习惯和交际方式,用科技平台传达节日的祝福,具有更为快捷高效的优点,这是值得我们肯定的。
2.利用新载体创造新的节日风俗
当代社会出现许多新的文化载体,利用新载体创造新的节日风俗,是为传统节日注入新的文化内涵的重要手段。媒体是春节文化新载体的代表,在由其形成的新的节日风俗中,“春节联欢晚会”和“贺岁片”最引人注目。看春晚是当今过除夕不可或缺的一项文化活动。春晚以各类文艺节目为主体,将相声、戏曲、武术等传统曲艺形式,与当代流行的魔术、歌舞等新兴文艺形式荟萃一堂,并注重渲染春节的欢庆氛围。因此,自1983年春晚开办以来,观看春晚就逐渐成为民众喜爱的春节新风俗。贺岁片则是随着电影产业发展,诞生的一类为庆贺新年而拍摄上映的影片。这类影片往往以喜剧居多,重在使观众通过观看影片获得轻松愉悦的心情。贺岁片的文化主题与春节的喜庆气氛相表里,观看贺岁片,也成为人们在春节中乐于参与的一项文化活动。然而,新载体所创造的文化风俗,其功能并不仅仅在于为民众提供更多的娱乐方式,更在于它们是承载传统文化和当代文化的重要平台,对于传播当代价值观念、培育民族精神、增强文化自信具有不可小觑的作用。
(三)加强春节文化的海外传播
全球化将西方节日引入了中国,同样也将中国的传统节日推向了世界。面对这样的时代机遇,在海外传播春节文化,对于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具有特殊意义。这一意义可以两个不同主体为着眼点加以认识:
1.海外华人华侨
在世界范围内,海外华人华侨已成为一个数量庞大的移民群体。对于海外华人华侨来说,传承春节民俗具有特殊的文化意义,它集中显示了海外华人华侨对于中华文化的认同。这种认同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现实意义。
在海外华人群体的形成过程中,常常受到移民国的排挤与打压,各国不同形式的“排华”运动及政策,揭示了海外华人遭受的不公待遇,反映出其处境的艰难(15)相关史实参考沈已尧:《海外排华百年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王九龙:《战后东南亚排华探究——以马来西亚、印尼为案例的分析》,暨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6年。。在这种历史境遇下,华人华侨对于春节等传统节日民俗的传承,除了庆祝节庆之外,更具有凝聚团结华人群体,增进历史文化认同等深刻意义。对传统节日活动的继承,使得海外华人能够在异国他乡创造出故土的文化氛围,通过文化活动汲取文化精神,以中华文化强调的“自强弘毅”“开拓进取”等观念自勉,以此来应对严峻的外部形势。随着华人华侨的抗争以及中国的和平崛起,海外华人华侨在他国的地位、处境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具有歧视性质的法案被逐渐废除,海外各国对于华人在国家建设中的贡献也予以承认。在新的历史环境下,以传承春节民俗等方式所传达出的文化认同,更多地显示出民族自豪感以及文化自信。此种心态更有利于与外国文化展开平等、和谐的交流,是中华文化融入世界,得到外国认同和接受的前提。
华人华侨对于国家的经济文化建设功不可没。庄国土曾指出:“华侨华人不仅是中国最重要的海外资源,更是中华民族复兴的主动力之一。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事业发展一直建立在充分利用华侨华人资源上。海外同胞提供中国大陆现代化建设最急需的资金、现代化企业和国际营销网络。华人华侨与大陆的合作不但推动了社会经济硬实力飞速发展,而且对本土软实力的发展也做出了重大贡献。”(16)庄国土等:《海外华人华侨是中华民族复兴的主动力之一》,《中国海洋报》2011年6月10日。因此,依托华人华侨群体,发展以春节为代表的传统节日,对于加强华夏儿女对于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增强海外华人华侨和祖国的血脉联系具有重大意义。
2.海外国家及民众
如上所论,中国的国际影响力的提升,海外华人群体的增多及其经济、文化地位的改善,使得海外国家和民众能够以更为平等的态度对待华人群体,以更为尊重的态度对待中华文化。农历春节作为华人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也越来越多地受到外国社会的接受和认可,其表现有三点:
(1)农历春节被许多国家和地区确立为法定节假日。2002年,印度尼西亚将春节列为其国家节日之一;2005年,菲律宾也将农历初一定为全国节假日;美国纽约州于2004年将春节立为本州的法定节日;2008年,美国马里兰州也将农历新年定为“亚裔农历新年日”。
(2)各国政府对春节民俗活动的鼓励与支持。2004年法国巴黎为庆祝春节,以“中国红”装饰埃菲尔铁塔,巴黎市政府批准华人可在香榭丽舍大街举行春节游行活动;2005年,罗马尼亚总统在春节期间向中国人民发表节日祝福,并前往中国驻罗大使馆与中国居民欢度春节;2007年,联合国举办“和谐之声”新春文艺晚会庆祝中国农历新年。
(3)外国普通民众对春节民俗的广泛参与。2002年,马来西亚在霹雳州首府怡保市举行春节庆祝活动,其中所表演的民族舞蹈,就由华族、马来族和印度族三大族群的人员组成;2007年,美国旧金山举行元宵节游行活动,在100多个游行方队中,很多方队由当地民族及其他族裔组成;2007年春节,在荷兰海牙市政厅广场举行的舞龙活动中,出现了由当地人组成的一支舞龙队(17)以上相关民俗史实参考沈立新:《海外华人民俗文化研究》,《八桂侨刊》2008年第1期;阮静:《中国春节在海外传播的影响及策略分析》,《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
以上事实,体现了春节民俗正逐渐受到外国政府和人民的认同,这一过程对于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具有启发意义。首先,中华文化与世界文化的沟通交流,其前提是双方人民必须彼此尊重对方的民族和文化传统,任何偏见和歧视只会引发文化间的冲突,造成社会的动荡和矛盾。其次,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其实质是中华文化与各国文化间的吸收交融。海外诸国的春节民俗活动,绝不是中国春节民俗活动的简单移植,而是在其中加入了很多外国的文化元素。这些文化元素的存在,使得当地民众创造出属于他们的、独特的春节活动。正因如此,海外民众才乐于参与到春节文化中来,这也为春节文化的内容点缀了独特的民族风情。最后,华人华侨带来的春节,转而成为海外诸国的新民俗,这不但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成功典范,对于海外各国也具有突出的现实作用。春节能够团结各国华人与其他民族,促进当地的社会和谐;春节融入当地文化,有利于各国塑造多元的文化气质与格局,更有利于深化外国对于中国历史文化的认识,为中外合作奠定相互尊重理解的基础。
加强春节文化的海外传播,是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中的一项重要课题。春节文化能够展现当代中国的发展成就以及当代中国人的精神风貌,对于民族文化的弘扬和国家形象的塑造具有重要作用。总之,让世界认识一个新的中国,离不开春节文化在海外的传播。
中宣部《关于运用传统节日弘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的意见》指出:“中国传统节日,凝结着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情感,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和思想精华,是维系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的重要精神纽带,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宝贵资源。”(18)转引自王文章:《弘扬传统节日文化现状与对策——中国传统节日文化调研实录》,文化艺术出版社2012年版,第35~36页。传统节日与文化软实力建设息息相关,在当代社会传承发展节日文化,是我们每个中国人的责任与义务,因为它关乎着中国文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